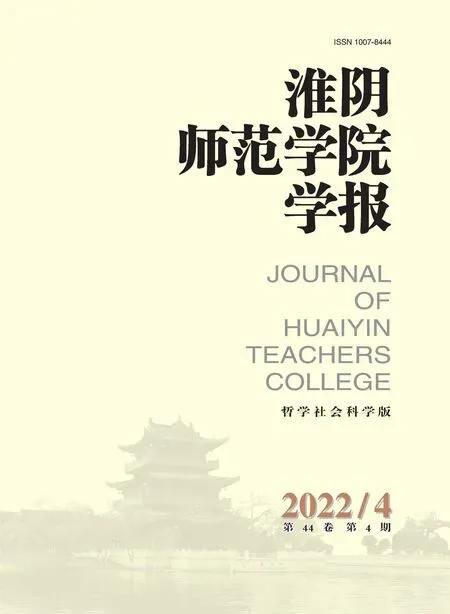出土史料与唐修《晋书》相关问题再考察
张 峰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王国维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傅斯年亦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2]回眸百余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新史料的发现、推动关系密切。就唐史研究领域而言,发现于20世纪初期的敦煌文献,早已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随着国内基础建设的开展与考古发掘的深入推进,大量有关唐代的石刻史料出土。这部分史料为唐代历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契机。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中国史学史之研究,尤其是对中古时期史学的探讨,应将着眼点从原来聚焦传世文献扩大到出土墓志史料,注重“墓志中的史家”与“史家所撰墓志”两个层面的问题,进而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古时期史学发展的脉络。
本文初步运用近年来出土的《薛元超墓志》《辛玄驭墓志》与《卢承基墓志》,对唐修《晋书》的起始时间、不同文献关于《晋书》撰人的歧义、《新唐书》对于《晋书》撰人的误判等问题加以讨论,冀图从微观层面说明出土墓志对于唐代史学研究的意义。
一、《薛元超墓志》与唐修《晋书》的起始时间
《晋书》是唐初继“五代史”之后编纂的第六部前朝纪传体断代史书。关于《晋书》编纂的起始时间,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晋书》的编纂始于贞观十八年(644)。这缘于《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记载令狐德棻于“(贞观)十八年,起为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寻有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3]2598。与之相呼应的是,此次担任《晋书》监修的房玄龄本传文载:“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京城留守,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军戎器械,战士粮廩,并委令处分发遣。玄龄屡上言敌不可轻,尤宜诫慎。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3]2462-2463考之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所载,此次太宗征伐时间为贞观十八年十一月,故而《旧唐书·房玄龄传》亦载《晋书》纂修的时间始于贞观十八年。
二是认为《晋书》编纂的起始时间为贞观二十年(646)。《唐会要》记载唐初纂修前朝史时说:“(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4]1091同样,宋人编纂的《唐大诏令集》记载唐太宗颁布《修〈晋书〉诏》的时间为“贞观二十年闰三月”[5]467(1)《唐大诏令集》记载《修〈晋书〉诏》颁布的时间为贞观二十年闰二月,根据余嘉锡考证,此处的“闰二月”应为“闰三月”。参见氏著《四库提要辨证》卷三《晋书一百三十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赵俊将诏书内容与唐太宗东征高丽的史事相互关联,认为《晋书》之编纂始于贞观二十年闰三月。他指出:
尤其值得注意诏书开头“朕拯溺师旋……”一段。关于唐太宗亲征事,两《唐书》都记载较详。《新唐书》卷二《太宗纪》载: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唐太宗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世勣、马周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六总管兵以伐高丽……十九年二月庚戌,(太宗)如洛阳宫,以伐高丽……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大飨军……六月……己未,大败高丽于安市城东南山……九月癸未,班师。……二十年……三月己巳,至自高丽。”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只有这一次亲征,回到京城时间是贞观二十年三月。《修〈晋书〉诏》所署时间则是贞观二十年闰三月。这个事实正与诏书中“朕拯溺师旋”一段话相吻合。如果说贞观十八年诏修《晋书》,就说不通。[6]
自赵文出,学术界基本认可《晋书》编纂始于贞观二十年。
然而,1972年出土的《大唐故中书令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薛公墓志铭》(以下简称《薛元超墓志》)为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薛元超是唐修《晋书》编纂者之一,新、旧《唐书》与《唐会要》《册府元龟》均谈及薛元超以太子舍人身份参与《晋书》编纂,但是却未言及薛氏参与《晋书》编纂的时间。于此,《墓志》记载:“廿一除太子通事舍人,仍为学士,修晋史。”也就是说,薛元超是21岁时以太子通事舍人的身份参与《晋书》编纂的。又据《墓志》所载,薛元超“以光宅元年十一月二日薨于洛阳之丰财里,春秋六十有二”[7]147,151(2)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所收《薛元超墓志》载其卒年为“光宅元年十二月二日”(第280页),并标明志文录自1986年黄山书社出版的《乾陵稽古》。然《乾陵稽古》所载薛元超之卒年为“光宅元年十一月二日”(第97页)。又,据在乾陵博物馆工作的樊英峰所见,墓志所载薛元超卒年为“光宅元年十一月二日”(参见《唐薛元超墓志考述》,《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乾陵稽古》及《唐薛元超墓志考述》的记载,与最早刊布《薛元超墓志》的《乾县文物志》记载时间一致,遂本文所引《薛元超墓志》,以最早刊发此文的《乾县文物志》为准。。由此可知,薛氏生于唐高祖武德六年(623),21岁时正值贞观十七年(643)。这个年份比上文提到的《晋书》编纂始于贞观十八年、二十年都要早。《薛元超墓志》出自同时代人薛融之手,内容较之新、旧《唐书·薛元超传》都更为翔实、可靠[8]。因此,《墓志》提及薛元超于贞观十七年即开始参与《晋书》编纂应是可信的。这意味着,在《晋书》编纂始于贞观十八年、贞观二十年两种观点之外,尚有始于贞观十八年之前的可能。
根据《旧唐书》对当时参与《晋书》编纂之李淳风史事的记载,可以看出《晋书》之编纂在贞观十五年(641)便已开始:“(贞观)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寻转太史丞,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3]2718同样,参与《晋书》编纂的李延寿,在其自撰的《北史·序传》中也提及了贞观十五年的这次《晋书》纂修:“十五年,任东宫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阳公令狐德棻又启延寿修《晋书》,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9]3343这条史料提及贞观十五年李延寿因令狐德棻提携,得以预修《晋书》,而此时令狐德棻官“右庶子”,这与《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说他“(贞观)十五年,转太子右庶子”[3]2598的记载正相吻合。
如果说,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唐太宗下《修〈晋书〉诏》,标志着《晋书》编纂正式开始的话,那么何以《薛元超墓志》《旧唐书·李淳风传》以及李延寿《北史·序传》都不约而同地提及这些当时参与《晋书》编纂的撰人在贞观二十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参与《晋书》的纂修了呢?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贞观二十年《修〈晋书〉诏》颁布之前,《晋书》的重修工作已被提上日程。从李延寿的自述中可知这次重修工作的主事者为令狐德棻,但因此时令狐氏为太子右庶子,受到太子承乾逼宫谋反被废的影响,“随例除名”;贞观十八年,“起为雅州刺史,以公事免”[3]2598。这致使《晋书》之纂群龙无首。加之,此年太宗要亲征高丽,无暇顾及修史,遂致搁浅,至贞观二十年太宗东征归来,《晋书》的编纂才重新启动。
综上,《晋书》的编纂应在贞观二十年之前即已开始,但因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收效甚微;直至贞观二十年唐太宗下《修〈晋书〉诏》,才组建了一个庞大的修史群体,接续了之前的编纂工作,并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晋书》的编纂。
二、《辛玄驭墓志》与《旧唐书》记载《晋书》撰人的遗漏
比对《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和《新唐书》四份文献对于《晋书》撰人的记载,我们发现《唐会要》载有“辛邱驭”,《册府元龟》载有“辛玄驭”,《新唐书》载有“辛丘驭”,而此辛姓撰人却不见于《旧唐书》。那么,此人到底是“辛邱驭”“辛玄驭”还是“辛丘驭”?为何《唐会要》《册府元龟》和《新唐书》均提及此人参与《晋书》修撰,而《旧唐书》却未提及?对此,新出土的《大唐故刑部郎中定州司马辛君墓志铭》(以下简称《辛玄驭墓志》)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突破口。
《辛玄驭墓志》铭文提及,此人实名辛骥,字玄驭,以字行,曾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参与《晋书》编纂,“(贞观)廿二年敕授屯田员外。太宗躬刊晋史,傍招笔削,遂复声华延阁,誉起仙台,蔼彼良书,义均不朽”[10]369。这篇墓志铭文出自“长水县令崔行功”之手,而崔行功正是《晋书》的作者之一,这表明辛玄驭实际参与了《晋书》的编纂,但参与的时间是在贞观二十二年,此时《晋书》纂修已近尾声。为了说明辛玄驭在《晋书》编纂中的作用与地位,有必要对《晋书》撰成的时间略做考察。
各类文献虽未明言《晋书》最终撰成的时间,但却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二》记载:“后数载而书就,藏之秘府……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焉。”[11]6682《唐会要·修前代史》亦载:“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4]1091-1092《册府元龟》和《唐会要》都记载《晋书》撰成后赐给新罗使者一部。查《旧唐书·新罗传》,明确记载了太宗赐给新罗使者《晋书》的时间:“(贞观)二十二年,真德遣其弟国相、伊赞干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3]5335-5336而《资治通鉴》更指出新罗使者来唐的时间为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12]6265。据此,赵俊推测此书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更有学者以房玄龄的去世为届点,将《晋书》的成书时间细化到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以前[13]和贞观二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之间[14]。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断定《晋书》成书的具体日期,但是该书成于贞观二十二年应无问题。
既然《晋书》成书于贞观二十二年,辛玄驭又是此年入馆参修《晋书》,表明他入史局时此书已基本纂成,所以实际参与编纂的工作并不多。根据《辛玄驭墓志》提供的信息,有学者推论辛玄驭在《晋书》编纂中主要负责了《刑法志》的编纂[15],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旧唐书》未提辛玄驭参修《晋书》之事。《旧唐书·令狐德棻传》中提到当时《晋书》“同修一十八人”,但没有列出具体人名。我们通过对《旧唐书》诸传的合并考察,得出这18位参与《晋书》编纂的人员分别是:《旧唐书·房玄龄传》提到房玄龄与褚遂良2人受诏重撰《晋书》,房玄龄又奏请“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3]2463。所以,《房玄龄传》中提到参与《晋书》的编纂者共10人。在此之外,《旧唐书》之《李安期传》载:“贞观初,累转符玺郎,预修《晋书》成,除主客员外郎。”[3]2577《李延寿传》载:“又预撰《晋书》,寻转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3]2600《李淳风传》载:“寻转太史丞,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3]2718《刘祎之传》载:“预修《晋书》,加朝散大夫。”[3]2846《敬播传》载:“参撰《晋书》,播与令狐德棻、阳仁卿、李严等四人总其类。”[3]4954《文苑上·崔行功传》载:“行功前后预撰《晋书》及《文思博要》等。”[3]4996这些列传分别又提到李安期、李延寿、李淳风、刘祎之、敬播、阳仁卿、李严(3)李严参与《晋书》编纂,出自《旧唐书·敬播传》:“参撰《晋书》,播与令狐德棻、阳仁卿、李严等四人总其类。”而在《唐会要》和《册府元龟》中,“详其条例,量加考正”者则是李怀俨,《新唐书》载录《晋书》撰人也是李怀俨,可知李严与李怀俨为同一人。、崔行功8人参与了《晋书》编纂。这18位参与《晋书》编纂的作者,或以职高位重受宠当朝,或以专攻文史名重一时,他们有的在《旧唐书》中被设立专传以载其事,有的是以附传、类传的形式保留其事,即便未有传记记载的人物,五代史家也按照“以类相从”的编纂方法将他们参与《晋书》修撰的史实载入相应列传之中。反观辛玄驭其人,一则生平事迹在整个唐代历史发展中影响甚微,尚未达到五代史家为之作传的标准,因而其参与撰修《晋书》的史事无从附焉;二则参与《晋书》编纂的时间晚,承担工作量少,不在《晋书》初撰时“同修一十八人”之列,故而《旧唐书》在涉及《晋书》撰人时没有提到他。
三、《卢承基墓志》与《新唐书》对《晋书》撰人的误判
《新唐书》作为继《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之后成书的文献,虽然有丰富的资料可资凭借,但在整合前人记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误判。《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载录《晋书》云:
《晋书》一百三十卷。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李淳风、辛丘驭、刘引之、阳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怀俨、赵弘智等修,而名为御撰。[16]1456
《新唐书》与《唐会要》《册府元龟》所载《晋书》撰人的总数均为21,但较之后两部文献,《新唐书》记载的《晋书》撰人名单中少了卢承基,多了赵弘智。《新唐书》的这一记载是否有所依据?新出土《大唐故使持节郢州诸军事刺史卢君(承基)墓志》(以下简称《卢承基墓志》)为这一学术疑问提供了答案。
关于卢承基其人,在《新唐书》《旧唐书》中均未有专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卢承基曾担任“主客郎中”[16]2895,此职实与《唐会要》《册府元龟》记载“主客郎中卢承基”作为《晋书》编修人之一的史实相契合。再者,《册府元龟》于《国史部》之《选任》《恩奖》《采撰》三篇都曾提到卢氏参与《晋书》的编纂工作,而《册府元龟》在史料上又多取自原始史料,剪裁甚少,有所依傍。唐史专家黄永年言:《册府元龟》在编纂时,有关唐代的“实录、国史以及唐令、诏敕奏疏、诸司吏牍等尚在,故这部分……可直接采用这些较原始的史料,这些绝不是目所常见。试取此书与《旧唐书》对勘,即知此书记载往往比《旧唐书》详尽,以《旧唐书》编纂时有剪裁润色,而此书则直接移录原始史料”[17]262。从这个角度来说,卢承基若未参与《晋书》编纂,《晋书》撰成后,他不应该出现在恩奖之列。新出土《卢承基墓志》证实了卢承基曾参与《晋书》编纂,文曰:“除水部员外郎。(贞观)十八年,内甫丁家忧,寒泉与泣血同哀,匪莪共如栾俱极。太宗幽求遐册,稽古前言,躬修晋史,以弘劝诫。同耻之画,列圣攸重;引从笔削,获奉能事。寻转礼部员外郎、守主客郎中。文昌五曹,仙台六尚。循丹墀而布武,切黼帐而含香。及史成,加秩,诏授朝散大夫,守主客如故。”[18]18据此可知,卢承基在参修《晋书》之前,担任水部员外郎,贞观十八年(644)因丁母忧,守孝三年,故其参修《晋书》时约为贞观二十一年(647),后迁礼部员外郎、守主客郎中。《晋书》撰成之后,卢承基受到赏赐,因而《册府元龟》记载卢承基因修《晋史》而受赏,是有所依据的。这也说明,《新唐书》在记载《晋书》撰人时,有可能受到《旧唐书》未载卢承基的影响,故而在《艺文志》中将卢氏置于《晋书》作者之外。
遗漏卢承基是《新唐书》在整合前代史料过程中出现的误判之一,而误植赵弘智则是《新唐书》在整合前代史料过程中出现的又一误判。有关《晋书》的作者,早于《新唐书》的《旧唐书》《唐会要》和《册府元龟》三部文献均不曾记载赵弘智,为何《新唐书·艺文志》却将其置于《晋书》作者之列?依笔者看来,其原因应在于《旧唐书·赵弘智传》载其“预修六代史”[3]4922。据此,不少学者释解说:所谓“六代史”,盖指《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晋书》。(4)如冉昭德在《关于晋史的撰述与唐修〈晋书〉撰人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弘智传》谓预修六代史,盖兼指《晋书》而言”;李培栋在《〈晋书〉撰人续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所谓‘预修六代史’,或是习称的‘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加上《晋书》,已非高祖诏修的‘六代史’。”彭久松还从赵弘智的学术地位、与令狐德棻的密切关系以及贞观二十一年(647)“弘智以光州刺史摄国学司业的身份留驻京师,预修《晋书》就有了时间和地点的可能”三个角度,指出“赵弘智《晋书》撰人的身份应属可信”[14]。对此,岳纯之认为彭久松“为证明赵弘智为《晋书》撰人做了不少推测”,却只字未提《新唐书·赵弘智传》“会天子废,免官,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入为陈王师”这条实实在在的记载,从而说明“修撰《晋书》时,赵弘智并不在京城,当然也就不大可能参与《晋书》修撰活动”[19]79。
对于赵弘智是否参与了《晋书》的撰修,应结合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来做分析,而不能仅仅从情理上作出推断。从两《唐书》均为赵弘智立传的史实来看,他若参修《晋书》,应在其专传中有所提及;即便参与修撰时间晚、承担工作量少,也应在恩奖之列。然而《唐会要》和《册府元龟》所载《晋书》具体撰人中并未提到赵弘智。其次,学界对赵弘智“预修六代史”所指为何争论不休,这一争论的根源始于《旧唐书·赵弘智传》,传文载其一生事迹,文短不长,迻录于下,以观全貌:
赵弘智,洛州新安人。后魏车骑大将军肃孙。父玄轨,隋陕州刺史。弘智早丧母,事父以孝闻。学通《三礼》《史记》《汉书》。隋大业中,为司隶从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应诏举之,授詹事府主簿。又预修六代史。初与秘书丞令狐德棻、齐王文学袁朗等十数人同修《艺文类聚》,转太子舍人。贞观中,累迁黄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以疾出为莱州刺史。……稍迁太子右庶子。及宫废,坐除名。寻起为光州刺史。永徽初,累转陈王师。[3]4921-4922
《旧唐书》这段史料将赵弘智的生命轨迹按照时间脉络划分为“隋大业中”“武德初”“贞观中”和“永徽初”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均记载了赵氏的任职经历,而“预修六代史”正值武德年间,而非贞观年间。由此表明,这里所谓的“六代史”,是指高祖时期欲修而未成的梁、陈、北齐、北周、隋和北魏的六代史。
再者,此处的“六代史”若兼指《晋书》而言,则说明赵弘智还同时参与了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的编纂,但是从现存反映“五代史”纂修的文献来看,“五代史”的作者各有其人,没有材料能够证明赵弘智参与了“五代史”编纂。故而,《旧唐书·赵弘智传》中所说的“预修六代史”,只是唐高祖武德年间未及完成的“六代史”。由此,学术界依据《旧唐书》中赵弘智“预修六代史”的言论,证明其参与《晋书》编纂的论证很难成立。
再者,不仅《新唐书》之前的史籍中均未记载赵弘智参与《晋书》编纂之事,即便《新唐书·赵弘智传》也未提及他是《晋书》的作者,唯《新唐书·艺文志二》“《晋书》”下著录其名,据此而认为赵弘智参与《晋书》编纂很难令人信服。之所以《新唐书·艺文志二》提到的《晋书》撰人会著录赵弘智,应是《新唐书》典志的作者在整合前代史料时对《旧唐书·赵弘智传》所载“预修六代史”的误判,于是导致后世言《晋书》撰人者均会提及赵弘智。
结合以上三方墓志史料与唐修《晋书》相关问题的考察,我们认为新出墓志对于重新审视唐代史学发展过程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能够提供直接的答案,或是启迪我们发现解决问题的新线索。因此,当今的中国史学史研究,除了重视理论的借鉴与方法的更新之外,还需观照出土史料的史学价值与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