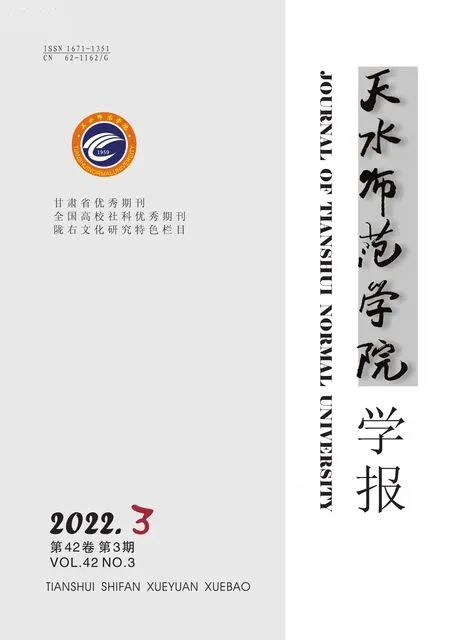“子不语怪力乱神”新释
刘 彦
(1.青海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2.天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自《论语》成书以来,无数前贤时彦对其诠释、注疏并著书立说,流派纷呈。然而,受诠释者所处时代背景、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一些篇章的断句和注释在当今看来就显得不太合理,“子不语怪力乱神”便是如此。“子不语怪力乱神”短短七个字,看似语意明确,其实不然。现将《论语》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注释进行钩稽爬梳,结合《论语》与其他典籍中孔子言行的记载,尝试再释“子不语怪力乱神”,试图明晰符合孔子理性思想“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本来面目。
一、“子不语怪力乱神”已有断句注释
《论语》的诠释工作始于西汉,流传至今最早的全本见于何晏等人所著的《论语集解》,其中“子不语怪力乱神”断句为“子不语怪,力,乱,神”,注释采用了王肃的“怪,怪异也。力,谓若奡荡舟,乌获举千钧之属。乱,谓臣弑君、子弒父。神,谓鬼神之事。或无益于教化,或所不忍言”。[1]33此后诸多前贤,如皇侃[2]169-170、邢昺[3]105、刘宝楠[4]146、程树德[5]480-482等人均沿用“怪力乱神”一断四事的断句,采用王肃的注释。儒学集大成者,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是将“怪力乱神”一断四事[6]98,虽注释与王肃见解有所差别,但大致相同。除此之外,还有将“怪力乱神”一断二事的断句,最早见于皇侃《论语义疏》中:“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乱神也。怪力、乱神有兴于邪,无益于教,故不言也。’”[2]170此种断句方式及注释虽非传统主流认知,却也被邢昺、程树德所采用。
今之学者,诸如蒋伯潜[7]144、钱穆[8]254-255、杨伯峻①本文除“子不语怪力乱神”,其余《论语》引文及标点均引自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故不再一一注出页码。[9]106、金良年[10]75等先生也采用“怪力乱神”一断四事的断句,将其认定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四件事,释义与传统主流认知无甚差异。然而,徐振贵先生结合《论语·述而》上下篇章排列顺序,将“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至“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四节章句连贯起来当作一个完整的段落进行注释,进而得出其中“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孔子在前后两句话语中的停顿、凝思、沉默,注释为“孔子不说话了,惟恐用力分散影响集中精神”。[11]这属《论语》注释新创,独辟蹊径。
二、关于已有断句注释的不同看法
“子不语”对应的是“怪力乱神”,依照前面三类断句注释,将“怪力乱神”作为“子不语”的原因无可厚非,但将其理解为孔子不谈论(不回答)有关怪异、勇力、悖乱、鬼神、怪力、乱神之事,或是前后篇章中过渡的表情和心理状态等注释均有不妥之处。
(一)关于“子不语”
关于“语”,郑玄注《周礼》云:“发端曰言,答述曰语。”[12]787传统的诠释者也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不语”,多注释为问答语境下的“不忍言”“不诵答”[2]170“不谈论”[10]75“不讲”[8]255等意。综上,关于“不语”的注释众说纷纭、言人人殊,皆将“不语”认定为孔子关于“怪力乱神”谈论(或问题)的沉默或是不愿主动提及、答复,因其无益于教化,故而孔子的“不语”甚至带有刻意回避的意味。
既然以上诸多“不语”释义是匹配“怪力乱神”特定断句方式而产生的,那么想得知这些释义是否符合编撰者想要表达的真意,就需要依据不同的断句方式,再结合《论语》与其他经典文献中孔子言及“怪力乱神”的章句进行分析,或许可以窥见“不语”的一二真意,从而验证以上释义是否适当。
首先按“怪力乱神”一断四事的断句方式进行分析。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渴望遇见赏识他的明君,但却屡屡碰壁、备受挫折,故而在迟暮之年发出“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的无奈感慨,“凤鸟”“河图”是古代传说,孔子借此寓意吉祥的事物隐喻自己对圣人及天下太平的企盼,当是孔子语怪的表现。诚然,亦有孔子回答鲁哀公时“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13]297之否定夔的怪异,也是孔子语怪的例证。对于力,孔子的态度也是褒贬同存,比如称赞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又如贬斥勇力“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可见孔子褒扬的是具有正向、积极作用的智谋之力、仁义之力,贬斥的是没有仁义约束的可能会导致社会祸乱的勇力、武力。对于乱,在《论语》中孔子语得最多,但多是分析致乱的原因,比如“勇而无礼则乱”“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对于鬼神,孔子的态度始终敬畏、慎重,不仅强调参加祭祀的重要性,如“吾不与祭,如不祭”,而且也强调祭祀时要注重保持内心的虔诚,即“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综上可见,若从语还是未语即孔子言行上看,孔子语及怪、力、乱、神的章句在《论语》中俯拾皆是;若从语还是不语即孔子态度上看,孔子对乱、神二事的态度始终如一,对怪、力则是称道与否定、褒扬和贬斥俱有。因此,匹配怪、力、乱、神的“语”既有主动提及也有被动回答,端看孔子言及此四事的语境或欲教化的目的则呈现出各种相异的表现。在一断四事的语境下,作为态度的“语”若被限定成唯一的释义进行注释,则不足以概括孔子对怪、力、乱、神的诸多态度。
其次分析孔子对怪力与乱神是否有“语”。关于怪力,“力不由理,斯怪力也”,不由理的力就是没有道理的力,结合孔子对“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论语·阳货》)“勇而无礼则乱”的态度,李充所述的“力不由理”极有可能是孔子所言之没有仁、义、礼规范的勇力,或是“季氏将伐颛臾……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不合道义的武力(暴力)。关于乱神,“神不由正,斯乱神也”,按孔子崇礼的人生态度,“不由正”的神应是未列入祀典(不合礼制)之祭的鬼神。《周礼·春官宗伯》将祭祀的对象分为天神、人鬼与地示[12]757,据《国语·鲁语上》:“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14]161可见,列入祀典的皆为有功于国家或是有益于世人繁衍生息的鬼神。李充所述的“乱神”应是特指未列入祀典且无功、无益于国家或世人生息的鬼神,是为乱神。《礼记·曲礼下》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12]1268淫祀不会带来福分,反而会劳民伤财,或是被降下祸端。对于淫祀,孔子必然反对,但对于淫祀对象——“乱神”,鉴于笔者学识有限,尚未发现孔子有言之相关的章句记载。综上,孔子虽未语“乱神”却语及“怪力”,可知孔子并非如李充所言对此二事皆“忍言”。
括上可知,就“怪力乱神”一断四事或一断二事而言,前贤们对“不语”的任一释义,都难以囊括《论语》以及其他经典文献中诸多记录孔子语及“怪力乱神”的态度,因此已有的断句注释早已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困窘境地。因此,要推理出“子不语怪力乱神”章句的合理释义,注释的重点应落在如何理解“怪力乱神”四字的含义上,而不是再纠结于“语”之释义,只有明确“不语”的对象是什么,“语”的释义自然会清晰明了。据前文已知,《论语》中有诸多孔子关于“怪力乱神”的言行,但孔子弟子以及门人仍将“子不语怪力乱神”郑重记录于《论语》中,可推论子不语的“怪力乱神”与《论语》中孔子语及的诸多“怪力乱神”应不是一类事物,否则在《论语》的编撰过程中为了逻辑通畅,众多弟子及门人就应将此句剔除而不是收录,故而孔子不语的“怪力乱神”应是另有所指。
(二)关于“怪力乱神”
“怪力乱神”即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注释重点,那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什么样的“怪力乱神”才是孔子所不语的。
就《论语》而言,除“子不语怪力乱神”,其余言“怪”1处、“力”12处、“乱”14处、“神”6处,量化的统计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是孔子在言行上语怪、力、乱、神最好的力证。因此在“怪力乱神”一断四事的断句注释中,“不语”此四事的说法始终不能摆脱在《论语》中释义不通、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在态度上,依据孔子部分语及怪、乱之事时所持的否定态度而臆断出孔子对所有怪、力、乱、神的态度都是“不语”,未免有些以偏概全。至于“怪力乱神”一断二事的断句注释,据前文已知孔子对“怪力”亦有语之,故而此种断句注释亦与《论语》相关章句存有扞格,难以释通。
既然否定了“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或怪力、乱神的释义,那么“子不语”的对象就极有可能不是“怪力乱神”字面上所指代的事,而是“怪力乱神”字面下引申的其他事,那徐振贵先生的解释是否就合理了?
徐振贵先生认为《论语》某些篇章并非杂乱无章而是相互之间有所关联,“子不语怪力乱神”应为前后两章语录之间孔子的过渡表情或是沉思状态,而不是具体指代孔子不语何事何物。然而,与《论语·述而》中“子不语怪力乱神”所处章句顺序不同的是,《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却是在“‘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之后[15]1940,可见距离孔子时代较近的司马迁,也未认可《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位置及其与前后两章之间的逻辑顺序。众所周知,《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语行事的书,没有确切的开始编撰时间,也没有确切的成书时间,甚至由谁人执笔亦未可知,因此每一篇中的各章是否发生在同一时间,是否存在前后顺序相承还有待商榷。正如杨伯峻先生所说:“《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9]导言31既然无法从有限的传世文献中找出确切可信的逻辑顺序,那还是暂且将原本独立段落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仍视作描述孔子言行态度的章句,而非表情抑或心理状态更为妥当。
综上,无论是以王肃为代表的一断四事断句注释,还是李充的一断二事解说,均与《论语》中载有孔子语及怪、力、乱、神或怪力言论前后抵牾、彼此轩轾。而徐振贵先生提出的孔子表情、心理状态的解释,虽然合乎假定的段落情境,但不符合语录体注释的要求。
三、“怪力乱神”新解
要揭示什么是孔子不语的“怪力乱神”,应先从孔子的鬼神观入手,确定孔子对“神”的态度,进而推理出何种“怪力乱神”才是最合乎情理的“子不语”。
孔子对鬼神的态度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在生产力普遍低下的农业社会,对自然的崇拜、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使得人们观念意识中产生了可以主宰世间万事万物的神并对之心存敬畏。《论语》中虽未明言孔子信鬼神,但作为遵天命信鬼神殷人的后裔,成长于最为重视周礼的鲁国,孔子对鬼神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孔子在被子路误解时,对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颜渊死时孔子抒发悲痛心情的“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以及被匡地群众拘禁时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等。以上虽是在特定情境下孔子宣泄愤懑、悲痛、牢骚情绪时的语言,甚至还带有赌咒的意味,但孔子选择宣泄的对象是“天”,可见孔子敬畏的“天”不仅具有人格神的性质,还是道德秩序的化身①“孔子心目中的天,虽仍具发号施令的人格神性,但主要是殷周之际所确立的那种传统的‘道德之天’。”参见邬可晶:《孔子与天命》,《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4期。。同时,孔子认为“天”还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如孔子受蒲地人的胁迫,与其盟誓不去卫国,但在离开蒲地后却又前往卫国,当回答子贡“盟可负邪”时却言“要盟也,神不听”[15]1923,认为被胁迫而立的誓言被立誓人违背,具有人格神的“天”是不会计较被胁迫人责任的。此外,孔子还相信天人之间存有感应,认为天能通过梦境预示世人祸福,让人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比如孔子因“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15]1944便知自己时日无多,即将面临死亡。综上,孔子对“天”的认知,应是继承了自殷代以来人们对“天”的角色赋予,即“天”为至上神,是世间万物的最高主宰,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除却对“天”这一至上神的敬仰,对于地位次于“天”的其他鬼神,孔子亦是满怀虔诚、谨慎与敬重。对鬼神的形态、功能等孔子也曾做过较为详细地解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12]1628亦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综上可见孔子认知中不仅承认鬼神存在,还非常尊敬鬼神,相信鬼神具有超自然的神力。因而,当回答季康子提问卫灵公昏庸无道却未丧国的问题时,孔子将“祝鮀管治宗庙”(《论语·宪问》)作为三个卫国不会丧国的原因之一,说明孔子认为做好宗庙祭祀,祭祀的鬼神们就可以起到庇佑后世子孙安康、国祚绵延的作用。不仅如此,在遭遇困难与病痛时,古人也常向鬼神祷告祈求平顺与安康,孔子亦是如此,如生病时“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如若孔子不信鬼神,又何来祷告、祈求鬼神的言行?但清醒也如孔子,知鬼神不会因世人的祭祀与祷告而轻易许诺。因此,孔子认为对待高高在上的鬼神,众人应该顶礼膜拜、虔诚侍奉,要有最大的诚敬之心,不能存有一丝懈怠或亵渎。在事人与事鬼的关系上,当“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的回答并非是对事鬼、死二事避而不答,反而是明确告诉季路能够事鬼的人必定是能做好事人之事的,故而先有事人后有事鬼,事鬼当高于事人。生死之道亦是如此,未能明白生的意义就不能领悟死的道理,因此知生便是知死。一言以括之,死与鬼是较之生与人更为复杂、深奥的道,非常人能够理解与领悟,所谓“学之有序,不可躐等”[6]125,就是告诫世人勿要越过事人追求事鬼或越过知生而追求知死,否则不但会乱己且易陷入困惑之中,还会产生乱神行为而破坏礼制,无论何种结果皆不利于孔子所倡导的“克己复礼”以及礼治社会的重建。故而孔子此番回答,即是阐述自己重事鬼的观念,也是教化季路重事人后才能事鬼,重死亦要重生,学习、做事要循序渐进且遵守礼制。孔子重事鬼的观念应是渊源有自。众所周知,周礼重祭祀,生长在最为重视周礼的鲁国,孔子从小耳濡目染并加以模仿,才会有“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15]1906在其后的人生中,孔子始终孜孜不倦地追求“克己复礼”,倡导恢复周礼,制定周礼的周公则必定成为孔子尊崇、学习的榜样。在事鬼之事上,无独有偶的是据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所载,周武王病重,周公在祝告先王时说“惟尔元孙发也,不若旦也,是佞若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16]158通过祝告之辞可见,周公认为自己能替代武王侍奉鬼神,较之武王更为适合侍奉的优势在于自身的能言善辩与多才多艺,虽身份不及武王尊贵,但侍奉能力却胜过武王,这表明了在周公的认知中,意欲侍奉鬼神的人的身份可以不是最尊贵的,但必须要具备超越常人的优秀品质与能力,祝告之辞表现的周公事神观念与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事鬼标准不谋而合,可见孔子的事鬼观念追本溯源应是来源于周公。
祭祀是事鬼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非常重视祭祀。比如,在歌颂禹时孔子首赞的是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而将“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置于其后,可见孔子认为禹薄待己身、不图个人享乐却“致美乎黻冕”“尽力乎沟洫”的美德,均不及同样薄待己身却用丰盛祭品“致孝乎鬼神”的美德。通过这段章句可知,孔子敬鬼神,不仅要求祭祀者在意识上要高度虔诚与重视,在祭品准备上还要能够做到省己厚供才是事鬼“致孝”的最高境界。孔子除却重视祭祀,也会身体力行慎重遵守“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论语·乡党》)的各种斋戒礼仪,因而孔子的重祭祀、慎斋戒并非是利用鬼神做出各种敬神的姿态以教化世人谨守礼仪,而是真正地将信神、敬神做到了表里如一。
然而,鬼神之事又是玄奥难述的,对于说不清楚也不能熟知的领域,孔子则是不如不说。继承孔子鬼神观的朱熹也言“人且理会合当理会底事,其理会未得底,且推向一边。待日用常行处理会得透,则鬼神之理将自见得,乃所以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17]33这也正是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的严谨治学理念。因此,在回答樊迟“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时,孔子便清楚地陈述了自己对鬼神的态度。“敬”与“远”即是孔子对鬼神存而不议的理性鬼神观,也正是孔子不随便与人论难鬼神的印证。正如庄子所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8]34此处圣人,当是孔子无疑。否则,以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的态度,不可能在《论语》中没有一句批判鬼神的言论。
既然《论语》与其他经典中存有诸多语及“神”的章句,且孔子信神、敬神的态度始终如一,那么“子不语”的“怪力乱神”又指代的是什么事呢?或许揭示“怪力乱神”确切句意的关键在于“乱”字。春秋时期王室衰弱、诸侯兼并、天下无序,在《论语》中多处可见此类描述,如“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季氏旅于泰山”(《论语·八佾》)等,对于诸多“乱”象,孔子不仅态度鲜明地进行批判,更是在行动上“乱邦不居”(《论语·泰伯》)言明立场,即使有孔子欲应公山弗扰与佛肸之召前往相助却实未成行的章句,也不能就此判定孔子为了出仕而不择效力对象。相反,孔子则是借应召来表达自己欲拨乱反正的目的,正如孔子回答子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来言明其志是要建立一个像西周一样的国家,即使用人者为叛乱之人,邀请他前往相助的目的也并非欲用其治国理政之能,而是欲借助其声望为自己的不义行为披上合礼的外衣,对此孔子也是以“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论语·阳货》)来表达自己即使是应乱者之召,也能够坚持本心,拥有不为他人改变自己信念的坚强意志。因此,孔子的应召,并非是助叛乱者行乱事或者是顺叛乱者之意无所作为,而是希望借叛乱者给予的权力实现自己长久以来坚持的理想——恢复周礼,期冀建立一个充满仁爱、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
孔子崇尚周礼、恪守礼制,在他看来不守礼会导致因权利争夺而臣弑君、子弑父,会出现天子权威衰弱、诸侯权力旁落以及陪臣执国命的各种社会乱象,其根源皆为没有恪守礼制。孔子认为恪守礼制不是做给他人看的各种礼仪,而是要求世人不仅要将“礼”外化于行,更是要将“礼”内化于心,表里如一的恪守“礼”的精神。如若内心不能守礼,即便是礼仪做得再好,也会在个人欲望膨胀时误入歧途,出现各种非礼行为,而这些行为正是产生和滋长社会乱象丛生的原因。
礼,不仅是个人心与行的规范与约束,更是衡量其德行的准则。“礼乐,德之则也”[12]1822而“天道福善祸淫”[12]162,要避免天道的惩罚,就必须顺应天道,然“天道无亲,唯德是授”[14]396,有德才能得到天道的认可,有礼才会有德。因此古人认为要顺应天道得到天道的认可,就要尊礼,只有人人都按礼行事,具备了德行,才能有天道认可下人间社会的和谐与天子政权的稳定。否则,无礼失德就会受到天道的惩罚,“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12]1426孔子向往贤人治理、上下有序、和谐统一的天下,渴望拨乱反正,崇尚周礼,强调尊礼,因而一切的僭礼现象或是非礼的行为都成为孔子深恶痛绝并加以批判的对象,是故孔子在回答言偃时引用诗经“人而无礼,胡不遄死”[19]69表达他对无礼行为的深恶痛绝与不能忍言。
礼,《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20]3礼源于敬神祈福,敬神以礼,因此礼源于祭祀。孔子主张“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祭神如神在”,对鬼神“敬”而远之,不妄言鬼神。据前已知,孔子信神、敬神却“不语怪力乱神”并不是孔子对于怪、力、乱、神、怪力、乱神之事闭口不说,而是“不语”的内容与孔子坚持的礼治思想有关。孔子崇礼、守礼,不遵循礼制的事神行为自然会受到孔子严厉地反对,因此我们做一个猜想,孔子“不语”的内容肯定与“神”有关,而这个内容定是无益于教化,换言之就是不利于规范和约束世人的行为,不利于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不利于礼治国家的建立,结合孔子的重礼思想与敬神言论,唯有非礼鬼神的言论最是让孔子不愿主动提及。
何谓非礼鬼神?古人认为祭祀鬼神有着严格的规范和完整的仪式,若祭祀者希冀从鬼神处获得更多的益处,则会枉顾礼制的规定,即非礼鬼神。梳理典籍文献,非礼鬼神的行为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祭祀不该祭祀的鬼神,“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譬如季氏以大夫身份凌驾于公室之上,掌握鲁国实权而旅于泰山,越等级祭祀了本应是天子与鲁国诸侯才能祭祀的鬼神,是对鬼神的献媚,是对鬼神的非礼。其二,祭祀可以祭祀的鬼神,却借祭祀对鬼神提出无理的要求,也是对鬼神的非礼,比如“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12]1736,在郑伯看来只要提供了丰厚的祭品供鬼神享用,即使是为平众怒而借鬼神之名行诅咒之事,鬼神也不会怪罪自己,或许鬼神还会帮助自己达成目的。其三,将鬼神人格世俗化,认为鬼神亦可被欲望、利益驱使帮助世人实现自己的心愿,比如“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12]1826虽衣着服冠亦为祭神之物,应做祭品主动供奉,但在子玉的梦中却成为河神为了得到华美的皮弁,而主动许诺子玉战能得胜,撰写者这种将神尊人卑的关系变换成神人之间可以互利互惠的平等关系,其实也是世人非礼鬼神的表现。其四,不顾神位主次之分,越过主神祭祀有实权的主管神,譬如“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论语·八佾》),此句虽为王孙贾暗示孔子之语,但通过其所借之俗语①“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疑为当时已有之语,如钱穆认为“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古有此语,贾引为问”(见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90页。),再如杨伯峻注释“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这两句疑是当时俗语”(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0页)。可窥见当时世人祭祀鬼神时已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这种带有功利目的的祭祀亦可视为对鬼神的非礼。概而言之,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古人认为鬼神可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端看祈求的人是否能够拿出鬼神心仪的祭品以打动鬼神受己驱使,在非礼鬼神的世人心中,无所不能的鬼神具有了很强的实用性,不仅能作为祈福的对象为世人降下福祉,也能顺应世人的祈求降下损人利己的祸事。总之,越级越境祭祀祀典中的鬼神,或是祭祀祀典之外的鬼神,或是借祭祀鬼神提出诸多要求进行利益交换,或是越过主神祭祀次神等各种不合礼制的淫祀之风盛行下,世人不再是自律自强顺应天道,人鬼之间实质已成为鬼神顺应人道的互利合作关系,在当时世人的认知中被祭祀的鬼神已不再具有公正无私、明辨是非的形象,变成善恶不分、是非不辨、有求必应的欲望之神。
孔子认为非礼祭祀鬼神不一定能达到祭祀者祭祀的目的,却能滋长祭祀者的不轨之心,助长其个人私欲的膨胀,助长其心理上对各种责罚的逃避,这种寄希望于得到鬼神庇护而放心大胆做尽坏事的心理,客观上会造成社会的混乱与动荡。因此,非礼祭祀鬼神,求的虽是鬼神,但乱的是礼制,乱的是人心,会有兴于邪,无益于教化,所以孔子“不语”。在淫祀盛行的时代,孔子告诫世人不要非礼祭祀,既不能违制越级越境祭祀,更不能滥祀鬼神,要抑制和消除对鬼神的各种非分之想,杜绝各种对鬼神的非礼行为,同时规劝世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须知“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不仅要抛却一切不合礼制的想法和行为,做到敬鬼神须尊礼,还要做到时时、事事都知礼、尊礼、守礼、敬礼,才能立身处世,才能有君仁臣忠,才能有被礼制统一言行的百姓,才能有孔子希望的天下太平、国泰民安。
综上,根据《论语》及其他传世典籍记载的孔子言行,结合孔子的鬼神观,可知“子不语”的不是怪、力、乱、神、怪力、乱神之事,因此一断四事或一断二事的注释,均不能完美地解释孔子因其无益于教化,所以不语的释义。但据孔子尊礼、守礼的思想态度与孔子深恶痛绝一切非礼行为的态度,结合孔子关于祭祀鬼神尤其要严格遵循礼制的思想,可推理出“子不语”的对象应为扰乱鬼神的怪异力量,即不符合礼制(非礼)的祭祀行为。
四、小结
总体而言,既然现有记载孔子言行的典籍都无法提供“子不语怪力乱神”发生的场景,以及在何情境下产生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貌似“孤立”编排于《论语》之中,其实不然。历来的注释,解说者均受到了所处时代主流文化的影响,统治者为加强对被统治者的思想控制,不利于社会控制的言论必会受到统治者严厉禁止。不论是怪、力、乱、神还是怪力、乱神,确实有利于邪说的兴起,无益于对民众的教化,更不利于统治者的政权稳固。因而解说者的注释,从某种意义上也迎合了统治者加强社会思想控制的意图,也因此得以流传至今。
然而,对于经典的诠释,我们不能脱离孔子的思想妄自揣度,应将其置于《论语》整本的语境中,辅之以其他载有孔子言行的典籍,以及能影响孔子思想的时代特点,条分缕析。从孔子礼制思想的维度,结合孔子对非礼之事的批判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无需断句,可将其理解为孔子“不语”的内容是非礼祭祀,即非礼鬼神之事。孔子追求礼治社会,渴望再建像西周一样的国家,而非礼鬼神则是破坏礼制,这与孔子长久以来坚持的理念背道而驰,且孔子认为非礼鬼神不仅会扰乱人心,或许还会得罪鬼神祸至人世,因此,无论是人为的致乱还是鬼神的惩罚,皆会导致社会秩序动荡,故而孔子会“不语”,会抵制反对。既已明确孔子“不语”的对象是非礼鬼神,那么“语”的释义也就明晰起来。
首先,“不语”不代表简单地说与不说,涉及非礼鬼神之事孔子还是要说的,比如批评冉有不阻止季氏旅于泰山,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等。“不语”应为孔子对非礼鬼神行为的理性态度,“直言曰言,论难曰语”[20]160,“不语”可取不与论难之义。孔子能对非礼鬼神之事直言批评却不与人论难其害,究其缘由或是因为鬼神之理深奥难懂常人难于理解,无法与其明晰非礼鬼神的害处,且易陷入无休止的辩论之中,即“论难者,理有难明,必辨论之不已也”[21]1411;又或是因为身处动荡、混乱且淫祀盛行的春秋时代,依孔子的身份地位、影响力还不足以撼动、改变世人非礼鬼神的观念与言行,若与人论难非礼鬼神的害处,势必会惊世骇俗且易被视为“异端”,故而孔子不与人论难非礼鬼神。但孔子对非礼鬼神明确的反对态度必定会时常出现在教化弟子的过程中,弟子对其印象深刻故记录于《论语》,这种对非礼鬼神不予论难的理性态度也恰恰正是孔子具有大智慧的深刻表现。
其次,从语法上讲,“怪力乱神”四字关系也可推演为怪力乱→神,即形容词+名词+动词+名词结构,其中“怪”作形容词性修饰“力”,“怪力”即怪异的力量作定语修饰动词“乱”,乱的对象是“神”。由此可见,作为孔子思想吉光片羽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也就只是孔子不与人论难非礼鬼神的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