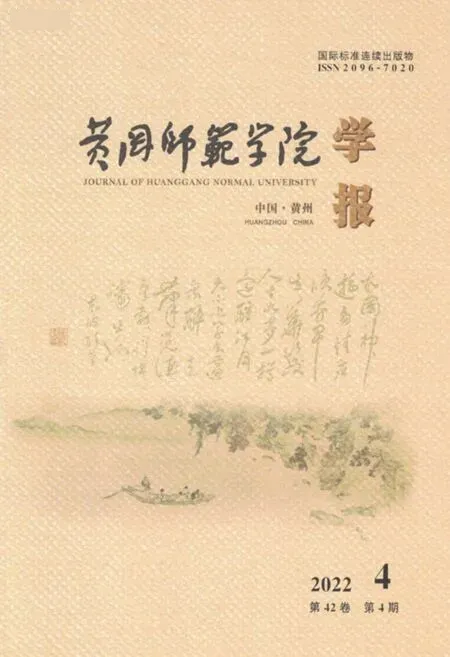“也算翻身”,如何“翻心”?
——作为“翻身小说”的《刘二和与王继圣》
宋 喆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一、从“翻身”到“翻心”
在40年代华北地区土地改革纪实文学《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卷首,作者韩丁特别界定了“翻身”的意义:“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汇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官,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1]在土地改革的官方文件和新闻报道中,与“翻身”并列的还有“翻心”一词。《中共冀晋第四地委宣传关于纪念“七一”诞辰纪念的指示(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中提到:“在发动群众上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使群众彻底的翻身翻心。”[2]1947年2月20日,《人民日报》以“翻身先翻心”为题,介绍涉县启发落后农民的经验[3];3月31日,《人民日报》又在总结太行区平川县的“反倒算大翻身”经验时指出:“这次能大干起来,主要是用了‘普训农民先翻心’方法。去秋群众没翻心(即未觉悟),只是干部给了些果实,战争到来,不少群众给地主退果实。”[4]
这一词汇同样进入了作家的创作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地主李子俊不斗即倒,主动献出土地,老百姓又偷偷将地契送回去。对工作队而言,这是没有发动起来,用丁玲的话说,则是“庄户主还没有翻心啦,他们害怕,不敢要嘛”[5]。因此,我们不妨把韩丁界定的“翻身”,拆解为政治经济意义上的“翻身”和思想觉悟意义上的“翻心”两个部分。
1947年2月1日,《新大众》第34期刊登了赵树理新作《刘二和与王继圣》首章,“编者的话”提到这部“翻身小说”预计写三个部分,分别是儿童时代、青年时代和群众运动以后。该刊共连载六期,到7月1日出版的第39期登完第一部分(即前三章),此后没有继续。1955年8月,小说在《人民文学》重新发表,未再分章[6]。1966年,赵树理回忆称,小说断更的原因是“提纲失落,小报停刊”[7]412。事实上,《新大众》到1947年底方才停刊改版,并于1948年元旦起,改为周报《新大众报》[8];小说第二部分,也已写出两章,赵树理生前未发表,1980年工人出版社出版《赵树理文集》时,从遗稿中整理辑出,编者在脚注中提到:“第六章以后,是原稿遗失,还是没有继续写下去,无法判断。”[9]352
黄锐杰在《灾荒年、劳动互助与新干部的诞生》一文中指出,赵树理自述的原因可能并不可靠。若是因为“停刊”,则小说“儿童时代”写完,距离杂志停刊尚有小半年连载空档期;若是因为“提纲失落”,则在第四、五章中,赵树理似乎有意避开了初始大纲,直接从群众运动之后写起。他认为:“与其将原因归之于‘提纲失落’,不如说赵树理在按提纲往下写时遇到了切实的困难,这种困难与他要处理的抗战时期的互助组有关。”[10]
必须的承认是,无论是原稿遗失,还是无法继续,斯人已逝,研究者难以猜测个中原因。然而,从具体的文本内容和形式入手,我们却能够发现赵树理对“翻身”与“翻心”问题更为复杂的思考。
二、如何“组织起来”?
和赵树理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刘二和与王继圣》的故事包含明确的时间和空间形态,具有特殊的象征意味。①小说前三章的时间观念表现出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特点,从“宣统复位”到“塘沽协定”的十几年,作为于己无关的“国家大事”,在乡绅马先生的口中混为一谈;叙述者主要通过叙述数小时内不同人物的活动,将黄沙沟的主要空间场景(放牛坡、打麦场和关帝庙)、不同人物关系和积蓄已久的矛盾全景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一章中的“学校与山坡”象征着地主、“小疙瘩户”与外来户之间的阶级光谱,第二章中拜亭上的座次格局则代表统治者内部的尊卑秩序,第三章的核心“关帝庙挤不挤”则是一种空间化政治,小说最终借助聚宝之口道出:“只叫你们活吧!东西楼上、拜亭上、台上、台下,满庙都成了你们的世界,哪还有别人活的地方?”[9]380
而在小说未刊的后半部分,也即黄沙沟群众“翻身”之后,时间与空间出现了明显变化。首先,“静止”的时间“流动”起来了。第四章以“十来年”“十来个月”“十来天”等一连串密集的时间词开头,营造出快节奏的阅读感受,呼应着打麦场上的新气象。其次,“开始”于“群众翻身运动”的时间,构建起新的公共空间和政治秩序,伴随着二和等人的成长,社会交往场域由山坡转移到麦地和打麦场,伴随着传统士绅政治的落幕,“合作社”与“说理会场”取代了“拜亭”和“戏台”,成为了新的公共空间。
然而,黄沙沟的“时间”和“空间”变动却并不同步:当“时间”已进入“革命后的第二天”,“空间”却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第一部分的格局。亲眼所见的割麦图景固然动人,但是聚宝很快失望地发现当地“翻身”并不彻底。他移步换景,所到之处,无论是麦地、合作社,还是打麦场,都蕴含着从“翻身”到“翻心”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套用1946年初赵树理所在的武安县斗地主的口号,“理要说清,账要算清”[11],聚宝眼前的黄沙沟,可谓既没算清账,又没说清理。
首先,麦地里的一番对话带出了农民“翻身”不彻底的问题:王光祖留下三十来亩地,还雇着二和做长工。小胖埋怨几人“教着曲子也唱不响”,到了场上不会说话,“自己不想翻,别人有什么法?”[9]382对此,老刘表示自己不用说话,做人要知足,给王家当伙计是出于自愿。大和觉得自己不会说话:“像我们这些人,平常只在黑处钻着,上了大场面能说个啥?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说出去谁知道是啦不是啦?”[9]383比起父亲和哥哥,昔日就试图与王光祖“说理”的二和,显然对现状多有不满。他沉默半晌,终于开口:“说起来咱也算翻了身了,可是咱还是人家的伙计,人家还是咱的东家!”[9]383束缚着老刘的,固然是乡土社会的人情(“你们如今说那理我就听不过去!”[9]384)和宿命论的观念(“那还不是咱的命穷?”[9]384);而大和的困境,则体现出农民在“革命”与“革命话语”面前感到的隔膜和无措。
翌日打麦场上爆发争吵,二和一番“算账”固然解气,然而说服不了继圣他娘、老驴、父亲,更无法说服满口“这年头”的王光祖。李国华在《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中指出,赵树理小说以“说”为中心,形成了“说”的欲望和能力的问题网络,主要命题是寻找“能说话”的人,并使(“能说话”的)人(重新)学会“说”。[12]而在现有的文本中,“能说话”并能说服别人的人,尚且没有诞生。
另一个与“说”有关的空间是合作社,此处呈现的是传统精英依靠文化资本继续把持乡土社会话语权的问题。第三章社房楼上的宴席体现了人情社会的话语秩序:谁先说话、谁后说话;谁必须开口,谁有权沉默;谁能东拉西扯掌控话题走向,谁应该顺着别人的意思往下说,两边都不得罪。于是我们看到,赵永福正欲分辨却被打断,李恒盛费劲想到的妙语被王光祖碰散。相似的局面在第四章的合作社中重复上演。群众虽已“翻身”,然而象征着崭新“时间”的合作社(也是毛泽东所谓“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组织起来》)[13],却仍是继圣、喜宝和宝三等人的活动场。老张老婆进门买东西,继圣动辄截住她的话:“你光说买点这个买点那个,你就不知道一升麦价多少钱,你要买的那些东西值多少钱?”面对如此态度,老张老婆只能放弃自己起初的要求:“我不知道,凭你算吧!”之后,继圣故技重施,向群众抱怨自己工作的繁琐与艰难,“听话的人,跟在台下听讲一样,都只是瞪着眼睛听,都觉得人家比自己想得通透”[9]388。
继圣的“算账”知识与能力,构成了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意义上的“文化资本”②。群众“翻身”之后,传统精英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复存在,但是附着于个人身体、通过积累而习得、内化为“知识”与“品味”的“文化资本”,却不会轻易丧失。这种“文化的武器”,或曰“识字的用途”,在乡村秩序的重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李家庄的变迁》中,李如珍等人依靠类似的方式抵制“减租”:“铁锁他们都拿不起笔来,我们就故意弄上很详细整齐的表册慢慢来填,填完了就说还要往上报——这样磨来磨去,半年就过去了。”[9]290在同年创作的《小经理》中,合作社经理三喜不是通过“翻身”斗争,而是通过识字算账,才完全掌握了合作社的主导权,并最终促成曾为地主狗腿子的掌柜王忠的转变。③
小说以《刘二和与王继圣》为题,前者未能“翻心”,后者依然掌握话语权力,而在第五章的“打麦场上”,上述矛盾集中爆发,并牵扯出互助组“自愿还是自流”的问题。老驴和继圣他娘阻止二和在自家场上摊麦,王光祖看似宽容,却借着几句“这年头”宣泄心中不满。于是小胖直言:“我这头一场欢迎人多!这年头咱不跟他互助!”[9]395他主持互助组会议,提议将王家开除出组,并自有一番“算账”逻辑:“在地里做的话,就算还有个等价交换;晌午打场,谁也没有给谁算过工。……咱们给人家白白服了务,连人家一个场边也不能用一用,这还互助个什么?”[9]397除了二和痛快赞成,谁也没有话说。老刘不赞成小胖,却碍于对方武委会主任的身份不便直言;大和同意小胖的道理,知道自己和继圣家互助吃了大亏,但也不想和大家过不去,又怕说出来小胖不赞成;铁则和鱼则觉得事不关己,宿根则心向继圣一家,却因吃过亏而不敢包庇。小胖心生气馁,认为“照你们这样,一千年也翻不了身”[9]398。对此,黄锐杰在《灾荒年、劳动互助与新干部的诞生》中敏锐地指出:“小胖真的理解‘互助’的涵义了吗?……借助互助,劳动创造的价值具有了公共指向。然而,仅仅将不愿‘分有’者开除出去是真正的‘分有’吗?”[10]
1948年,赵树理结合晋冀鲁豫地区“土改”工作中的问题,在《新大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其中《“自愿”不是“自流”》一文提到:“最近有些地方,干部和群众都把自愿解释错了,劳力强的只愿意跟强的碰组,有牲口的也只愿意跟劳力强的碰组……像这样想组就组,不想组就罢;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叫做‘自流’。‘自流’就是没人管,弄成啥算啥。这完全不合乎上级提倡互助的精神。”他进而指出:“互助的好处,就在组织起来,用合理的分工,避免劳力的浪费。”[7]220所谓的“组织起来”,从来不仅仅是生产意义上的;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抓革命、促生产”始终是一体两面。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着亲戚邻里之间避免算钱的小规模季节性互助,它依靠人情伦理降低协调和监督成本,并反过来促进人情伦理的维系。40年代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将这种民间互助引导并转换为组长领导、人员固定、简单计工的常年互助组,赵树理在《刘二和与王继圣》中触及的问题恰好与此相关:小胖“武委会主任”的身份,是否对沉默的群众造成了新的压制(毕竟所谓“嘴一份手一份,能说能打”[9]383,其重点始终在“打”不在“说”)?“等价交换”的“算账”逻辑,如何贯通乡村传统人情伦理,真正说服以大和、老刘为代表的农民?至于光谱的另一端,一口一个“这年头”的王光祖、无法被二和说服的继圣他娘、在合作社中给群众“上课”的继圣,又如何被“组织起来”,真正进入新的、以“互助组”为象征的秩序中呢?
“翻心”何以可能?小囤、小满和小管在区上开会回来,带来了新消息。小说没有继续,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尝试探究赵树理可能给出的答案。
三、“主体”的诞生
作为一部“翻身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不仅试图处理“土改”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也尝试建构“农民”的主体形象。换言之,“翻心”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的生成,本身也是“组织起来”的前提与结果。赵树理笔下频频出现的“说理会”,在官方文件中多以“诉苦”代替。这是一套相当重要的群众动员机制,核心在于通过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技术和策略,使农民从表达走向行动,从诉苦走向斗争,掀起群众运动的巨浪[14]。作为一种“文学政治”,赵树理惯用的“说理”与“诉苦”拉开了微妙的距离;“农民”主体的诞生,不是源自刻意的“诉苦”引导与动员,而是出自“说理”的欲望和自发的激情。
《刘二和与王继圣》的发力之处,在于填补此前文本留下的空白。如果说从《小二黑结婚》到《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书写了如何“夺权”与“翻身”;那么《刘二和与王继圣》,以及同期的《福贵》《小经理》等作品,则进一步处理从“翻身”到“翻心”的问题。一方面,赵树理提到了农民“说理”的欲望,却多少省略了“说理”的过程。在《李有才板话》中,农民“说理”能力的实现,靠的是板人李有才神乎其技的宣传功力。老杨提议斗争恒元,小保第一反应是:“怎样去集合人?怎样跟人家去说?人家要说理咱怎么办?人家要翻了脸咱怎么办?……”[9]193解决之道是让李有才编歌子号召大家加入农救会。在《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游历太原,接触共产主义知识,方为心中的愤概寻找一套合理解释;小常向他介绍“牺盟会”章程,帮他填写入会志愿书:“就照这样收会员,以后有什么要做的事,大家开会决定了大家来做,这就叫组织起来了。”[9]382但一个不会编歌子,也没有远游经历的农民,要如何言说自己呢?仅仅收了会员,就算“组织起来”吗?民主生活要怎么过呢?在1946年10月考察太岳区期间创作的《福贵》中,赵树理已经开始处理这个问题。对于在剥削中沦落为乡间流氓的福贵来说,土地的账笔笔清楚,自己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谁又该为他的堕落负责,才更加值得说道。小胖批评二和等人“教着曲子也唱不响”[9]382,事实上赵树理想问的也许是:“教”出来的“曲子”,真的“唱得响”吗?
另一方面则是农民“说理”的效果。《地板》由小学教员王老三现身说法,讲述“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9]224的道理,却并未描写地主王老四的切实转变;《李家庄的变迁》结尾,李如珍被肉体消灭,小毛暂且偷生,白狗的解释是:“他要没有真心改过,咱的江山咱的世界,几时还杀不了个他?”[9]324《福贵》在“我想请你老人家向大家解释解释,看我究竟算一种什么人!”[9]351处戛然而止;《小经理》的王忠变得老实,与其说是出于觉悟,不如说是为了保住饭碗,因为“滚出去便再没有个干的了”[9]403。由此可见,《刘二和与王继圣》的确有着更大的野心,标题结构既象征着故事前期的对立,也暗示着故事后期的并立,并最终指向“组织起来”的远景。竹内好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中指出,赵树理超克现代文学与人民文学的方法,是“在创造典型的同时,还原于全体的意志”[15],以《李家庄的变迁》为例:小说起初直接刻画铁锁,常常以独白的手法告诉读者他的心中所想;在“牺盟会”成立后,完成了典型的铁锁迅速溶入作为整体的背景里,只在间接描写中露面。反观《刘二和与王继圣》开篇,赵树理给了“地主”以同等分量的关注,细致描述了继圣的心态,很可能要在后文让继圣“心服口服”,成为另一种“改造”成功的“典型”,并且融入背景之中。
四、游戏的“失败”与互助的“成功”
在上文所述的两重意义上,我们必须追问:所谓“农民”的主体性,究竟是谁的主体性?在这篇小说中,它是否能够涵盖整个乡村的阶级光谱,将所有人“组织”到集体之中?赵树理是否在文本内部提供了这种“组织”的可能途径?此时,让我们再次回到小说开头的“游戏”场景。继圣倚仗现实中的优越地位,试图掌握游戏主导权:“我不跟你们这些放牛的孩子算一伙!”[9]356对此小囤的反应则是:“不跟老子们合伙,谁去你家叫你来?”[9]357把继圣按倒在地后,小囤更表示:“他不玩咱们玩!”[9]358此处孩子们将继圣排除在游戏之外,与第五章中小胖要求将王家开除出组前后照应,相似的“驱逐”之举,使“游戏”带上了复杂的政治意涵。
一方面,儿童游戏中的言语互动、心理变化是乡村政治形态的缩影,“学校”与“山坡”的对立是阶级秩序的投射。这种借助日常生活表现农村政治状况的手法,在赵树理的小说中相当常见,《邪不压正》软英的订婚就是一例。另一方面,赵树理对游戏的描写有着阶级视角无法涵盖的“剩余物”,恰恰是“游戏”蕴含着生成新秩序的可能。社会学家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分析道,游戏是根据共同规则将不同孩子扮演的角色有组织联系在一起,孩子将这种组织化的整体内化,成为共同体成员,才成为整体自我[16]。也就是说,游戏并不只是“表象”(representation),作为一种“实践”(practice),它同样形塑着“现实”。
首先上演的是放牛孩子们的游戏。关帝庙中的社戏属于王光祖等人主持的宗族仪式,而山坡上的戏剧则是乡村底层放牛孩子们的创造:“咱们看不上,咱们也会自己唱!”[9]354“兵”“将”的角色安排并无绝对约束力,小胖和鱼则打起来后,张飞和罗成两个主将根本叫不住,“他们起先还画了个方圈子算戏台,后来乱打起来”[9]354。学生们加入后,新的游戏开始酝酿。二和站在山坡上,说迟来的继圣是“害人精”,因此继圣红花夹袄联锁绳的形象,起初便有些滑稽。之后他压扁了铃铛,照例栽赃给学生们。“七个放牛的不受先生管,看见继圣当面扯谎,就挤眉弄眼笑个不止”[9]355,笑声让继圣“无法抵挡”。如果说二和等人是逃荒者的后代,在乡村中无权无势;那么对于山坡上的孩子们来说,继圣才是格格不入的外来者。
十二个孩子们合了伙,重新讨论玩法。放牛孩子们掌握着主动权,小胖提议到沟里耍水,多数人主张玩学生们并不熟悉的“水汪冲旱汪”,小囤则为他们解释规则。游戏分组并不照搬现实,而是基于人数与实力进行了较为公平的考虑,并将坚持“身份”的继圣排除在外。四个学生和铁则、鱼则六人在上水,剩下四个放牛孩子在下水,喜宝们一心要和小囤们赌胜,生怕六个人输给人家四个人,新的认同短暂生成。此后,继圣试图干涉游戏,却反遭众人“老牛看瓜”的报复。有商有量、团队协作、公平对决的“游戏”逻辑,冲击着“学校与山坡”的格局,继圣援引自现实世界的地位和权力,在这里部分地失效了。
赵树理将这一可能流于琐碎的“闲笔”置于《刘二和与王继圣》开头,试图唤醒深藏于每个读者(尤其是农村读者)心中的遥远记忆,那个“张飞打罗成”的画面,同样长存于他的心头。他在《戏剧为农村服务的几个问题》中写道:“记得我小时候去驮煤,走过两个河滩,三五个小孩就你扮罗成,我扮张飞打起架来,这就和我小时候看戏联系起来,剧中人对我起了作用,这就是戏剧潜移默化的作用。”[17]作为一个包孕性的场景,“游戏”揭示出各种可能:对传统文化的挪用与盗猎,放牛孩子与学生的融洽相处,对现实秩序的拒斥,平等的商量与协作……这是乡村自然生长出来的逻辑。当赵树理饱含深情地书写这一场面,兴致勃勃地介绍何为“老牛看瓜”时,他的确相信这一逻辑能够作为互助劳动的参照,帮助解决从“翻身”到“翻心”的问题。
但仅仅如此,便够吗?游戏“成功”了,同时也“失败”了:它联结了放牛孩子与学生们,却未能将继圣纳入儿童共同体中;破坏游戏的继圣遭到“老牛看瓜”的惩罚,其中蕴含的暴力、侮辱与驱逐,一来并非赵树理真正赞同的做法,二来最终导向了继圣对二和的报复。儿童的游戏,只存在于远离打麦场与关帝庙的山坡上(这又是一个空间隐喻);短暂的平等与协商,无法改变凝滞时间中乡村的权力格局。“农民”主体性的建立,绝不能简单地在过去中寻找依凭。
共同游戏“失败”了,那么在“年头腊月黄沙沟搞群众翻身运动”之后,在区上会议带来了新消息之后,共同劳动会“成功”吗?可以想见的是,如果小说继续,赵树理将着手解决农民“翻身”不彻底、传统精英借文化资本占据优势地位以及互助组“自流”的问题。而在这些具体的问题背后,则是赵树理对“新人新事”如何写、“农民”主体性如何建立、农村如何“组织起来”的关切。“也算翻身”,何以“翻心”?独自留在山坡上放牛的二和身上,或许就有着成长为“新人”的可能:他从小顾家,为王家放牛之余不忘为自家看田;他有组织能力,在“张飞打罗成”的游戏中管分拨人;不论童年抑或青年时代,他都是小说中唯一试图和王家“说理”的人。小说第五章结尾,区上会议带来了新消息,在赵树理未写出的部分,二和自发的“说理”激情与传统的人伦考虑,结合外来的革命伦理和互助组的“算帐”逻辑,将会唤起农民的“自愿”情绪,并让以继圣为代表的“地主”心服口服。届时,黄沙沟的空间秩序将与时间同步;乡村自然生长的“游戏”逻辑涤除了“暴力”与“驱逐”,汇入新的集体伦理之中;涵盖了阶级光谱的“农民”主体性,也将在“翻心”之后生成。
注释:
①此前已有论者关注赵树理作品中的时间与空间。比如罗岗在《回到“事情”本身:重读〈邪不压正〉》一文中,重点探讨了《邪不压正》里“农历纪年”“民国纪年”“公元纪年”所蕴含的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与“三重道理”的交织。贺桂梅在《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中,谈到了《三里湾》的时间与空间叙事,指出小说一方面勾勒出了三里湾基于稳定的空间构成和时间惯例的内在运行方式,另一方面又从这种传统的内在视野出发,呈现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及其现代的历史新事务如何出现并改变了乡村的基本格局。
②皮埃尔·布尔迪厄将人的资本区分为经济资本(financial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三大形态。经济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身体化的(embodied)、客观化的(objectified)、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其重,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个人的审美趣味、学识教养、风度技能等,它是一套培育而成的倾向,通过社会化而加以内化,附着在个人的身体上,可以通过积累而习得,但是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传承。家庭背景和教育是文化资本的两大主要源泉。教育和经济购买力能修补的只是一部分文化资本,家庭背景的因素使得社会化的差异最为根深蒂固。
③在《三里湾》中,“文化”和“劳动”均是范灵芝择偶的标准,二者孰高孰低,对“文化”的偏重又是否会导致农村青年的异化,也成为赵树理后期创作的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