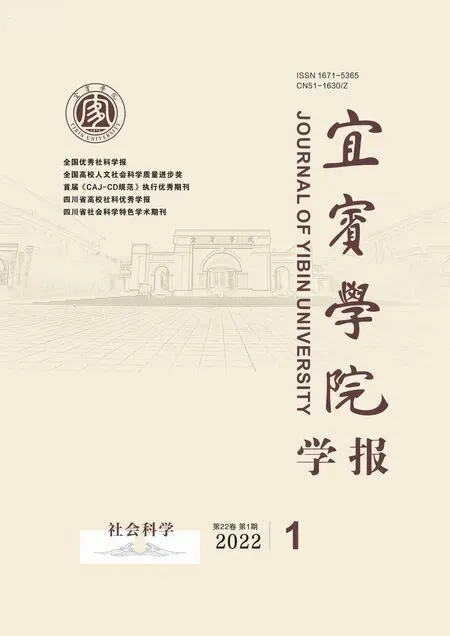从印证到佐证:性侵案件证明的困境与出路
林慧翔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近年来,随着恶性性侵案件频发以及“第一号检察建议”的出台,无论是实务界还是学界,都开始重点关注性侵案件证明难的问题。从立法规范来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高法解释》)第143条规定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不利被告人的证言,需要有其他证据与之相互印证,才可作为定案依据。根据该规定,性侵案件中被害人作为与判决结果有利害关系并且不利于被告人的证人,其证言必须要有其他补强证据与之“相互印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然而,从司法实践证据收集角度来看,性侵案件有其独特的证据特征:其一,性侵案件往往呈现“一对一”局面,即被害人指控性侵行为而被告人辩解无罪,除了双方当事人再无第三人或监控录像能够完整证实案发过程;其二,多数性侵案件案发时间晚,关键性物证毁损灭失严重;其三,言词证据多为传来证据,证明力有限。将证明要求严格限制在《高法解释》第143条规定的“相互印证”,必然会导致部分案件处于追诉不能的困境。
对此,不少学者和司法工作者主张加强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辅之以品格证据、报案经过等证据加以证明[2]。对于旨在提高证言可信度而不直接作用于案件事实的证据,可以称为“佐证证据”,区别于直接补强案件事实的“印证证据”[3]。在穷尽现有侦查手段都无法获得印证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时,通过佐证证据补强被害人陈述真实性并以此作为追诉犯罪的根据,具有现实合理性。结合当前司法改革大背景,在性侵案件中引入佐证证据补强证明方法具有现实可行性。
一、我国性侵案件佐证补强适用现状
从当前司法实践来看,在缺乏被告人有罪供述的情况下,法官极力寻找能够印证案件事实(犯罪行为、被告人)的补强证据,包括在被害人体表、衣物提取到被告人DNA信息,经被害人转述而知悉案情的证人证言,被害人伤痕鉴定,双方聊天记录,陌生人犯罪案件中强调有辨认笔录。当未有其他证据“印证补强”时,单靠增强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佐证证据不足以认定案件事实,无论佐证证据的数量有多少。在“李振江强奸案”①中,控方从多个角度收集了指控证据:被害人陈述、案发时大声呼叫、三份案发后的目击证言“被告人光着身体,被害人哭泣且衣着凌乱,未穿内裤(手攥内裤)”、被害人辨认、案发现场凌乱程度、案发后立即报案、被害人无陷害动机。然而,本案法官认为送检物证鉴定意见“未检出人精斑”及诊断证明书“被害人外阴未见明显异常”,未能印证证明“性侵行为发生”,导致“被害人孙某相关陈述内容得不到其他证据印证”,最终判决被告人无罪。
诚然,印证补强有利于减少“孤证定案”隐含的错案风险。从性侵案件本身性质来看,被害人作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明显利害关系之人,其证言可信度存疑。在某些性侵案件中,被害人或出于恶意,或事后对自愿进行的性行为感到羞耻、后悔而提出虚假控告,运用印证补强可以保护被告人免受不真实、不诚实或者恶意的控告。除此之外,性侵案件由于其隐蔽性极强,在追诉难度增大的同时,被告人同样面临着难以辩解的难题。正如十八世纪英国法学家马修·黑尔爵士所述:“‘强奸’是一种很容易被提出、很难被证实、更难被辩解的指控,尽管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被告人。”[4]635-636然而,高要求的追诉标准必然会导致一部分案件处于“追诉不能”的状态,在防止“错判”的同时也导致了部分真凶被“错放”。根据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统计的强奸罪案件审结数量,每年至少审结两万多起强奸罪,属于高发犯罪。但是另一方面,强奸案件出罪率远高于全部案件的平均水平②。出罪率高意味着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更难被追诉,有更多受害者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讨回公道”。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一味强调“印证补强”势必会加剧两种不良后果:要么放纵犯罪,要么采取一些非正当方法获取甚至伪造印证证据。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对我国司法环境造成严重伤害。
二、性侵案件证明难题的出路——引入佐证补强证明方法
我国印证补强的失灵说明了在面对因案件本身特殊性导致“欲取证而不能”的此类“一对一”案件时,司法审查的重点应当转向于定案证据的“质”,而非一味局限于追求证据“量”。其中,对定案证据“质”的审查要求引入佐证补强证明方法。佐证补强证明方法,是以被害人陈述(主证据)为核心,以佐证证据“单向”补强主证据真实性,在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对主证据的合理怀疑时,以主证据单一证据定案的证明方法。当前,可以试点引入佐证补强证明方法以破解我国性侵案件的证明难题,同时相关司法改革措施也为此提供了可行性环境。
(一)性侵案件引入佐证补强证明方法的必要性
1.有利于打击犯罪,解决印证补强潜在的司法僵化问题
从域外角度看,多国在面对“证据短缺”的性侵案件问题上都引入了佐证补强,强调对被害人证词本身进行补强。早在19、20世纪,英美法系国家严格限制性侵案件补强证据范围,补强证据是一种“特殊的证据”,需要涉及被告有罪的要素(犯罪行为,被告人),仅仅用于提高被害人证词可信度的证据不属于补强证据③。但是随着追诉难度的增加[5]以及补强规则操作的技术化[6]1-19,英国《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明确废除了性侵案件补强要求,随同废除的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废除了补强要求意味着陪审团可以直接以被害人证词作为定案依据。在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陪审团充分审查其所能接触到的所有证据,包括被害人出庭作证时的表情、神态、行为举止,医学检查或物证,被害人前后行为的变化,未成年人关于性知识的异常了解,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机会,被告人先前不良品格证据以及专家关于被害人心理、精神方面的证言等[7]。凡是可以佐证言词证据可信度的并且具有可采性的证据,都可作为补强证据使用。例如在1980年Fitzgerald v.United States一案中,法官认为证人作证看到被害人“哭泣……跑到她的房间”以及“案发第二天告诉朋友”这些证据都足以用于补强被害人的证言。最终在仅有被害人陈述这一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判决被告人有罪④。
不同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者认为证明犯罪所需证据的最低数量和质量与其整体语境有关,应当交由法官视庭审情况而自由裁量,裁判者既可采取“印证证明”方式,也不排斥在“内心确信”时以孤证定案。在审查性侵犯罪等“一对一”案件时,裁判者采取总体评价法,必须仔细考察所有可能影响自由心证的因素。例如在一个性虐待案件中,最高法院撤销了初审法院的判决,原因在于“原审法院还没有查明传闻证人据以相信小女孩说真话的具体情节(如被害人向他们倾诉苦衷时的言行举止)”[8]212-224。
可见之,尽管世界各国在诉讼构造以及具体的诉讼制度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在面对证据短缺的性侵案件时,都倾向于引入佐证补强证据,补强规则从原先简单的“数量规则”转向更为灵活的判断言词证据可信度规则,避免了人为限制补强范围导致的司法僵局。事实上,是否引入佐证补强证明方法是司法价值权衡的问题。当正义的天平向被告方倾斜时,严格适用“印证补强”有利于防止错判,但是同时也以牺牲被害人合法权益以及社会稳定为代价。当前我国所面临的性侵案件证据收集难题与域外各国相似,在追诉职能与被告人权利之间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在仅有“被害人陈述”这一核心证据时,通过佐证补强证明方法审查被害人证词真实性,既能降低仅凭单一证据定案的风险,也有利于打击犯罪,实现追诉犯罪与保障被告人权利二者之间的平衡,解决印证补强潜在的司法僵化问题。
2.探索“孤证定案”的可行路径
对于性侵案件国内有学者主张引入“自由心证”证明方法,采取“内心确信”证明标准[9]。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我国司法改革前进的方向,逐步从注重证据“外部性”转向注重法官心证“内省性”,充分尊重法官自由心证对案件的认定。但是完全交由法官自由心证需要完整的配套措施,包括法官对判决书的详细说理义务、提高司法公信力等等,对此我国司法改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司法实践中囿于定案证据数量要求,以及对“孤证定案”可能带来的错案风险的担忧,基本上排除了纯“自由心证”的做法。从人类认知规律来看,对于某个事物的准确认识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手段或其他辅助证据。例如,对于“长”的概念需要有“短”的物品作为对比,或是有明确的“长”的标准。言词证据的“真”“伪”辨析亦是如此,或是有明确的客观事实作为客观标准,或是通过其他证据对比得出相对标准。无论哪种情形,在诉讼意义上都离不开证据,通过辅助证据去增强或削弱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单靠一份言词证据而无其他辅助证据,犹如只给裁判者一根棍棒要求其判断“长”“短”,难以排除裁判者内心的“合理怀疑”,并且纯粹依赖于经验法则免不了会出现“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混乱场面。当前解决裁判者内心确信“有罪”但证据不足的难题,更为合适的选择为扩大补强证据的范围,将“佐证补强”纳入其中,通过外部审查“佐证证据”证据能力以及对主证据的证明力,逐步加强内心确信,在被害人证词经佐证补强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时,认定被告人有罪。相比起纯“自由心证”证明方法,佐证补强证明方法保留了外部审查的特点,通过对外审查佐证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力,法官心证形成历程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视化”,一定程度上既满足了客观主义的要求,也有利于监督心证的合理性,避免直接采用“内心确信”证明标准可能产生的司法混乱局面。
(二)性侵案件引入佐证补强证明方法的可行性
性侵案件等“一对一”案件证据收集难并非近几年才出现的问题,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证据收集难题从一开始就存在,但是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出现改革的趋势。究其原因,并非裁判者未曾意识到佐证证据的重要性,而是裁判者所处的司法大环境尚不足以支持其采信佐证证据。以动态的、主观形式存在的佐证补强证明方式的引入,需要诉讼条件的支持。具言之,不仅需要初审裁判者对事实认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还需要裁判者有机会对被害人察言观色,再者需要考虑如何减少缺乏统一标准的“佐证补强”适用之后可能会带来的司法混乱问题。随着近几年“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引入佐证补强证明方法的司法环境日渐成熟。
1.程序条件:庭审实质化背景下证人出庭作证情况
从司法实践来看,佐证证据主要包括被害人陈述时的神态、言行、举止,被害人是否因回忆起曾经的经历而心生恐惧、哭泣等动态证据,被害人案发后是否立即选择报案,是在何种情况下向第三人转述受害经过,报案是否自然、正常,双方先前是否存在矛盾,被告人先前不良品格,尤其强调具有特殊行为模式的相似行为证据的运用。不难看出,绝大多数佐证证据属于“主观证据”,需要裁判者通过感官感知去了解、审查证据真实性,这就需要被害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我国司法实践长期依赖于书面证词,导致证人出庭作证率不高,但是该情况随着2014年“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落实逐渐得以改善。从各地区示范庭证人出庭作证情况来看,较之以往证人出庭率显著提高,其中不乏有被害人、鉴定人等关键证人⑤,并且出庭证人的采信率也在逐步提升⑥。相比起庭前证人证言,被害人出庭作证一大重要作用在于裁判者可以直接观察到证人陈述时的言行举止,包括眼神闪烁、语言流畅程度等,直接影响裁判者对证人证言可信度的判断。随着“庭审实质化”诉讼改革的推进,未来可以将申请关键证人(如被害人、目击证人)出庭作证视为被告人质证权的一部分,经辩方申请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应当排除书面证词的适用。
2.主体条件:“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的权威性
构建佐证补强证明方法必须以加强初审裁判者对事实认定的权威性为前提,只有在初审裁判者敢于遵循“内心确信”而不需承担司法责任时,动态的、富有主观色彩的佐证补强才有适用的空间。对此,近年来试点改革的“人民陪审员”制度逐步向此方向靠近。根据2018年《人民陪审员法》的规定,在重大复杂的案件中引入人民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共同审理,其中“3+4”七人大合议庭配置模式确保了人民陪审员发挥着实质审判作用。相比起职业法官,人民陪审员在加强裁判权威性方法发挥着重大作用。首先,人民陪审员采取“随机抽选”方式确定,避免了非法律因素对裁判者形成干扰。其次,人民陪审员不事先阅卷,对案件事实、证据的认定“形成于法庭”,减少了庭外证据的适用,提高了庭审证据的权威性;再者,人民陪审员基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以及逻辑法则做出裁判,难以如同职业法官逐一审查证据是否相互印证,是否满足补强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陪审员裁判方式更接近“自由心证”。当前“适格”案件中人民陪审员参审率高达将近90%[10]。也就是说,除了职业法官“独任”案件外,目前绝大多数案件都引入人民陪审员审判。随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贯彻落实,我国司法证明模式有望从追求客观主义的“印证模式”逐步转向基于逻辑与经验的“自由心证”模式,逐步提高裁判者对事实认定的权威性。
3.司法条件:刑事指导意见的完善
引入“佐证补强证明方法”不可避免的一个难题在于如何平衡“自由裁量”与“维护司法统一”二者的关系。一方面,佐证证据以主观证据为主,对证据的审查认定很大程度上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但是另一方面,“司法统一性”要求避免法官个人素质、认知带来的司法不确定性。从近年来最高院、最高检主导的“刑事指导案例”改革来看,目前我国司法实践正努力以“刑事指导意见”形式缓解二者矛盾。以最高检发布的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⑦为例。最高检在本案中以“要旨”形式明确提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陈述稳定自然,对于细节的描述符合正常记忆认知、表达能力,被告人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结合生活经验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能够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可以认定案件事实。”该指导案例不仅明确了“佐证补强证明方法”的可行性,同时也为“如何运用”提供了明确指导意见。随后,各地法院根据该指导案例纷纷做出相应调整。例如黄某权强奸、猥亵案⑧,广西南宁检察机关认为“该案证据状况与最高检发布的第11批指导性案例高度相似”,依据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抗诉将无罪改判为十二年。刑事指导意见在保留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规范了裁量权的行使,对于正确适用法律以及统一裁判标准具有重要的指导、调解作用,避免了佐证补强可能带来的司法混乱状态。
三、我国性侵案件佐证补强证明方法的构建
性侵案件佐证证明方法的具体构建,需要从证据法角度深入剖析此类佐证证据本身应当具备的“证据能力”,对主证据的补强程度以及具体证明方法。此外,相比起严格补强规则,佐证补强仅增强了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案件核心事实仍是“孤证”,不可避免会增大“错判”风险。对此,需要完善相应配套制度,以消解或降低佐证补强存在的错案风险。
(一)佐证补强证明方法的具体构建
1.佐证证据的证据能力要求
英美法系国家以证据可采性规则来限制佐证补强证据范围,对于不合法或者可能引起陪审团严重道德偏见的佐证补强证据,由法官在庭前审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我国未规定法官事先审查证据资格制度,但是作为定案根据的佐证证据,同样必须具有证据能力。通说认为证据能力包含“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三性。其中,合法性强调证据收集程序合法,不得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客观性于“印证证据”而言强调“必须是伴随着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而遗留下来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事实”。[11]53但是对于佐证证据而言,多数佐证证据属于动态的、主观性证据,以“客观性”作为证据能力要求显然不合适。对此,建议以“可信性”作为佐证证据资格。相比于不以人之主观意志转移的客观标准的“客观性”,“可信性”保留一定的主观判断成分,在经过“真”“假”对比之后倾向于认为佐证证据为“真”。强调佐证证据的“可信性”有助于裁判者对证据进行审查,避免未经审查将虚假的佐证证据错误用于补强被害人陈述。“关联性”是审查的关键,与被害人陈述毫无关联性的材料不得作为佐证证据使用,同时“关联性”也影响着单个佐证证据对于主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我国立法未对关联性做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倾向于严格限制“关联性”范围。例如徐亿芳猥亵儿童罪⑨一案,控方出具被告人手机微信qq聊天内容以证明被告人有迷恋儿童的倾向,而法院认为此份证据无关联性并排除适用。对于佐证证据可以适当扩大“关联性”的范围,借鉴《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⑩的规定,凡是“有此证据将比缺乏此证据时更为可能的”,都满足佐证证据“关联性”要求。
2.佐证证据的补强程度要求与具体证明方法
在探讨单一证据定案规则时,刑事证明责任以及证明标准并未随着定案证据数量的减少而降低。相反,即便是定案实质证据仅有“被害人陈述”这一孤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也必须得到满足。因此,佐证证据对于主证据的补强程度必须达到使主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在定案决定性证据仅有被害人陈述时,对被害人陈述持有“合理怀疑”时必须依法判决被告人无罪。
至于佐证证据的具体证明方式,笔者建议借鉴德国“否定性假设检验法”,通过假设被害人陈述为“假”,再用佐证证据去检测是否与该假设矛盾。“否定性假设检验法”与惯用的评价方法相反,一般论证方法侧重“建构”,在主证据这一核心支柱上不断添加佐证证据加固,从而构建起事实认定大楼。但是“否定性假设检验法”则侧重于“解构”,先假设主证据为“假”,将其拆解成零碎的小命题,再通过一个个佐证证据予以反驳,进而重新构建起新的事实认定大楼。相比起一般的“建构”过程,“解构”成零碎小命题时放大、细化了“合理怀疑”,更能凸显出主证据存在的问题。当前“解构——建构”的证明逻辑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验证适用。在人民陪审员参审的七人合议庭中采取“问题列表制度”,由审判长将有争议的事实问题逐项列举,细化分解成各个具体问题,再由人民陪审员仔细审查各个具体问题,最终得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结论。“问题列表制度”的论证方式实为先“解构”再“建构”,与“否定性假设检验法”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从试点结果来看,当前试点取得较好的成果[12]。
(二)佐证补强证明方法配套制度的完善
1.原则上保障被告人质证权
英美法系国家废除了补强规则的重要前提在于保障被告人对质权,被告人有权当面质问对己不利证人,通过交叉询问审查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此外,《欧洲人权法院》第6条明确规定了被告人享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即被告人有权质证对己不利的证人,也有权传唤有利于己的证人。性侵案件中的被害人作为于被告人不利的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来自辩方的询问,除非被告人已于庭审前或庭审外行使了该权利,或被告人的防御权已被充分补偿[13]。当前我国未将证人出庭视为被告人质证权内容,证人是否出庭作证仍需经过法院必要性审查,唯有在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的情况下,证人才必须出庭作证。从审查证据真实性的角度考虑,建议将作为定案依据的被害人出庭作证视为被告人质证权的一部分,经辩方申请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应当排除被害人书面证词的适用。与此同时,我国应当加强对被害人出庭作证保护,尤其是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避免受到二次伤害。借鉴域外相关措施,保障措施包括禁止被告人直接对被害人发问,以及使用矫饰等保护手段。
2.有条件的情况下引入询问时同步录音录像
尽管被害人出庭作证有利于审查证言真实性,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被害人出庭可能会遭受“二次伤害”。对此,多国允许例外情况下适用传闻证据。同时为了审查证词真实性,对于不出庭作证的被害人多国均规定了审前证言录像制度,在法官、辩护人共同参与的情况下以录音录像形式记录证人审前证词,个别国家允许被告人在场[14]。考虑到我国性侵案件中多数被害人为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健全,出庭作证可能会遭受“二次伤害”,或者在庭前取证环节经诱导容易改变原先的记忆,目前司法实践中已有案例尝试引入被害人询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例如乔明进强奸罪一案⑪,由于被害人辨别能力有部分缺陷,询问过程中引入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视频显示被害人能够辨别是非,能够明确表达,对于民警询问的问题,没有作出夸张或带有幻想性的回答。”由此作为审查被害人证词真实性的根据。借鉴该案例,对于作证能力欠缺的证人(例如未成年证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为避免遭受“二次伤害”而不愿意出庭作证的被害人,可以通过引入询问时同步录音录像,记录被害人陈述时的神态、言语、行为举止,以此作为审判的依据。
3.加强判决说理义务
加强判决书说理是我国司法改革中重要的一环,通过在裁判文书中详细说明佐证证据采纳情况以及具体理由,有助于防止法官滥用自由心证。从域外角度看,大陆法系国家对裁判者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判决说理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无须理由判决,“科层式”审级结构模式下的大陆法系法官需在判决书里详细写明判决理由,详细分析事实、证据的采纳情况。对于违背经验和逻辑的判决,二审法院有权在审查后予以改判。面对证据短缺的性侵案件,法官的说理义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直接取代了补强证据的作用。例如尽管荷兰立法明确规定了“孤证不能定罪原则”,但是在法官拒绝严格遵守最低证据数量要求时,最高法院也倾向于要求法院说明判决理由,而非裁定驳回原审判决[2]。当前我国判决文书说理存在“重事实说理,轻证据说理”“‘三性’论述缺失”“说理笼统”等问题,判决说理制度有待完善[15]836-849。对于以动态形式存在的佐证证据,法官应当尽可能详细描述证据内容,阐述佐证证据与被补强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对主证据的补强程度。结合“否定性假设检验法”,法官在判决书中将被害人陈述明确分解为具体的待证问题,再详细论述在案的佐证证据是否足以补强该待证问题为“真”,最终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通过判决说理,有助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进行监督,及时纠正下级法院存在的错误,从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4.限制二审对案件事实的改判权
佐证补强证明方法的适用前提在于裁判者的“亲历性”,唯有亲身经历才可深入感知动态的、主观的佐证证据的证明力。但是从审判模式来看,我国采取“科层式”审级结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享有监督权,下级法院所做的裁判以书面材料形式提交上级审查,而上诉审查一般都采取书面审查形式。这就导致以动态的、主观形式存在的佐证证据无法完整地再现于上级审查中,加之我国不完善的判决书说理制度,一场雀跃的、声情并茂的初审庭审经书面化表述极有可能变为仅有“被害人陈述”这一单薄证据,佐证证据的证明力严重降低甚至荡然无存。此时初审裁判难逃经由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命运,严重打击初审裁判者适用佐证证据证明方法的热情。结合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庭审实质化”以及“人民陪审员”改革,笔者建议限制二审对案件事实的改判权。在一审严格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应当重点审查审判程序是否合法,问题列表内容是否合理,人民陪审员职权是否受到保障等内容。二审以“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为理由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必须符合经验法则、逻辑法则,不得单纯以二审法官的心证直接取代初审裁判者的心证,并且二审应当详细说明改判或发回重审的理由,逐步强化初审裁判者对事实认定的权威性。
结语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过分强调“印证证明”,尤其在实物证据薄弱的案件中,强调被告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的相互契合,以减少言词证据的不确定性、虚假性。然而,过分强调印证证明必然会导致部分案件追诉不能,尤其是缺乏被告人供述的性侵案件,如何审查被害人陈述真实性是目前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佐证补强证明方法突破了“印证证明”的局限,将情态证据、破案过程、品格证据等佐证证据纳入补强证据范畴,解决了该类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印证模式僵化问题,有利于打击犯罪。结合当前庭审实质化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以及刑事指导意见的进一步完善,推行佐证补强证明方法具有现实可行性。通过完善被害人作证时同步录音录像、加强判决文书说理等相关配套措施,为佐证补强证明方式的落实奠定基础。
注释:
① 李振江强奸二审刑事裁定书,(2017)冀10刑终60号。
② 参见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中国法律年鉴2013-2018年无罪判决数据,年平均无罪判决率约为0.08%,而强奸罪的年平均无罪判决率约为0.14%。
③ R.V.Baskerville,All ERRep 38.(1916)。
④ Fitzgerald v.United States,412 A.2d 1.(1980)。
⑤ 从对成都中院示范庭调研结果来看,示范庭证人出庭率是对比庭的20余倍,其中示范庭关键且争议证人将近占50%。参见李文军《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成效与路径研究——基于实证考察的分析》,载于《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5期。
⑥ 2016-2018年山东法院审结的证人、鉴定人出庭案件中,62.5%的证人出庭证言被法庭采信,71.3%的案件承办人认为证人出庭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90.2%的鉴定人出庭案件相应鉴定意见被法庭采信。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刑事案件证人、鉴定人出庭实证分析》,载于《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⑦ 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检例第42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19年第1号,第14-17页。
⑧ 2019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之四:黄某权强奸、猥亵案,参见北大法宝,【法宝引证码】CLI.C.93907527。
⑨ 徐亿芳猥亵儿童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8)鄂1083刑初162号。
⑩《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规定:“有相关性的证据指具有下述盖然性的证据,即任何一项对诉讼裁判结案有影响的事实的存在,一若有此证据将比缺乏此证据时更为可能或更无可能。”
⑪ 乔明进强奸罪二审刑事裁定书,(2020)川01刑终2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