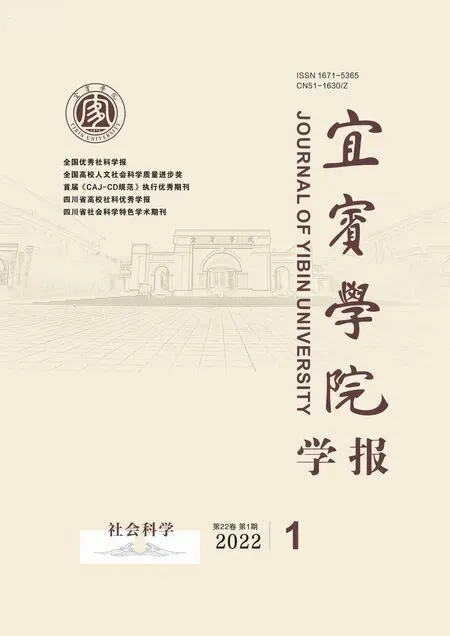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古代文学教学路径探析
汪舒旋
(宜宾学院文学与音乐艺术学部,四川宜宾 644000)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其教学内容和思路方法都很成熟。但目前面临教学内容过多和教学方法单一的问题。综合考察这两个问题,多与教学局限在纯文学的思路中有关。如果从“大文学”观的角度丰富教学思路,以引导式教学改变灌输式教学,这两个问题可以得到改善。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学者使用跨学科的“大文学观”的方法对古代文学进行研究。而把“大文学观”放置古代文学教学中,已有学者进行尝试,例如加入宗教学的内容和视角、整合文学类课程教学等。笔者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出发,对目前古代文学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思考,并在教学实践中尝试改进,探讨于下,以求教方家。
一、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般按照古代文学史教材,以先秦至清中期文学的历史顺序讲授文学史,配合各时代的文学史选读相应的文学作品。授课方法大多以教师讲解、学生阅读为主。这种教学内容和方法,使课程内容丰富、逻辑清晰,课程成熟,新手教师也能较好地完成教学,保证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达标。但目前古代文学教学面临两个实际问题。
第一,教学内容过多。中国古代文学历时数千年,作家作品繁多,有些高校设置的课时在300个左右,尚觉课时紧张。如Y学院所设古代文学课程,过去是216个课时,近两年经过专业培养计划调整,减为192个课时。因为Y学院校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要教学目标,需要增加实践类课程的课时,导致古代文学课时减少。这样的调整虽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的定位与要求,但也给课程教学带来了问题。过去课程内容已是选重点进行讲解,教学进度较快,而现在课时减少,怎样在重点内容中再挑选重点?若再加快教学进度,则会影响学生对基本知识的学习。因此,教师必须在重点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方式的转变上下功夫。
第二,信息化时代,纯知识讲授的方法不适合教学需求。在当下信息化时代,学生很轻易就能从网上获取各种知识,具体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上,从网上能检索到作者的生平经历、作品原文,进一步还能查到作品的注解和评论、作者的创作风格、文学流派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和课程的基本内容,学生能通过网络轻易自学,甚至还能在网上找到不同版本的文学史教材进行自学。如果在课堂上,教师再一味进行单一知识的讲授,容易给师生都带来教学的疲惫感和枯燥感。不过,新的问题是,网上这些爆炸式的信息,学生应该如何去选择、鉴别?单纯的知识灌输也无法教给学生判断专业知识的能力。
结合以上两个问题,古代文学教学可以从教学方法的改变入手,课程内容的选择则配合教学方法来进行。信息时代对教师有知识教学上的挑战,却也促使教师放弃单纯知识灌输的教学法,回到对学生学习方法、专业技能的培养上来,古人早已强调“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学的本质是技能的培养。尤其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面向的学生,刚结束高中的知识性学习,需要逐步了解、掌握大学的专业学习方法,对专业的话语体系、基础常识有充分的认知,培养专业的思考力、判断力,这样才能有效地自学专业知识、检索专业信息,并能够鉴别网络检索出的信息的真伪,正确运用专业知识。因此古代文学课程可以在教学方式上尝试以学生学习方法、专业技能的培养为目标,培养学生专业的学习思路、专业信息检索的能力、专业信息鉴别和运用的能力,并为想要进行继续深造的学生提供基础的学术研究训练。
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除了挑选特别重要的知识点进行讲授外,其他内容则根据教学方式的选择而进行详略的安排。如下文所举两个案例,从内容上看都是古代文学的重要知识点,但教学方式有别。《诗经》教学案例着重培养学生阅读、分析原始文献,进行理论探讨的能力,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学进度相应较缓。词曲教学案例则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与音乐艺术感知力,教师的理论讲解简洁,以文艺欣赏为主,教学进度相应较快。
而在教学方式的选择上,结合古代文学学科研究,应重视跨学科思维的运用,例如引入史学、文献学、音乐学等研究法。将跨学科的思维和方法运用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是否恰当?我们可以从学科研究方面对此可行性进行探讨。
二、大文学观与古代文学教学
跨学科的概念,首先要在“学科”的概念成立下,才能成立。而我们对于学科的理解,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概念,为我们今天大学课程设置沿用。正如学者所说:“跨学科是在近代学科分类基础上,进行的交叉学科研究。跨学科一词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纽约出现,指关于或涉及两门、多门学科的研究”[1]。而在我国,文学学科中跨学科的研究法早已应用,为学者们所公认的是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如其名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文学与史学结合的典范。
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名作增多,例如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皆把唐代科举的历史问题与文学发展结合起来研究。此后唐代文学研究者也有意识地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因为“唐代文化中政治、宗教、绘画、音乐、舞蹈乃至于地域、家族等等均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学者们不仅把文学与政治、历史、艺术、宗教结合讨论,还扩展到建筑、医药、园林等学科。而就“中国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而言,又与“大文学”这一观念密切相关。
21世纪以来,学者们逐渐提倡“大文学观”,最具代表性的是杨义先生所说“文学三世”,他认为“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2]。这种大文学观不仅仅是文学史观念问题,“它的实际指向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转型的命题”[3]。的确,高校学术研究的风向,应当及时应用到教学中,高等教育应该具备与专业研究随时接轨的能力,这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基础教育的一大要点。
已经有学者切实地将这样的“大文学观”用在教学中,并进行了教学理论上的总结和反思。例如在本科的古代文学教学中加入道教文学内容。由于道教文学的教学会涉及“宗教、心理、哲学、物理化学等多学科知识”[4],因此“以大文学的视角审视道教文学……一方面扩大中国古代文学的涵括面,一方面丰富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与内涵……道教文学参与到高校本科教学中,可以扩充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4]。
还有应用大文学观对高校文学专业各类课程进行整合者,他们认为“文学教育的理想化状态应当是一种‘大文学’教育,多学科的联动与协调能够充分整合文学类课程的教学资源……相对应的是‘大课堂’理念”[5]。根据这样的观点,不仅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应该使用大文学的教学,在整个文学专业中都应建立大课堂的教学。另外,学者们也注意到把跨学科思维应用到中学的文言文教学里,让文言作品思想内涵更深刻、全面、真实展现[6],这将大文学观的教学理念扩展到了基础教育。Y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属于师范类,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因此本科时期大文学的专业思维训练,或能够帮助学生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扩展教学视野,优化教学内容。
运用大文学的跨学科思维进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即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大文学观的跨学科研究,这符合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一切文献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它促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开放型、宽泛型结构”[7]“西方观念源于西方文学经验,往往与中国经验存在错位……轻易套用西方观念,也就很难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很难从本源上发挥中国文学思维和理论概括的优势”[2]。实际上,“古代文学的涵括面,远大于今天对文学的认知”[4]。
因此“文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沟通的”[1]。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即“把作品文本和作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统统打成一片……作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7],所以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也“必然地和其他各个学科……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7]。这就回归到西方“学科”概念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文学的范畴内。
当然,大文学观的跨学科研究法,必须要注意文学的本位问题。罗宗强先生认为,清理史料、研究历史背景,“一定要回到文学上来。假如不回到文学本身,那就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历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8]。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也是如此,必须坚持文学的基本概念传达、基础作品学习,锻炼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能力,其他学科的思维、方法学习,都是为了文学的专业理解,不可本末倒置。教学实践中,这是一个度的把握,“回归文学本位,并不意味着要回归‘纯文学’观念……应该坚持‘文学性’标准,回到‘文学’本位的审美立场”[9]。
显然,在大文学观念影响下,“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仅是在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内部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而且始终是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7]。显然,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必然会运用到史学、经学、文献学的知识与方法。
具体而言,先秦文学“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对于此类作品……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互为参照,进行比较”[10]。而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10]。文学家还兼通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故而如“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10]。
中国古代文学还有结合文学、音乐表演的文体,例如词、曲“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10],“词的本质是配合燕乐而兴起,在音乐与文学关系中才能探讨词的起源”[11]。由此可见,音乐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非常重要的辅助学科。
那么这种大文学观视野下的跨学科思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如何实践?接下来以两个教学知识点为例,探讨教学中如何运用跨学科思维。
三、大文学观的教学应用
《诗经》和词曲,是古代文学中诗歌史的重点内容,《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词曲是古代诗歌主要的诗体之一。二者也是教学的难点,因为《诗经》在传统学术分类中属于经部之学,而非集部之学,集部之学对应今天的文学,而《诗经》所属的经学显然超出文学的范畴,从纯文学角度理解《诗经》的基本概念较为困难;词曲的兴起与其最初的形式,与古代音乐紧密联系,从纯文学角度难以清晰界定词曲。因此涉及《诗经》和词曲的教学,须从大文学观的视角出发,融入经学、文献学、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这样不仅能解决教学难点,还能丰富课程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强学生对专业技能、研究方法的学习。
(一)《诗经》的来源与编订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通常把《诗经》放在先秦文学的“诗歌”部分,因此对《诗经》的解读都围绕着“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个定位。然而,客观地从中国古代的学术和文献分类看,《诗经》位列经部,是经学的核心经典。如果仅从现代的文学概念,去理解《诗经》的体裁、分类、来源、编订、流传、版本、内容性质、写作风格等问题,容易误解或引起争议。
例如在《诗经》的“来源与编订”这一问题上,历来有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三种主要说法,学者们对三种说法有所争议。如果单从“纯文学”创作的角度,就比较难以理解采诗的目的、献诗的活动,更难解释删诗的理由。但若从经学的思想和文献的形成历史来看,会发现这三种说法不仅不会造成争议,还共同体现了经学的政治功能和经学文献形成与早期流传的过程,符合中国传统学术史、文献史的规律。
因此在教学时,需要重点引导学生们跳出“《诗经》只是古代的一本诗集”这种纯文学的思维,向学生简单介绍经学的概念,突出经学的政治功能,让学生认识到《诗经》在古代本质上是一种经学的典籍,反映经学的特点。通过教学引导,能观察到学生被激发了探讨兴趣,开始理解大文学观的思考方式。
在此基础上提出颇有争议的“《诗经》的来源与编订”问题,列出采诗、献诗、删诗三说,但不能向学生灌输三说的内容,而是列出原始材料,引导学生阅读、分析、讨论材料给出的信息。例如下引材料。
材料1:《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12]1123。《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13]4965。
学生通过分析这条材料,得出结论:采诗是中央派人到民间收集诗篇,这两条材料都体现了中央统治者派官员采诗的流程,说明了采诗的目的是统治者通过民间所采之诗来了解民风、民情,以便于治理天下。
材料2:《国语·周语》邵公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4]11-12。《国语·晋语》范文子云:“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14]387-388。
学生通过疏通材料2的文义、讨论后,一般也能得出结论:献诗是地方官吏收集诗篇或者臣下作诗献上,也有专为祭祀而作的诗篇,同样献给中央。天子的各级官吏向天子进献各种文献,其中包括献诗。献诗的目的在于供王者政治借鉴,而臣下也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上的谏议。
学生通过材料分析,自己大概能得出采诗和献诗的含义。学生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已经使用了文献学的训诂法、史学的原始材料分析法。教师在这一过程中,采用引导式教学,做到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跨学科的分析能力。
除了分析能力,对所分析出的结论进行总结,也是学生需要培养的能力。所以还需向学生介绍更多经学中的礼学、先秦政治史常识,最后引导学生总结诗经的采集、编订问题:《周礼·春官》中太师的职责直接决定了《诗经》的形成。太师掌管音律的制度,以此来编制乐曲,这其中包括了《诗经》的配乐;负责王官教学中的《诗》教,这形成了后来经学中的《诗经》思想;负责祭祀、大射等礼仪用乐,这是《诗经》的应用和编订的目的之一。总之太师将采诗、献诗途径而来的诗篇,进行文字和音乐的整理编订,然后用于王官教学和礼仪。
但“删诗”问题比较复杂,因此我们在引导式教学外,还要加上传统的讲解法。给学生讲解是“删诗”的背景,即《诗经》早期的流传:太师整理的《诗经》,是最早期的版本,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季札观鲁国之周乐事件,可知《诗经》编订成文本比较早,但东周王官失守使得《诗经》有散亡、淆乱。同时《诗经》教育也进入到私学中,先秦诸子的文章中多有引《诗经》,可见对《诗经》的普遍学习。这里的讲解内容,也是大文学观的体现,融入了文献学史的阐述。
引导学生阅读分析几条材料:在《论语·子罕》《史记·儒林列传》中都提到孔子曾对《诗经》进行过整理,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论次《诗》《书》”。而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则提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5]1936-1937。
学生由此梳理出孔子对《诗》所作的工作有:第一,统一诗篇的文本,将重复的部分删去。第二,整理《诗》的篇次、分类。第三,整理《诗》的配乐,以使《诗》更好地与乐结合进行唱诵。
尤其让学生们注意到材料中的关键词“去其重”,说明孔子收集到同一诗篇的不同版本,对其进行文字的统一,这符合早期经学文献流传的特点。宋代以来对孔子“删诗”的争论,是因为没有仔细分析文献记载造成的。这就培养了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锻炼学生对材料分析的耐心和细心,让学生体会学术研究的特点。厘清《诗经》来源这种学术争议论题,还能激发学生的学术研究兴趣。
总之在这个案例中,教师尽量减少知识性的讲解,对关键概念作阐述和提示,着重引导学生阅读原始文献、解释材料含义、分析提取关键信息,培养学生探究性的思维;同时补充经学、文献学的常识,介绍经学、文献学的方法,让学生了解多学科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形成大文学观。
(二)词曲兴起的音乐问题
晚唐兴起、至宋代蔚为大宗的词体,金元兴起并影响至今的戏曲,它们与此前的诗歌体裁有什么区别,词曲内部有怎样的差异?如果单从文字来看,例如词中的小令和散曲中的小令,就颇为相似。而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来看,诗与音乐从来密不可分,因此要理解这些新文体的产生和文体特点,必须要结合中国古代音乐史来看。
由于音乐学的专业性和实践性强,这个案例不再采用上一案例中的引导分析式教学,而以讲解和展示(尤其音乐表演展示)为主,重点培养学生的感知力。如在解释同是“合乐而歌”的诗体,词和《诗经》、乐府诗的根本区别时,可以用提问式讲解法:在历史上,合乐而歌的文体并不始于词,《诗经》、乐府诗在早期皆是合乐而歌,那么为什么这些合乐而歌的诗体会形成不同的类别呢?这个问题从音乐史角度来看比较明晰,例如汉魏乐府所配的是清商乐,而词所配的是隋唐时期受西域音乐影响而产生的燕乐,曲调不同,相应的文体的格式、修辞也产生了变化。燕乐是隋唐时代非常流行的一种音乐样式,它结合了中国当时的民间音乐和西域传来的外国音乐,当时被称为“胡夷里巷之曲”。唐代的教坊曲是燕乐的典型,而在唐人崔令钦的《教坊记》中记录的三百多个教坊曲名里,有不少后来都转成了词牌,说明词的形成与唐代教坊曲有直接关系。
燕乐是隋唐时代的流行乐,还以今天流行歌改编翻唱(尤其粤语歌)为例,说明唐五代词是先有乐、后有文,所谓“词牌”便是曲调格式,所谓“填词”便是依曲调填写歌词,这与我们今天根据流行曲调重填歌词的创作很相似,这样结合现实的讲解,能让学生更理解词的音乐特点,能将当下与历史连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
要学好元明清的文学大宗——戏曲文学,也需要了解燕乐的常识。因此在讲解时,注重历史线索的贯通,引导学生根据讲解,总结戏曲乐调的发展,向学生强调“历史感”的思维,让学生认识到:宋元明清戏曲的乐调主要按燕乐的宫调来设置,从燕乐二十八调的宫调基础上发展出词、曲的音乐调式和戏曲上的南北曲声腔系统。从音乐上看,南宋的词乐使用的是七宫十二调,金、元时期简化为六宫十一调,元代的北曲使用的是十二宫调,元末南曲使用的是十三宫调,到了清代南北曲就只用九宫(即五宫四调)。唐代燕乐曲调的传承和简化,深刻影响了词、曲各类文体的发展,各类文体的区别均与音乐上的差异有关。
除了让学生从文学与音乐的双重理论角度学习词曲问题,音乐的感知也很重要。音乐具有演奏的实践性,所以音乐曲调比文辞更容易失传,无论《诗经》还是乐府诗,其曲调在古代就已亡佚。词调也基本都亡佚了,现存唯一完整的宋代词乐资料——姜夔词——集中于自注工尺旁谱的十七首词,有学者整理出不同的演奏、演唱版本。在戏曲方面,尽管北曲杂剧在万历年间成为绝响,但明代最为流行的昆腔至今还在场上演出,明代戏曲主流“明传奇”的代表作《牡丹亭》仍是今天一直上演的剧目,甚至还有青春版《牡丹亭》的创新,以迎合年轻观众的口味。
因此,改变单一的语言讲解法,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姜夔词乐的音频、《牡丹亭》经典选段的视频,让学生结合音乐、表演,鉴赏词曲、讨论评析。这样不仅可以丰富课堂形式,让课堂更加生动,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直观感受词曲的形式和内容的异同,培养一种文学与音乐的审美力、感知力,这是古代文学课程除了理论学习之外,另一重要作用。
此外,音乐、表演的欣赏,还能激发学生自主探索的兴趣。课后学生能通过网络,查阅更多的词曲知识,补充课堂未能涉及的部分。这就将古代文学的学习延伸到了学生生活中,有助于学生良好自学习惯的养成。
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其教学内容是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教学方式是文学史讲解结合文学作品解读,这在各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中具有普遍性。但在实践中,教学一般会因为教师的个人特点而具有特殊性,尤其在课程改革的尝试中,教师根据自己的特长,对教学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个性化的调整,如上所述,教师尝试把文学类课程进行整合、进行多学科联合教学,引导学生养成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思维,加强学生的文艺审美和感知力。
大文学观下的跨学科教学,符合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契合文学研究的方向,能促进古代文学课在内容上的选择和方法上的改进。教师可以把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专长与具体的教学知识点结合起来,进行个案的尝试。例如,研究先秦文学的教师,应该会注意到“诗乐礼一体”这个问题,那么在《诗经》的教学里,是否可以延伸出对中国礼乐文化的探讨,引导学生认识先秦的音乐与礼学思想?研究汉代历史散文的教师,必然知道《史记》《汉书》本身就是历史学文献,对《史》《汉》的体裁分类、写作风格、写作目的、文章选读,必须引入历史学、文献学的概念和方法。还有研究魏晋玄言诗、宋代理学诗的教师,就需要对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思想史、哲学观有充分认识,那么他们在对这些类型的诗歌的产生发展、内容旨趣、风格特色的教学中,就需要史学、哲学的参与。
总之,在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方式上,引入相关学科的基本范畴、核心知识点和学术研究法,并利用多媒体技术,不仅可以丰富教学方法,而多样的教学方法能帮助教师更好地选择教学内容,以解决文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过多、教学方法单一的问题;还有利于拓展学生视野、建立更完善的学科知识体系,进而促进创新意识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