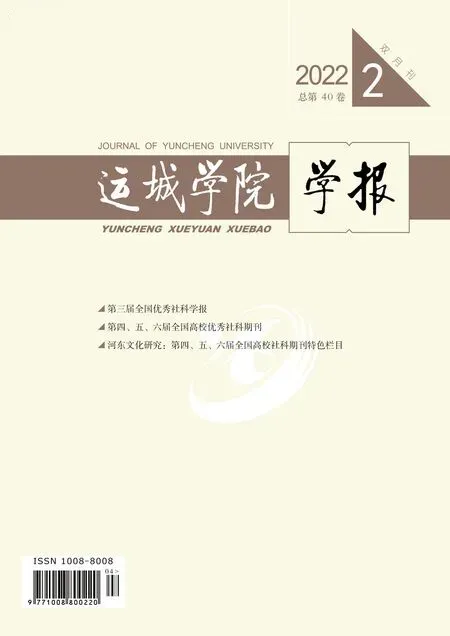《金瓶梅》中“嗑瓜子”的意蕴及作用
任 若 嘉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金瓶梅》一书将视野聚焦于市井生活,它以西门庆及其妻妾、同僚、朋友为中心,以网状结构辐射到整个社会阶层,小到走街串巷卖果子的郓哥,大到权倾朝野的蔡太师乃至最高统治者宋徽宗,其所涉及描写的人物无不极具个性、形象鲜明。书中围绕形形色色的人物,展开了各式各样的场面描写,其中对饮食、服饰描写十分详尽,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明代后期的社会生活。在《金瓶梅》中,作者不厌其烦地对饮食场面进行细致地描写,无论是西门庆与妻妾的日常饮食,还是与官场中人、友人的往来宴请,其中许多场面往往都与情欲密切相关。而瓜子作为日常食用的零食,也经常出现在人物的生活之中,“嗑瓜子”作为一处多次出现的细节,在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嗑瓜子”这一细节描写入手,分析其在《金瓶梅》中的含义以及作用。
一、明清文学中的“瓜子”书写
明清文学中的“瓜子”多指西瓜、南瓜等蔬果的籽粒,而非今日所常食的葵花籽。向日葵虽在明代中期便已传入中国,但是最初的作用仅仅在于观赏,直至清末的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方才明确记载向日葵用作零食[1]。瓜子作为一种零食小吃,在宋元时期便已进入民间日常,成为世俗生活的重要装点。如宋代苏轼在与妻弟王箴的书信中写道:“与君对庄门吃瓜子炒豆,不知当复有此日否?”(《与王元直二首其一》)[2]121又如元杂剧《百花亭》中,正末提着查梨条一连叫卖了许多瓜果名,其中便有“魏郡收来的指顶大的瓜子”[3]231。可见宋元时期,瓜子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吃食。至明清时期,食用瓜子更加普遍,在文学作品中多有提及。在冯梦龙《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刘四妈一见杜美娘的丰富积蓄,心中惊想,自家所养粉头与美娘相比,不过有几文钱在荷包里,“闲时买瓜子嗑。”[4]41明时人胡文焕《群音类选·补卷二》收录郑墟泉【点绛唇·贺节】套曲,其中【寄生草】一支写道,衣冠济楚、花费银钱一逞风流的浪荡游子“将瓜子儿嗑着排门儿混”[5]2518-2519。瓜子成为粉头浪子们喜爱的休闲零食,其在明代世俗生活中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嗑瓜子作为一种大众化的饮食活动,在明清文学的描写中多有着一定的意蕴指向和功能。首先,嗑瓜子在明清文学中往往与女性描写相关,文学作品中,嗑瓜子常作为女性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元代《燕青博鱼》杂剧中,燕和之妻王腊梅与杨衙内有奸,在燕和离家之后,王腊梅等待杨衙内到来时,说白云“嗑些瓜子儿,等着他者”[3]1434,嗑瓜子成为她在等待奸夫到来时的一种消遣。
文学作品中的嗑瓜子不仅是女性打发时间的方式,也是一种特别的细节呈现,展现出女性独特的心理状态和外貌神情。如明代诗人汤尹宾《南中春词》云:“衫薰石叶宿香凝,满槛莺花一袖凭。掩将一袖双齿缝,费来瓜子日三升。”[6]406其中便以佳人凭栏观赏春景、掩袖而嗑瓜子的细节刻画,展现出佳人百无聊赖、令人心倾的风采。又如《红楼梦》第八回写宝玉见宝钗劝说吃冷酒不好,“便放下冷的,命人暖来方饮”,黛玉便“嗑着瓜子儿,只抿着嘴笑”[7]121,活画出黛玉一副含嗔带笑的神情。第六十六回写尤二姐见三姐回护宝玉为人行事,便问“竟把你许了他,岂不好?”此时三姐见有兴儿在旁,不好多说,便“只低了头嗑着瓜子”[8]854。三姐此时的顾虑正在无言之中借嗑瓜子的描写展现了出来。
其次,嗑瓜子这一饮食活动在男女两性的交往之中体现出独特的交际功能。首先,瓜子被用作传达对异性的倾慕与爱意的一种媒介,情人之间时有掷瓜子以示爱的亲昵活动。袁宏道《迎春歌和江进之》云:“青莲衫子藕荷裳,透额垂髻淡淡装。拾得春条夸姊妹,袖来瓜子掷儿郎。”[9]153在美好的春季,少女们身着春装,柔婉动人,将瓜子掷向中意的少年,表达自己的爱意。明代胡文焕《群音类选·清腔卷六》载傅玄泉【南步步娇·男相思】套曲,写男子对情人的思念,其中【北雁儿落带得胜令】一支云:“俺也曾偎着肩把手腕掐,俺也曾隔着人使瓜子打。”[5]2363主人公回忆起与情人的相处,曾经向她掷瓜子打情骂俏。这种爱意的传达还通过赠送给情人嗑好的瓜子来实现。清代项鸿祚《鹊桥仙·即席戏咏瓜子》词云:“相思一点,合欢双剖,掷向檀奴衫里,十三刚是破瓜时,怕里许、人还未有。”[10]51(《忆云词·丙稿》)“破瓜”双关两意,意谓在破身时节,将嗑好的瓜子赠予情人,其中多有郑重之意。又如清末诗人樊增祥《忆饮》诗云:“阁盏时时破瓜子,赠郎犹带口脂香。”[11]1476(《樊山续集卷二十六》)也是以嗑好的瓜子作为一种情爱的表达。
其次,赠送嗑好的瓜子被用作安慰情人相思之情、寄托希望的一种方式。《忆饮》诗中“赠郎犹带口脂香”一句,尚且含蓄,但已然有着身体相亲的隐喻与暗示。清代华广生所辑《白雪遗音·卷二》中收有《瓜子嗑了》《瓜子仁》两支俗曲,写女子将自己亲口嗑好的瓜子仁儿包好,送给情郎。两支曲子都在强调,瓜子是女子亲口所嗑,上面有着自己的唾液。“一颗敌十颗,一颗颗都在奴的舌尖儿上过。”(《瓜子仁》)[12]29“个个都是奴家亲口嗑。红的是胭脂,湿的是吐沫。”(《瓜子嗑》)前者是希望情人吃下自己所嗑的瓜子仁儿之后“切莫忘了我”,后者是为了“保管他的相思病全好却”[12]42。
再次,嗑瓜子在文学书写中成为一种情欲的暗示。《白雪遗音·卷四》所载《玉蜻蜓·弹词》申贵升游庵,寻访心上人尼姑志贞,向志贞说道:“昨日山塘同看戏,你秋波频转为谁来。一把多情瓜子壳,分明召我赴阳台。”[13]44-45前引项鸿祚《鹊桥仙》词着意写道嗑瓜子的女子的手指是“春葱细擘玉纤纤”[10]51,此处云“你秋波频转为谁来”,由于女性嗑瓜子时在指尖、眼中所呈现出的风情,使得嗑瓜子这一简单动作具有性感的意味,从而成为了一种情欲的象征。
可见,明清文学中的瓜子饮食活动,在女性书写与两性关系书写中具有多向的意蕴,它本身即是纷繁的世俗生活画面在文学作品中的生动呈现。《金瓶梅》作为明清文学中杰出的世情小说,多有嗑瓜子的场景描写,更成为这一文学性呈现的上国大观。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指出:“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14]1《金瓶梅》虽然以市井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但是却以小见大,反映出整个明代社会的风貌。《酌中志》载,明神宗好食瓜子,“好用鲜西瓜种微加盐焙用之”[15]181,上行下效,这种宫廷的饮食偏好影响到了明代民间的食俗。统计《金瓶梅》全书,关于瓜子的描写多达26处,其中对“嗑瓜子”进行细致描写的有12处。这些“嗑瓜子”的场景细节刻画都有着特定的内在意蕴与艺术功能。
二、《金瓶梅》中“嗑瓜子”的内在意蕴
(一)身份地位的间接呈现
食用瓜子在明朝虽然已经十分普遍,但是对于忙于生计的下层普通民众来说,平时是很少有闲暇的时间坐下来嗑瓜子的,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得以有时间消遣。这一点,在书中有明显的体现,例如第四十六回中,在元夜时,玉箫和书童二人在一处嬉笑打闹抢着瓜子嗑;小玉也和玳安也在一处嗑着瓜子。又如在第七十八回中,元旦时,玳安与王经换上新衣,放爆竹,嗑瓜子。总观全书一百回,提到下人们嗑瓜子,都是在元旦和元宵节,这便说明,即使在瓜子已经风靡一时的宋代,处于底层的人应很少有时间享受用来消磨时间的零食。故而作者才不惜笔墨加以叙写。
在书中,还有多次赏赐瓜子的情节。如在第十六回之中,西门庆于元宵夜与李瓶儿私会,李瓶儿为答谢玳安的掩护,便赏与他二钱银子买瓜子。又如在第二十四回中,另一个元宵之夜,李瓶儿赏给贲四娘子的女儿一方汗巾,又赏了一钱银子让其买瓜子,贲四娘子欢喜地连忙道谢。在第七十七回中,西门庆差玳安给郑月儿送银子过节,郑管家便给了玳安四钱银子买瓜子。尽管这几处并未直接刻画嗑瓜子的动作,但是从这些互动之中,可以明显看出上下地位之区别。同时也可以发现,这些赏赐或赠予也都发生在元旦与元宵这两个节日之中,而平常的赏赐仅是银子或是方巾,并不会特意说明是让受惠者买瓜子。以此,也从侧面说明这些身份地位低下的人也只有在年节时才有空闲的时间和闲钱买瓜子。
闲时和闲钱往往与嗑瓜子之人的身份与地位相关。统计可知,书中“嗑瓜子”次数最多的是潘金莲,文本多处描写了她在嫁给西门庆后嗑瓜子的场景。刚入门的潘金莲备受西门庆宠爱,又尽力讨得大娘子吴月娘的欢心,风头正盛的她或是在元宵节夜于楼上露出春葱般的手指嗑着瓜子,一边把嗑下的瓜子皮吐落在行人头上,或是在李瓶儿房门外一边偷听,一边嗑着瓜子(第二十回),又或是在门首嗑着瓜子等西门庆回来(第二十一回)。潘金莲虽然不像李瓶儿、孟玉楼那样自身就拥有大笔的财富,但是凭借西门庆的宠爱仍然有闲钱和闲时选择瓜子这一零食作为消遣解闷的方式。与潘金莲相似,书中有一个名号“小金莲”的人物——宋惠莲。宋惠莲原本只是西门庆家的一个下人,身份低贱,但是自从和西门庆通奸之后,从西门庆处得到了不少的银钱和首饰。在西门庆巧言欺骗下,宋惠莲便自认为与其他下人不同,开始以“主人”的身份自居,“常在门首成两价拿银钱买剪截花翠汗巾之类,甚至瓜子儿四五升量进去,教与各房丫鬟并众人吃”[14]268(第二十三回),开始炫耀自己与众丫鬟小厮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此外,在元宵夜宴时,其他人都忙的不可开交时,宋惠莲却坐在那里嗑着瓜子,把瓜子皮扔的满地,并且让画童帮她打扫(第二十四回)。此外,潘金莲差人叫她做最拿手的烧猪头时,她也只是嗑着瓜子,推说没空。西门庆不过只是把宋惠莲当作解闷的工具,但宋惠莲却开始恃宠而骄,迫不及待地彰显自己所处的新阶层,不仅以主子的身份恩惠、指使下人,甚至连真正主子的差遣都敢抗拒不从。从这个方面来看,是因为宋惠莲把自己当作西门庆的妻妾,随着身份的提高,行事做派自然都应该改变,宋惠莲的这种心理便可以通过“嗑瓜子”这一细节体现出来,同时也刻画出了一个出身低微却心高气傲、不甘屈服于命运的下层女性形象。
(二)性暗示与争宠的外在表现
《金瓶梅》中有关饮食的描写十分丰富,而关于宴饮的场景,往往食色掺杂、相互勾连。比如在第六回中武大郎死后,西门庆、潘金莲二人一番云雨过后,西门庆便以潘金莲的鞋为酒杯。三寸金莲在以小脚为美的时代,已然成为女性的“第二性器官”,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性欲的象征。正如潘金莲初时经常在门帘下坐着,有意露出自己的小脚,以引起门外浪子的注意。而套在小脚上的鞋,也成为了一种极具情欲象征的器皿,这就将肉体与饮食相结合,即食与色的结合。除了直接的饮食描写,书中人物在平常生活对话之中也经常使用与食物有关的俗语。比如在第二十三回中,宋惠莲与西门庆暗中通奸,被平安儿知晓,便出言讽刺:“我听见五娘教你腌螃蟹——说你会劈的好腿儿。”[14]265这句话也是隐指性交,诸如此类的俗语在书中尚多,食物与情欲相连之密切于此可见。食物此时已经不仅仅是单纯满足人口腹之欲的东西,更是潜入人物的内心深处、勾出情欲的引子[16]。
瓜仁是西门庆家的常见干果,经常一碟一碟的出现在餐桌上,和其他食物一样,被赋予了情欲的含义。郑爱月就曾亲口嗑了瓜子,并亲手拣了泡螺儿,差人给西门庆送去(第六十七回)。以此可见郑爱月的心思:其一,借嗑好的瓜子仁以表对西门庆的相思之情;其二,借泡螺儿告诉西门庆,并非只有死去的李瓶儿会做,由此引起西门庆对李瓶儿的思念之情,进一步希望西门庆把对爱妾的情感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无论是郑爱月亲口嗑出的瓜子仁,还是泡螺儿,目的都是为了争取西门庆的宠爱,这两样信物都成了郑爱月争宠的方式和手段。最终西门庆也成功地被郑爱月的“真情实感”所打动,带着一众人等来到郑爱月家进行消费。以此,便可确定,瓜仁也确实超出了食用的范围,而成为一种性暗示的工具。
“嗑瓜子”的这一动作,有意无意间唇齿的触碰与发出的声音,在书中所刻画的这群沉迷于酒色财气的人看来,无疑是一种性感的流露。从年节时玳安与小玉、书童与玉箫来看,两两一对凑在一起嗑瓜子,但他们之间的动作不仅仅限于嗑瓜子,更有许多肢体上的接触。小厮与婢女尚且如此,那么便可以小见大,作为一家之主的西门庆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第七十二回中,西门庆进到潘金莲房里时,潘金莲正踩着炉台,悠闲地嗑着瓜子等着西门庆,见西门庆回来,赶忙取了盏子,用纤手抹去盏边的水渍,亲自点了一盏“浓浓艳艳,芝麻、盐笋、栗丝、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海青拿天鹅、木樨玫瑰六安雀舌芽茶”[14]951,哄得西门庆“满心欣喜”,便迫不及待地与妇人上床交欢,期间潘金莲还不忘把嗑下的瓜子仁一口一口地送与西门庆吃。潘金莲借瓜子满足自己的情欲,在文中表现的十分明显,先是点一盏含有瓜仁的浓茶,而这瓜仁,可能是闲时亲口所嗑,这就先让西门庆在味觉上享受一番,心情大悦,再加上佳人在旁,西门庆自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于是潘金莲满足自己性欲的想法也成功达成。书中多次出现“风流茶说合,酒是色媒人”,食色相通,食欲得到了满足,色欲就被激发出来。作者对潘金莲这一嗑瓜子的描写,无疑是食色相通的最好证明。嗑瓜子尽显潘金莲之风流,所点的浓艳瓜仁泡茶则尽显潘金莲之奉承,以口送瓜子则尽显潘金莲之情欲,小小的一个动作便可看出潘金莲为争取宠爱、满足性欲的急切心理。
《金瓶梅》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的同时,也被称为“淫书”,书中充斥着大量淫秽的性描写,但作者对于“淫”的态度,无疑是否定的、批判的。体现在对人物命运的设计上,好淫之人最终走向灭亡,比如西门庆、李瓶儿、潘金莲、庞春梅,都是作者批判的对象。西门庆因为食用过多胡僧药而“遗精溺血”;李瓶儿因西门庆而死于“崩漏之疾”;潘金莲为贪图西门庆而毒杀武大郎,最终被武松报仇而杀死;庞春梅也因“贪淫不已”,而死于非命。纵观全书,作者对潘金莲嗑瓜子场景的刻画次数最多,而这些场面描写部分与她的淫欲活动紧密联系。
作者往往将淫欲与贪欲相联,而不仅仅是单纯地写淫,正如上文所阐述的“嗑瓜子”这一细节动作的特殊含义,借瓜子传情的郑爱月,她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借此“拉客”,获得西门庆的钱财;又如韩道国的老婆王六儿,更是赤裸裸地将与西门庆的性交作为获取利益的方式。
三、《金瓶梅》中“嗑瓜子”的艺术功能
(一)以场面促情节
《金瓶梅》中有大大小小几百场宴饮场面的描写,有些宴饮场面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7]。如第三回,王婆为西门庆与潘金莲牵线,为了增进二人的了解,王婆便整治了一桌的肥鹅、烧鸭、熟肉鲜鲊、细巧果子以及一壶酒。在酒席中,西门庆便按照王婆所说的方法,借机试探潘金莲的心意。从此二人便互通心意,时常来往。而武大郎知道西门庆、潘金莲二人奸情的起因,也是因为二人正在房内饮酒作乐,王婆拦住了找西门庆做生意的郓哥,并与郓哥发生争执,郓哥一气之下将西门庆潘金莲私通一事告诉了武大郎,后来才有武大郎捉奸、潘金莲毒死武大郎的情节。可以说西门庆潘金莲的第一次宴饮,决定了潘金莲今后的命运,也是因为一次宴饮,结束了武大郎的生命。宴饮场面的描写与故事情节息息相关,由于人物宴饮目的的不同,便导致了人物的走向和结局不同。
“嗑瓜子”作为书中出现次数较多的小的饮食场面的描写,同样也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如第四十六回,元宵夜西门庆宴请亲朋好友,玉箫和书童便在一起抢着瓜子嗑,过程中还碰倒了一壶酒,被春梅斥责了几句,二人便悻悻地分开了。此时便已暗伏玉箫与书童早有私情,但因二人感情不坚,终会离散的结局。在第六十四回中,玉箫与书童的私情被潘金莲撞破,书童害怕被潘金莲责罚,在不知道后果的情况下,便丢下了玉箫,自己一个人逃回老家,留下玉箫一个人,这一场景正与嗑瓜子一回中二人刚被春梅呵斥两句就立刻分开的情节吻合。
同样“嗑瓜子”的情节也发生在小玉与玳安身上,在第四十六回中,同一个元宵夜,小玉与玳安不仅一边嗑着瓜子,还一边家常聊着天,甚至筛酒吃肉。二人处于一个相对独立且安静的环境中,相比于玉箫、书童嗑瓜子时的嘈杂环境,且被春梅打散的情节,更衬托出小玉与玳安二人情感的稳定与和平。在第九十五回中,月娘撞破小玉与玳安的私情,便将小玉许给玳安,二人顺理成章地结为夫妻。而二人元宵夜私下相见的场景,俨然像一对成婚已久的夫妻,即使被琴童撞破,也只是淡然地招呼琴童喝酒,不似玉箫、书童相会场面一般混乱,丝毫没有被撞破私情的窘态,可见此处便已经为玳安、小玉二人顺利成婚埋下了伏笔。
这两处嗑瓜子的情节同时也说明了西门庆治家不严,张竹坡就认为西门庆家无家法,就连一直以贞洁为重的大娘子吴月娘身边的两个丫鬟都与小厮有染,遑论西门庆家中的其他人,在这样的家庭之中,情欲色欲掺杂,充分体现了人性欲望贪婪的一面。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都被酒色财气的欲望遮蔽,那么这个家庭只能一步步地走向没落和消亡,体现出书中所揭露批判的意旨。
(二)以动作塑性格
《金瓶梅》善写人物,写潘金莲,又写宋惠莲,又写李桂姐;既写李瓶儿,又写如意儿,又写吴银儿,善用犯笔而不犯,每个人物既有相同之处却又个性鲜明,可见作者的艺术功力之深厚。此外,作者也通常将人物置于饮食活动之下,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真实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色。
书中“嗑瓜子”的描写也是如此,潘金莲作为一个爱嗑瓜子的人,许多嗑瓜子的情节都生动形象地体现出了潘金莲的性格。如在第十五回中,元宵节夜晚,西门庆一家妻妾都在李瓶儿狮子街的房子里赏花灯,只有潘金莲一人吵闹,在窗口搂着衣服袖子,露出她带满戒指的手,嗑着瓜子,故意把瓜子皮吐落在下面行人的身上,引得不少浮浪子弟议论,直至月娘看到围观的人多了,才将潘金莲叫至身边坐着。潘金莲这一连串的动作,一是为引起人的注意,炫耀自己如今的富贵与地位,二是有意无意的情欲的展露。与月娘的保守、洁身自好相比,更加衬托出潘金莲性格的张扬与风流成性。
书中也描写了潘金莲两次在李瓶儿门口嗑瓜子的场景,在第二十回,西门庆娶回李瓶儿,却因为之前李瓶儿入赘蒋竹山之事生气,在房内鞭打李瓶儿。此时的潘金莲正与孟玉楼在李瓶儿门口嗑着瓜子,聊着天,等着春梅从房内出来问话,打听房内的情况;同样的场景出现在第三十回,李瓶儿即将生产,家中其他人都在忙碌,就连孙雪娥都急忙赶来询问关切,潘金莲却“扶着庭柱儿,一只脚跐着门槛儿,口里嗑着瓜子”[14]349,不忘对孙雪娥冷嘲热讽一场。自李瓶儿入府以来,潘金莲就把李瓶儿作为自己的敌人,几次三番挑拨吴月娘与李瓶儿的关系,不仅对李瓶儿进行冷嘲热讽,之后更是使用恶毒的手段使官哥儿受惊离世,让李瓶儿痛失爱子,成为李瓶儿死亡的重要原因。这两处潘金莲“嗑瓜子”的场景,都是在李瓶儿受苦之时,此时的潘金莲却摆着一副悠闲的姿态嗑着瓜子,若说潘金莲的心理,第一次只是好奇房内的场景,且对李瓶儿被打毫无怜悯之情;第二次对李瓶儿更多的是嫉妒和诅咒,在官哥儿呱呱坠地之时,潘金莲便生气回房哭了起来,可见潘金莲的由嫉妒至仇恨的内心变化。同样是在李瓶儿门口“嗑瓜子”,但是前后两次潘金莲的心理却是有所发展变化,由此可见潘金莲善妒与无情的性格。
《金瓶梅》中关于人物活动的描写,以饮食场面为多,或是铺张而精致,或是温馨而平淡,真实地展现出明代社会的市井风貌。“嗑瓜子”不仅成为《金瓶梅》中人物身份地位的象征与争宠的方式和手段,也是在其所蕴含的食色关系中,表现出作者寄寓时俗、对“淫”与“欲”的批判与谴责,同时也起着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