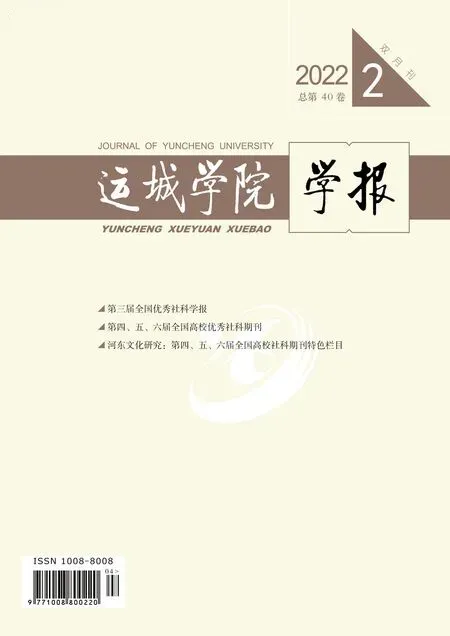试论唐朝田狩礼的“名”“实”及其政治关系
吕 学 良
(运城学院 文化旅游系,山西 运城 044000 )
在生产力不发达时期,狩猎是人们获得食物的主要来源,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活动[1]106。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农耕成为古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狩猎下降为补充形式。与在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地位下降相反,狩猎被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加以利用,转变成为一种称之为“礼”的意识形态工具,并延续后世。《周礼·夏官·大司马》对田狩礼有比较详尽的记载,后世举行的田狩礼也以此为蓝本。田狩礼仪几经变化,至隋唐时期定型[2]72-76,以《大唐开元礼》的颁布为标志,田狩礼最终确定下来。唐代帝王田狩频繁,但有是礼仪还是娱乐狩猎的区别,因此研究田狩礼首先需要探讨田狩的“名”与“实”。
一、田狩的“名”“实”之分
唐朝帝王喜猎,狩猎之风可算作家族文化的特征[3]19。唐朝有史可查的田狩记载始于高祖终于昭宗,时间跨度长达二百七十多年,几乎贯穿整个唐朝,多达87次。文献中关于田狩的记载繁多,诸如田狩、田猎、校猎、大蒐、畋猎、猎等,笔者对众多称呼不作统一的整合处理,但为行文方便尽量在行文中表述为田狩、田猎等词语。这些不同名称背后体现的是它们性质上的区别,其中一部分只能算作田猎活动,不能称之为礼,因此唐朝举行的田狩活动可划分为仪式性的田狩礼和非仪式性的打猎娱乐活动两类。对如何区分二者,颜逸凡认为狩猎、出猎、射猎、畋游指非礼仪性的打猎,蒐狩、田狩指礼仪性的活动,田猎则为二者的通名使用[4]5。这是他从名称上进行的分类。他在文中进一步指出“三驱”是唐代仪式性田猎礼的标志,以此区别于飞鹰走狗的射猎畋游[4]25。这是他根据田猎活动中是否有“三驱”这一礼仪程序做的区分。笔者以为上述分类方式似较随意。由于史料的欠缺,我们不能对历次田猎活动作一一区分,但我们可根据文献中的蛛丝马迹对其做一定性。
唐朝皇帝田狩场所可大体分为长安、洛阳禁苑及两京周边地区。长安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东至灞水,西连故长安城,南连京城,北枕渭水。苑内离宫、亭、观二十四所。汉长安故城东西三十里亦隶于苑中”[5]1394。洛阳禁苑“在都城之西。东抵宫城,西临九曲,北背邙阜,南距飞仙。苑城东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苑内离宫、亭、观一十四所”[5]1421。两京周边地区包括范围更广,如高宗时期一度在距离洛阳三百多里的许州田猎[6]1377。在如此大的区域内举行狩猎活动,随行侍卫、官员和军队的数量必定不在少数。数量众多的随军参与狩猎,因田狩礼中的布围这一环节。
《新唐书》卷16《礼乐志六》载:
皇帝狩田之礼,亦以仲冬。
前期,兵部集众庶修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于其后。前一日,诸将帅士集于旗下。质明,弊旗,后至者罚。兵部申田令,遂围田。其两翼之将皆建旗。及夜,布围,阙其南面。驾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围,鼓吹令以鼓六十陈于皇帝东南,西向;六十陈于西南,东向。皆乘马,各备箫角。诸将皆鼓行围。乃设驱逆之骑。皇帝乘马南向,有司敛大绥以从。诸公、王以下皆乘马,带弓矢,陈于前后。所司之属又敛小绥以从。乃驱兽出前。初,一驱过,有司整饬弓矢以前。再驱过,有司奉进弓矢。三驱过,皇帝乃从禽左而射之。每驱必三兽以上。皇帝发,抗大绥,然后公、王发,抗小绥。驱逆之骑止,然后百姓猎。[7]388
由上文所引田狩礼仪知,唐朝在举行田狩礼的前一日便集合诸军将士布围。合围成功后,皇帝和公王入围,然后由驱逆之骑驱赶野兽至皇帝面前,皇帝、公王、百姓依次进行射猎,可见合围的目的是驱赶野兽。唐朝田狩礼仪式呈现的先后顺序是:首先布围,布围成功后皇帝、公王入围,后行三驱之礼,最后皇帝、公王、百姓射。这是一个严密的礼仪程序,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差错。贞观十六年(642)十二月,太宗在骊山举行田狩,将士在合围时出现了断围现象。《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蒐狩》载:“帝登山顶,见围断,顾谓从官曰:‘此山险绝,马蹄不通,缘危越涧,人亦劳止。若依军令,阙围有罪,朕为万乘主,不可登高就下察人之过。’乃回马避之。”[6]1377此处没有提及三驱之礼,但唐军有合围之举。按照礼书规定,合围之后便是三驱,然后是皇帝射猎,高宗时期的一次田狩更能证明这一礼仪过程。龙朔元年(661)十月,高宗狩于陆浑县(今河南嵩县)。九日,“又于山南布围,大顺府果毅王万兴以辄先促围,集众欲斩之。上谓侍臣曰:‘军令有犯,罪在不赦。但恐外人谓我玩好畋猎,轻弃人命,又以其曾从征辽有功。特令放免’”[8]527-528。王万兴在合围后“辄先促围”,违反了军令,理应受到处罚。我们从这段史料中可以再次确认,在合围之后必须按照礼书的规定流程进行,不然便是违礼违令。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即便在史料中没有出现三驱之礼的记载,我们也不能轻易地按照名称或者有无“三驱”二字来断定一次田狩活动是否属于礼的范畴。因此,笔者的观点是对娱乐性明显的田猎活动可认定为非仪式性的狩猎活动,对不能明确属于娱乐性田猎活动的则承认它们为田狩礼。
二、田狩的“名”——非仪式性田猎活动
田狩礼包含军事性和娱乐性双重特征,两者此消彼长,在唐后期娱乐性特征占据了主流,导致的结果便是唐代皇帝举行的田猎不属于礼的范畴,而是单纯的狩猎活动。虽然唐后期田狩属于非仪式性的田猎活动,但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仔细甄别。
田猎中使用猎犬、猎鹰、猎豹等动物进行狩猎不合礼书规定,这是非仪式性田猎活动的典型标志。唐后期的皇帝频繁地在田猎中使用猎犬等辅助工具,娱乐性特征突出。元和三年(808)七月,宪宗谓宰臣曰:“朕昨因阅秋稼,行至苑东,只以鹰犬自随,本非畋猎,于时虽觉行人聚观,亦无伤稼之意。而谏官在外,章疏颇烦,不解何为,卿等知否?”[8]529宪宗出行之所以被误认为是畋猎行为,这与当时用猎犬、猎鹰狩猎的社会风气相关[9]252-259,宪宗本人也深知鹰、犬与畋猎之间的关系,所以才有“本非畋猎”之语,由此可见当时皇帝畋猎行为普遍,并对百姓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宪宗此次畋猎便是一次游猎活动,不属于田狩礼。穆宗“荒于游畋,内酣荡,昕曙不能朝”[7]5017。长庆四年(824)三月,穆宗下诏“鹰犬之流,本备搜狩,委所司量留多少,其余勒州府,更不得进来”[8]530。穆宗在身患风疾的情况下认识到自己田猎过度后作出这一决定,但鹰、犬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只是在确保拥有鹰、犬数量足够保证搜狩活动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不再增加而已,并无多大效果。敬宗的行为更是荒诞,超出一般田猎活动的娱乐性。他好深夜猎狐狸,被称为“打夜狐”。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帝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瑞打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谋害帝,即时殂于室内,时年十八”[5]522。敬宗夜猎狐狸不符合田狩礼的礼仪规定,超出此前帝王一般的田猎行为,荒诞至极。敬宗之死是新旧两派宦官争夺权力导致的结果[10]286,但耽于田猎无疑为乱臣谋逆提供了机会。
其实,田猎中使用猎犬、猎鹰、猎豹等动物辅助工具在唐前期既已存在,懿德太子墓志壁画中便有猎豹、猎犬和猎鹰图。这体现的是皇室成员的田猎活动,是田猎之风的一种反映,但皇室行为与皇帝田猎之间不能划等号。唐朝前期,君主勤征,臣子善谏,如若在田猎中使用猎豹之类狩猎工具必定引起臣下的重视和劝谏[9]238,这样便会留下历史记载,然而在文献中未见唐朝帝王使用猎豹进行狩猎。永徽二年(651)十一月,高宗下诏曰:“弋猎畋游,素非所好,常谓此志布于远近,而蕃夷有献鹰犬者,有阻来远之情,时复为受,示以不违其意。其诸州及京官,仍有访求狗、马、鹰、鹘之类来进,深非道理,自今后,更有进者,必加罪责。”[6]2025高宗下诏停止地方进贡鹰犬,以期杜绝助长田猎的不良之风,这从侧面体现了当时普遍使用猎犬等动物的现状。这种局面在玄宗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开元初年,唐朝设置五坊宫苑使,管理雕坊、鹊坊、鸦坊、鹰坊、狗坊,以供时狩。五坊宫苑使的设置无非是猎犬等狩猎动物多且需要规范管理,但无形之中承认了鹰、犬之流在田猎中的合法性地位,助长了使用猎物打猎的风气。唐廷默认鹰、犬在狩猎中的合法地位,客观上致使进献成风,肃宗时期不得不下诏“停贡鹰、鹞、狗、豹”[7]165。有学者认为田狩礼在安史之乱后开始衰落[2]85,但由上文可知它衰落的苗头在玄宗初期便已显现。
综上,非仪式性田猎活动或行为在唐代举行的田猎中占据一定数量和比例,其在唐后期所占比重更大一些,但这只是唐代田狩活动的支流,主流仍是具有仪式性的田狩礼。
三、田狩的“实”——仪式性田狩礼
唐朝皇帝举行田狩活动除个人喜好外,多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它在政权初建的不稳定时期举行的频繁且军事性特征突出,政权稳固之后田狩礼的军事性便开始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娱乐功能的凸显。
(一)唐朝前期
1. 高祖朝
高祖晋阳首义,后南下长安,建立李唐王朝。建政初期,外有强大的突厥不时侵扰,内有割据势力还未平定,国内统一尚未完成。在当时群雄竞逐的局面下,李唐王朝也只是割据关中的一股势力而已,所以摆在高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击败对手,完成统一,确保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李渊在建国初期需重视武备和军队训练,融合军事训练的田狩礼无疑是礼仪实施的首选。
高祖初次狩猎是在武德元年(618)六月二十四日,时间不符合礼书仲冬之月的规定,有学者以此时田狩礼还没有被规范予以解释[2]76。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众所周知,唐承隋制,在礼制上也是如此,即“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11]68。唐朝立国之初照搬隋礼,武德之际,沿袭开皇旧制,但并没有完全排除大业制[12]1206。无论怎样,此时不会出现不知礼或无礼可遵的情况。高祖此次田狩后,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书奏请高祖蒐狩应顺应四时[8]525。臣子尚且知道狩猎规则,作为帝王又岂会不知?所以高祖蒐狩不遵守礼书的时间规定是有意为之,目的在于通过举行皇帝田狩礼庆祝李唐建国,宣示皇帝权力和李唐王朝的合法性。同年十二月,高祖“幸周氏陂,过故庄。丙戌,校猎。置酒高会,极欢而罢,赐钱绢各有差”[6]1375-1376。孙伏伽上书之后,高祖举行田狩活动便安排在冬季,注重顺天应时。
武德四年(621)闰十月,高祖连续转战多地田狩,对此史书有较多记载。
《新唐书》卷1《高祖本纪》载:
十月己丑,秦王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齐王元吉为司空。庚寅,刘黑闼陷瀛州,执刺史卢士睿,又陷观州。……乙巳,赵郡王孝恭败萧铣于荆州,执之。
闰月乙卯,如稷州。己未,幸旧墅。壬戌,猎于好畤。乙丑,猎于九嵕。丁卯,猎于仲山。戊辰,猎于清水谷,遂幸三原。辛未,如周氏陂。[7]13
此次高祖长时间连续多地田狩是在唐朝统一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之际,庆祝之意明显。当时唐军相继平定和降服王世充、窦建德、萧统、冯盎等几大割据势力,统一战争最大的阻碍因素消除,坐镇长安的高祖兴奋不已,不仅对太子、秦王、齐王等有功之臣进行封赏,还对唐朝群臣以及父老故吏进行了赏赐。在此背景下,高祖在故宅旧地连续举行四次田狩活动,宴请赏赐父老故吏,田狩活动成为了狂欢的载体和平台。秦王文学褚亮劝谏高祖不能过多狩猎的理由便是“寇乱渐平,每冬狩猎,遂上疏谏”[8]525。可见,高祖举行田狩有重视武备和军事训练的意图,随着战乱减少,田狩也有减少的必要[13]341。
武德五年(622)十一月,高祖讲武于宜州同官县,声援皇太子李建成出征,鼓励士卒一鼓作气取得战争胜利。讲武结束七天后,高祖移军富平举行田狩礼。富平位于同官之南,显然这是高祖在回京途中举行的。这次田狩伴随着讲武进行,显示了二礼的密切关系。同年十二月九日,高祖再次猎于华池县,这引起了谏议大夫苏世长的批评。此次田猎距离上次间隔不足半月,性质却显然不同,高祖娱乐的主观意图明显,“在狩猎活动的快乐中寻找慰藉”[14]304,故而引来朝臣的进谏。
武德八年(625)十月,高祖校猎于周氏陂,褚亮上疏劝谏,高祖纳之。十一月,高祖为抵御突厥进攻第三次亲临宜州同官县举行讲武,宣示保家卫国的决心,以图达到震慑突厥的目的。此次讲武过后,高祖紧接着再次举行田狩。十二月,高祖于临潼鸣犊泉之野举行狩猎,并指出目的是“搜狩以供宗庙,朕当躬其事,以申孝享之诚”[8]526。对此,有学者认为是一次以贡献宗庙为借口的狩猎[4]48,但我们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便知高祖所言非虚。这次田狩活动紧邻同官讲武,其目的与讲武具有一定的相同性,高祖祈求祖先保佑之意不虚。
2. 太宗朝
有唐一代,太宗举行田狩活动多达22次。太宗文韬武略,率军征战身先士卒,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唐朝完成统一后,战事减少,太宗只好通过狩猎来体会当年的戎马生涯,这也客观上造成了他在位时期频繁地举行田狩活动。太宗朝举行的田狩活动多与政治密切相关,它的举行也脱离不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包含政治动机。
贞观四年(630),唐朝击败东突厥,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太宗被尊称为“天可汗”。这次胜利一洗太宗的渭水之耻,也真正奠定了唐朝的强国地位[15]164。事后太宗借举行田狩对将士进行赏赐。四年十月辛丑,太宗“校猎于贵泉谷,赐将士帛有差。甲辰,校猎于鱼龙川,亲自射鹿献于太安宫。十二月甲辰,腊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蓝缕,遣侍中王珪赈赐贫人焉”[6]1376。当时高祖居住于大安宫,太宗献鹿于高祖显示孝心,对穷人进行救济则彰显太宗爱民如子的博爱之心。通过此次田狩活动,太宗不仅赏赐了征战有功的将士,还获得了孝子和仁君的美誉,而这正是礼仪活动所能达到的效果。
贞观五年(631)正月,太宗大狩于昆明池。此次田狩引起后人重视是因为太宗对田狩做过如下评价,史载:“(太宗)大蒐于昆明池,蕃夷君长咸从。帝谓吕王〔高昌〕麴文泰曰:‘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耳。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田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今日王可从禽,明当欢宴耳。’丙子,至自昆明池,亲献禽于太安宫。”[6]1376太宗此话经常被用作证明他偏爱狩猎,但这段史料也可用作论证唐朝与高昌交恶的原因[16]37-38,且这一观点指出了麴文泰入唐的政治背景和太宗举行田狩的深层用意。东突厥灭亡后,西突厥转变成为唐朝的头号政治对手。西突厥是唐朝的长久之患[17]153,太宗着手经营西域首先需要的是争取西域诸国的支持。当时西域诸国势力强大者当属高昌,虽然高昌臣服于西突厥[18]103,但是麴文泰也有称霸西域诸国的野心[19]425-426。贞观四年十二月,麴文泰携其夫人入唐,有考量唐朝国力虚实的目的。唐朝对麴文泰之行没用应有的“宾客”之礼接待,有轻视和傲慢之意[16]37。唐朝的这一态度在狩猎昆明池时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次田狩兼有娱乐、礼仪、展示武力三重性质,太宗亲自狩猎,蕃夷君长咸从,麴文泰只是其中之一,陪衬之意明显。另外,太宗畅言狩猎之乐,他所说的第二“乐”不仅展现了自己的骑术射技,还展现了随军的军事素质和箭术水平,在高昌王面前显露了唐军实力一角。太宗所说的第三“乐”暗指高昌王不远万里前来长安,有朝集拜访之意,言外之意则是高昌承认臣属唐朝,遵守以唐朝为天下中心的国际秩序。太宗通过举行田狩礼仪,完成了一次外交活动,向西域诸国最强者展露了实力,起到了炫耀武力的作用。
贞观十一年(637)二月,太宗车驾行幸洛阳宫。太宗居住洛阳期间狩猎频繁,引起臣下进谏,“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20]6131。十月,太宗狩猎于洛阳苑,差点为野猪所伤。唐俭以身护驾,趁机劝谏,太宗罢猎。十一月十五日,太宗狩于济源。太宗曰:“古者先驱以供宗庙,今所获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荐享。”[8]526-527太宗下令将所获猎物献于宗庙,此次狩猎当为田狩礼无疑。这次狩猎距离上次罢猎间隔不足一月,太宗按照礼仪流程进行,有阻谏官之口和践行颁行的《贞观礼》之意。《贞观礼》是唐朝官修的第一部礼书,也是太宗的一大政绩。在它颁布后,太宗按照礼书规定举行田狩,以身示范,起到了宣扬新礼典的作用。同时,此次田狩也是太宗朝田狩礼规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太宗举行田狩礼时选择亲身避让以护礼,不对将士违礼行为予以惩罚,展现了太宗重礼爱人的形象。贞观十六年(642)十二月,太宗在骊山举行田狩,将士在合围时出现了断围现象。《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蒐狩》载:“帝登山顶,见围断,顾谓从官曰:‘此山险绝,马蹄不通,缘危越涧,人亦劳止。若依军令,阙围有罪,朕为万乘主,不可登高就下察人之过。’乃回马避之。”[6]1377在合围中出现断围现象是为失礼,按军令应当给与处罚,但当时天气“寒阴晦冥”[8]527,骊山又地形险绝,客观上不利于合围的正常进行。太宗不因礼罚人,选择“回马避之”来调和礼仪与军令之间的矛盾,在这一选择中太宗仁义之君的形象被刻画出来,达到了制定和实施礼仪的目的。
3. 高宗朝
高宗性格柔和,“宽仁孝友”[5]65,不好狩猎[7]51,加之显庆年后身体多病,所以在位三十余年只举行了9次田狩。永徽元年(650),高宗初次狩猎遇雨,接受臣下劝谏后停止。此后高宗举行的几次田狩与讲武紧密连接在一起,为升洛阳作为东都预热。显庆二年(657)十一月乙巳,高宗狩于嗤水之南,“行三驱之礼,设次于尚书台以观之”[6]1377。不久,高宗“亲讲武于许、郑之郊,曲赦郑州”[5]77。这次田狩按照礼书规定举行,实行三驱,与之后举行的讲武礼相结合,刻意突出洛阳的东都地位。显庆五年十一月乙卯,高宗“狩于许、郑之间”[5]81。同年十月,高宗“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自此“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20]6322。此时高宗身体欠佳,他却依然亲身参与田狩,这应与苏定方平定百济献俘洛阳有关。《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载:“十一月戊戌朔,邢国公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责而宥之。”[5]81高宗不顾身体不适举行田狩礼,庆祝唐军凯旋,凸显唐廷对战胜百济之役的重视。显庆五年,高宗为平定百济相继举行了讲武礼、田狩礼和献俘礼,显示出唐廷对征讨百济的重视,同时也显示了三礼暗含的密切关系。
咸亨二年(671),关中大旱,高宗就食洛阳。十二月,高宗幸许州,“陈冬狩之礼,因校猎于许州华县昆水之阳”[6]1377。高宗狩猎许州,依然与洛阳作为东都的地位相关。许州地居洛阳之东南,郑州之正南,汴州之西南,自古为交通都会之地[21]1871和中原一军事重镇[21]1899。它作为洛阳的东大门,控制着江淮地区西进和东南地区北上的要道,同时又扼守北方南下之交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洛阳成为东都之后,许州成为它面向江淮和东南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许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故高宗在此进行狩猎,表达唐朝对它的重视。
4. 玄宗朝
唐朝在高宗末年至玄宗继位这段时期几乎未曾举行过田狩礼,玄宗即位后立即予以恢复。先天元年(712)十月,玄宗登基不久便狩猎于骊山,恢复一度停止的田狩礼,在礼制上抹除武则天实际掌权时代的痕迹。开元三年(715)十月,玄宗大蒐于凤泉汤,下制:
昔周有岐阳之蒐,汉有扶风之命,或讲师习武,跨胡曜威。故王者狩必以时,虞人招之以礼,时则远矣。朕自祗膺图箓,于今四年。每巡幸郊畿,不出百里,且爱力而节用,岂盘游而好乐。间者四方无事,百谷有成,因孟冬之月,临右辅之地,戒兹五校,爰备三驱,非谓获多,庶以除害。一昨长围已合,大绥未举,而夜间朔风,天降微雪。狐裘且御,未免祁寒,鹑衣不充,宁堪冻露。朕便截狡兽,要轻禽,以此游娱,孰云矜恤?况为之父母,育彼黎元,中宵耿然,明发增惕。其围兵并放散,各赐布一端,绵一屯。围将赐物三十段,副使二十段,押官十段,岐州兵马于此给付,余兵马至京请受。[6]1377-1378
玄宗此制言明了田狩的意义不仅在于复礼,还在于军事训练和为民除害。在这次田狩中,玄宗同样重礼爱人,因严寒气候会对士兵造成伤害而停止了田狩,并给予随军将士以物质赏赐。玄宗这一体恤士兵的举动笼络了人心,但随意停止田狩的行为却显示出田狩礼开始衰落的迹象。开元二十年(732)十一月,玄宗在太原举行田狩礼。《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载:“十一月辛丑,如北都。癸丑,赦北都,给复三年。庚申,如汾阴,祠后土,大赦。免供顿州今岁税。赐文武官阶、勋、爵,诸州侍老帛,武德以来功臣后及唐隆功臣三品以上一子官。民酺三日。十二月辛未,至自汾阴。”[7]136-137这次田狩礼是玄宗巡幸太原和祭祀后土的组成部分,玄宗对功臣进行赏赐,密切君臣关系,同时举行具有军事性的田狩礼,显示对武备的重视,玄宗恩威并施,确保北都局势的稳固。另《大唐开元礼》在同年九月修成,此次田狩礼在它修订颁行两月后举行,玄宗有实践新礼的用意,然而这也是玄宗朝举行的最后一次田狩礼。此后的玄宗早已失去勤政进取之心,校猎也变为娱乐性的田猎活动。此后田狩礼与其它军礼一样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二)唐朝后期
安史之乱的爆发,打乱了唐朝正常的统治秩序,礼制建设和实施也趋于混乱和停滞。这一时期是田狩礼的衰落时期,仅有少数帝王田狩属于礼仪范畴。
1. 代宗朝
代宗时期举行过一次田狩活动,地点在禁苑。大历七年(772)十月,代宗“畋于禁苑,一发连中二兔,遣使出示宰臣,仍赐之。宰臣等拜舞称庆”[6]1378。由此看来,此次田狩规模较小,可能是代宗及身边近臣参与。代宗将射猎战利品出示宰臣,炫耀技艺,宣传自己的英勇行为[14]212-223。丸桥充拓认为在田猎中捕获的猎物从上级品开始,依宗庙、宾客、君主以及其他参加者的顺序使之共食,如此可确认并显示“帝国的秩序”[22]323。其实这种做法自古代一直保留至近代的草原地带,体现的是一种特殊君宠[14]310-311。代宗将所射猎物赏赐给宰臣也具有上述两种含义[23]565-566。这次田狩是代宗试图恢复礼制的一种尝试,但收效不大。代宗的努力被德宗继承,田狩礼在举行次数和规范程度上有所增加和提高。
2. 德宗朝
德宗是唐朝后期较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在位期间举行了四次田狩礼,田狩礼有所恢复和规范,颜逸凡将德宗时期称之为“崇重礼制期”[4]54。笔者认为这一论断还有待完善之处。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遭受严重破坏,礼制也不例外。肃宗、代宗、德宗、宪宗四朝对国家祀典进行改造和重建,礼仪制度出现复兴和更新。这一时期,唐朝的礼制建设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继续贯彻《开元礼》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另一个是继承和总结开元、天宝以来的礼仪变化,为现行“仪注”提供依据和补充。这两方面的礼制建设在肃、代之际即已开始,德宗以后更被提上了日程[24]214-215。可见,德宗朝只是礼制建设的重要时期之一。贞元二年(786),德宗将《开元礼》列为举选科目[8]1396,把恢复和建设礼制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中。然而这一时期的礼制恢复和建设集中于吉礼和凶礼,对军礼重视不够。德宗朝举行过四次田狩礼,而同属于军礼的讲武礼、射礼却未曾举行,由此可知德宗对同一属性礼制的恢复和建设也是有选择的。
德宗重视田狩礼首先体现在重新恢复实施田狩礼。贞元三年十二月,德宗于新店狩猎,“幸野人赵光奇家”[8]522。时值两税法颁行,德宗便就此询问赵光奇,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20]7508德宗与赵光奇的对话成为后人研究两税法和税收问题的一条重要史料,却忽略了它作为田狩活动本身蕴含的意义。德宗狩猎的政治目的性强,或许狩猎只是借口,借机体察民情才是德宗的真实用意。贞元十年十二月,德宗“令诸卫将军畋于南城”[6]1378。德宗在此次田狩中令将士狩猎,自己作壁上观,与之前有所不同。这可以算作德宗对田狩礼的一种变革,背后或许隐藏有考量禁军将领之意。
德宗重视田狩礼还体现在对礼仪的规范上。贞元十一年十二月,德宗“腊畋于苑中,止多杀,行三驱之礼。军士无不知感,毕事,幸左神策军营,劳军飨士而还”[6]1378。此次田狩严格遵循三驱之礼,程序规范,拒绝滥杀,力图复原唐前期规范化礼仪之景象,令将士感到震撼。翌年四月,“左右十军使奏云:‘銮驾去冬巡幸诸营,于银台门外立石碑,以纪圣迹’”[8]522。德宗通过举行规范化礼仪获得了禁军将士的敬畏和臣服,达到了以礼卫政的目的。
德宗之后的宪宗、穆宗、敬宗、武宗、昭宗等人以畋猎居多,娱乐性质明显。这一时期唐朝皇帝举行的田猎活动存在较多的不合礼书之处,因此我们也很难判断它们具体属于礼仪活动还是娱乐活动。随着唐后期皇帝田狩活动的军事性特征衰退和娱乐性的增加,它与唐朝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最终演变成为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在史书中用来体现皇帝的荒淫。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概述田狩礼在有唐一代的实施状况,讨论了其与唐朝政治之间的关系。田狩在唐朝实施次数最多,却颇为人诟病,原因在于该礼仪在实施过程中因过“度”产生的性质转换。田狩礼兼具军事性和娱乐性,随着唐朝国力和政治局势的演变,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唐朝前期面临实现统一、巩固政权、稳定边疆等历史重任,同时君主勤政,国力日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除高宗后期至玄宗登基前的短暂沉寂外,田狩礼因客观需要和君主推动举行频繁,突出彰显了其军事性质,起到了巩固政权、稳定边疆等政治作用,实施过程也基本符合礼书的规定。唐朝后期,国力式微,君主多假行礼之名行欢娱之实。一些荒诞的狩猎行为,不但丧失了应有的政治功能,还突破了礼的形式约束,这一时期娱乐性占据主流。
田狩礼包含宣扬君威、礼仪教化、训练军队、展现实力、羁縻藩属、笼络民心的政治功能,这些政治诉求可以从其举行背景、实施过程、政治影响、猎物分配等方面体现出来。田狩礼是皇帝实现既定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在唐前期和后期的个别时段,它成功发挥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安定边疆等政治作用。田狩礼军事性和娱乐性二重属性的消长,也体现了它过多地受到了皇帝自身政治素养的影响,缺乏客观、规范的约束机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