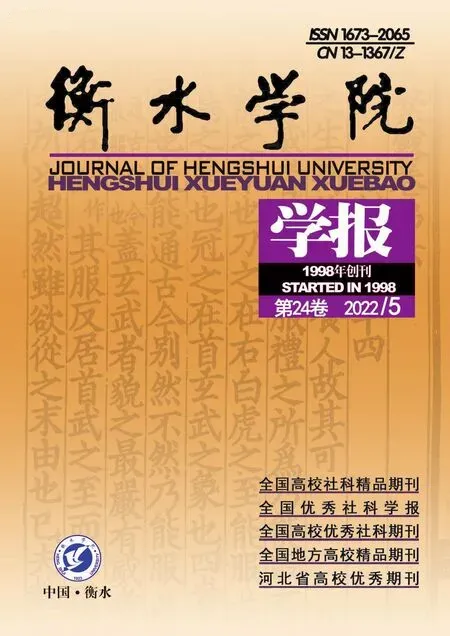“名伦等物不失其理”
——董仲舒的“物”哲学
张靖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241)
既往对于董仲舒的思想研究往往侧重于从其“天的哲学”“政治哲学”等角度,把握董子思想之大略,却往往忽略了对于“物”的研究。然而,作为认识与语言的对象,“物”在董仲舒的思想中自有其一席之地。一方面,在董仲舒的名学思想中,名物(名实)关系作为基础得以确立;另一方面,董子以阴阳、四时、五行等图示解释世界的理论,自然不可能略过“物”这一抽象的、代表一切存在者的范畴。然而,历来的研究者或将之归于“天人感应”的框架内,将“物”视作天人关系中的参与者,或将之归于认识的或语言——或统之曰“名”——所把握的对象,始终缺乏就“物”而论“物”的系统研究①例如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以“辨物理、真天意的认识论”囊括了对“物”的讨论。余治平《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2页)则以“物莫无邻、以类相召的感应思想”将对“物”的分析统摄其中。。事实上,董子发挥《春秋》“五石六鹢之辞”,形成其独特的“名物”观,有别于“多识草木鸟兽之名”的名物训诂。又继先秦名学思想之余绪,并将之组织进其宇宙论、本体论的论域之中。“物”的不同面向之间环环相扣,共成一体。因此,本文即试图以“名”为视角,系统剖析董仲舒的“物”哲学。
一、从“五石六鹢”到“名伦等物”
辨物理、别物类的研究往往被归于“训诂”的范畴,更确切地说,则是“名物训诂”。所谓“名物”,大抵指称专有名词,如草、木、鸟、兽、鱼、虫之类,也包括宫室、车舆、器皿、服制、天文、地理等。因古字、古言之不可得而解,所记之名物有不可得而闻者,则有考镜源流,还其故训的必要。如最早的字书《尔雅》,除却《释诂》《释言》与《释训》三篇外,大抵皆为名物训诂。《说文解字》《释名》亦包含大量训释名物的条目。《论语》记载孔子教导“小子”学《诗》,认为其有“兴观群怨”之教化功能外,尚可有助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诗》中所载名物之繁复,这也使得《诗》成了名物训诂之大宗,自汉讫清好之者不绝。
不过,细绎“名物”一词,又可以析分为“名”与“物”。《周礼·天官·冢宰》:“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1]86贾公彦疏以“名物”作“名号物色”解。又《地官·司徒》:“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1]241郑玄注曰:“名物者,十等之名与所生之物。”[1]241贾疏作“十等形状名号及所出之物也”。又孙诒让释“名物”曰:“名物,若《尔雅》之《释鸟》《释兽》《释畜》所说,种别不同,皆辨异之也。”[2]综合以上释读,可以认为:“物”当然可以依“名”而辨异或别类,但“名”与“物”之间并非自然而然地连缀成词。其中所谓“名物”二字虽联属而其含义又有间隙,也并非专指草木、鱼虫、鸟兽之专有名词。若要在字义上锱铢必较,则大可推断:“名物”二字连缀成词,本身即意味着将“名”可以(有效地)指称“物”作为前提接受了下来。当然,这一前提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因此“名物训诂”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还其本原,也就是试图还古书、古言中的“名”以其本身所指称的那个“物”。
如果说承自孔子“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名物”之学以博闻多识为目的,那么董仲舒对于“名物”的看法则纯是“名物”之学的对立面。《春秋繁露·重政》篇(以下只注篇名)曰:“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知其分科条别,贯所附,明其义之所审,勿使嫌疑,是乃圣人之所贵而已矣。”[3]33董子明确认为圣人虽能说鸟兽草木之名,却不愿多说,圣人真正关心的是“仁义”二字。在《仁义法》篇中,董子强调“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并试图通过将“仁”训为“爱人”,由为政者之“爱人”等同于“爱民”推至“鸟兽昆虫莫不爱”。“说仁义而理之”中的“理”当然有条理、分理的含义,故要“分科条别,贯所附”。这一说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认识与名物意义上分类、拣择,赋其条理之意,却更侧重于以人道而范围之,并非就草木、鸟兽而分类别属之意。这里,孔子“多识”之说与董子“非圣人所欲说”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对立的关系。苏舆试图调和这一矛盾:“孔子学《诗》,亦云‘多识’,盖视为余事,不侈浩博。观《古今注》所载芍药蝉蚁之答,《论衡》所纪识重常之鸟,知董未尝以博物为非。程子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亦畏其得小而遗大也。”[4]144要之,《诗》之“兴观群怨”要重于“多识”之功,董子未尝以博物为非,却亦不以博物为要。可见,董子重道德而轻名物,虽不废博闻多识之功,却在学有小大之辩的问题上表明了立场。
这一对于“名物”的不同理解在董子对于《春秋》的解读中又进一步放大。董子所谓“名物”大抵以《春秋》为依归,这与其作为《公羊》先师,善言《春秋》的历史形象若合符契。其言曰:“《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则后其五,言退鹢,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五石、六鹢之辞是也。”[3]60-61董子所谓“名物”,并不排除草木鸟兽、天文地理等专有名词,将对于霣石、飞鹢的考察归于“名物”亦未为不可。不过,“名物如其真”,却更多地指向命名、指称事物如其所是的含义。或许可以认为:“名物训诂”之“名物”侧重在“物”,而董子所谓“名物”侧重在“名”(或谓“言”“辞”)。前者关注的是如何辨物、真物,后者则更侧重于正名、慎辞。
以对于五石、六鹢的考察为例。《春秋》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①“鹢”,《谷梁》作“鶂”。参见范甯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僖公六年至十八年,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左传》解经,专就“名物”立论,其意平实。所谓“陨石”即“陨星”,解“六鹢退飞”之缘由为“风”,可知风大而致鹢鸟退飞①又《史记·宋微子世家》:“六鶂退蜚,风疾也。”参见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963页)。。《公》《谷》则不同。《公羊传》曰:“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嗔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5]434-436五石、六鹢,《公羊》着眼全在语序,于陨石,则先闻、再见、后察,于飞鹢则先见而后察。因为认识由粗入精,故在记述上则有石先于五,六先于鹢之文辞。《谷梁》则以为:“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六鶂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6]陨石散于宋之四境,圣人记之以耳闻,故“后数”。六鹢聚而飞过宋都,圣人记之以目见,故“先数”。与《公羊》之说略同,不过更添释义,却难免牵强之嫌。董子所谓“于言无苟”“名物如其真”,显然是站在《公》《谷》的立场上强调圣人以耳闻目见之序,纪实而录,以明确《春秋》之于辞无苟。这与《公羊》以《春秋》为圣人笔削之书,虽讥贬诛绝以托圣人志意,却仍是耳闻目见之序则纪实,阙疑阙传之处则阙如的“信史”。且《公羊》一般以《春秋》中之“君子”为孔子,故“君子于其言无所苟”就不仅仅是孔子“正名”观念的表述,也被董子用来说明圣人笔削《春秋》时之于“辞”无苟。
《玉英》篇中另一则对于《春秋》辨物之理的论述同样可以为证:“《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螽坠谓之雨,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3]20“星坠”曰“陨”,“螽坠”曰“雨”,均为坠落之意,《春秋》即以“辞”别嫌疑。苏舆注曰:“星降于天,不可言雨星。雨亦降于天者,嫌使同也。螽本发于地,不嫌同雨,言雨正状螽死坠。”[4]73“星霣”可言“如雨”,但“如雨”毕竟不是“雨”。《公羊》对之即有释义:“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5]1136可知,未经孔子删削之《春秋》本作“雨星”,孔子笔削而成“星霣如雨”。一般以为,经孔子笔削之《春秋》于记事上要更为精确。记录者不可能如此切近地观察到陨星的坠落,所谓“尺而复”者大抵为传闻或臆说,且“雨星”与“雨螽”又辞同而嫌疑。以“如雨”称“星霣”,以“雨”称“螽”则可以起到别嫌明疑的效果。董子的解释即以陨星降自天,而蝗虫生于地,“雨”亦地气蒸腾所生,故与蝗虫同发于“地”,自与陨星不同。故“螽”可言“雨”,而“星”不可言“雨”。其说牵合与否姑且不论。依董子之意,突出“星霣”与“雨螽”之异,表明的是对《春秋》中的“名”(或“辞”)的重视,“辞”以别嫌疑,故于“辞”之嫌微、同异之处必须慎之又慎。
无论是五石、六鹢还是雨星、雨螽,尽管仍围绕着“物”而展开,但却并非狭义的“名物”之学所能范围。五石、六鹢关乎语序问题,而雨星、雨螽则更多牵涉词义及搭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考究名物。或可认为,董子所谓“名物”,当解之为“名伦等物”更为确切。《精华》篇曰:“《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3]22苏舆注曰:“因伦之贵贱而名之,因物之大小而等之,故曰‘名伦等物’。”[4]82钟肇鹏分释四字,即以“名伦等物”包含名称、人伦、等级、事物四者[7]159。下文又就小夷、大夷,战、获、执之嫌疑处一一剖析,最终指向了“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3]22。可见其所关注者并非狭义的“名物”,而是如何由“辞”而达乎圣人之“义”(“意”)②《春秋繁露·盟会要》篇的一段文字则直接将“名伦等物”组织进理解“圣人至意”的一隅中,经由“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即通过小大、尊卑、贵贱之序,以明乎政治得失:“至意虽难喻,盖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贵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遍矣。……故曰: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采摭托意,以矫失礼。善无小而不举,无恶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别贤不肖以明其尊。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始于除患,正一而万物备。故曰大矣哉其号,两言而管天下。此之谓也。”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第32页。。
综上,董子所谓“名物”虽然不排斥狭义的“名物”之学,甚至以之为基础,却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了人伦、政治领域,体现出轻物重人的倾向。其在《春秋》的语境中所提揭出来的“名物如其真”,关注的其实是言如何达意——更具体地说,则是如何由《春秋》之辞(或圣人之言)透入圣人之意——的问题,而非对具体事物的考究。
二、“名物如其真”——“名”的基本功能
董子所谓“名物”尽管与“多识草木鸟兽之名”的“名物训诂”有所不同而更倾向于人伦、政治的论域,然而,若回到董子所谓“名物”的基本规定,即以“名”命“物”,则其对于“物”的讨论也同样触及了先秦以降一切名学思想都无法绕过的基本议题,即名实关系的问题。大体而言,先秦时期的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黄老等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可以区分为循名责实与依实定名两种不同的进路。前者主张名对于实的规约,甚至认为“名”具有超越于其所指称对象之现实性的指导意义;而后者则主张名以指实,乃至名副其实,强调名与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先秦诸子的论述虽然各有侧重,但两种致思进路之间并不存在正误之分,事实上,在《荀子》那里,“制名以指实”与“名定而实辨”两种倾向得以并存。当然,也可以认为依实定名,主张名与实之间近乎严丝合缝的关联侧重于对自然物的命名。而循名责实,则更适用于对人伦的、政治性的“名”。不过,无论采取何种进路,名与实(或其所指称的对象)之间的关联,作为论“名”的基石是没有争议的。
董仲舒的名号学说承先秦名学思想之余绪,其以“真”字关联起的“名”与“物”,恰恰包含了名实关系的上述两个面向:一方面,“名之为言真也”“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3]60,即将“名”视作对“真”(或“实”)的呈现或反映。先有物而后有名,强调“名”之为对“物”的真实反映,恰是还“名”与“物”之关系的本原。苏舆则从造字(“字”亦“名”也)的角度解之:“先有物而后有名。象形而为字,辨声以纪物。及其繁也,多所假借,原其始,皆以其真。”[4]283万物各有其“名”,即便“名”与其所指称对象的形象业已相去较远,但其所假借而为“名”者,若原其本,则同样为“真”;另一方面,“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3]60,“名”成了圣人用以探真伪、审是非的工具,循其名而后可以责其实,所谓“凡百讥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则黮黮者还昭昭耳。……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3]60。天下之事有黯而不明者,皆以“名”之不正,而若要使黯者得以大白于天下,则势必要在“名”与“实”之离合处着眼。可见董子所谓“真”,包含了以实检名与以名正实两个面向。一方面,“名”以“真物”,这与孔子为政必先“正名”的主张如出一辙,侧重于循名责实的进路;另一方面,“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又更多地观照到了“名”与“实”间的相互关系,而非单方面地主张“名”对于“实”的作用。
如果说“真物”意味着依物之所是而认识、把握物(用程颐的话来说则是“物各付物”),那么,物之万殊则势必体现为“名”的分化,“名”也就承担了辨别事物——即董子所谓“别物”——的功能①苏舆曰:“万物总总,藉名以散殊之。”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80页。。或可谓,“名物如其真”即意味着“别物”。首先,“名”有洪、私之分,所谓“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私名,此物也,非夫物”[3]99。凡一切存在皆可名之为“物”,故谓“洪名”,又谓“皆名”②《说文·白部》:“皆,俱词也。”又《仪礼·聘礼》“三揖皆行”,郑玄注曰:“皆,犹并也。”《诗·大雅·绵》“百堵皆兴”,毛亨《传》作“皆,俱也”。可知“皆”之为并、兼、俱等相近之义。参见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页);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8页)。。物又各有其性,如鸟兽草木性质各异,黑白方圆各自不同,彼此相别而至于万殊,各以其一己之性而名之,故曰“私名”;其次,“名”与“号”的区分体现出详略之别:“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3]59-60钟肇鹏以为,所谓“号”当作《荀子》之“共名”解,其义可通[7]651。暴君、仁君,其为“君”者一也;顺民、公民,其为“民”者亦一也,下文由“祭”之“号”,而分为春祠、夏祗、秋尝、冬蒸之“散名”,由“田”之“号”,而分为春苗、秋蒐、冬狩、夏狝之“散名”,皆依从“名”与“号”之为详与略的区分,最终落实于“物莫不有凡号,号莫不有散名”这一自“物”而“号”,自“号”而“名”的详略之序。董子所谓“号”,承担了《荀子》所谓“共名”的角色,而自“物”到“号”,再由“号”到“名”(散名),正与《荀子》以“共”“别”区分详略或《墨经》所谓“达、类、私”者略同。
“名”之为“别物”,也并不仅仅意味着散殊万物。如果仅示以区别,则世界所呈现的面貌无疑是一片混乱。事实上,“别物”即已包含了整肃以秩序的义涵于其中,这一秩序即体现在“理”与“义”这两个范畴。就“理”而言,无论是作名词用的“《春秋》辨物之理”,还是作动词用的“《春秋》理百物”[3]20,无论作条理、分理还是整理解,都体现出赋予某种秩序的隐含意图。万物散殊而不可知,但“名”之为“别物”的功能即体现在分门别类、别嫌决疑、董理万物。譬如名册,个别的“名”仅仅用以命名个别的对象,而作为整体的“名”册,则有将秩序与规律灌注于“名”之集合的意义。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董子认为《春秋》可以起到“辨物之理”或“理百物”的作用,因为其中所记名物繁复,且圣人于一字行褒贬,于用名上则不免要锱铢必较。
如果说“理”大体倾向于就“物”而言,那么“义”则更倾向于在人伦世界中发挥作用。《天道施》篇:
名者,所以别物也。亲者重,疏者轻,尊者文,卑者质,近者详,远者略,文辞不隐情,明情不遗文,人心从之而不逆,古今通贯而不乱,名之义也。男女犹道也。人生别言礼义,名号之由人事起也。不顺天道,谓之不义,察天人之分,观道命之异,可以知礼之说矣。见善者不能无好,见不善者不能无恶,好恶去就,不能坚守,人道者,人之所由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万物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而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义从也,故正名以名义也。[3]99
上述文字从论“名”之“别物”功能起笔,却通篇围绕“义”字展开。首先,亲疏、尊卑、远近、详略即是“义”的具体呈现。《精华》篇曰:“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3]22“义”代表的是人伦秩序——当然也包括《春秋》文辞——中所体现出的差别意识,这与董子所谓“别物”之“别”合契;其次,“人生别言礼义,名号之由人事起”[3]99,即从生成的角度将“名”组织进“礼”(义)的范围。人生于天地之间,本无所谓君臣父子之名,礼制而义定,则有尊卑之序、上下之别。其中,君臣父子之“名”与上下尊卑之“礼义”是表与里的关系。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草木鸟兽之名,也只有在进入人类世界之中才被赋予名号,其存在乃至使用也就有了一定的限度与规定。换言之,“名”是“礼义”所代表的人伦秩序的外在呈现;第三,“正名以名义”,通过将“义”的范畴嵌入“正名”的理论。命物以名就不仅要合乎“义”,同时更要彰显“义”。这与《左传》桓公二年“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的逻辑如出一辙①《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晋国大夫师服针对晋穆侯名子曰仇一事发表议论:“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名,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可见命名关乎道义、礼法、政事等各个方面。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3页)。。
总的来说,董仲舒对于“名”所具有的“真物”与“别物”功能的理解大体上未能超过先秦名学思想的基本框架。不过,经由上文的讨论可以进一步明晰:“真物”即内在包含了“别物”,而“别物”也绝不是“别离分散”以至于万殊。区别的同时即意味着整肃以秩序,对“物”而言则是赋予“理”,对“事”而言则是制以“义”。从认识与语言的角度来看,将“理”赋之于“物”,才有可能进行认识的拓展与逻辑的推演;从经学自身的脉络来看,将“义”赋之于“事”,则可以在《春秋》之辞中体圣人之微。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理”与“义”——即作为“物”的内在规律与秩序——究竟以何种面貌呈现?散殊之万物究竟又如何进入这一秩序的人道世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妨在董仲舒对于“物”的解读中予以进一步明晰。
三、一元、耦合与推类——“物”何以有规律
在认识或语言的论域中,“物”作为“名”所指称的对象始终呈现出一定的规律,不可言说或不可认知的“物”,或“物”之为“物”的本性则非“名”所能范围。换言之,命物之“名”便具有了赋予万物以一定规律的功能。荀子所谓“共名”与“别名”之分,董子所谓“洪名”“私名”之别,即体现出“名”所承担的分门别类、董理万物的职责。不过,仅从共、别区分“物”之详略仅仅是“物”的规律之一隅,董子对于“物”有着更为周密的思考。
“天”之于万物的本体论意义,使得万物散殊却系于“一元”。作为认识和语言的对象,“物”的存在始终处于与人的交互之中,但人如何认识与把握对象的问题,则涉及认知与言说的主体与客体自身的条件及其限制。一方面,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其认识与言说的官能本即有限,对于不可名之“道”,对于“物”之为“物”的本性,都是认识或语言所无法触及的边界,甚至天地之广、万物之博,也总在挑战着有限个体的认识边界;另一方面,圣人制“名”的意义在于将万物分科别条,但作为认识与言说的对象,势必要由“博”而转“约”。或者说,分科别条之依据何在,此物与彼物何以可以按照特定的规则予以分门别类,董子显然将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托付于“天”。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3]85。可知,天地万物共有一个“祖”,即生成的、形上的本体,也就是“天”。立足于人类世界,则是“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3]33。“元”字的含义当然十分丰富,如以“天”为“元”,以“元”为“元气”,以“元”为“纯时间概念”等①“元”作为本原不难理解,即便在《春秋繁露》中亦有这一含义。如《立元神》篇:“君人者,国之元。”等。持“元”之为“元气”的说法可以远绍至何休《公羊解诂》,其言曰:“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徐复观、金春峰等学者即持此说。周桂钿则主张一种“元一元论”,认为“元”是一个纯时间的概念。参见何休解诂,陆德明音义,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7页;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第328-329页;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还有一种对于“元”的解释或许更衷于《春秋》,即将“元”视作“人君”。刘敞《春秋权衡》:“元年者,人君也,非实太极也。以一为元气,何当于义哉?其过在必欲成五始之说,而不究元年之本情也。”这一解释本身实出于宋代《春秋》学者舍传求经的解经方式,如若准之以《公羊》传文,则断不如是。参见刘敞《春秋权衡》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七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55-266页)。。若仅从“物”的角度看,仅将“元”视作本原即可,而这一本原即是董子所十分推重的“天”。而所谓“属”,《说文·尾部》作“连”解,可知“属”即连及、联属之意[8]。圣人的工作即将天地万物联系于一,也就是“天”。其说虽然本《春秋》而就人伦政事立言,亦可推之于一般意义上的论“物”之说②“《春秋》变一为元”“春正月”等,显然是就《春秋》所谓“五始”之说立论。其所谓“物”,自然也偏向于“事”的面向。又如《立元神》篇曰:“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即站在黄老的立场上强调为君者的重要性,“万物之枢机”,当然侧重于政事,却亦含庶物于其中。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第37页。。一则,人与天地万物均以“天”为“本”、为“元”,且人的认识与言说官能亦象天而成,作为认识与言说工具的“名”与“号”亦本于天地,以此认识与言说才成为可能;二则,天地万物在本源上的相通担保了在认识与语言的层面上对“物”的把握可以采取循理、比较、类推等方法。换言之,“物”所呈现的规律并不在于“物”自身,而在于“天”的背书。更进一步,“天无所言,而意以物”,“天”不仅为“物”之规律与秩序背书,同时也可以由“物”之运化来呈现“天意”,故“君子察物之异,以求天意,大可见矣”[3]95。
“天”不仅将万物系之于一,以奠定“名”得以命“物”的基础,也在“物”的具体展开中呈现为特定的规律。天道分列阴阳,于“物”而言则为耦合。《楚庄王》篇:“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3]10又《基义》篇:“凡物必有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3]73所谓“耦合”或“合偶”,即以阴阳的对举为范式来范围天地万物。苏舆注曰:“物皆有所合,以为阴阳。就一物言之,亦各有其阴阳。身以背面为阴阳,背面又以带上带下为阴阳,山以前后为阴阳,气以清浊为阴阳,质以流凝为阴阳。”[4]342也就是说,万物皆可以阴阳而范围之,一物又有一物之阴阳。不过,“物”虽有合却无会,譬如阴阳于四时之运行总是交而替之,所谓“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3]71。又:“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3]72就论证阴阳交替运行,事物运转有其自身的消长规律而言,主张“物无合会”并无可怪之处。不过董子却以之论证阳尊而阴卑,以为君尊于臣、父尊于子、夫尊于妻张本,却指向了特定的价值观念。总之,“阴阳”作为“天道”领域的一对范畴,在“物”的论域中可以直接转化为耦合的认识规律。
以阴阳范畴背书的“物”之耦合作为规律尽管可以范围天地万物,但仅以两分的方法看待世界未免失之过简。“类”范畴的引入则进一步将“物”的规律予以细致、条理,所谓“类”,大抵可以理解为范畴、范式,归于某一类者皆有相似或相同的特性。首先,天与人的关系可以用“以类合之”来概括。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政有庆赏刑罚,皆“天人合类”之效。而在《人副天数》篇中,天与人的关系又呈现为“副类”与“副数”两种,所谓“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3]75。其说虽以天人立论,亦范围百物,或作为在天人之范围内被安排的对象,如“春生夏长,百物以同;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或作为被“副”的对象,如“腹胞实虚,象百物也”。无论如何,“物”始终被置于天人之以“类”(或以“数”)合之范围内;其次,“天有十端”,“端”亦可视作“类”。《天地阴阳》篇:“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故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之此。圣人何其贵者?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投所贵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3]98-99“天”之十端作为事物之萌芽、发端,同时构成了事物的端绪与要点,万物虽殊,亦可以“十端”范围之。所谓“投”字,钟肇鹏引《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投劾而去”,以为“投”作“下”解,以为“投”表达的是“‘物’是下于所贵的十端,而不在十端之中”[7]1087。“十端”代表了某种特定的性质,而具体的“物”虽然具有某种属性,却并不就是那种属性,即便是“五行”之“木、火、土、金、水”,也并不指称具体的五种实存的物质。在此意义上,天地万物皆可在一定的意义上归类于“十端”。值得关注的是,作为认识与语言——或者说用“名”制“名”——的主体,“人”在十端之中有超然的地位,换言之,在人与物之际,天与人之际,“人”始终占据主导的位置;再次,“类”的规定不仅在静态的意义上将散殊的万物依照特定的性质归于一“类”,也促成了物与物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在《同类相动》篇中,作者以“平地注水”“均薪施火”为例,又以“同气则会,同比则应”为证,试图说明:“物固以类相召。”“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3]75从“物”的角度而言,“以类相召”使得“物”的运动有迹可循。对人而言,董子以灾异劝导善政的理论根据亦在于此。因为在董仲舒看来,所谓“灾异”大抵皆是人事之应,圣王之政召至祥瑞,暴政之行致使灾异;最后,仅就“物”作为认识与语言的对象而言,“类”的规定使得“比类”与“推类”成为可能。在《深察名号》篇中,董仲舒明确以禾米、卵雏为喻,最终推出性待教而成善的结论,其论证的关键环节即所谓“比类率然”,即以同类之相通来勾连起卵-雏、禾-米和性-善的关系。又:“推物之类,以易见难者,其情可得。”[3]98由推物类则可以体物情,这是推类方法的一般表达。而在《春秋》之中,“属辞比事”的方法原则上即是一种类推论证,董子对之即有明文,其言曰:“《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翻援比类,以发其端。”[3]13又:“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3]24可见,以类推之方法解读《春秋》,可以范围天下之所有庶务与政事。
从一元到耦合再到推类,董子对于“物”的解读建基于“天”的本体,又在逐渐条分缕析,最终所追求的是实现像郊祝之辞所谓的“庶物群生,各得其所”的状态[3]84。从“天”之本体到阴阳之耦合,再到“类”之推于“万物”,这不仅是董仲舒的“物”观念在其本体论的基础上的分化与衍生。也可以在“名”的——确切地说则是认识与语言的——论域中为“物”提供内在的秩序。
总之,本文分别从名物、真物与别物的角度分析董仲舒的“物”哲学。董子所谓“名物”与孔子主张《诗》教之“名物”不同,董子基于《春秋》“五石六鹢”的诠释所主张的“名物”观念,更侧重于“名伦等物”的含义,既包含了草木鸟兽之名,也包含人伦与政治制度,且以后者为重。若回到董子所谓“名物”的本义——即以“名”命“物”的含义——来看,“名”与“物”的关系作为名学思想的基石,又在“真物”与“别物”的意义上得以强化。“物各付物”即意味着把握、认识万物各以其性,因此,“真物”又内在包含了“别物”。而将“物”分门别类则意味着整理万物,或整肃万物以秩序。这一秩序在董仲舒对于“物”的体认中可以进一步领会,建基于“天”的本原为认识与把握“物”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而阴阳之耦合则是认识、领会天地万物之基本规律。“类”的引入则使得推类成为可能,由推类出发,则可以触类旁通,范围天地万物。
——评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