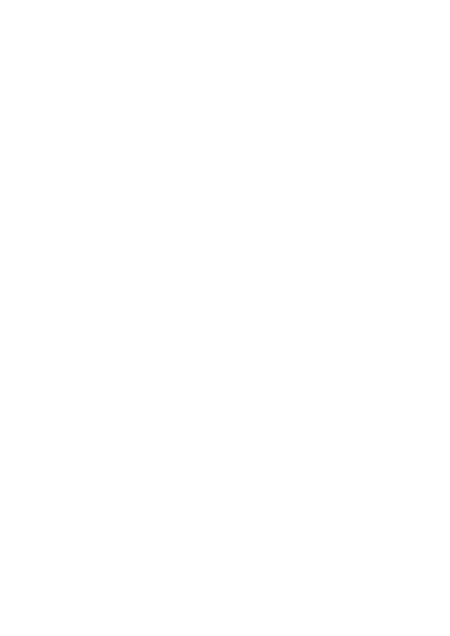从《性命古训辨证》看傅斯年的古史观
雍 蕹
(吉首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416000)
傅斯年在中小学时期接受的是最为传统的中国教育,虽有学习新思想,但总归是在中国的传统学科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傅斯年1916 年进入北大国文科,这一时期在学业上迅速成长,在中国传统文学、语言方面的学习为后来转向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傅斯年学术著作、学术思想的研究从未断绝。早期学界将他认定为史料学派在中国的代表学者,事实上他虽重视史料学,但他同样不排斥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以及对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傅斯年从赞同顾颉刚“古史辨派”的治史方法开始对史学研究产生兴趣,游学归国后走向“古史辨派”的对立面,与顾所代表的学说开始分庭抗礼。再到《性命古训辨证》的发表,他希望通过对史料的整理、解释,将西方的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经学训诂结合在一起,验证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史学道路。傅斯年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也对“破后而立”有了更大的野心。
一 从《性命古训》到《性命古训辨证》
《性命古训辨证》一文发表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此时傅斯年已担任史语所所长十年之久,与顾颉刚的学术论争也进行了十多年。这一时期的傅斯年已经将自己在西方的所学与传统的经史文学内化吸收完整,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傅斯年为何会选《性命古训》来做辩证,来立出自己不同于时人所推崇的“古史辨派”的古史观,这一点除去傅斯年师从章太炎的古文经学学习经历外,《性命古训》自身具有的语言、文学、史学价值也值得傅斯年去做这样一篇辩证。
(一)社会价值
《性命古训》是阮元经学研究中比较重要的篇目,在清时,训诂考据成为主流,整理先代思想、经史文集成为每个学者必行之事,阮元作为对传统经学考较深厚之人,是不可能免其俗的。辨析传统经学诸范畴,也成了阮元做学问必经一环。实际上《性命古训》不光是考察其源流,更多的是如何建立不同于先代的“性命”观。阮元反对唐李翱的“复性”之说,提倡节性,重个人道德,行家国之治。江藩对阮元《性命古训》所立之意有着更为深刻的看法:“宋儒性命之学,自谓直接孔孟心原,然所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初,实本李翱《复性书》,以虚无为指归……云台尚书述圣经古训以诎之,使千古沉霾之精义一旦轩露,可谓功不在禹下。读是书者,勿以旧说汩之,尽心以求其蕴,存性以致其用。大可以探礼乐之原,致治平之要;小可以进德居业,乐行忧违矣。”[1]《性命古训》所探讨的内容已经扩及到了人的社会责任之中,人欲与社会道德如何相协共生。
(二)思想价值
《性命古训》问世于一个重考据、轻本源与创新的旧学环境下。虽然所释义理,有“新瓶装旧酒”之嫌,但阮元意图避乾嘉学派烦琐考证,“另开新局”的做法还是很有借鉴之意义。对于《性命古训》的成书,阮元与陈寿祺的书信来往中这样说道:“生近来将胸中数十年欲言者,写成《性命古训》一卷,大抵欲辟李习之复性之书,而《书·召诰》节旨为主,少暇当再抄寄。”[2]阮元的经学思想并不限于只做训诂一途,追随乾嘉学派的脚步,阮元更希望可开新途,在深化内涵一道上有独立作为。傅斯年正是看到了这点,选择传统经学中并不显眼但又具有打破意义的《性命古训》来佐证自己对于历史研究发展走向的看法,试图做到破而后立。阮元的《性命古训》是“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是对传统训诂学的一次总结,加有一些开创之意;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则是更大程度上的总结,不光是在传统治学方法上面,更是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打破和创造。思想的问题总是会有许多复杂性,用辩证一词来探析“性命”义理,既有古代传统训诂治史之意,又有西方语言学的方法。这篇《性命古训辨证》的写作用意并不在训诂一途上,而是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的整理,以及对其开端源起的思考。在傅斯年看来,中国的思想并不是哲学的、宗教的,而是有异于西方思想发展的独特路径。从西汉开始,中国的思想发展进入了另一个时期,从“百家争鸣”开始走向集百家之长的“杂儒”之路。儒学成为官方思想,从汉的性二元论向宋明理学不断演进。“性命论”也日渐成熟,成为研习经学的必要理论。
(三)方法价值
不断开拓是傅斯年治史的核心方法,但他也并不提倡一切只求“新”而忽略“旧”。“旧”与“新”之间对错并不是一概而论,要如何使用也与其真实性相关,对待语法、词句方面要更多一些谨慎的态度。训诂的要点是在语音方面,但超越前代势必就要用新的材料来支撑新的观点和论断。通过字形、字音、字义来辨析词的发展本源,傅斯年与阮元有同样的想法,只有弄清文字形、音、义之间的关系,才能窥探经学之指归,回到中国思想史发展开端的地方,探究“性命说”与“天人论”最本质的关系。这里面也能看到傅斯年对于语言学如何辅助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体现,与训诂相同夹有西方语言学的特色,来辅证自己的观点:“ 春秋时有天道人道之词,汉儒有天人之学,宋儒有性命之论。命自天降,而受之者人,性自天降,而斌之者人,故先秦之性命说即当时之天人论。至于汉儒天人之学,宋儒性命之论,其哲思有异同,其名号不一致,然其问题之对象,即所谓天人之关系者,则并非二事也。”[3]第2 卷,568“性命说”与“天人论”是同一个本源、两种不同的发展。
同时,傅斯年借用当时出世的大量考古材料,引用大量的殷周彝器铭识,借用先代与当代金文学成果,不仅仅只是侧重于阮元所用《尚书》《孟子》。有学者对本篇做了一个总结:“傅斯年搜集卜辞、金文中有关性、命二字的资料二万余条。”[4]增加新材料来解旧题,用“直接史料”来证明“间接史料”,做最细密的研究,这是傅斯年毕生志向。
二《性命古训辨证》从“疑古”到“考古”
《性命古训辨证》是傅斯年从语言学的角度剖析中国思想史的作品。从史语所建立开始,傅斯年着手打破中国旧的史学话语体系,同时也在思考怎样建立起不同于明清考据学、不同于西方实证学派独立的东方学话语体系,构建发端于中国内部领先于世界的史学话语体系。《性命古训辨证》是傅斯年史学“立”的开端,也是代表傅斯年古史观的作品之一,是他不断思考后的一次尝试,是他从五四运动开始将“破后而立”的思考付诸构建新史学体系的一次实践,是逐步建立“要科学的东方学在中国”的一次努力尝试。
(一)“疑古”风潮
在傅斯年游学期间,国内学术界掀起一股改革风潮。首先是史学界的“疑古”风潮,其次是思想界发生科学与玄学论战。1926 年,远在国外留学的傅斯年知晓国内发生的史学论战后,在给胡适的信中表达赞同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①[5]同年,傅斯年在给顾颉刚的信中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古史辨”这一论断有极大的兴趣。“在当时本发愤想写一大篇寄去参加你们的论战,然而以懒的结果不曾下笔而努力下世。”②[3]第1 卷,447
此时的傅斯年赞同顾颉刚在古史研究方面的思考以及一些学术贡献,对于乾嘉学派在史学研究领域的突破是非常认同的,但对于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看法又有诸多的分歧,尤其是在经史重合的方面。傅斯年“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他致信胡适,提出语言学在研究中国古代方术或思想史的重要地位,在自己学术笔记中留下有关中国古史的灵感记录。这些迹象表明,他的学术境界正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③[6]
傅斯年回国后,一改之前对疑古派赞同的态度,开始了另一种理论上的重建。他看到新史学方法的可行性,并开始进行理论建构。比起疑古派一味地怀疑古史、重传说经历、不论史实,因史料不传而判定史实为假而言,傅斯年有了新的想法:“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3]第2 卷,103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切不可从这不充足的材料中抽结论”。
1928 年,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一职,正式站在顾颉刚学术研究的对立面,开始对顾颉刚破坏后的古史研究进行新的建设,这与他之前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对文学革命以及五四运动冷静后的思考一样,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史学界的“疑古”思潮大论战。
虽然傅斯年在学术论战中站在了顾颉刚的对立面,但傅斯年的研究中并没有完全抛弃“疑古派”的一些治学方法。顾颉刚的“古史辨”是破的开端,传统史学的研究路径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但新的路径是全盘接受西方的,还是由新的和传统的并行发展,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考量的,中国古史的复杂性不是单纯“疑古”就可一劳永逸的。破坏具有两面性,破后而立,立比破更为紧要。傅斯年在五四时期的热潮过去后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提到破坏是不能长期执行的:“(1)长期的破坏,不见建设的事业,要渐渐丧失信用的。(2)若把长期破坏的精神,留几分用在建设上,成就总比长期破坏多。(3)发表破坏的议论,自然免不了攻击别人,但是必须照着‘哀矜勿喜’的心理。”④[3]第1 卷,156破坏之后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也影响到他之后对于史学方面的一些研究倾向。
(二)“考古”的史学方法探索
在傅斯年看来,“掘地三尺”的考古发现是重要的,证实现存文书的清白也是重要的。他在1926 年给顾颉刚信中的称赞是不作伪的:“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论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素,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3]第1 卷,447那么傅斯年担心的不是考古资料推翻疑古派的论调,而是“古史辨”的讨论会对传统丢得太过于彻底,脱离历史现实,脱离史料,不断证明逻辑的正确。
傅斯年揭起“史料学”的大旗,无论打击的对象是谁,其以“立”来“破”的隐曲应该是存在的,这从他的史学著述中也可看出。立是为了破,破是为了更好地立。怎么立,怎么破,在傅斯年看来是方法论的问题也是如何进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问题。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思想史的问题,无疑会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更是让学界看到考据和考古学的应用,促进传统经学的发展。夫子自道承认史料的有限性,肯定历史的丰富性,同时用扎实的经学功夫与丰富的考古资料证实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驳斥一切未经史料证实的“神话”推论。用傅斯年的“从语言学来看历史”观点看《性命古训》,“性命”为中国思想的本源的契机,成为为何“破后而立”的关键,揭示了傅斯年的古史观,“即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问题是也”。[3]第2 卷,505
“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7]是疑古派惯用的方法,疑古成为风潮后就会出现“百千年后人曲喻百千年前事”[3]第2 卷,59。按照疑古派建立的学术逻辑看,历史的真相是让位于逻辑合理,一味疑古就会出现历史虚无主义。傅斯年希望的史学不是一味疑古,也不是传统汉学中的一味信古而不加考证。对待距今较为远久的历史时,历史的不知道不代表不存在,依照逻辑推理出的古史虽然有可信的地方,但仍然不是具有真实性的历史,容易进入一种自我思维的误区,当下逻辑合理的推理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不具有同一性。
逻辑推论远没有可靠的考古资料来得真实,就像《性命古训辨证》中对于殷商文化发展程度的推论,就是依靠足够可靠的考古资料得出合理推论。历史推论的可靠性极低,考古资料可以推进古史不断发展,并确定和辨析一些历史疑点。
傅斯年撰写《性命古训辨证》时,中国的考古学有了一定的发展,大量考古资料的发掘,使得史学发展有了更多的路径。其实在傅斯年的理念中,考古的定义与现代考古学是不同的,考古应该是两考:一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的传承,二是西方传入的“掘地三尺”考古。从傅斯年史语所建立的初衷和旨趣也可看见这样一种倾向,而《性命古训辨证》就是传统与西方结合的史学实践。从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思想史的发展,辅以各类新发掘的考古材料,同时也没有放弃传统考据学的要义,从音、形、字对字词进行释义,这些都代表傅斯年从疑古到考古的史学方法上的探索和总结。
三 从传统汉学到“东方学”
在傅斯年看来,汉学的进一步发展不能止于语文学的成绩,在史学方面也应该更有进益,打破一些固有的束缚。同时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也不仅仅止步于汉学的框架中,而是建立中国的“东方学”。《性命古训》是传统汉学的作品,就像前文中所说,虽然有突破,但研究方法并没有新的改变,也没有更新的材料出现。《性命古训辨证》虽对阮元的《性命古训》是一个补释,不赞同傅斯年此作的会认为只是一个材料的扩充,没有对经学和史学有着实质的发展。实则不尽如此,材料的补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如何用新方法、新材料去做旧命题才是其中真意。傅斯年的史学革命有受他早年跟随胡适文学革命的影响,他想打破旧的束缚,但并不是彻底抛弃一切旧的因素与方法,更不是怀疑一切历史存在。傅斯年是一个具有强烈思考意识的建设者,他从不认为西方的一切都适合中国,更不认为中国的未来必须都是西方的。
在五四运动开始前,傅斯年就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疑虑,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他就指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因为中国人遗传性上有问题。”“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3]第1 卷,245傅斯年认为中国改革应是自下而上地徐徐图之,而非一阵风潮,风潮过后湮灭无声。从1928 年史语所建立到1938 年《性命古训辨证》的发表,傅斯年提出要建设“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3]第3 卷,11这一发刊语已有十年。傅斯年在史语所创立之初学术野心就已经不止于国内的汉学正统,也不是国内史学短暂几年的研究热潮,对于傅斯年而言,不仅仅要做一个传承者,更想做一个开拓者,从史语所建立开始,傅斯年就在做各种尝试。《性命古训辨证》有尝试,但更像是尝试过后的一种试探性的融合,也是一种总结,总结自己的史观和积累的方法,为“东方学”的建立在思想史方面作新的尝试和探索,建立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学方面的现代化认同。
(一)打破中华文化“西源说”
傅斯年并不赞成中华文化的“西源说”,这一点在《性命古训辨证》里可见大致:对于中国古文化最早发展,尤以殷商文化而言,“即以文字论,中国古文字之最早发端容许不在中土,然能自初步符号进至甲骨文字中之六书具备系统,而适应于诸夏语言之用,决非二三百年所能达也。以铜器论,青铜器制造之最早发端固无理由加之中土,然制作程度与数量能如殷墟所表见者,必在中国境内有长期之演进,然后大量铜锡矿石来源之路线得以开发,资料得以积聚,技术及本地色彩得以演进,此又非短期所能至也。此两者最易为人觉其导源西方,犹且如是,然则殷墟文化之前身,必在中国东西地方发展若干世纪,始能有此大观,可以无疑。因其事事物物皆表见明确的中国色彩,绝不与西方者混淆,知其在神州土上演化长久矣”[3]第2 卷,595。虽然在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可以窥见与西方相同的部分,但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仍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西源说”是对中国古史缺乏正确认识的表现。
同时,傅斯年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是由多个高级文化融合而成的。在殷商以前,中华大地上不止有夏文化一源,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高级文化共同发展。“殷墟文化系之发见与分析,足征殷商以前在中国必有不止一个之高级文化,经若干世纪之演进而为殷商文化吸收之。”[3]第2 卷,595夏文化是否存在,还未有具体论证。“然夏代都邑,今日固未遇见,亦未为有系统之搜求。”[3]第2 卷,595(傅斯年撰写此文时“二里头文化”还未发掘)
(二)精神文明的变革
傅斯年认为商周之际是历史文化大变革时期,这种变革不是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而是精神文明的变革。“故曰,殷周之际大变化,未必在宗法制度也。既不在物质文明,又不在宗法制度,其转变之特征究何在?曰,在人道主义之黎明。”[3]第2 卷,587傅斯年为何会有如此说法,主要是考古发掘出的商代器物与周初期器物没有太大变化,技术也未有变革性发展,但一项传统的古老习俗(大规模的人殉)在逐渐消失。“年来殷墟发掘团在清理历代翻毁之殷商墓葬群中所得最深刻之印象,为其杀人殉葬或祭祀之多。如此大规模之人殉,诚非始料所及,盖人殉本是历史上之常事,不足怪,所可怪者,其人殉人祭之规模如此广大耳。”[3]第2 卷,587到春秋战国时,大规模的人殉已经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始作俑者”。同时“殷墟记载所表示之思想系统乃当时王家之正统思想,虽凭借之地位至高。却不必为当时最进展之思想,且必较一部分王臣之思想为守旧。世已变矣,而统治者不能变其心也。变其心者,新兴之族,新兴之众,皆易为之,而旧日之宗主为难”[3]第2 卷,585。所有的改革都已经迫在眉睫,要么从内到外改革,要么从外到内改朝换代,进行一次彻底的更迭。
另一项变革,则是“人定胜天”的自信。天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代指,对人的行为、思想没有束缚,同时这种“人定胜天”的自信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开端。“盖古代人自信每等于信天,信天每即是自信,一面知识发达,一面存心虔敬,信人是其心知,信天是其血气,心知充者,血气亦每旺也。”[3]第2 卷,589
一个高度发展的文化,不是突然跳出来的,势必要经历漫长的发展期,在发展过程中也会留下许多文化遗存;这时考古学的方法、考据学的方法就可以辅助史学研究的更进一步。不知道不代表没有,未发掘不代表不存在,就古史研究而言,不断扩充新材料、新方法是有必要的。在傅斯年看来,一味遵循某种要求的研究是不合适的,要不断探索新意,更要做到研究中的通达。破与立不是对立而是互相服务,为古史研究服务,为现代史学发展服务。史料不是束缚理论的绳索,而是推进历史研究的工具。
四 结语
傅斯年反对“国故”“疏通”,“认为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3]第3卷,10,反对所谓“普及”。按照自然科学的态度、方法研究史学,能使其达到更接近科学的程度,史学相较于其他人文学科,更像一门科学,积极地靠拢科学,并成为一门严谨而有力度的科学。打破旧史学带来的束缚,就应该立出新史学。观念方法都应有所变化,如同顾颉刚的“古史辨”,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是真真切切地为大众服务,了解更多考据之外的新材料、新视野、新方法,不断创造新的学术高峰,不拘泥于一家一姓之言,互相借鉴,吸取经验教训。史学工作是集体工作、集体的智慧,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更有发挥的前途,它需要互相补充,也需要严谨认真,更需要夯实基础、不断开拓。
注释:
①傅斯年致胡适的信,1926 年8 月1 日,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七册。
②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史书》原载于1928 年1 月23日、31 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三、十四期。
③有关傅斯年留德时期的学术思想变化,参见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收入《新学术之路》上册。
④傅斯年《破坏》原载1919 年2 月1 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