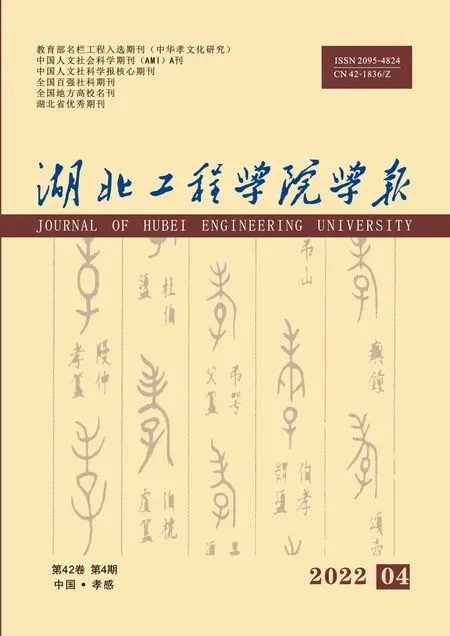人类学孝道研究:走向整体实践的“孝道”
王天鹏
(淮南师范学院 法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一、问题的提出:多学科视野下的孝道研究
了解一个民族或族群,必先了解其文化。文化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文化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生活包罗万象,文化也纷繁复杂。社会生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则是人们社会生活的抽象体现。文化可以分为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与此相对应的生活传统则也相应地可以分为精英文化大传统和民间文化小传统。[1]
“要了解中国社会系统的性格,特别是它的安定(或不安定)的原因,有一个可用的研究角度即是寻找社会中普遍流行而具有社会规范作用的文化概念”,[2]孝道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概念。孝道研究与其他诸如“关系”研究、“人情”研究、“面子”研究、“报”的研究等一起构成了研究者以中国本土文化概念来挑战西方主流话语努力的至关重要的方面。
《说文解字》里许慎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就是讲的老(父辈)和子(子辈)之间的关系,当父母年老的时候,子辈在下面把父辈支撑起来。也就是说孝实际上指的就是亲子关系,以子辈对父辈的赡养为主。“善事父母者”,孝道首先是关于奉养父母的准则,即在家庭中晚辈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子承老也”,孝道也是父辈到子辈之间的传承继替,因此也形成了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香火观念。
几千年来,关于孝的典籍浩如烟海,对于孝道的研究集中于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尽管各门学科同样是关于孝道的研究,但关于孝道研究有所侧重,如政治学的孝道研究主要集中于孝道与政治观念、孝道与国家治理、孝道与社会秩序等的研究(1)代表性的研究有王垒:《传统孝道伦理与现代政治文明》,《学术论坛》2005年第2期;马海军、贺小霞:《中国古代孝道与政治》,《理论月刊》2005年第2期;黄修明:《论中国古代儒家孝道政治观念中的“人臣之孝”》,《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3期;魏艾:《传统“慈孝”美德的农村现代治理之维》,《东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刘芳:《社会转型期的孝道与乡村秩序——以鲁西南的H村为例》,上海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等。;历史学的孝道研究主要集中于各个朝代、时期孝道理论的具体实践、传承与变迁(代表性的研究有李洪权:《论金元时期全真教对孝道伦理的维护》,《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郑彦君:《历史上的孝道入法》,《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范兴昕:《论孔子孝亲观在两汉时期的异化》,《东方论坛》2014年第6期;关健英:《从魏晋时期的孝道讨论看传统孝道的变迁》,《哲学研究》2013年第9期等。);伦理学的孝道研究主要集中于诸子的孝道伦理观、大儒先贤对孝道伦理的观点与阐释等(2)代表性的研究有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陆爱勇:《孔子“孝”的伦理意蕴与道德自觉》,《东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周延良:《“孝”义考原——兼论先秦儒家“孝”的伦理观》,《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陈睿瑜:《论曾子以孝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伦理学研究》2010年第5期;王武林:《宗教伦理孝道观及其现代价值》,《理论月刊》2014年第5期等。;社会学的孝道研究主要集中于孝道变迁所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城市与乡村中的养老、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与养老相关的社会自组织问题等(3)代表性的研究有风笑天等《机构养老与孝道:南京养老机构调查的初步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潘剑峰《论传统孝道中的养老思想》,《学术交流》2007年第4期;李琬予等:《城市中年子女赡养的孝道行为标准与观念》,《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李志强:《西方养老保障制度对我国孝道文化传承的立法启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胡宜等《复兴孝道:老年组织与农村养老保障——以洪湖渔村老年协会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徐元君:《孝道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等。。当然,各个学科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多数研究是两个学科或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孝道研究,都注重孝道的宏大叙事,大多数是从官方或学者的立场考察孝道的政治作用、孝道的历史变迁、孝道的伦理准则等,同时,上述诸学科的研究大多从制度层面考量孝道,而很少关注到孝道背后数以亿万计的活生生的人。社会学与前述学科不同的是,开始关注孝道背后的人,但所关注的更多的是群体的人而非个体的人。那么,有没有一个学科所关注的孝道研究更倾向于孝道的原初意义,如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孝道所进行的研究?人类学的孝道研究即从民间文化的立场、从最底层孝道主体的视角进行研究,也更接近孝道原初含义的研究。笔者在这里作此类区分,并不是故意贬低其它学科的研究,抬高人类学的孝道研究。因为各个学科的研究并无高低上下之分,而只是学科本位不同,研究视角不同而已。
文化研究可以分为两种研究视角: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主位研究指研究者尽可能从被研究对象的视角去审视理解当地文化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高于自身的位置,把研究对象的描述和分析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主位研究高度熟悉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知识体系、分类系统。通过研究者深入的参与观察,最终做到能够像本地人那样思考和行动。客位研究指研究者以文化外来或以专家或学者的视角用比较的或历史的观点看待田野调查收集到的民族志资料,从而对被研究对象日常行为的原因和结果作出解释。根据主位和客位的视角来看,传统的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倾向于从客位的视角对被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新锐的研究者也开始尝试从主位视角研究报道人的文化,但到目前来看,这还只是一些有益的尝试。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分为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不过从目前来看,质性研究者还不是目前研究的主流。而对人类学来说,主位研究是其研究的最基本视角,否则就是一个不合格的人类学者。
人类学的孝道研究虽然也会对制度层面的孝道进行研究,而且关注到孝道背后活生生的人。不同于其他学科孝道研究的视角是,人类学的研究更多地是从民间的视角审视孝道,更多地把抽象的孝道同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孝道不仅被视为一种伦理制度,更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元素,视为粘结和整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性因素。人类学的孝道研究不仅关注子女对父母的孝养、赡养,也关注父母对子女的慈祥和关爱,关注双方的物质和情感的交流,这种交流不同于市场经济的交换,更多的是精神和情感的交流,此即代际交换的研究。人类学的孝道研究,不仅专注于代际交换的研究,而且关注驱动这种代际交换的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祖先崇拜即是这种因素。人们认为,父辈和子辈的这种交换不仅在人活着的时候存在,在人死后依然存在,子辈通过香火的祭祀维持着对父辈的孝敬,父辈则冥冥之中保佑着后辈子孙,无人祭祀的祖先则成为孤魂野鬼。为了使这种长久的祭祀不致中断,必须世世代代生育男性子孙,因为他们是传统社会香火的继替者,因此,才有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
人类学的孝道研究,还把孝道同面子、人情、关系等一起,当成以中国传统概念挑战西方主流话语的一部分,其背后的问题意识理所当然包括人类学的中国化,而不是紧跟在西方人类学理论背后亦步亦趋。当然人类学的孝道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关注和加强。梳理人类学的孝道研究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比较,评述其得失,是本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
二、人类学孝道研究的现状
人类学关于孝道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主要表现在代际交换、祖先崇拜和生育观念等学术领域,笔者在本文中将主要针对人类学界孝道研究的以上领域进行介绍和评述,并点明目前人类学界孝道研究的不足之处及今后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以期抛砖引玉,促进人类学孝道研究的反思。
(一)关于代际交换的研究
由于孝道涉及到父辈对于子女的抚养,子女对于父辈的赡养,因此可以将赡养看作是对抚养的回报或交换。一些人类学学者将互惠的概念引入代际交换的研究中,从而阐释孝道与代际交换之间的逻辑关系。
杨联升认为,孝道同家族系统的交互报偿原则密不可分。儿子因为受到了父母较多的照顾,尤其是在他们的幼年时期,因此必须以自己的孝道来回馈父母的养育之恩,父母养儿育女就是一种投资,子女以孝道来报偿。杨联升把孝子比喻成不能偿付他父母养老保险的不成功的生意人。[3]
费孝通则在比较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对中西亲子关系的模式对比后得出结论:中国和西方亲子关系的模式分别是反馈模式和接力模式。因此赡养老人在西方并不是必须的义务,但在中国,由于养儿防老的传统,却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儒家孝道在这种互惠式传递中起着最基本的维系作用。[4]
杨国枢认为传统中国以孝立国,孝是最重要的善行与德行。诸善之中孝最具有超越性,诸德之中,孝最具有普遍性。父母与子女之间以慈养孝,以孝换慈。子女是以孝行来交换父母所控制的某种资源,从而满足某种需求。亲子关系的运作中,“公平”的原则也必须遵守,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地维持孝道的行为。[5]
戴惠思认为传统的代际互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发生了动摇。城市与乡村的养老观念具有明显区别:乡村人的养老观念较多地建立在理性算计的基础之上,与此相比,城市人的养老观更多的是建立在感情互惠的基础之上。[6]
黄坚厚的研究与上述诸人的研究稍有不同,他认为古人所谓孝道,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以父母为对象的,而更多的部分是让一般人能够透过良好的亲子关系来促进子女健全人格的发展、人际关系的适应。孝道是一切行为适应的基础,而并不一定要让父母获得了什么。[7]
黄敏则认为上述研究基本上基于共时的、物质的研究,而对历时的,情感的代际互惠研究较少。而且,情感、精神的交换是无法量化的。其次,这种交换是延续性的,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虽然从两代人之间来看互惠是不对称的,但从三代人来看则是对称的。[8]
(二)关于祖先崇拜的研究
除了代际交换之外,祖先崇拜的研究是人类学界关于孝道研究的重点与核心。中国传统孝道除了体现在对生者的孝敬,还体现为对已逝祖先的祭祀,此即慎终追远。祭祀场所一般在家中、祠堂或墓地。人类学界对于祖先崇拜主要从作为沟通中国大小文化传统的祖先崇拜、作为宗族组织核心的祖先崇拜和作为神鬼中界的祖先崇拜三个维度进行研究。
1.作为沟通中国大小文化传统的祖先崇拜。杨庆堃认为,中国家庭中最重要的宗教内容是祭祖。后人所获得的幸福和成功都被看作是祖先功业的延续,是祖先荫蔽的结果。于是通过祖先崇拜,死去的先辈作为一种精神源泉始终激励着在世上活着的后人。杨庆堃认为,虽然士绅、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分别把祖宗崇拜看成哲学或宗教,但并不妨碍他们利用祖宗崇拜各取所需,在这个层面上,通过祖宗崇拜这个媒介,大小传统得以勾连起来。[9]
华琛通过文化标准化的研究也力图寻求能够勾连大小传统的因素。在对天后信仰的研究中,华琛认为对天后的崇拜能够把来自完全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包容在一起,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天后的看法,但这并不阻碍他们共同的天后信仰的存在,这就如同中国文化的缩影。因此,在创造统一文化中,基本标志的模糊性是一个重要因素。[10]在华琛的另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了文化标准化的问题。他说,如果有什么事物可以创造和维系着一个统一的中国文化的话,那就是仪式的标准化了。中国社会里有一套与人生周期相匹配的仪式动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婚礼和丧礼,普通民众按照被官方认可的仪式程序融入文化整合的过程。[11]
劳格文在对客家传统生活进行研究时认为,乡村生活被两种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与民俗所支配,分别和宗族社会结构和神明崇拜发生关联。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们要不断地为获取好风水而进行斗争,风水在宗族间的互动与空间的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2]
2.作为宗族组织核心的祖先崇拜。许烺光通过对大理喜镇的研究认为,从喜洲镇的文化来看,在祖先的庇荫下,对人格有着重要影响的两个因素是权威和竞争。祖先只会对后代进行庇护而不会伤害后代,这一观点引起弗里德曼和武雅士等人的讨论或质疑。(4)需要指出的是,许烺光是把大理喜镇的居民作为典型的汉族进行研究,而在民族识别中,大理的喜镇的居民却被作为白族。这也可以看出,大理喜镇的白族已经充分汉化,和汉族文化已经没有质的区别。[13]
弗里德曼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发现中国宗族成立的根本原因是对祖先的崇拜,并且在崇拜的过程中涉及到祖产。共同财产、高生产率的稻作经济以及宗族精英和国家官僚之间的连接是中国东南大规模宗族组织得以存续的基础;大规模的宗族组织、反国家的行动以及宗族之间的世仇成为地方宗族与国家权力关系持久张力中的来源。[14]
科大卫(David Faure)的《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的研究是对弗里德曼的“宗族其实是法人”的看法落实到具体的历史脉略中去。[15]
华如璧对香港新界邓氏家族的研究意在批驳弗里德曼的研究所导致的中国世系群研究所出现的混淆,尤其是在对阶级与继嗣之间关系的认识方面,作者认为厦村邓氏群的形成不符合弗里德曼的假设。[16]
3.作为神鬼中界的祖先崇拜。武雅士在其论文《神、鬼、祖先》中论述了台北盆地居民的信仰体系。他通过对台湾地区人们的三种崇拜方式即神、鬼和祖先的考察,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及这三种崇拜对中国社会的意义。而这种分类体系,是和中国人对自身及外界的宇宙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的论文认为中国农人的超自然的世界是他们社会图景的忠实复制。神是官员;鬼是土匪和乞丐;祖先是父母、祖父母”。[17]武雅士的论文一出,就埋下了争议的种子。
在武雅士研究的神、鬼、祖先三种分类的基础上,渡边欣雄认为,汉族的宗教属于民俗宗教,大体上由神明祭祀、祖先祭祀和鬼魂祭祀三种类型组成。诸神住在天界,鬼魂和祖先住在阴间。祖先就是这样的介于鬼神之间的存在。[18]
(三)关于生育观念的研究
《孟子·离娄上》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汉代经学家赵岐曾经在注释这一篇的时候写道:“于礼有不孝者三……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因此,对于各族群生育观念的研究成为人类学者进行孝道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中国村落社会的生育观念,不少学者已经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费孝通通过对江村的调查发现,在农村,人们结成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生育。传宗接代,当地称香火绵续,这意味着持续祀奉祖先,死者在另一个世界还能得到生者的照顾。[20]
李银河认为,中国村落的生育动机可以从物质动机和精神动机两个方面加以划分。她认为,在物质动机方面,传统社会人们社会孩子本身就是物质财富。儿子可以作为养老的寄托,现行养老法律也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从精神动机而言,生育可以满足个人成就感,可以用来传宗接代,可以满足天伦之乐。现阶段,村民的生育动机受到两个因素的限制,即社会经济因素和计划生育政策。[21]郑卫东也提到,在传统社会,由于法制观念淡漠,人们倾向于以暴力解决冲突,因而有生育男孩的冲动。因为,生育男孩可以娶妻生子,生育女孩也出嫁,村民也会认为养育女孩子亏本。另外,村民并不普遍认为多子多福,只是受节育技术的制约,才造成生育多胎的事实。这种多胎生育,也是客观上对当时高死亡率、低存活率的一种适应。[22]
不过,阎云祥根据自已对下呷村的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不少年轻夫妇满足于只生育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女儿的事实,这说明到了90年代末期,乡村已经出现了新的生育观,可以从人口学、性别学、经济学、社区等角度来分析这种新观念。[23]
三、走向整体实践的孝道:人类学孝道研究的反思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国、天下是三位一体的,而且是逐步递升的。齐家方能治国、治国方能平天下。国是大的家,家是小的国,家庭中的社会关系也一直延伸到国和天下之中。而在家庭中最主要的关系是亲子关系,维系亲子关系的是孝道。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即使贵为一国之君,也要非常重视孝道。
如费孝通所述,在传统社会中,个人和他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就像石子投入水中形成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4]这波纹的圆心,也就是以自己为圆心所形成的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家庭中的亲子关系。随着波纹一圈圈扩大,这种亲子关系,先是在家族内部延伸,如叔父、伯父均视为父亲的替身代为行使父亲权力。紧接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延伸,如师生关系、师徒关系也是一种拟制的父子关系:师父、徒儿。官民关系、君臣关系亦是父子关系的延伸:父母官、子民;君父、臣子。处理亲子关系的核心规则是孝道。而亲子关系又是其他任何社会关系的推演。换句话说,亲子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轴。除了父亲的儿子这一固有角色之外,每一个男子在社会中还需要扮演一系列角色,宗族的后裔、老师的学生、官员的百姓、皇上的子民,在这一系列角色中,孝(忠)是不可缺的元素。
综观人类学的孝道研究,基本是围绕孝道本原的意义上展开的,在中国历史文化脉络中对孝道进行阐释和研究的,人类学的孝道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孝道文化传承,甚至在当前历史时期如何进行复兴孝道从而消弭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当前的人类学的孝道研究并非完美,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代际交换的研究是建立在“善事父母”的基础之上的。但代际交换主要从互惠和功能论方面对孝道进行研究,把对父母的赡养和侍奉看作是对父母对子女的爱护和抚养以及子女对父母的孝行看作是礼物的交流和互惠,是一种资源控制权的获取手段,把孝行看成是理性的经济算计,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不排除交换理论在一些人选择行孝与否方面会有所影响,但需要强调的是,交换理论并非通行于任何领域,人并非完全的理性人,更是道义人,交换理论会将本来质朴的孝行行为庯俗化。
祖先崇拜和生育观念的研究是建立在“子承老也”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香火绵延不断、子子孙孙无穷尽是重要的人生追求,父母即使死亡之后也会在另一个世界冥冥之中决定着后代的命运,如果祖先得不到定期的祭祀,他们就会给后代以惩罚,由此,父母即使去世之后,后代子孙也要在家里、祠堂和墓地等场所对父母定期祭奠,而且要为去世的先辈寻找好的风水,好的风水也会决定后裔子孙能否旺盛繁衍。祖先崇拜和生育观念又是二元一体的,没有子嗣就没有香火祭祀,就没有“子承老也”的基础,由此,人生在世必须生育男性后代,这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生育观念。
现有的祖先崇拜的研究着重从象征体系进行解释,看到较多的是人观和宇宙观的意义系统,他们的研究路径是放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脉络进行解释。孝道分为现实层面的对父母的赡养和仪式层面的对父母、祖先的丧葬和祭祀。祖先崇拜的研究着重仪式层面的孝但却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孝。实际上,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现实层面的孝敬和仪式层面的丧葬祭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重视仪式层面的孝却忽视了实践层面的孝无异于舍本逐末。同样,生育观念的研究虽然把现世的互惠与祖先的交流的象征结合在了一起,但依然重理论轻田野,重文本轻实践,重一方区域的调查忽视多点民族志的比较。笔者作此类评述,并不是说笔者的视野比这些学者的研究高明,而是认为现在的研究者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侧重点各有不同,这主要和他们的问题意识有关。而且祖先崇拜和生育观念的研究都侧重文本的分析或抽象的论述,描述过于抽象化和理想化,缺少鲜活的田野叙述以及日常生活的关联。而且一些研究割裂了孝道实践中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联系,片面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从而失之偏颇。
笔者认为,在传统社会,孝道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中,而且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祖先崇拜、宗族治理、生育观念、养老送终、丧葬祭祀、风水鬼神等。人们的社会生活是整体性的,因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祖先崇拜、宗族治理、生育观念、养老送终、丧葬祭祀、风水鬼神也不是可以人为地割裂开来的,它们彼此联系,并行不悖,这其中有一个核心要素可以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此核心要素即孝道。孝道又不仅是民间社会的一种思想观念,同时也是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一种模式,一种儒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大小传统的联结点。封建社会实行家国同构、出忠入孝、移孝作忠,把孝道作为选拔人才,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内容。民间社会则利用孝道中的族规、家规加强宗族的团结,进而在地方区域社会的宗族互动中取得优势地位,在内部的宗族治理中处于井然有序的状态;利用孝道中的祖先崇拜来慎终追远,维持家族的社会化再生产。因此,在传统社会,在孝道观念方面,大小传统是耦合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大小传统二分的状态。大小传统通过围绕孝道所形成的互动,形成一种礼治秩序,并且通过士绅的中介,沟通国家和民间社会,并缓和二者之间的矛盾。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孝道同样有其社会价值所在。自近代社会以降,孝道发生重要变迁。孝道的衰落与否是衡量家庭是否和美、社区是否和睦、乃至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志。研究孝道衰落的原因,弘扬传统孝道文化,重建与当前社会相适应的新孝道文化,对沟通中国大小文化传统、融合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消弥社会矛盾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近几十年,人类学者又掀起反思的思潮,人们又开始对主位研究的视角展开反思,保罗·拉比诺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他认为,研究者和报道人双方互为主体,都各自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之网中,研究者理解报道人最多只能达到报道人理解研究的程度。因此,研究的过程是双向的,既是研究者了解报道人的过程,也是报道人了解研究者的过程,只有双方尽可能地互相沟通,了解,研究他者的文化才有可能。[25]人类学理论的后现代思考同样对于人类学的孝道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因此,我们进行人类学的孝道研究,也要沉浸到报道人的现实世界,和报道人互为主体,达到最大程度的理解和交流,不能割裂孝道的诸因素如代际交换、祖先崇拜、生育观念等孝道元素,而是把孝道作为整合祖先崇拜、宗族治理、生育观念、养老送终、丧葬祭祀、风水鬼神等社会诸因素的一个全息元,作为了解中国人文化因素的整体性元素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呈现整体性的孝道,接近孝道研究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