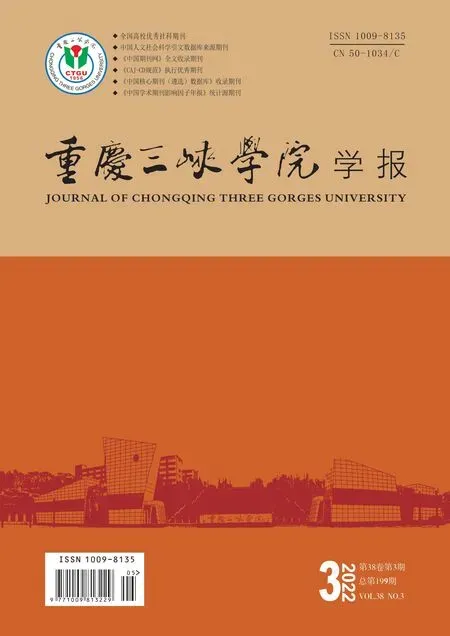记忆与想象中的20世纪——论余华《活着》《兄弟》《文城》
陈广通
记忆与想象中的20世纪——论余华《活着》《兄弟》《文城》
陈广通
(大连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622)
《活着》《兄弟》《文城》中的暴力与苦难以及对于二者的平静态度,沟通了余华对20世纪中国的整体记忆和想象,它们证明余华的创作“转向”并非那么明显,而是始终有一条线索贯穿着。通过个体经验与历史现实的融合,余华用这三部作品概括出了自我对于现存世界的认知图景,并在这图景里寄寓了微温的同情、平静的讽喻,以及寻找个体存在证明的努力。
20世纪;记忆;历史;暴力;苦难;平静
文艺界有一个广泛的共识: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不会随着历史的行进被时代风云掩盖,它之所以不朽的关键因素在于艺术成就。当历史在不经意间还魂,对一位天性敏感的作家来说,显然是一场幸福的偶遇,他很可能在此基础上运用想象力的加工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出自对文学创作环境极度压抑的反抗,20世纪80年代后半段的中国作家们将形式的突破作为个人写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余华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时年少轻狂的他似乎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嗤之以鼻,趾高气扬地将小说称作“虚伪的作品”。然而,时过境迁,曾经特定氛围里的那些所谓的“反抗”也可能只是一种姿态,因为个人性的艺术表达被压抑,势必会产生一些矫枉过正的极端做法。随着20世纪80年代过去,“那时候为了冲破什么的气氛已经不存在”[1]了,文学绕了一个小小弧度后,依然回到回忆与历史的本质上来。事实上,“写作就是一种回忆,每个人所写的东西都是对或远或近的事物的记忆”,作家不会像记者一样将眼前发生的事马上报道出来[2]261。小说的回忆本质决定了历史在我们头脑中挥之不去,反映记忆中的时代并超越它,是一部经典作品有且必须有的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余华的艺术表达接近评论家们的这一“苛求”。由于战争实际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战争文化心理”,中国的20世纪充满了暴力,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苦难随之而来。余华生于1960年代初,根据他的成长经历,对暴力和苦难不会陌生,二者共同构成了《活着》《兄弟》《文城》的主题。面对这种主题,他的叙述态度是平静的,平静沟通了他“转向”前后的整体创作,也继承了鲁迅、福楼拜的艺术传统。在余华的观念里,“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在他们笔下,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亮。应该看到,这过去的现实虽然充满了魅力,可它已经蒙上了一层虚幻色彩,那里面塞满了个人想象和个人理解”[3]128-129。“处于遥远状态”是记忆,“虚幻的色彩”是想象,二者共同构成了某一个体关于特定有限时间段内的主观历史,“个人理解”让这段历史闪闪发亮。余华通过自我对于20世纪的记忆与想象完成了一位有人文担当的作家对于人类命运悲悯的使命,同时在幽默中实现了对现实社会的反讽和批判。
一、暴力的空间
一直以来,学界都将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视为“先锋”作家集体“大逃亡”的时间节点,余华也被认为从这一时期开始了文学写作风格的“转向”,特别是在有关暴力的书写以及由此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姿态方面表现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风貌。余华本人也承认,从那时以后创作中的暴力叙述大大减少了。他与评论家们共同举出的例证是《在细雨中呼喊》之后的一系列长篇小说,大家将余华定义为沉迷暴力的“冷酷”写作者的依据是在此之前的以《现实一种》为代表的短篇作品。笔者认为,从所谓的“转向”以来,余华对暴力的书写并没有大面积减少。大家(包括余华本人)之所以觉得减少,是出于阅读印象的误差,即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在篇幅上的巨大差异。余华出道于短篇创作,一篇作品就是一种感觉的集中展现,一篇小说就是一个凶杀、恶斗的惨象,多篇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他的“冷酷”标签。如果我们以量化方式统计的话,可以清晰地看到余华“转向”后的长篇里暴力场面总和并没有减少,只不过没有短篇里那样集中,而是散落在叙述的各个板块里。一个短篇可以从头到尾聚焦于暴力场面,但对于几十万字的长篇来说显然是不适用的。我们不可能要求读者在每一页的阅读中都对暴力欣然接受,一个作家也不可能将几个或一群人的斗殴与厮杀抻长在好几百页的纸上,这样做不符合读者乃至作者本人对于长篇小说的体裁定位。它必定有铺垫、有穿插,还有由多重主题复合性所决定的人世间其他方面的书写。对于余华来说,暴力显然是他观察理解中国20世纪的出发点和总基调。暴力意味着对于秩序的颠覆,而20世纪的中国恰好处在秩序被不断颠覆——重建——颠覆的循环过程中。“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4]167,这才是余华眼中的最高真实。
对于20世纪的整体展现是余华在创作前半期就萌生的一个愿望,《活着》《兄弟》和《文城》共同标志着这一愿望的实现,它们代表着迄今为止余华创作的总体题材取向与风格面貌和艺术表达的高峰,不管“转向”与否,三者表现出的艺术追求是一以贯之的。余华“觉得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只不过“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而已[5]9。余华的成长经历里充满了血腥,大环境是“文革”时期的“武斗”及其少年时代阅读的革命历史小说。他父母都是医生,本人在医院周围长大,父亲做完手术后工作服上沾满的鲜血是他挥之不去的记忆,他自己也当过几年牙医。就取材来讲,暴力仍然是《活着》《兄弟》《文城》串联起叙述的主要线索,余华的笔并没有比从前柔软多少。
《活着》《兄弟》这类偏向于“写实主义”的作品自不必说,即使是传奇写法的《文城》也按捺不住余华对过往现实的记忆与想象,虽然他自己笃定减少暴力描写,但各种死法仍然在他笔下层出不穷。林祥福被张一斧用尖刀插进了耳根,小美和阿强被冻死在雪里,李光头的亲生父亲被淹死在粪池里,苦根撑死在床上,二喜被水泥板夹死,凤霞产后大出血而亡,“和尚”断臂流血而死,宋凡平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庆被抽血抽死,孙伟的父亲用砖头将铁钉拍进天灵盖,宋钢的身体在火车轮下被截成几段……除了死亡的结果,余华对于暴力场面的经营仍然不遗余力。在他早期的短篇作品中,暴力多来自非现实题材,更像是某种寓言,在这三部作品中比较有现实依据了。《文城》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期,那时正值党派林立、军阀混战,更兼土匪横行、浑水摸鱼,林祥福、陈永良的侠义价值实现于他们与土匪的生命对峙中。军阀混战自不必说,里面有的是枪林弹雨,战斗惨象中并不缺少肠子流了一地,眼球挂出眶外等恶心场景。关于土匪的刻画则以冷兵器带来的切身感受为主,里面有割耳朵、卸膀子,亦有连肩带头一刀切。坏人对村民的报复,大规模的屠杀频频上演。《活着》虽不是以战争为叙述主体,但20世纪40年代解放战争的杀伐场面依然足够震撼,炮火震天、流弹飞窜,伤号成堆连片。《活着》描写“文革”中武斗的篇幅占整个叙述的比重并不大(只有村长被打和春生之死),不过到了《兄弟》中这部分得到了完整补充。《兄弟》的上半部由李光头偷看女人屁股起首,引出李兰与宋凡平的婚姻、爱情往事,权衡之下,关于李光头和宋钢兄弟俩的交叉叙述并不是特别多,总的讲述框架还是“文革”前后的故事。“文革”“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兄弟》后记),本能被压抑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所以才有了精神狂热下导致的身体暴力。宋凡平被关押后,被打得鼻青脸肿,胳膊脱臼。为接回李兰,逃走途中又在车站被围攻。他不顾围追堵截者们的拳脚棍棒,誓要把钱递到售票员手里,终于被打断了的棍子戳入躯体,血尽而亡,喂了苍蝇。即使到了20世纪末期,暴力的故事仍在上演。李光头赔了合伙人的钱,被债主们以各种不同方式“从春天揍到了夏天”,赵诗人甚至只为了多年前的一句话,就想趁人之危揍揍李光头,不想却被后者着实揍了一顿。
除物理暴力外,同样使余华记忆深刻的是语言暴力。所谓“暴力”者,不仅指以武力对受害者施以肢体上的打击,也包括以非武力形式对受施者造成心理上的伤害,语言就是此种暴力形式之一。《文城》里的小美被休掉后受到村民们的评论指点。《兄弟》中的李光头揍完赵诗人,围观群众(这里的“群众”显然有所特指)想起曾被他揍过的刘作家,想要再看一次,于是进行言语挑拨。当李兰在车站包起浸满丈夫血迹的泥土,捡去落在宋凡平尸体上的苍蝇,邻人们并没表现出同情之心,而是兴致勃勃地议论消遣。李兰悲痛于宋凡平的暴亡,在人群前一头晕倒,人们却没有一个蹲下看看如何解救她,而是拿号啕大哭的宋钢和李光头取笑。“我们刘镇的群众”兴趣广泛、好奇心强,有人死了要围观,有人结婚要围观,有了桃色新闻要围观,有了游斗要围观,有了打架要围观,而围观总不能悄无声息,于是产生出各种流言,给被围观者(死人除外)以及被围观者的亲人造成极大心理压力。20世纪的总体社会氛围、道德标准、政治观念所产生的言语环境是一种不亚于物理强力的无形暴力,余华的“冷酷”哲学由此而生。
余华对于暴力与死亡的专注其实是对于中国新文学开创者鲁迅传统的继承,鲁迅文学创作道路本身就始于对“砍头事件”的忧愤难当。被视为现代文学开山之作的《狂人日记》是一个关于生命被终结的恐惧故事,其后的《孔乙己》《药》《明天》《风波》《阿Q正传》《祝福》等也无不以暴力与死亡作为主题实现的最终载体。暴力与死亡是20世纪的显在主题,鲁迅开手就写,早期乡土派在写,沈从文在写,革命文学更在写。暴力与死亡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永恒归宿,只不过余华将它们集中化了,这或许也可看作是他经典观念的一种实现方式。无论是物理暴力还是心理暴力,余华都将它们描绘得毫发毕现,尽力与鲁迅一样以细节的力量使主题深入人心。两种暴力结合起来后,表现出的是二者对于20世纪中国人民苦难命运的忧虑或者悲悯。
二、苦难的行程
作为一位有相当造诣的艺术创作者,悲悯情怀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道德素质。曹文轩认为悲悯情怀“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任何一个古老的命题——如果的确能称得上古老的话,它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才被称为文学,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离不开的意识形态”[6]215。就小说创作来说,悲悯情怀主要表现于作家对人间苦难的展现与同情。余华在《活着》《兄弟》《文城》的创作中秉持了这一观念。
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城》就是20世纪初期中国普通民众的一部灾难史。在那个年月,战乱频仍,匪祸横生,加之封建势力回光返照的余威和人性本真的复苏,中国大地上满布着流浪者的足迹,林祥福、陈永良在各自命运的安排下不约而同地漂流到了溪镇,而阿强和小美则漂流到了林祥福的老家。《活着》里的福贵本来是个衣食无忧的阔少爷,抗战结束不久,由于赌博输光了家产,全家人的苦难从此开始。他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国民党军拉了壮丁,全家失去了徐父去世后的顶梁柱。土改时期日子虽然安稳,却也一样使人愁苦,苦到要把女儿送出去才能供儿子上学。“大跃进”时期全家人忍饥挨饿,人民公社运动初期的兴奋过去后又回到了贫穷,“文革”里看着朋友受辱而死,他们毫无办法。好不容易盼来包产到户,可福贵已老,只身一人,只有拼命干活。困苦的日子偶尔也有一些小小的精神慰藉,让人感受到生活里的一丝光亮,但这种光亮并不会一直存在,它往往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倏忽掩盖。有庆越长越懂事,还夺得了跑步比赛的冠军,随后却被抽血抽死;凤霞终于嫁给了二喜,而且喜怀贵子,怎奈产后出血,留下小的,走了大的;面对这些,家珍已无力承受,撒手人寰;唯余苦根多少给了福贵和二喜一丝安慰,二喜却被水泥板夹死;剩下福贵祖孙二人,生活虽苦,苦根却也聪明可爱,谁会想到,他又因吃豆子撑死。唯一活着的福贵就像一条破船,完全不可自主地颠簸在随意起伏的生活波浪上,他的故事串起了抗战末期到改革开放之初半个世纪左右的中国历史。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的苦难也仍在继续。《兄弟》里的宋钢下岗后去码头扛活扭伤了腰,卖白玉兰花又受到别人的嘲笑,打零工收入微薄,在水泥厂又被呛坏了肺,无奈之中浪迹江湖,甚至不惜做了隆胸手术,身心两面备受摧残。小关剪刀与老婆流浪途中的相互照应,宋钢与林红之间的彼此关心,宋钢李光头兄弟之间的两相记挂这些慰藉和《活着》中的温暖一样,转瞬即逝。比起物质,精神上的苦难更使人难以承受。福贵为自己多给了苦根豆子耿耿于怀,小美为偷走林祥福的金条和弃夫抛女负疚终生,李光头和林红为背叛宋钢各自饮罪。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物质匮乏,福贵不会把苦根独自留在家中。如果不是因为封建伦理,阿强和小美不会远走他乡。如果不是历史的压抑,李光头和林红或许不会偷情。然而,余华并不是用“如果”经营情节的走向,而是将它作为挖掘20世纪中国人民苦难命运的一个引源。我们不排除余华在对他者苦难的同情中寻找情感平衡点的人性诉求(正如《祝福》里鲁镇人对于祥林嫂故事的反复倾听),但普通读者感受更多的是生发于苦难中的穿透力。文学只有在面对苦难时,才会被唤起它隐藏的力量,这种力量或者使人振奋,或者使人安详,余华的创作正应验了这一常规。
从现有的余华本人对其生活轨迹的概括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并没有经历过上述苦难,他的父母都是有正规编制的城市医生,物质匮乏感不大可能如农村人那样强烈,不像莫言、阎连科那样对于饥饿有那么深的记忆。他家也没有在“文革”中受到什么冲击。莫言在很多场合坦言,自己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因为梦想每天都能吃上饺子。在阎连科看来,“童年,其实是作家最珍贵的文学的记忆库藏。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贫穷与饥饿,占据了我童年记忆库藏的重要位置”[7]4。余华很少有这种自白,他的自白是“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至极。当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有一次我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问他为什么经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倒是很适合我。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4]109。由此看出,余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并不是因为“发愤著书”,也不是因为物质享受,而是因为“无聊至极”。所以从暴力和物质生活两方面造成的苦难来看,余华的展现可能并不是出自亲身体验,更多的是一种感同身受,或者说是一种眼见为实过后的想象加工,是基于20世纪中国社会大环境的一种主动提炼。苦难和暴力是20世纪中国的两个基本主题,在当时的人们眼里确实是司空见惯的。余华在谈到马原《黄棠一家》时说:“我读完这本书有一个感觉,这是一个江湖中人写出来的书,一个经历了很多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书。至于里面有一些什么细节或者故事你们可能在网上看到过,有些人拿这个来批评马原。其实文学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了,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题材都被写过了。”[5]210
余华的《第七天》面世时也受到了同样的批评,很多评论家认为新闻串烧式的写作没有什么新意,它提不起人们的兴趣。问题是,在互联网极度发展的今天,还能有什么让我们惊奇呢?更不用说一个主题,文学(其实是整个人生)中也无非这几个主题:生命、人性、历史……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这个例证序列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而这些主题大多数成年人都会想到。作家要做的只是在众所周知的领域里与读者交流一下自我的感受,小说不是猎奇的工具,而是孤独者呼唤共鸣的手段。想象中的苦难触动了余华的心灵,所以他要将其表现出来,是悲悯情怀的适度释放,是一个人文意义上的灵魂对于世界的入于眼出于心。
《在细雨中呼喊》出版后,人们普遍认为余华也让大家看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亲情关系仍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存在着,犹如灰烬中的余火,给人意想不到的温暖”[8]102。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余华笔下的温暖(包括亲情以外的)绝大多数是在人物遭受苦难的前提下渗透出来的,如果没有冷酷世界里产生的苦难,温情也就无从表现。宋钢和李光头的相依为命开始于李兰的逝世(《兄弟》),福贵、家珍对春生活着的规劝产生于有庆之死和春生受迫害以后(《活着》),当王先生由于被土匪割掉一只耳朵,形成了一个在讲课时不由自主向教室门口跑偏的毛病,几乎所有学生都离他而去,唯有陈耀武主动投入他的门下,原因在于耀武曾经和他一起被土匪割去了耳朵——同病相怜(《文城》)。
纵观余华对于苦难的表现,会发觉人们的苦难行程并不是由某个“坏人”使然,而是由当时整体社会环境所决定。没有人存心使坏,只是人类天性中的邪性被时代的斧凿开掘出来,随后在席卷一切的风潮里弥漫开来。《文城》里的苦难来自于20世纪前半期的军事、土匪势力横行,《活着》里的苦难来自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至“文革”的“战争文化心理”、非实际战争环境下的群情亢奋和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自然灾害,《兄弟》里的苦难增加了改革开放后物欲横流大潮中人对物质生活无度追求状态下的作茧自缚。没有坏人的苦难可能更像一种宿命,在那样的时代,在大环境和个人贪欲的主导下,个体存在者很难把握自我的命运。在这种观念覆盖下的余华实现了对于人世的佛系领悟,悲悯情怀由是生发。但是,余华的悲悯和同情并没有表现为以泪洗面、捶胸顿足,而是一以贯之的平静。
三、平静的态度
虽然余华的创作多是呈现,较少评价,但还是能在叙述的间隙里看到他关于现实态度的蛛丝马迹。出道之初的余华以“冷酷”名世,“转向”之后以“温情”为标签,二者之间虽有界线,但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冷酷和温情既有各执一端的并峙性质,又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暴力的延续和苦难的引入,冷酷和温情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化合,催生出介于二者交叉地带的情感形态,综合考量余华“转向”之后的创作,我们更倾向于将他对世界的态度归结为平静。
余华的平静首先表现在对司空见惯的词语的个性化运用上,或者是大词小用,或者是庄词谐用,也可能是重词轻用。当他用某些形容词时,我们可以清楚地明白故事情景和人物内心的状态,但有时却并不会陷入一般情形下的叙述氛围里,它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审美距离。“凶狠”是余华写到暴力场面时常用的一个词,他可以很形象地让人看到施暴者的拳头或者武器从扬在半空到接触于受暴者躯体的浓缩过程,但读者内心却并无痛感。“温暖”会让人想到火、阳光,但同样较少让人感到余华笔尖上的热度。“近似成语”通俗易懂,它们的罗列更使叙述者的姿态跃然纸上。《兄弟》里宋凡平对宋钢和李光头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兄弟,你们要亲如手足……互相帮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天天向上。”余华似乎只在传达人物内心的想法,忽略了语言的形象性问题,更像是“转述”。这并不是说作者由于写作水平低下用词不当,更可能是其参悟透所谓创作技法后的有意为之,他并不在意一个词语的普遍效果和一般功用,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重重提起,轻轻放下。他以平静的观察和准确的表现让我们看到真相,没有将我们煽情到一塌糊涂的打算,虽然也写感伤和感动,但不会让我们跟着一起哭泣(但这并不意味着余华小说中没有使人感动的地方)。他无意于使读者泪流满面,只让人感到似曾相识。
余华的平静也表现在叙述细节的凸显和场景的经营上。他仍然保持着“先锋”时期的写作风格,人物的每个细微动作和微妙感觉都被他用凸透镜放大了。《兄弟》里宋钢之死,余华并没有写得悲悲切切,而是静穆幽远。宋钢卧轨之前先是呼吸了几口刘镇的新鲜空气,看看田里的稻子、被晚霞染红的河水、日落时的天空,他在这样的环境里似乎感到了生命本身的肃穆庄严。火车来临时宋钢心里平静如水,面对即将实现的死亡,他从容不迫。先是“取下眼镜擦了擦”,然后又戴上,接下来有意识地将它放在石头上,但“又觉得不明显,他脱下了自己的上衣,把上衣铺在石头上,再把眼镜放上去”,然后戴上口罩,“他那时候忘记了死人是不会呼吸的,他怕自己的肺病会传染给收尸的人”。然后余华写道:
他向前走了四步,然后伸开双臂卧在铁轨上了,他感到两侧的腋下搁在铁轨上十分疼痛,他往前爬了过去,让腹部搁在铁轨上,他觉得舒服了很多。驶来的火车让他身下的铁轨抖动起来,他的身体也抖动了,他又想念天空里的色彩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远方的天空,他觉得真美;他又扭头看了一眼前面红玫瑰似的稻田,他又一次觉得真美,这时候他突然惊喜地看见了一只海鸟,海鸟正在鸣叫,搧动着翅膀从远处飞来。
火车响声隆隆地从他腰部碾过去了,他临终的眼睛里留下的最后景象,就是一只孤零零的海鸟飞翔在万花齐放里。
通过上述描绘,我们能够感觉到在由生到死的间隙里宋钢心绪的淡然或者麻木,他的悲伤故事已经结束,留下的只是缥缈人世的万物虚空……《文城》里的林祥福为女儿乞奶时是一副木讷表情,叙述者的平静和主人公的呆板达到了统一:
那时候的溪镇,那些哺乳中的女人几乎都见过林祥福,这些当时还年轻的女人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总是在自己的孩子啼哭之时,他来敲门了。她们还记得他当初敲门的情景,仿佛他是在用指甲敲门,轻微响了一声后,就会停顿片刻,然后才是轻微的另一声。她们还能够清晰回忆起这个神态疲惫的男人是如何走进门来的,她们说他的右手总是伸在前面,在张开的手掌上放着一文铜钱。
在这一场景里,细节的刻写冲淡了情绪本该有的鼓胀。林祥福敲门乞奶时的神态本应是一副可怜、辛酸模样,但作者的描绘并不催泪。余华并非心无同情,只将它做了还糙处理,让人感到滞涩。空气中弥漫着陈年木料的气息,人物的动作、形态细节构成的雕像更像是一个神秘的寓言。当这座“一动不动”的雕像被作者用笔尖轻轻掀起,很多往事就从人与大地之间的接触点上漫流开来。
在写《兄弟》的时候,余华已经将自己对现实的冷静态度拉了回来,只不过程度比先前减少了一些,到了《第七天》有所加强,到了《文城》又下跌到《兄弟》的水平。这是作家在有意无意间对叙述力度不断调整的结果。“转变”并不意味着与从前一刀两断,而是一种发展和完善。在余华从前的冷酷里较难看出他对社会存在的现象进行干预的实质性行动,而当冷酷被调整为平静之后,反讽的意味就不请自来了。《兄弟》中的许多主打场面都在“我们刘镇群众”的眼前展开,这本身就暗示了一种旁观立场,余华站在群众包围圈的最外层,面无表情地观察着看者和被看者的一举一动,他只看热闹,一言不发。“刘镇群众”可以被当作一个专有名词来理解,他们是麻木又亢奋的一群人,被叙述人抱以俯视的目光。宋钢和李光头的命运连接了两个时代,它的正面叙述从“文革”开始,面对那段使中国人民记忆惨痛的历史,余华采取了与“新时期”伊始时的作家们迥然有异的处理姿态,不像刘心武、卢新华们正襟危坐、义正词严式的讨伐,更多的是经过多年沉淀后形成的置身事外的戏谑式讽刺,其中充满了对当时历史环境下催生出的丑陋人性的无情揭露。作品开头即是一幕充满戏剧性的偷窥犯被游街的场面。李光头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后,被赵诗人和刘作家押解示众,二人努力使自己的言语接近高雅,却总是适得其反。他们押着李光头几次在派出所门前经过,却偏不将李光头送进去,无非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作为正义使者的虚荣心。“受害者”“胖屁股”对李光头义愤填膺的指责控诉给看客们留下了讥笑双方的把柄,其话语内容泄露出的信息正是使她蒙羞的渊薮。我们不禁想到,如果她不大叫大嚷令其丈夫惩罚“罪犯”,或许会减少丢人的程度。她对其丈夫的倾诉和催逼,更像是作者对鲁迅《祝福》里村人们欣赏祥林嫂的苦难片段的反其道而用之,“胖屁股”想通过对丈夫的倾诉让大家看到她受到了多么大的委屈和屈辱,以便将自己放在弱者地位,从而得到些许同情(或者是骄傲?)。这一情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鲁迅小说“看”——“被看”的创作模式,但鲁迅多是对“被看”者同情,对“看”者批判,余华似乎是对“看”与“被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的冷静比鲁迅来得更彻底。李光头最终还是被送进了派出所,期间的审问像极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警察们如饥似渴地想看到林红的屁股,但有贼心没贼胆,所以“拿住了李光头自然是机不可失”,哪怕听听别人看到的细节也多少解解馋,听到紧要处,他们的“眼睛突然像通电的灯泡似的亮闪闪了”,甚至“憋住了呼吸”,俨然将审问演化成了打听。公家的走卒也难逃天性的“龌龊”,却偏偏拿出一副正义的嘴脸,背地里也一样腌臜。《文城》里的北洋军兵在饭馆吃饭时的喊声被比作牲口的叫嚷,他们嫖娼时却要排队保持军威。
当20世纪经济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果后,人性的浮躁、贪婪、虚伪、唯利是图随之而来。《兄弟》里的李光头看得比任何人都透彻,他直言不讳,五年前用福利厂的残疾人照片和诚意就可以拉到大把生意,“现在时代不同啦”,只有靠“行贿才能拉来生意”。李光头第一场生意失败,其他合伙人的心理反复几次变化,他们并不是为了基本生计,而是想拥有更多的资本。当听说李光头将要返回,他们极尽客气之能事,当得知李光头并没有拉着生意就开始拳脚相加。给李光头的服装加工厂投资,赔了钱的王冰棍和余拔牙当初对李光头恨之入骨,后来眼看李光头的旧品收购公司日益红火,他们又见风使舵,完全忘记了曾经对李光头的破口大骂。那时和二人一起投资的另外三人因为对现在形势有所忐忑,没有参加第二次投资,彼此之间相互埋怨。余华将他们当作跳梁小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上演着你来我往的小戏。余华的平静并非毫无来由,在20世纪的暴力环境下,“与失去牲口后哭天嚎地的悲哀不同,失去亲人的悲哀显得平静”(《文城》),加上肉体饥饿经验导致的唯利是图,性情的麻木也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了。从人文主义角度上来说,余华在平静的表情里实现对丑恶的嘲讽,其目的在于提纯美好。二者并存于作家对世界和历史理解范围的中心,作家以超然的姿态使它们互通有无,借以完成对现实的展现与同情。冷眼旁观的嘲讽其实是幽默的一种方式,而余华“对幽默的选择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不是叙述中的机智讽刺和人物俏皮的发言。在这里,幽默成为了结构,成为了叙述中控制得恰如其分的态度,也就是说幽默使余华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好方式”,他通过这种方式解放了从前短篇小说中表现出的“自己越来越阴暗的内心”[3]28。
小说创作是记忆的累积,余华在回忆,其笔下的人物也在不断回忆。陈永良每每想起初到溪镇时的情形,林祥福死后他又回忆起林祥福与他初次相识时的模样,宋钢和李光头频频回忆起小时候,福贵的讲述本身就是一场关于记忆的行旅。余华说:“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9]余华在这三部作品里利用回忆基本上实现了对于中国20世纪的独特表达,延续了自己一贯的写作观念,并对之前有了调整,在叙述和感知两方面几乎都达到了纯熟境地。唯一的遗憾可能就是缺少对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关注,在这一时期,由于各党派集团、各军事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及各自政策、方针的制定调整,中国社会展现出与其前后各阶段迥异的暴力、苦难形态。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疏漏,就余华对于过往记忆与想象的呈现来说,《文城》《活着》《兄弟》来自他对20世纪中国的基本认知图景。回忆是图式,想象是理解,《活着》《兄弟》里的记忆和《文城》里的想象一起构筑了余华个体经验与历史现实的融合。福贵之所以令“我”难忘,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而那些由于记忆的单薄显出对往事木讷的老人们往往被后辈们鄙视:“一大把年纪全活到狗身上去了。”余华对历史的记忆与想象可能也在于为自我的存在找到些许证明,他说:“回忆在岁月消失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有时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3]144-145这是记忆和想象合谋的成功,余华或许做到了,或许没做到。
[1] 余华.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J].文艺争鸣,2015(12):12-13.
[2] 张炜.小说坊八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261.
[3]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28-129.
[4]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67.
[5]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5.
[6]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215.
[7] 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
[8] 郜元宝.小说说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102.
Twentieth Century in Memory and Imagination:On Yu Hua’s,, and
CHEN Guangtong
Violence and suffering are common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Yu Hua’s works,, and. These spiritual connotations combine with the author’s calm attitude towards them run through his overall memory and imagination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they prove that Yu Hua’s creative “turn” is not so obvious and there is always a thread running through in the three books. Yu Hua integrates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historical reality in the three books and summarizes his cognitive picture of the existing world,and in this picture, there is warm sympathy, calm allegory, and effort to find proof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Twentieth century; memory; history; violence; suffering; calm
I207.42
A
1009-8135(2022)03-0096-11
陈广通(1982—),男,满族,辽宁大连人,文学博士,大连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郑宗荣)
——读余华小说《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