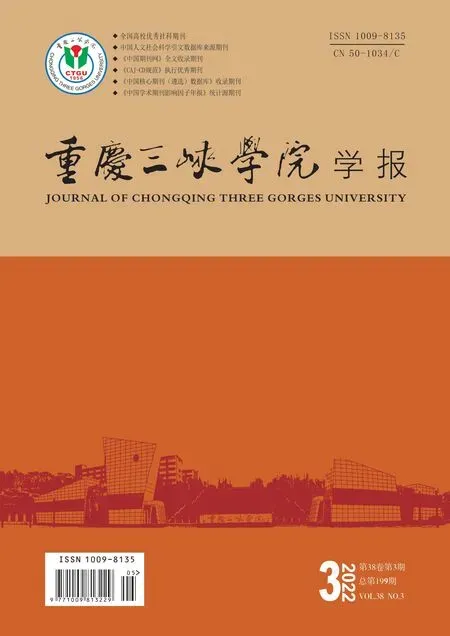库普兰德小说中的北美西海岸空间与时空乌托邦
秦臻 陈世丹
库普兰德小说中的北美西海岸空间与时空乌托邦
秦臻 陈世丹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北美西海岸空间是加拿大作家道格拉斯·库普兰德小说中的核心叙事空间,也是作者乌托邦思想的具象表征载体。库普兰德用动态的眼光审视北美西海岸长期被视为静止的城市、荒野和郊区三种独特且互相关联的空间,重思乌托邦与空间的关系,探索乌托邦希望。超真实的加州城市空间生产出已实现却走向末日的乌托邦;崇高的西海岸荒野空间蕴藏着天然存在却拒绝人类栖居的乌托邦;阈限性的温哥华郊区空间打破了城市和荒野之间的壁垒,以非正面对抗的方式缓和了人类和自然对撞产生的巨大张力,开启了通往时空乌托邦的希望之门。
库普兰德;北美西海岸;空间批评;乌托邦
道格拉斯·库普兰德(Douglas Coupland,1961—)是加拿大当代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其作品的核心主题是对乌托邦的追寻。库普兰德注意到,存在于空间乌托邦中的、由物质主义空间观导致的个体幸福多样性和理想空间同质性间的矛盾,以及存在于过程乌托邦中的、由地理纬度的缺失引发的时空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倡对共时性矛盾的分析与历时性规律的思考相结合,在此基础上重思乌托邦与空间的关系。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美国的真相只能被欧洲人发现[1]28;库普兰德则认为,拥有和美国人相似空间经验的加拿大人处在一个更易认识美国的位置。库普兰德的小说多聚焦于北美当代文化,在美国的接受度丝毫不逊于加拿大。为他赢得极高知名度的处女作《X一代》(Generation X)最早出版于美国。《诺顿美国后现代小说选集》()也将他作为“X一代作家群”中的一员收纳在册,称他为“品钦、加迪斯和德里罗的新一代接班人”[2]。库普兰德的小说多以北美西海岸为背景,着力描绘三种独特且互为关联的空间形式——加州城市空间、西海岸荒野空间和温哥华郊区空间。小说人物总是向下一个空间移动,重要故事情节的发展也依托于地理位置的转换。这些空间内蕴多样的意识形态和丰富的文化价值,是言说乌托邦体验、参与乌托邦建构的动态叙述元素。在空间批评视域下,将城市、荒野和郊区三种空间形式置于多元的整体空间网络中,以北美西海岸的地理、人文状况为切入点,考察库普兰德的乌托邦思想,有助于深入挖掘乌托邦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探寻通往乌托邦理想的空间路径。
一、超真实的加州城市空间和走向末日的乌托邦
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西海岸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也是“天堂”和“地狱”并存的矛盾性空间。它见证了西进运动中的拓荒精神,目睹了熊旗暴动、美墨战争和印第安人被驱逐的惨烈景象。“它是自由之源,也是危险之所;是令人兴奋的挑战,也是令人疲惫的原因;是英雄主义的土地,也是种族主义、施虐和暴行的借口。”[3]库普兰德笔下的加州空间既有作为新世界引发欣快感的乌托邦的一面,也有现代性发展到高潮后不可避免的末日的一面。从根本上说,这种含混性是由加州在美国版图中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一方面,加州集高山、峡谷、湖泊、沙漠、海岛等多种地貌于一身,东西部连绵高峻的山脉和南部干旱荒芜的沙漠合围的中央谷地狭长肥沃,加之地中海气候带来的充足阳光,为花园神话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特纳(Fredrick J. Turner)的“边疆假说”指出:“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4]对加州这一典型边疆空间的开发是大西部拓殖史上的重要部分,参与建构了美国独立的国家意识,强化了国民的天定使命观,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性格。时至库普兰德开始创作的20世纪90年代,荒芜的加州变成美国最繁华的州之一。20世纪初期,好莱坞的崛起、中期硅谷的诞生、后期核能基地的建立,又将“加州梦”延续到娱乐、科技、核能领域。
另一方面,作为美国西部拓殖史上“最后的边疆”,加州易被设想为乌托邦的终点站,在诞生乌托邦理想的同时也终结了乌托邦理想。首先,在加州的定居标志着人们到达了地理上的尽头。浩瀚的太平洋阻断了人类向西开拓的脚步,来自欧洲和美国中西部的大规模农业移民潮被挫败之浪冲散,“永远不会再有礼物一般免费赠与的土地”[5]。其次,海滨也是象征蜕变和灭绝的地方,是稳定与混乱、生存与毁灭的过渡空间。达尔文指出,生命从海洋向陆地的转移为人类起源提供了条件,这一论断难免引发人类的灭亡也发生在海滩上的设想。鲍德里亚在《美国》()中也有类似的描绘:“世界终结于一片缺乏意义的海岸,正如旅行在抵达终点之时就失去了一切意义。”[1]60鲍德里亚将美国称为由“欧洲梦幻材料”铸成的“已经实现了的乌托邦”——欧洲人梦想的“正义、富庶、法治、财产、自由”等一切理念都在这里实现[1]61。但他同时指出,业已实现的乌托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同一性思维指导下的乌托邦虽然“实现了一个本质主义终极目标,到达了一种毫不含混的透明状态”,但丧失了其积极作用,成为“某种形式的末世论”[1]26。
加州“乌托邦的一面”充分展现在库普兰德早期作品中。库普兰德笔下的加州城市变动不居、丰富多彩,主人公们首次与现代迷宫般的加州城市空间相遇时,表现出面对新事物的欣快。《香波星球》()中的泰勒(Tyler)在加州之旅中偶遇“如珍珠般散落在硅谷中”的未来城镇,激动地称“这些未来主义空间是人类最深处欲望的铸造厂,怀疑它们就是怀疑一切”[6]218。《微软奴隶》()中的丹(Dan)将加州微软园区描述为“铸造我们终极文化梦想的麦加圣地”[7]。在《怀俄明小姐》()中,约翰(John)开车穿过好莱坞山的山顶,“闪耀着奇异的七彩光芒的洛杉矶撞进他的视线”,那是“一个比它所在的土地本身更大的东西,一个超越了自然的城市”[8]106,这一建构景观引发了约翰的狂喜。加州城市空间带给主人公们的最初印象与鲍德里亚在《美国》中的描述十分相似。同样被洛杉矶深深震撼的鲍德里亚,这样描绘这座灿烂到令人眩晕的城市:“一种明亮的、几何学的、灿烂耀眼的辽阔之物,一个比无垠的土地‘大十倍的城市’,可能目光从来不曾有机会遭遇如此的广度。”[1]43加州城市空间中鳞次栉比的建筑、琳琅满目的商品、熙攘喧闹的人群汇聚成快感、美学、欲望、消费的感官盛宴,释放出乌托邦的诱人引力。
在库普兰德的后期作品中,加州呈现出千篇一律、生气全无的景象。人造景观带来的新鲜感被麻木和冷漠取代,主人公们显露出对城市空间的失望甚至反感。《怀俄明小姐》中经历空难、劫后余生的苏珊(Susan)再次漫步在洛杉矶的街道上,原本熟悉的城市空间引发了陌生的感官体验,“就像第一次认识她的国家一样”,她的感官被花哨的店面、纷乱的商品、夸张的广告和庞大的人群占据,“但内心却一片荒芜”[8]78。《逝者的拍立得相片》()的叙述者称,加州的涵义之一即“天堂是可制造的”[9]111:加州见证了20世纪最集中的幻象生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华丽、宏伟、繁复的“外立面”(façade),即使那些提倡节俭的建设者,也会为建筑物设计一个观赏价值远大于使用价值的外立面,以维持宏伟文明的幻想。被资本生产出的加州城市乌托邦“在那些由钢铁、混凝土和玻璃构成的纪念碑式现代建筑中获得了自我意识,迫使建筑用一种理性化推动的综合符号系统再现它抽象化的本质特征”[9]112。对空间形式感的迷恋走向极端的产物就是“超真实”(鲍德里亚语)。高度饱和、无限亢奋、日夜运转的加州城市试图在规则化系统中依据没有真实源头的模型模拟乌托邦。换言之,加州乃至整个美国都在重复一种用理念建造现实的模式,人们在永恒的符号呈现出的替代性现实中狂欢。这一模式的不断重复使人们丧失新鲜感,强烈感官刺激遮蔽下的精神空虚日渐显现。因此,加州城市乌托邦逐渐丧失了超越性,不可避免地走向末日。
总之,库普兰德笔下的加州是处于线性历史尽头、无深度的城市空间的缩影,既内蕴乌托邦理想照进现实的神话,也包含“核威胁、汽车垃圾、破碎家庭、庸俗艺术和整形手术”的现实[10]。作为最后的伊甸园,它吸引着人们对乌托邦的追寻;作为真实的荒漠,它又消解和否认了这种追寻,带来末日般的精神体验。加州城市并非处在新纪元的开端,而是处在旧时代的末端,承担着实现乌托邦的沉重历史负担,却被晚期现代性的困境所定义。不同主体的具体乌托邦想象被集体收编,统一纳入以进步为名的乌托邦的旗帜下。乌托邦的实现意味着对辩证思考的放弃,其终点必然是末日和死亡。已实现的乌托邦是无内容的结构,是纯粹的模型,是无法到达、不宜居住的。
二、崇高的西海岸荒野空间和触不可及的乌托邦
荒野是美国文化的一项基本元素,拓荒者与荒野的独特互动构成了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环境史学家佩里奥特(Melanie Perreault)指出,欧洲移民在踏上新大陆时,“随身携带了一套先入为主的荒野观”[11]。以蛮荒和野性为主要特征的荒野被视为文明世界的对立面,以康德式的崇高激发了人类宰制自然的信心。拓荒者肩负着超越自然的使命,最大程度地发挥理性和主体性,任意地“模塑自然,压倒自然,把自己的个性施于自然”[12]。随着加州的田园理想走向终点,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乌托邦的主人公们将目光投向加州沙漠,重访这片移居者西进时经过的广阔土地,坚信乌托邦尚在一块未被地图绘制的空间静静等待。当年,他们来自欧洲“文明世界”的祖辈们将这片土地视为“荒野”,将印第安原住民视为“野人”甚至“野兽”。如今,这些虔诚的朝圣者重复前辈的路线,仍将荒野视为纯粹抽象的目标,将其从现实中抽离出来,继续制造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但加州城市的末日困境清晰地展示了这类乌托邦的虚幻性——它永远处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外,人们只能使用关于进步的语言和将来时态表述它,这也是主人公们最终一无所获地从加州沙漠中失望而归的原因。《上帝之后》()的匿名叙述者在莫哈韦沙漠的“虚无”(nothingness)中遇到更多的是恐惧而非启发[13]167。《昏迷的女友》()中莱纳斯(Linus)花费四年时间重现了《出埃及记》中的沙漠之旅,无功而返的他承认“未能在流浪中获得任何启示”[14]76。《X一代》中三位主人公从繁华都市搬到沙漠小镇棕榈泉,寻找如“章节末尾的空白”般纯粹的空间,但最终只能将目的地推向更荒僻的墨西哥[15]。《怀俄明小姐》中的约翰直接将他的加州沙漠之旅称为“一场骗局、一个天大的笑话”,看着“这片野蛮和破碎的空白”,这位流浪者认识到,他的后代“既不会理解也不会驯服这片土地,这片土地总是比他们更聪明、更残酷”[8]174。
库普兰德对康德式崇高持批判态度,不认同康德对理性的大肆褒扬,拒绝将荒野视为无意识空间,反对通过压抑自然和他者建构“目的王国”(康德语)。这与伯克(Edmund Burke)的理念吻合。伯克将崇高定义为具有“极端维度”并呈现出“无限概念”的东西,它引发灵魂的强烈震颤,让人充满“愉悦的恐惧”[16]。库普兰德作品中的另一荒野空间——加拿大荒野——无论在黑暗与无垠中,还是在神奇与美丽中,都体现出令人欣喜又畏怖的伯克式崇高。《昏迷的女友》中“坚实如铅、洁白如光”的贝克山“被神秘的黑暗森林包围”,这座火山“华丽、撩人而悲伤的喷发”引发了莱纳斯“关于死亡、无限、生存和时间的思考”[14]234。《上帝之后》的叙述者走进温哥华的荒野,“漫长而陡峭的林中之路和巨大山脉”,使他体验了拓荒者面对新世界“恐惧而着迷”的情感[13]8。
伯克式崇高要求人类必须和自然保持一定的距离。伯克的崇高论在朗吉努斯(Longinus)的“超越说”上增加了疼痛、恐惧等情感因素,这些负面情绪转变为崇高的审美快感,关键在于人们处于能够感知危险却不必亲身涉险的旁观者位置,获得了一种从危险中幸存的庆幸感。库普兰德的《加拿大的纪念品》()开始于作者对加拿大北部荒野的一次远距离的空中俯瞰,“那里只有这片土地,一片空白,无人居住”[17]4。叙述者凝视着这片神秘的土地,重新思考人类与土地的关系。库普兰德的视觉叙事带有浪漫的怀旧情怀,呼应了可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关于欧洲人与美国风景接触的文学描述。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处,尼克•卡罗威(Nick Carraway)从东海岸眺望,怀着对这片土地最终会被亵渎的忧虑,揣测17世纪的殖民者对这片土地的看法:
我的眼前逐渐浮现出这座古老的岛屿当年在荷兰航海者眼中的那种妖娆风姿——一个新世界的翠绿欲滴的胸膛。它那现在不复存在的林木曾经温馨地煽起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短暂的神奇时刻里,人类一定在这片大陆前屏住了呼吸,情不自禁地耽入他既不理解也没希冀过的美的享受之中,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面地欣赏着,这一与他的感受惊奇的力量相称的景观。[18]
菲茨杰拉德的用词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翠绿欲滴的胸膛”让人联想到一个纯真的女性空间即将被移民男性商业化的利益侵犯,在看似无辜的“游客-旁观者”和他们对土地的暴行之间建立联系。面对加拿大北部的荒野,库普兰德也存在同样的担忧。“这些被冰冻的巨石有朝一日会成为现代城市的地基吗?巴芬岛会被亮视点眼镜和芭斯罗缤冰淇淋连锁店占领吗?面对人类残酷的入侵,这片圣洁的土地还能抵抗多久?”[17]4不同时代的两位作家对原始景观的相似描绘,反映出理性主义乌托邦带来的无情破坏。菲茨杰拉德关注人类失去纯真的后果,库普兰德则描述了更模糊的后现代空间体验。空中俯视的角度赋予人们上帝般的视角,修正我们熟悉的认知世界的模式,暗示人类干预的非永久性,表明崇高的荒野空间需要一种不同于历史和社会标准概念的解读方式。
库普兰德对荒野的描述是笨拙的,通常简单地将其称为“无处”(nowhere)、“虚无”(nothingness),这种表征困境表明,由于语言的限制,人类触及到了认知的边界,无法用康德的理性统摄方式把握崇高。在《昏迷的女友》中,库普兰德通过一个关于鲸鱼的设想,再次表达了语言在面对自然时的无力:“如果一只人工繁殖饲养的鲸鱼被放归野外——回到它祖先的海洋,它会是什么感觉呢?当被抛入未知的深渊,看到陌生的鱼,触到崭新的海水,它那有限的世界立即爆炸了。它甚至没有深度的概念,也不了解它可能遇到的鲸群的语言。”[14]108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指出,崇高客体抗拒语言,具有不可呈现性。语言将具体的世界简化为同一性结构中的概念,在命名行为中压抑了他者,自身也受到这种控制结构的诅咒。面对崇高客体的人类缺乏言说的能力,无法达成对自然的完整再现。因此,崇高审美只能表现为“对不可呈现之物的呈现”[19]。加拿大荒野是无法被人类意识感知的超感性存在,以绝对抽象的姿态抗拒传统的意义解读。因此,直面荒野的主人公们体会到身体和认知上的双重瘫痪感,这与伯克所说的“如临深渊”的体验十分相似[16]。他们唯有将全部注意力投注在此时此刻,调动被庸常封闭的感官,直面灵魂的震颤,接收以非语言形式传递的自然的秘密。库普兰德对荒野空间的描述显示了真理的浪漫吸引力,也表达了崇高对传统求真方法的排斥。荒野先于任何表意系统出现,是确定之物的对立面,是解开主体与客体之间矛盾的密码,时刻提醒主体超越僵死的自我疆界,与荒野建立非强迫性的关系,与自我内在和外在的他者和谐共处。库普兰德通过对北美西海岸荒野空间的描绘提醒读者,乌托邦天然存在于未受干扰的自然中,但此种乌托邦拒绝人类介入,是无法抵达、不能居住的。
三、阈限性的温哥华郊区空间和辩证的时空乌托邦
从荒野到城市再到下一个荒野,追寻伊甸园的脚步不断向前。当以加州神话为代表的美国梦出现末日危机时,加拿大成为下一个孕育梦想的空间,通往乌托邦的旅程又一次推迟了终点。《香波星球》中的泰勒,在驶向温哥华的渡轮上,激动地表示自己“越过了一条看不见的边界线,感到不可预测和令人震惊的新”[6]187。这种复兴感与当年拓荒神话的诞生如出一辙。《昏迷的女友》中的理查德也认为,没有历史负担的加拿大“保留着美国本来的样子”,甚至声称“做着美国梦的人们梦见的其实是加拿大的土地”[14]88。那么,加拿大会成为救赎的终点和永恒的居所吗?库普兰德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区域间的地理景观差异被资本抹平,加拿大城市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城市的复制品,面临着同样的坦塔罗斯困境——乌托邦就像树上的累累果实,明明近在眼前,却永在触及范围之外。《昏迷的女友》中的理查德(Richard)在“一座黑色的山顶”俯瞰山下的温哥华,这个“做着新生儿之梦的崭新城市正闪耀着希望的光芒”[14]7。理查德对山下之城的远距离观望让人联想到《圣经》中约翰面对新耶路撒冷——山巅之城的情景。同新耶路撒冷一样,完美的温哥华似乎也游离于历史之外,不可接近。从洛杉矶到温哥华,北美西海岸的城市同样面临着末日命运。人们的乌托邦想象被困在只有增长的单向未来中,任何怀着占有企图的靠近都只会将它推向更远的地方。
在《昏迷的女友》中,库普兰德通过区分机器和有机体的不同运作模式进一步说明了乌托邦困境:机器的运行模式是设定目标,向目标前进,实现目标后停止运转;有机体的行动则是一个交互、有节奏、不那么稳定并且永不停止的过程。维持自身存续就是有机体的目标。用“非此即彼的二进制机器思维”思考就会建构出“欧几里得乌托邦”[14]46。欧几里得思维倾向于把具体简化为概念,抹除他者的属性,为征服者用强制遗忘的方式抹杀文化和生命价值提供了借口。它压制和扭曲了人类的本能和激情,强制他们在幸福和自由之间二选一。因为工具理性和自主人格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统治者不得不“在伊甸园旁建立关押反叛者和异端的集中营”[14]47。库普兰德推崇的乌托邦不是把人变成机器,也不是把机器变成人,而是让机器保持机械模式,让人类保留自身的有机模式和生物节律。
既然“乌有之乡”无法在地图上被清晰地标注出来,那么通向乌托邦的路径也必非“寻常之路”。在《昏迷的女友》中,库普兰德反复引用一句克里族俗语:“懂得后退的人才能更好地前进。”[14]98只有采用迂回或侧移的方式,才能找到真正的乌托邦。库普兰德认为,非欧几里得的路线蕴藏在某种特殊的空间中,他尝试将空间视为一种动态形式,推崇没有具体身份且不断变动的地方,并以此种视角审视看似静态的温哥华郊区。对于数百万加拿大人来说,郊区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空间,但郊区却总是被人们轻蔑地提及:历史书在住宅区、轻工业园区和大型购物中心修剪整齐的边缘戛然而止;大众文化中郊区同质化和墨守成规的形象无处不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的郊区总是同单调压抑的保守主义与个人堕落或暴力相关联[9]107。库普兰德认为郊区是拟像和崇高的独特混合体,是一个比城市更具多样性、更后现代的空间,蕴藏着通向时空乌托邦的门扉。
《怀俄明小姐》中遭遇空难的苏珊,在即将坠落的飞机上瞥见一个“家家用汰渍洗衣粉、户户吃金宝汤罐头的平庸小镇”,想当然地认为“这又是个每十年至少发生一场奇怪杀戮的地方”[8]51。但当幸存的苏珊闯入这个郊区的一所空房子时,郊区的平凡消失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安睡于城市和自然之间的神秘空间”[8]53。同样的主题在《埃莉诺·里格比》()中再次呈现:厌倦人生的利兹(Liz)意外闯入一所临时腾空的郊区房屋,在“介于主动和被动、强大和软弱、光明和黑暗之间的模糊体验”中获得重生——“就像一个尚未远离肉体的鬼魂,通过两双不同的眼睛审视这个世界”[20]。利兹的“伪幽灵”状态就像苏珊在意外中的“死亡”和在郊区的“复活”一样,象征着人们在郊区空间获得的有别于庸常的他者视角。《昏迷的女友》中生长于北温哥华郊区的理查德拥有丰富的郊区生活经验,他的姓氏“多兰德”(Doorland)是“门”(door)和“土地”(land)的合成词,暗示他生长的郊区是位于城市和荒野之间的“门槛”——一个特殊的阈限空间。“阈限”(liminality)一词的拉丁文本义恰巧就是“门槛”,引申义为边界。“阈限空间”是位于两个空间之间,起间隔、过渡作用的分界,呈现一种介质之间的居间状态。作为具有临界性和矛盾性的居间空间,郊区空间阻断了传统的编码过程,突破了固有的二元思维,以非正面对抗的方式缓和了城市和自然正面对冲产生的巨大张力;作为具有包容性和延展性的双向空间,郊区空间融合、渗透、协调了城市和自然中的各种对立因素,为多元思维和全新话语的产生留下余地。库普兰德小说中的温哥华郊区凝视着人类和非人类空间之间的本体鸿沟,提醒人们线性时间神话之外的另一种选择——非欧几里得路线。
非欧几里得乌托邦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变动体,其动态轨迹可通过莫比乌斯环说明。莫比乌斯环是将一条纸带扭转180度后首尾相接产生的拓扑学结构。纸带本身是二维概念,通过三维的拧转,实现了起点和终点、A面和B面的重合。从莫比乌斯环的某一点出发的持续移动必将重回该点,于开始处结束。莫比乌斯环暗示看似对立的事物之间原本模糊的界限,隐喻人类历史的进程从来不是从过去向未来的单向、线性发展,未来终将成为过去,过去也必将孕育出新的未来。在《昏迷的女友》中,理查德看到“一千只逆流而上的鲑鱼”[14]107,它们的生态轨迹是非欧几里得的循环系统而不是欧几里得的线性系统。在帕姆(Pam)和汉密尔顿(Hamilton)的末日之梦中,商店指示牌上“闪烁的00︰00”暗示结束和开始处在交替循环的过程中——“当时间消失,无穷大和零就会成为同一件事”[14]125。书中也多次出现隐喻莫比乌斯带的数字“8”,理查德返回温哥华时所乘的飞机“在阿尔卑斯山脉上空懒8字(lazy-eights)飞行”[14]175;理查德和朋友们经常在老街区绕着“慵懒的8字”漫无目的地开车[14]263。
库普兰德笔下的郊区空间正如莫比乌斯带上A、B两面的接合处,是连接城市和荒野空间的桥梁。郊区作为中间地带,既可以借用自然的崇高之力将人类思维从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又不完全脱离追求进步的道路,通过开启城市与荒野的对话寻找人类和自然的契合点,有效实现城市和荒野空间的交融和共存。这个三维空间中蕴藏着主张多元交融、万物和谐的时空乌托邦,它关注对立元素间的相似和联系,用不断的整合与分化代替压抑和对抗。在这里,界限被打通,矛盾被调和,断裂被缝补,各种元素彼此碰撞交融,意义指向不再清晰,理论界限不再分明。随着郊区作为孕育乌托邦的梦想空间不断更新,乌托邦也在新的梦想里不断自我重组。处于阈限空间的主体也因超越阈值产生边缘状态和阈限心理,既可超然于结构外,脱离结构控制,又可深入结构内,对其进行颠覆和瓦解,从而成为具有双重身份和双向思维的第三方,即库普兰德推崇的“拥有流动边界的自我”[14]166。
德国学者阿斯曼(Aleida Assmann)曾说:“历史的绘画展厅里,时间和空间的纬度、历史和领土融合在一起,成为一道民族的记忆风景。”[21]库普兰德在北美西海岸承载着历史和时间的城市、荒野和郊区空间中穿梭,打破结构框架,在旧世界的角落中寻找散落的乌托邦密码。库普兰德的时空乌托邦构想,既未放弃传统乌托邦遗产,又试图超越现代主义构想;它批判理性对自然和他者的压抑,反对欧几里得思维,却并未否认理性的治愈力量。时空乌托邦借助阈限性的第三空间弥合了由空间形态乌托邦和社会过程乌托邦的对立导致的空间与时间的分裂,为未来乌托邦研究提供了有益启发。
[1] BAUDRILLARD, J. America[M]. Trans. C. Turner. New York: Verso, 1989.
[2] GEYH, P. & LEEBRON, F. G. (Ed.) Postmodern American Fiction: A Norton Anthology[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509.
[3] DURHAM, P. & JONES, E.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Literature[M].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80: 1.
[4] TURNER, F. J.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1: 1.
[5] BANHAM, R. Los Angeles: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Four Ecologies[M]. London: Penguin, 1971: 24.
[6] COUPLAND, D. Shampoo Planet[M]. London: Simon & Schuster, 1993.
[7] COUPLAND, D. Microserfs[M]. London: Harper, 2004: 3.
[8] COUPLAND, D. Miss Wyoming[M]. London: Flamingo, 2000.
[9] COUPLAND, D. Polaroids from the Dead[M]. London: Flamingo, 1997.
[10] KATERBERG, W. H. Western Myth and the End of History in the Novels of Douglas Coupland[J]. 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 2005(3): 272-299.
[11] PERREAULT, M. American Wilderness: A Histo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
[12] BERLIN, I.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80.
[13] COUPLAND, D. Life After God[M]. London: Simon & Schuster, 1994.
[14] COUPLAND, D. Girlfriend in a Coma[M]. London: Flamingo, 1998.
[15] COUPLAND, D. 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M]. London: Abacus, 1992: 25.
[16] BURKE, E.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
[17] COUPLAND, D. Souvenir of Canada[M].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2002.
[18] FITZGERALD, F. S. The Great Gatsby[M]. London: Penguin, 1990: 171.
[19] LYOTARD, J-F. 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M]. Trans. G. V. D. Abbeel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165.
[20] COUPLAND, D. Eleanor Rigby[M].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4: 45.
[21]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6.
The West Coast of North America and Spatiotemporal Utopianism in Douglas Coupland’s Fiction
QIN Zhen CHEN Shidan
The West Coast of North America is the core narrative space in Douglas Coupland’s fiction and also the representational carrier of the author’s utopian thoughts.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Coupland examines urban, wilderness and suburban spaces on the West Coast of North America, three distinct and interconnected spatial forms that have long been seen as static,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topia and space, and exploring utopian hope in free and open spaces. The hyperreal urban space in California produces a realized but doomed utopia. The sublime wilderness space on the West Coast harbors a utopia that exists naturally but rejects human habitation. The liminal suburban space in Vancouver breaks down the barriers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wilderness, alleviates the huge tension generated by the collis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a non-confrontational way, and opens the door of hope to the spatiotemporal utopianism.
Coupland; the West Coast of North America; spatial criticism; utopia
I109
A
1009-8135(2022)03-0107-12
秦臻(1988—),女,山东济宁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英美文学及西方文论。陈世丹(1959—),男,黑龙江七台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西方文论和西方文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丁·艾米斯小说中的后现代生态思想研究”(19BWW049);中国人民大学重点规划项目“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总论”(16XNLG01)。
(责任编辑:张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