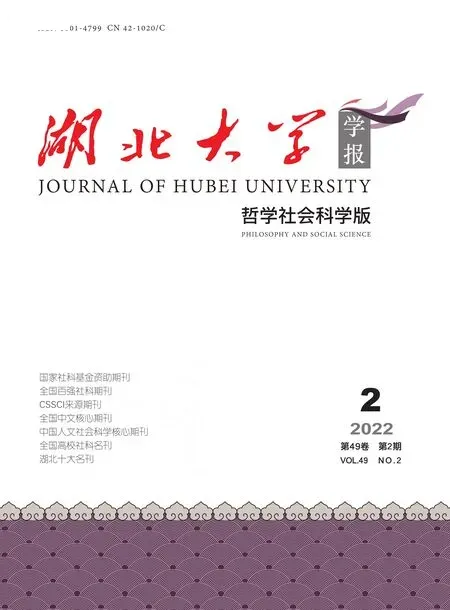春秋含章:汉至唐代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论
彭安湘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自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古代辞赋理论研究才开辟出自己的一片领地。从近三十年的研究历程来看,学者们对辞赋理论言说内容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其言说形态(1)目前学界对赋论的言说形态或言说方式有不同的称呼,或称“批评形态”,或称“批评形式”。的注目。这样的研究态势,除了研究者主观喜好及认知程度等原因外,恐怕更多的是与研究对象的特性相关。
中国古代辞赋理论大量混存于广义的“文”类中,虽不乏理性的、较成系统的赋学专论,更多的却是以感性的、零星散碎的片言只语居多,“造成了我国古代长期缺少独立的赋学批评,似乎也就缺少相应的赋学批评形态”(2)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86页。。受此影响,学界多关注赋学批评依存的资料文献来源和非独立性特征,而没有对这一赋学现象作更进一步的学理性的探讨(3)如何新文揭示出古代赋论形态除论赋专文和赋话外,尚有历史、哲学著作、文集、笔记、诗话、四六话及赋篇、赋集的序、跋、凡例或附录中存录,参见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第13页。程章灿则认为它们广泛地存于别集、总集、诗文话、赋话、史传、书目、诸子、笔记、类书、出土文献之中,参见程章灿《赋学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页。踪凡、郭英德依据文献性质,将赋学文献概括为专门性、兼容性和依附性三大类:专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编集(含编选)、评论、注释的文献,而不涉及诗歌、骈文和各体散文的文献,为专门性赋学文献(纯粹性赋学文献);历史上一些史部、子部文献,载录或摘引部分赋体作品或者赋论文字,为依附性赋学文献;收录、评论或注释赋体作品较多的总集、别集和诗文评文献,往往诗、文、赋兼收,但赋体文学占有较大比重,或者有独成篇章的赋论文字,为兼容性赋学文献。参见踪凡、郭英德《历代赋学文献的变迁、类型与研究》,《求索》2017年第3期。。鉴此,本文借助相关研究方法,聚焦汉至唐代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试图揭橥其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以及在赋学批评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一
形态学(morphology)研究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被引入到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后来才逐渐被广泛应用到文学批评领域。本文借助这一研究方法,首先从表层特征和深层意义两个向度来界定“赋学批评形态”这一概念。
就表层特征而言,“赋学批评形态”是指辞赋理论言说的形式特征。我们依据其外在的、表面的形式特征,可以分出若干种具体的批评形态。具体的操作是,考量古代赋学批评理论言说在其依附的文献中所占的分量比重、出现的频率、运用的时长、达到的范围、形成的规模、造成的影响等综合因素后进行分类,以了解不同类别、门类、样式、品种的批评形态的共性和个性。其中,了解个性至关重要,这是其是否立类的关键。如笔者《中古赋论研究》第五章“展示与迁流:中古赋论形态论”部分提及的史传式、赋序式、赋注式、选本式、专论式等具体批评形态,均着眼于其外部表现形式和个性标识。比如称曹魏和晋初赋序式批评形态“多为叙述性言说,一般序文较短,内容的负载量也有所限制,以一两句话交代出作赋动机,有一些固定化的模式可遵循”;专论式批评形态“第一,有明确、统一的论赋纲领;第二,论说的内容广博全面,是较成体系的理论论述;第三,以骈体行文,凸显论者个人风格”(4)彭安湘:《中古赋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15、219页。云云。
从深层意义而论,“赋学批评形态”除了指称理论言说的外在特征外,还要揭示其内蕴的批评思想、观念等,并将之与批评范型和话语视作一个有机系统。如许结论选本式赋学批评形态,从“重体类意识”、“现实的功用”、“品鉴的眼光”和“以作品为中心的多元批评方式”(5)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第96-100页。四个方面对之进行系统的观照,着眼于观念、意识、视角和方法的有机统一。
汉至唐代史书纪、传、志体中载有丰富的赋学资料,以其跨时长、份额多、比重大、频率高、成规模等原因,已具备了成为赋学批评形态某一样式的基本条件。可姑且称之为“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它是在形态学分类思维运作下呈现的具体样式之一。不仅对赋学文献的保存和流传,对赋学批评内涵的丰蕤与形态的构建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史书中那些行文含有文采、美质、情怀和志向的赋篇、赋句,那些“文皆诣实,理多可信”(6)刘知几:《史通》,白云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12页。的传主、赋家本事,那些简省、洗练、精到的论赋之语与辞赋评论,以及内蕴的批评思维和文化意义等等,既增加了传主的风采,又使得质实的史事叙述增添了几许诗性色彩、人文光泽和评鉴气息。“春秋”泛指史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类,因此,“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正可谓“春秋含章”,如春有草树、山有烟霞,自成魅力风光。
二
我国有着悠久的史官文化传统。因“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7)梁启超撰、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页。,至西周时,史官不但成为重要的文化主体,而且分工精细明确。据载,太史掌国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就见存史书而论,纯记事之史,最早为文句极简而类“账簿”的《春秋》。主记言之史,则是性质颇似资政“档案”的《尚书》。它录存的古代策命诰誓之原文、单词片语之格言及少数歌谣,正是史书载言和载文之肇始。对《尚书》所载《元首之歌》、《五子之歌》,唐代刘知几在《史通·载文》篇特意点明且给予高度评价,称“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8)刘知几:《史通》,第202页。。其后,传释《春秋》的《左传》打破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史职原则,“言之与事,同在传中”,不仅“言事相兼,烦省合理”(9)刘知几:《史通》,第42页。,更主要的是,它进一步发展了《尚书》创设的史书载言、载文的传统。
《左传》载言、载文现象非常普遍。其中,载言以大夫词令、行人应答最为典型。《史通·申左》称:“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10)刘知几:《史通》,第656页。有学者认为它们应该是作为当时的“成文”(11)邵炳军、梅军:《〈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页。而被写进史书的。依此意,则载言亦当属于广义的载文范畴。除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外,《左传》中的“成文”还包括祝盟、铭箴、诔碑、诗赋、颂赞、谐隐之零星文句或完整篇章。如《襄公十年》“骍旄之盟”中“世世无失职”的盟辞;《宣公十二年》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箴辞;《哀公十六年》中“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的诔文;《僖公二十八年》“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的舆人诵(颂)辞;《襄公四年》鲁国国人歌“侏儒”的谐辞等等。至于《左传》所引《诗经》,据清人魏源统计有217条(12)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诗古微》,何慎怡校点,汤志钧审订,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182页。。所引诗作不但展示了春秋外交间诸侯交接行李往来中的“赋诗”活动,带有强烈政治功用色彩;还展示出赋诗者“言志”或听诗者“观志”,皆跳出诗的本事本义而按照“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的原则进行引申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在完备的礼乐体制下,《诗经》已经从早期简单的、原始的群众性参与的艺术转变成专门化、职业化的观赏性艺术,由此鉴赏的、品评的理论逐渐成熟起来(13)傅道彬:《“诗可以观”——春秋时代的观诗风尚及诗学意义》,《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典型者莫如《襄公二十九年》对吴公子季札在鲁国“遍观周乐”的记载。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左传》载文的主要特点:一是带有文体意味;二是载文是为了叙事;三是已有鉴赏与品评倾向。
《左传》载文的前两个特点也同样鲜明地体现在其载“赋”的现象中。第一则见诸《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置其母姜氏于城颍,后受颍考叔点化,“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14)马积高认为这则是“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前人并无定称,亦可称为“诗体赋”。参见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页。第二则见诸《僖公五年》:晋国政令不统一,士蒍感叹而作,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从文体角度而言,郑庄赋“大隧”,士蒍赋“狐裘”,“虽合赋体,明而未融”(15)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34页。,属不成熟的赋体之前身,但在刘勰看来,这正是赋体由“赋诗言志”的行为功能向“词自己作”的文体创作转变的标志,更是史书载“赋”的开始。从叙事功能而言,“《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则是叙郑国内乱平息的余波和晋国内乱纷争的前奏,以彰“郑庄至孝,晋献不明”(16)刘知几:《史通》,第202页。。因此,如果追溯史书载赋之源,当萌蘖于《左传》。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史书载赋、论赋,还是兴起于汉代。

自汉以后,宋前诸正史(19)主要指《史记》、《汉书》及之后的《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旧唐书》这14部史书。之纪、传、志均不同程度地载录有与赋相关的内容。据统计,诸史之传体共收录完整赋作86篇,赋题156个,赋序5则,引用赋句20余处;诸史之志体如《汉志》载辞赋家58家,赋篇1004篇;《隋志》载赋集18部;《旧唐志》载赋集14部。这些数据足可说明,史书确实是载纳丰饶辞赋资料的富矿,对保存和传播辞赋文献有着重要的意义。
不过,对于史书载赋,自唐以来存有两派意见。一派或因史书纪实事与辞赋立伪假的矛盾而力主否定。如唐代刘知几认为“史氏所书,固当以正(实)为主”(20)刘知几:《史通》,第202页。,而“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21)刘知几:《史通》,第773页。,故在《史通》之《载文》、《载言》篇对《史记》、《汉书》所载司马相如、扬雄、班固、马融赋“皆书诸列传”的做法颇有微词,称“不其谬乎”(22)刘知几:《史通》,第202页。,建议将收录于纪传的人主、群臣、文士之文辞,“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23)刘知几:《史通》,第44页。。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对《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传》也发出了“但采辞赋”的质疑,称“贾、屈同传,以渡江一赋耳,不载《陈政事疏》,与《董仲舒传》不载《贤良策对》同,几等贾、董于马、卿矣。舍经济而登辞赋,得毋失去取之义乎?”(24)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07页。
另一派以史迁载文“心知其意”和“重文”的原则而力主肯定。如清代刘熙载对正史“以文传人”、“读赋知人”的史识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称“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即知其人也”(25)刘熙载著、薛正兴点校:《刘熙载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夏炯也称“史公之意犹是圣人存十五国之风之意也”(26)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84页。,对《司马相如传》载录的赋篇及赋评均表示认同。章学诚虽因史书对古人之书有所删节不尽传写而略有微辞,称“史传之例,往往删节原文,以就隐括,故于文体所具,不尽全也”,但盛赞了《史记》、《汉书》载赋,曰:“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载于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27)章学诚撰,吕思勉评,李永圻、张耕华导读整理:《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页。近人徐复观亦赞《史记》,称“至屈原、贾谊、司马相如诸列传,为重视文学在历史中的意义,更不待论”(28)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64页。,算是对清人观点的一个有力回应。
现在,我们不纠结于史之纪实与赋之虚夸的文类区别,也不拘泥于史书是否是“舍经济”而具知人、扬文的功能之别,而是正视史书载赋的事实,从“形态学”的角度重新阐释,以发掘出其赋学批评的意义。
三
赖大仁在《文学批评形态论》中称:“形态学研究至少包含三个方面或层面:一是描述事物的外部形状,区分事物的类型……二是研究事物的内部结构或者叫形态结构……三是研究事物的形态变化及其规律。”(29)赖大仁:《文学批评形态论》,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28页。下面即依循由内而外、由现象而规律的思路,揭橥出专属于“史传式赋学批评”的内涵与形式特征。“史传式赋学批评”的内涵是极为丰蕤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载录赋家代表作,树立选赋标准




(表1) 宋前史书择录的完整赋作篇目分布情况
(二)交代作赋动因,评骘赋作亮点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3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96页。
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后汉书·张衡传》)
中兴二十三载,余……涉湘川而观汨水,临贾生投书之川,慨以永怀矣。及造长沙,观其遗象,喟然有感,乃吊之云。(《晋书·庾阐传》)
泰始八年,拜修仪。受诏作愁思之文,因为《离思赋》。(《晋书·左贵嫔》)
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前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后汉书·祢衡传》)

除了绍介作赋意图、动机外,史家还擅长对辞赋进行直接或间接评骘。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论《离骚》曰:“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36)司马迁:《史记》,第2482页。这段文辞对《离骚》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给予了高度的概括与中肯的评价。不过,这种全面的长段式评骘,在宋前史书中较为少见,史家更普遍采用的是对赋篇作简要式评点。形式如下:
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后汉书·崔骃传》)
又为《雪赋》,亦以高丽见奇。(《宋书·谢方明》)
作《海赋》,融文辞诡激,独与众异。(《南齐书·张融传》)
率又为《待诏赋》奏之,甚见称贺。手敕答曰:“省赋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梁书·张率传》)
萧子显……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梁书·萧子显传》)
史传中此类评论数量可观,内容丰富,或论其风格,或赏其文辞,或议其旨归,或评其积习,是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手赋学批评资料。后世论赋者也多从中取资。如清代李调元的《赋话》,就从史辞及其他文献中摘录了大量的赋评资料而形成了一种采撷赋中“佳语”以置评说的新体例。与在赋前交代赋作背景或动机的撰文意图相似,史家之所以对赋作进行直接或间接评骘,也暗示了史家录赋的缘由,是史家“文之将史,其流一焉”(37)刘知几:《史通》,第201页。观念的体现,从而达到“以文传人”、论赋以褒贬人的目的。
(三)叙述赋家本事,揭示赋学背景
纪传体史书,以写人为要,以叙事为工,二者融合无间、密不可分。所谓“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38)刘知几:《史通》,第35页。,故叙事是其主要特征。就《史记》之屈贾、相如列传来说,司马迁在传写他们的本事时,往往揭示出较为深广的赋学背景,诸如文化制度、评赋标准、创赋经过、效果影响等。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司马相如列传》所载相如本事,其辞曰:
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赋奏,天子以为郎。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39)司马迁:《史记》,第2999、3002、3043、3054、3056、3063页。
许结对此段赋本事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兹引如下,以广识见:“其一,记述了汉宫廷大赋崛兴于武帝朝的史实,为研究汉宫廷赋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文献;其二,记述了相如赋由藩国向宫廷的转移,反映出当时大赋与大一统政治的联系;其三,记述了相如赋‘三惊’汉主的史事,既彰显相如《子虚》《上林》《大人》三赋的创作背景,也说明了汉武帝对汉赋隆盛的贡献;其四,分析了相如赋虚构夸饰的特点,以及‘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的创作旨归。换言之,检阅该传记中述赋与论赋文字,不仅使读者对相如一生为赋的主要经历和代表性成果一目了然,而且于景帝、梁孝王、武帝对赋的态度,西汉盛世的献赋之风,赋家作为内侍居职郎官的特殊意义,以及汉宫廷大赋的创作意图与功用,均有明晰记载,其中内含的意义,更可供后世阐发与研究。”(40)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第88页。
诚如斯言。司马迁所叙相如本事确实包蕴丰富,大有读一传而概知西汉赋学全貌之感。司马迁作七十列传,入选者大多为“立功名于天下”者。其自序中对相如“《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41)司马迁:《史记》,第3317页。的“功名”总结,并不是无根之论,而是传主本事与大一统时代的政治风会、文化思潮、制度礼俗等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从作家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着眼,着重考察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了社会生活面貌和社会文化心态,并对这种反映的正确与否和价值意义进行评判的做法,又含有“社会文化批评”的意味。
后世正史因体例相似,大都步武司马迁笔法。如《汉书·扬雄传》、《晋书·文苑传·左思》、《宋书·谢灵运传》、《陈书·江总传》等都于赋家的本事叙述中揭示出较为丰富的赋学文化背景,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正确与否和价值意义的评判。
(四)设置辞赋目录,展示赋学流变
《汉书》对《史记》开创的“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既有承继又有创新。《汉书》列传对贾谊、枚乘、枚皋、司马相如、扬雄等大体依循《史记》为赋家立传和收录赋篇、评论赋家赋作的路子,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设置辞赋目录及其叙录,却是新创。
《诗赋略》著录辞赋与歌诗两种。其中辞赋略载屈原、宋玉、荀况及秦代、西汉辞赋家共78家,作品1004篇,分为“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四类。前三类著录,只载赋家姓名及其作品篇数,如“屈原赋二十五篇”、“枚乘赋九篇”;所载赋家作品也不列简介内容体例的叙录、提要,但间有对赋家事迹的注释,如在著录“宋玉赋十六篇”后曰:“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42)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1747页。第四类“杂赋”类因“皆无作者”、“皆无年代”、“皆署主题”、“多冠杂字”(43)程千帆:《俭腹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页。而异于前三类。对此,历代学者对辞赋分类的义例多有探讨,却终究是推论之辞而难有定论。不过,由此目录依然可见出:其一,编撰者对诗、赋体例的基本看法,即歌诗之体与赋不同,而(楚)辞之作则同属赋体(44)何新文、苏瑞隆、彭安湘:《中国赋论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页。;其二,辞赋略本身就是先秦至汉代学术文化的一部分,体现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特色;其三,编撰者所生活的汉代及此前的战国末期,是诗赋繁荣的时代,《诗赋略》是对历史与当代学术文化的总结归纳。
自《汉书》以后,宋前史书继承志体载录辞赋目录传统的还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如《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有41家赋总集和若干赋选(如《文选》)。它们或以主题、或以题材、或以音韵而成集,均载有卷数及编撰者。新旧《唐书》体例与之相同,稍异的是《新唐书·艺文志》还录有张仲素《赋枢》、范传正《赋诀》、浩虚舟《赋门》三部重要赋论著作。隋唐时期志体设“集部”著录赋学文献,“虽为前代志经籍,亦即为当代立法程”(45)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世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5卷第1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且“节次而下,亦有条理”(46)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后序》,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5卷第4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49页。,成为当时赋学目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并客观地反映了赋学随年代迁徙而有所新变的真实状貌。
《汉志·诗赋略》在著录诗赋目录后约有一篇长三百字左右的序文。内容包括:首先,是“不歌而颂谓之赋”的“探本之论”,指出与音乐脱离,靠口诵成声是赋与诗最本初的区别;其次,是赋由行为到文体的“演变之论”,指出赋本是“必称《诗》以谕其志”的行为,因礼崩乐坏,士人身份移易,于是才有“贤人失志之赋作”的赋文体出现;再次,是揭示赋源于“学诗之士”的“溯源之论”,阐明了赋即源于《诗》的基本立场(4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1755-1756页。。《诗赋略》序文字不多却含义丰富,已涉及到了赋体、赋源、赋史等诸多内容。换言之,此序概述了赋的文体特点以及诗、赋繁荣发展之流变,颇具一般文学流变史和赋学批评史的学术性质。
可见,汉史创立的“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其批评内涵在后世史书中颇有示范性与影响力。《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等史书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赋家身世学养、作赋背景、赋家轶事以及辞赋评论的文献材料,同时也收录了大量的赋篇。当然,纪传受体例限制,有的只点出赋名和赋篇数目,但是其丰富的赋学批评内涵,确为赋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与汉至唐代其他赋学批评形态如赋序式、选本式、专论式相比,“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在形式上还具有如下鲜明特征:
第一,传人与传赋互见。《史记》为纪传体鼻祖,“史迁增饰词藻,亦欲显其人、申其人之精神耳。故虽似传奇之代作喉舌,非欲虚构故事,但求‘伟其事,详其迹’,而不失其真也。班固删削,虽较翔实,而马传之奇遂失”(48)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80-81页。。之后的史书虽在“奇”上不及《史记》,但都较注重用赋家本事与作品互见的方式来阐释赋家的人格与艺术风格,重视纪人与传文的合一,使人“读其赋者即知其人”。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称:“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49)章学诚撰,吕思勉评,李永圻、张耕华导读整理:《文史通义》,第24页。因此,读《史记·司马相如传》之《子虚、上林赋》,由其“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50)王世贞著,陈洁栋、周明初批注:《艺苑卮言》,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32页。而知“长卿有艳才”(常景《赞四君四首》其一)、由“始以游猎动帝之听,终以道德闲帝之心”(51)于光华:《评注昭明文选》,上海:扫叶山房,1919年,第12页。而知其借文才达志的深密心思;读《宋书·谢灵运传》之《山居赋》,由其描写的山明水秀、物资丰实的庄园景致和“弄琴明月,酌酒和风”放情山水、肆意游邀的庄园生活,则可以窥见暂别名利场的高门名士的潇洒风度;读《周书·庾信传》之《哀江南赋》,从其抒发的“身世”之“悲”与“王室”之“哀”以及描写的“逼迫危虑,端忧暮齿”的悲凉晚景,体味到一位客居异乡的羁旅之臣的深深哀怨。

《史记》列传……独于司马相如之文采之最多,连篇累牍,不厌其繁,可谓倾服之至。而所载之文,又复各呈其妙,不拘一体……驱相如之文以为己文,而不露其痕迹;借相如之事为己照,并为天下后世怀才不遇者写照,而不胜其悲叹。洋洋万余言,一气团结,在《史记》中为一篇最长文字,亦为一篇最奇文字。(53)李景星:《四史评议》,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09页。
刘熙载称“太史公文,精神气血,无所不具。……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处。至读者或谓之悲,或谓之愤,又可以自徵器量焉”(54)刘熙载著、薛正兴点校:《刘熙载文集》,第64页。,道出了史书传人与传赋互见的用意所在。
第二,叙事与批评结合。传统的中国史家大都习惯于通过变换体例结构和提高叙事技巧来表现以褒贬为主旨的史学批评倾向。《史记》的“叙事不合参入断语”(55)刘熙载著、薛正兴点校:《刘熙载文集》,第64页。及“序事中寓论断”(56)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2页。,则是有意识地发展了史书叙事性的批评方式——将赋学批评夹杂在对传主本事的叙述中,叙事与批评融为一体。
比较典型的例子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之赋本事外,他如《晋书·左思传》中左思造《三都赋》及他人作序、评价、叹服的史事与《三都赋》“研核”、“博物”、“用心于明物”、“品物殊类,禀之图籍”的评价结合无间;又如《晋书·袁宏传》述其撰《东征赋》后,因漏写名流而遭其后人发难的故事与当时重赋、以赋当史志的风气相符;再如《北齐书·魏收传》叙魏收与邢劭比才学高低与作品臧否的史事,则紧紧围绕着“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的赋论议题来组织等等。而且,以上诸例,对传主叙事是主体,批评则需读者在高超的叙事技巧中去意会和领悟。“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57)刘熙载著、薛正兴点校:《刘熙载文集》,第64页。,这样一来,赋学批评便自然而然地融化在叙事之中了。
另外,司马迁还创立了“太史公曰”和“太史公自序”的形式,前者发展为“史臣曰”的“论赞批评”模式。它们于正文叙述之外,单独地发表评论,作为一种补充来满足批评的需要,起到了对所记述的历史事实进行带有综合意味的评价作用,使史家的历史观点、思想倾向和才识见解得到了较集中的表现。如“太史公自序”中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即是。当然,较典型的是《宋书·谢灵运传论》,沈约在“史臣曰”部分,以诗赋为重点,将之放于文学整体发展的大循环、大流变中去认知,系统地叙述了自先秦至南朝宋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评论了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从一篇完整纪传文的表达手段来看,先叙后议再评,无疑也是叙事与批评相结合的体现。
第三,容量大与依附性兼具。称“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包容量大,一方面是指批评内涵非常丰富。对此,张新科进行了很好的归纳,称其包括“论赋的发展”、“论赋的作用”、“创作论”、“作家论”、“作品论”五大类(58)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5-262页。。也就是说,史传式批评基本上是围绕着赋家的文学创作,诸如创作经历、创作心理、作品选录及评价影响等方面展开的。它反映了撰史者较为全面的赋学批评观念。另一方面是指史传式批评内含的样式多样化。如载录完整赋篇、撰写或收录赋序、采用直评或述评、录用赋注、采用“某某曰”的论赞、载录赋学目录等形式,对赋序式批评、选本式批评、赋注式批评、笔记式批评及赋学专论批评等均有重要的影响。
而尤需引起注意的是史传式批评与笔记式批评的关联。赋学笔记式批评的典型为南朝宋刘义庆撰、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将其归为子部小说家类。然而,《世说新语》的内容并不属虚构,且无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相反,所记内容属于历史事实,其中的史料多被《晋书》和研究魏晋史的今人大量采用。因此,《世说新语》不属于小说,而属于史料笔记。
具史料笔记性质的《世说新语》,记载了丰富的言赋材料,涉及嵇康、皇甫谧、刘伶、张华等数十名赋家、名士。或记赋坛轶事,或载作赋故实,或叙时人评议,或是记事中兼有评论,包括了赋的创作、评论及其社会功用价值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带有轻松、诙谐意味的语调中叙事谈赋,展现了第三人评议、二人论辩、多人讨论等多种谈论形式,生动活泼地反映了两晋士族社会谈赋重赋之风,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丰富了两晋尤其是东晋的赋论(59)何新文:《清谈与赋谈——从〈世说新语〉看两晋士人的辞赋评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其中,对左思《三都赋》、庾敳《意赋》、庾阐《扬都赋》、袁宏《东征赋》和《北征赋》、顾恺之《筝赋》、孙绰《游天台山赋》等的载叙多为《晋书》采录。换句话说,《世说新语》所载赋学资料,虽不入正史,却能与正史相发明。故这种偏于赋学史料辑录,以划分条目、互不连贯方式的笔记式批评亦是对严肃、典重的“史传式赋学批评”的补充。
然而,历代正史书事、记言、写人,或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60)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2735页。,或是“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6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4235页。,或是“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62)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等等,虽目的不一,但大抵不离治国安邦大道的效用,所谓“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63)刘知几:《史通》,第506页。。自汉史始,正史史传多体现着一个时代社会政治的主流意识。擅长诗赋等文学素养,虽是传主才学心智的体现,亦只是其治国齐家修身的必要要素之一而已。所以,尽管史传中也涉及到了有关传主的辞赋创作及辞赋批评,但这并不是撰史者撰写的重点和关注点(除以文才立世者外)。大部分的史书只是顺带涉及,更多的是“某某著诗赋奏议数十篇行于世(传于后)”这样的简略表述而已。与之相应,在内容和形式上包容量甚大的“史传式赋学批评”,亦只是厚重史书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是宏大历史叙事中的一些史学素材和文学批评片断。因此,史传式批评是一种非独立状态的赋学批评,它紧紧地依附在宏大的史事叙述中。这是中国古典赋学批评形态混融性特征的共性表现,史传式批评自然也不例外。
四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64)章学诚撰,吕思勉评,李永圻、张耕华导读整理:《文史通义》,第65页。。“义”、“事”、“文”三者中,“文”既指笔法文采,也指作为史料载于史书中的多种文体文辞。赋即为史书载文的一种。自春秋史书载言萌始,至两汉正史载赋现象的兴发和繁盛,再至各代正史对它的承接和赓继,“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在汉至唐代漫长的历史时段中已然发展为一种较为成熟且颇具代表性的批评样式。由于我国史传文学历史的悠长性与不可比拟的权威性,含融其中的“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不同于其他赋学批评形态(如赋序式“在它趋向于成熟的同时,已经划上了句号”(65)徐丹丽:《魏晋六朝赋序简论》,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总第7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的阶段性存在,而是与史书这一载体同生共育,并得以历代相继。其批评内涵和形式特征不仅能反映那个时代大体的赋学观念和文化意识,使读者能在整体的史学观照中把握一代代赋学发展的脉搏,而且,它的理论生命和示范意义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在后世不断地被承祧、发扬并产生重要的影响。
譬如载录“辞赋目录”的传统,即为元明清正史所继承。其所载书目既有重要的赋论著作,也有知名的赋集。如《元史·艺文志》载有吴莱《楚汉正声》二卷、郝经《皇朝古赋》一卷、虞廷硕《古赋准绳》十卷、祝尧《古赋辨体》八卷;《明史·艺文志》载有刘世教《赋纪》一百卷、俞王言《辞赋标义》十八卷、陈山毓《赋略》五十卷;《清史稿·艺文志四》之“诗文评类”更是载录了大批清人的论赋之作,像王之绩《铁立文起》、刘熙载《艺概》、孙梅《四六丛话》、王芑孙《读赋卮言》、林联桂《见星庐赋话》、李调元《赋话》等等。另据许结搜证,后人在补续正史《艺文》(《经籍》)志时也辑补了大量赋类,如姚振宗对照《汉志》就辑补了“梁孝王群臣赋”、“汉郎中枚皋辞赋一百数十篇”等七种(66)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第90页。。到了明清时代,一些地志学家亦认为“方志可以有艺文志,仿《汉书·艺文志》之例”(67)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5页。。如录乡贤诗赋遗著,可以从诸史艺文志、经籍志和诸家书目中取材,以补前志所未收,也起到了史志的目录学功用。无疑,与宋前史录相比,这些载录除具有“包涵文学作品的文本整理、文学典籍的文献承递、文学知识与经典的传播”等“文学史权力”(68)程章灿:《总集与文学史权力——以〈文苑英华〉所采诗题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外,还具有重视赋学衡鉴批评功能的强大宣传力和包容力。
再如揭示赋学背景中呈现的赋与制度的关系,也为后世史书所承传。内容上,由对汉代“献赋”制度的事实与功用的记述,转换为唐宋以来对“考赋”情况的载记。像《文献通考》记述熙宁罢赋与经义的关系(69)马端临:《文献通考》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清代翰林院考赋的渊源与变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呈现、《清史稿·选举志》对清代八股与诗赋及学术关系的发明,对“科举之弊,诗、赋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7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八《选举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50页。的揭示等等,无不从制度的层面反映了其时的政治文化面貌和社会文化心态。
不止如此,“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的影响还溢出正史的范围而辐射至中国古代小说文本,尤其是由史事敷衍而成的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等)中。这类小说不但蕴藏有较丰富的赋学作品与赋论资料,而且在小说评点盛行之时,又衍生出独特的赋学批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学语境中雅、俗(或正、谐)两种文学体式的相融互渗(71)王思豪:《〈三国演义〉中的赋学史料及其与小说之关联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这又是史传式赋学批评在后世回响过程中旁衍出的有意味的现象。
有学者称“(形态研究)不仅是解决批评本质与多种批评关系的重要途径,而且科学史的研究证明,一门学科理论上的成熟,往往以形态研究作为标志”(72)杨扬:《文学批评形态的艺术分类》,《当代文坛》1988年第4期。。现代辞赋研究已进行了几十年,大量的研究学者、丰硕的学术成果、十余届的赋学会议,皆证明这个学科应该到了相对成熟的研究阶段。我们结合赋学批评形态概念界定的两个向度,对汉至唐代正史这一研究对象作理论层面上“类”的划分,将分类研究与系统观照相统一,纵向梳理与横向比照相结合,既探讨了“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的生发、演进,又揭示了其显于外的批评内涵、形式特点,蕴于内的赋学观念、文化意识,以及传于后的辐射与回响。希冀这些思考能为推进古代赋学研究的成熟化进程有所助益。
-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古代谣谚的文体特征
- 民国时期的茶叶对外贸易
- 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