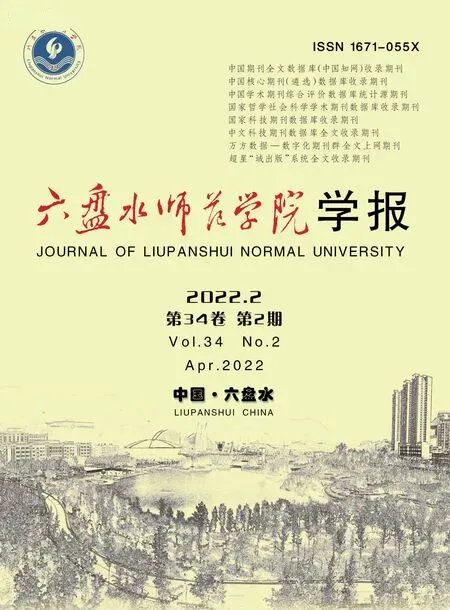赋体“听声类形”的艺术运造及其审美特征
支 媛
(1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2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4)
音声具有稍纵即逝、随生随灭的特点,很难像其他呈现“具象形式”的艺术那样表现出空间的实在感,其本质上体现为抽象性和模糊性。因此,要对音声(非物理属性)进行描述,就必须建立在接受感觉即听感外化的基础上。语言符号的介入,无疑让抽象化的音声具有了可释义的手段,语言通过字段的结构性表征系统、词义组合构建的名实对应关系来表达意义,听感的外化以语言为介质得以实现。文学语言利用自身独特的阐释性对音声进行转译,通过语言文字的精绘营构,达成以语像呈现声像的审美意识。以语像呈现声像需要创作主体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通过锻炼准确描摹听感的各种语言技法,才能使音声融入到语言意义生产的过程中,或者说使音声文学化。
对音声描绘的文辞技法突出地表现在赋文创作中,反映了文人对艺术语言的自觉运用。赋是中国古代最具语言艺术特质的文体,以善用辞藻、修饰词章见长,赋家凭借深厚的学养,通过搜选、创制、巧构、精琢字词来提升语言文字的质感与美感,基于创作需求,赋家刻意强化遣词用字,因求新好奇,大量创制繁难生僻而又脱离口语的词汇,客观上造成了“言”与“文”的分离,推动了文学由言语艺术向书面艺术的转变。赋擅于“写物图貌”“随物赋形”,精心描绘事物形态造成视觉形象的清晰感,在晦义的音声与显义的语言如何关联对应方面作了重要的尝试和突破,也为其他文体在描述音声的语言运思上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一、赋体音声描写的技法
相较其他传统文体,赋体文学具有显著的语言艺术特质,并特别体现为文人化的书写特征,较文学的“实用”性,赋更加注重字类形体的阅读美感及书面艺术化的表达效果,显示用字与修辞的自觉意识。在创作中通过新创拟声、化虚为实等语言技法,传达对音声听感形象的文学塑造。
(一)新创拟声
拟声也称象声或拟音,是摹拟声音声响状态的描述性语言,最初人们以主观的音感辨别转由语言的音位系统模拟,以语音连接自然音。郭绍虞认为:“语音之起,本于拟声与感声。拟声是摹写外界客观的声音,感声是表达内情主观的声音。拟声语词既善于摹状声貌,感声语词尤足以表达声情。”[1]《诗经》中就有许多拟声词的运用,如:鸟声(关关、喈喈、雍雍、嘤嘤、嗷嗷),虫声(喓喓、嘒嘒),水声(活活、濊濊)、风声(习习、弗弗),乐器声(简、镗、将将、渊渊)等等,可谓相当丰富。赋在拟声的运用上,一方面继承吸取了前人拟声的语言技巧,祖述袭用《诗经》中的拟声词,且多取叠字。如
众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鸣相号。王雎鹂黄,正冥楚鸠。姉归思妇,垂鸡高巢。其鸣喈喈,当年遨游。[2]卷十九,348(宋玉《高唐赋》)
呦呦相招,《小雅》之诗。[3]42(公孙诡《文鹿赋》)
王雎关关,鸿雁嘤嘤。[2]卷八,171(扬雄《羽猎赋》)
雷隐隐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2]卷十六,294(司马相如《长门赋》)
另一方面,赋又通过新创拟声语词,将汉字的形、音、义进一步书面化、艺术化,不仅让主观听感的摹音更加近似自然音的音响效果,而且更注重对音声情态的表现,增加了对音声的立体化描述。这类语词在赋作中相对于袭用的拟声词数量更为丰富也更为常见,其多出于赋家临文新创,目的是在语言文字的择用上避免重复,追求变化,表现出文学语言书面化的自觉追求。如:
砾碨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礚礚。[2]卷十九,347【礚礚:砾石相摩之声】(宋玉《高唐赋》)
扶与猗靡,翕呷萃蔡[2]卷七,154【萃蔡:衣服飘动摩擦声】(司马相如《子虚赋》)
金鼓迭起,铿鎗闛鞈。[2]卷八,163【铿鎗:钟声;闛鞈:鼓声】(司马相如《上林赋》)
铚钉钟涌,声讙薄泙。[3]160-161【铚钉:水冲击声;薄泙:波涛如雷鸣之声】(扬雄《蜀都赋》)
方辕齐毂,隐轸幽輵。[3]162【隐轸:车声】(扬雄《蜀都赋》
雷叩鍜之岌峇兮,正浏漂以风冽。[2]卷十八,328【岌峇:椎铁声】(马融《长笛赋》)
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2]卷一,31【嶈嶈:水激山之声】(班固《两都赋》)
这类拟声词借用汉字以形表意及语音象征的功能,强调音声的震动源和主体的听觉感受,出于描写形容的语用需要而“肆加偏旁”,多借联边、双声、叠音等造字。有的词语直接利用偏旁与发音体的物性接契,尽量仿似音声来源的原始状态,如“礚”表“砾石相击之声”,“轸”表“车声”,“嶈”表“水击山石之声”等。有的词语遵循同旁相从的原则,如“铿鎗”“岌峆”“浏漂”,凸显赋文造字运词从属“类聚”的语用考量,以符合赋体繁复异形的铺陈需要,在行文上造成绵密整饬的视觉美感。
还有一类拟声并不单纯地模仿自然声响,而是注重对声音整体感受和印象的传达,相当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声音图画”“借助一个或一些声音来描写这一切,首先是描写动作。但是,对于声音、气味、味觉与触觉印象,也有这样的声音图画的摹仿或声音再现。某些声音图画与色彩、丰满、程度、悲伤、安宁等等的表现结合着”[4]。其在“拟声”的基础上扩大了音声描写的指涉范围,包含着指代动作或状态的特征,加强了对音声面貌的立体化呈现。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将“极声貌以穷文”[5]277作为赋命名和立体的依据,指出了赋体文学的语言特征,即描摹物象,曲尽物态。赋体造字拟声,形容尽致,或直接新造一字一词表述音声的特定情态,或通过加注表示情态的限定词来表现音声的形状,对音声哀乐、高低、大小、快慢、悠扬、低徊、连续、断奏等等情状极尽描摹,实现了语言文字转述的“情感形式的音调摹写”[6]。如:
白鹤噭以哀号兮,孤雌跱于枯杨。[2]卷十六,295【噭:哀鸣声】(司马相如《长门赋》)
由衍识道,噍噍讙譟。[2]卷十八,326【噍噍:鸟鸣细碎声;讙譟:群呼喧乱声】(马融《长笛赋》)
驞駍駖礚,汹汹旭旭,天动地岋。[2]卷八,169【驞駍駖礚:声响众盛;汹汹旭旭:鼓动之声喧嚣猛烈】(扬雄《羽猎赋》)
眺朱颜,离绛唇,眇眇之态,吡噉出焉。[3]162【吡噉:歌声抑扬】(扬雄《蜀都赋》)
激呦喝啾,户音六成。[3]162【激呦:乐音激切;喝啾:乐音幽咽】(扬雄《蜀都赋》)
榜人歌,声流喝。[2]卷七,154【流喝:声音嘶哑】(司
马相如《子虚赋》)
哮呷呟喚,躋躓连绝。[2]卷十七,320【哮呷呟喚:大声;躋躓连绝:声音或升或降,或连或绝】(王褒《洞箫赋》)
这些语词前无所本,多为赋家自创,艰涩生僻,拙重繁复,甚至违背了《文心雕龙·练字》所提出的“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5]1463用字原则,体现赋体用字脱离日常、陌生又整齐的复杂性。但无可否认,赋文出于书面修辞的需要铸造新语,这的确极大地丰富了汉字的内容含量,增加了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彰显出书面语言与生活口语的极大区别,显示了文学逐渐文人化的轨迹。
(二)化虚为实
音声缅邈,旋生即灭,其信息带有含混或“复义”性,描述者根据听觉记忆的体验和审美经验来获得清晰的具象形式因素,将无形转换为有形,通过语言文字转释,将听觉表象转换为视觉表象,以引发人们对听觉场域的实在感,进而唤起他人(指读者)间接的听感体验。朱光潜认为赋“较近于图画”“有几分是‘空间艺术’”[7]。《文心雕龙斟诠》说:“论其描写景物,图模形貌,文采郁茂,有似雕刻绘画之美。”[5]310赋体“写物图貌,蔚似雕画”[5]309的创作特征,以语象将虚体实像化,使听感形象呈现画面感,在赋文中,尤以音乐赋的记载最为丰富,也最为精妙。根据不同的表现方法,大致从“以物态类声形”“以此声释彼声”“设具象以衬托”几种情况进行阐述。
1.以物态类声形
音声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因此赋在呈现音声形貌时也并单不是静态的语言描述,而更多关注于音声的流动势态。一是利用容易感知的动作、行为、色象来状声写貌,再是用譬喻的修辞手法将音声形象化,把音声连续变化的状态以可感可观的形式呈现出来。兹举数例如下:
趣从容其勿述兮,骛合遝以诡谲。或浑沌而潺湲兮,猎若枚折。或漫衍而骆驿兮,沛焉竞溢。惏慄密率,掩以绝灭,霵晔踕,跳然复出。[2]卷十七,318(王褒《洞箫赋》)
时奏狡弄,则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愺恅澜漫,亡耦失畴,薄索合沓,罔象相求。[2]卷十七,319(王褒《洞箫赋》)
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峩峩。[2]卷十八,335(嵇康《琴赋》)
远而听之,若鸾凤和鸣戏云中。迫而察之,若众葩敷荣曜春风。既丰赡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终。嗟姣妙以弘丽,何变态之无穷。[2]卷十八,337(嵇康《琴赋》)
乃相与集乎其庭,详观夫曲胤之繁会丛杂,何其富也。纷葩烂漫,诚可喜也。波散广衍,实可异也。牚距劫,又足怪也。啾咋嘈啐,似华羽兮,绞灼激以转切。[2]卷十八,328(马融《长笛赋》)
尔乃听声类形,状似流水,又象飞鸿。氾滥溥漠,浩浩洋洋。长矕远引,旋复廻皇。[2]卷十八,328(马融《长笛赋》)
2.以此声释彼声
在听觉感知中,有的声音人们并不熟悉,缺乏已有的听感体验,因此需要通过以较为熟悉的声音来进行比恰。如:
纤条悲鸣,声似竽籁。[2]卷十九,347(宋玉《高唐赋》)
声噌吰而似钟音。[2]卷十六,294(司马相如《长门赋》
礧石相击,硠硠礚礚,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2]卷七,154-155(司马相如《子虚赋》)
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渭。其仁声则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2]卷十七,318(王褒《洞箫赋》)
上下砰礚,声若雷霆。[2]卷八,171(扬雄《羽猎赋》)
音声从听感上来讲,带有一定的模仿和指示性,“声音话语是以感觉塑造为目标,围绕某种‘造型’而建立的隐喻修饰组织”[8],因此“借助这种思维方式,人们可以通过已知的事物来认识和理解未知的事物,或者重新体验、界定已知的事物”[9]。虽然同是虚体的音声,但相比而言,为大众熟悉的声音已通过接受外化成为广泛可被感知的实体,从心理因素考察,人们通常会依据现实的客观对应物来把握抽象的事物,并且调动知觉系统中已知的部分来理解未知的部分,音声的抽象化能被感知和理解也基于这种心理机制。
3.设具象以衬托
赋描写音声有时并非直接求取音象,而是将音声所引起的听者(包括人与物)的接受反应以虚饰夸张的语言表现出来,突出“感人动物”的音效。枚乘《七发》:“歌曰:‘麦秀蔪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槁槐,依绝区兮临廻溪。’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蝼蚁闻之,柱喙而不能前。”[2]卷三四,636此虽然描述的不是音之本身,却以音声的衍生效果作为侧面衬托,以虚构之言铺陈敷衍,反复描绘推阐,以达到娱目动人的艺术效果,同时显现赋综缉辞采、繁类成艳的鲜明特征。试举数则为例:
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倡,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2]卷八,163(司马相如《上林赋》)
于是繁弦既抑,雅韵乃扬。仲尼思归,《鹿鸣》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飞,别鹤东翔。饮马长城,楚曲明光。楚姬遗叹,鸡鸣高桑。走兽率舞,飞鸟下翔。感激兹歌,一低一昂。[3]581(蔡邕《弹琴赋》)
是以尊卑都鄙,贤愚勇惧,鱼鳖禽兽闻之者,莫不张耳鹿骇,熊经鸟伸。鸱视狼顾,拊譟踊跃。……鱏鱼喁于水裔,仰驷马而舞玄鹤。于斯时也,绵驹吞声,伯牙毁弦。瓠巴聑柱,磬襄弛悬。留眎瞠眙,累称屡赞。失容坠席,搏拊雷抃。僬眇睢维,涕洟流漫。[2]卷十八,330-331(马融《长笛赋》)
于时也,金石寝声,匏竹屏气,王豹辍讴,狄牙丧味。天吴踊跃于重渊,王乔披云而下坠。舞鸑鷟于庭阶,游女飘焉而来萃。感天地以致和,况蚑行之众类。[2]卷十八,339(嵇康《琴赋》)
以上,赋文所用“化虚为实”之法,皆以语言连接可听与可观,形成“声—言—画”的文学视觉形象,循声得貌,创造了高妙的音声绘摹艺术,诉诸语言文字意义表达的具体指向,以直观的音声形象唤起相应的听觉感知,标志着音声摹写艺术的发展与进步,可以说,中国古代其他文体对于音声的描绘形容多得益于赋在语言技法上的先导经验。
二、赋体音声描写的审美特征
(一)“尚乐”的艺术化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以乐论为重要批评内容,旨在强调“乐”具有政教风化、抒情宣志的功能。《尚书·舜典》载:“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10]《礼记·乐记》亦云:“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11]卷三十八,1103尊礼崇乐也融织于赋家的创作,不过并非如“史佚之言”“诸子义理”载录阐述乐音的教戒作用,而是以文学形态将音乐政教观念艺术化,以艺扬德。试观王褒《洞箫赋》一段:
此乃与“乐”可“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1]卷三十七,1081训诫之辞的精神无异,然而赋文利用铺排虚构的艺术手法,呈示音乐“去恶反仁”,可“入道德”的规谏,具有语言艺术与德化契合的内涵。
因乐音蕴藏社会心声,故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借以修正时弊,移风易俗,教化人心。“声音之道与政通”表明音乐与政治密切相连,透过音乐可达“崇礼治国”的目的。先秦儒家尤其重视乐教,孔子提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2],发展了以“乐”为中心的教育。荀子《乐论》云“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13]380,也强调音乐可治心,可化人。赋文中也不乏因器乐明道以寄“美化风俗”之意,如:
况感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哉![2]卷十七,319(王褒《洞箫赋》)
各得其齐,人盈所欲。皆反中和,以美风俗。屈平适乐国,介推还受禄。澹台载尸归,皋鱼节其哭。长万辍逆谋,渠弥不复恶。蒯聩能退敌,不占成节鄂。王公保其位,隐处安林薄。宦夫乐其业,士子世其宅。[2]卷十八,330-331(马融《长笛赋》)
乐音通于心识,故具抒情宣志的功能。荀子《乐论》谓“君子以钟鼓道志,琴瑟乐心”[13]381,嵇康在《琴赋》中也说自己少好乐音的缘由:“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 ”[2]卷十八,332傅毅《琴赋》也认为音乐具有泄导郁积,抒发苦闷的功用:“尽声变之奥妙,抒心志之郁滞。”[3]287
赋体文学对音乐的书写呈示了倡德音、和音、悲音的艺术审美标准。如马融《长笛赋》“心乐五声之和,耳比八音之调”[2]卷十八,327,认为乐音之和要在协调,嵇康《琴赋》认为通过音乐之和最终要达到“总中和以统物,咸日用而不失”“感天地以致和”[2]卷十八,339的状态,王褒《洞箫赋》曰“赖蒙圣化,从容中道,乐不淫兮。条畅洞达,中节操兮”[2]卷十七,320,又曰“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2]卷十七,319,也认为“中和”之乐最符合圣道德化,是政治德音的音乐演绎。再有,认为悲音有动移情感、化感人心的功效,如枚乘《七发》中吴客给太子治病的药方,其中“天下之至悲”之乐为第一药剂,蔡邕《弹琴赋》曰:“一弹三欷,凄有余哀。有清灵之妙。苟斯乐之可贵,宣箫琴之足听。于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乱节而忘形。哀人塞耳以惆怅,辕马蹀足以悲鸣。”[3]581嵇康《琴赋》也说:“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2]卷十八,332-333钱钟书就认为悲音为善,“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14]。
赋文“在技艺的描写中始终存在以德化为美的审美观念”[15],但它区别于训诫式的道德律令和自我人格修养的箴言语录,而是以“文”的面貌来推广礼乐精神。譬如马融《琴赋》认为琴最具德音,“晋师旷三奏,而神物下降,玄鹤二八,轩舞于庭,何琴德知深哉”[3]508,完全是文学艺术所呈现的“尚乐”观念。《文心雕龙·时序》云:“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5]1668说明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汉赋,是和政治学术上的儒学独尊,以归复建构礼乐制度相统一的,如马融《长笛赋》“故聆曲引者,观法于节奏,察度于句投,以知礼制之不可逾越焉”[2]卷十八,329,亦可以看出汉赋的创作具有配合汉代礼乐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礼乐精神内核。
(二)类比的形象思维
音声与语言分属不同的符号体系,具有非同类性的艺术特性,不可能完全对称和转译。音声作为特殊的艺术符号,本身的隐喻性和丰富性也不可能被完全充分地传达和表现,由于主体听感的差异与文字表达的局限,又必定存在其可感知却又无法形容描述、“不可言传”的隐喻成分。比如音乐,黑格尔就认为“在于反映出内在的自我,按照它的最深刻的主体性和观念性的灵魂进行自运动的性质和方式”[16]。亦有研究者认为,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充分地描述音声传达的直觉经验,无法复制和还原音声的现场感受,斯蒂芬·戴维斯说:“我们常常感受带音乐说出了比我们的详细描述还要多的东西。音乐并没有为我们留下语词,我们总觉得文字的描述不充分,这些描述只是我们所有寻找的东西的近似物。”[17]
但尽管如此,辞赋家仍凭借驱遣辞藻和锻字造语的功力,将晦义的音声与显义的语言作了最大化的对接,其思维机制主要是基于物类和事类的相似性。文艺修辞“以类比的方式建立形象的相似性关联,藉以引发读者的想象,获得生动形象的表达效果”[18],艺术主要用形象思维,不以抽象的概念为出发点,即使像音声这种接近抽象化的艺术形式,当它作用于感官,其“接受”的反映过程也必然是通过形象思维进行意识活动,否则无实像的音声就不可能被感知和记录。赋体擅长描绘形容,拟声图貌,“在不宜展示的情感与声音方面,赋家却尝以形象化与对象化的方式加以呈现”[19]。赋描述听感形象主要的方式,一为“类形”,一为取象譬喻。“类形”主要通过文字铺排组合形成视觉冲击,以类似相像的物事呈示难以捉摸的音声,带来感觉的直观。如:
或杂遝以聚敛兮,或拔摋以奋弃,悲怆怳以恻惐兮,时恬淡以绥肆。被淋灑其靡靡兮,时横溃以阳遂。[2]卷十七,318(王褒《洞箫赋》)
此在铺排形容箫声,或众多相聚,或奋迅分散,有时连续不断,有时又清晰悠扬,细腻刻画技艺的高妙与多层次的听觉感受,将听感转换为视感与触感,以语像呈现听觉可感知的形象,从而获得审美气象的集合。
“取象譬喻”属于听觉表象的相似联想,而相似联想乃是比喻、象征等表现手法的心理基础。知类乃可作比,“赋欲纵横自在,系乎知类”[20],只有对物性博通、知类融汇、洗练辞藻方可描述恰至,《文心雕龙·诠赋》谓“拟诸形容,则言务织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5]288,以细密的言词描摹事物的形貌,根据物性而作贴切的比附。赋描述音声多“类于”“状若”“或似”“又似”之辞,如描述乐音飘飏,“状若捷武,超腾逾曳,迅漂巧兮”[2]卷十七,320(王褒《洞箫赋》),形容声音众多,以色象声,“啾咋嘈啐,似华羽兮”[2]卷十八,328(马融《长笛赋》),再如以行为状声,“震郁怫以凭怒兮,耾砀骇以奋肆。气喷勃以布覆兮,乍跱蹠以狼戾”[2]卷十八,328(马融《长笛赋》),形容声音就像满怀郁怒的人在大发雷霆一样,宏亮高昂而奔放。通过拟声响或拟声态的方式,使音声形象化,以取得可“观”的审美效果。
(三)注重音声的情感体验
《礼记·乐记》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11]卷三十七,1077音声的本初,缘附于心理感知而引发的深层想象与情感知觉,作者在描绘音声时,显然是融入了自身的情感体验,充满情感意味的音声实质上本于描述者情感体验的投射,又可唤起欣赏者的情感反应。“音乐形象透过作者的感知,经由联想与想象,以文字表达出来,至于读者,则借着文字,透过作者的想象与联想,逆向还原到作者所经历、感知的音乐形象。”[21]读者通过经作者想象的音声来间接地感知声情,基于相似的情感体验,音声描写的文字搭建了一座桥梁,将读者带入作者的感情世界。赋体文学善于描摹,可将哀乐、惆怅、悲鸣等复杂的情感变为有形的视觉联想,激活读者脑海中贮存的声音记忆,使作者与读者在情感体验上援相感应,熔铸进双方主观的情志,超越音声表象的限制,将音声传达的情感体验上升为一种艺术化的诗性表达。如下二则:
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顺叙卑迖,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悲怆怳以恻惐兮,时恬淡以绥肆。……哀悁悁之可怀兮,良醰醰而有味。[2]卷十七,318-319(王褒《洞箫赋》)
故论记其义,协比其象。徬徨纵肆,旷瀁敞罔,老庄之概也。温直扰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清厉,随光之介也。牢刺拂戾,诸贲之气也。节解句断,管商之制也。条决缤纷,申韩之察也。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剺栎铫,皙龙之惠也。[2]卷十八,329-330(马融《长笛赋》
第一则描写箫声与歌声的和音,以“慈父畜子”的联想传达乐音和谐,描写妙声恬静深远,以“孝子事父”的联想来表现乐音顺从无违、流畅无阻,形象地展现声音的特点。第二则以诸子之义理来协比笛音所内涵的哲理和外在状态,以老庄的风度比拟笛声放纵敞闲,以孔孟之道比拟笛音温和正直、柔顺刚毅,以下随、务光的节操比拟笛音激切明朗、高昂刚烈等等。所谓“科条譬类,诚应义理”“论记其义,协比其象”即为赋家贴合自身的感知经验纵其神思,使音声形象化。“真正创造想象的推动力是艺术家的情感体验”[22],因此,唯有“深层知觉”,即心理体验、情感体验才有可能进一步达成对模糊和不确定性的音声的理解。“音乐情感的深层心理体验与欣赏者自身的生活经验有关,欣赏者在想象与联想的技法下,以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艺术修养丰富、补充、指导、发现音乐中的美,在声音与视觉、动觉等感官的‘通感’引起的联想下,扩大了欣赏者的知觉范围,在隐蔽曲折的类比中间接地借用已知的感受获得声音的形象”[23]。在赋的创作实践中,依靠听感想象和联想以实现不同感觉类型之间的关联意义,使读者更容易感知声情,以实形绘制虚像,以熟悉诠释陌生,皆是以情感体验引发的艺术想象和联想为基础。
三、结语
语言文字利用自身独特的解释性对音声进行转译。通过语言文字的精绘营构,达成以语像呈现声像的审美意识,使抽象的音声转化为容易被感知的物态化与意态化,音声的“形貌”通过语言符号被表现出来。赋家竭力捕捉音声的各种特征,并试图用极为精准的文字组合来传达所听所感,尽管傅修延在《听觉叙事研究》中认为“听声类形”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毕竟用语言表达声音的手段有限[24],但赋体音声描写的创作实践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文学早期语言发展的观测视角,即从“说与听”的言语向“观和看”的书面文字的转移,使文学的视觉形象被突出显示。吉川幸次郎在《论司马相如》一文中说汉赋的时代是“向有文学的时代,或艺术性语言存在的时代的转变”[25],其依据主要是因为汉赋创作中对文字本身的关注及其体现出的美学意识。赋体文学凭借对汉语文字的研思与开拓,创造了宏丽瑰玮的辞文形制,极大开掘了汉字形音的审美潜能,展示了高超的修辞技艺,本质上反映了文学形态由“言”到“文”的重大转变。赋家把书面语言修辞看作审美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传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赋体“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的表达特点与创作技艺,以擅长描绘显示其修辞艺术,自赋始,文学方以词章修饰、虚构想象为独立的审美特征,显示出以赋家为代表的文人阶层对语言文字审美价值的认识与实践,标明作为语言文字艺术化表达的审美形态进入新的阶段。
——评陈辉《浙东锣鼓:礼俗仪式的音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