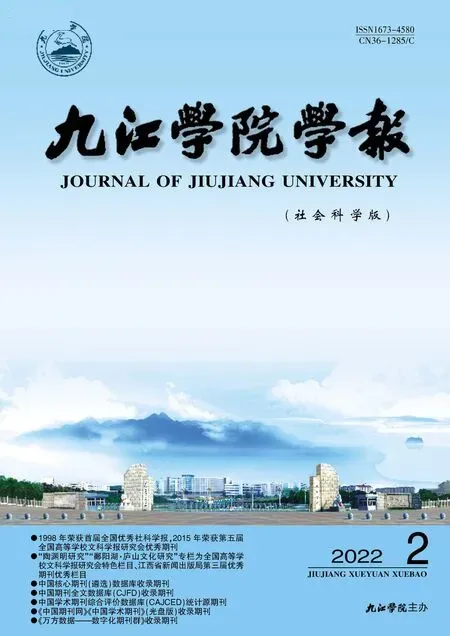黄庭坚骚体辞赋的创作特点
李广帅
(青海师范大学新闻学院 青海西宁 810000)
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山宗祖,黄庭坚向以诗歌创作为人所称道。其诗歌学古创新而自成一体,是迥异于“唐音”的“宋调”代表,鲜明体现了宋代诗歌的独创性特色。尽管相对于诗歌来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黄庭坚辞赋均无法与之抗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辞赋尤其是骚体辞赋被深刻打上了诗人黄庭坚气质的烙印,相当一部分作品有较高的辨识度。据曾枣庄、吴洪泽主编的《宋代辞赋全编》统计,黄庭坚现存辞赋30篇,其中骚体辞赋17篇,占一半以上,从中可窥见黄庭坚对骚体的重视程度。故本文拟以黄庭坚骚体辞赋为中心,探析其创作的特点。
一、继承楚辞发愤抒情的特点,以骚体辞赋述写哀情
诞生于巫风浓郁的土壤,楚辞因和原始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具极强的情感激发力和诡谲神奇的想象力。祭祀过程中人神交接的困难,现实社会中屈原坎坷不遇终至湛身的悲剧,又为楚辞涂抹上了一层浓厚的伤感色彩[1]。以上种种造就了楚辞辞藻富丽,感情激切,多抒写哀情的传统,即《文心雕龙》所谓的朗丽哀志、绮靡伤情。
屈原、宋玉是楚辞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创作对后世骚体辞赋产生了重要影响。屈原“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经司马迁阐发,“发愤抒情”和“温柔敦厚”成为文学史上两条相济相成的文学创作原则。而宋玉《九辩》开启了千古文人的悲秋嗟贫的主题,同样是发愤抒情原则的延续。黄庭坚的骚体辞赋中,悼亡赋可以视为祭祀亡灵之作,而《悲秋》《秋思》视为悲秋主题在宋代的回响。
黄庭坚骚体辞赋中,最有艺术价值和感人至深的就是《悼往》《毁碧》《张翔父哀词》这三篇悼亡赋。《张翔父哀词》是悼念朋友,《悼往》是悼念亡妻兰溪,《毁碧》是为亡妹而作,因后两者所悼都是至亲,读来更觉凄楚悲哀。楚辞本身就有《招魂》《大招》等深情呼唤“魂兮归来”的哀吟之歌,适合抒发悲恸之情,加上山谷是重情之人,和妻子伉俪情深,和妹妹骨肉深情,对朋友满腔赤诚,因此这三篇骚体赋虽无意雕琢,纯任性情流动,却不经意之间以真挚深沉的感情动人心魄。
据《山谷年谱》,兰溪去世在秋季。《悼往》起首即渲染了萧索悲凉的秋景:“西风悲兮败叶索索,照陈根兮秋日将落。彷佛兮梦与神遇,顾瞻九泉兮岂其可作。俄有悲乎之羽虫兮,自伤时去物改,拥旧柯而孤吟。四郊莽苍声断裂兮,久而不胜其叹音。”[2]
接着山谷以沉痛的心情倾诉了亡妻去世后自己对过往细节的追忆:“平生之梗概兮,欲萧萧而去眼,将绝之言语兮,忽历历而经心。谓逝者有知兮,何喜而弃此去也。谓逝无知兮,谁职为此梦也。凭须臾之不再得兮,哀此言之不予听。回廊窈窕月皓白兮,无复曩时之履声。揽平生之余制兮,芗泽其犹未沫。虽飘飘其日败兮,吾不忍改其此佩。愁薨薨其中予兮,如醳酒之不化。欻别离之几时兮,谁与此夏日冬夜。”[3]妻子兰溪弥留之际的语言尤在耳际,而今只能和她在梦中相见。月下回廊依旧,却再也听不到兰溪的脚步声。所穿的衣服是妻子缝制的,如今只遗留她的香泽,纵然败破,也不舍得换掉。自此生离死别,只能独自在漫长的时间里忍受愁苦煎熬。对细节的展衍铺叙折射出作者试图捕捉到过往点点滴滴的努力,这努力的背后正是作者的无限深情。
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伤感惋惜之情层层堆积,而亡人一去不返,尽管作者试图以庄子击缶的达观自我排解,然而作者也承认这只是虚妄,最终哀悼之情难以抑制,喷涌而出,作者结尾写道:“饮泣为昏瞳之媒,幽忧为白发之母。忧来泣下不可安排兮,如孟津之捧土。彼寒暑之寖化兮,天地尚不能以朝莫。目茕茕而不寐兮,夜亹亹而过中。虽来者犹不可待兮,恐不及当时之从容。”[4]哀婉缠绵,一往情深,深契楚辞内质。所以一向对文学持论甚为严苛的朱熹也认为该辞赋符合赋体传统写法,有比兴意。《古赋辩体》云:“山谷长于诗,而尤以楚辞自喜。然不若诗者,以其大有意于奇也。晦翁云:‘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如《离骚》只是平白说去,自是好。后来黄鲁直恁地著气力做,只是不好。《悼往赋》,赋也,起二句有比义;中间发乎情,有风义。山谷诸赋中,此篇犹有意味。”[5]
《毁碧》是黄庭坚为悼念亡妹而作,以“毁碧兮陨珠”喻妹之殇,可见亡妹在其心中的分量。据此赋的序言可知,山谷之妹“眉目如画,玉雪可念,其为女工,皆妙绝人”[6]。然而因不愿嫁洪民师而得罪姑婆,死后不能归葬洪家坟茔,竟落得“焚而投诸江”的悲惨下场,十四年后黄母得知,泣不成声,恐女儿魂归无所,黄庭坚弟兄为宽慰母心,为亡妹筑亭刻石,写下这篇骚体以召亡妹之魂。
赋中以“归来兮逍遥,采云英兮御饿”“归来兮逍遥,西山浪波何时平”“归来兮逍遥,增胶兮不聊此暇”三致意焉,呼唤亡灵归来。“山涔涔兮猿鹤同舍,瀑垂天兮雷霆在下。云月为昼兮风雨为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绘画。”亭子周围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既有楚风遗泽,又带有山谷个人的瘦硬风神。朱熹在《楚辞后语》评价该篇:“《毁碧》者,豫章黄太史庭坚之作也。庭坚以能诗致大名,而尤以楚辞自喜。然以其有意于奇也太甚,故论者以为不诗若也。独此篇为其女弟而作,盖归而失爱于其姑,死而尤不免于水火,故其词极悲哀,而不暇于为作,乃为贤于他语云。”[7]
《张翔父哀词》是黄庭坚为诗友张翔父所作的墓志,在词中,山谷将张翔父比喻成不朽的白壁黄金,他坚守“君子固穷”的原则,洁身自好,“我观翔父兮白壁黄金,艺兰九畹兮寂寞中林”,然而现实社会却颠倒非白,贤良不遇而小人得志的情形历千年不变,“骥思天衢兮款段参驾,西子扫除兮嫫母荐衾”,与屈原贤而遭谤一样,翔父虽“志则日月”,然而却免不了俯仰庸人之间,“走官穷海兮齑恨下泉。”结合辞赋写作背景是党政激烈的元丰年间,可知辞赋既是悼念亡友,又是山谷用以讽喻现实。辞赋最后,黄庭坚传达了对友谊的珍重以及对翔父后嗣有人的劝慰。
《悲秋》《秋思》延续了宋玉悲秋的主题,只是和宋玉自伤身世不同,黄庭坚《悲秋》用以伤婉“天然之形缺”的“知命弟”。且赋中黄庭坚几乎没有涉及到对秋景的任何描写,只是把秋作为文章的引子,为赋中人物的登场营造一个悲凉的背景:“有美一人兮,临清秋而太息。”赋中大量笔墨集中于对知命弟的劝慰同情。
《秋思》起首渲染秋景,更接近宋玉的写法。与宋玉辞赋中浓郁的伤感寂寥有所不同,黄庭坚描绘的秋景是为了展示舅氏李公择的德者人格和仁者境界,所以虽有些许寂寞清苦,但更多是恬淡自然、舒朗高洁的风致:“柴门扃兮,牛羊下来其已久。四壁立兮,蛩螀太息不可听。夜冉冉兮,斗魁委柄若授人。天寥寥兮,河汉风浪西南倾。山川悠远兮,谁独不共此明月。维德人不见兮,采薇蕨于江之南。风露寒兮,薇蕨既老而苦涩。江道险难兮,不知先生之何食。”[8]柴门关闭,牛羊来归。家徒四壁,蛩螀太息。夜幕列星,天空寂寥。河汉转移,山川悠远。但见明月,不睹斯人。江南采薇,风露凄寒。读来好似一副恬淡悠然的秋景图。对舅氏的思念经理性的节制,在辽阔秋景的衬托下显得平淡中和。
赋作中间部分,山谷以文学性的笔墨回忆了舅氏对自己在进德修业途中披荆斩棘、导夫先路的作用:“天地施我生兮,先生厚我德。水波无津兮,即拯我舟杭。路微径绝兮,又翦我荆棘。秉道要而置对兮,一与而九夺。曾不更刀兮,破肯綮於胸中。湛湛兮如长江之吐月,霏霏兮若旋盘之落屑。会鉏铻于一堂兮,曾不侮予以色辞。”[9]经过回忆的铺垫,作者的内心感情得到激荡,不再克制冷静,结尾以浓烈深挚的伤感抒情煞笔,并以宋玉自况:“已矣乎,芳兰无泽兮岁遒,众芳歇兮曷予佩之求。绝万里兮吾以子牛,横大川兮吾以子舟。窃悲吾子之多暇日兮,愁嗟黄落如郢客之见秋。”[10]
从以上几篇辞赋来看,黄庭坚继承了楚辞抒写哀情、铺陈哀景的传统,尤其悼亡之作缠绵悱恻,深得楚骚神韵。屈原在后世备受推崇,除九死不悔的忠贞外,他的遭遇亦常引起封建时代的士大夫的共鸣,一部中国文学史,充满了多少怀抱利器而郁郁不得志的声音!尤其党争激烈残酷的宋代,文人士大夫动辄得咎。面对险恶的环境,通过践履佛老圣贤之道、涵养内在修为对抗外部挫折,或通过发愤创作来泄导内心的抑郁不平,成为此时期士大夫的普遍选择。这在黄庭坚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诗文既给人得道君子温柔敦厚的感受,又给人傲岸不屈的桀骜印象。黄庭坚骚体辞赋既不懈求道,又继承了楚辞发愤抒情的传统,以宣泄哀情为主调。不过黄庭坚毕竟是生活在宋学发轫生长期,追求理致是文学创作的普遍风气,因此相对于楚骚的哀转欲绝、绮靡伤情来说,黄庭坚辞赋因理智的克制,道德的涵养,情感力度有所削弱,在缠绵悱恻之外,更显示出含蓄深沉,怨而不怒,咀嚼有味的风格特征。
二、发展辞赋说理议论的风尚,在骚体辞赋中追求理趣
辞赋本有议论传统,汉大赋劝百讽一,曲终奏雅,已包孕议论的萌蘖。逮至宋代,士大夫参政热情被极大激发,说理议论成为时代风尚,并浸渍到各类文体创作之中。宋代诗赋取士注重经义,造就了一批博古通今的思辨型学者,他们的律赋引经据典,大发议论,如同政论文一般无二。不同于律赋成熟定型于宋代,服务政治,以议论为宗,骚体辞赋受议论化倾向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得益于骚体辞赋的创作传统和思维定势。骚体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以抒情为主,战国末期楚辞横空出世,即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引来历代无数文人的歆羡模仿。拟骚作品在骚体辞赋中比比皆是,后世骚体辞赋创作也必须以抒情为宗才能称得上本色当行。这也是力主文艺创作求新求变,不随人后的黄庭坚也不得不以骚体抒写哀情的根本原因。只不过在议论为宗的时代大背景下,黄庭坚对儒家道德的身体力行和对佛老思想的饱参深悟,使其骚体辞赋中也充满了理趣。如《录梦篇》结尾乱词,满是议论,简直就是老庄格言语录:“乱曰:刍狗万物兮,天地不仁。体止而用无穷兮,播生者于迷津。有形而致用者之谓器,无形而用道者之谓神。背昭昭而起见兮,聚墨墨而生身。犯有形而遗大观兮,动细习于游尘。彼至人而神凝兮,同予梦而先觉。顾天下孰不学兮,乃会归于无学。予心之不能忘兮,将波流风靡而奈何,唯镇之以无名之朴。”[11]
这一类的格言语录般的说理议论枯燥乏味,没有太大的文艺价值。这种情况在黄庭坚的骚体赋仅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时候,黄庭坚是将抱朴守拙,见微知著,无用之用,全身远害的老庄哲学用文学意象表达出来,这类辞赋大多作于北宋党争白热化的熙宁、元丰、元祐时期,从中可也窥见该时期黄庭坚谨小慎微、抱道而居的心路历程。
创作于熙宁元年的《木之彬彬》,以东汉末年名士孔融、祢衡、杨修皆先为曹操所礼后为其所杀的历史事件为引子,并以《韩非子》记载的隰斯弥伐木的寓言故事,阐发见微知著、全身远害的老庄处世哲学。此篇的序文提到“田子将成大事,恶人知其微”,联系该年王安石造朝入对,意欲掀动神宗变法的历史,不难看出其中的讽喻。正文中对因有用而遭斩伐的草木描写实则是庄子关于大樗寓言的重新抒写:“木之彬彬,非取异于人。可宫室则斩则伐,可笾豆则捋则撷。草之茸茸,非求显于世。中刍牧则刈则狂钅且,中医和则剥则枯。非以其材故耶。是非之歧,利害薰蒸。”[12]文末黄庭坚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易其言则害智,用其智则害明”,所以“为君子则奈何,独见晓于冥冥。”也就是要见微知著,守拙藏智。同样作于本年的《渡江》,以比兴手法形象展示了黄庭坚在此时期进退失据的内心感受:“行渡江兮吾无舟,……行渡江兮吾无楫,……嗟行路之难兮。”元祐二年在《予欲金玉汝赠黄从善》中,黄庭坚写到“雁以不鸣烹,木以才而斲,天下皆羿兮,矢来无乡,惟应以无名之朴”,这更是面对四面环敌的险恶处境,无论有用无用都会罹患,倡导以拙保身。在《邹操》一文中同样因流露出“求其用以丧其生”的担忧。
北宋熙丰年间政治环境的凶险,让士人常有如履薄冰的心态。为了平和挣扎的内心,禅宗及老庄思想在这一时期成为重要的心灵安慰剂,不难看出黄庭坚辞赋中老庄思想的广泛存在。作为士大夫的黄庭坚,除以老庄任性逍遥、保身远祸思想来抵御外在的凶险之外,还注重修习内在的君子人格,以儒家的信念和守道不移的决心来求得心灵的宁明和维护人格的高洁。如《濂溪诗》序中称颂周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这实际上也是黄庭坚本人的志趣所在,他通过表彰周敦颐阐发了自己的人格追求。还比如《听履霜操》序云:“士有有意于问学,不得于亲,能不怨者,预听斯琴也。予故为危苦之词,撼其关键,冀其动心忍性,遇变而不悔。”可知黄庭坚创作这篇骚体辞赋的用意在于开导鞭策有志问学之士培养坚韧性情,不为外界所动。
在《龙眠操三章赠李元中》一篇中,黄庭坚同样通过自己行道过程中克服遇到艰难险阻执着于儒道来劝勉友朋后进,勉励李元中求“道”不止。第一章开篇云:“吾其行乎,道渺渺兮骖弱,石岩岩兮川横。”道渺川横,前路艰难,然而作者却抱定“吾耕石田兮为芝,乃三岁兮报我饥”的信念。黄庭坚经常用“耕石田”来比喻不顾艰难险阻毅然进德修业的执着精神。第二章借鉴《楚辞》周流求女的情节,表达对进德修业的向往,以及不被世俗理解并遭众人馋毁的现实。第三章以贫贱不动于心展示得道之后的安乐境界,并用“牧牛兮于鼻,牧羊兮不歧”一句说明修道只有抓住要领不至于误入迷途,并以李元中向自己问途喻问道,并表达了在“道”上与之同归的愿望。这三章骚体赋更多带有黄庭坚诗歌的创作特点,即善于点化典故,浑然无迹,并以具体意象阐发抽象哲理。
黄庭坚对感情的克制是有意追求,对“温柔敦厚”的诗美传统的崇尚,使山谷在骚体意象语言的营造中引入《诗经》辞藻的构写方法,如“木之彬彬”之于“桃之夭夭”,“南山有葛”之于“南山有桑”,“我非伤悲”之于“我心伤悲”等。山谷甚至将《诗经》里的语言嫁接到自己的骚辞中,如《悲秋》开头的“有美一人兮”,《秋思》开篇的“柴门扃兮,牛羊下来其已久”,还有文中提到的“采薇”,都让人不免联想到《诗经》。《诗经》高雅平和的韵味冲淡了骚辞的慷慨激烈的感情,而对儒家道德的涵咏以及对老庄思想的吸收则从理性方面进一步限制了感情的过分张扬。
三、融入自身诗歌特质,扩大骚体辞赋表现技巧和功能
黄庭坚诗歌以善于用典著称。他诗中的典故一是来源广泛。清人翁方纲认为:“其用事深密,杂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说,隽永鸿宝之书,牢笼渔猎,取诸左右。”[13]黄庭坚现存的骚体辞赋也大量用典,仅这30篇骚体辞赋典故就涉及到了《易经》《诗经》《楚辞》《老子》《庄子》《孟子》《韩非子》《三国志》《史记》《山海经》《字林》及禅宗典籍等各类文献。二是追求新奇。黄庭坚诗歌不屑使用陈俗语言,步武前人,而是点铁成金,力求争新出奇,典故运用往往出人意表而又和表达内容密合无间。对典故的运用出神入化、得心应手的特点在这些骚体辞赋中也有所体现。比如《秋思》中“霏霏兮,若旋盘之落屑”一句描写雪花飘落,暗用了《诗经》“雨雪霏霏”的典故,但是黄庭坚并没有直接点破,而是以“旋盘”的姿态,“落屑”的形态让读者去联想雪花。这种言其用而不言其名的用典方法是以陌生化手法使词语生新,在黄庭坚诗歌中经常出现。相对于诗歌来说,辞赋毕竟是不同的文体,有自己的创作传统,黄庭坚在骚体辞赋中用典虽多,但生新出奇的特点并不突出。然而过多的虽并不过于生僻的典故究竟阻碍了感情畅快淋漓的抒发,李耆卿在《文章精义》评价道:“学楚辞者,多未若黄鲁直,最得其妙。鲁直诸赋及他文,愈小愈工,但作长篇,苦于气短,又且要句句用事,此其所以不能如长江大河也。”[14]李耆卿对黄庭坚骚体辞赋用典过多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
黄庭坚诗歌创作因注重句法曾一度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然而诗歌本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诗歌创作对形式一定程度的研磨锤炼无疑是必要的。在句法方面,山谷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诗学概念,即“诗中有眼”。周裕锴认为,“句中之眼相当于弦外之意。……黄庭坚把禅家‘句中有眼’之说引入诗歌批评,在诗学上有重要意义。……虽然后来不少人郢书燕说,理解为句中精彩的字眼,但仍保持了从文字形式中求韵味的精神。”“郢书燕说”的这层理解因切合黄庭坚“安排一字有神”的提法,在宋以后的诗论中被广泛接受。诗论家往往去从黄体庭坚诗歌中经过反复锤炼的关键字去抉发“句中之眼”。对诗句中关键字的反复锤炼和精心安排是黄庭坚诗歌奇峭生新的重要法宝,这样的手法也被黄庭坚引入了骚体辞赋的创作中去。《复小斋赋话》云:“古人句法有相似者。如山谷《悼往赋》云:‘饮泣为昏瞳之媒,幽忧为白发之母。’石湖《问天医赋》云:‘孤愤为丹心之灰,隐忧为青鬓之雪。’而山谷较胜。‘媒’字、‘母’字,犹诗中之有眼也。”[15]“媒”“母”的使用将哭泣和忧愁人格化,让整个句子摆落蹊径,生新出奇,耐人咀嚼。他如“我为直兮棘余趾,我为曲兮不如其已”,其中“曲”“直”的辩证对立,“棘”字的词类活用,都属于黄庭坚诗句常用到的句法技巧。
为诗歌作序在中国诗歌史上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宋代之前,无论是自作序还是代作序,一般篇幅不长。北宋时期苏轼“以文为诗”,将序言大量引入诗作并扩展序言篇幅,黄庭坚继承苏轼做法,大量使用序言并展衍序言篇幅,如其五言律诗《送莫郎致仕归湖州》,诗歌正文仅 40 字,而诗序竟然高达 262 字,诗序至此已成为理解诗歌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黄庭坚现存的17篇骚体辞赋中,有序的有8篇,分别是《木质彬彬》《濂溪诗》《王圣涂二亭歌》《秋思》《听履霜操》《邹操》《灵龟泉铭》《张翔父哀词》。以上8篇,最长的序言当属《濂溪诗》的序,这篇序简直就是一篇关于周敦颐的人物传记,此序在后来的理学家中备受推崇,序言中“光风霁月”一词也几乎成为了形容周敦颐等理学家所具有的“圣贤气象”的专用词,《濂溪诗》正文反倒不为人熟知。由上可以看出黄庭坚诗序对其骚体辞赋的影响。
从这些序的内容来看,主要用于交代辞赋创作的缘由和背景,如《木之彬彬》序最后一句说“感二三子行事,作《木之彬彬》”,《听履霜操》序说“予故为危苦之词,撼其关键,冀其动心忍心,遇变而不悔”,《邹操》结尾云“故君子见微,归在邹,作《邹操》”。这些都是明确地交代了作赋的缘由。其他几篇序文基本都是说明了赋作的背景。
从远源看,黄庭坚骚体辞赋用序是继承了汉赋创作的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写道:“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广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16]序言作为发端,首先是要引出作赋的情事根由的,黄庭坚这些骚体辞赋的序言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这一点。赋本诗之变体,是界于诗文之间的特殊文体。诗文的特色影响赋的特色,诗文的功能同样会拓展到辞赋。宋人常用诗歌来酬唱交友,交际功能得以扩大。此功能在黄庭坚的骚体辞赋中也得以实现,如《龙眠操三章赠李元中》《予欲金玉汝赠黄从善》《明月篇赠张文潜》《至乐词寄黄几复》,从题目就可看出都是赠人之作,拿这些辞赋和黄庭坚诗歌《寄黄几复》《寄黄从善》《次韵文潜》对读,可加深彼此的理解。
总之,黄庭坚的骚体辞赋,既继承楚辞发愤抒情的特点,以骚体辞赋述哀情,又发展辞赋说理议论的风尚,在骚体辞赋中追求理趣,还融入自身诗歌特质,如善于典故,注重句法,使用赋序等,扩大了骚体辞赋表现技巧和功能。以上几种特点使黄庭坚辞赋尤其是骚体辞赋呈现出含蓄蕴藉,丽则典雅的总体风貌,有音调铿锵,一唱三叹之概。在宋代黄庭坚的辞赋就被人所喜爱,除上文提到的理学大师朱熹,还如宋末元初的刘埙,他和傅幼安以诵读黄庭坚辞赋为人生乐事,曾说:“愚亦素喜山谷诸赋,诵之甚习,每与此先生会,剧谈至意气倾豁处,此先生辄曰:‘相与读山谷赋,可乎?’因振袂同声朗诵激发,觉沆瀣生齿颊间。”[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