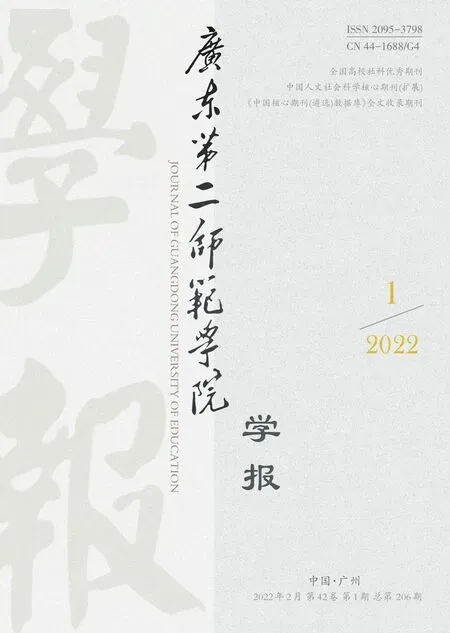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研究的演进、重点特征与展望
周仕德, 高思超, 关荆晶, 刘永帆
(1.汕头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广东 汕头 515063; 2.西华师范大学 教务处,四川 南充 637002; 3.韩山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41)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进入21 世纪,国家进一步加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发展步伐,相继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 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 年)、《教育部关于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2010 年),为基础教育课程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和指南。《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 年版)》和《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0 年修订版)》均指出基础教育课程承载着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思想,规定了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是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在立德树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这一系列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的研究蕴含着新的使命。
在反思中育新问,于成就中寻新向。 自1978 年5 月邵瑞珍在《外国教育资料》发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题名含有课程论的成果《布鲁纳的课程论》开始至今,我国课程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为我国课程论研究的系统总结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目前学界对我国课程论发展已有梳理,如靳玉乐、杨艺伟认为百年以来我国课程论的繁荣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课程论的生长立足中国实际,课程论的丰富是借鉴国际经验,课程论的充实是关注学生发展[1]。王鉴、单新涛总结百年中国课程论学科构建的立场经历了从外来到本土化的不断推进,课程论的学科边界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到依附教学论,再到独立并走向与教学论的整合,课程论领域关注的主题体现了从静态的文本课程到文本课程与体验课程并重,从课程编制为主到多元课程研究谱系共生的变迁[2]。 周仕德、刘翠青指出40 年来中国课程论研究聚焦稳定的研究队伍、重要影响的研究论著、学科发展难点与热点、课程论系列主题研究持续推进、研究视域呈现多样[3]。 侯怀银、任桂平分析了中国课程论学科建设70 年在学科基础、学科性质、学科地位、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和学科群建设上取得的相应进展[4]。 郭华则认为中国课程论40 年,从一般课程论发展分化为一个学科群;形成了一套有内在联系的、体现中国课程实践与发展特色的课程话语体系;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课程研究与发展模式;构建了应对未来挑战的多级、多类、多样化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课程论研究的开放性、自觉性日益增强;学生发展真正成为了课程研究的核心目的[5]。 总的来看,这些代表性成果主要从我国课程论的时段性或整体性、宏观性方面进行探讨,而专题性课程论关注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研究与基础教育发展一样,困难与机遇并存;既有独立发展之路的探寻,又有世界课程动态的追踪;既有注重基础教育课程研究的本土场域,又有关照世界基础教育课程的实践译介;既有国家层面的多类型基础教育课程研究基金资助,又有以师范大学为核心的基础教育课程研究机构的涌现,呈现多样的理论研究视域,产生了显著的实践影响,形成了新中国72 年来基础教育课程论研究的基本格局。 站在新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新的历史起点上,专题性回顾和总结这一时段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研究整体情况,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论迈向更加科学、理性、自信的发展和研究之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的研究演进
(一)基础教育课程论研究演进的阶段划分
学界对我国课程论研究的起始时间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张廷凯在《我国课程论研究的历史回顾:1922—1997(上)》中认为是20 世纪20 年代,靳玉乐在《现代课程论》中认为是20世纪30 年代,廖哲勋在《课程学》中认为是20 世纪70 年代,目前学界仍未能达成共识。 在发展阶段划分方面,也存在着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三阶段说,张廷凯提出课程论学科在我国的建立时期(1922—1949 年)、课程论作为教学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的时期(1949—1988年)、课程论作为教育学分支学科的重建时期(1989 年以后);周仕德、刘翠青提出独立迈步的课程论阶段(20 世纪70~80 年代)、崛起发展的课程论时期(20 世纪90 年代)、扩容蓬勃的课程论时期(21 世纪以后)。 二是四阶段说,王鉴、单新涛提出课程论学科的初创与课程研究的兴起(1919—1949 年)、课程论发展的停滞与课程研究的失语(1950—1979 年)、课程论学科的重建与课程研究的复苏(1980—1999 年)、课程论学科的壮大与课程研究的多元化发展(2000年至今);侯怀银、任桂平提出课程论学科的停滞阶段(1949—1977 年)、课程论学科的重建阶段(1978—1984 年)、课程论学科建设的本土化阶段(1985—1988 年)、中国课程论学科的建设阶段(1989 年至今)。 三是五阶段说,靳玉乐、杨艺伟提出课程论的认识探索阶段(1921—1949年)、课程论的学习借鉴阶段(1949—1980 年)、课程论的独立发展阶段(1981—2000 年)、课程论的深化发展阶段(2001—2016 年)、课程论的繁荣创新阶段(2017 至今)。 这些已有研究成果是基于整体性、宏观性的我国课程论研究来做出的阶段划分,虽未能直接明确阐释基础教育课程论阶段划分问题,但对如何从专题性、微观性的视角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研究阶段进行判断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研究来说,如何划分研究阶段还必须考虑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事件和教育改革的主要节点。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教育领域主要是借鉴苏联教育学理论,课程论依附于教学论之下的身份未能发生根本改变,加之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正常进行,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1978 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85 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8 年国家教委印发《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使得基础教育课程逐渐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人民教育出版社陈侠的《课程论》和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的《现代课程论》于1989 年出版,成为当时我国课程论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进入20 世纪90 年代,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课程研究的学术团体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于1997年3 月成立。 同年11 月,第一届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随后以1998 年教育部颁发《面向21 世纪教育振兴计划》和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为标志,全国掀起了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 200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2010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同年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开始新一轮义务教育课程改革;2014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2016 年,经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审议确立了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大举措。 2019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2020 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0 年修订版)》,标志着以核心素养为目标的新一轮国家课程改革的开启。 同时,教育部和各省市相继于2014 年、2018 年开展第一届、第二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并颁布实施相关奖励政策,极大地激发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领域内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活力,对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国家相关教育改革的政策文件及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情况,本研究尝试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研究演进划分为缓慢发展、快速发展、拓展提升三个阶段。
(二)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的研究演进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 世纪80 年代:课程论研究缓慢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课程论研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进入缓慢的发展阶段。 表现在:第一,开始撰文概要介绍国外课程方面的研究。 如美国布鲁纳的课程论基本思想,英国丹尼斯·劳顿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美国杜威的课程论思想,德国赫尔巴特学派课程论评论,梳理美国课程论研究中的课程定义,对近现代主要课程论流派尝试评介。 第二,在立足学习西方课程论的基础上关注我国课程论相关问题。 主要侧重探讨我国课程论的研究范围、指导原则,关注课程结构与人才结构关系,课程的研究对象,课程论的学科地位及与教学论的关系,本土教育家陈鹤琴的活教育课程论思想,学校课程现代化问题,课程与科技革命、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课程论在教学论中的地位问题等。 这一阶段,课程论研究附属于教学论之下发展,从直接译介到开始思考课程论的重要性问题,初步显现学科的使命感和应用意识,出版了课程相关论著,探讨课程论在教育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特别关注对国外中小学课程变革的介绍和应用。
第二阶段,20 世纪90 年代至21 世纪初:课程论研究快速发展。 20 世纪90 年代,因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我国教育改革的推动,课程论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主要表现有:第一,国外课程论有关主题的译介出现新成果。 要素主义课程论,体验课程论,人本主义课程论,斯宾塞的课程论思想,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论思想,伯恩斯坦的社会课程以及M.杨的社会课程论概况,美国现代的课程发展史探讨,英国现代课程论研究评述,日本课程的改革趋势,西方课程论的哲学社会学基础介绍等。 第二,对我国本土课程论相关问题进一步研究。 中学化学课程论,中学作文课程论,陶行知的师范教育课程论,课程论的逻辑起点追问,语言课程论涉及,电教课程论的基础研究,如何进一步认识课程论的地位、主要任务、基本内容问题,自然科学课程编制的理论依据,提出建构课程论想法,尝试对课程论进行历史性回顾总结。 这一阶段,课程论专业学术会议开始活跃,1990 年10 月,以“课程发展与社会进步”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是我国首次举办课程研究领域的专业性国际会议。 1997 年3 月,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课程论学术研讨会机制正式确立。 课程论逐渐摆脱教学论的依附身份,对国外课程研究译介从国家到具体学者范畴,逐渐扩大,涉及化学、数学、体育、科学、语言等具体学科课程论问题,关注课程论学科发展的方向,首次出现建立比较课程论意愿。
第三阶段,21 世纪以来至今:课程论研究进一步拓展提升。 进入21 世纪,因国家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助力,课程论研究成为我国教育学界的研究热点。 该时期研究较前两个时期出现了新变化:第一,国外译介持续增多并拓展新内容。 如潜在课程论,批判课程理论研究,诠释学课程理论研究,女性主义课程观,建构主义课程论,概念重建主义课程理论,过程哲学的课程论研究,永恒主义课程观,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拉丁美洲课程论,德国体育课程论研究进展,以及对国外课程领域人物如多尔、阿普尔、詹姆斯·林奇、施瓦布、巴格莱、威廉·派纳、布尔迪厄、亨利·吉鲁、麦克莱伦、泰德·奥奇、贝尔·胡克斯、艾沃·F·古德森、博比特、托马斯·波克维茨、马克辛·格林、德韦恩·休伯纳的课程思想进行探讨。第二,对本土课程论有关问题的探究更为宽广。 首现回顾我国课程论前辈学者的贡献等成果并涉及本土课程论建设方略、对信息技术时代的课程论、学科核心素养的课程论意义、整体课程论、校本课程论、微型课程论、智慧教育的课程论基础、探究课程论重构方法、我国课程论建构理路的“后课改”反思、从课程论迈向课程学发展的必然逻辑、中国特色课程理论的文化学构建,课程与教学论关系及本土化构建等内容。 这一阶段,以“课程发展与社会进步”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及全国课程论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继续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大量论著的发表和出版推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研究迈向新高度。
三、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的研究重点
(一)课程要素研究:由模糊走向清晰
在课程论的研究探寻中,对其要素组成的认知不断迈向深入,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人从课程结构的调整、课程设计、教材编排三方面概述[6];有人从对课程论的关系问题、课程形态及其相互关系、隐性课程等五方面详细评述[7];有人系统对课程本质、课程基础、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实验、课程评价、课程发展、课程改革八方面进行系统性概述[8];有人认为体现在课程论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变、课程论的理论体系多元建构、课程论的学科建设体系建构、课程论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平衡、课程论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五个方面[9];有人对新课程研究的理论基础、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五个方面论析[10];有人认为包括学科基础、学科性质、学科地位、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和学科群建设七个方面[4]。这些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课程理论、学科课程论、课程实践应用三大相对稳定构成要素,对课程本质、课程的理论基础、课程编制的基本原理、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改革、课程开发、课程类型、课程组织、课程实施、课程管理、课程评价等的认知在系列探讨中从模糊走向清晰。
(二)课程本质研究:由单一走向多维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学体系以参考和借鉴苏联教育学为主。 课程被当作教养和教学的内容归属于教学过程,实际体现为教学计划、教科书和教学大纲,一直延续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我国课程论奠基人陈侠认为课程是“为了实现各级学校的教育目标而规定的教学科目及其目的、内容、范围、分量和进程的总和”[11]。 另有学者提出广义的课程就是“为了实现学校培养目标而规定的所有学科(教学科目)的总和,或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动的总和,狭义的课程就是特指某一门学科。”[12]20 世纪90 年代,课程内涵发生新变化,廖哲勋提出课程的本质应“是由一定育人目标、基本文化成果及学习活动方式组成的用以指导学校育人的规划和引导学生认识世界、了解自己、提高自己的媒体”[13]。 施良方从词源学考察后总结出课程本质六说:课程即教学科目,课程即有计划的教学活动,课程即预期的学习结果,课程即学习经验,课程即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课程即社会改造[14]。 21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领域的影响,课程本质在原基础上又出现新认识,具代表性的观点如课程的真正本质是再选择和再实现课程发展目标的活动论[15];课程的信息本质论[16];课程本质即发展资源论[17];信息时代课程本质资源论,将课程视为服务于年轻一代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的信息要素(科学性资源要素、人文性资源要素、基础性资源要素、规定性资源要素、拓展性资源要素、个性化资源要素)的总和[18]。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课程本质问题研究从早期单一性的分析到现今的多元样态探索,从知识传递过程到学习经验的多种解读,再到活动论、发展资源论、信息资源论、信息本质论等,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的认识演进,这些认识推动着新中国课程本质研究的不断深入。
(三)课程身份研究:由依附走向多元
我国课程论因诞生的历史背景特殊,在发展过程中,首要探讨的就是身份问题。 戴伯涛在1981 年的《课程·教材·教法》创刊号上首次提出“要把课程论作为学校教育中一门重要的科学分支”的期望。 6 年后,陈侠提出课程论依附教学论说[19]。 20 世纪90 年代,王鉴、刘要悟、田慧生提出平行分支说,认为教学论与课程论是两个关系密切、部分内容相互交叉但同时又有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和专门研究对象的平行的教育分支学科,两者都从属于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下位学科。 郝志军与高兰绪提出并列交叉说,认为它们既不是平行并列之关系,亦不是包容关系,而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并列交叉关系,而交叉的部分就是教材论部分[20]。 进入21世纪,黄甫全提出大课程说,认为课程论及其下位学科、教学论及其下位学科、分支课程论及其下位学科、分支教学论及其下位学科以及教育技术学及其下位学科,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具有有机结构的大课程论学科体系[21]。 闫守轩提出本源统一性与次差异性说;杨小微提出交叉迈向整合说;王光明提出独立平行分支说;张华、杨仲杰、李方、令狐艳丽、金志远、吴晓玲提出整合说,其后对于如何深度思考整合之道,胡扬洋提出课程—教学整合说,且呼吁“推动课程论与教学论整合发展”[22];杨龙立与潘丽珠提出课程论上位说;洪明提出自我特色说;廖哲勋相继提出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说;邓宗怡与匡芳涛提出相互依赖又互为补充说;丁邦平提出中国特色论说;杨晨未定论说;王飞从教育学科本土化视角提出课程—教学论说;唐莉清提出独立说;程岭提出新论融合-交叉说。 梳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论身份研究核心观点,仅以论文研究成果文献数据统计,20 世纪80 年代的依附教学论一说,90 年代的平行分支说和并列交叉说两说,21 世纪以来的大课程说到融合-交叉说等共十三说。 这一现象既可以说明21 世纪以来中国课程论身份的受重视程度之高,更在一定程度表明中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的身份已由早期依附迈向当今多元,极大地推进了课程论研究的发展。
(四)体系研究:由初探走向成熟
学科体系问题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学科体系问题的认识水平,也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23]。 20 世纪80 年代,史国雅开始关注课程论的研究范围及指导原则,廖哲勋发问课程论的研究对象,陈侠首谈课程论的学科位置和它同教学论的关系。 20 世纪90 年代,黄甫全进一步提出大课程学科体系,并详细诠释课程论的主要任务、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张廷凯系统地回顾我国课程论研究的历史并提出建议,靳玉乐与师雪琴反思了课程论学科发展的方向,曾继耘探讨现代课程论的基本问题所在,徐平利尝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课程论的建构。 进入21 世纪以来,丁念金的课程论体系结构之探讨,冯生尧的再论课程论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侯怀银和谢晓军回顾了20 世纪我国学者对课程论学科建设的探索,侯怀银和任桂平回顾了课程论学科建设的基本情况和展望,廖哲勋多次关注课程论学科建设的规律性,并进行了从课程论到课程学的逻辑诠释,进而直接提出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针构建新时代课程学的理论体系新见解等。 从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八次课程改革进程来看,中国课程研究成果对基础教育实践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而这一实践又促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论学科体系的逐渐成熟。
四、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的研究成果特征
(一)涌现一批稳定的研究机构
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研究,历经三个时期的发展轨迹,在中国知网上采用主题词“课程”并含“基础教育”进行统计整理,可以看到一批相对稳定的核心研究机构。 中国知网(CNKI)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12 月26 日),基础教育课程论研究的机构群体排名前十位为:第一,华东师范大学,重点关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上海市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比较研究、教师专业发展、国家课程标准、校本课程、化学课程;第二,西南大学,关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小学教育、新课程改革、课程设置、课程实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资源;第三,东北师范大学,关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小学一线教育、教师教育课程、个案研究、校本课程开发、基础教育信息化;第四,华中师范大学,关注基础教育改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标准、科学课程、均衡发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第五,南京师范大学,关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比较研究、课程标准、技术课程、信息技术教育、课程资源、课程体系;第六,北京师范大学,关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改革、素质教育、核心素养、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基础教育国际化、基础教育教师教育质量;第七,西北师范大学,关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甘肃省基础教育、校本课程开发、行动研究、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调查研究、教育信息化、农村中小学课程实施、民族地区教师培训、课程课堂教学;第八,陕西师范大学,侧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职前师范生、免费师范生、新课程实施、课堂教学、中小学教师、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第九,湖南师范大学,关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教科书编写、教师专业发展、新课程实施、小学教师、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课程价值取向、体育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农村课程改革问题;第十,上海师范大学,关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校本课程、比较研究、课程标准、学业评价、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社会科课程、教育政策。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的研究主体,从早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个别学者,发展到以全国各师范大学为核心的研究机构群体,是值得肯定的好现象。
(二)展现多样的课程研究视域
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研究,经多年发展已展现出多样的视域。 如从出版的著作来看: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5 年编辑出版了国内第一套《课程研究丛书》,陈侠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完整的课程论专著”[24]《课程论》和钟启泉编著的《现代课程论》,标志着我国课程论真正意义上开启独立研究步伐。 此外还出现了译介日本学者对学校理科课程论的思考、台湾地区的课程论成果,对科学教育课程论的几个问题反思。 20 世纪90 年代,学界对未来中小学课程和中国近代课程史论进行专题性研究,对美国课程论研究进行介绍,探讨课程论的研究范围及指导原则,对国外课程改革进行详实的报道,对课程变革进行思考,现代课程论论述,对课程的基础、原理和问题系统阐述,首次出现阶梯型课程引论。 21 世纪以来,出现了经验课程论、校本课程论、综合课程论、活动课程论、课程新论、整体课程论、研究型课程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论、微型课程论、协商课程论、游戏课程论、初等教育课程论、人生中心教育课程论、课程论研究二十年(1979—1999)反思、课程论的新进展、课程论热点问题、跨文化视野下的课程论,出版了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的系列性多部课程论教材或教程。
(三)显著影响课程改革实践
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论研究,在引领基础教育改革实践,深化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展现出越来越强的影响力。 其一,承担国家级的科研项目。 截至2020 年,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中可以查询到涉及基础教育课程领域的资助项目“普通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研究”“面向21 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研究”“国家基础教育新课程的研究、实验与推广”等共计130 余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课程论在国家层面的认可度,也充分显示出21世纪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论取得的成就。 其二,对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影响巨大。 新中国成立至今开展的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就是中国本土课程改革创新的多维度研究不断探索的结果。 在此过程中,举办了聚焦中国课程改革且有重大影响的系列学术会议。 从20 世纪90 年代至今,共举办了12 次以中国课程改革实践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具体为:1997 年,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的“课程理论与课程改革”;1999 年,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的“21 世纪中国课程研究与改革发展”;2001 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的“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2004 年,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反思与评价”;2006 年,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的“课程理论发展与实践进展”;2008 年,在聊城大学举行的“课程理论与实践创新”;2010 年,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新世纪课程改革十年——趋向与愿景”;2012 年,在福建武夷山举行的“课程改革再出发——下一个十年”;2014 年,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课程改革在路上——向着《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迈进”;2017 年,在广州大学举行的“核心素养与中小学课程教学变革”;2019 年,在河南大学举行的“未来课程变革的挑战与方向”;2021 年,在温州大学举行的“新时代高质量课程体系建设:目标与使命”。 12 次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主题不断拓展,从课程理论到课程实践,从课程反思到课程评价,从趋向到愿景,从课程到教学,从借鉴考察国外课程到聚焦设计本国课程,从现在课程到未来课程,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研究展望
(一)构建中国特色课程论的学术思想研究体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应对激烈的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在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的同时增强我国的文化创造力、民族凝聚力,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思想。”[26]
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课程论研究相比,我国的课程论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成果在国际课程界的影响力仍微弱,与新时代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还不相称。 “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否,既与其研究方法有关,也与其理论基础有关。”[27]今后应深入系统地进行古今中国课程学者的思想研究,中国课程在国家、地方与个体方面的现象学研究。 重视中国课程研究的理论创造,中国课程研究的方法论创新,中国课程走向世界的身份认同,中国课程意识及教学中的课程决策等在一线教师身上的凸显,中国课程文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文化认同与课程研究等,“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而正确处理课程研究者在研究方向、研究态度和思想方法诸方面存在的种种矛盾,从而把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本国课程问题研究与外国课程理论研究、理论工作者的研究与各类学校教师的研究这几组重要因素有机结合起来。”[28]这是“迈向中国课程论的新时代,实现‘中国气派’愿景则是一项新使命”[29]。
(二)关注课程与人的深度关联研究
进入新世纪,世界各国都在总结过去的教育成绩,反思存在的问题,审视未来的教育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 年发表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Learning To Be: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1996 年发表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Leaning:the Treasure Within)之后,2015 年发表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Rethinking Education: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提出反思,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指出“世界在变化,教育也必须变化。 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这种形势呼吁新的教育形式,培养当今及未来社会和经济所需要的能力。 这意味着超越识字和算术,以学习环境和新的学习方法为重点,促进正义、社会公平和全球团结。 教育必须教导人们学会如何在承受压力的地球上生活;教育必须重视文化素养,立足于尊重和尊严平等,有助于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结为一体。”[30]这一系列的反思中出现的“尊重”和“尊严”,核心指向“人”,表明教育的目标不再是简单地以“知识”为重点,而是通过教育使人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让“人”成为教育过程的重点。
课程是教育的关键环节。 “人的教育需要人的课程来支撑”[31],不管多么理想的育人目标一定要落实到学生的层面,让人得到最大的自我实现,而不重视人的课程遮蔽课程与人的深度关联,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课程内涵方面,只关注自然课程和社会课程,或者将人文课程置于社会课程之下,过分强调自然科学课程,忽视自然课程背后的故事和人文,没有人文课程的一席之地;课程价值上,一味要求课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不知道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课程地位方面,自然科学课程、社会课程是核心课程,人文课程成了边沿课程、外围课程,成了摆设和装饰。 应用课程、技术课程、工具课程是核心课程,理论课程、永恒课程、经典课程成了边沿课程;课程在促进人的发展目标上,紧盯高考指挥棒的单向度智力教育,注重对学生的知识习得和思维训练,缺乏对学生的健全人格、道德情操的锻炼。”[32]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又直接强调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之中,而这一育人根本任务的实现有赖于在课程研究中加强对人的关注,“课程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33]。
(三)提升基础教育课程研究服务国家育人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问题是创新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 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26]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论研究虽已取得不错的成就,但从满足教育发展的国家课程需要来看,急需加强对新问题的关切和回应。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成为新的育人任务。 在中国知网以篇名“劳动教育”并含“课程”进行检索可以发现相关成果不多,而且论题主要集中在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的变迁,回忆农场课程的价值,劳动课程的价值,劳动课程的必要性,校本课程和社会实践等对劳动教育的作用,学科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劳动教育的意义所在等方面,仅有个别研究者论及新时代劳动教育课程设计问题,关注劳动教育的价值、意义、使命,这说明当前劳动教育课程研究与行动实施的需求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课程研究在教育发展和变革中承担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上承国家教育目标落实,下引具体教学实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在时代性层面上,课程研究要承载立德树人的使命,研究如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助力国家的发展;要紧紧立足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来展开课程研究,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的课程理论。 在实践性层面上,课程研究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全面准确地进入大中小学课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融入大中小学课程,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课程担当,如何借助现代社会的网络媒体技术展现更为强大的课程影响力,如何通过课程构建体系满足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国家育人需要等方面发挥作用。 总的来说,无论是时代性还是实践性,归根结底都要体现课程研究必须服务国家育人需求,这是今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研究的新课题。
从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课程论的学术思想研究体系,加强关注课程与人的深度关联研究,服务国家育人战略愿景方面来看,我们仍然需要做更多创新性的研究工作,这些“将会是我国未来课程领域应当重点解决的问题”[34],也是“课程理论发展和创新课程实施的契机”[35],需要中国课程领域学术共同体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