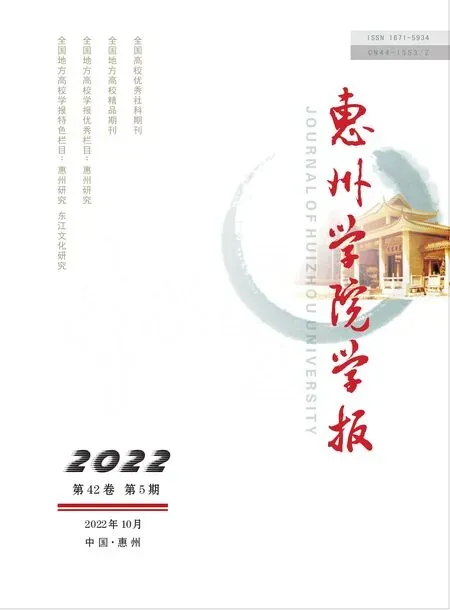略论晚清至五四时期革命与小说的互动
孙述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晚清以降,至五四前后,最重要的文类就是小说。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将晚清小说分作狎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丑怪谴责小说和科幻奇谭。革命叙述是晚清科幻小说(即王德威所说“科幻奇谭”)和革命前期政治小说中的重要一环。晚清小说家在纵情放理的想象中,将自己对国家、政治、革命的期望寄托于内,发未敢发或不便发之言,王德威将其总结为“作者对历史困境所不能已于言者,尽行投诸另一世界”[1]15。小说的繁盛是包括政治在内的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革命的发展也离不开以小说为主的晚清文学的传播、启蒙之功。
一、现代革命观念在中国的形成和传播
要探究现代革命观念,就要涉及“革命”一词。“革命”的本意是指通过激烈的方式将政治权力变更到新的统治者手中,最直观的表现便是改朝换代。中国历来讲求儒家文化,强调师出有名、忠国忠君,因此革命在古代往往带有贬义色彩。近代革命者为了唤醒广大民众,在宣传时或多或少都带有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色彩,以此来贴合民众、减轻阻力,中国古代革命观念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革命运动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孙中山在不遗余力建成民国的过程中,便时时借用儒家经典中的革命观念,宣扬其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而发动底层人民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在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古代革命观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帮助西方近代革命观念进入中国,并为广大群众的接受降低了阻力。
投影到文学作品上,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狮子吼》等皆是如此。《狮子吼》仅有八回,是未完之作。小说结构类似“黄粱一梦”,写自己在梦中偶遇雄狮发出巨吼,又梦见参加“光复五十年纪念会”,醒来后竟发现梦中所看“光复纪事本末”就在手边。《狮子吼》在主题上同《猛回头》《警世钟》一脉相承,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罪恶行径,期望全民族觉醒,共同建立新共和国,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书中的民权思想。《狮子吼》第三回“民权村始祖垂训,聚英馆老儒讲书”,借着文明种的口说到“三代以上勿论,自秦以后,正不知有多少朝代。当着此朝,口口说要尽忠,和此朝做对敌的,痛骂为夷狄,为盗贼;及那盗贼、夷狄战胜了此朝时,那盗贼、夷狄又为了君,各人又要忠他,有再想忠前朝的,又说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君也,夷狄也,盗贼也,其名随时而异。是第二项又说不去了。何如以国为主,统君臣民都在内,只言忠国,不言忠君,岂不更圆满吗?”[2]127这里陈天华引入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实则是为读者接受西方近代革命观念创造条件。又说到“照卢骚的《民约论》讲起来,原是先有了人民,渐渐合并起来遂成了国家。比如一个公司,有股东,有总办,有司事;总办、司事,都要尽心为股东出力;司事有不是处,总办应当治他的罪;总办有亏负公司的事情,做司事的应告知股东,另换一个。倘与总办通同作弊,各股东有纠正总办、司事的权力;如股东也听他们胡为,是放弃了股东的责任,即失了做股东的资格。君与臣民的原由,即是如此,是第一项说不去了”[2]127。此为民权思想的阐述,开始过渡到西方近代革命观念。
中国人最早以“革命”一词翻译“Revolution”,是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这个翻译本身就具有革新意义。西方的“Revolution”指掀翻根底、新造世界,更多带有正面色彩。将“革命”与“Revolution”搭桥挂钩,将中国古代的王朝易姓转换成近代意义的社会制度之大变革,从而赋予了“革命”一词全新的词性。中国革命观念从古代向现代形态转化的一大关键点即在于此。
西方近代革命观念传入以后,在中国早期革命派思想家的努力下,开始与中国人的反清革命相结合,并经过邹容的《革命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完善补充,逐渐形成了中国现代革命观念。邹容的《革命军》提出了革命的目的、根据、性质、理论、前途等内容,将革命扩大到了普遍的人性权利上,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是中国革命观念的一次历史更新。但邹容对下层民众缺乏关心,这一点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那里得到了改善。三民主义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民生问题,至此中国现代革命观念有了完整内涵与长远目标,逐渐丰富充实起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引入,则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上起到了主导作用,最终成了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更新了西方近代革命思想观念,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并最终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促成了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跨越式更新。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开辟了园地。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以后,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带给了广大人民群众新的思想动力和希望,并取代维新成为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国家。这一切,无不归功于现代革命观念的首发之功。
二、异国他者形象的社会化:以“小说界革命”中的法国大革命形象为例
法国大革命高潮在1793年,但迟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其基本面貌和发生方式才逐渐为中国高级知识阶层所接触掌握。其时法国大革命形象多出现于政论文章这样一种高级知识阶层文体中,很难与下层民众发生关系。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到了法国大革命,“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3]77。他在这里把法国大革命当作革命之指导,但这样的影响很难突破上层,直达底部。
异国他者形象的社会化往往要靠文学化来实现,法国大革命形象为大众所熟知,实现从政治向文学(社会)转化,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为其开启了大门。《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记叙了法国吉伦特党的成员之一罗兰夫人的事迹,但梁启超对其进行了拔高,完全写成了英雄传奇,这对当时影响巨大。不仅各种形式的“罗兰夫人传”层出不穷(如《黄绣球》第三回“梦中授读英雄传,天外飞来缧绁灾”中记叙了罗兰夫人在黄绣球梦里给她讲述俾斯麦和拿破仑事迹,最后承黄通理替她讲清楚罗兰夫人是何许人也[4]16-23),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开创了法国大革命形象与中国传统叙事的融合模式,这个模式在接下来的“小说界革命”中进行得更加彻底,并不断制约和改变着双方。
“小说界革命”中最首要的改变是主题的开放,这一时期随着外来文化的输入、小说地位的上升,严肃主题得以进入小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开篇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5]349,这为小说提出了衡量的新标准,为法国大革命形象进入中国小说提供了正当理由。梁启超在1902年提倡“小说界革命”时,力举小说的塑造英雄人物之功,借此来重铸民族之魂。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小说能改良人心、改善群治、改革国运,这其实就是我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观,故能得到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理解,容易为他们所接受。但这个“道”开始有了扩充,许多不属于传统的西方理论学说开始进入,与此相对应,许多西方词汇和形象开始进入小说,其中就包括法国大革命。另一个重要改变是“小说界革命”中对历史小说、历史题材的推重,尤其是以外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受到相当欢迎。西方思想的进入对传统历史小说内涵进行了改变与修正,大家普遍将容易阅读的小说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小说作者在写作之初就带有对民智的开化意识,所以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往往借法国大革命形象对现实进行影射。在这样的情形下,法国大革命形象不可能完全融入中国传统叙事,而是加强了“他者”形象,呈现出了全新面貌。
法国大革命形象在进入中国小说时,受到了本土叙事与传统模式的影响,并做出了改变。首先是题材的制约。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才子佳人”模式,演变至晚清成了“英雄”和“男女”的主题,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往往是通过英雄传奇的叙述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如罗兰夫人的进入中国,便演化成了一个带有中国读者想象的英雄形象(如《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黄绣球》),其恋爱经过带有“才子佳人”结构(如《法国女英雄弹词》),革命爆发前的罗兰夫妇生活带有中国古代名士状态(如《血海花》)。其次是法国大革命形象在中国传统叙事模式中产生了偏移。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好坏对立现象影响了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如路易十六死便必然百姓狂欢,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化场景,其来源是中国古代昏君奸臣下场的文学描述;又如法国吉伦特党和雅各宾派的争权,进入中国后演化为“忠奸对立”的模式。在法国大革命形象进入中国传统叙事模式的过程中,两者都对对方进行了改变与转化,这样一种角力,使得大革命这一异国他者形象逐渐进入了普罗大众的视野中,完成了其社会化的过程,同时普通百姓的视野也随之打开,望向大洋彼岸。
三、世界大同的理想:以晚清乌托邦小说为例
“乌托邦”一词最早由托马斯·莫尔提出,后来扩展到文学领域,人们把描绘未来美好社会的小说称作乌托邦小说。晚清小说创作繁盛,其中以乌托邦小说为大门类,出现了一大批描写未来新中国的乌托邦小说。晚清以来,众多有志之士受西方科技、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刺激,有感于当时中国的落后状况,借鉴西方乌托邦小说的创作手法,写出了政治色彩鲜明、未来性突出的数量众多的晚清乌托邦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的《新中国》、蔡元培的《新年梦》、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晚清乌托邦小说的大量出现,离不开《新小说》的提倡之功,开山之作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构思《新中国未来记》花了将近5 年时间,但小说只写了5回就戛然而止。尽管没有写完,但它开创的构想未来、宪政为先,并在富强之后引领全球,最终召开万国和会、天下大同(见第一回“楔子”)这样一种模式,为后来的乌托邦小说奠定了基础,起到了范式作用。
晚清乌托邦小说的一个重要相同之处是将实行宪政作为未来中国新兴富强的前提,可看作是当时政治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新中国未来记》第二回“孔觉民演说近世史,黄毅伯组织宪政党”借孔老先生的口说到“诸君啊,你道我们新中国的基础在哪一件事呢?其中远因、近因、总因、分因虽有许多,但就我看来,前六十年所创的‘立宪期成同盟党’算是一桩最重大的了。这党的名字怎么解呢?原是当时志士想望中国行立宪政体,期于必成,因相与同盟,创立此党,合众力以达其目的,所以用这个名”[6]92。可见立宪政体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性。不过,究竟新中国在立宪之后是怎样到达如今这个富强地步的,《新中国未来记》仓促之中未及详细展开,后来的乌托邦小说对其进行了补充,最重要的就是科技强国这样一条道路。
陆士谔的《新中国》里勾勒了未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地道里行走的电车、跨过黄浦江通到浦东的大铁桥、扩充以后有学生二万六千多名的南洋公学、苏汉民发明的医心药和催醒术、冶铁所里的自行斗以及空行自由车等等,描摹了一幅未来中国繁荣发达的景象。正是这些形色各异的科技发明,从军事、民生甚至人心上帮助中国实现了富强。中国既已遥遥领先世界各国,有着绝对的军事、科技、经济实力优势,那么在此之后中国的发展道路又该如何呢?众多乌托邦小说的处理呈现了这样两种路径:一条是中国走上了称霸全球的道路,形成了黄、白种战主题模式,以《新纪元》《新野叟曝言》和《电世界》等为代表;另一条是晚清乌托邦小说追求的最高境界,即世界和平、天下大同的理想模式,以《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新年梦》《新石头记》等为代表。前者体现出了晚清时期文人落后的种族观念以及清末民众的民族主义心理,后者描绘了一幅世界和平的美好画面,是儒家传统长久以来对士人浸润的必然结果,给处于激烈变动与黑暗社会的时人以美好慰藉,更加反衬当时的苍凉现实。本文重点讨论后者:世界大同的理想模式。
陆士谔的《新中国》第十二回(最后一回)“立宪四十年普天同庆,大会廿三国决议弭兵”,描绘了世界和平这样一幅大同愿景。“咏棠道:‘可知,你也是个背晦人呢!现在,全世界二十多国会议设立弭兵会,并万国裁判衙门,都已决议了。那弭兵会会所和万国裁判衙门,都设在我们国里。并且,弭兵会会长,就举了我国大皇帝。你想,不是天大的喜事吗?’”[6]82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在第一回“楔子”里写到“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已经将太平条约画押。因尚有万国协盟专件,由我国政府及各国代表人提出者凡数十桩,皆未议妥,因此各全权尚驻节中国”[6]87。蔡元培的《新年梦》更进一步,不仅同其他乌托邦小说一样设立了“弭兵会”“一万国公法裁判所”,更是在最后连国家都消灭掉了,把裁判所什么的也都撤掉了,“立一个胜自然会,因为人类没有互相争斗的事了,大家协力地同自然争,要叫雨晴寒暑都听人类指挥,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呢[6]229”。晚清知识分子在对当时国民命运感到忧虑的同时,也在思索弱肉强食的西方文明,并反映在了他们的笔下,通过这样一个大同世界的建构,表达了他们建立平等、文明的现实世界体系的愿望,说出了历来人类的博爱主张。并且在蔡元培那里,各国家、民族平等互爱还不是最终理想,消除民族、国家的界限,彻底实现人与人平等无差的大同理想才是世界的终极模式。此外《新中国》《新年梦》等乌托邦小说还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共同叙事模式:由梦开始,由醒终结。即小说世界的展开都由做梦切入,在进行名目繁多、花样迭出的叙写之后,最终又让读者苏醒,一方面让读者清醒地认识到和现实的反差,另一方面不动声色地说明小说描摹的美好世界也许就在未来,也许可以展望。正如《新中国》结尾所讲“我道:‘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女士道:‘我与你都在青年,瞧下去,自会知道的’”[6]84。
事实上大同模式能够在晚清乌托邦小说中蔚然成风,除开梁启超的首创之功,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乌托邦精神能够同我国长久以来的儒家大同思想相契合,让广大晚清文人从中找到了古今中外相维系的结合点。晚清乌托邦小说中的世界大同思想,其具体表现为:一是政治与道德交融,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改良国民本性,将国家的运转维系在理想国民的自觉上,没有完整的政治管理体系;二是直接来源于小说家的儒家忧患意识,在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下,知识分子普遍希望通过未来回到一种儒家建构的和谐、稳定的大同社会,也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们救亡图存的政治意图;三是可以看出当时醒悟过来的晚清知识分子们的矛盾心态,在西方文明不断侵蚀的时刻,看着古老民族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内心不停升起希望祖国、民族强大起来的愿望,因而将政治、科技、军事、民生种种未来想象都诉诸笔下,对西方文明既渴慕又抵触,对民族国家既痛心又热爱。晚清乌托邦小说多以“新”字开头,有“新”必有“旧”,从这种新旧结合与对比中,可以看出作者们试图降低民众接受小说思想的难度、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努力、实现政治意图的想望以及希冀国家民族走向富强的责任感,起到了相应的启蒙作用。
晚清乌托邦小说的一大特色是对新国民的完美想象,大都写到了未来国民的完美形态。陆士谔在《新中国》第四回中写到苏汉民发明的医心药和催醒术,“那医心药,专治心疾的。心邪的人,能够治之使归正;心死的人,能够治之使复活;心黑的人,能够治之使变赤。并能使无良心者,变成有良心,坏良心者,变成好良心;疑心变成决心;怯心变成勇心;刻毒心变成仁厚心;嫉妒心变成好胜心……自从医心药发行以后,国势民风,顷刻都转变过来……那催醒术,是专治沉睡不醒病的。有等人,心尚完好。不过,迷迷糊糊,终日天昏地黑,日出不知东,月沉不知西。那便是沉睡不醒病。只要用催醒术一催,就会醒悟过来,可以无须服药[6]30”。对此,龙慧萍、胡倩在《晚清乌托邦小说中的理想国民形象》中对新国民特征做了如下总结:一是有公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二是重视科技与实业的发展,多为科学家与实业家;三是体魄强健,但也在文章结尾处说到:“不过,晚清乌托邦小说中的理想国民形象固然光彩夺目,却因为过分律己、合群,并非有血肉、性格鲜明、内心充实的个体;人物都有强健的体魄,也导致女性和男性的差异也几乎被抹杀殆尽;人物的思考、行为方式大体相同,也使得理想国民形象落入类型化的窠臼”[7],指出了乌托邦小说为服务政治建构而牺牲文学形象的瑕疵之处。事实上以政论入文本正是晚清乌托邦小说的一大特色,众多作品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作家的政治改革主张阐述,故思想大于情节,政治盖过文学,这也是由当时的时代氛围决定的。晚清小说家通过对未来中国的想象与建构,进一步丰富了民族主义的内涵,并通过报刊发行等方式广泛传播,扩大了民族主义的群众影响。
纵观整个晚清乌托邦小说中的大同想象,基本都超不出康有为《大同书》的架构——科技强国和道德救国的历史进化;整个晚清作家的西方民主理论,基本来自赫胥黎的“进化论”和卢梭的“民约论”。晚清文人在乌托邦想象中构建的世界,是西方冲击下东方世界破碎后,又在对西方世界带有怀疑的情况下,构建出的西方和东方以外的第三个世界。这个新的世界是对当下生存处境的一个回应,它将众人的目光带向未来,启动了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征程。同时这一大同想象,将社会制度架构在了个人命运之上,个人的独立性作为现代社会建构的基本前提没有得到充分考虑,没能摆脱民族主义的束缚。
四、“庶民”胜利的新纪元:以五四文学中的“俄国革命”为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李大钊指出这次胜利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被打败的是世界军国主义。李大钊认为1789 年法国大革命是19 世纪各国革命的先声,而1917 年俄国革命是20 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改写了一战胜利的意义。李大钊通过“俄国革命”所提出的胜利意义,改变了中国人对20世纪文明的看法。庶民的胜利,意味着20 世纪文明与19 世纪之间的断裂,其直接表现就是俄国革命。一战标志着英国体系的破产和美国制度的创建,俄国革命的胜利则指向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小说和政论作品中,俄国革命运动的话题备受欢迎。如岭南羽衣女士所著的《东欧女豪杰》,详细叙述了俄国民党人的活动;陈冷血创作了短篇小说集《虚无党》;林纾翻译了《双孝子噀血仇恩记》;《民报》上也刊出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运动情况的介绍和评论文章。新文化运动以来,《新青年》作者群发表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章,其中以陈独秀和李大钊最为活跃。陈独秀相继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和《社会党与媾和运动》等文章,李大钊相继写出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论俄国革命之远因和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等文章。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又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向中国热情宣扬十月革命,认为其是世界历史新时期的开端。
俄国革命的开创意义是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在此影响下,中国诞生了五四运动;在十月革命、马列主义、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实践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以后,我国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因此翻译介绍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是五四本身的文化和革命要求,是当时文化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的工作占了相当大一个比重。瞿秋白在1920年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言中提道:“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十月革命前后,中国翻译的俄国作家作品中最多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辛亥革命后,高尔基的作品也开始被翻译到中国来,此后屠格涅夫、安特列夫等人也相继与中国读者见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俄国革命随着译介进入到五四作品中来,从属于当时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社会真理的步伐,并最终转化成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一部分,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从无产阶级到庶民,从世界到中国,五四以后这一胜利最终指向了人民主权。推动这一转变的,是与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有密切关系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工业化扩张带来了亚非拉的崛起,催动了政党组织的产生,由此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成了对其自身的重大挑战。由此俄国革命支持民族自决权,支持民族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庶民的胜利就是要将帝国主义的战争转化成无产阶级的战争,因为一战是资本主义为了扩张生产力而发动的,布尔什维克就是要团结全世界的庶民,发动阶级战争,创造一方自由的国土。李大钊断定,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五四以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热情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都使得中国的文学革命开始出现新变化,向着新民主主义转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开始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毛泽东明确指出,五四时期中国虽然还没有共产党,但是已经出现了大量赞成俄国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前途,带领着中国知识分子,向着革命不断地前进。走俄国人的路是当时众多小资产阶级作家的革命愿望,五四之后中国各地纷纷成立文学社团,出版刊物,探讨俄国革命、马列主义。1919到1921年中国爆发了三次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大论战,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新文化战线也由分裂走向统一。俄国革命影响下的五四文学革命,最终没有走向胡适、周作人的道路,而是走上了鲁迅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五四时期的鲁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所代表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因为鲁迅从一开始,就自觉地以文学革命思想从事战斗工作,深刻反映人民大众的需求,坚决地同一切反动主义做斗争,这本质上与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战斗方向是一致的、战斗任务是重合的。鲁迅关心俄国革命的社会和文艺状况,先后编译《文艺与批评》(1929)、翻译《工人绥惠略夫》(1922)、《艺术论》(1929)、《文艺政策》(1930)、《毁灭》(1930)等俄国文学作品和理论书籍,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郭沫若的诗歌在表现了五四精神的同时,也深深反映了俄国革命的影响。他的《晨安》一诗,直接喊出了“我所敬畏的俄罗斯呀”的语句,还将列宁和托尔斯泰写入诗里(《巨炮之教训》),打下了俄国革命深深的烙印。此外还有茅盾,自他接手《小说月报》起,就为俄国革命文学作品的输入不停地做着努力,一手创办的《海外文坛消息》栏目,更是为中国认识俄国革命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
俄国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我国的文学革命开始出现了新动向和新因素,但五四时期对俄国文化、革命、文学、社论等的接受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引入俄国启蒙主义的时候,并不单单是情感上的强烈需要,而是更多出于强烈的现实目的性。不论是李大钊还是鲁迅还是茅盾,都是在这种“为人生”的现实需要接受视野下,译介了大量有关的作品,促成了五四时期启蒙、现实主义盛行的主流文化,这就将复杂的俄国文化、文学、思想现实进行了简化,使五四时期相当一批青年不能全面认识俄国。其次五四时期为了俄国文化的实用性,放弃了审美尺度和思想力度的判断,导致相当一批平庸之作进入中国,将俄国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简单化的实用布尔什维主义,曲解了俄国革命,也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质量。最后是引入无产阶级文化时,放弃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精神,导致五四所推崇的自由、民主精神衰落,专制主义的阴影笼罩,使知识分子屈从于意识形态,缺失自由思考而日益肤浅,缺乏文化宽容精神而未能正视传统文化。这也给后来的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带来了迷途和损失。
综上所述,晚清至五四时期政治革命走过了一个相当艰难且曲折的路程,小说也愈来愈承担了重要繁复的功能,在此期间,革命与小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成全。中国革命进入了全新阶段,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也完成了自己的更新迭代。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昭示着后来发生的一切:中华民族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处理自己的遗留问题,文学也随之继续着现代化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