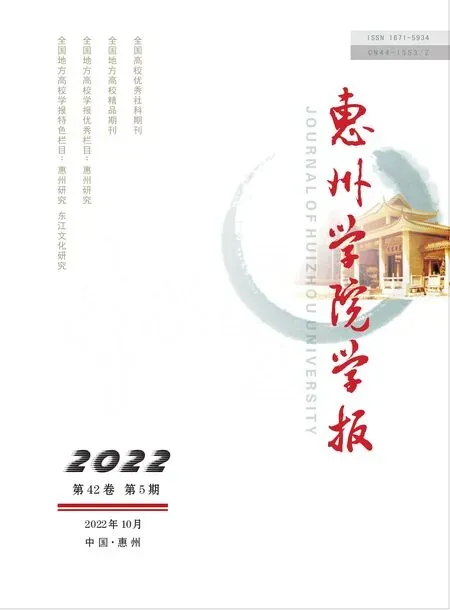再论State 汉译名的厘定
——兼论20世纪初“国家”观念在中国的流播
万齐洲
(惠州学院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惠州 516007)
关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颇多,如李华兴《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建构》、葛兆光《“国语”与“国家”》及其专著《中国思想史》的相关论述,其中不乏精彩之论。但“State”的汉语译词“国家”,如何进入人们的视野,又如何摆脱其汉语古义,学术界关于这一演变过程少有关注,偶有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提及。笔者在相关论文(著)中亦略有阐发①,现围绕这一问题再作探讨,就教于方家。
State 含义:“The political system of a body of people who are politically organized;the system of rules by which jurisdiction and authority are exercised over such a body of people.”[1]1443
State一词出现于13世纪,经过近600年的演变,到19 世纪初,State 的含义为:“A state is a community of persons living withincertain limits of territory,under a permanent organization which aims to secure the prevalence of justice by self-imposed law. The organ of the state by which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are managed is the government.——Theodore D.Wools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1]1443
20世纪,State的内涵更加丰富:
John Salmond 在 1947 年出版的 Jurisprudence 一书中,将 State 定义为:“A state or political society is an association of human beings established for the attainment of certain ends by certain means.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various kinds of society in which men unite,being indeed the necessary basis and condition of peace,order and civilization.”[1]1443
J.L.Brierly 在 1955 年出版的 The Law of Nations 解释 State:“A State is an institution,that is to say,it is a system of relations which men establish among themselves as a means of securing certain objects,of which the most fundamental is a system of order within which their activities can be carried on.”[1]1443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all Machiavslli 1469-1527 年)是最早在近代意义上使用State 的思想家之一。在《李维史论》一书中,马基雅维利论述State 与Citizen(公民)的关系时说,公民应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此后,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 年)又将State 与Sovereignty(主权)联系在一起,认为主权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
国家由Citizen(公民)、Territory(领土)和Sovereignty(主权)三个核心要素组成。Sovereignty(主权)是其主要特征,具有永恒性、绝对性、无限性等特点。没有Sovereignty(主权),State就不再存在。
一、传教士与State的汉译名
早期英汉字典中,State 即翻译为“邦、国、国家”:
1845年,英国人墨黑士《华英字典》中,State译为:“形势,光景,情形;品级,地位;邦,国;体面”[2]251。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1847 年2 月3 日完稿的《字典》中,将State 解释为:“Country 国,邦,域,国家,邑;High official of state,大臣;State affairs 国家之事;Counciallor of state 军机大臣;a state prisoner 钦犯;State of nation 国势”[3]S部82。
1864年,德国传教士罗布存德编著的《英华字典》面世,该字典中,State除了被译为“国,邦,邦国”外,还被译为“国家”:“an affair of state,国事,国家之事”[4]1011。
1865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其译作《万国公法》中,将 State译为“邦”“邦国”“国”“国家”:
1.As independent communities acknowledge no common superior,they may be considered as living in a state of nature with respect to each other.[5]3
邦国天然同居,虽无统领之君。[6]7
2.So also of confederated States;their right of sending public ministers to each other,or to foreign States,depends upon the peculiar nature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union by which they are bound together.[5]274
合盟各邦互相通使,或遣使至国外,其可否必视其合盟之法而定。[6]142
3.All the members of the enemy State may lawfully be treated as enemies in a public war;but it does not therefore follow,that all these enemies may be lawfully treated alike.[5]419
凡遇有公战,敌国人民俱可以敌视之,惟不可一律看待。[6]199
4.The State does not even touch the sums which it owes to the enemy;everywhere,in case of war,the funds confided to the public,are exempt from seizure and confiscation.[5]368
至国家自欠于敌人之债,则不能不还。缘无论何处,有托公信而存钱物者,皆至于捕拿之权外。[6]137
丁韪良笔下的“邦”“国”“邦国”三字的含义大多数情况下是互通的。对“邦”“邦国”“国”三者的区别与联系,丁韪良做了如下说明:“邦国二字虽系通用,然书中所称自万乘以至百乘,皆谓之国也。若邦,或偶指自主之国而言,而于屏藩以及数国合一,则以邦名其各国者为常”[7]1。丁韪良随后与人合作翻译的《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陆地战例新选》等几部国际法著作中,State的四个汉语对译词“邦”“邦国”“国”“国家”,多次出现:
1.在蛮夷尚有尊上敬长之礼,则文教盛行之邦,其职分尊卑,岂可无衣冠礼节以辨异乎。[7]22
2.英国阿斯富学院有教习苏志者,著书名曰《邦国通法》。[8]6
3.盖释放之权,系属国家行之,而遵循定章也。[9]17
4.Her tributaries included all the petty States of Eastern Asia. These vassal States had few 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The existence of independent States,so situated as to require or favor the maintenance of friendly intercourse;That those States should be so related as to conduct their intercourse on a basis of equality.[10]113
按亚洲东境诸小国,悉隶中国藩属。此小国者,彼此绝少往来。若于自主之国,境壤相接,舟车可通,势不能不讲信修睦,以联邦交,一也;诸国交际往来,各以平行相接,而无上下之分,二也。[11]19
5.若不得已而行报复,则所加之害,不可甚于敌国之所为。非将帅允准,亦不可行之。虽行报复,总不得有违于仁义。[12]1
1880 年,与丁韪良同时任职于京师同文馆的法国教习毕利干,翻译了《法国律例》一书。该书中“国”“国家”一词频频出现。
1.翻译《法国律例》之设,实为本国四民一切行止动作,划一界限,使之有所率循,不致或获于罪也。[13]1
2.凡此制定之例,其事中有关系之处,系有干国家君民所享升平绥靖之福者,则凡本国人民自应一体钦遵谨慎守。[13]2
3.凡属国家所有之平林、遥林,自今以至将来,不准有给人以权有如上文二条所载之情者。凡不论何等使用情节,不准于国家所有之平林、遥林,而挟有此例应者,除事经于设此定例之时,即有人执有切实之凭,谓于此等平林、遥林分上确有根底,实挟有得以使用之权者,则始可行或由国家查明,给有切实执据。[13]41
1868 年,受聘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英国人傅兰雅与徐寿、华衡芳等人合作,翻译西书100 余种,其中有多种国际法著作,如《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交涉便法论》等。傅兰雅的译著中,“邦”“邦国”逐渐演变为“国”“国家”内的一个单位,State 的汉语对译词固定为“国”“国家”,而且“国家”出现的更加频繁。
1.又交战之国与局外之国亦有分所当得与分所当为之事。……国家所管之地,与民间业主之有其地者,关系相同。[14]6
2.从前国家派赴他国办事之公使人员,大半皆用教主,盖其学识胜于平常有爵之人,且明各种律例。[15]6
3.此三十年间,各国中人心最恶,其国家之法与教会之法,国王与教王可以作主。[16]10
4.凡国家所欠之银,无有不还者。[17]14
被誉为近代玄奘的翻译家严复,在《社会通诠》一书中,将State亦译为“国家”:
1.Character of the State. The new type of community formed by these events differed fundamentally from that which preceded it.[18]75
严译:国家形性 以前者之二事,而新社会兴.言其形性,有绝异于蛮夷、宗法二社会者。[19]80(今译:国家特点:与前者有别的新型共同体)
2.Incidentally,also,its action sowed the seed of the great problem of pauperism,or State relief of the indigent.[18]139
严译:自行社制亡,而鳏寡孤独者不得其养,此国家赈贫之政之所由兴也。[19]163(今译:其结果是带来贫穷后果的同时,国家也随之开始履行救济的职责。)
“国”的繁体作“國”。“國”字最初出现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字形从口、从戈、从一,三个部分加在一起就是“或”字。《说文解字注》释“一”:“惟初大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汉书》:元元本本,数始于一”[20]1。由“一”可以引申出土地之意。“口”:“人所言食也。言语饮食者,口之两大端舌下亦曰口,所以言别味也”[20]54。“口”可以引申出人口、民人之意。“戈”:“戈,平头戟也。《考工记》:冶氏为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20]628。“戈”指兵器,从中可以引申出战争之意。
“国家”由“国”与“家”两个单音节词组成,组成词组“国家”后,其含义为:
1.指“国”与“家”两个概念。《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表明天下、国、家是三个彼此联系、又严格区分的概念。
2.国家为国之通称。《尚书·立政》:“其惟吉士,用劢我国家。”
在历史文献中,“国家”常与“土地、人民、祭祀”联系在一起:
《三国志·魏书》:“然则士民者,乃国家之镇也;谷帛者,乃士民之命也。”
《明史·陈友定传》:“郡县者,国家之土地。官司者,人主之役。而仓廪者,朝廷之外府也。”
比较State 与其汉语对译词“国家”,可以看出两者的内涵大体相近,从“国”字的构成,可以看出国家与“土地、人民、主权”的关系。正如刘庄“何为国家”一文所说:“我国昔日无专门国家学。……《说文》曰:国,邦也。以邦解国,犹如以国解邦,皆无所说明也。《周礼夏官》,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是国即天子所辖之全境也,殆与天下二字之意相同。《冬官考工记》曰:匠人营国,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是国即都城也。《礼王制》曰:五国以为属,十国以为连,二十国以为卒,二百一十国以为州。是国不过天子所辖之一小区域耳。汉西域诸国,有城郭国,有行国,城郭国以筑城为守,是以城为国也。行国不立城,以马上为国,是只以人为国矣。就以上诸说观之,我国自来之所谓国,殆含有三意:一为领土,二为人民,三为管辖此领土及人民之主人。故有释国从口,指疆土言,从只指活存于地上之主人言,从戈指保守此疆土及生人之武力言。是虽出于牵强附会,要亦有可观之处。然于国字之意义,终未阐明国家二字连用,不知始于何时。自大禹弃尧舜揖让之制,以位传子而开家天下之例,国与家无遗焉。……国即是家,家即是国,此似为国家二字连用所由始”[21]1-9。
近代西方State 一词与古代中国“国”“国家”的最大区别有二:一是古代中国只有臣民,没有公民。二是国家主权归属有异,前者归民,后者归君。
二、State的汉译名东渐及其回归②
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1864年中国出版后,迅速传入日本,State 的汉语对译词“国家”也被日本学界接受,日本学界借此译介西方国家学说,使得与“朝廷”“天下”有别的近代“国家”观念得以广泛传播。
明治二十年(1888年),《国家学要论》:“自由国ニ於テ国家ハ豫メ其臣民多数ノ同意ヲ得ルニ非ザレバ運行スルコト能ハズ。然レドモ一旦此同意ノ得ラレタル以上ハ、国家ノ目的ハ法律ノ威力ヲ以テ之ヲ強行シ得可シ。国家ニ必用ナル経費ハ租税ノ法ニテ之ヲ獲得シ得可シ”[22]245。
明治二十一年(1889年),有贺长雄《国家学》:“国家有テ人民有リ、人民有テ国家有り、国家人民元ト同物ナリ、昔ハ国家ノ事ヲ挙テ當局ニ委シ、今ハ人民自ラ其事ヲ執ラントス、古今ノ差異之ヨリ著シキハ無シ。凡ソ国家ノ人民タル者、国家ニ依テ其生命ノ目的ヲ達センコトヲ欲セザル無ク、又之ヲ達スルノ権利有リ”[23]19。
明治二十二年(1890 年),ブルンチュリー《国家论》:“國家ノ目的:國家ノ人民ニ對ンテ公共り安事及幸福ヲ諜ラサル可カラサル義務アルコト”[24]48。
20 世纪初,始创于中国的“国家”侨词回归,近代“国家”观念也渐渐为国人接受。
1904 年,专为中国留日学生开设的“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速成科”(简称法政速成科)正式成立,其课堂讲义《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关于“国家”的论述对于中国留日学生影响较大:
国家云者,以一定土地为基础,其以权力所统一人民之团体也。……第一,人民。国家之生存,必以人类之团结为前提。其人类之数不必要多数,苟得作团体则足矣。第二,土地。……第三,权力。无论何国,皆有治者与被治者之别。[25]474-476
关于国家之目的之学说亦多,兹略举其二、三:第一说,国家之目的在维持国家之存立。……第二说,国家虽为人民而存立,而其目的专在防御人民之危害。……第三说,国家之目的,以积极论,则在谋人民之福利,以消极论,则在除人民之危害。合此二者,国家之目的始全。[25]479-480
国际公法之主体,厥惟国家。国家者何?受主权力所统治之定域内人民之团体也。[26]58
1906 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法律学堂”——京师法律学堂成立。聘请日本教员岩井尊闻讲授《国法学》,书中介绍“国家”:
国家者,有一定之土地、人民及主权者也,故谓国家为政治团体。[27]27
国家之活动范围:国家为无限制政治团体,故其所行事项,本无限制,唯其场所与人(领土、人民)确有范围,不能不受限制。[27]30
国家本属抽象无形,故欲实行其权力,必用自然人。……国家有人格而无人之本体,故国家为无形之体,所谓法人者是也。国家既为无形之体,则国家权力,必藉有形者之意思而发动之。发动者,机关也。充国家之机关者,非自然人不可也。[27]33
三、中西涵化③之“国家”及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的中国还处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民众只知“朝廷”,对于近代西方“国家”观念所知甚少。正如1904 年署名“三爱”的作者在“说国家”一文中所说: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的销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哪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28]1
随着中日文化交流频繁,侨词“国家”渐为知识界接受。在各种思潮的涌动中,国家的三个核心要素(主权、领土与人民)逐渐被人们理解、接受,作为State 汉语对译词之“国家”通过这种涵化得以广泛传播,“国家”所包含的“公家、帝王”以及“国”之“封地、食邑、国都”等古汉语义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何为“国家”?“人有恒言曰‘国家’,世界人类无不范围于国家之中,是故人类之大问题未有过于国家者也。德腊开(Treitscke)曰‘人类之于国家,其重要犹其语言。’故人类不能须臾离国家之组织而营共同之生活[29]7”。“国家有定义焉,国家云者,即人民集合之区域,以达共同之志愿,居一定之疆土,组织一定之政治,而有独立无限之主权者也[30]771”。1903 年发表的“论国家”一文以墨盒与墨的关系进一步解释“国家”与“人民”“土地”的关系:“请以墨匣譬之,墨匣之铜壳譬之土地,墨匣内之墨与丝绵譬之人民。无墨与丝绵,则墨匣无所用,若并墨匣之铜壳而去之,则不见此墨匣矣。犹之但有土地而无人民,则土地无所用。若并土地而俱无之,安得称为国家乎?”[31]11919 年,廖仲恺在《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一文中说:“构成近世国家最紧要的要素,就是人民、领土、主权三件物事,这是近来国家学者的通说”[32]1。《法律大辞典》定义“国家”:“(英)State、(德)Staat、(法)Etat、(意)Stato、(拉)Res publica,国家者,据一定之领土,依一个之主权而统治人民之集团也。由此意义分析,可知国家乃包含领土、主权、人民三要素而成者也”[33]622。
领土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领土对于国家的“作用凡二:其一则在其领土内不容外国之权力侵入,是排斥之作用也。其二则在其领土内,无不应服从本国统治权之人,是充实之作用也”[34]13。国家观念和领土观念有密切关系,“能使国民对领土观念十分强固,然后国家观念才能强固。爱护国家的要素,是要能保持领土,然后才能维护我们在这块领土上生存的人民和建设的国家。所以爱国的第一个责任,是保护国土[35]9”。
主权是国家的重要标志,没有主权,就不成其为国家。“主权之称,始于罗马,其义为最高之上权,或曰至高权。……主权之于国家,关系甚大,故言国家者必言主权。……主权有四要焉:独立不羁,一也;尊严不可犯,二也;至尊无上,三也;独一无二,四也。四者缺一,即失其为主权,是不可以不知也[36]19”。1912 年,朱芰裳“国家主权论”:“国之成也,必自人民有团结精神始。组织政府,执行法律,既绝对不受外来之干涉,又绝对有权力以加乎国民之上,或国内之社会。是故,国家在至尊无上之地位,而国家之权力亦随之而至尊无上。所谓国家权力者,即主权是也”[37]8。
State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主权在民是其重要标志。对于清政府而言,无异于洪水猛兽。20世纪初期,“国家”和“国民”的关系得到全新的诠释,国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这一观念逐渐被大众认可,且日益深入人心。
1907 年,笔名“补天”论述:“国家何所属乎?曰:国家者,人民共同之国家,而非一人专制所得拥为己有者也”[38]5。“作之者言曰:‘无国即无家,无家即无我。’鄙人之意,则以为无民即无国,无主权即无民。无国无民,安有政府?[39]8”一名高等小学三年级学生在回答试题“论国家与国民之关系”时写道:“今夫国也者,国民之代表也。民也者,国家之主人也。国家与国民,犹手足之与头目,互相关系而不可相离者焉”[40]15。
国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才会爱国,国家才会强大。“共和国家由人民组织而成,所以叫做民国。共和国家的人民,都是国家一分子,所以叫做国民。可见人民与国家,是万万不能分开的。……现今欧洲强国,他国的人民到了外国,没人敢蔑视他,只因为他国家强盛的原故,问他国家何以强盛,只因为他国的人民,都能爱国的原故[41]9”。1907 年,《国民的国家观念》一文说道:“若夫国民之国家观念,则国家之荣辱,性命争之,国家之安危,死生以之,身可粉,骨可碎,而国民之性质不能变,山可移,海可涸,而国家之观念不能渝。呜呼!必有如此之国民,始可成立为今世界之国家,而与人竞争生存也[42]64”。“国家是国民的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所以,无论男女老幼都应爱国。如果你不爱国,你就是自己害自己,自己不爱自己。你不爱国,别个国家的人民就要害你。你不爱国,国家就不会富强,不富强就要衰亡[43]41”。
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观念首先进入中国,紧随其后,20 世纪20 年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也得以广泛传播。“国家是阶级对立社会中之一阶级,为抑压他阶级起见,所组织之权力。‘它是支配阶级的一阶级抑压被支配阶级的他阶级之机关。无论在居立政治或布尔乔亚民主国家都是一样的。’(昂格斯)但在阶级独立之社会中,以资本家阶级为支配阶级时,则为资本家国家,以劳动阶级为支配阶级时,则为劳动阶级国家——即无产者独裁之国家。前后两者,于国家之本质上是毫无区别,两者皆系阶级对立社会之所产,皆系存于支配阶级手中的阶级斗争之工具[44]3”。1928 年,叶白华发表“国家是什么?”“马克斯(即马克思)发现‘一切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他的著述《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百七十七页里面说道:‘所以国家决不是由外部课于社会的权力,同样也不是像黑格尔所主张的道义的观念的现实性,理念的姿态及现实性。’国家却是一定发展阶段里面的社会的生产物。……国家一般是强大的,对于经济有支配能力的阶级的国家,这些阶级因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了支配的阶级。同时由这统治的地位,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剥削手段。’……对于国家的结局,恩格斯说道:‘所以国家并不是从太初就存在的。……阶级,同它以前所以发生的一样,将会不可避免地消灭。同阶级消灭一共,国家也将会不可避免地消灭。’……至于国家机构,据恩格斯讲,是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的生产物,是个有限的、相对的。……只有由无产阶级组织他们自己的半国家,在他们的政权底下,彻底地主张自己的阶级的利益,消灭布尔乔亚才能实现[45]9-25”。
State初入中国,即出现“邦、邦国、国、国家”多个汉语译名,表明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汉语语境中难以找到与之一一对应的词汇。而由“邦、邦国”演变而为“国、国家”,且“国,国家”的内涵与其古义大相异趣,表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State认识的不断深化,“国家”一词传入日本后,日本学界借以译介西方国家理论,通过留日学生等渠道又回归中国,这一过程正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缩影。
注释:
①参见拙文《<万国公法>与近代西方国家理论及其术语的输入》(《惠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拙著《京师同文馆输入的国际法术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三章第三节)。
②“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创制的一批对译西方概念的汉字新语,当时在中国并未流行,却很快传入日本,在日本得以普及,有的还被重新改造,至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赴日,把这些新语转输中国,国人亦将其当作‘日本新名词’。其实,这是一批逆输入词汇,称其为‘回归侨词’,较之‘外来词’更为恰当。”——冯天瑜《新语探源——中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91页。
③“近代汉字新语较为普遍的制作方式,是用古汉语词汇对译西洋术语。故其生成机制,是中西概念间的对接、渗透,终于走向‘涵化’的结局。”——冯天瑜《新语探源——中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