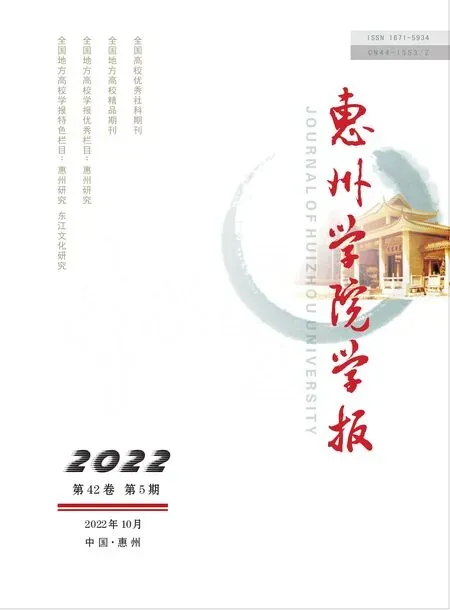中文“新闻自由”概念的早期生成史(1899-1911)
周光明,闫倩玮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新闻自由”是新闻传播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近代中国具有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一个关键词。随着十九世纪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新闻自由观念也逐渐传到中国本土。传教士来华办报活动之初,即留下了《印刷自由论》[1]与《新闻纸略论》[2]这两份重要文本。作为一种外来的新观念,新闻自由最初是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混为一谈的①,但到了清末的最后几年,它开始显露出独立的倾向,并形成“新闻自由”或近似于“新闻自由”的一些概念。到戈公振时代②,新闻自由的专业含义逐渐明确起来。而到1940年代国际新闻自由运动③的兴起,“新闻自由”才真正流行开来。
需要说明的是,新闻自由观念与新闻自由概念不可等而视之。一般来说,观念(idea)在前,概念(concept)在后。先出现某种观念,再形成某个概念。因为有了概念,观念就会变得明确或更加明确(系统化)。概念由词语、语义、语境等要素构成,并通过语法与语句来实现其交流功能[3]。概念的形式是词或词汇,它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这意味着最初往往会冒出许多同类词(词群),“新闻自由”也不例外。“新闻自由”也经历了一个由观念到概念、由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关键词)的演变过程。
“新闻自由”基本上算是外来语,准确地说,它是个日源外来词。最新的研究表明,“新闻自由”一词早在1907年就出现在翻译作品中[4]。此时,“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才使用了不到几年时间,为何还需要“新闻自由”这个新词?近代新名词的引入,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它能被成功地引入,乃是一种创造,是在本土环境中的一种再创造[5]。在这一过程中,域外因素与本土因素交织在一起,而本土因素的作用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大的。
一、“新闻自由”出现的语义基础
大约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来华外籍人士开始通过中英文双语渠道向中国本土输入各种各样的自由观念,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或印刷自由)。当然,中文渠道的影响更为直接。《新闻纸略论》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学界的确认,笔者还有理由相信,它由更早的《外国书论》④而来,然后通过《海国图志》等晚清实学著作让更多的中国读者所知晓⑤。
除报刊文本外,早期的双语词典也值得重视。现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对译情况简单整理如下:Freedom of speech,马礼逊《英华字典》译为“大开言路”,罗存德《英华字典》译为“任意讲之权”,《赫美玲官话》译为“言论自由”。Liberty of the press,罗存德《英华字典》译为“任人印、随人印”,颜惠庆《英华大辞典》译为“印书之自由、出版之自由、印报自由”,《赫美玲官话》译为“出版自由、印书自由”⑥。
虽然英文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观念很早就登陆中国了,但可能受制于“自由”迟到的定译⑦,“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这两个新名词晚至清末民初才出现在双语辞书中。而另一方面,新开辟的日本渠道却后来居上了,横滨出版的康梁系机关报《清议报》大放异彩。1899年4月,梁启超首次提出“言论著作之自由”:“厘定臣民之权利及职分,皆各国宪法之要端也,如言论著作之自由”[6]。同年8月,欧榘甲论及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之关系,认为“行为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三者是并重的[7]。稍后,梁启超又引用密尔(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8]。至1901年12月《清议报》最后一期,梁启超总结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9]。研究近代新词的学者也因此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日语四字词首次进入汉语的文本确定为《清议报》[10]。
严复与梁启超是清末输入自由主义思想贡献最多的本土籍知识分子,尤其是后者,因其借助于新兴的大众传媒,社会影响更大。梁启超的自由观非常丰富,仅以上述之“三大自由”说而言,其表述就多种多样。比如,“一大自由说”:“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11]。“二大自由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12]。“四大自由说”:“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之自由”[13]。作为中国近代新知识体系的主要奠基人,梁启超在自由的观念领域,也毫不例外地展示出其强大的造词能力,比如“文明自由”“野蛮自由”“真自由 ”“ 伪 自 由 ”“ 全 自 由 ”“ 偏 自 由 ”“ 自 由 之 德 ”“ 自 由 之俗”“团体之自由”“个人之自由”等等。总之,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西方近代自由主义观念传入中国后,经过当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接受与转化,为“新闻自由”概念在清末的出现,提供了丰富的语义基础。
二、“新闻自由”的初出例
1902年,作新社出版《万国历史》一书,其第三卷第一章“拿破仑一世后之法兰西”有如下记载: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其弟查尔斯十一世嗣位。时宰相愚昧,专权自私,遂废立宪王政,夺新闻之自由,以恣行其专制政治。人民大愤怒,蜂起而抗王,卒放逐之……
时拿破仑亦由投票得任为十年大统领,遂放逐与己为敌者,夺报纸之自由,以行专制之政治,一仿其诸父拿破仑之所为。⑧
《万国历史》未注明编译者,猜测应是戢元丞⑨。也未标明原著作者,可能是由译者混编而成⑩。引文中出现的“新闻之自由”与“报纸之自由”,意思相同。因日文汉字词“新聞(しんぶん)”即新闻纸之义,也即中文的“报纸”⑪。国人的第一本《新闻学》(1919年)曾如此解释:“新闻纸”之名词,在英文为Newspaper,在日文为“新聞”,国人亦简称曰“报纸”,曰“报章”,曰“新闻”,或曰“报”[14]。1906年,《民报》上再次出现“新闻之自由”:“三大自由:良心之自由,新闻之自由,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其法律之规定,甚重大之件也。制定此等法律,则不可不举可防止伴此自由之弊害措置之权能委诸政府”[15]。此为同盟会方面对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的一场议会辩论所发表的时评。1907年,日本议员神藤才一博士的《欧洲列强近世外交秘史》当年被三次译为中文,原文是: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には聯合国会を停止し、新聞の自由を束縛し、警察権を励行し、波蘭の国語を用ふるを厳禁し、更に猛烈なる大侯爵コンスタンチンをして、波蘭を酷治せしめたり。而して此惨酷なる処置は終に蔑的爾、及普国をして亜歴山帝を誹毁する好材料を得しむるに至れり。[16]
外交报馆的译文是: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停止联合国会,限制报章自由,禁用波兰国语,复以残忍成性之君士坦丁侯爵,治理波兰,密布警察以资讥禁。于是梅特涅及普国人民皆诋毁之。[17]
新译界社的译文是: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停止联合国会,束缚新闻自由,厉行警察权,严禁用波兰国语,更举猛烈手腕大侯爵孔斯镇酷治波兰,而此残酷处置,终使梅特涅及普国得诽谤亚历山大好资料。[18]
达达社的译文是: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既其联合国会亦停止,束缚新闻之自由,厉行警察之权利,禁用波兰国语,且使猛烈之大侯爵控斯但清酷治之。夫如是之残酷处置,又安不使梅特涅及普国得诽议亚历山帝之好材料也耶。[19]
原文“新聞の自由”被分别译为:报章自由、新闻自由、新闻之自由。笔者曾推测“新闻之自由”为日文“新聞の自由”的直译[20],现在终于找到了确切的证据。相信前引《万国历史》与《民报》时评中的“新闻之自由”原文也应是“新聞の自由”。而“新闻自由”则为“新闻之自由”的缩略语,换句话说,“新闻之自由”可视为“新闻自由”的短语形式。也即:“新闻自由”来自“新闻之自由”,而后者又来自“新聞の自由”。当然,“报章自由”的译法也没错,因在清季民初,“报纸(或报刊)”多被称之为“报章”⑫。
三、“报章自由”或更具本土意味
在1905年1月20日的光绪朝外交档案中,已出现了“报章自由”的表述:
英国司丹达报俄京访事人云,罢工者已集议三次,除要求每日作工八小时外,并决议要求与日本停战,大赦公罪之犯,报章自由、信教自由、会集自由等款。[21]
这条电讯稿来自英国路透社。在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为了解日俄两国政情及战况,逐日接收路透社提供的有关新闻电报,交外务部人员进行翻译,作为中枢外交决策的重要参考[22]。由于相关档案的缺失,当时发出的电文已无从查考,但文中提到的司丹达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确曾发表过一篇题为Great Strike in Russia的文章,且内容与电报基本一致,原文如下:
The young priest who initiated,and is now leading,the whole movement addition to the usual demands for the eight-hour day and higher wages,the meetings passed resolutions embodying the following political programme 1.The immediate convocation Constituent Assembly,elected universal suffrage;a Cessation of the war in the Far East;& A complete amnesty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exiles;liberty of the Press and of conscience;&Freedom of meetings and associations.[23]
电报中“报章自由”的英文表述应为“liberty of the press”,也即如今的“出版自由”。事实上,至迟1830年代初,广州出版的英文报纸《中国差报》和《广州纪录报》已将这种出版自由的观念带到了中国[24]。“liberty of the press”首次进入辞书时,德籍传教士罗存德译其为“任人印、随人印”,或“任意写印”。如此翻译,仅为一种说明性的陈述,离其“词化”尚远[25]。1899年8月,梁启超显然照搬了日语的“出版の自由”,形成新的中文词组“出版自由”。1902年《万国历史》的译者使用了“报纸(新闻)之自由”的短语。而1905年初,不知其名的外务部译员则首次使用了“报章自由”。
1906年出版的《政治讲义》中使用“报章自繇”,也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译者严复在该书第六章讲解了三类自由:
总而覆之,见世俗称用自繇,大抵不出三义。一、以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牵掣干涉为自繇。此义传之最古,于史传诗歌中最多见。二、以政府之对国民有责任者为自繇。在古有是,方今亦然。欧洲君民之争,无非为此。故曰自繇如树,必流血灌溉而后长成。三、以限制政府之治权为自繇,此则散见于一切事之中,如云宗教自繇、贸易自繇、报章自繇、婚姻自繇、结会自繇,皆此类矣。而此类自繇,与第二类自繇往往并见。[26]
据研究,《政治讲义》一书主要参照了剑桥大学教授约翰·西莱爵士的《政治科学导论》[27]。西莱的原文是: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is the principle most strongly asserted,but when the power of church courts is limited,when religious toleration is introduced and dissenting worship is permitted,when the Licensing Act is allowed to expire,and so the Press acquires freedom,in all these cases we see government not submitting to responsibility but limiting its province.[28]
“报章自繇”对应的是“Press acquires freedom”,直译为“报纸获得自由”或“报纸得以自由”。从这段引文来看,严复对其增改颇多,难怪他自称“纂述”,而不称“译著”。严复对“liberty”“freedom”的中译一直是很讲究的,大致经历了由“自由”到“自繇”再回归“自由”的变化。至于中间为何改用“自繇”?概言之,一求古雅,一依西例⑬,一避时忌,一抗俗论⑭。但最终他仍为时代潮流所扰,不得不从俗了。1905至1906年间,正处于从“自繇”改回“自由”的节点上,《政艺通报》连载其《政治讲义》时,用的就是“报章自由”[29]。但无论是“报章自由”还是“报章自繇”,严复都是最早的一批使用者之一。
在实践方面,“除了在生长过程中,同化物可以再分配再利用,人们发现,收割后作物贮藏期间茎叶中的有机物仍然可以继续转移。这一特点在生产上被充分利用。例如,北方农民为了减少秋霜危害,在霜冻到达前,把玉米连杆带穗堆成一堆,让茎叶不致冻死,使茎叶中的有机物继续向籽粒中转移,即所谓‘蹲棵’。这种方法可以增产5%~10%”[《植物生理学》(中国林业出版社)(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174页)]。北方农民为防霜冻而采取的“蹲棵”办法,就是“同化物具有向库性的这个原理”的具体运用。
四、从“报章自由”到“报馆自由权”
与前述翻译语境中的“报章自由”不同,清末著名报人汪康年赋予“报章自由”以新的意义:
日前某报略谓:居辇毂之下,多所顾忌,故不能畅所欲言云云。按此说误矣。报章之自由,固无有如今日吾国之京城者,上自王公,下至编氓,任意诋毁,莫或过问,甚至加人以极不堪之名目,诬人以无理由之事实,或形容闺阃,或演说隐匿,而莫或与辨,一任诪张。吾谓言论自由,此为最矣。[30]
此处的“报章之自由”,也即“报章自由”或“报章自繇”,在1905 年至1907 年间,已有多次使用,甚至在更早的《万国历史》中译本中也能看到它的身影。但在汪康年笔下,它并非一个借词或译语。此前,《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8月)、《钦定报律》(1911年1月)已经颁布实施,清政府承认了人民享有一定的言论、著作及出版等多项自由。某种意义上讲,报章的出版自由问题已经解决,但汪氏认为,报章的言论自由还存在很多问题,不是“不能畅所欲言”,而是出现了“任意诋毁”,太过自由了。这种自由观诚然具有较多的中国本土因素,但他强调“报责”“报识”,则是很有远见的。监督政府的报馆自身也需要被监督[31],从而凸显了报章(或报馆)的主体性。
1905年初,还出现了“报纸言论自由”:“俄京圣彼得堡各工厂同盟罢工之事,察其情形,并非关于商务,实为政治起见,伊等要求,即一复百姓之各项权利,二舒百姓贫困,三去资本家之压制。此外,尚有数大要求,为万民同仰之教育自由、报纸言论自由、信教自由、聚会自由,及设立代议政体”[32]。“报纸言论自由”也写作“报纸言语自由”,后者也称“报纸(报馆)言语自由权”[33]。
从权利的角度理解自由观念是很重要的。严复之所以“旬日踟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自由(或自繇)”其实在的一面,即它是一种权利(right)⑮。实际上,十九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很重视自由观念中的法制意识与权利意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34]”。“自主之理”即自由、自由精神、自由主义⑯。“例”即“国之律例”,国法也。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法无禁止即自由。至于权利意识的表述,当时的材料也不少,仍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例。“自旧王之除以来,佛兰西人自主倜傥,大开言路,自操其权[35]”。讲的是法国的言论自由。“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开诸阻挡,自操权焉[36]”。讲的是英国议院尊奉自由之原则。《罗存德字典》译“freedom of speech”为“任意讲之权”。至《清议报》时代,国人已经接受了自由权的概念,要求发挥“人民天赋自由之权”[37],梁启超更是宣传自由与权利的同一性:“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11]。稍后,一张很有影响的通俗报纸呼应道:“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做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权,我们都应该享受的”[38]。1908 年初,《大清报律》出台,报界反应激烈。《申报》发表评论说:“中国预备立宪后,首以剥夺报馆自由权为急务”[39]。二天后,《申报》再次提及“报馆自由权”:“近自葡皇及皇子被弑,新王先以回复报馆自由权为急务。自皖抚被刺,虽有庶政公诸舆论之旨,未几而箍制学生束握舆论之谕下矣,未几而严定报律之举行矣。此制造革命党之一征也”[40]。
从新闻法的角度谈论言论自由,是清末新闻自由言说的一大特点。清末新政启动之初,针对中央正酝酿起草报律的传言,有识之士就提醒政府注意中西立法精神的差别:“外国之定报律也,盖先允民间之自由出报,先予民间以言论之自由,然后再设以范围使不致过流于悖谬;中国之定报律也,盖极不愿民间之自由出报,极不愿民间得言论之自由,于是托以仿照外国之例,趁此严加束缚,使业报者渐即消亡而不敢大张旗鼓”[41]。至清末,既是报人又是学者的章士钊援引英国专家的观点如此界定二大自由:“言论自由者,乃谓凡人可以发表其意见,不受国家之检阅。”“出版自由者,谓无论何人可以任意出版,无需国家之特许也。”并从法理上论证了检阅(事前接受检查)和保押费(提交保证金)之为“有罪推定”[42]。另一方面,从清末的新闻实践上看,已经涉及了读者的阅读自由[43]和记者的采访自由⑰,可以说,“新闻自由”已开始了它的概念化。
五、结语
“新闻自由”的观念史始于近代报刊登陆中国之初,至清末最后几年,不仅出现了这一新名词,也开始了它的概念化进程。所谓概念化,本文指的是它不仅仅作为一个新名词,它还初步具备了“高级词语”的某种性质[44]。当它一进入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就开始生成自己的意义网络。它最初从属于“自由”的下位概念“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换言之,可以把清末的“新闻自由”理解为“报纸的言论自由”与“报纸的出版自由”。与此同时,它还拥有自己的同类概念:报纸自由、报章自由、报馆自由以及报馆自由权等,并开始派生出“采访自由”⑱“阅报自由”⑲等专属于自己的下位概念。
“新闻自由”概念的英文表达为“liberty of press”或“freedom of press”,但它与“freedom of speech”关系密切,不可分割。大致来说,到了戈公振时代,“新闻自由”概念开始具有一定的国际新闻传播的语境,而到了1940年代的国际新闻自由运动时期,它不仅具有更强的国际传播的语境,而且内涵更加丰富,其所包含的“freedom of information”(情报自由、信息自由)意义凸显出来了[45]。但是,中文“新闻自由”同时具有浓厚的日源词色彩,形式上它是从“新聞の自由”而来,证据确凿。其情形类似于“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等从东洋而来的日语四字词。“新闻自由”实为近代中西日文化互动的一个结晶体。
自由有两种指称,其一指政治方面的保障,即权利;其二指某种精神状态⑳。本文的“新闻自由”主要指自由的第一种含义。当然,无论是新闻自由观念还是新闻自由概念,因其牵涉广泛,含义演变的过程十分复杂。笔者删繁就简,先从清末入手考察,而对“新闻自由”的界定,则较倾向于其狭义,即所谓的三项自由:“采访自由、传递自由、受授及发表自由”[46]。
从1902 年“新闻之自由”的出现,至中华民国成立,不过十年时间,仅为其生成史的一个片段。自民初起,相关语料逐渐增多,又出现了“出报自由”[47]“报纸自由权”[48]“报界自由”[49]等词汇,至1927年戈公振再次使用“新闻自由”[50],这一时期(1912-1927)“新闻自由”概念的具体演变情况,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迄今三者之间的关系仍然存有许多争议。参见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70-72页。
②戈公振(1890-1935),中国近代第一批新闻学家中的重要成员,编著有《新闻学撮要》(1925)、《中国报学史》(1927)等。本文使用“戈公振时代”,指称中国近代新闻学的草创期。
③1944年4月,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倡议在全世界范围推广新闻自由原则,当时中国新闻界对此热烈响应。
④《杂闻篇》,马礼逊主编,1833年8月。笔者初步判断,《外国书论》与《新闻纸略论》为同一作者,或《新闻纸略论》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编者据《外国书论》改写的。
⑤“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出于意大里亚国。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海国图志》四卷本,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56页。此处引文虽标明出自《英吉利国夷情记略》,其实叶钟进的《寄味山房杂记》也参考了《东西洋每月统记传》。
⑥参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华字典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1815至1919年间各类辞书共计24部。
⑦严复曾为“liberty”的汉译大费踌躇,虽新创“自繇”一词,但仍觉不甚妥当。1899年他将密尔的On Liberty一书译为《自繇释义》,1903年出版时改名为《群己权界论》。参见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1页。此外,“自主”“自治”等词也具相当的竞争力。
⑧作新社《万国历史》,1906年版,第189、190页。1906年版为此书的第11版,初版在1902年6月。
⑨戢元丞(1878-1908),名翼翚,湖北房县人。1896年成为首批官费赴日的留学生。参见邹振环《戢元丞及其创办的作新社与<大陆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106-116页。
⑩有学者也认为,该书“取日本当时各种最新历史著作编译而成”。参见吴小鸥、石鸥《晚清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5期,第89-96页。
⑪新聞(しんぶん),新闻纸之略语。新聞紙(しんぶんし),报纸。参见作新社编《东中大辞典》,1908年版,第567、569页。
⑫“报纸”与“报章”,均出现于1870年代。“报纸”稍早一点,初见于1873年1月4日的《申报》,“报章”初见于1874年6月18日的《申报》,但“报章”的说法在晚清要正规一些。参见周光明编《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新词词源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7页。
⑬严复认为,由、繇虽为通假字,但“自由”较“自繇”为虚,“自繇”较“自由”为实,故“依西文规例”,改用“自繇”,以“略示区别”。参见严复《群己权界论》之《译凡例》,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27页。
⑭参见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第三章“为自由正名:《政治讲义》理论意义之二”,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⑮以“权利”对译“right”,仍有争议,因为前者不具备后者的一项重要含义“正当”。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104页。
⑯十九世纪初中期,freedom、liberty多译为“自主”,且存在从“自主”到“自由”的翻译走势。参见冯天瑜、聂长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0页。
⑰“外务部对各国访事,无不招待,独中国报馆访事往则不理。”(《民立报》1911年2月11日)。据研究,1907年清廷民政部已批准记者旁听司法审判,1909年各省咨议局均允许记者旁听辩论。参见殷莉《清末民初新闻出版立法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198页。
⑱“采访自由”虽然出现较晚(《大公报》1944年11月21日),但相关的表达清末就有,此后逐渐增多,比如,“公共场所记者自由出入采取新闻”(《申报》1927年4月11日)。
⑲“阅报自由”初见于赵雨时的《北平晨报社论集》,1933年第26页。
⑳两种自由分属不同的意义系统,第一种自由其意义十分明确,第二种自由则从无公认的标准。参见张佛泉的《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下篇《自由与人权》的第二章“自由之确凿意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