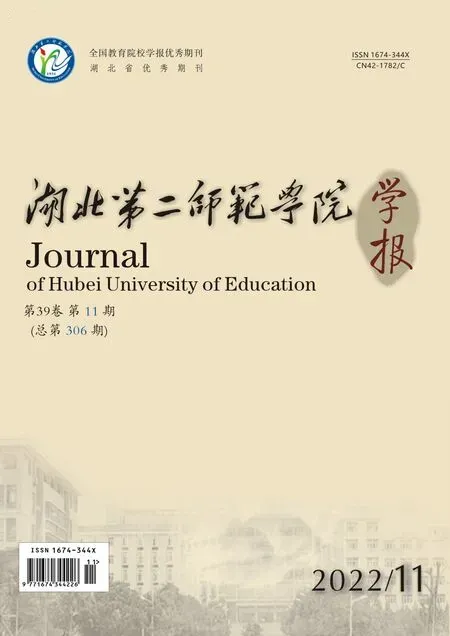云南地区说唱艺术的传承
杨柳琴
(阜阳师范大学 音乐舞蹈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按照民俗学家所强调的表演性定义,说唱艺术属于作为交际的口头文学模式。[1]按照中国曲艺界给出的概念, “说唱艺术是指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表演的艺术形式的统称”[2]。以《曲艺概论》中给出的解释看,侯宝林等一众中国老辈曲艺家直接将曲艺界定为 “民间的说唱艺术” 。[3]对于云南说唱艺术的研究,本研究更倾向于运用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给出的民俗叙述风格中的结构制定,在表演的新生性理论之下,关注特定地域、特定文化范畴、特定语境中的艺术文化传承脉络,并将说唱艺术这个特定语境下的交流事件作为观察、描述和分析的中心。
云南说唱艺术作为一个富有地方语言魅力且与云南各民族民众生活紧密联系的口头艺术形式,它的传承、发展正面临岌岌可危的存续危机。与此同时,基于曲艺艺术根植的社会背景、人文环境,对云南少数民族说唱艺术的研究、观察、分析、保护与传承,务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起源、历程、传承困境进行文献研究和民族志考察,如此才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对董秀团先生于《说唱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所提出的 “曲艺新生” 号召进行传承实践。
一、云南说唱艺术的起源:仪式艺术
古时,人们思想认识混沌未开,对自然界的诸多不可认知事物素有敬畏之心,所以面对灾祸或遇到节令时会举行一些祈福驱魔、祭天祭祖等仪式性活动,云南地域少数民族亦不例外。在很长时期内,云南各少数民族会在各类仪式活动之中讲述人类起源、神明开天辟地的神话或者先祖事迹等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举行仪典的祭司、巫师、族长便有了展示说唱传统的舞台。故而在因循传承之下,这种具有 “仪式” 意味的说唱活动,附带着神圣、神秘的色彩,保留于云南地域各少数民族的神话史诗说唱艺术之中。对云南说唱艺术起源于云南地域各民族的宗教、仪式活动的论断与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例如从彝族的《梅葛》、拉祜族的《牡帕密帕》中的说唱内容可获悉,具有仪式意味的仪典性说唱传统,是云南各少数民族的规矩与讲究。[4]
在云南地域本土的原始土著少数民族之中,说唱艺术以一种自然形态的、极具趣味性的、甚或有宗教意识或教化意味的方式存在。至今保留完整、传承未曾中断且受外界社会文明进程发展影响极小的当属云南藏区民间说唱艺术,如 “百协” “例” “擦丫” “折格” “芭例” “惹姆” ,这些源于一千多年前的仪式性歌卜(藏区神话史诗说唱),民族色彩与地域色彩浓厚,艺术性极强,极具生活趣味。下文将对 “百协” 这一歌卜形式做展开性描述,以此,借助杰当·西饶江措对云南藏区民间说唱艺术的调查,我们或可管中窥豹一睹云南地域横断山脉藏族仪式性说唱艺术的风采。[5]
“百协” ,在云南藏语中意为激励,是古时战争之中做战前动员之用,藏族人民称这种说唱活动为宝剑颂,表达主题非常明确,即举剑誓师激励士气。在藏族传唱千年的神话史诗《格萨尔(斯)》[6]中描述,格萨尔王菩萨于凡界之中降妖除魔,于强盗贼寇手中拯救弱小,在其征伐统一各个部落之时有一项传统,即,每每在兵戈挥指之前,英雄格萨尔王都要举行这种盛大恢弘的动员仪式。在藏区民众因循传承之下,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凡送宝剑、凡遇战事亲属同谊之间必要说些激励之词的传统。一般在表演颂剑仪式之前,百协说唱艺人(藏族传统只准男子充任)都要身着藏袍,头戴 “苏夏” 帽,手持藏式宝剑,舞跳说唱。区别于娱乐表演仪式,以军前动员为目的的百协颂剑仪式没有乐器伴奏,只有气势磅礴、恢弘正气的人声颂鸣,后来百协中又加入了舞剑动作,这使得其艺术感染力更为富有雄性威猛倾向。百协的说唱内容一般分为三个主题:佛颂、宝剑颂和英雄颂。佛颂,颂美三宝和日月星辰;宝剑颂,颂述宝剑的铸造、淬钢过程及其装饰;英雄颂,颂扬格萨尔王、三军将士及宝剑威力。如英雄颂片段歌唱: “英雄男儿持此剑,不怕四方敌人强。宝剑若是指东方,不怕东方敌军强,宝剑一挥全灭亡,/宝剑若是指南方,/不怕南方敌军强,/宝剑一挥全灭亡,/………好呀!好呀!真是好!颂剑!颂剑!颂宝剑!” 百协这种颂词式说唱是七音节格律,词文内容可长可短,依场合情境可自由变换,它的说唱内容以颂剑为主,但不限于此,其内容还可以颂诸一切如:刀、弓箭、战马及出战勇士等。百协仪式对颂演者的即兴创作能力要求非常高,他们有诗人的才华,具备大量民歌、谚语、历史故事、哲理知识的底蕴,加之表演技巧的助力,这些说唱艺人可以活灵活现地向人们吟诵神话史诗故事而备受民众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在表演过程中基于神话史诗但又不局限于曲本的即兴表演更具有趣味性,也更能带动表演氛围。按照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表演的新生性与创造性理论(emergent quality of performance)解释,正是因为表演的新生性特质使得表演者的个人能力、参与资源(颂词)和参与者(盟誓将士)在这种互动之中,构建起了惯常化的表演的结构性体系。[7]
二、云南说唱艺术的流播:语言艺术
云南说唱艺术的流播缘于各民族因循承续的日常生活语言。说唱艺术作为一种交流模式,能够广受欢迎与当地的民族生活习俗息息相关。云南各民族的说唱艺术是云南各民族民众最为日常、最为欢愉、最为热闹的民俗活动,是云南各民族民众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如傣族的章哈、哈尼族的哈巴、白族的大本曲和 “吹吹腔” 等等,民众邀请说唱艺人来了(实际是艺人四处游荡所致),并不讲究什么场合、时节、地点,村口草台、镇市集口甚或井台沿、大树底下,说唱艺人们就可出口成章,颂扬成文。通常是艺人 “唱完这个村,又走进那个寨” ,有名头的艺人通常出门后把附近的村村寨寨逛唱完之后才能回家。按照将口头艺术看做交流的观念,民俗学派会认为这样的说唱形式已经具备了表演的性质,因为他们对表演本质的定义决定着他们大致会视这种说唱为一种交流的方式(a mode of communication),从而将这种口头艺术理解为表演。其实不然,首先这种说唱展演形式在非民俗活动中也可以惯常性地进行,它是少数民族联谊、获悉外界消息、精神娱乐的日常消遣,它超越民俗活动范畴而存在于当地民众的生活日常;其次,它与完全舞台化的职业性质的表演也有区别,表演者与观众是一体的,他们互相愉悦,他们是在特定的语境、特定的文化习俗、特定的场合、特定的社区之中存在,其说唱的形式、内容(曲目)仍然主要是因袭传承下来的仪式性颂歌,纯粹性的娱乐表演较少。
以白族乡戏 “吹吹腔” 作为研究样本,我们可以发现,云龙吹吹腔在口头传说阶段,白族先祖因为别族人咒骂白族人野蛮、未开化、没有文字,所以在劳动之余不断研究,以紫金竹为杆做唢呐,以落落腔为基调,最终以 “吹吹腔” 的形式通过言传身教传承了本民族的文化与习俗。[8]就像《三出首》演出的形式,村民们请出财神、魁神和赐福天官之后,艺人才开始吹吹唱唱,所演内容也多是请神、谢神,这样的说唱更多的有传承文化的意味,是融于百姓日常生活的,也是融于百姓的美好愿望的,它不限于民俗活动,又不具备完全舞台化的纯粹娱乐性质的表演特征。因此,这样的说唱表演可理解为语言媒介下的民众的日常生活展演。
三、云南说唱艺术的传承:表演艺术
云南说唱艺术起源于仪典性的说唱颂歌,流播于各民族因袭相传的各项民俗活动,发展于具有舞台范式与一定戏曲程式性的舞台表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升级,演唱艺人们由以往的兼业化发展出现了向职业表演转变的趋势。换言之,说唱艺人们由民俗活动的参与者和表演者双重身份,逐渐衍化为舞台剧场中 “表演者-观众” 模式的单一的表演者身份,观众也不再在街边巷口的草台边集中观看表演,剧场或文化广场成为了特定的表演场所。表演的内容经过广大民众的长期的参与、加工与再创造,曲目、腔调、内容都渐渐脱离史诗神话说唱的核心。随着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很多艺人顺势在新媒体爆发的时代环境之中开始发行说唱的音频、视频,而且在电视台、网络传媒平台、社交平台的相关节目之中也有艺人亮相表演。各地政府出于保护、传承与发展的目的,也由成立专门的剧团转变为多向度的多元化促进发展,现时代云南说唱艺术剧团剧场演出、走场演出、传媒视频录演并行,一派生机勃勃。
以云南大理白族地区大本曲为观察样本,我们可以发现,云南大本曲的流传历史、流传地域、传承场合、传承媒介、艺人生活状态等无不与上文描绘的概况类似。
大本曲的起源早在明代的《白族文学史》《大本曲简志》中就有笔墨确切提及。及至清代,被称为 “南腔始祖” 的老艺人杨旺将其发扬,大理上湾桥杨华得以传承,并于 “探牢狱” 中运用 “五更调” ,如泣如诉、哀婉悠转的深情表演感动观众,名噪一时。1949年以后,大本曲仍流行于白族民间,经过 “文革” 暗淡时光后,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转折期,并借电影、电视等现代媒介重新出现在民众视野。大本曲曲折的 “断代式” 发展史,使得其丧失了本土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拥趸,其宗教、祭祀的功能也大大弱化,大本曲艺人因而也失去传承根基。白族大本曲的时代遭遇并不是个案,云南各民族说唱艺术的发展史多与其类似。如何解决传承问题,成为影响云南说唱艺术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于大本曲的流传地域,因与全局视角的说唱艺术传承内涵无关,且各民族说唱艺术先天自然存在地理环境的差异,所以在此不再展开。但大本曲的传承场合与白族的民俗传统密切相关,这使得大本曲的传承有了落脚点。场合,一指时机、时令、时节等因素;二指空间环境因素。一般在白族民间流传俗语中有 “三月三开曲头,唱到九月九” 一说,这是指大本曲的演唱时间,其中白族的火把节(农历六月二十五)也在上述期限内。这样的演唱时令传承,恰是农闲时节,这也意味着参与的人更多,所以有了作为集体活动的民俗事件开展的条件。其外,婚丧嫁娶时也符合民俗开展情境,所以大本曲既有《富罗白寻母》《三下阴曹》等与鬼魂相关的丧葬曲目,亦有《蔡状元造洛阳桥》这样的喜庆曲目。从空间角度分析,大本曲既在开放性的广场、晒场、戏台中演出,也在家庭庭院、厅堂中演出。由此可见,大本曲的传承场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十分紧密,娱人、娱神的文化消费功能使得其留存在民间更多地保留了生活气息。
大本曲传承的媒介有语言与文字曲本两种形态,其中,现场即兴发挥式的口头展演是基于语言媒介;曲目记录是基于文字媒介。鉴于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的 “表演的新生性与创造性” (emergent quality of performance)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笼统地理解大本曲基于口头的语言传承媒介是无固定形式的,但是它为我们理解白族社区普遍文化体系的表演语境(the context of performance)中特定表演的独特性(uniqueness),提供了途径。毕竟大本曲艺人限于文化程度较低不可能脱离口承方式,所以研究大本曲艺术也不能将视野局限于案头文学。由此,我们可以下一个粗略的定论,白族大本曲有关结构性的、惯常的表演体系的民族志构建,基于纸媒传承常常描述标准化和均质化的表演内容。与之相反,口头临场表演每一次都不是相同的,最为重要的是观众在欣赏表演时乐于欣赏到每一个表演的独特个性,同时这也能证明在白族社区内大本曲表演具有相对的 “模式性” ,如固定的唱腔、身段、表情、动作以及特定的与观众的互动、交流方式等等。这也是其能够延绵至今仍具艺术表演活力的根本所在。大本曲的传承曲本在材质、形式、格式等方面都遵循着大致的规范,如高腔标示、汉语和白语发音转换的标示等,这种简单的画以圆圈、波浪线的提示经常在流传的曲本上出现。我们可以获悉的是,曲本是大本曲区别于一般的歌谣、传唱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从董秀团在《云南大理白族地区大本曲的流播与传承》中关于大本曲艺人分布状况、性别结构、年龄结构、艺人演出收入状况所作的情况统计表来看,随着艺人的减少,大本曲在民间的生存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总之以大本曲作为个案透视云南各族的说唱艺术传承状态,我们可以基本确定的是大本曲自产生至今,在民间几历盛衰,其流传地域较为固定,始终集中于云南洱海地区的白族社区,其传承场合与年节、民俗活动密切相关,但随着艺人减少其传承面临存续困境。曲艺艺术传承的根本在于人,将白族大本曲的个案研究放诸云南全境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云南说唱艺术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文化传承丧失了人文根基,失去了社区民众的支持,导致说唱艺术在民间逐步凋零。
四、云南说唱艺术的发展:革变新生
云南说唱艺术的发展目前呈现出地域不平衡、民族不平衡的趋势。由于云南的民族种类纷杂多样,各民族在其共生共存的同时源于生态环境、历史发展、社会背景、文化传统、地域经济水平的差异性,各民族的说唱文学及相关的说唱艺术形式渐趋失衡。方李莉指出: “经济富足的地区,随人们精神文化的消费升级,脱胎于说唱艺术的云南戏曲类艺术的发展越是繁盛,表演形式也花样繁多,有固定的剧场、剧团及特定的观演群众支撑。经济不发达的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处于横断山脉的高海拔贫瘠狭窄的山区,山歌非常发达,山民村民们随走随唱,说唱是民众拿来自娱自乐的,当然,此区的说唱艺术形式相对原始,与祭祀、宗教、婚恋习俗等也有较大的关联,多是处于吟诵、叙述等初级阶段”[9]。
在文化层面,由于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大,现时代的云南少数民族说唱艺术面貌脱离了单纯的吟诵和叙述,趋于向较为完备的综合性表演艺术方向发展,演唱内容也由过往以《格萨尔》《牡帕密帕》《梅葛》等神话史诗为主加入了不少世俗曲目,这种表演形式的多样化、表演技巧的成熟、表演内容的拓展与汉属文化的影响深切相关,侧面也反映了说唱艺术的包容性与自我革变特性。曲六乙指出: “白族吹吹腔是戈阳腔遗脉,壮族师公戏受汉族傩舞影响,侗族黔剧有花灯的遗痕,藏族格赛尔受蒙古族呼麦影响。”[10]可以说,戏曲表演代表的是比原初的说唱艺术更为成熟的发展形态,两者笼统意义上可以被认定为 “艺术表演形式的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 ,如白族的传统民间叙事长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衍变为大本曲,受到汉文化中的变文、俗讲、说话、宝卷等说唱形式的影响,云南各地域少数民族的说唱艺术形式发展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向 “综合性的舞台范式” 方向迈进。云南地域少数民族说唱艺术整体上讲,如傣族的哈尼、哈尼族的喊半光等说唱形式,其本土题材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虽则受汉族文化影响颇重,有朝向综合性的舞台范式方向迈进的趋势,但是相较京剧、昆曲等类极尽完备丰富的艺术表演形式,其题材仍较为单一且明确,即主要取自传统神话史诗的本土题材,间或有少量的婚恋习俗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承中华文化在于古为今用,在于辩证取舍,在于推陈出新和继承积极思想。云南地域说唱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亦当遵循此规律,要在中国曲艺 “一体万殊” 的格局之下,重塑传统曲艺的人文根基,使其重回民众的民俗生活,赓续中华文明精神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