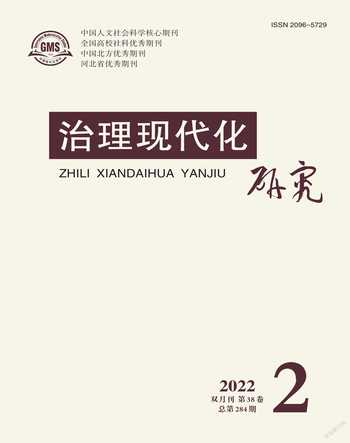格拉斯哥会议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特征与趋势
王谋 吉治璇 陈迎
摘 要:格拉斯哥会议是继2019年马德里会议后举行的第一次正式气候谈判会议,也是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参与的第一次谈判会议,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格拉斯哥会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达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在适应资金、碳市场、1.5℃目标以及退煤等问题上达成了广泛共识,同时也开启了《巴黎协定》全面实施的进程。本文梳理和分析了格拉斯哥会议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格局、特征和趋势以及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就我国应对新形势、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提出建议。
关键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格拉斯哥
中图分类号:X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2)02-0089-08
随着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认识的不断推进、全球环境意识的不断提升,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一方面,美国总统换届以后,民主党一改共和党政府消极的气候政策,不仅重新签署《巴黎协定》,还积极推进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进程在内的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另一方面,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逐步成熟,全球能源转型步伐加速,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也给各国注入更多信心,许多国家纷纷提出更具雄心的减排目标甚至是碳中和目标。这些新的国际形势,共同推动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关注由低谷走向热点,在格拉斯哥会议前后达到国际关注的高点,并促进达成《格拉斯哥气候协议》。格拉斯哥会议后全球气候治理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梳理和研判这些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对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进程,既维护发展权益又体现大国责任担当具有积极意义。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程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展历程及主要里程碑
为了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试图采取全球协作的形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多方努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终在1992年5月获得通过,同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的154个国家以及欧洲共同体的元首或高级代表共同签署,于1994年3月正式生效,奠定了世界各国紧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基础。
《公约》的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并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
由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仅是一般性地确定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浓度目标,没有明确不同阶段的实施目标,需要就不同阶段更加具体的目标开展谈判。因此,在第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1,1995)上,各缔约方就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阶段性执行协议开展磋商,并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COP3)上达成了《公约》的第一个执行协议,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首次为附件I国家(发达国家与经济转轨国家)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目标,并引入排放贸易(ET)、联合履约(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三个灵活机制;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公约》第13次缔约方会议(COP13)上达成《巴厘行动计划》,勾画了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路线图和基本框架,也将游离于国际合作之外的美国拉回谈判轨道。2011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第17次缔约方会议(COP17)形成德班授权,开启了2020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进程;2012年,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公约》第18次缔约方会议(COP18)明确了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包含美国在内的所有缔约方就2020年前减排目标、适应机制、资金机制以及技术合作机制达成共识,并形成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决议文件;2015年,在巴黎气候大会(COP21)上,由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各方大力推动而达成的《巴黎协定》基本明确了2021—2030年期间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安排和合作模式;2019年的马德里会议(COP25)和2021年的格拉斯哥会议(COP26),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国际气候治理由此转入以《巴黎协定》履约为主的实施进程。
(二)《巴黎协定》概况
《巴黎协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21—2030年期间的执行协议。该协定于2015年12月在《公约》缔约方第21次会议期间达成,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巴黎协定》是继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之后,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达成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条约。《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将全球相对于工业革命前温度水平的平均气温升高控制在低于2℃以内,并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之内,从而大幅度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危害”2。2021年11月,在英国举行的第26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完成了对《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巴黎协定》是在变化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下,为实现《公约》目标而缔结的针对2020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法律文件。
(三)格拉斯哥会议的情况
格拉斯哥会议是继2019年马德里会议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进程几乎停滞两年后举办的谈判会议。大会的特殊性还表现在,这是新冠疫情开始后,全球环境治理领域举办的第一次大规模现场会议,也是美国回归《巴黎协定》后参与的第一个缔约方大会。格拉斯哥大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自然会被赋予更多的期待。联合国系统,包括公约秘书处、联合国秘书长以及主办国英国因为疫情推迟举办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也因此赢得更多时间筹备会议。格拉斯哥会议参会人数不仅达到4万人[1],还邀请到了包括中国、美国、欧盟、印度等多國元首发表致辞,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进行全球政治动员,提出更具雄心的贡献承诺目标。会议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中尚未达成共识的议程项“市场机制”“透明度”“共同时间框架”等问题进行了重点推进,并就以上议程和包括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议题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将国际气候治理进程推进到《巴黎协定》全面实施、履约的阶段。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格局
(一)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体的多元主体治理框架
全球气候治理是以各主权国家为主,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通过气候公约机制和公约外机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模式。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限制发展空间,影响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也可能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机遇,因此,各国均给予高度重视,并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人类社会必须理性地通过国际制度安排应对气候变化,明确各国应承担的责任,同时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与保护全球气候的共赢。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方包括主权国家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主体等。主权国家政府是主要参与方和治理主体,在考虑本国诉求和发展情况的条件下,通过气候谈判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功能是协调各国利益,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UNFCCC)为核心,同时也包括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联合国环境署(UNEP)、国际能源署(IEA)、清洁能源部长会议(CEM)等相关组织;非国家行为主体包括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非政府国际组织、社会团体、企业以及个体等,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谈判等气候治理活动,影响政府决策,一方面也是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负责实施行动的主要承担者。
(二)公约内和公约外机制相互补充
从1979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召开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呼吁保护全球气候,到1990年国际气候谈判拉开帷幕,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逐步进入了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主要分为气候公约机制和气候公约外机制两大类,公约外机制包含了定期的、不定期的、国际的、区域性的、行业性的、专业性的多种机制。所有的这些机制因其不同的定位和功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气候公约机制。1992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开放签署,1994年3月21日《公约》正式生效,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法律基石。随后,各国基于联合国平台开展谈判,并先后達成《京都议定书》(1997年)《多哈决定》(2012年)和《巴黎协定》(2015年)等重要成果,明确了在《公约》框架下不同时期全球合作开展气候治理的阶段性目标和全球气候制度框架,明确了全球合作方向和路径。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在联合国气候公约引领下不断前行,气候公约也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平台,并通过各方努力,不断巩固和形成各国开展气候合作国际法律基础。治理气候变化问题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需要坚持和完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合作平台,巩固和发挥气候公约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保障气候安全。
气候公约外机制。为了推动气候公约谈判,国际社会在气候公约体系外也建立了多种机制和合作平台,以增进缔约方相互了解,推动各方就气候治理中的关键问题达成共识。这些机制与合作平台主要可以分为政治性、技术性和经济激励/约束性三种类型。第一,政治性的公约外机制,主要包括联合国大会、二十国集团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经济大国能源与气候论坛、千年发展目标论坛、七国集团会议等。这些机制的共同特点是由政府首脑或者高级别官员参与磋商,就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大问题达成政治共识,但一般不就具体技术细节进行磋商。这些公约外机制,通常主要在全局性、长期性、政治性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参会级别高,尤其是首脑峰会,往往能就一些重大事项和问题达成一致,成为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第二,技术性的公约外机制,这些机制以行业或者专门领域为基础,主要包括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这些公约外机制针对气候公约谈判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专题磋商,形成的结果和政策行动将反馈公约谈判进程,并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体系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机制相比气候公约的谈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气候议程不是这些专业性机构的主要工作,这些机构对气候议程的关注度和专业程度,都无法与气候公约相比;同时,虽然都是国际机制,但不同机制的实施原则和议事规则存在较大差异,对待同样的问题,指导原则和思路的不同,也可能导致行动路径和结果的较大差异。第三,经济激励/约束性的公约外机制,主要包括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贸易机制,与生产和消费活动相关的国际标准等公约外的国际磋商和治理机制。经济激励或约束措施与减排、适应等议题相比,并不是气候协议中的关键要素,但这些问题与各国经贸利益、居民消费息息相关,尤其是随着部分国家提出碳关税实施方案后,国际社会关注度明显上升。国际贸易机制、国际标准制定等机构,在纳入或者考虑气候变化影响之前,就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国际治理机制,但在纳入气候变化问题后,不同机制间由于指导原则、议事规则等存在差异,看待问题的视角和结论可能出现偏差,不同机制间的协同治理还需要不断磨合,争取最优解。
(三)两大阵营名义上存在,各方立场分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联合国启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到2007年巴厘岛气候大会,国际气候格局基本上分为南北两大阵营:发达国家以欧盟、美国为代表,发展中国家以“77国集团+中国”为代表。尽管两大阵营内部在利益诉求和目标上颇有差异,但两大阵营的总体格局基本稳固。在发达国家内部,美国先是规则的制定者,《京都议定书》后又成为规则的破坏者;欧盟奉持国际道义,一直追求充当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导者与《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维护者。尽管美国和欧盟的利益与目标不尽一致,但在共同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方面,发达国家集团基本稳固[2]。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存在差异,各国或者各个小集团利益诉求有所不同,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减排、资金和技术义务的目标与利益诉求相近。因而,当今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基本格局可以概括为:南北交织、南中泛北、北内分化、南北连绵波谱化的局面,大致可以描述为“两大阵营”“三大板块”“五类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南北”两大阵营依稀存在,发达、新兴和低收入国家三大板块大体可辨;发达经济体可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人口较快增长国家及以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人口趋稳或下降经济体两类,新兴经济体也可分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人口趋稳国家及以印度为代表的人口快速增长国家两类,低收入经济体主要为低收入国家。这些经济体将来可能有不断的分化重组[3](P3),传统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二元立场可能进一步分化,形成复杂博弈局面。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特征
(一)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热度增加
民主党人拜登于2021年1月21日上任当天即宣布签署并重返《巴黎协定》,并于1月28日颁布应对气候危机总统行政令,从联邦政府层面全面重启、部署应对气候危机工作,并积极争取国际气候治理领导权。2021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拜登邀请包括中、俄、欧盟等在内的40位国家(地区)元首齐聚云端,举办领导人气候峰会,并提出美国新的《巴黎协定》下的贡献目标。拜登政府新目标提出,美国2030年相比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降低50%—52%,这相比2015年奥巴马政府提出的2025年相对2005年温室气体减排26%—28%的目标有了显著提升。拜登政府气候政策还包括:第一,提升气候议题优先级,以“气候危机”代替“气候变化”,并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国际、国内事务中心工作;第二,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建立清洁能源经济,通过大力投资清洁能源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第三,强调环境公正,通过开展气候、环境治理,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推进环境公正和公正转型实现;第四,统筹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建立清洁能源经济作为经济增长引擎,推动环境治理和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第五,明确目标,提出碳中和、电力系统零碳排放等目标,建立国家气候工作组、白宫国内气候政策办公室等机制、机构,保障行动令实施;第六,激励为主,通过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资等激励措施推进气候治理工作,但尚未提及碳税、排放贸易等约束性机制安排。
(二)目标竞赛,重新不重质
美国自重返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后,为提升气候问题在国际、国内的显示度,联合欧盟、小岛国联盟等,通过推动各方提出《巴黎协定》下的更新目标以及通过多边、双边机制,推动各国不断更新减排承诺目标。如我国自2020年9月22日提出“双碳”目标后,于2021年4月16日宣布接受《〈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10月G20大会二十国集团集体承诺“停止资助海外煤电”目标;11月10日中美联合申明1中承诺对甲烷(CH4)制定规划进行管制;11月13日《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中突出强调1.5℃目标以及“退减煤炭消费”的表述等。美国回归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掀起了全球减排目标不断更新的热潮,国际社会也因此弥漫着对于不断更新减排目标的激进作风和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忽略了对发达国家2020年前减排目标实现情况以及各国新提出目标能否兑现的关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部分缔约方在提出新的目标时,甚至缺乏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一味跟风更新目标和提出新的气候目标。国际社会各种目标层出不穷,包括各种碳中和目标、能源发展目标、不同温室气体管制目标等,基准年份也各有提法,呈现出有些非理智的混乱局面。各国如果只是把关注重点放在各色目标上以吸引国际社会关注,而不重视提高《巴黎协定》贡献承诺的实现质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一些以新奇和吸引眼球为目的的减排目标终将是纸上谈兵。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行动
《巴黎协定》开辟了各方共同承诺并开展行动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范式。《巴黎协定》缔约方基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相对《京都议定书》《坎昆协议》等更为积极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体现了各方共同开展行动的积极意愿。在《哥本哈根协议》的国家适当减缓行动信息文件中,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减排目标都是以获得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支持为条件的承诺目标,但在《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体系中,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展现了以我为主开展行动的积极姿态,并且在资金机制、透明度、盘点机制等议题的谈判中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体现了共同行动的意愿和承诺。《巴黎协定》下有180多个缔约方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NDC),这些贡献目标所覆盖的实施阶段大多为2021—2030年,部分NDC为2021—2025年。这些目标提出之前,各国已经开展了国内咨询、讨论和调整过程,《巴黎协定》达成后,这些基于国家自主提出的贡献目标将被确立为缔约方国内政策和行动目标,从而保证《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从《哥本哈根协议》到《巴黎协定》以及《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制定,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各方合作模式,已经由《京都议定书》时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和引领、发展中國家跟随,过渡到所有国家共同承诺并开展行动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范式。
四、全球气候治理趋势
(一)拜登任期内,气候治理热度不减
从拜登政府强势回归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以及2021年以来的密集行动和行动效果来看,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不容置疑。气候变化问题是美国两党政治中存在认知分歧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显示执政党影响力的象征,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科学认知的问题。因此,拜登政府未来希望持续扩大民主党在国内、国际议程中的影响力,也会积极推动其国内和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巩固其大选中的基本盘,并通过强化舆论宣传和政策行动,拓展更多选民支持。因此,可以预见,在拜登政府任期内,无论是拜登本人还是民主党政府都将继续大力推动美国国内气候议程。习惯了做世界领袖的美国,也必然将其国内进程与国际进程关联,要求世界各国配合或者参与美国引领的气候行动,在形式上实现共同减排。因此,在拜登政府任期内,全球气候治理的热度不太会衰减,这就需要我们研究气候议题持续成为热点问题对我国可能形成的影响。
(二)减缓目标不断提升
《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写入1.5℃目标的相关表述和“消减甚至退出煤炭使用”的表述后,国际社会对于各国提升减排目标的要求也会相应提升。格拉斯哥会议相对2019年之前的气候协议中,更加凸显了对1.5℃目标以及减煤退煤目标的关注。一方面,反映了随着全球经济、技术的发展,之前各方分歧较大的问题正逐步走向形成共识;另一方面,欧盟、小岛国联盟等也必将站在1.5℃目标的角度,要求各国提出更具雄心的减排目标,或是与1.5℃目标匹配的全球和各国的减排目标。这将导致目前以《巴黎协定》中提及的2℃目标为主要考虑的缔约方,可能面临大幅提高减排目标的压力,这种压力将会是持续的,并且伴随着减排目标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大。
(三)发展中国家责任与义务明显提升
与《多哈气候协议》《京都议定书》等阶段性执行协议的特征相比,《巴黎协定》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承诺、共同行动,且发展中国家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相比之前的协议明显有了提升。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1990年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GDP全球占比由18.3%提升到41.0%,碳排放全球占比由34.5%提升到66.8%1,经济实力有了明显提升,开展气候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也都有了相应提升。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巴黎协定》谈判以及提交《巴黎协定》更新国家自主贡献进程中,都展现出更加积极的行动计划和目标。未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大部分增量将由发展中国家产生,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控制的大部分压力也将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将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将不断增大。
(四)诉求差异导致集团重组,博弈格局更加复杂
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在不同集团内部产生了更小的利益共同体,如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产生了代表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相近国家集团(LMDC)、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小岛国联盟、非洲国家集团等次一级国家集团。这些集团由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在不同议题上已经出现立场分歧;在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分类上,也出现一些认知调整,如土耳其已经连续多次在缔约方大会上要求大会同意调整其所属国家集团,希望从附件I也就是传统认为的发达国家集团调整到非附件I也就是发展中国家集团,以减轻其减排义务;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在大会上表达调整所属集团的立场,如俄罗斯等,但在谈判中实际支持和所持立场已经与发展中国家更为接近。因此,在当前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南北国家立场分界线已经逐步模糊,在减排、资金等许多议题上,已经难以形成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立场,各国根据自身谈判诉求,在不同议题上形成新的立场联合体,导致气候治理中各方博弈格局复杂化、具体化。这种立场分化的趋势,对谈判能力较强的国家相对有利,对于国力较弱、谈判能力也相对较弱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失去发展中国家整体立场,单个国家各自争取自身诉求将变得非常困难。发展中国家立场离散,有经济差异发展的客观原因,也是发达国家乐见甚至是主动推动的结果,未来还可能保持同样的趋势,全球气候治理博弈格局的复杂性也将保持或者加剧。
五、气候治理新格局对我国的影响
(一)美国回归对我国构成减排压力
美国执政党轮换,民主党政府执政白宫并重返《巴黎协定》,积极争取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总体来看对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意義是积极的。在中美关系不太顺畅的情况下,拜登政府仍然派出气候磋商代表团与中国开展高层磋商,并发布联合声明,也展现了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对中国的特殊关注和需求,这种需求必然需要中国予以应对,并在全球范围做出表率。美国作为最先进的发达国家,在全球开展示范性的减排行动,既是其全球责任和义务,也是民主党在国内体现党派影响力并赢得民众支持的需要,开展积极的气候治理宣传意义大于行动意义,且由于执政党派更迭,现任政府的很多承诺和政策可能实现断崖式的下降或者退坡。中国当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国内政治结构也并不需要以强调宣传的方式来促进国内气候治理议程的开展,因此更重视行动的实效而不是强调口头承诺、追求华丽目标。中美两国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思路和目的并不完全一致,开展双边磋商以及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必然面临立场的妥协,从而对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构成额外压力。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通过多次中美双边对话[4]、G20机制、11月中美联合申明以及《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等双边和多边机制,推动中国不断采取新的行动或者接受新的气候治理目标,对中国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
(二)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责任义务明显提升
根据CAIT数据库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11.71GtCO2e,已经高出欧盟3.33Gt、美国5.79Gt的总和,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重37%1。较大的总量和较高的全球占比,必然让我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最显著的受关注方之一。国际社会通过双边如中美、中欧磋商,多边如UNFCCC、G20、APEC等多种平台和渠道就我国提升减排力度、更新减排目标进行磋商。相应地,我国也于2020年9月提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以及2021年4月批准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加强对氢氟碳化物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管控等承诺。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连同欧盟和小岛国联盟等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对我国施加了更大压力,这种压力还将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存在,并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的扩大而变大。当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经济总量和质量的提升,我国面临外部压力的能力和韧性也在加强,国内环境、气候治理的诉求也在增强,可以部分对冲全球气候治理责任义务加重的压力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不仅仅是在减排领域,在出资方面也同样给予压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南南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基金,未来该基金的拓展应用将不仅在资金问题上,也同样在减排问题上发挥缓解外部压力的作用。
(三)发展中国家立场离散,对我国构成谈判压力
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推动形成发展中国家集团立场,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同争取实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2007年前后,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度快速上升,部分国家甚至要求与我国实现对等减排,忽视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我国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诉求更可能被认为是不愿开展减排行动的借口。因此,推动形成发展中国家集团立场更有利于保护和争取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维护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团结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和一致的发展中国家立场,对维护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我国谈判利益更加有利。当前,发展中国家集团立场逐渐离散,甚至在部分主要议题立场上存在较大分歧,这一形势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也对我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构成压力。
六、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建议
(一)落实“双碳”目标,推动高质量履约《巴黎协定》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宣布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2021年10月,我国提交了《巴黎协定》下自主贡献目标更新目标。这些行动表明了我国积极推动《巴黎协定》实施和积极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目标。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要把“双碳”目标纳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5]。“双碳”目标的实现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重点关注,并写入经济社会“十四五”规划。2021年10月,我国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后续将陆续发布部门层面的碳达峰方案,指引我国碳达峰和《巴黎协定》履约工作的高质量实现,以扎实行动和优异成绩向国际社会展现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绩效。
(二)积极参与、引领国际治理进程,管控预期,明确红线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掀起了一轮关注高潮。一段时间内,各国目标层出不穷,包括不同年份的碳中和目标,不同含义、不同基准年的减排目标,以及包括非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等。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呈现出关注度高但比较混乱的局面。各方在已经提出积极减排目标的情况下,仍然费尽心力提出新的目标,而相对忽略了对既有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的关注。作为最大的排放国,我国也被迫内卷加入不断更新提出新目标的进程,提出了包括甲烷管控、自主贡献目标更新等目标。未来的气候治理进程中,需要更加强调预期管控,推动国际社会关注热点由不切实际的目标竞赛向既有目标的履约和高质量实现转移。应结合我国未来十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识别我国未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诉求和红线,并选择合适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传递信息,以避免国际社会对我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产生不切实际的过高预期,从而保障我国正常经济社会发展权益和秩序。
(三)强调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因此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将长期处于国际关注的核心,未来面临的压力不会下降,甚至可能逐步增加。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气候治理作为一个环境议题,并不是人类发展、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程,需要把气候议程放到人类社会整体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下与其他议程一起整体推进,强调包括气候治理目标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实现。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范式转型,开展气候治理不仅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生产、生活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通过气候治理行动,能够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UNFCCC. COP26 Facts and Figures [EB/OL].(2021- 11-10).https://cop23.unfccc.int/news/cop26-facts-and- figures.
[2] 庄贵阳,周伟铎.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和全球气候治理体 系转型——城市与城市网络的角色[J].外交评论(外交 学院学报),2016,33(3):133-156.
[3] 潘家华,巢清尘,王谋,等.后巴黎时代应对气候变化新 范式:责任共担,积极行动[M]//郑国光,巢清尘,胡国 权,等.应对气候变化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6.
[4] 中美气候特使将开展面对面对话,克里今日开始访华 [EB/OL].(2021-08-3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709592110745728831&wfr=spider&for=pc.
[5] 习近平时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中国有底气[EB/OL]. (2021-03-1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490
609209830958&wfr=spider&for=pc.
The Pattern,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Trends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fter Glasgow Conference
— impacts on China and its responses
WANG Mou1,2,3,JI Zhi-xuan1,CHEN Ying1,2,3
(1.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China;2.Research Institute for Ecocivilization,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20,China;3. Researc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20,China)
Abstract:the Glasgow Conference (COP26) is the first formal climate negotiation conference held after the Madrid Conference in 2019. It is also the first negotiation conference held after the retur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Paris Agreement.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parties,the Glasgow Conference made substantive progress,adopted the Glasgow Climate Pact,reached broad consensus on adaptation funds,carbon market,1.5 ℃ target and phasing down coal,and also started the process of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is Agreement. This paper combs and analyzes the new pattern,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trends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fter Glasgow Conference and its possible impacts on China,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China’s response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Key words:climate change;global governance;UNFCCC;Glasgow
責任编辑:郭建民
收稿日期:2022-0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角色定位的动态分析与谈判策略研究”(16AGJ01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的绿色发展战略研究”(2021STSB01)
作者简介:王谋,理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气候治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区域可持续发展等;吉治璇,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陈迎,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气候治理、双碳目标实现路径等。
3820500338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