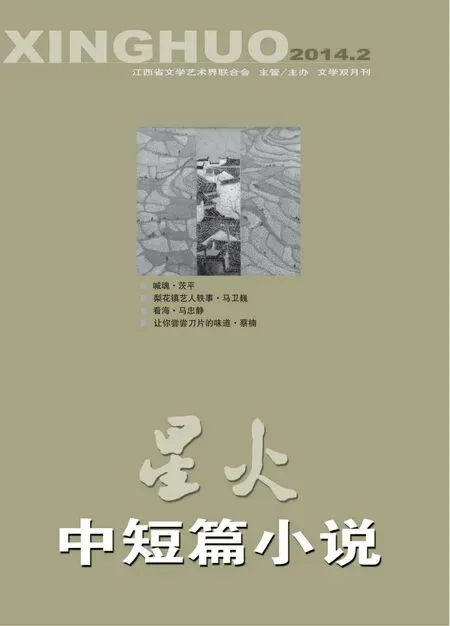时间的影像
○华真一
织
小时候,除了夏天,其他所有的季节我都能穿上母亲帮我织的毛衣。冬天是粗的羊毛衣,春秋会是细的羊绒,或是线纱,长的短的,宽松的,各种款式,都来自于母亲的灵感。
好像我童年时期生活的这个城市四季温和些,冬天的雪春天的花和秋天的果实,准时抵达。不像后来,冬天很少下雪,还有今年的夏天,居然发了洪水。小时候的冬天,约莫一月份就会下雪了。一下雪小学会放假,有时候放三天,有时候放五天。天很冷,但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还是会出去玩,戴着手套,穿着皮球似的羽绒服,一起趴进雪地,在雪地里互相扔雪球,或者把雪塞进别人的衣服里。雪地的最底层混着泥巴,我们在雪地里滚啊滚,于是衣服裤子就变成了黑色或者土黄色,脏兮兮的像个田里的野孩子。可那时候我们的脑海里完全不在意形象,而是担心回家会不会被骂。
父母在我小的时候对我很宠爱,所以我一般不会被骂。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帮我把湿湿的裤子脱下来,换上她亲手织的毛线裤。现在很少听说毛线裤这种东西了,那是童年的产物。小时候放学回家经常看到母亲拿着两根竹子做的大针,正对着两根毛线不停地戳啊戳。除了那两根大针,旁边还有一个薯片桶里装着各种各样的针:钢丝的,塑料能弯曲的,长的短的,粗的细的……针下就是已经打好的部分。母亲织衣服很快,通常我喊过几声“我回来了”之后,就能看见一条小毛线裤或者小毛线衣。我知道那都是给我的。并不是说母亲舍不得给自己织,而是她觉得在我小的时候这样给我不停变换服装很有意思。我太小,即使能分辨美丑也不敢大声说出来。我小时候对母亲唯一的抗拒就是不洗头,除此之外基本算得上是个听话的孩子。我温顺地穿上母亲织的各种毛衣或毛裤,也许这能让她觉得自己是个设计师。
穿上毛线裤的我通常感到很别扭,因为很厚很保暖,再在外面套上一条灯芯绒的小裤子,就真的是两只小水桶了。好在我小的时候个子不矮,不然真的不敢想象能丑到什么地步。我从小就知道母亲虽然没念过什么书但绝不是那种庸俗的家庭妇女,但我也同样不能理解为什么她要在毛线裤上织出那么复杂多变的花纹。母亲不喜欢一成不变的衣服,不在乎美丑,在乎的是对她来说有没有挑战性—从头到尾都用一种针法打,太磨灭她的天赋了。母亲总是在网络上找一些欧美风格的毛线衣,有些花纹很复杂,有些很简单,她挑中了一个好看的就会在网上下载出织毛衣的针法图,然后对着学。我看过那些奇奇怪怪的图,有点像吉他谱,或者电路图,反正看不懂。从小我就不爱动脑子,我喜欢睡觉,听说睡觉能让孩子长高,的确,我小时候比同龄人高。
母亲热爱的东西绝不止毛衣,她没有上过几天学,却能写出几万字的小说,但她不想在这方面过多努力,发表了几篇后她放弃了。母亲会画工程图,她自己学的水利设计专业知识,经常接一些业务自己做。她懂计算机,小时候很多邻居的电脑坏了,会请母亲去修理。可如果让母亲在她那些梦想和家庭之间选择,我打赌她一定选家庭。她总是淡淡地说自己老了,不再适应这个时代,如果出身不凡,上过大学,肯定会有很多追求。我知道这是借口,她只是放不下不争气的我和懒惰的父亲。于是她只能在还未到冬天的时候就不停地织毛衣,这是她的爱好,也表示出她对我和父亲的关心。她愿意花钱在网上买几百一斤的毛线,各种各样的颜色,互相交叉着,织成一件漂亮的混色的毛衣,然后放进洗衣机脱水,再用熨斗熨平,真的就像从商店里买的一样。那些日子总是一成不变,我在房间里写作业,母亲坐在我旁边的凳子上,两只手不停地动啊动。有一天我对母亲说,我也想学。母亲说我不行,性子急,肯定会半途而废。我不信,拿来两根针和一捆线,让母亲教我。母亲笑着手把手教我。我觉得那很容易,不一会儿就学会了最简单的织法,然后自以为掌握了织毛衣的技巧,果然就没再碰过那两根针。母亲没有抱怨,继续织自己的毛衣。现在想想,我很佩服母亲,在我和父亲的不断打扰下还能如此认真地完成一件件毛衣,这都源于她内心的执着。
童年的我是胆小安静而听话的。性格形成的原因大概是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没有陪在我身边,我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在和我父母同一个单位的邻居的照料下过了大约四五年。那之后爷爷不在了,父母开始不做生意,安安分分上起了无所事事的班,我也不再让邻居照料了。一家人搬到了一个大房子里。但我仍然胆小而沉默。
母亲觉得亏欠了我,觉得我原本不应该这样沉默,我应该是那个扎着两个小辫子到处接别人话的捣乱鬼,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上个厕所都不敢对他们说。可我对自己很满意,除了在学校里很少有人跟我玩以外,其他的都挺好的,因为我每天看到的是父母,而不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隔壁邻居家的姐姐。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那个时候决定放弃她自己的梦想,好好抚养我的。早知道我就不那么沉默了。真的,我真的认为她这样不值得,我不值得她为了我放弃什么。
长大以后,母亲对我很无奈。我早就料到我会是现在这副德行。我不爱读书,可爱读书的母亲为了让我读书而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每次我考试成绩出来之后,母亲都会被父亲骂一顿。父亲从来没有认真地管过我,这点我很庆幸,但他总会骂母亲没有好好管教我,会和母亲大吵大闹,好像我母亲是个巫婆应该受到诅咒。我为父亲感到可耻,为母亲感到伤心,却对自己犯下的过错没有丝毫的悔恨。如果我不是这个样子,母亲会成为一个专职写作者或者设计师而不只是爱好织毛衣的知性女子,父亲会是一个每天很开心地喝酒打麻将整天对我开不着边际的玩笑的中年男人。可是因为我,这些大概是不可能了,就算有一天我真的脱离了他们,他们也还是会在我身上找借口而放弃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
长大以后,我不再穿母亲亲手织的毛衣,并不是觉得它不好看,而是想通过这种举动让母亲找点别的事情做。在我跌跌撞撞地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本科大学后,母亲果然换了劲头。她开始一天到晚对着几本建筑设计的书看,从早到晚,比我读书的劲头不知道强多少倍。她考了一个证书。我为母亲感到高兴,她终于开始实现她那么多理想中的一种,而不是用空洞的手工来打发她原本该更丰富的人生。
我现在18岁,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我也没有多么怀念童年,因为在那里我没有看过美少女战士或者哆啦A梦,甚至任何一部有头有尾的电视剧,而是过早地见证了我那织毛衣的母亲的内心挣扎。我不喜欢这样,我只是一个孩子。
年
我不知道我生活的地方是不是算南方,反正这里过年时湿冷湿冷的,也不下雪,没有地暖,只有火炉。火炉是我对外婆家过年时的印象,我每年的正月初二回外婆家。外婆家在农村,习惯用山上的柴火做木炭烧火暖身。火炉分大小两种,大的叫火桶,人可以坐进去,盖上被子,双脚踩在固定好的钢条上,下面是一盆刚刚烧好的炭。我很喜欢整个人埋在火桶里的感觉,周身放松,坐在木制的座椅上,享受冬日的一个下午。看着电视里喜庆热闹无聊的节目,村庄上过年的人们来来往往,他们喊我的小名,摸我的脸,而我,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年对于我来说,就应该这样被莫名其妙地消费,即便有太阳,我也宁愿待在火桶里。
还有一种小的才叫火炉,用泥土烧制的一个小小的盆,盆里同样有燃着的木炭,盆上还有刚好能让双手感到温暖的很粗的把手,方便人们外出携着。外公经常两只手搂着火炉走街串巷,迈着缓慢的步子踱过家家户户,等待着别人的新年祝福。在火桶里睡着的我不会记得脸上的那块疤是什么时候被火桶里的钢丝烫出来的,只是翻看小时的照片才得知这件事。照片上的我笑得很开心,右脸有一道长长的黑色疤痕,火桶里木炭的颜色,这让长大的我对火桶有了一丝淡淡的恐惧。于是后来的年里,外婆家暖烘烘的冬日离我而去,我选择出去,漫步也好,疯跑也好,总之我要出去透透气。
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提“家乡”二字的,因为我从未真正地离开过家乡。走出去的家乡人回到了这里,在大年三十的前两天,小县城的街道显得异常拥挤,喇叭声,叫卖声,寒暄声,还有争吵声,能大声说话,谁也不再憋着,有些刺耳。回到家乡,回到一个可以肆无忌惮斗面子的地方,空间小了,可是,心和嘴都宽敞。那些大大小小挂着外地牌照的车,开起来有点不让人的野,仿佛在说:你们看,我在外面过得很好。从前只要回到了家,大家只按辈分说话,现在呢,是按照身份吧。时代在我人生的十八年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很多与人相关的东西。
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我应该是不会在家停留太长时间了。一是压力太大,没有时间;二是我不太喜欢过年时大人们之间的热闹。很多不大碰面的人会突然来拜访你,寒暄着尴尬着,互相说着新年快乐,即便是你讨厌的人,也得祝他福如东海。这对于有一点点习惯城市生活节奏的我来说,觉得非常无趣。因此我总在逃避,逃避年夜饭,逃避敬酒,逃避那些在我听来不走心的吉祥话,逃避转眼就将交换给别人的压岁钱。所有的一切在我眼中不过是一场盛大的表演。年的传说最初也只不过是一场驱赶怪物的仪式,我不明白后来的人们为何给它加入那么多专属于个体的情感。但是,如我爸爸一样守旧的人在这一天应该会感受到非常大的存在感,他们嘴里冒出来一句句的漂亮话让人应接不暇,不论真心与否,他们总能在这一天与别人称兄道弟,顺便做些莫名其妙的约定。不就是个年吗,七天的假期,安安静静地陪陪家人,或者看自己喜欢的书,做平时没有时间做的事,有什么不好呢,何必要走来走去地把自己的生活展示给亲戚朋友……我的这些想法放在人情味浓重的县城,可能是大逆不道的。
包括鞭炮声,在我眼里都是哗众取宠的。当各大城市和网络媒体都在宣传过年不要放鞭炮,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在过年前一天又买回了三盘大大的鞭炮,还有六箱烟花。妈妈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他说孩子们喜欢,我就多买点。我在一旁傻乐:“明明就是你自己想放!”大概家中除了爸爸,谁也不喜欢放烟花了。那种伴随着成长的欣喜早已在我和哥哥的身上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们都知道鞭炮为什么会变成红地毯,也知道烟花不是真正的花,点燃后会在空中转瞬即逝。为什么我们要为转瞬即逝的东西疯狂?在那短短的一夜里,我从来没有睡过好觉,因为我总能被鞭炮的声音吵醒。这些吵闹的人中有我的爸爸,所以我不能责怪他们。毕竟,新年是他们展现个人喜乐最重要的时刻。那些哗众取宠的鞭炮声停止之后,世界又恢复平静。爸爸总是不愿意打扫那些鲜红的鞭炮碎屑,仿佛那是专门为过年铺下的红地毯,一旦掀开,年也就结束了。
我的表姐直接选择不回家过年。表姐是八〇后,北京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在一所大学教书。前年暑假正式与男朋友结束十几年爱情长跑,表姐夫老家在江西上饶,离安徽很近。他们不愿意回来。我想起我第一次去北京找他们的时候,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乡下丫头,我以我浅薄的视角看到两个在首都努力奋进、苟延残喘的读书人。他们在北京的四环外租了一套带阁楼的小房子,一进门就是一屋子的书。除了书,我不知道他们还剩下什么。那时我觉得他们丟弃了小城市的传统,又没有变成真正的都市现代人,像那些外地打工者一样,处于一种无根漂泊的状态。不过既是读书人,就有读书人的傲气,我的传统观念还是被他们完完全全地嫌弃,三观也在那时被彻底清洗。我欣赏表姐表姐夫很多东西,也会质疑他们。我外婆家所在的村子,中国千万小乡村中的一个,表姐即使作为村里的凤凰,一飞回,还是难逃一些东西—表姐一回家就能听到舅舅对她说她的初中同学生了孩子,高中同学在外打工买了房子,还有那个谁,刚刚开着一辆大奥迪过去了,舅舅认得四个圈圈套在一起的车牌……表姐在无数次考试中得到的那些荣耀忽然在乡村不值一提了—她还没有房子,没有生宝宝,只有一份不算太高的薪水,知识这个东西只有被冠上北大博士头衔的时候才能显得有一些价值。这价值通常是给外人看的,它能使舅舅挺直腰板做生意,使外公保持不紧不慢的语速还留有威严。但表姐回到家只能作为一个展览品,乡亲们会带着好奇的眼光走进舅舅的家门看看这位来自北京的农村人到底有没有变得像一个北京人。而通常表姐是会让他们失望的。事实上表姐在北京时的穿着打扮普通而家常,饱读诗书反而让她远离了时尚与流行。就在昨天,我在家中的微信群里看到表姐对大家说:“今年我们就不回家过年了。”
除去那些不愿意回来又不得不回来的人,还有一直留在这里的人,过年到底在谁的心里最有意义呢?是老人吧。奶奶会在过年前几天搬进我家,一家人嘘寒问暖,将她送上餐桌的首席。即使奶奶家离我家中间只隔了一条不算太长的河,一年到头我也去不了几次。老人为何还是执着于过年,真的只是因为儿女的陪伴吗?别的老人我不了解,我的奶奶好友很多,常常与一群老太太在广场上唱歌跳舞。去掉一年两百场以上的麻将,她还喜欢在外面吃快餐,目的是把时间省下来去陪伴一个卧病在床的老友。以友情为中心的老人在生活中应该很少见吧,可奶奶确实这样,看起来真的丝毫不孤单。可能奶奶是为了减少儿女的负担故意隐藏自己的孤独,但在我眼里,奶奶在失去爷爷之后的日子里一直很坚强。年夜饭这一天,奶奶会将大伯给她的红包转交给我,再由我转交给我爸爸。大家真心祝愿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奶奶用那双做出了多少碟儿好吃的豆腐乳的手捏起酒杯,抿一小口,说:“你们发财,打麻将杠开。”奶奶看着年夜饭从年轻时的自己操办到老了任由儿女主持,应该会感慨一声逝者如斯吧。她不会说这么文绉绉的话,只会用乡音叹几句不干不净的语句,类似于“搞么精子搞,一晃我都八十了”。
小县城里的年没有任何谈得上民风民俗的东西,一切可以简化的仪式都被简化。鞭炮倒是响个不停,这个364天不见雾霾的小城,新年的第一天却雾霾重重。伸手不见五指。灰白色的浓烟布满天空。疯狂地庆祝。不变的是人们口中违心的话和越来越厚的红包。一觉醒来就到了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新年的第一天。爸爸早上七点半就会外出拜年,我和妈妈则留在家里恭候来我家拜年的人。我负责微笑和端茶送水,当然新年快乐是要说一下的。那些大人通常会说:“新年好啊新年好!呀!今天还是你生日吧?你看看我都没有准备就来了。”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指望他们能做好为我过生日的准备来我家,可他们又非得提一嘴巴说自己忘了准备。这让我很尴尬,也很愤怒。愤怒于不相干的人在我生日这天无端地影响我心情,好像他们是专门来提醒我的生日早已经被遗忘了似的。确实,我的生日不被重视,除了过年收两次红包以外,好像没有人问过我生日愿望。这两年就直接往我手机里打钱,父母的解释是快递都回家过年了,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朋友们在这一天也不会围着我转,他们要走亲戚。每每想起我的生日,我都会快速在脑袋里将它清空,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就是无聊吧。还不如躺在火桶里睡一个长觉,做一个美梦呢。而十八年前,我那还很年轻的妈妈在过年时坐月子,不能穿漂亮的衣服,不能和朋友们一起玩,怀中还有一个我在吭叽吃奶,妈妈一定也无聊坏了。
关于过年这件事,我所能想到的全是积怨许久的内心世界里的小九九,无处发泄,只能敲敲键盘,还不敢让外人看到。我希望有那么几个人和我一样没有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中,想着点年外的事儿,我就不会显得那么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