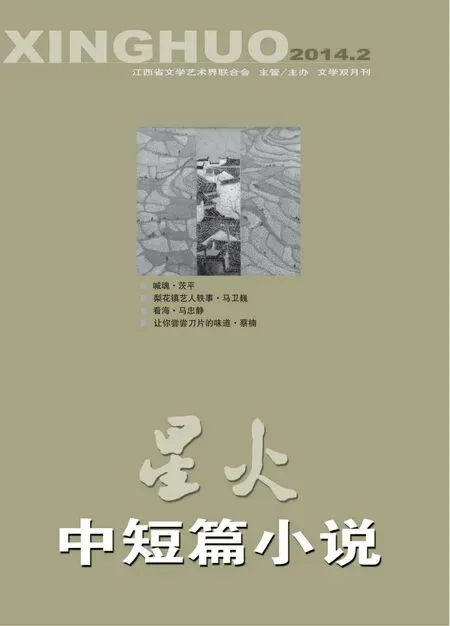我想要件隐身衣
○晏铌
1
我挺直腰背,坐在办公桌前,把材料一张一张地叠放,装订。全部完成,又检查了两遍之后,才揉了揉有些酸胀僵直的脖子,再借着转脖子的机会四下里瞟了瞟,见办公室没其他人,就立刻把头高高仰起,再伸直双臂,呈十点十分状,站在了座位上。这个动作,是我近来常做的,它可以缓解肩颈乃至腰部的疲劳。
桌上这沓材料,足足有两百页,光是打印,就花了近一个小时。上午打印时,我手心里汗渍渍的,口也干,身体还有些别人难以察觉自己却清清楚楚的颤抖。我有点不安,我怕那台老旧打印机持续不断又不堪重负的“吱扭”声影响了同事们,我更怕同事们不耐而嫌弃的眼神。
我是个怕麻烦的人,尤其怕给别人添麻烦。我觉得,我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母亲一定忽略了一些什么,以至于我无论如何努力,也没办法点亮人际交往的技能。我实在无力应付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看不清五花八门的面具下是怎样的脸和心。在百般努力也无济于事之后,我决定自暴自弃。我想:不如给自己找一件隐身衣呢,这个怕是更实际些。
我不想整理材料,也不想去参加什么评比。但领导通知的时候很郑重:“这个机会可是我们帮你争取来的。好好准备吧,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咱们单位的荣誉!”对于领导的这种看重,我很惶恐。我不想要这些,虚名对我来说,麻烦大于价值。我不愿意耗费心力,更不想面对可能随之而来的身不由己,尤其不想被异样的眼光和形形色色的议论凌迟。
我甚至能想得出那些人在议论时眼珠要翻出眼眶的表情和如刀子般的话语:
凭什么啊,凭什么又是她的?
凭什么?就凭她在领导面前的乖巧样儿!你会吗?你做个脸红红、眉低低,受宠若惊、感恩戴德的样子来看看……
一想到这些,我就抑制不住地打颤。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放下双臂,坐了下来。
当目光触及最上面那张A4纸上“186人参与投票,160人赞成,16人弃权,10人反对”的字样时,我刚刚松弛了一些的胸口又有点儿发闷。工会主席那句刻意压低了声音的话语响起在耳旁:“怎么会这样呢?以前从来没有过啊!”
怎么不会呢?这次是用“问卷星”投的票,以前此类情况,多是举手表决。众目睽睽之下,不举手的人是不大有的,一个单位,低头不见抬头见,面子上过不去。方式一修改,大家各自在办公室,甚至在卫生间拿着手机点,当然可以随意愿发挥了。没准,还暗戳戳兴奋呢。谁让自己在工间休息时不能和同事们开无伤大雅的玩笑,不能无所顾忌地聊八卦呢?我试过好几次的,只要我加入多少就会有些冷场。当同事们打着哈哈四散开去的时候,我只想立地消失。那天,我清楚地听到一位同事一边嘟囔着“千古第一聊天终结者,半天都憋不出一个屁来”,一边晃悠悠回到自己的工位。
我甩了甩头,狠狠地鄙视了自己一把,重重转而又轻轻地拉开抽屉,找出了一个大号的黑色长尾夹,双手同时使劲,捏开,夹在材料上端的正中间。
下午两点时,工会主席端着一贯的似笑非笑的圆脸,把材料交还到了我手上,说:“要盖的章我都盖来了,剩下的几份材料,我用微信发给你,你去打印出来。汇总后,你自己送到总工会去吧。我有点事,去不了。”
我看着工会主席的脸,看到经过伪装的鄙夷藏在话语的背后从他翕合的嘴唇缝里丝丝缕缕地逸出来,看到明晃晃的不耐闪烁在他圆硕发亮的额头上一粒粒的汗珠里。我双手把材料接了过来,听着自己的心跳声越发响亮起来,犹如鼓点一般,鼓槌落下时,响起的声音幻化成肉眼可见的黑体加粗大字“自—己—去—送”“自—己—去—送”“自—己—去—送”,这些字不受控制地从嗓子眼里冲了出来,凌乱地跳跃在眼前。
“对,你自己去送,有问题吗?”直到工会主席的声音响起在耳边,我才惊觉心里的恐惧居然发而为声。
“没,没,没问题,没问题。谢谢主席,辛苦您了!”我再三弯腰低头,直到工会主席转身离去。
2
我左手抱着材料,右手拎着包,出了办公室的门。虽说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阳光还是很强烈,皮肤都在太阳的烘烤下紧缩了起来,有隐隐的刺痛一波一波地往脑门上涌,密密匝匝地,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我觉得,防紫外线太阳伞、防晒披肩什么的,最大的作用就是给人以心理安慰。真不知道烤箱里的面包蛋糕怎么还能在红彤彤的高温里愉快地膨胀而不是缩小。除却太阳的威胁,自己本来也恨不能缩到最小,就像冬天走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中那样地蜷缩。我觉得,越小,应该就越不为寒冷或炎热所注意。尽力做好自己的事,也是我缩起来的一种方式。虽然也怕被边缘化,怕丢了这份稳定的工作,但我更怕活在大家审视的目光之中。只不过没想到,适得其反,反倒把自己给突出来了。
走到区行政服务中心门口,我把防晒披肩脱了下来,团成一团,裹在手里。照我的习惯,是要把它塞包里的,拿在手上,不好看。我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已经够不受欢迎的了,如果还邋里邋遢,恐怕要被大家的眼光杀死了。可今天带的包太小,放不下。
中心大厅门口有喇叭在循环播放:市民朋友,请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排队有序进入大厅。
我每天都在包里揣着口罩,这成了习惯。在密闭的空间,比如电梯里,更是如此;太阳猛烈时,也戴着,防晒。还是因为今天的包太小,就没塞。大家都说封闭管理的那段时间憋坏了,可我很喜欢那两个月居家的日子,一点儿都不用和外人接触。迫不得已出门时,也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安全。
我有点懊丧,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母亲论事时爱说的不大应景的老话:骑马没碰见亲家,骑牛偏偏就遇上了。每次听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都会替这个“骑牛”的人尴尬,因为自己就经常有这样的窘迫。比如,想着不过是下楼丢个垃圾,两分钟的事,碰不上熟人的,所以就穿着家居服,披散着头发。可刚一出楼道门,就听见前面有惊诧的声音:“呀,你住这里啊?好巧。”那一瞬间,“隐身衣!隐身衣!”我满脑子满心里都是这三个字。但我没有隐形衣,也不能遁地,只能飞快地瞟一眼,嘴角扯出一个笑容,嘴唇抖索着挤出“好巧,好巧”的音节,再举举手里的垃圾袋,以它为“掩体”,迅速撤离。
有一次,我实在没忍住,就问母亲:“如果您骑牛时遇见亲家了,怎么办?”
母亲稍稍把下巴收了一下,眼光从老花镜上方扫向我,“有什么怎么办的,遇都遇上了。挺直腰杆,把牛当成马骑呗,别人不知道,自己还不知道家里养着马吗?”
我挺喜欢这些老话的,尤其爱听母亲说。母亲不但能赋予这些老话以新意,而且说的时候,不紧不慢,一边说,一边干着手上的活儿,仿佛那些话就长在她的皮肤血液里,再随着呼吸一起从心肺里呼出来。但我害怕母亲的眼神,我觉得,母亲的眼神里有细细软软的刺,一旦扎进皮肤,就会化为无形,找不到,拔不出,却扎得人连筋骨都痛。我知道,母亲对我的恨铁不成钢和我对她的敬畏一样多。我一直想学母亲的沉稳淡定游刃有余,但这么多年了,不管怎么努力,还是连皮毛都没学到。我很沮丧,是太笨了,还是在意的东西太多了?
我有些忐忑又存了一点侥幸,哪能这么倒霉呢?说不定只是这么咋呼,有健康码就能证明自己健康,也能说明自己的活动轨迹。这个偏僻的小城,和疫情,从来就没有真切的关系,而自己,也快十个月不曾离开过小城了。我点开支付宝,把健康码调出来,朝向坐在门口的保安。保安面无表情地对我稍稍抬了一下下巴,示意我往里走。我暗自庆幸,脚步轻快起来,拔脚朝里走去。刚进门,里面坐着的保安问:“口罩呢?”
“不好意思,忘带了,我有健康码的。”我边说边赔笑脸。
“不能进。”说完,保安的目光又投射到了我后面,重复着刚才的话:“口罩呢?没有口罩不能进。哎,哎,哎,说你呢!懂不懂规矩的啊!”
我知道保安说的是后面那个径直往里走的人,但还是有一股灼热从心底深处升起,霎时传遍全身,烫得我的心脏和皮肤一样疼。
3
我忙不迭掉头朝外走,一边走一边想着是不是让女儿骑自行车送一个过来,随即又否决了这一想法。时间来不及,等女儿下楼,骑车过来,至少要十分钟,再耽搁一下,人家可能就要下班了。而且女儿骑自行车也不安全,还是去买一个吧,反正又不认识人家,怕什么。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卖的,也没带钱出来。想到这儿,我不由骂了句“傻子”。果然是光窝在家里和单位不出门窝傻了,这年头,都是刷手机刷脸的,谁还带现金?谁又想收现金?科技真是个好东西,它在保证人们安全的同时又无限地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记得有个名气挺大的又是赛车手又是作家的小伙子调侃说,这年头,除了床上运动,啥事都可以不面对面。一般来说,我挺反感这些所谓的俏皮话,但这句,确实是话糙理不糙。干吗一定要去办公室呢?居家办公多好啊,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视频会议什么的,有头像就行了。在单位开会,哪怕是坐角落里,也还是会有被点名的危险。
我尤其不爱碰钱,每次拿过钱,都要用洗手液洗好几遍手,不然,总觉得手指头上有异感,脏得慌。刷脸刷支付宝多安全,完全避免了一切不必要的接触。我顿住了脚步,背心里一阵凉飕飕的,晕,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不能再胡思乱想了,好好找卖口罩的地方吧。我抚了抚胸口,左右瞟了瞟,悄悄出了一口气,继续朝前走。
我决定朝来时的路找过去。我知道,大约五六百米远的地方,天天上班要走过的那条路对面有一家药店。药店是肯定有口罩卖的,不像那会儿,哪哪都脱销。酒精、口罩,甚至双黄连之类的,反正专家说什么,什么就被哄抢一空。在生命的恐慌中,大家什么都不信,又什么都信。我信命,更信母亲。母亲说:性格是生就的。母亲还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倪萍有一本《姥姥语录》,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写一本《妈妈语录》,母亲有太多朴素的至理名言。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就是老天爷决定的,而不是后天养成的,更不是母亲赐予的。不然,这么多年了,努力了那么多,怎么就没有一点儿长进呢?那么聪明又能干的母亲,怎么可能为女儿选择这样一种性格?
我其实不愿意去想那个词,那个百度来的词:社交恐惧症。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都有一点的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不愿意到人多的地方去,不愿意在人前表现自己,不愿意主动和人交流吗?人性那么复杂,人心那么险恶,谁不防着谁呢?只不过,自己更敏感一些罢了。我有时候又觉得,敏感挺好的,封闭也挺好的。就像蜗牛,有个厚厚的壳,随时都可以把自己缩到壳里面,不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多安心啊。
刚走出二三十步,我看见一个门洞里有两个高大的保安,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坐着的那个一半衣襟扎在裤子里,一半衣襟耷拉在外面,头发凌乱。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走上前问道:“请问您知道哪里有口罩卖吗?”
站着的保安面色黝黑,肚子高高耸起,肚子上的那粒扣子有点不堪重负,眼看着就要被崩开。疫情之后,多少人变了身材,这保安恐怕就是其中之一。保安看都不看我,手一挥,含混地说:“旁边水果店。”一副了然的腔调。
兴许问的人多了吧。确实也挺烦的,不停地回答一模一样的、没有一点思维含量的问题。干工作,还是要有点新鲜感、有点成就感才好,今天是昨天的复制,明天又是今天的粘贴,人不烦躁不懈怠才怪呢。
4
我道过谢,继续往前走。我记得,来的路上,确实有一家水果店,叫“胖子水果店”。这个名字我曾听办公室小姑娘说过几次,所以路过时注意到了。小姑娘说他们家水果很贵,小姑娘还说他们家代收快递。小姑娘是个很外向的人,成天叽叽喳喳的,她应该还说了很多其他的什么,但我不记得了。我很喜欢小姑娘的热情,但又有些吃不消这种热情,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小姑娘说一些和我无关的鸡毛蒜皮的时候,我是不太应和的,只是做个听众而已。我觉得,小姑娘也不需要应和,她只是想说,想有一个人听她说而已。小姑娘和我本质上是一类人。
我其实也不在意,对和自己没关系的事物我都不怎么在意。我一直在意的是,自己该做的做没做好,别人会怎么看自己。刚刚走过的这些地方,都在我家方圆两公里之内,可我的生活,只有家和单位这两个点。周边的这些地方,我可能曾从外面经过,但从来都没有走进任何一家去过。我的生活,是两条线段,家、单位、楼下水果店,再无其他。就拿倒垃圾来说吧,自从那次遇到同事之后,我再也不去了。放假时,三五天不下楼是常事。买菜是夫包揽的,拗不过时,才偶尔陪他去一回。买了十几年的那家服装店,也都半年没去了。超市更不去,有种服务叫“外卖”,一切都可以送到门口。疫情之后,一年一次的陪父母出门远游也省了。要说疫情对我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让我原本就简单的生活变得更简单了。
走出一百米左右,我看见了一家水果店,玻璃门上用胖乎乎的白色字体写着,“关于水果,可以搞哪些事”。我停了一下,又抬脚朝前走了。太花哨的东西,我不信任。继续往前走了十来米,就看到了“胖子水果店”。
“胖子水果店”准确地说应该叫杂货店,店里水果确实不少,其他东西好像也挺多,一眼看过去,有些杂乱,还有些暗。售货员也不胖,大概老板是胖子吧。
我没心思打量,径直问:“请问有口罩卖吗?”
“有。”
“怎么卖的啊?”
“两块钱一个。”
“麻烦帮我拿一个。”我点开支付宝,扫码,输入数字,发现居然能优惠两毛钱。上午闲下来时,我点了一个抽奖码,抽到了两张优惠券。连续十天了,支付宝每天八点、十二点都有抢消费券的活动,满60减10块,满30减5块,满10块减2块,另外还可以抽奖。
那天办公室的人都在咋呼之时,我也偷偷抢了一次,居然就抢到了。我开心得手脚都有些发抖了,但我不敢说出来,在那么多同事都懊丧别人手太快自己该换手机了的时候,我不敢表露出一点开心和激动,会遭嫉恨的,尽管内心已经绚烂得如同单位院子里那几株开得像爆炸头般的山茶花一样。我实在喜欢那种抢到券的感觉,就像是真被幸运女神眷顾了,满心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但一忙起来,就不记得哪个点要去抢券了,也没想到可以设个闹钟。
今天照旧忘了抢券,想起来时,便抽了奖,抽了两次。一次的奖励是满10块减2块,一次的奖励是连续一周,每天进实体店消费都可以减两毛钱。有了前一次的抢中记录,这个抽奖就没什么吸引力了,抽过也就忘了。
因为额外花两块钱买口罩而有点不高兴的心,又随着这被自己遗忘的但实打实的两毛钱的优惠而高兴了起来。小姑娘说的,有便宜不占,天理难容。嗯,有可占的便宜占,确实很美好。一会儿回去时,到楼下水果店买点小番茄,把那两块钱的优惠券也用掉,明天早上继续烤披萨。
我要走出店门时,进来一个女人,还没进店就问:“有口罩卖吗?”我没去看人家的表情,应该和我一样,也是要进服务大厅的,没必要去见证别人的懊丧,换做是自己,在这样的时候被别人注目,是会很难受的。
5
再次回到服务大厅门口时,我因为戴着口罩而有了底气,下意识地把脊背挺得笔直。外面的那个保安,还是面无表情地撇头,里面的保安这回也没说话。我倒是说话了,我的声音里有一丝自己都能觉察出来的小愉悦:“您好,请问一下,我要到26楼,在哪里乘电梯啊?”
“26楼啊,这里不行。你往那边走,有一个大通道,通道那边有电梯可以上26楼。”保安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朝一个方向指了指。我以为他会出来给我指清楚,便回头等着,却见他又一屁股坐了回去。我想,算了,大不了再问问其他人,又不割舌头的。“又没人割你舌头!”这是母亲每次看我半天都张不了嘴的时候从牙齿缝里漏出来的话。
走了二十米左右,果然看到一个大通道。走到通道口时,两个保洁员打扮的中年妇女也进了通道。我上前一步:“两位大姐好,我想去26楼,请问是在这里坐电梯吗?”
“是的,是这里。”两人同时回答。
再走到一个门口时,又看见了一张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保安,前面竖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满了字。考虑到时间可能来不及,我就没细看,只是拿出手机,亮出了健康码,问:“您好,我想去26楼,请问应该在哪里坐电梯?”
保安靠着椅子背,没说话,也不看我,似乎陷在某种情绪中,拔不出来。两个保洁员从我后面上来了,其中一个说:“往这边走,跟着我吧。”
我跟了过去,感激地说:“谢谢大姐,你真好。”这句话甫一出口,我的心底里就涌起来一阵轻松,就好像读大学上体育课时,跑完一千五百米后被老师允许自由活动时的那种轻松。我是不怎么会夸人的,刚刚这句话,我说得由衷,我真心觉得,这位保洁大姐,很善良,很好。
“我很好吗?”保洁员爽朗地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这牙可真白,这样的笑容久违了,我也从心底里有了笑意,“是的,大姐,你真的很好,这么热情。”这种热情,是我羡慕而学不来的,也是我所遇不多的。
6
“你真好”是我一直藏在舌头底下的一个句子。每每说出这三个字时,我的心里就会有一波波的轻松和熨帖。我喜欢这种感觉,这让我觉得自己和人群没有距离。
上午整理材料,贴照片时犯了难,没有胶水。只好硬着头皮去了隔壁办公室借。那位平日里看起来颇有几分冷傲和疏离的同事瞄了我一眼,低下头一边扒拉着,一边说:“我有双面胶,要不要?”
我说:“双面胶贴了怕撕不下来。”
“固体胶行不?行的话这个就送你了。”同事把固体胶递给了我,眼神有点儿躲闪,脸上有一丝若隐若现但我很熟悉的不自然,耳朵根部还有一些些红晕。
我平生第一次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你真好!”我真的很诧异于他的热情。这位被其他同事称为“公鸡先生”的男士,走路时从来都如军人一般,挺着脊背,抬着下巴,目不斜视。我总觉得他的脸上分明写着“别靠近我”四个字。难道,这不过是他的伪装色?他和我,是一样的?
平日里,我总是告诫女儿,善良是人最重要的品质。可鸡零狗碎的现实生活,总是把这种品质给磨得面目模糊。我向来不敢随便就对人展现出善良友好的一面,怕被怀疑、被拒绝,更怕被讥讽。所以每每遇到愿意朝自己伸出双手的人,我都觉得很幸运,都想要真诚地对人家说一声“你真好”,只是,说这句话,于我而言,也需要莫大的勇气。
今年唯一一次去菜场赶早集时,我也说了这句话。买完仔姜后,卖仔姜的小伙子应该是看见我和夫都拎了一手的塑料袋,就扯了一个很大的红色塑料袋递过来,“给你个大袋子,这样就能你老公一个人拿了。”当时下着小雨,我一手打伞,一手拎菜,手指头上勒出了深深的凹痕,指尖红黑红黑的,确实吃力。
我有些诧异地接过塑料袋,脑子一热,就冲小伙子说了句:“你真好!”
小伙子高高坐在敞开的卡车车厢里,车厢上面用塑料布搭了个棚,是那种红蓝白条纹的塑料布,映在人脸上,有些斑驳。听了我这句话,他明明暗暗的脸上有了几分忸怩,“这种力气活儿,该男人干。”
走出去几步后,夫挑了挑眉,又撇了撇嘴,说,这小伙子怜香惜玉呢。
我剜了夫一眼,有些好笑地伸手去拎袋子。
夫说:“可别,别人都能帮我心疼老婆,我自己还能不心疼?”
7
“叮”的一声响,电梯停下了。保洁员带着我七拐八拐,一直到能看到2626办公室的牌子才掉头。我目送她,等她拐过了弯,才往2626走去。站在门口深吸了两口气,按了按胸口,我抬手在门上轻轻扣了两下,“您好,请问这里是总工会办公室吗?”
“是的,进来吧。”一道清冷的女声自办公室最外面的那张办公桌电脑屏幕后面传出来。我从电脑屏幕的一侧看见一只白皙的手把口罩带子挂在了耳朵上。我走上前,双手把材料递给了电脑后面那位画着粗眉,看起来三十五岁上下的女人手边。女人掀了一下眼皮,瞟了我一眼,接过材料,往旁边一丢,说:“可以了。”口罩的包裹下,我看不到她更多的表情。
我默了默,又吸了一口气,上前了一小步,弯着腰,轻声说:“麻烦您看看,不知道材料有没有遗漏。”
女人抬头扫了我一眼,眼睛里有毫不遮掩的嫌弃。她把材料拿起来,捏着两个细长的手指翻了翻,说:“你难道不是照着文件要求去准备的?”
“是的,是按照要求一项项准备的。”
“那就不会有问题。这么多的材料,我怎么可能一份份检查?全不全的,你自己负责。” 女人又一次把材料丢在一旁,抽出一张消毒纸巾擦了擦手,再用脚踩开旁边的灰白色垃圾桶,把消毒纸巾丢了进去,就又把眼睛盯在了电脑屏幕上。
我突然觉得口干得厉害,似乎刚刚是从一楼一层层爬楼梯上来的,有些脱力,胃里还有一点刺痛感。我把双手按在了胃上,再次道了谢,踮着脚快速朝办公室外面走去。刚要走出办公室时,又进来了一个人。
“呀,来了?久违了。”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个自口罩底下发出的热情又沉闷的声音。
“您好,您好!久违了,久违了!又来麻烦您了!”迎面走来的这个人,口罩之外的眼角眉梢全是笑意。他疾步走上前的同时伸出了右手。
我忍不住回头去看,果然,那个已经站在办公桌后的男人眉头几不可见地皱了一下,手往后缩了缩,又快速地抬了起来,抬至胸前时,和另一只手合抱在一起,作了两个揖。
迎面而来的这个男人稍一愣神,伸出去的右手也瞬间朝上抬起,盖在了握成拳头的左手上,行了个拱手礼,原本有些弯着的腰背在拱手时也不由地跟着挺直了。
我转过头来,加快了步子朝外走去,脑子里闪出某天看过的“六六”的一句话:911之前,坐飞机是不用安检的。我想,六六还应该加上一句:新冠肺炎之后,握手这一礼仪就消失了。是不信任呢,还是戒备?或者,和自己一样,单纯就是不想和别人接触?以前,我出行,只要不是特别赶时间,都开车,或者干脆步行,什么公共汽车、地铁、共享单车之类的,从来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夫经常开玩笑:你啊,应该长两只翅膀,这样,就连高铁、飞机也不用坐了,更不用在箱子里放上床单被套。你个傻女人,累不累啊,酒店的床单比家里的还白,你怎么就不放心呢?
夫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搭腔,只是笑笑。最开始时,这种嘲笑会让我难受上好几天,但现在慢慢习惯了,夫没有恶意的。我比谁都清楚,安全感这种东西,除了自己,别人似乎好像很难给。不,自己也不见得就能给自己多少安全感,给自己造成麻烦的,多半都是自己。我的切身体验:别人确实不会割你的舌头,但自己却总有恨不得把舌头拽出来丢掉的时候。
新冠疫情之后,我做这些事情时就很坦然了。哪怕是在单位,除了自己的座位,能不坐下时我就坚决不坐。必须得坐时,我会用含75%酒精的消毒湿巾擦拭凳子。回到家里,先换家居服,再用热水洗手洗脸,洗完后还用消毒湿巾把每根手指都擦一遍。我坦然是因为不只是自己,其他很多人也都在这样做。有一位做医生的同学还想在家门口装个消毒房,消完毒再做其他。没准,过不了几年,这样的房子会成为常态?
8
我来到电梯旁,隔着消毒湿巾按了下行键,退后一步站定,再把湿巾翻转一面,折叠起来,捏在指尖。电梯在走廊的尽头,旁边是高大的玻璃幕墙。在等电梯上来的间隙,我转了头,透过布满灰尘的玻璃看着脚下迷蒙的城市,看着路上蚂蚁般大小、不停穿梭的人们,突然间有了些恍惚,有些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所为何来。
电梯到站声把我解救了出来。进电梯之前,我把口罩拿了下来,抻了抻,用力搓了一把有些酸胀的鼻子,又重新把口罩戴上。戴好后,再捏了两下口罩上方靠鼻梁的地方,严严实实地把口鼻捂在了口罩里面。
戴口罩的时候,我眼前突然闪现出眉目含笑地注视着我的母亲,全然不是那一贯斜着眼睛瞟自己的模样。
我有些想母亲了。
母亲不愿来小城,我也以疫情为由,许久都没有去看她了。是该找个时间去看看她老人家了。我想要当面告诉她,我这样的性格没什么不好,挺安全的,就像健康码和口罩一样。没准,比健康码还安全,比口罩更能保护自己。
我抬起头,盯着电梯轿厢上方依次递减的数字,感觉呼吸顺畅了不少。电梯开开合合,踢踢踏踏进来又出去几个人。我没看他们,只是盯着那个不停变化的红色阿拉伯数字。那个数字像一盏灯,又像一个火把,或者是个精灵……
我的脑子里有短暂的空白,又仿佛挤进了一些东西,那东西若隐若现的,像穿了一件隐身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