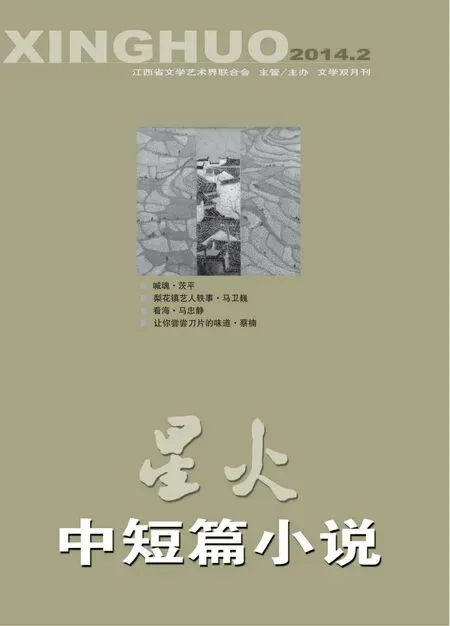一堆行李
○朝潮
奔跑和忧伤
跑了一千米左右,身体里就多出一台蒸汽机;光是张大嘴巴喷发还不够,身上的皮肤也大面积参与了这项物理蒸发运动。大口喘气时,忧伤用一种不屑的眼神看了我两眼。我用手挥了两下想驱逐它。忧伤就后退了两步,看我的眼神警惕起来,警惕又不屑。我在旁边的绿化带边沿上坐下来喘气。忧伤也在原地蹲坐下来,与我保持着一定距离。这一路上,大多数时候忧伤跑在我前面。它跑得很轻松。
忧伤是一只普通的柴狗,眼眉中间有两小撮深色的毛,看上去像永远皱着眉头一样,有点警惕又有点不屑,更多的是忧伤。第一次见到它时,就注意到那两撮眉间的异色毛,我就叫它“忧伤”。此后多次看到它在楼下转悠,不知有无主人。我问过门卫,也说不清楚。有一次在楼上透过玻璃墙面,看到忧伤被某路人踢了一脚,它不像别的同类那样被惹怒,表达出激烈发应;它只是受到惊吓的样子,卑下地退到街边去了。我经常无聊地在玻璃墙面前发呆,好几次看到它一路小跑来到这里,在附近的小广场、商铺、公交站四处转悠,无所适从地东张西嗅。
我喘着气看着面前的忧伤,生出一种抚摸它的想法。我嘬着嘴呼唤,伸出手招引,忧伤只是保持礼貌地晃动着尾巴,挪动了一下屁股,没有进一步的反应。我第一次叫它忧伤时,它也是这种反应,好像它原本就叫忧伤一样。它可能不敢轻易相信人类;换句话说,它可能受到过太多人类的欺骗和伤害。不过它对我肯定没有坏印象。我去楼下买早餐时,给过它食物。有一次我特意带着食物去见它,它也只是用肢体语言表达对我的亲切和感谢。忧伤似乎拒绝人的身体接触,这有些异常。
休息了十多分钟,完成一个短暂的能量代谢过程后,我开始往回快步走。快走与奔跑,有着明显不同的感受。奔跑时,由速度带动的内啡肽上升,使人愉快,愉快又加速脑神经的发光和活跃。坐高铁时也有这种体会:当我望着车窗外的景物飞速掠过眼前时,大脑会误以为是在奔跑,会相应高速地带动我的思维和想象;如果只是无聊看着车厢内的人和物,时间长了会犯困。
此前的一千多米奔跑,好像耗尽了我大部分体力。已经有几个月没有锻炼了—年初一场家庭的重大变故,影响我的不仅仅是生活习惯。没有读书,没有写作,甚至连脑子也懒得转动了,更不要说跑步。最近我又恢复了间歇性的奔跑,也就是天气好的时候跑千米左右,然后走回来,或者跑一程,走一程。“跑”字在古代出现得很早,先秦时代就有了,不过当时它的意思是“刨”;杭州虎跑泉的“跑”,就是这个意思,传说虎跑泉是一对兄弟变身为虎后,刨出来的。古代的“走”,反而是奔跑的意思。比如初中课文里的《木兰辞》中,就有“双兔傍地走”一句,这个“走”便是指奔跑。至于“奔”,《说文解字》中说:“奔,走也。”“疾行曰趋,疾趋曰走。”于是有了“奔走相告”这个成语。
我在前面快步走,忧伤显得比较淡定,不紧不慢跟着我。回头看它一眼,它就停顿一下,这时的眼神里全是卑下。到了门卫处,它就蹲下来不再前进,无奈地看看我,再看看门卫的窗口。我猜门卫不止一次驱赶过它。我往里走了十多米远,回头看到忧伤还蹲在门口。看上去真的有了点忧伤。
小时候,周边的家犬全是散养的,没有宠物一说,没有烈性犬,偶发的咬人事件只会出现在狗受到人攻击的时候。现在的圈养狗品种丰富,烈性犬、大型犬也很常见,它们完全没有自由外出的机会,丧失了生命自然态;出门会被套上项圈、拴着绳,只能限时跟着主人散步,本性被操控。大概在楼房里被关得时间太久,狗一出门就兴奋,难得见到同类更激动,偶尔主人一松手它就发疯,人狗冲突在所难免。为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安全和秩序,狗被统一拴上绳索,之后冲撞人、咬人的事件反而多了。狗没有绝对的自由,人也一样。
与城市里被主人牵着散步的狗相比,格林的命运更好些。格林是一只狼。成都女画家李微漪去草原采风,救活并收养了一只出生不久的野狼,取名格林。格林的父母刚被偷猎者杀死。养了几个月,画家李微漪还是决定将格林放归自然,希望它能回到草原上自由奔跑。随后,画家带着格林回到草原上,一路追寻狼群,历经艰辛,终于让格林重返狼群。
可以说,成长环境是决定动物性情的关键。格林只是与画家生活了几个月,就像家养犬一样跟人亲近,听话,懂事。在草原寻找狼群的日子里,画家带的食品吃完了,格林就去猎捕兔子给主人;主人在荒野里扭伤了脚无法走路,格林就去附近放牧的马群里咬住某匹马的缰绳,一直将马牵引到主人身边……野狼格林有生以来的这几个月,一直是画家在养育,对人来说几乎没有危险。在草原上,它见了生人就家犬一样晃尾巴;画家只会担心它受到生人的欺负和被时不时出现的猎人追杀。格林重返狼群后,可能会重蹈它父母的命运;它和画家、猎人、狼群三者的关系是一种选择性关系,没有最好的一种,只有相对符合其本性的那个选项。活在一个善的环境里,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关怀。
奔跑是一种状态,也可能是生命意义上的一种修辞,就像阿甘坐在亚拉巴马州的一张长椅上,跟每位过客讲述自己生命中的奔跑故事。
第二天晚上七点,我又出门去跑步。刚出大门口没几步,就看到忧伤向我小跑过来。在两边的太阳能路灯光照之下,忧伤看上去容光焕发。跑步时,我喊一声“忧伤”,它就起劲向前冲;跑远了,我再喊一声“忧伤”,它又摇着尾巴跑回来。我远远跑不过忧伤。
第二天比第一天多跑了一段距离,回来的时候还是快步走。回到楼下的路口时,我在一家便利店买了两根火腿肠给忧伤。忧伤还是不让我碰它。我咬开其中一根火腿肠的包装,将火腿肠放在地上,它才小心地咬住;第二根火腿肠,忧伤犹豫了一下,直接从我手里咬了过去—这个动作让我愉快了很久,似乎是一种关系有了进展。
此后好几天接连下雨,秋雨绵绵,夜跑也就取消了。后来天气转晴,也有几天没出去跑步。习惯和惰性是一对好兄弟,它们总是结伴而行。有一天傍晚去门卫室取快递,听两位门卫师傅在聊天。一位说:“前段日子,那只狗每天晚上七点左右在大门口蹲着,也不知道在等谁。最近这两天好像不来了。你见到它来了吗?”
另一位说:“还真是,这两天没看到它来。”
“完了,说不定被哪家狗肉店杀了。天气也快冷了。”
“路上的车这么多,撞死也很有可能。”
我的心跳突然开始快速奔跑,那是一种情绪复杂的奔跑。我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出门卫室,看了一眼大门口路灯下的空旷处,大脑的指挥室里全是忧伤坐蹲在门口的样子—这个画面长时间挥之不去。我心里坚持认为,忧伤可能等了几天失望了,跑到别处去了;也可能是被人领养了,被套上绳索关在小镇的某个房间里,只有在主人方便时才会被牵出来散散步。
此后每次夜跑,总会一路想着忧伤,想着眉间那两小撮深色的毛,看上去像永远皱着眉头一样。后来甚至唯心地想:真不应该给它取这么个名字。
我的确再也没有见过那只叫忧伤的狗。
闲人和椅子
日子像秋风一样闲散。案前工作再紧密,也挡不住我注意力的松懈。
人一松懈就闲,毛病就多。最大的毛病是发呆,站在玻璃墙面前发呆,看街道上堵车,看红绿灯的十五秒倒计时;站在顶楼的平台上发呆,看盆栽植物一天天向上成长,看西边夕阳一遍遍洇染天际……这是现实主义的闲。看纸质书、包书皮、陪老妈聊天是古典主义的闲。早上不想醒来,深夜不愿入睡。深夜太黑,人们通过睡眠穿越而过;对于闲人来说,深夜是用来修补白天,涂改心情的。
白天的大多数时候,我不会坐在椅子上超过一堂课的时间,坐在椅子上也容易纪律松弛。离开椅子的原因多种多样,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得职业病,怕长肉,怕混迹于别人的中年;还有一个原因是自己的身份简单、自由,没有长时间坐在椅子上的理由。我的椅子必须够结实,即使不起身,也会在椅子上折腾:手撑椅子的不同部位做身体的拉伸,会双脚腾空练臂力,会像一只鸟那样停栖在椅子上打字。先前那把椅子是钢结构,坐垫和靠背由软皮和记忆棉组成,坐在上面很舒适。上月,我把椅子一侧扶手的支撑螺丝给撑断了。最近换了一把实木椅,五六十斤重,移动椅子时木地板会发出宽厚低沉的一声吼。
实木椅子的动静有点吓人,坐在上面硬邦邦的也谈不上舒适,不过看着有气派。如果不发生意外或野蛮使用,这把椅子可以使用一两百年,甚至更久远。椅子很稳定。一天的流程也稳定,时光也稳定;不稳定的是人类,尤其是他们的大脑。
我脖子上的这颗脑袋,它有五种功能和五种方法论,听、看、闻、说、想,以及它们演绎出来的千万种色彩和人间气象,繁复如星球。譬如,看到的、闻到的、听到的,与说出来的有着遥远的距离,更与想到的有着星际之间的差距;又譬如,眼睛做不到独立去发现什么,看到的东西通常是大脑想看到的东西,眼睛最容易被大脑蒙蔽。五种功能之间的辩证关系本身就值得怀疑。这也是我时常发呆的原因。发呆,就是任凭五种功能临时瘫痪,或者听任某种功能飞越星际,无法无天—这是闲人的隐秘时刻。
五种功能如果表达出来,就是公开的,否则就是绝密,这应该是最大的隐私。别人看到的这颗星球,和自己感知的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无处不在的感知、触觉和想象围绕着与生俱来的轨道运行。它们构成了另一个银河系。有关相对意义的美与丑、是与非之类,它们有着既定的认识和不断的建设、更新。如果某天做错了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个后果就会像一个失联的航天器,长期漂浮在这颗星球的四周。
每颗星球,独一无二,喜欢或讨厌对方,似乎都隔着一个银河系—这有悖年轻时的认识,那时候行不择义,学不闻道,以为相识的人皆可成为朋友。事实上,一个人的心思是由内而外的,跟长相和精神面貌紧密相联,跟与生俱来的五种功能无关。这种关联日积月累而形成,脸上和精神上的特征会朝你肉眼看不到的认定方向去发展。所谓近朱者赤,起点就是人们常说的“眼缘”。当你感觉与某种面部特征有好感时,就有了与之成为朋友的向往。
闲人的精力供大于需,通常只能自我消化,或者是输出的渠道被自己的世界观管控住了。闲人的重要生产资料有:椅子、书籍、茶具、香烟等等。椅子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四条腿的支撑,符合事物确立的稳定性,它是闲人精神建筑的基础。
活过人生马拉松的半程,大概是最需要毅力和坚持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认知,承前启后。对于闲人来说会经历新一轮事物认知,也可能是对过往的重新认知;先前看似无比稳固的东西会动摇或倒塌,先前枯萎的论调会被某种事实滋润后复苏—这是我脖子上这颗星球目前的常态。有一次跟朋友坐在一起闲谈,谈到对事物的认知,我说,其实我们谈的认知很狭隘,只能是一群生理结构相同、成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相同的生物中的认知;最要命的是,这种狭隘的认知在同一生物种类中也存在巨大的差别,甚至可以黑白颠倒。
我的认知不止一次被自己革命或策反。这种过程一点不难过,还值得细细回味,类似精神进化。大概只有很闲的人才会计较这些,还乐此不疲。精神世界所有的不确定性和疑问,在闲人那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生产力,当然是没有现实价值的那种。经常坐在椅子上想:实木椅子的前身应该是一棵长势良好的树,枝繁叶茂,器宇不凡。那棵树当初的理想应该不是现在的样子。现在我就坐在那棵树的灵魂上。坐在椅子上是用来感知和想象灵魂的。
椅子很可能是促进人类进化(也可能是退化)的主要道具。先是把尾骨坐没了,把腿骨坐细了,把腰椎坐坏了;坐的时间长了,力量弱了,大脑更发达更复杂了……
椅子在唐朝之前的几百年就出现了,始于汉魏时从西域传至中原的“胡床”。胡床体大,扶手、靠背更像是周边装饰用的,可坐卧,可文案。发展到唐朝时,胡床中分野出一类,其体积与现在的椅子差不多(还分野出了圆凳的式样),也有了“椅子”这个名称的文字记录,只是习惯上唐朝人还是称之为“床”。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中的“床”,不是课堂上被认为的“睡床”“井床”“围栏”或者台基之类的,指的应该是椅子。唐朝诗人笔下经常出现的“床”字,大多是指椅子。不过那时的椅子没有扶手,从那时流传下来的相关画作上看,外形相当于现在的方板凳之类;高档些的椅子有靠背,坐面下端有些雕花之类的延伸或装饰。唐朝的椅子基本上是有钱有权的人家使用,它并没有取代民间的传统坐榻的地位(千万不要相信影视剧里的画面)。到了宋朝,椅子的概念和实用性才普及起来,也产生了有扶手、靠背的真正的椅子。著名的太师椅,就诞生于那时;著名的合餐制,也因椅子的普及而诞生于宋朝。现在,太师椅的现实地位多半被沙发替代了;合餐了一千多年,现在再提倡分餐制难了,起码不是短时间内能实施并普及的。这让我想起古代那个叫冯妇的人,对他身份的勇士—善士—勇士的否定之否定,现在有了新的认识。从分餐到合餐,再到分餐,“再作冯妇”不是一个简单的重操旧业的意思,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只要有老虎的出现,冯妇迟早还是要再做勇士的。
我几次在大家庭里提倡过分餐制,没有一个人赞成,只有一位表示理论上的支持。作为家里唯一不理家政、不会开车、不用上班的闲人,我完全没有决策权,参政议政也只是象征性的。闲人不在乎这些,反而享受家里这种特殊地位。闲人最擅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白日梦,或者用反向行为去拓展一些新的没什么用处的价值认知,或者花半天时间把家里花木的每片叶子擦拭一遍,之类。做一个不累于俗的闲人其实是有讲究的,专业性也很强:不从众,不依赖,相对没有约束和压力,不能对自己有现实的要求,不能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面对现实世界,要像一株幼苗那样做美好单纯的梦,像树干那样尽量挺直、心无旁骛,像一把实木椅子那样笨重、稳定。
嗯,听起来也不坏,就是一心一意过闲肆日子,与繁复的人际社会龃龉不入。继续喝茶,发呆,爱这个季节的晴朗,也爱阴雨,以及整个秋天的宽敞。不要去追问价值啊意义啊,它们一会儿在远处,一会儿在近处,它们比我更闲散。
房间和田径
小镇像一个暴发户,它用了三十多年时间,由乡镇蜕变为一座小城,只是行政级别上还是镇,称呼上还是习惯叫小镇。它被称为中国五金之乡,还有一个国家湿地公园。小镇的命名很薄弱,也卑微,背后却是浩浩荡荡的民营企业队伍。它由两个相邻的小镇连接合并而成,面貌狭长,从地图看上去像一个人的腿脚,从膝盖一直延伸到脚尖。脚尖的方向是诸暨,小腿的方向是绍兴,这两个方向还在拓展,延伸;脚后跟方向已是杭州一个区的边界了。我的房间处于脚踝的位置,这个部位比较稳定。我也稳定。我比别人想象的还要稳定。
我的稳定还体现在日复一日的背诵中,背诵房间里的独处和简单,以及这个长方体里的无穷想象;背诵朝南窗前的一小片湿地和其间两只白鹭—尤其是雨后,白鹭在湿地上空展开翅膀的样子清朗又抒情。只是建筑工地已经在一点点入侵这片湿地。所有经济模式的读写中,土地永远押着韵母,新建的高楼以押韵的方式一幢幢并立生长。
六年前,刚搬进这个房间的那年夏天,我每天晚上在“脚踝”到“小腿”的一小段区间内奔跑两三个来回,很轻松。这属于长距离奔跑了,结束后喘会儿气就没事了,浑身舒坦。那时的小镇晚上比较安静,宽阔的大街上车辆也不多,人行道上一个奔跑的人偶尔会想起白鹭的清朗,那么舒展。有一次跑步到半途,忽然天降阵雨,也不避雨,眯着眼睛一直跑回家。
进入深秋时节就不再出门,外面气温低,出汗后容易着凉,便改在活动室的跑步机上跑。活动室比较大,健身设施众多,还有台球桌、乒乓球桌、棋牌室之类。两年后活动室被清空,跑步机也撤了。每晚就在空旷的活动室里绕圈跑,像一根秒针那样顺时针跑、逆时针跑,跑累了就改为竞走;或者在房间里做各种身体的拉伸和耐力运动,也跳绳,也做操,也倒立……自己跟自己竞赛。房间成了一个微型的田径场。
两个房间,其中一间的使用率不高,主要用于放绿植、冰箱之类,成为微型田径场完全没有问题。天冷时,我会在房间里原地跑,也可能是一寸一寸向前跑,不论速度,四肢的幅度还是用力奔跑的样子。这时候就会想起那则著名的寓言:龟兔赛跑。房间里的奔跑速度就是龟速。房间里还可以进行田赛项目中的立定跳远,以跳过十格木地板为及格线。另一个房间集工作、睡觉、娱乐于一体,主要娱乐就是看电视新闻,或者看体育比赛,尤其是奥运会一开赛,其他事情就放一边了。一个爱好奔跑类项目的人,生活节奏和工作效率却很慢,而且大部分时间被自己圈定于房间中。
奥运田径比赛分田赛和径赛,我主要关注径赛,也就是奔跑类项目,尤其是短跑。据说古代的奥运竞技起始时只有短跑项目,到古代第十四届奥运会才增加了中短距离奔跑,后来又逐步增加了长距离奔跑、五项全能、跳远、投掷、摔跤等,再后来又陆续增加了拳击、四马战车、赛马等,越来越向军事化方向发展。中国古代的竞技也趋向于军事化,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武术,它是古代军事的一项必修技术;秦汉时期“角力”“击剑”也很兴盛,还有后来的岳家拳、杨家枪等,更是军中技能。
写《孙子兵法》的孙武,被伍子胥引荐并聘为吴王阖闾的军师后,他以一位军事家的眼光,格外注重军人的体格和奔跑能力,尤其重视长途奔跑能力方面的训练。在训练时,孙武要求士兵们全副武装跑完三百里路后才能宿营。后来在攻打楚国时,他选拔了三千名长跑能力相对较好的人组成先锋作战部队。凭借这支队伍的灵敏和快速,战事接连告捷,很快就攻占了楚国首都郢城。现代战争史上,以速度制胜的例子也很多: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奇袭三所里,十四小时穿插七十二点五公里;红军长征时,红四团飞夺泸定桥,一昼夜急行一百二十公里……
小镇的发展也像在跟谁竞赛一样,更快更高更强:区域发展更快,楼房越建越高,全国小镇一百强的排名越来越靠前。区域扩大得越快,停车位反而越难找;街道手术缝合后没到一年,又要接受新的手术;楼下那条街,下午五六点经常堵车,从上一个路口堵到下一个路口,密集的红色车尾灯一眼望不到头,让人联想到一段血脉的堵塞。小镇传染了大城市的常见病。
中年人的身体状况也出现了常见病症:记忆力下降,体质也一往无前地开始下滑,肺活量在下降,剧烈的奔跑明显会加剧我的疲劳。长时间坐在房间里的一把椅子上,身体的某些部位偶尔会隐秘生长出一两个或酸或胀的种芽;它们想扎根下来,想破土而出。我的工作性质是它们的契机,我可期的衰老是它们的动力和目标。
事物总是有两面性。身体的一部分正在缓慢衰败,另一部分可能还在奔跑着成长,很可能还有一部分正在孕育的路上。譬如年轻时的各种欲望已经衰败得差不多了,淡泊、宽容和感恩之类越长越盛;譬如年轻时的视力比较短浅,只能关注到眼前的东西,现在再远的地方也能看得到。每天会在房间里生出一些小念头、小感想,它们在头脑中发芽的过程很神秘,会在某一刻快速爆出一棵小苗,重视它,它就成活,否则就很快消失。我的案上杂陈着一些小纸片,偶尔会把这些小念头、小感想记录下来,更多时候会错过。那些错过的瞬间,类似于异军突起的超自然,转瞬间全军覆没,或许是一种精神微能量的代谢方式。
那些小纸片上的一两句话,可能会在未来的某天下午或晚上松动起来,萌芽并迅速破土而出,然后在一个文档上枝繁叶茂地成长。这种方式并不是一直会流水所到之处自然成渠,很多时候它需要一种力量,也可能是某个契机—那是一种无形的神秘—去催生或触动。譬如,我曾在老家的一棵树下发呆,这时候大脑里那棵叫做神经元的树就开始释放出微量的化学物质,随之幻影出一位老年女性的形象:她开始在我的大脑投影屏上走动,从一个女孩走成一位百岁老人。我在小纸片上记了一行字:一棵某某树下,讲述她传奇的一生。这行字如同一位煽动者将我拖拽进一种没有预兆的精神刺激。现在,她一生的旅程断断续续写在一个文档里,像永远写不完似的,这是一场精神旅行。所有的写作是在房间里的旅行。
一七九〇年,法国一位名叫萨米耶·德梅斯特的二十七岁贵族军官,因为提剑跟人决斗,被罚禁足在自己房间里四十二天。在一个没有任何娱乐和通讯工具的年代里,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反而在周长三十六步的房间里自得其乐(只是偶尔有男仆和小狗出现),精神旅行了四十二天,还为此作了一部随想录式的游记《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五年后这本书出版了,并成了畅销书。房间里的旅行,是一种自己照见自己,或者说自我发现。
我们大脑里的东西,极少是可以做到独立自主的,绝大多数是别人替你选择的;即使在房间独处,想到的也是别人和别人的方式,以及如何取悦别人和得到别人的认同。一只小小手机里的海量信息,我们看到的方法、立场、意志等全是别人的,不可能有独立的选择。萨米耶·德梅斯特说:“人有一个更好的自己,那个自己要在面对自己的旅行中去寻找。”
十个手指在电脑键盘上的间歇性奔跑,与在大路上奔跑的体会不一样。手指奔跑时,脸色估计是那种原始的凝重,只有结束后才会有舒展和清朗的感觉。如果此后在卫生间的镜子中看到自己,会发现那是一张万象更新的脸,自信,欣欣有光。我喜欢那时的自己。脸是一个人的灵魂;房间是私密的,是一个人的灵魂寓庐。
最近家中大清理,我换了房间,还是两间。两个房间采光很好,有四个窗户,分别朝向西面和北面,这两个朝向注定了冬天的阳光很难直接照射进房间;房间的优点是,傍窗而立,看落日的视角很宽敞。我在这两个房间住的时间不会太久,在这段时间里,还是期待着精神旅行的秘密接洽。
代谢和手艺
冬天像年轻人一样冲动,说来就来。刮风,降温,昨天穿外套还嫌热,今天厚厚的毛衣和外套也抵挡不住西北风的遍身搜刮。风吹着风,像钱塘江大潮那样一浪接一浪涌来,一路欢声雷动地吹到江南。行人低头匆匆赶路,眯着眼睛,不敢偷窥西北风的音容笑貌。风精湛地吹动着楼下整排的大树原地起舞,步调一致。午后在平台上抽烟,看到一红一白两只塑料袋在空中戏闹,你追我赶。
寒潮硬生生把气温吹低了十余摄氏度,电视新闻也在反复提醒这一波大降温的来势凶猛。气候专家在接受电视新闻主播连线时说,酷暑和酷寒以后渐渐会成为常态。同一天的重要新闻还有能源危机和即将召开的全球气候大会。看电视新闻时一再走神,两只塑料袋的生动形象感染着我,像一个典型的细节。
老妈每次从街上回来,手上总会提着三五只盛放菜蔬的塑料袋。那些轻薄的塑料袋相对方便、耐用,清洗后可反复使用,直到最后用作垃圾袋—这是老妈的保留项目。家里的厨房、客厅、阳台永远能看到塑料袋,包括食品袋、保鲜袋,它们深得一个家庭日常主事者的偏爱和工作精髓。便捷的消费品通常苟合于现代人的惰性。譬如一次性的鞋套、手套、杯子、快餐盒、筷子等等,家里这类东西唾手可得,用完即扔。人的身上每天也有废弃物,那些掉下来的细小物体绝大多数肉眼难见。这些被代谢掉的东西,散落在房间的任何地方;它们不会像塑料袋那样满天飞舞,即使不清理也会自行分解,除了掉落的头发。曾经多次鼓动家人使用布袋、化纤袋之类,就像提倡分餐制一样,始终落实不下来。习惯是个顽固的敌人。
第二天,气温继续下跌。据说山区已经下了薄薄的一层雪,附近某家企业的一截露天水管也冻裂了。家里的一些因季节更替而代谢下来的用具需要清洗、晾晒和收藏。外面西北风在怒吼,晾晒工作难度很大,薄一点的衣服很可能会像塑料袋那样飘飞出去。替换下来的坐垫、床上用品也全堆在洗衣间,洗了也没法晒。
随之家里开始了一轮大清理,清理出一大堆过时的、废弃的大小家用电器:手机、剃须刀、电水壶、电风扇、电脑、游戏机、影碟机……光是各种各样的充电器、遥控器、连接线就整理了一大袋,当然还有相应的各种塑料包装袋、盒。这些更新换代下来的用具,不知道怎么处理。文明程度越高,新陈代谢越快,消耗也越多。手机阅读替代了传统的阅读方式,致使一大批书店、书吧退出市场。卡尔·马克思将生物学的新陈代谢概念应用到社会、经济、环境等各领域,真的是一种再发明。
我近期发明了一种喝茶的新手法。茶叶冲泡几次后,味道就很淡了,通常的操作就是把茶叶倒掉。天气冷的原因,茶水凉得很快,我偶尔会把茶杯放在身边的取暖炉上,放一会儿再喝。有一次放在取暖炉上忘了,等想起来时茶水已开始沸腾,此时的茶色更浓,味更酽;然后继续加水煮,茶味依然浓酽……好吧我承认,这不算是发明,古人最原始的喝茶方法就是生叶煮饮;不过茶叶冲淡之后再煮,的确可以多喝上两轮。
最近十年,我不知道使用过多少茶具了,更新换代太快。不锈钢杯、防爆玻璃杯、宜兴紫砂壶、景德镇瓷盏,等等。各式茶具只领风骚一两年,很快就被取代。它们是我过度消费的直接证据。各式茶具的价格不便宜,弃用的原因,不是碰撞坏了,就是不易清洗、使用不方便。现在案前使用着的反而是一只最普通的陶杯,不值钱,好像是很多年前买咖啡时商家赠送的。陶杯比较厚实,掉木地板上不会破,使用、清洗也方便。这只陶杯跟我现在的实木椅子一样,结实,稳定。
家里大清理那些天,也清理出不少杯子,搪瓷的、玻璃的、塑料的,品种繁多;同时清理出来的还有两只用藤条编制的筐,一只方形,一只椭圆形,大小适合盛放水果。两只藤筐年代久远,老妈都记不清它们原先是做什么用的。正好现在又开始流行使用这种老旧物件,可以作为水果篮重新发挥它们的价值,作为怀旧装饰品也是不错的。
环保、耐用的旧物件还有竹篮,曾经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物件,现在菜市场里看不到它们的身影,已经被便捷的塑料袋替换下来很多年了。小时候常见的竹编手艺人(那时叫篾匠),大街小巷里也消失很久了。早在二〇〇八年,竹编工艺就进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现在只能偶尔在新闻中看到极少数的传承人,以及他们的竹编工艺品。竹制生活用品风靡了两千年,从热销到冷遇却只用了短短几年。这个降速跟现在的气温变化一样迅猛,一夜入冬。
大概是受两只藤筐的启发,老妈开始念及竹篮之类,认为现在使用竹篮反而显得独特和复古。她托人去附近村子里打听有没有竹编的手艺人,想订制几只竹篮和夏天用的竹编凉席。结果反馈回来的消息是:附近没有找到会编竹篮的师傅。当塑料袋一统天下之后,竹编手艺人渐渐失业,转行;当年那批手艺人,现在也老了,就算还能制作,估计也手生了吧。
老妈编织毛衣的手艺就生疏了。年轻时她很会织毛衣,几个晚上一件毛衣就织成了。等家里人的毛衣全有了,她又开始织围巾、手套。在我眼里,那时候老妈织毛衣都成精了,眼睛看着别处,嘴上说着话,十个手指照样精准地上下飞舞。前一阵看她老坐着,看那些家长里短的电视连续剧,我就鼓动她重新打毛衣。一来有事做,心里有着落;二来可以活动手指和筋络。老妈笑笑说,那些编织技法忘得差不多了;又说,现在毛衣多得穿不完,谁还织毛衣啊。
织毛衣这门家庭手艺,可能也正在大面积消失。
某日忽有熟人相告,手机某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位竹编手艺人,可以去定制。这位手艺人已成网红了,国外都有一大批他的粉丝。物稀则贵,这是价值规律。一百多年前塑料刚发明时,它的制成品也很贵;几经更新换代,发展到一体式聚乙烯购物袋(俗称塑料袋)后才成为万家必备用品。当初发明塑料袋是为了替代纸质购物袋,遏止纸质袋的泛滥,解决树木大量消耗的环保危机;没想到塑料袋成了新的更加严重的环保危机。
世事无常,或者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本身就是一个循环;至于这个循环是良性还是恶性,大概开始就已注定。
冷了四五天,气温还是回升了一些,尤其是中午太阳直晒时段,似乎又回到了初秋时节温度宜人的样子。毕竟江南的十一月不该这么冷。楼顶的平台上又开始忙碌,各种洗,各种晒,当然也会夹杂着几只醒目的塑料袋—它们在微风中摇头晃脑很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