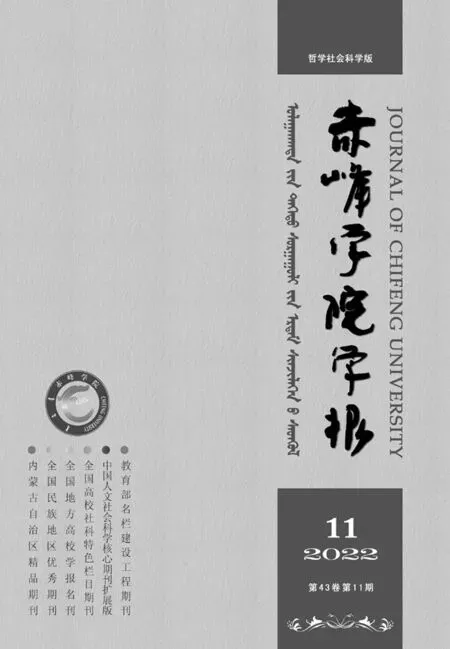“借才异代”视角下金人“中国”观的形成与发展初探
宋 卿,王 森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1]。随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2]。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工作会议中进一步指出:“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多元一体的组成结构,是中国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汇聚而成。辽金宋是中国历史上的“前中华一体”时期,此时民族关系及民族意识发生着重大的转折性变化,各族先后步入中华行列。辽金宋皆是中国,共同促进了“中华一体”的发展[4]。
金朝是女真人建立的多民族王朝,肇兴于中国东北地区,历时百余年。女真人以武建立政权,凭借其强大军队迅速吞并原辽疆域及宋朝北部地区。面对如此广阔的疆域及众多的人口,女真统治者自知仅靠女真人无力管理新占领地区,遂在灭辽荡宋过程中注意吸纳辽宋士人为新兴政权服务,史称“借才异代”。“借才异代”之策帮助女真统治者有效管理了新占领地区,同时也影响到了金人“中国”观的产生与发展。金人“中国”观的产生与发展充分体现了北方民族继承发展历史上统一多民族一统思想的轨迹,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于金人“中国”观这一问题,前人已有探讨。齐春风认为,金朝初年尚未萌生金是“中国”的概念,“中国”在金初指北宋,中期指包括金朝统治区域,最后指整个中国[5]。刘扬忠认为,金人“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的产生与汉化趋势及统治中原的需要有关[6]。赵永春对金代“中国”观系统论述,认为金人自称“中国”是依据“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的理论,金朝自称“中国”并未将辽宋排除在“中国”外,而是有多统意识[7]。熊鸣琴从多角度论述金人“中国”观的发展变化,认为金人的“中国”认同在族群上不分华夷、地域上不分南北、文化上具有多元性[8]。上述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金人“中国”观的认识,为“中国”观的深入探讨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已有研究主要关注金人“中国”观发展变化、理论来源及特性特质,关于辽宋士人对金人“中国”观产生与发展的影响尚有讨论空间。本文拟从“借才异代”这一视角,探讨二者之内在关联。
一、异代文士与金人“中国”观的萌发
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加强自身统治权的合法性,是历代王朝统治者都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女真人兴起于白山黑水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但远离中原文化核心区,经济水平和文化发展都较为落后。金朝统治者在灭辽荡宋过程中,很快便意识到女真旧俗并不适用于新的被统治民族,仅依靠女真人无力统治原辽宋地区,遂大量吸收精通中原文化的原辽宋士人,为新兴政权服务。史载“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9],后人亦多认为“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煟兴”[10]。金初文化渐兴,渐立制度,得益于太祖、太宗时对辽宋士人的吸纳。辽宋士人多来自汉人聚居地区,文化修养较高,他们进入金朝后,或传礼讲学,或参与政治改革,推动了中原先进文化在女真人统治区域的传播,为金朝迅速崛起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在吸纳异代文士进入金政权的过程中,金人的“中国”观逐渐萌生。
金立国初,文化水平较低,统治者尚无认同自身为“中国”的观念。天辅五年(1121 年),金太祖诏令:“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11]在此语境中,“中”应是指金源内地,而“外”当指辽朝统治区域,表达了金人灭辽代之的志向,并未认同自己是“中国”。宋使奉命交涉燕云事宜时,金太祖对赵良嗣说:“我自入燕山,今为我有,中国安得之。”[12]说明此时金朝统治者明确以“中国”代指北宋。而异代文士的到来促进了女真统治者“中国”观的萌生。
渤海人杨朴、高庆裔等较早进入金朝。阿骨打起兵反辽后,迅速取得宁江州之战、出河店之战等战斗的胜利,辽朝统治摇摇欲坠。为进一步削弱辽朝实力,阿骨打提出“女真、渤海本同一家”[13]的口号,对渤海人实施招抚政策。女真人占领东京辽阳(今辽宁辽阳)后,继续招徕辽朝文士,“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14]东京多渤海人,杨朴、高庆裔等人应是此时加入金朝[15],很快便受到金太祖赏识,史载:
“天辅三年六月,辽大册使太傅习泥烈以册玺至上京一舍,先取册文副录阅视,文不称兄,不称大金,称东怀国。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幹、希尹商定册文义指,杨朴润色,胡十答、阿撒、高庆裔译契丹字,使赞谋与习泥烈偕行。赞谋至辽,见辽人再撰册文,复不尽如本国旨意,欲见辽主自陈,阍者止之。赞谋不顾,直入。阍者相与搏戟,折其信牌。辽人惧,遽遣赞谋归,太祖再遣赞谋如辽。辽人前后十三遣使,和议终不可成。太祖自将,遂克临潢。”[16]
杨朴、高庆裔辅佐女真贵族处理对辽事务时,承担着翻译及润色文字等工作。渤海人以通晓中原文化著称,仕辽渤海文士加入女真政权,助推了女真统治者“中国”观念的萌发。
女真人建立前长期受到辽朝的统治,以辽朝为自己的宗主国。辽道宗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17]认为契丹用中国礼法,与古代中国历代王朝无异,也是“中国”。金人俘获天祚帝,其降表中称“奄有大辽,权持正统”[18],辽人以中国正统自居。金人在与辽人接触中,对“中国”“正统”等观念有所了解。渤海文士的到来,更是加快了金人对“中国”“正统”等概念的认识与理解。杨朴在女真建立初,便向阿骨打建议:“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或求大国封册。遣人使大辽,以求册封。”[19]杨朴认为,金政权的合法性需要通过禅让或辽朝“册封”来实现。阿骨打接受杨朴建议,遣使赴辽,请求辽朝“册封”。虽然“册封” 一事因辽朝统治者的傲慢以及宋人介入不了了之,但阿骨打接受“册封”提议的行为,说明金朝统治者已接受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的理论精神,并以此谋求政权的合法地位。此后,金人开始考虑取代辽朝而自为“正统”一事[20]。
金军进入燕云地区后,逐渐掌控该区域。燕云地区多汉人,仕辽汉人比女真人有更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争取燕云地区汉族士人的支持,对确保女真人在燕云地区的统治至关重要。为巩固新占领地区,阿骨打承诺“大小官员可皆充旧职”[21],以拉拢仕辽官员。“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22],燕云地区士人的政治选择具有灵活性,许多汉人文士,如左企弓、韩企先、时立爱、刘彦宗等人审时度势,入仕金朝,得到金朝统治者重用。在仕辽文人的帮助下,金太祖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参照辽制,以汉制治汉人,在燕云地区“踵辽南院之旧”[23],设置枢密院进行管理。史载:“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号。”[24]太宗时,继续任用异代文士管理燕云地区,并将枢密院移到燕京,原辽士人韩企先、刘彦宗、时立爱等相继任职枢密院长官。设立枢密院是金朝统治者对燕云地区的统治手段,左企弓、韩企先、时立爱、刘彦宗被擢为燕云枢密院的最高长官,负责汉地的赋税征发、人才招揽等事务,“专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责任”,“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推毂士类,甄别人物,一时台省多君子。弥缝阙漏,密谟显谏,必咨于王。”[25]除在枢密院任职外,女真统治者亦安排仕金汉人参与到地方治理中,如李三锡“参与元帅府军事,改知严州”,伐宋时“领行军猛安”,“进官安州防御使”,后“改安国军节度使,除河北西路转运使”,“政事强明,所至称治。”[26]毛子廉“除上京副留守”,管理地方十余年,“吏民畏爱如一日”[27]。异代文士入仕金朝,为女真统治者在汉地的统治提供了保障,亦为金初制度增添了许多“中国”因素。
在异代文士的影响下,女真贵族为了稳定统治,开始认同并采用“中国”制度。天会二年(1124年),“平州既平,宗望恐风俗糅杂民情弗便,乃罢是制,诸部降人但置长史,以下从汉官之号。”[28]完颜宗望时任伐宋东路军最高统帅,与燕京枢密院及地方汉人官员接触较多,在其影响下,宗望罢旧制,用汉制,逐渐认同“中国”制度。宗室贵族斜也、宗幹辅政时,“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29],天会三年(1125 年),“始议礼制度,正官名,定服色,兴庠序,设选举,治历明时,皆自宗幹启之”[30]。完颜宗幹,太祖庶长子,金初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辽朝灭亡后,协助太宗进行政治改革。宗幹对仕金汉人颇多礼遇,曾主动选请原辽汉人韩昉为养子完颜亶的老师,令其传教中原文化,天会年间韩昉入职金朝礼部,“当是时,朝廷方议礼,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礼部兼太常甚久云”[31],韩昉积极参与金初制度建设。其他入金原辽宋士人亦同样得到女真贵族器重,如韩企先,“宗翰、宗幹雅敬重之”[32]。宇文虚中,原宋人,“历官州县,入为起居舍人、国史编修官、同知贡举”[33],建炎二年(1128 年,金天会六年)以祈请史的名义赴金,被金扣留。起初,宇文虚中不肯为金人所用,直至天会九年(1131 年,宋绍兴元年)七月,才“朝至上京,夕受官爵”[34]。天会十二年(1134 年,宋绍兴四年),宇文虚中开始参与金朝制度改革,“朝廷方议礼制度,颇爱虚中有才艺,加以官爵,虚中即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35],为金初典章制度改革做出重要贡献。同年,韩企先亦进入金朝中央,任职尚书右丞相,“于是,方议礼制度,损益旧章。企先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36]。在诸多异代文士的帮助下,女真统治者以“中国”制度为主体,积极构建金朝政治体制架构,推动女真政权“中国化”。在此进程中,女真统治者的“中国”观念逐渐萌生。
至天会四年(1126 年,宋靖康元年),金人攻到开封城下时,金给宋的国书中已有“今皇帝正统天下,高视诸邦”[37]等话语,明确说明金朝统治者以天下正统自居。天会五年(1127 年,宋靖康二年)金灭北宋后,立张邦昌为“伪楚”政权皇帝,册封榜文中称“恭以大金皇帝,道奉三无,化包九有,不以混一中外,为己私念,专用全活生灵,为国大恩,明下诏音,曲询众议,矜从诸夏,俾建列藩,共推宗公,以治国事。”[38]金朝统治仍自称“中”,但与讨伐辽朝时内涵有所不同。此时辽与北宋已亡,金人的“中外”观念已从辽金统治区域扩大到辽金宋统治区域。且金人“矜从诸夏”“俾建列藩”等语,显然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有取代辽宋自居正统的意味。金人册立“伪齐”政权皇帝刘豫时,提到“如构者,宋国罪余,赵氏遗孽,家乏孝友,国少忠勤……比闻远窜,越在岛夷”[39]金人扶傀儡政权统辖汉地,将南宋政权称作岛夷,名义上不混一中外,实际上已有取代辽宋,自称“中国正统”的意图。
在与高丽交涉中,韩昉作为金使出使高丽,以中原古礼对质高丽,使得高丽向金奉表称臣。
“高丽虽旧通好,天会四年,奉表称藩而不肯进誓表,累使要约,皆不得要领。而窻复至高丽,移督再三。高丽征国中读书知古今者,商榷辞旨,使酬答专对。凡涉旬乃始置对,谓窻曰:‘小国事辽、宋二百年无誓表,未尝失藩臣礼。今事上国当与事辽、宋同礼。而屡盟长乱圣人所不与,必不敢用誓表。’窻曰:‘贵国必欲用古礼,舜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诸侯各朝于方岳。今天子方事西狩,则贵国当从朝会矣。’高丽人无以对,乃曰:‘徐议之。’窻曰:‘誓表朝会,一言决耳。’于是高丽乃进誓表如约,窻乃还。宗幹大说曰:‘非卿谁能办此。’因谓执事者曰:‘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择人。’”[40]
金朝对高丽的外交胜利,体现出韩昉作为外交使臣的外交才能。此外,宗幹“大悦”及其称赞韩昉的态度,可以看出女真贵族除有对韩昉不辱使命的肯定外,还有对韩昉外交辞令的认同。即以金朝为上国,可与“中国”正统之舜、周类比,周边政权应按古礼朝会金朝。正是女真贵族认同自己乃“中国”正统政权这一话语体系,才会有“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择人”的话语。赵永春即认为,此时金人虽未自称“中国”,但萌生了视自我为“中”的思想,开始向自称“中国”过渡[41]。
要言之,金太祖、太宗时,金朝统治者吸纳辽宋士人为金政权服务,辽宋文士加入金政权,或任职中央,或出仕地方,凭借自身较高的文化素质及政治能力,客观上维护了金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在辽宋文士及其带来的中原文化影响下,金人“中国”观念逐渐萌生,并以正统自居,视周边政权为蛮夷,这是金人“中国”观念萌生的重要表现。受制于缺乏统治汉地的经验以及守旧派的桎梏,女真贵族中也存有“中国岂吾所据”[42]等声音,但这一声音湮没于异代士人及改革派引领下的政治改革中,将女真人引向以“中国”自居的道路。
二、异代文士与金人“中国”观的形成
金熙宗完颜亶自幼受异代文士影响颇深,在渐染中原文化同时产生“中国”认同。完颜亶继位后,继续重用异代文士,推动金朝政治改革。在制度建设日臻完善的情况下,熙宗提出“四海”观念,并推动金人“中国”观念逐渐形成。
完颜亶幼年时即以韩昉作为自己的老师,并跟随老师及其身边儒士学习中原文化,对中原制度、礼仪等内容有着深入了解。在学习中原文化的同时,金熙宗“中国”观念逐渐形成。史载:
“今虏主完颜亶也,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窻及中国儒士教之。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奕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由是则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大功臣则曰‘无知夷狄也’,旧大功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既如是也。”[43]
据宋人记载,金熙宗完颜亶虽不能明经博古,但其生活诸方面已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如“赋诗”“烹茶”等,都失去女真人旧态,女真旧贵族大臣皆认为完颜亶更像是一位“汉家少年子”。作为女真皇族,完颜亶学习中原文化,并在生活诸方面践行之,将不学习中原文化的守旧派视作“无知夷狄”。赵永春认为此处“汉”与“夷狄”并非种族概念,而是先进与落后的文化概念,“汉”或“汉人”在古代常是“中国”的代名词,代表着先进,夷狄蛮貊则是代表着野蛮落后[44]。金熙宗此时自我认同且被旧大臣视作“汉人”,将守旧派大臣认为是“蛮夷”,当是其“中国”认同的表现。熙宗在异代文士影响下认同“中国”,进而推行“中国”制度,并向自称“中国”迈进。
金熙宗继位后,宗幹、宗弼先后辅政,对金朝官制进行全面改革,以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这次革新,前后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对宗庙、社稷、祭祀、尊号、朝参、车服、仪卫及宫禁等诸多方面都以中原汉制为主体进行改革。在中央,三省制代替勃极烈制进行统一领导和管理,以尚书省总领全国行政事务。设御史台,置都元帅府、国史院、宣徽院等。在中原地区,官员的组成以原宋朝地方官为主,同时参用女真、契丹、渤海人等。异代文士宇文虚中、蔡靖等参与到政治改革中,史载“自古享国之盛,无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并依唐制,衣服官制之类,皆是宇文相公共蔡太学并本朝十数人与评议”[45]。在金朝中央官制改革中,礼制改革最为深入。女真人灭北宋后,“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46],草创礼制。熙宗时,金朝的礼仪制度逐渐建立。史载,天眷二年(1139 年)四月,“百官朝参,初用朝服”,六月“初御冠服”[47]。天眷三年(1140 年),熙宗幸燕,“法驾仪仗筈讨论者为多”[48],筈即原辽汉人刘筈,为刘彦宗季子,于天辅七年随父仕金,后官至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早在太宗时,刘筈即参与金朝外交礼仪的制定,“宋、夏遣使吊慰,凡馆见礼仪皆筈详定”[49],此际刘筈积极参与皇帝仪卫制度的建设,在其帮助下,“始备法驾,凡用士卒万四千五十六人,摄官在外”[50]。皇统元年(1141 年)正月,金熙宗“初御衮冕”[51],“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焕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52]。
在推动制度改革同时,金熙宗尝试提高儒学地位。金熙宗亲自祭拜儒家先师孔子,皇统元年(1141年)“熙宗诣文宣王庙奠祭,北面再拜,顾儒臣曰:‘为善不可不勉。孔子虽无位,以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如此。’”[53]并大力提高儒学地位,“诏求孔子后”,得孔子四十九代孙孔璠,“加璠承奉郎,袭封衍圣公,奉祀事”[54]。自小受异代文士影响,几乎成为“汉人”的金熙宗效仿中原王朝确定礼仪制度,尊崇中原正统文化代表、儒家先师孔子,日夜苦读儒家经典。熙宗身边儒士更是“教以宫室之状,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义之尊,府库之限”,以中原王朝“为君之道”[55]要求之。金熙宗俨然以“中国”帝王身份自居。
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 年),金对南宋册文中已有“尔越在江表”“世服臣职,永为屏翰”之语,宋高宗对于金人册封用语并无异言,而是保证“谨守臣节”[56]。北方民族政权视汉人政权为偏安一隅的臣子,汉人政权向北方民族政权称臣纳贡,彰显出女真人此时明确以“中国”正统自居,并为周边政权认同。《金史·熙宗纪》载皇统八年(1148 年)十一月,熙宗谓大臣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谚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57]宗贤等人口中的“本国人”当是指女真人,熙宗所称“诸色人”应是金朝统治区域中包括汉人、渤海人在内的其他民族。熙宗并不赞成“并用本国人”的建议,而是要求不拘族别,一律按才擢用。从其“四海之内,皆朕臣子”的观点,与上文所谈及熙宗册封宋高宗的姿态来看,他是把自己视作整个“中国”的统治者[58]。
金熙宗认同中原制度,学习中原文化,提高儒学地位,进而视自己为“中国”天子。在此基础上,金熙宗的“中国”观念不断发展,体现在追尊先祖谥号的活动中。皇统五年(1145 年),“增上尊谥曰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并解释为:
“以道合于天,灵承眷命,谓之应乾。肇启皇图,传序正统,谓之兴运。刚健文明,光被四表,谓之昭德。拯世利民,底宁区夏,谓之定功。深思远虑,贯通周达谓之睿。精义妙物,应变无方,谓之神。恭敬端肃,威而不猛,谓之庄。践修世德,丕承先志,谓之孝。贵贤亲亲,慈民爱物,谓之仁。照临四方,独见先职,谓之明。充实光辉,广被弘覆,谓之大。行道化民,博施济众,谓之圣。肃将天威,克定祸乱,谓之武。体仁长善,尊无二上,谓之元。”[59]
金人将金太祖功业说成是“传序正统”“拯世利民”“底宁区夏”“克定祸乱”之举,有意将金太祖也塑造为历代中原王朝一样的“中国”正统皇帝。此外,熙宗为祖宗上尊谥时,认为金先祖创业之功劳“与殷周之兴无异”[60]。金朝廷长达数年追尊祖宗谥号的举措,在强调皇位传承正统的同时,也有彰显金政权是“中国”正统的精神和内涵[61]。
至此,金朝地理上占有中原,制度文化上受异代文士影响颇多建构,金朝统治者已拥有自称“中国”的条件。从其吸收并效仿中原程度颇深,认同中原制度及中原文化,且周边政权均承认金朝的合法地位来看,熙宗时金人已自我认同为“中国”。
三、异代文士与金人“中国”观的发展
海陵熟习中原文化,对中原文化及中原制度了解更深。海陵即位后,仍认同自身“中国”天子地位,重用异代文士,深化政治改革,清除女真旧制。其后,受其“中国”观念影响,海陵主张迁都燕京,明确以“中国”自居。在制度成熟与迁都中都的前提下,其“中国”观念进而发展为“大中国”观念,对后世统治者产生深远影响。
海陵王完颜亮自幼接受了较深的中原文化教育,受中原文化影响更深。据记载,完颜亮自幼即“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登上帝位后“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62]。海陵王虽是篡位登基,但自小受中原文化耳濡目染的他,仍如金熙宗一样推崇“中国”文化与制度,自我认同为“中国”君主。
海陵继位后,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清除女真旧制。“罢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63]。正隆元年(1156 年),完颜亮颁行“正隆官制”,罢“中书、门下省”[64],只存尚书省,创立一省制度的新体系,加强君主集权。完颜亮比完颜亶更加注重儒学教育发展。天德年间,“初置国子监”[65],“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传以词赋取士”。贞元元年“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66]。金朝科举制度得以更加完善。熊鸣琴对海陵正隆官制后宰执人员构成统计分析,得出外族人在宰职集团中的比例和官职相比之前有明显提高和增多的结论[67]。据笔者目及,正隆年间宰职集团中仍有异代文士的身影,如蔡松年(降金宋人蔡靖子)、李通(降金宋人)、渤海人张浩(降金辽人),异代士人在海陵时仍在金朝中央发挥着重要作用,“海陵迁中都,徒榷货务以实都城,复钞引法,皆自松年启之”[68]。
伴随着政权建设的成熟,海陵“中国”观也有一定发展,主要体现在海陵主张迁都燕京及伐宋的决策中。“是时,上封事者多陈言,以会宁僻在一隅,官难于转输,民艰于赴诉,宜徙居燕山,以应天地中会”[69]。海陵令原辽士人张浩、张通古征募天下工匠,耗费三年时间建成新都。金上京深处女真内地,交通不便,且“中国化”程度较低,而燕京地处中原,是汉人聚居区,拥有较深的文化底蕴。所谓“燕京地广土坚,人物蕃息,一乃礼义之所”[70],更符合海陵的统治理念。可见海陵同意迁都的建议是为了对应“天地会中”之语。中国古代有占据中原即为“中国”的讨论,海陵迁都燕京,当是有借助这一观念自称“中国”的意图。至海陵伐宋前后,金人已明确以“中国”指称金朝。如海陵嫡母徒单氏认为:“国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我尝谏止之,不见听”[71]。梁珫对海陵伐宋表示支持,史载:“议者言珫与宋通谋,劝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国”[72]。这两条史料所说“中国”,都是指金朝,说明海陵王完颜亮时,金人已经习惯以“中国”称呼金朝了。可见,金人进入中原地区后,即继承“占据中原即中国”的理念,明确以“中国”自居[73]。
但从海陵南伐举动来看,他并不满足于历代以来“占据中原即中国”的“中国”观念。海陵在阅读《晋书·苻坚传》时,感慨“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帝纪归之,而以列传第之,悲夫”,并对大臣蔡松年等人说:“朕每读《鲁论》,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74]与金熙宗不同,海陵并不否定自己是“夷狄”,但他认为不应以地域及民族区分贵贱尊卑。前秦皇帝苻坚占据中原,却未被视作“中国”正统,这对以“中国”天子自居的完颜亮是一种刺激。在这种反对以种族和地域区分贵贱尊卑,渴求更大功业以证明金朝正统性思想的支配下,海陵在定都燕京后,又下诏营建南京开封府,造战船,南下伐宋。此时,海陵王已有灭宋一统来彰显金朝是“中国正统”的观念,并宣称“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75],“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76]。在海陵王与张仲轲论《汉书》时,海陵王对张仲轲说:“汉之封疆不过七八千里,今吾国幅员万里,可谓大矣。”张仲轲回答曰:“本朝疆土虽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东有高丽,西有夏,若能一之,乃为大耳。”[77]说明海陵王时,认识到金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只有将南宋的版图纳入金朝,才可称作“中国正统”。赵永春认为这是一种不分华夷,不分中外的“大中国”观念[78]。海陵伐宋虽以失败告终,但这一观念影响着元明清时期的“中华一统”意识。
海陵幼时即在异代文士影响下,受汉文化熏染,即位后重用汉人及渤海人,仿效中原制度,继续推进金朝制度改革,其确立的“中国”式政治制度为之后金朝统治者所继承。在制度建设完善的前提下,海陵对熙宗时的“中国”观进一步发展,他以“中国”天子自居,迁都中都,“应天地中会”,又南伐宋朝,尝试通过统一天下来证明金朝是“中国”正统政权,形成了“大中国”观念。在制度、文化、教育及地理等因素影响下,海陵时金人已普遍自称“中国”。海陵以后的金朝帝王仍以“中国”自居,并进一步通过讨论德运等方式论证金王朝的正统性。
四、结语
金朝是女真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肇兴于中国东北地区,历时百余年。从“夷狄中至贱者”到“文物远盛辽元”,金朝文化发展迅速,这与统治者起用精通中原文化的士人密切相关。金朝统治者在灭辽伐宋过程中,吸收大量异代文士,并依靠他们统治中原汉地。在这一过程中,女真统治者受到中原文化中的“中国”意识和“正统”观念的影响,为确立自身统治合法性,有意识地吸收中原制度,推动政治变革,并以“正统”身份自居,而将周边政权称作蛮夷,逐渐萌生“中国”意识。太宗认同“中国”制度、推动政治改革的举措为熙宗继承,熙宗幼年受异代文士影响,更是以“汉人”自视,在改革派宗幹及异代文士的辅佐下以中原王朝制度为主体积极构建政治体制,逐渐以“中国”正统自居,其在皇统年间为列祖列宗上尊谥的行为进一步体现了其以“中国”天子自居的观念。在熙宗观念中,四海之内都应是金朝的臣子,南宋、高丽等都受到金朝册封,其君主也认可了金朝正统地位。海陵王继续推进金政权的中原化变革,更是以“中国”天子自居,迁都燕京以“应天地之中”,且不满足于“入中原者为中国”的理念,企图一统天下来证明金朝的“中国正统”,将金人的“中国”观提升到不分种族、不分地域的“大中国”层面。从海陵时的记载来看,金人此时已普遍以“中国”代指金朝,这显然是金人自我认同为“中国”,是中国认同得以继承的有力证明。而后金世宗、金章宗受其先人自称“中国”及“中国正统”的影响,也标榜金朝的“中国正统”身份,并通过“仁德”“德运”等理论论证自身作为“中国”的正统性。值得一提的是,金人在自称“中国”的同时,并不否认辽宋也是“中国”,存在承认辽宋都是“中国”一员的思想意识,即辽人、宋人、金人都是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中国人”,这是统一的各民族的中国人出现之必要历史前提[79]。异代文士参与到金朝的内政外交中,在金人“中国”观的萌发、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异代文士的辅助下,金朝统治者以中原王朝制度为主体积极构建符合时代特色的政治体制,更多的“中国人”加入认同“中国”的行列中来,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奠定了基石。金人“中国”观的形成与发展充分体现了北方民族继承发展历史上统一多民族一统思想的轨迹,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