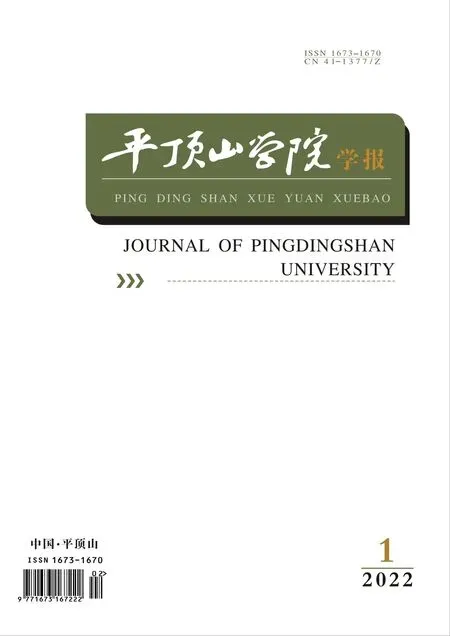王弼易学中的“情志”论
廖海华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王弼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据相当特殊的地位,其《周易》诠释上接汉代经学,下启魏晋玄学,是汉末魏晋学术思想转化的关键(1)唐君毅先生曾说:“王弼在中国思想史中之特殊地位,在其由经学以通玄学。”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序中将《周易》王弼注与郑玄注相比,认为“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1]序8。就《周易》卦爻辞本身来看,其内容确实主要为人在社会中之种种活动,王弼以“人事”为其诠释重点,无疑切中肯綮。从王弼的视角来看,《周易》诠释最根本的目标是要理解人的行为活动。而要理解人的行为,又必须理解这些行为的内在原因,也就是驱动这些行为的内在之“情”与“志”。由此可知,王弼之所以能在汉代易学之外别立一家新学,且渐渐取汉易而代之,其“情志”论应该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现有的研究中,对王弼的“情志”论关注不多,人们或曾从玄学研究的角度注意其“圣人有情”“性其情”的著名论断(2)可参考汤用彤先生《王弼圣人有情义释》一文,收入汤用彤:《汤用彤集》(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87—1795页。较近期研究可参考武道房:《儒家圣人观念的承继与开新——论王弼圣人性、情新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见《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第132—138页;王光照、仲晓瑜:《性、情及圣人——王弼性情理论探析》,见《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40—44页。,但对其“情志”论的整体内涵少有考察。因此,本文尝试结合王弼的易学诠释来探求其“情志”论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为理解其思想特色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一、王弼易学中行动主体的设定以及卦爻辞基本内容
考察王弼易学中的“情志”论,需要处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情志”概念在王弼的《周易》诠释体系中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占据怎样的地位?众所周知,《周易》古经包括卦爻辞和卦爻系统两个部分。卦爻辞(含卦名)由文字组成,而卦爻系统的内部则分布着各种单元结构,这些“结构”乃几何图形与思想意义的结合体。如何在卦爻结构与卦爻辞之间构筑起合理的、有机的联系,乃是《周易》诠释的基本课题(3)朱伯崑曾指出,历代的易学家“都努力寻求卦爻象和卦爻辞间的内在的联系”,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以证明《周易》是神圣的典籍,具有完整的奥妙的思想体系”。这是易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中心主题。详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情志”概念之所以重要,就跟王弼对这一课题的独到处理方式有关。
我们可以从卦爻辞开始看起。对于每一条卦辞和爻辞,王弼基本都要为之设定一个行动主体。对于此主体,王弼有时会明言之,称为“己”“我”“君子”等。如需卦上六爻“入于穴”,王弼注云:
至于上六,处卦之终,非塞路者也。与三为应,三来之己,乃为己援,故无畏害之辟,而乃有入穴之固也。[2]247
在王弼看来,需卦上六爻之所以能够“入于穴”并安然处之,是因为此爻与九三爻阴阳相应,九三对于上六是援助而非危害。因此,上六并不需要避让九三,而只需安处本位,等待九三之到来即可。在这一解释过程中,王弼将上六称为“己”,即意味着解释者或读者需代入此爻的视角中、从这一主体的立场出发来考虑问题。当然,在更常见的情形中,王弼对卦爻辞所隐含的主体并不明言,但其意思是一样的。如需卦初九“需于郊,利用恒”,王弼注云:
居需之时,最远于难,能抑其进。以远险待时,虽不应几,可以保常也。[2]245
所谓“居需之时”“能抑其进”,“居”和“抑”的主语是什么?虽然王弼并未明言,但类比需上六的例子可以知道,此主语无疑就是指初九爻自身,是解释者需要代入其视角、将之视为“己”来加以考虑的那个行动主体。解释爻辞时将爻本身视为一个行动者,且代入其视角来理解其行为,这种解释方法可以用王弼注解乾卦《文言》时说的“以爻为人,以位为时”[2]216来加以总结。不仅爻辞如此,王弼对于卦辞的解释实际上也遵循这一路径。在王弼的体系中,卦辞大多是围绕作为卦主的某一爻来叙述的。正如《周易略例》所云“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2]591,此所“立”之“主”,在王弼解释卦辞时即往往被设想为一种行动主体。
在王弼易学中,对各个具体的卦爻设定行动主体之后,其卦辞或爻辞就围绕这一主体而展开,以此主体为叙述焦点。对卦爻辞的这种理解,是王弼易不同于汉易的一个重要创新。汉易学者不像王弼这样有意识地、系统性地为卦爻辞设定行动主体,因此在其解释中,卦爻辞的主语可以较为随意地变换,在同一句卦爻辞中叙述的焦点往往不断变化。如否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荀爽和王弼的解释分别如下:
二与四同功,为四所包,故曰“包承”也。小人,二也。谓一爻独居,间象相承,得系于阳,故“吉”也。大人谓五,乾坤分体,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应,否义得通,故曰“否,亨”矣。[1]103
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至顺,包承于上。小人路通,内柔外刚;大人否之,其道乃亨。[2]281
按荀爽的解释,否六二爻辞总共有三个主语。“包承”的主语是九四,意为九四包六二,“小人吉”的主语是六二本爻,而“大人否、亨”的主语则是九五。爻辞的叙述焦点先从九四转到六二,后又从六二转到九五。但若按王弼的解释,则六二爻辞的主语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即“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的那个行动主体。此主体根据其所处之时位,可以完成“用其至顺,包承于上”的行为。而且,主体如果自甘为“小人”,则根据所居之时位,“包承于上”已经足以得小人之吉;主体如果欲成为“大人”,则需要“否之”才能得到“其道之亨”。在王弼的解释中,爻辞的叙述焦点始终集中在所设定的主体上,是围绕此主体而展开的。
由上述对比可知,行动主体的设定在王弼易学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构成其卦爻辞解释的前提。了解这一设定之后,我们可以围绕“行动主体”这一概念来对卦爻辞的基本内容作出归纳和分类。
首先,卦爻辞一般会描述主体所发出的行为或所呈现的状态。以屯卦为例。初九“盘桓”,是说此主体处于盘桓不进的状态;六二“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是说此主体如女子守贞一般,坚定不动,十年之后才有所遇合;六三“即鹿无虞”,是指此主体(爻辞后文称为“君子”)在缺乏虞人引路的情况下追猎禽兽;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是说此主体寻求与对象(即应爻初九)之“婚媾”;如此等等。整部《周易》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几乎无不包含(或隐含)这种关于主体之行为(或状态)的说明。
其次,卦爻辞往往会描述主体行为所引来的后果,以及基于此后果而对主体所作之告诫。仍以屯卦为例。六三爻辞“惟入于林中”,是说主体“即鹿”的行为并不能得到好的结果,只能徒劳一场。因此,爻辞作出如下告诫:“君子几,不如舍。往,吝。”此即告诫主体不如舍弃“即鹿”之行为。如果不愿舍弃,执意继续有所“往”,则必然导致“吝”的后果。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卦爻辞有时会根据应然的义理原则来评价、衡量主体之行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主体做出告诫。如屯卦九五爻:“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九五居于一卦之尊位,本应广施恩泽,但其不能如此,反而“屯其膏”。因此,“小贞”之事尚无大碍,“大贞”之事则无法顺利进行。按王弼的解释,九五为其私心所限制,违背了“恢弘博施,无物不与”[2]236这一“公”之原则。
上述三个类别,已经将《周易》卦爻辞的大部分文字囊括在内。也就是说,在王弼易学的视域中,围绕着某个行动主体而展开的卦爻辞,实质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主体之行为,另一个部分则是由此行为而引发的后果、评价、告诫等。主体行为无疑是卦爻辞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确定了主体与其行为之后,才能再由此讲到相关的各项内容。
至此,我们可以触及王弼易学中一个非常要紧的问题:主体之行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对于某个具体的卦爻,其主体之所以采取如此这般的行为,其原因究竟何在?应该如何加以理解?这个问题就将我们引向王弼的“情志”概念。
二、“情志”概念对于卦爻辞的解释功能
通观王弼的易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要理解主体之行为,关键是理解作为其内在驱动力的情志。所谓“情志”,乃是笔者对王弼作品中相关内容进行归纳之后所综合出的一个概念。在王弼的原文中,更多的是“情”字或“志”字的单独使用。此外,“意”“欲”“心”“愿”等若干字眼,在王弼系统中也是与“情”“志”相类的概念。这些词汇大致都是指称主体之心灵活动,只是它们所强调的重点略有不同。例如,如果强调心灵活动是有其明确目标指向的,那么一般用“志”字;如果强调心灵活动在当下将有所选择、有所动作,那么往往会用“欲”字;如果是泛称心灵活动的状态或强调其情绪性内容,则喜用“情”字。其间关系可以用“浑言无别,析言有异”(4)“浑言”“析言”乃是清代小学家分析同义词、近义词时常用的术语。如段玉裁分析“夜”与“夕”两字的关系时说:“夜与夕浑言不别,析言则殊。”详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七篇上“夕”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来加以概括。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其“异”的方面不太重要,因此下文不再一一区分,而统称为主体之“情志”。之所以将“情”与“志”两字特别加以突出,主要是考虑到王弼作品中这两个字均有着特殊的分量。在王弼《周易注》对具体卦爻的诠释中,“志”字最为常用。在其《周易略例》中,则“情”字又得到了较为突出的强调,而且“情”字常与“性”字对举,在哲学理论的表达方面较为重要。王弼对“情”与“志”的重视,显然是以《易传》为其根据的。如《彖传》喜欢讲“天地万物之情”,而《系辞传》说“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小象传》中“志”字更是出现几十次之多(5)对“情”的重视乃是《易传》的特色。唐君毅曾说:“《易传》为书,于‘情’之重视,盖犹有甚于‘性’者。”其说颇有见地。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王弼的“情志”论正是继承《易传》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的结果。
那么,王弼具体是如何运用“情志”概念来对主体之行为加以说明的?仍以屯卦为例。王弼对屯卦二、三、四、五爻的解释都涉及“志”这个概念。以下列举这四条爻辞王弼注的相关内容:
志在于五,不从于初。……故曰“女子贞不字”也。……十年则反常,反常则本志斯获矣。故曰“十年乃字”。[2]235

二虽比初,执贞不从,不害己志者也。求与合好,往必见纳矣。故曰“往,吉。无不利”。[2]236
系应在二,屯难其膏,非能光其施者也。固志同好,不容他间,小贞之吉,大贞之凶。[2]236
屯六二爻辞为何说“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这是因为六二“志在于五”,即使在初九的侵扰之下,仍“不从于初”,坚持等待,最终“本志斯获”。六三为何出现“即鹿无虞”之妄动?六三这一主体也志在于九五,同时观察到九五侧近的六四“志在初”,对自己不会构成妨碍。六三“见路之易”,却忘记揆度九五之“志”,忽视了九五与六二的相应关系,所以导致妄动,而最终不被九五所接纳,徒劳无所得。六四则志在于应爻初九,且准确地观察到初九侧近之六二“不害己志”,不与己争,所以爻辞云“往,吉。无不利”。九五则与六二阴阳相应,“固志同好,不容他间”,所以只专注于六二,不能“恢弘博施”,导致如爻辞所说的“屯其膏”。
由此例可知,如果没有对于主体情志的体察,则王弼对屯卦诸爻辞的解释均无法完成。在王弼易学的视域中,所谓“行为”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外在的现象,而是被领会为由内在情志所驱动和主导的现象,解释者必须以“切己体察”的方式才能达到对此现象的理解。由于主体行为乃是卦爻辞的核心内容,这种将行为还原为情志的理解方式无疑会对卦爻辞解释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例如,卦爻辞中关于行为后果的判断,往往可以转化为对主体情志是否得以满足的判断;卦爻辞中关于行为是否合于义理的评价,可以转化为主体情志是否合于义理的评价。而“情志”论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则是王弼通过对卦爻辞中告诫之辞的诠释展开了一套以情志为中心的工夫论。
卦爻辞之所以会有对主体的告诫之辞,主要原因无外乎两种:主体之行为在结果上不利或行为有违背义理原则之处。告诫之辞的作用在于引导主体改变其自身的行为,但既然行为是由情志所驱动的,那么这种改变往往在根本上就是主体对自身情志的改变。这样一来,《周易》的告诫之辞就有了相当深刻的工夫论意义(6)“工夫论”一词有广狭两义。如王正就儒家工夫论说,“广义的工夫论就是儒家所讲的如何实现内圣外王的具体方法”,但“儒家认为外王要从内圣推出”,因此其狭义的工夫论则“偏重于内圣”。详见王正:《先秦儒家工夫论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王弼通过诠释《周易》关于行为活动的吉凶告诫之辞,将之引向主体情志自我转化的层面,可谓兼涉“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无论在狭义上说还是在广义上说都当得起“工夫论”一词。。关于这一点,可用比卦九五爻“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为例加以说明:
为比之主,而有应在二,显比者也。比而显之,则所亲者狭矣。夫无私于物,唯贤是与,则去之与来皆无失也。夫三驱之礼,禽逆来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爱其来而恶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以显比而居王位,用三驱之道者也,故曰“王用三驱,失前禽”也。……虽不得乎大人之吉,是显比之吉也。此可以为上之使,非为上〔之〕道(也)。[2]262
在王弼看来,九五爻居于比卦君主之尊位,本应该做到“无私于物,唯贤是与”,但此爻“有应在二”,其亲比之情主要倾注于应爻六二。这是一种显比:“比而显之,则所亲者狭矣。”即如田猎中的“三驱之礼”一样,对于向自己奔来的禽兽,视之为归附者,所以舍之不射;对于背离自己逃走的禽兽,视之为背叛者而加以射杀。这种“爱其来而恶于去”的好恶之情,在某种意义上无疑也是人之常情,但对于“王”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有鉴于此,爻辞加以“失前禽”之警戒。为了能够做到“去之与来皆无失”,那么主体就必须进行一番化除自身私情私意的工夫,由此才能获得“大人之吉”(7)王弼认为“王用三驱,失前禽”表示“爱来恶去”,不能做到“无私”,这种解释是相当独特的。后世易学中,如程颐认为“王用三驱”即“天子不合围”之礼,表示王者仁心及于禽兽,而“失前禽”则是对于前去之禽兽往者不追,也表示“王道之大”。朱熹之说与程颐相似。分别见程颐:《伊川易传》(收入《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2页;朱熹:《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7页。。
如果说比卦九五爻的例子是重在说明如何以“公”之原则转化私情,指点出了情志工夫的方向,那么王弼“性其情”的论述则更进一步,涉及了情志工夫如何持恒不变的问题。乾卦《文言》王弼注云:
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2]217
关于王弼的“性其情”,孔颖达《周易正义》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可供参考:“性者,天生之质,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则不能久行其正。”[3]33将“情”定义为“性之欲”,可与孔疏在另一处所说的“随时念虑谓之情”[3]13相参照。“性”本身一定是“正”的,“情”“欲”虽为“性”之所发,但却为“随时念虑”,是随后天时境而变动不已的,因此并不能保证其“正”,而往往流于“邪”。如果不能“以性制情”,那么也就不可能“久行其正”。即使最初有行正之情、行正之欲,也不能“久”,不能终始如一。
关于主体自身情志的改变与转化,可说是关于“己之情”所应做的工夫(8)王弼关于“己之情”所说的工夫论,对后来宋代理学工夫论有相当的影响。冯友兰先生指出,“后来宋儒对付情感之方法”与王弼是相同的。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7页。,但在王弼的情志工夫论中,还有颇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即关于“物之情”的论述。在王弼注中经常见到“物”字,此字的意思并非如现代汉语中那样主要指无生命的物质或物体,而是主要指处在同一卦时中的其他行动主体。从上述屯卦诸爻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到,主体行为在后果上的不吉、不顺,往往是因为未能调顺主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他人之合作;而他人之所以不合作,归根结底又出自他人自身的情志。如屯卦六三与六四两爻之所以在结果上一吉一凶,就是因为六三对于应爻九五未能“揆其志”,而六四对应爻初九则做到了“见其情”。《周易略例》将这种情况归纳为“见情者获,直往则违”[2]597。由此,王弼极为重视主体对他人之情志(所谓“物之情”)所应有的察识与顺应之工夫。关于这一点,可以如下两条注文为例:
夫体无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2]228
若能不距而纳,顺物之情,以通庶志,则得吉而无咎矣。[2]451
《周易略例》所说的“见情”,重在对于他人情志的察识与明见。在察识的基础上,则需要如升六四注所说,“顺”其情,“通”其志。而坤六五注所说的“极物之情”,应该是指对于“物之情”的顺通工夫达到极致。按此注所说,则若“体”是刚健,那么或许有一种强健之力,可以对“物”产生吸引的作用。坤六五爻作为阴柔之爻,则“体无刚健”,但是仍然能够“极物之情”。这主要是因为其能够“通理”。物之情随时而变动,是一种变动不已的现象,然而现象背后有“理”,只要能够通达于此“理”,那么就有助于主体对于“物之情”的认识和顺应。
综上所述,卦爻辞中所包含的行为、结果、评价、告诫等项内容,均与主体之情志密切相连,无不可通过与“情志”概念的结合而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与阐释。由此,又触及了一个新的问题:主体的情志从何而来?正如上引孔疏“随时念虑谓之情”这一定义所暗示的那样,主体情志之产生或变化无疑与其所处的“时”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主体所处之“位”、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等也都是能对其情志产生一定影响的因素。在易学语境中,这些因素都蕴含在卦爻系统的内在结构中,由此,我们需要转向本文的最后一项考察内容:王弼易学中卦爻结构与主体情志之间的关系。
三、“情志”概念与卦爻结构之关系
综合王弼的易学作品可以看出,卦爻结构主要蕴含三种意义:主体所处的时与位、主体自身所固有的某些性质以及主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时位、主体性质、自他关系也正是讨论主体情志之产生与定型时无法忽视的三项重要因素。以下拟分别探讨这三项因素与情志概念之间的关系。
正如王弼《周易略例》所说,“卦以存时,爻以适变”[2]598,“夫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2]613。“时”以及“位”乃是卦爻结构的主要意涵所在,同时也是主体身处其中的某种根本性、本质性的境遇,因此,时位对于主体之情志有着极为重要的规定作用。关于这一点,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投戈散地,则六亲不能相保;同舟而济,则吴越何患乎异心。”[2]597“六亲”以相保相亲为其常态,然而,若处在“投戈散地”之“时”,则六亲之间也难免产生“不能相保”之感。同样,吴越两国本为互相厮杀的世仇,但若在“同舟而济”之“时”,则两国之人也将同心同德。主体总是被置入某种具体的时位中,面对这种时位、境遇而心灵有所活动、有所念虑,此即“情志”。时位周流运转,变动无穷,而主体之情志也随之变动无穷。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时位相对于情志乃是一种先在性的背景,对情志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并不是说时位就完全决定了情志。情志始终保有自由变动的空间,所以主体才有可能在告诫之辞的引导下改变其情志。如果情志是被时位所完全决定而固定不变的,那么卦爻辞的告诫将变得毫无意义。
关于主体固有性质与其情志之间的关系,《周易略例》中有一段较为集中的讨论:
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夫情伪之动,非数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与体相乖。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巧历不能定其算数,圣明不能为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齐,度量所不能均也。[2]597
从王弼的这段论述中,可以抽取出两组概念来:一组是“体”“形”“质”这类用以表示主体固有性质的概念,另一组则是“好”“爱”“情”“愿”这类用以表示主体情志的概念。从《周易注》的具体用例可以看到,“体、形、质”这类性质是可以从卦爻结构中直接读取出来的。例如,对于刚爻,王弼常称其“体刚”“体夫刚健”“刚质”“阳之质”,对于柔爻,则常称其“体柔”“体夫柔顺”“阴质”。又如,蛊卦初六,因处于下卦巽体中,王弼称之为“柔巽之质”[2]308;未济卦九二,乃是处在下卦之中的刚爻,王弼称之为“体刚中之质”[2]532。可见,卦爻的“体、形、质”如何直接对应于其爻性、爻位等,乃是外显性的、稳固的特征。王弼这段论述的重点在于指出,“体、形、质”这类固有体质不能完全决定主体之情志,情志的方向往往与固有体质相反。然而,这并不代表固有体质对于情志没有影响。我们不可忘记,正是因为在大量情况下主体情志的方向受到其固有体质的影响,所以王弼才需要做这种辨析,以便读者能将两者区分开来。总的而言,主体之“体、形、质”仍应算是情志形成的一类重要影响因素,是情志产生的前提与背景之一,只是其对情志的影响显得不是那么确定。同时,与固有体质所具有的外显性、稳固性相比,主体之情志是内隐的,而且随着时境的变化而变动不已,因此,两者之间就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周易略例》所说“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应该放在这个语境中来理解(9)值得注意的是,“体、形、质”一类概念也是汉末魏晋时期的形名之学所重视的概念。如刘邵《人物志》第一篇《九征》云:“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又云:“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详见刘邵:《人物志》,北京:中国书店,2019年版,第14、18页。。
以上所述时位与主体固有体质这两项因素,可以说都是在主体之情志产生之前就已经先行存在的,相对于情志乃是一种“先天性”因素。相较而言,自他关系与情志之间则更接近一种相互摄入的状态。一方面,主体情志之产生在许多情况下无疑受到自他关系的影响。仍以上文屡屡提及的屯卦为例。屯六二“志在于五”,此“志”就来源于六二与九五之间的阴阳相应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考虑主体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形成中往往已经有双方情志在起作用。这是因为自他关系中本就包含客观与主观两种不同的要素。如屯卦六二与初九之间的关系,王弼称之为“相近而不相得”[2]235。此两爻是一种“相比相邻”的“近”之关系,这种空间上的“近”乃是一种客观状态,然而两者之间的“不相得”则是由六二与初九相互之间的某种情志作用所造成的。初九作为屯卦下卦的唯一阳爻,欲吸引其旁之六二,而六二却“志在于五”,并不愿意接纳初九之追求。正是两者各自所怀有的情志,导致了彼此“相近而不相得”的关系。由自他关系与主体情志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可以看出,在上述卦爻结构的三项意义之中,第一项“时位”与第三项“自他关系”虽然都可说是主体所面临的一种外在情境,但两者是有所区别的。时位乃是一种先在的东西,是主体被置入其中的先天性境遇。如屯卦九五爻,此爻处在屯难之时,居于尊位,这种时与位都是先在的,是屯九五这一主体所必然面对的境遇,其存在不需依赖于主体的心志和行为。相反,主体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则需要通过人的心志活动才能得以最终确定和呈现。
四、结语
综合本文所论,在王弼易学中,情志的位置实际上介于卦爻结构与卦爻辞之间,是两者之间一个必不可少的“连接点”。一方面,情志与卦爻结构有深入的联系,其根据深植于卦爻结构中;另一方面,情志虽一般未被记录在卦爻辞中,但对卦爻辞中各项内容均有极好的解释功能。情志论之所以在王弼易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主要就是因为它具有这样一种“连接点”的功能。王弼《周易注》对具体卦爻的诠释,一般总是从卦爻结构讲起,然后导向对于主体情志的理解,通过此情志来说明主体之行为,再由行为讲到其后果、评价以及相应的告诫之辞。若将之简化,则是一种卦爻结构—情志—卦爻辞的连锁关系。通过这一解释,王弼出色地完成了将卦爻结构与卦爻辞贯通一体的易学基本课题。对“情志”概念的运用,也使得其易学诠释与之前的汉易相比面貌大为不同。在汉易中,卦爻辞中的“行为”或“变化”一般会被直接还原为卦变、爻变、升降一类的卦爻象变化,因此,汉易虽然善于论述卦爻象变化所象征的天道之周流运转,但其对卦爻辞中“人事”方面的理解确实容易流于表面和机械。王弼对行动主体之设定以及对主体情志之深入体会,使得卦爻辞中关于“人事”的简单记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理论纵深,将《周易》经传构筑为一个事、情、理交融互发的立体性意义世界。其情志论的易学史价值可谓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