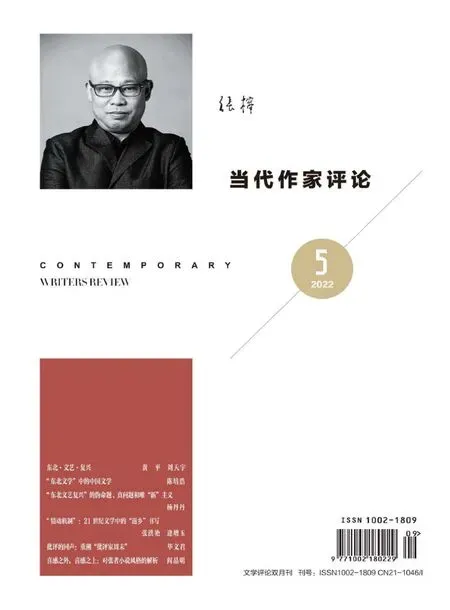“诗性”与“歌性”的互融
——当代诗歌的“宋词模式”探析
刘东方
一、现象说
中国古代诗歌史中,歌诗作为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从《诗经》、楚辞、乐府、南北朝民歌,再到唐声诗、宋词、元曲,歌诗底蕴博赡、源远流长,特别是宋词更具代表性。宋词依照曲牌的曲调格律填制词句,①宋词有很多选词配乐筛选后保留下来的曲牌,这些曲牌都是固定曲调的形式。据清代王奕清的《词谱》统计,不同的词牌有826个,后人补充后达1000余种。因曲调的长短决定词句的长短,宋词也被称为“曲子词”“长短句”。实际上,宋词就是当时的歌词,初始由乐工、歌女填词,大多简单粗俗,经知晓音律的文人将其“镀金”后,宋词由“令”“引”“近”发展为“慢词”,②“令”为一种篇幅短小的歌曲;“引”为唐宋大曲之后的引歌;“近”为大曲的慢曲过后渐快的曲调,它们都篇幅短小。“慢词”指曲调悠长、节奏舒缓,篇幅较长的歌曲形式。篇幅更大,审美性更强,愈发精致典雅,具备了诗歌的质素。宋词的这种生产方式使其插上了音乐的翅膀,扩大了传播途径与受众范围。其后,尽管它的音乐形式丢失了,③譬如姜夔曾收录大量宋词曲谱的《乐府浑成集》,在元末明初就失传了。但作为歌词的宋词,实现了歌诗与诗歌的有机融合,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新体式,成为古代诗歌雅俗共赏的经典文体类型,这就是本文所谓的“宋词模式”。但现代以降,我们的诗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这种诗歌与歌诗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呼应、你我难分的“宋词模式”,并由此带来了较大的问题。
自清末民初始,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白话势必“打破传统白话讲究‘口’与‘手’一致的‘声音场’的限制,赋予它新的言语方式,适度地与声音脱离,使白话进入‘文字中心’,开辟一个充满着张力的白话‘文字场’”。④徐德明:《中国现代叙事的语言传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现当代诗歌也如此,“当诗歌变成纸面上的文字,对‘视觉’的依赖自然超过了对‘声音’的要求”,⑤鲍良兵、孙良好:《作为被压抑了的现代歌诗——早期新诗音乐化的想象、实践和启示》,《浙江学刊》2015年第4期。人们习惯于“看”诗而非“听”诗,诗人创作时更注重诗歌的视觉效果,“声音”在诗中似乎变得“无足轻重”。现当代诗歌的创作方式、阅读方式、传播方式与古代歌诗传统,特别是“宋词模式”,完全割裂,它不再入乐而唱,与音乐行渐分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书面化、默读式的文体,更偏重于语言、思想与哲学层面的思考,追求所谓的“诗性”。长此以往,现当代的诗歌变得越来越高雅化、神秘化甚至晦涩化,现当代歌诗则以歌曲歌词的方式转型呈现,它以配乐演唱为主要传播方式,语言通俗易懂,旋律和谐优美,逐渐发展为大众化、通俗化的艺术体式,从流行歌曲、电影插曲,到红色歌曲、革命歌曲,再到摇滚歌曲、MTV歌曲等,受众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越来越强。
21世纪以来,诗歌与歌词二者之间的割裂现象呈现逐步加大的趋势。伴随着互联网多媒体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人们对传统纸质媒体的关注度不断降低,纸质版诗歌刊物的发行量逐年减少,受众范围和影响力度愈加萎缩。诗歌面对当下数字网络时代较20世纪更加力不从心,诗歌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受到进一步压缩,诗歌的地位愈发边缘化。近年来,数字化、多元化类型的歌曲形式迅猛发展,如网络歌曲、“经典咏流传”类型电视节目中的歌曲等,当下歌诗较20世纪形式和内涵更为丰富,更加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和欢迎,影响力和作用力更大,对诗歌的冲击力也更强。同时,就创作主体而言,当下写诗的人不愿意写歌词,而且词作者或是专职作词人,或由音乐界的跨界人士担纲,他们与诗歌创作少有“交集”和勾连。可以说,归属于音乐学科的歌词创作已经脱离了诗歌的轨道“自由”发展,并与诗歌呈现出“各自为政”的局面。针对当前这种歌诗与诗歌相互分离的现象,笔者认为,我们应借鉴“宋词模式”,重视诗歌与歌诗的相容与相融,重视当下诗歌的“歌性”功能研究,为当下诗歌发展摆脱困境寻求对策。
二、原因说
作为产生了中国古代诗歌经典的“宋词模式”,其在当下的式微并非无缘无故,而是有因可循。
首先,20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学科理念的输入,我们也逐渐建立起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现代学科门类,其中,带有“歌性”功能的歌诗被划分至现代音乐学学科,诗歌则归属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从学科诉求与专业要求出发,诗歌与音乐脱离,拘囿为纯粹书面化的默读体味式文体形式,追求语言逻各斯和现代诗学范畴内的“诗性”,不参与音乐领域内歌词的创作和发展;与此同时,歌诗创作由专业词人、谱曲作者和专业歌手等专业音乐人一起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也不参与诗歌的创作,两者界限森严,交集甚少。由于学科细化后产生的“厚壁障”,诗歌与歌诗已经无法像“宋词模式”那样亲密交融、互促互进,只能在各自固定的学科领域内,单维度地踽踽独行。
其次,文体功能的不同也是“宋词模式”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诗歌发展历程来看,中国诗歌的总体趋势为逐步从歌乐一体的模式中剥离出来,摆脱对音乐的依赖,向语言文字的维度发展。秦汉时期有专门的乐府机构进行民间采诗,负责采集民间之诗或飨宴乐歌,进行整理、编纂,其目的是为了观民风,解下情,知政教,察得失。宋词虽然也像汉乐府一样,是一种音乐文化,但其文体功能与汉乐府截然不同,无论是曲牌还是歌词,都是个人化的抒情言志。至现代,受西方诗歌哲理化、私人化、隐秘化的影响,现当代诗歌在个人化功能向度上相比宋词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纯诗”“象征诗”“朦胧诗”“第三代诗”,或追求诗的“纯粹性与暗示性”,或推崇“意象的朦胧”,或坚持“反崇高的姿态”,都十分注重私人性、个人化的体验。与之不同,伴随着现代音乐和网络音乐的发展,现当代歌诗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文体功能和社会功能既可以满足情感需求,也可以教化民众,宣传思想观念,引领舆论导向。与现代诗歌的语言逻各斯相左,歌诗的纯语言功用被限制和削弱,歌词与乐曲的节奏、韵律、声调相配合,形成高低缓和、跌宕起伏、委婉曲折的综合性音乐形式,让广大受众产生或积极向上、或昂扬兴奋、或悲壮悲伤等共通性情感体验,并与时代精神和社会趣味相协调。与诗歌的个体或私人小圈子式的自我欣赏和自我表现不同,歌诗的文体功能更多表现为世俗化、社会性和群体性。加上市场资本这只“无形的手”的幕后操作,快餐文化的需求,以及“短平快”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当代歌诗不能像诗歌创作那样精雕细琢,某种程度上会出现粗制滥造甚至媚俗之作,因而与诗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距离诗歌与歌诗互融互进的“宋词模式”越来越远。
再次,现代汉语的成熟和发展也是“宋词模式”式微的一大缘由。自胡适等文学革命先驱提倡现代白话文以来,现代汉语语法越来越精密,词汇越来越丰富,语言的逻辑性、哲理性、精确性越来越强,现代汉语越来越适合传达哲思化的思想,以承载丰富深厚的情感,表现内心朦胧、隐秘、暧昧与晦涩的情绪,这种语言成为现当代诗歌的最佳思维方式和文体方式,与表达哲理性、私人性和神秘性的现当代诗歌“一拍即合”,成为“绝配”。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语言文学受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如乔姆斯基的转化生成语法、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诗学、索绪尔的符号语言学等,诗歌开始“回归语言自身”,语言获得了本体论意义,诗人对现代汉语的话语方式更为痴迷,不断对其进行精细的推敲、锤炼、挖掘,将其运用得驾轻就熟,炉火纯青,诗歌创作更多的是在现代汉语的“诗性”语言中锤炼表达个体的思想理念,传达个人的美学体验,诗歌创作甚至衍化为语言的游戏、话语的圈套、文字的狂欢。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视之,锤炼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思想的凝结和固定过程,有利于表达哲理化和神秘化的理念,但对语言的过度重视可能会造成诗歌与世俗、大众脱节,在文字游戏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现代汉语除了书面的“诗性”语言外,还有口语化的另一失向。与诗人对后者视如敝屣不同,现当代歌诗却对此视为珍馐。“语言的彻底口语化就使歌曲中的歌词的表述过程与听者接受过程的阻隔被彻底打破,使歌曲在整体上呈现出与现代人的亲近感和交融性;表述方式、结构方法的自由性,就使这种歌词体式除了还受到音乐上的一些限制和规定外,是不定声调、不限句数字数和长短自由的。”①苗菁:《现代歌词:现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产物》,《诗探索》2002年第Z2辑。这种形式自由、表现灵活、鲜活生动、通俗晓畅、过耳即懂的语言方式成为娱乐化和通俗化色彩明显的歌诗文体的不二选择,与中国现当代诗性语言与口语语言二者间的罅隙越来越大。中国文学史上宋词的语言却弥合了二者的鸿沟,既有典雅精巧的文言“诗性”话语,亦有通俗化的白话语言,二者有机融合,半文半白,共生共进,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成就了独特的“宋词模式”的话语方式,被胡适称为“中国诗歌的第三次解放”。②胡适在《谈新诗》中说:“五七言成为正宗诗体后,最大的解放莫如从诗变为词……这是三次解放。”见胡适:《谈新诗》,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6页,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可惜的是,某种程度上,当下人们已经放弃了宋词的语言生成方式,割裂了与古代汉语的关联,文白融合、半文半白早已鲜见踪影,即使有人尝试、有人提倡,③见陈建华:《为“文言”一辩——语言辩证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源起》,《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陈平原:《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但在现代汉语的滚滚大潮面前,也显得人微言轻。因此,在现代汉语的日益成熟和不断发展的今天,在越来越“形而上”的现当代诗歌语言与越来越“形而下”的歌诗通俗语言各自发展的前提下,“宋词模式”的消失,歌诗与诗歌的分裂亦成为必然。
三、建构说
面对当代诗歌与歌诗分离而造成的诗歌逐渐边缘化的困境,笔者认为应该建构当代诗歌的“宋词模式”,既让一部分诗可以入乐传唱,也可以使部分歌诗增加“诗味”,成为名副其实的诗,让诗歌与歌诗有机融合,相得益彰。“歌诗的范围应当划清:不是所有的诗都能入乐,也不是所有的歌词都可以称为歌诗,歌诗只是二者交界的一部分。”④陆正兰:《“歌诗”:一种文学体裁的复兴》,《当代文坛》2016年第1期。这对于当代诗界与歌坛来说,都是未来能够实现良性发展的最好选择。当下,已经表现出建构歌诗与诗歌融合的新型艺术形式的端倪。
(一)诗词乐化
建构数字时代的当代歌诗,要继承古代歌诗传统,将诗人创作的诗词根据时代和音乐需求,重新谱曲演唱,并尝试与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相融合,“经典咏流传”式的经典传唱就是一种具体尝试。2018年2月16日,由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推出制作的音乐文化类节目“经典咏流传”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共播出4季44期,谱曲传唱经典诗词240余首,既有古代诗歌,也有近现代以来的诗歌。经典传唱主要采用“和诗以歌”的表演模式,由不同的经典传唱人对诗歌进行重新创作演绎,让传统经典诗词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或将本身具有韵律的古典诗词直接谱曲重新演唱,或引用部分原作诗词并结合当下音乐流行形式进行改编,与原作诗词的情感、风格、诗意、内涵等融为一体,从而重唱经典,传播经典,演绎经典,再造经典。
第4季第1期中,谭咏麟演唱的《定风波》就赢得了满堂彩,其歌词如下:
放下千斤重/只剩无法承受之轻/得之我幸/纵有失去不怨命/酒先干为敬/是非留给后人评/喧嚣过后/心中风波为谁定/英雄皆寂寞/铮铮铁骨尚有柔情/时光无心/留不住奔波的身影/愿不负曾经/半生爱恨岂无凭/万籁俱寂/梦里长歌还未静/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歌词方面,改编者结合现代白话将苏东坡的词进行了扩写,押韵自然,平仄谐和,唱来极富韵律美感,歌词内容本身又与原词意境符合,表现出面对风雨波澜,依然笑对人生、不畏坎坷的达观之态;编曲方面,将古诗词与现代音乐元素混搭,配合电吉他、爵士鼓等西洋摇滚管弦乐器,加之3D立体环绕双声道交替混音的现代音频技术,让该词在当下重放光彩。谭咏麟也真正参透了词人的心境与词的意境,体悟到苏东坡即使惨遭贬谪、屡处逆境却依然拥有无所畏惧、从容豪迈、旷达超脱的开阔胸襟,在音乐中间插入了扭动摩托车油门的音效,就像是古代肆意人生的策马奔腾,体现出潇洒豪放的气势。另外,在副歌部分唱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时,谭咏麟加入了“哈哈”两句爽朗的笑声,真正将苏轼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谭咏麟荡气回肠的歌声中,甚至可以想象出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快意达观的现代版苏东坡形象。《定风波》以现代摇滚旋律结合古典诗词元素,将古诗词中的文学叙事意象以视觉化、听觉化的方式表述出来,使观众以全新的方式品味音乐,重新认识诗歌经典,较为完美地实现了古与今融通,诗与歌共生。同样,歌曲《青玉案·元夕》的传唱人陈彼得借助吉他、贝斯、萨克斯,从诗词意境入手,以现代曲风进行演绎,将历尽沧桑与沉淀后的爱国诗人辛弃疾的形象呈现在听众面前。歌曲《沁园春·雪》的传唱人许魏洲以铿锵有力的摇滚曲调与豪迈磅礴的原诗词结合迸发出巨大能量,产生了震撼性效果。此外,从传播层面上看,节目除了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外,还在央视网、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视频等视频网站同步播出,同时在当代年轻人聚焦的微博、抖音、哔哩哔哩等用户平台进行短视频播放。为了拓宽传播渠道,该节目还在QQ音乐、酷狗音乐、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等各音频平台推出音频歌曲……这种多平台的“融媒”传播模式,真正实现了大数据“互联网+”的传播效应。
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的最大意义在于实现了互联网时代的诗乐结合、诗歌合一。一方面,通过多元化现代音乐演唱和多媒体传播方式,使经典诗歌的文化意蕴与个人情感融入当下音乐媒体中,与受众产生情感共鸣,重新展现中国经典诗歌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对于音乐创作而言,经典诗歌中的诗意、诗情、韵律也为当下音乐注入了浓厚的文学气息,提升了审美水准,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魅力。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诗乐”结合的尝试,也可以视为建构当代诗歌“宋词模式”的一个路径。
由谷建芬谱曲的《新学堂歌》也是建构当代歌诗“宋词模式”的另一次成功探索。研究《新学堂歌》,还应从“学堂乐歌”开始。所谓“学堂乐歌”,通常是指清末民初中国新式学堂中的开设的音乐“乐歌”。①1902年,清政府迫于形势,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确定新型学堂开设“乐歌”一科。一批启蒙音乐教育家如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辛汉、侯鸿鉴、赵铭传、胡君复等,纷纷创作新歌,以应新兴学堂教唱乐歌之需。当时的“学堂乐歌”为选曲填词,大多采用西方或日本曲调,以及我国民歌或小调,即“旧曲新词”,填词大多浅显易懂,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送别》《早秋》《兵操》《赛船》等。进入21世纪以来,谷建芬专为少儿谱写的古诗词歌曲——《新学堂歌》进入大众的视野。2006年,《谷建芬古诗词歌曲20首——新学堂歌》由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2018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再版。《新学堂歌》历时10余年写就,共50篇经典古代诗歌。与“学堂乐歌”借用西方的现成乐曲,配以维新变法时代需求歌词的方式不同,《新学堂歌》则先选好古诗词,然后依词创作新曲,量身定制,乐曲多采用传统的五声音阶,以传统的民族乐器箫、琵琶、笛子与之配合,兼以吉他、打击乐等现代音乐元素,紧跟时代潮流,旋律音韵更为协畅,诗乐更为和谐。如《出塞》,开始由清脆、明亮的琵琶声入场,“由慢到快渐渐进入创造氛围……大切分的音符,与每句的末句字形成对比,第一段音乐结束之后,快速的八分音符加密了音乐的节奏,琵琶也随之加快,渲染气氛”。②张巧鹃、黄睿:《古诗文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分析谷建芬〈新学堂歌〉》,《大舞台》2012年第1期。整体曲调坚定、铿锵,在音乐中传达出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使铿锵的音乐旋律与《出塞》的语言韵律和意蕴意境相融。《新学堂歌》所选取的古诗词的语言韵律节奏明显,辅以谷建芬节奏明快、旋律优美、风格清新的乐曲风格,使其既具有现代音乐的美感,也保留了古典诗词韵味,表现出诗乐双赢的审美效果与情感意蕴。不能否认,《新学堂歌》继承了宋词的衣钵,与百年前的“学堂乐歌”一样,是中国歌诗的一部分,也是建构当代诗歌“宋词模式”的有益尝试。
其实,无论是音乐类节目“经典咏流传”,还是《新学堂歌》,这种传唱诗歌的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早有尝试。20世纪初很多新诗人的作品直接被谱曲成歌,如胡适的《也是微云》《上山》《希望》、刘大白的《卖布谣》、徐志摩的《海韵》、刘半农的《织布》《教我如何不想她》《听雨》等,都成为赵元任的《新诗歌集》中的歌词,并得以广泛传唱。③《新诗歌集》为新诗歌曲集,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赵元任谱曲,现代诗人新诗作品为歌词(新诗作品13首,范成大《瓶花》七言古诗1首)。肖友梅认为:“近十年来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见肖友梅:《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1930年《乐艺》第1卷第1期。这也可视为当代诗歌“宋词模式”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前身”。
(二)歌词诗化
当今歌坛,以当代流行歌曲、摇滚、民谣为代表的歌曲形式中,存在大量的歌诗作品,如果抽离乐曲,这些歌词文本就像宋词一样具有诗歌的审美价值。“当歌词是一种文学文本时,它和诗最接近,是一种歌诗。在歌词和诗歌之间,文本的边界是模糊的,甚至没有。”④吕进主编:《中国现代诗体论》,笫38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现在很多学者已经将一些歌词作品视为诗歌纳入教科书和研究领域之中,歌词的诗学价值得到了肯定。2005年,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中,将罗大佑的歌词《现象七十二变》排在诗歌单元之首,并在导语中说:“今天的流行歌曲,或许就是明天的诗。”1996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收入崔健的《一无所有》《这儿的空间》;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专辟一节讨论了《一无所有》;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收入《我的中国心》(黄霑)、《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黄河颂》(光未然)。除此之外,有的研究者也关注到这种歌词中的歌诗,即歌词诗化的问题,如苗菁的《现代歌诗文体论》、许自强的《歌词创作美学》、晨枫的《中国当代歌词史》、魏德泮的《歌词美学》等。陆正兰认为:“从当代词作家来看,一部分音乐人的歌词作品在艺术品格上,已经不逊于成熟的诗,而且作词人对‘歌诗’这种文体已经相当自觉。比如著名词人张黎将介绍自己创作历程的著作取名为《歌诗之路》,方文山的歌词集《关于方文山的素颜韵脚诗》自称为是诗,歌手黄磊的歌曲专辑《等等等等》,就称为‘音乐文学大碟’,歌手胡海泉创作《海泉的诗》等诗歌作品。”①陆正兰:《“歌诗”:一种文学体裁的复兴》,《当代文坛》2016年第1期。他们把歌词当作诗来写,把歌词写成“谱曲后能唱的诗”,这些歌词文辞典雅,意境深邃,格律谨严,具有浓郁的诗性美,如方文山的《东风破》《青花瓷》、罗大佑的《童年》《光阴的故事》、黄霑的《沧海一声笑》《我的中国心》等。具体来说,方文山的《青花瓷》,就可以当作诗词来解读,“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清新古朴的歌词配以流畅优美的旋律,使人瞬间走入了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画间,温婉细腻的话语中透露着那一抹淡淡的离愁别绪,含蓄典雅,极具古典韵味。另外,还有乔羽、阎肃、李宗盛、秦齐、晨枫、张黎、陈小奇、李海鹰等人所作的部分歌词语言凝练,节奏鲜明,韵律和谐,意蕴深邃,叙事完整,完全可以视为当代诗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摇滚乐歌曲是“诗性”精神回归的集中凸显。“摇滚乐本来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音乐,而是诗,是音乐化的诗。”②高小康:《在“诗”与“歌”之间的振荡》,《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作为“中国摇滚第一人”的崔健,便是在摇滚中写诗的人。他的歌词是“诗性”思想与强劲旋律的极致碰撞,于生命本能的呐喊中,进行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如他的《一无所有》:“这首歌词的核心意念……表达的是一种艰难而痛楚的文化反抗的处境,它意味着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构筑了对立的关系,故此也就失去了来自外部的控制与文化的内援,而唯余下袒露了无助和唯我主义的个体心灵。”③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版),第32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而郑钧更多的是对于个人情感变化以及生命本质认知的考量,如关于爱情、关于世情、关于人性等,他的《赤裸裸》《极乐世界》《私奔》等充满着先锋性的倔强与反叛,涉及现代性主题的思考。汪峰则带有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他对快速发展的现代性社会进行反思,歌曲《存在》就试图唤醒听众重新思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另外还有许巍、窦唯、张楚等,他们的很多摇滚歌词也充满着“诗性”。
2000年以来的新民谣以周云蓬(《九月》)、赵雷(《成都》)、马由页(《南山南》)、陈粒(《自渡》)等歌手群体为代表,这些民谣内容多以“诗性”语言描述理想与现实,表达自我感受,表现瞬间情绪。由周云蓬作词并谱曲的《不会说话的爱情》获得了“2011年度人民文学诗歌奖”,④2011年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于11月3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民谣歌手、行吟诗人周云蓬获得人民文学诗歌奖。由此可见诗歌界、文学界对民谣歌曲中歌词“诗性”的青睐。当下的摇滚、民谣和流行歌曲等歌词诗意化的写作,确实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诗歌作品,出现了许多既可出乐为诗又可入乐为歌的“歌诗”,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欧美流行音乐中具有“诗性”特质的歌词创作也被文学界承认并获奖。加拿大摇滚歌手伦纳德·科恩早年是作家与诗人,后来转型为歌手,代表歌曲有《哈利路亚》(Hallelujah)、《与我共舞至爱的尽头》(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著名的蓝雨衣》(Famous Blue Raincoat)等,他获得了第52届格莱美音乐奖终身成就奖,被誉为“摇滚乐界的拜伦”。2008年,美国摇滚歌手兼词曲作家鲍勃·迪伦因“歌词创作中非凡的诗性力量”而获得了普利策特别荣誉奖;2016年,鲍勃·迪伦又因其“在歌谣的传统下,创造了全新的诗意表达”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歌曲《答案在风中飘》(Blowin’in the Wind)、《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铃鼓先生》(Mr.Tambourine Man)、《敲开天堂的门》(Knockin’on Heaven’s Door)、《时代在变》(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等都被认定为真正的诗。鲍勃·迪伦的获奖,无疑是严肃、典雅和神圣的文学殿堂对当代歌诗的一种接纳和认可。
通过对“诗歌入乐”与“歌词诗化”的几种表现形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管窥当下文学界和音乐界建构当代诗歌“宋词模式”的几种方式,由此说明,古代歌诗的传统在现当代并没有完全断裂或消失,它只是以新的音乐形态和媒介传播形态存在。
四、价值说
建构当代诗歌的“宋词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当代诗歌的“宋词模式”有望打破文学与艺术之间的壁垒,使歌诗与诗歌互相借鉴,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为互联网时代当下诗歌的突围寻找路径和提供策略。
现代学科建立之后,冲破其规范和体系的做法“古已有之”,如郭沫若之于甲骨文、陈梦家之于考古、沈从文之于服饰研究等。打通文学与艺术的藩篱也屡见不鲜,如鲁迅对文学书籍的装帧设计,对浮世绘、汉画像石和木刻艺术的关注。沈从文也是如此,1934年,他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就绘有十几幅“平淡写意”的湘西山水速写,并体味其文学创作与绘画内蕴之勾连,认为二者“又典雅,又恬静,又不做作”,①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22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均具有自然平静的美学风格。鲁迅、沈从文等都试图突破文学与艺术的边界,弥补学科过分细化的缺陷。诗歌与艺术之间,也有很多人尝试“跨界”,如李金发之于雕塑,艾青之于油画。此种“跨界”在当下愈演愈烈,如诗歌与现代装置艺术。②新世纪之初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明确涉及徐冰的《凤凰》《天书》《地书》《木林森》系列装置艺术作品,并且诗作与装置艺术二者间诗艺互文,试图打通诗歌与装置艺术的学科壁垒。其实,除了油画、雕塑、现代装置艺术之外,诗歌与音乐的关联最为紧密,古今中外的诗学理论中均有充分的论述,此不赘述。笔者认为“诗性”与“歌性”都是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关键词,对于二者“应以和谐相生、共同生存的理念,以‘和’的方式,不以‘同’的方式,更不以‘斗’的方式,让‘诗性’与‘歌性’既和而不同,又和谐共生”。③刘东方:《论中国现代“歌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4期。宋词依乐制词,因词合乐,音乐性与文学性完美结合,“歌性”与“诗性”浑然一体,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体式,“宋词模式”仍是中国诗歌中“诗性”与“歌性”二者美美与共的典范,仍可以为当下诗歌健康发展提供思路,为其从困境中突围找出对策。
当代诗歌应提高诗歌语言的“歌性”。一方面,向现代歌词创作借鉴和学习,运用现代歌曲和戏曲经常使用的“十三辙”④“十三辙”,即把字数繁多、发音复杂、韵母相同或相似的现代汉字归纳为十三种类别,且每个韵的称呼,均由同辙字中寻出两个相同韵的字组成。现代汉语韵辙规律,精心设置韵脚回环、双声叠韵,使当代诗歌的语言韵律更加和谐,节奏更加鲜明,“歌性”功能更加完美。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新月派的新格律诗、林庚的九言格律诗、吴芳吉的新古典诗、周氏兄弟的白话诗、中国诗歌会的歌谣体新诗、老舍《剑北篇》为代表的鼓书体叙事诗、高兰的朗诵诗、郭小川的新辞赋体等仍具有借鉴价值。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手段的迅猛发展,诗歌作为传统默读式的书面文学遭受很大冲击,当代诗歌若想扩大生存空间,必然需要利用现代传媒手段来拓展其传播途径,从平面的纸质语言向复合的声音、图像等多媒体语言过渡,某种程度上说,当下和未来的诗歌很可能是听觉、视觉、感觉结合的“立体文学”,现代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手段的意义就在于“助推”诗歌实现艺术形式的立体化与多元化,助力诗歌建构新时代的“宋词模式”,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论及的“经典咏流传”模式等,还有演唱会、唱片专辑、电台和电视、网络诗歌与歌曲平台模式等。尽管媒体平台不同,其本质均为“诗性”与“歌性”的有机融合,各类“传唱”形式的多渠道传播,以及多元立体的艺术生产。可以说,插上了音乐和多媒体翅膀的“宋词模式”的诗歌,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因为,该“宋词模式”既可以让音乐人为诗词谱曲传唱,扩大诗歌的影响力和受众范围;也可以让诗人加入歌词创作的队伍,为歌词创作注入更多的诗学元素,引领歌词与诗歌的融合;还可以从歌词作者队伍中涵养诗人,为诗歌创作注入新鲜的活力……所以,建构和发展当代诗歌的“宋词模式”,或许能够为当下诗歌从困境中突围找寻路径和提供策略。
其次,当代诗歌的“宋词模式”对于中国当代诗学理论的建构和当代诗歌研究观念的转变也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中国当代歌诗的概念。歌诗的概念,从先秦时期便开始出现,据《左传·襄公十六年》记载:“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①中华书局影印:《春秋左传正义》第33卷,第19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此时“歌诗”的概念为“唱诗”,指的是在公众场合演唱诗歌。魏晋始,人们有了“入乐之诗”和“不入乐之诗”的意识,歌诗的概念也由演唱诗歌衍化为专指可以演唱的诗歌。魏晋六朝以后又分化出两种情况,一种是只为诵读而作的诗,一种是可以合乐歌唱的诗,两者间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界限,人们一般把可以演唱的称之为“乐府”,不能入乐演唱的称为“诗”。此后,歌诗的概念就逐步确定下来,一般专指能够谱曲配乐而演唱的诗歌。现代时期,歌诗的概念与古代有所不同,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继承古代歌诗的衣钵,可以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部分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词;另一部分指不配乐演唱,但具有民间歌谣的“歌性”元素,具有一定的颂唱旋律,便于吟唱和吟诵的歌谣体现代诗歌。②刘东方:《中国现代歌诗概念初探》,《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到了当代歌诗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本身是诗,将诗词重新谱曲并运用多媒体手段重新包装后进行演唱,如“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包装演唱的古代诗词和现当代诗歌;另一种是诗化的歌词,如上文中提到的当代摇滚、民谣、流行音乐中存在的具有“诗性”元素的歌词作品。所谓当代歌诗就是内容上贴近现实人生,传达当代人的思想情感,表现中国当代社会的时代主题和精神内涵;形式上合乐演唱,高效传播,既有音乐的“歌性”,又有诗歌的“诗性”的多媒体综合性艺术形式。同时,歌诗在现代和当代又有所不同,现代歌诗更侧重语言的“歌性”,当代歌诗与多媒体的生产和传播方式结合得更为紧密,更侧重音乐“歌性”。综上所述,当代歌诗继承了古代歌诗和现代歌诗的传统,内涵和形式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应当引起诗学界的关注,成为中国当代诗学理论的一个有机部分。
关于建构“大诗歌”观念。中国古代诗歌由诗与歌两部分组成,前者为徒诗,后者为歌诗。在中国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有时以歌诗为主,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两宋的宋词,元曲等;有时以徒诗为主,如魏晋六朝、隋唐、两宋、明清的古体诗和近体诗。它们二者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井河不犯,歌诗与徒诗既可以相互渗透,也可以相互转化,它们都是中国诗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共同铸就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辉煌。然而,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转型,歌诗与徒诗被分割为音乐和文学两个学科,与古代相较,二者处于明显的“失衡”状态,文学领域内只有诗歌在单维度发展,现当代歌诗被悄无声息地人为性“祛魅”……现当代文学中人们耳闻则诵、如数家珍的诗歌概念,其实是不完整的,残缺不全的。然而,无论是现当代的诗歌创作界,还是评论界,抑或诗学理论界,都对此集体无意识般地视而不见,常见不怪……这种“盲视”的文学现象、狭窄的诗歌概念应该引起我们的认真考量。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转换思路,构建当代“大诗歌”观念。所谓的“大诗歌”观念,就是打破学科分界,借鉴“宋词模式”,承继古代传统,将当代歌诗纳入当代“大诗歌”概念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当代歌诗作为伴乐演唱的多维度立体化的诗体,与突出平面维度“诗性”语言的当代诗歌共同搭建当代“大诗歌”的平台,其中的“诗”专指当代诗歌,“歌”专指当代歌诗。在这个平台上,当代的诗与歌可以平行存在,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一起建筑当代诗歌的大厦高楼。
其实,这种观点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笔者心血来潮。龙榆生在《唐五代宋词选》的“导言”中说,他编选该书的目的是一方面“想借这个最富于音乐性而感人最深的歌词,来陶冶青年们的性灵,激扬青年们的志气,砥砺青年们的节操”,更主要的是“对于这种声调组织,得着相当的修养和训练,可以进一步去创造一种宜于现代的新体歌词”。①龙榆生:《〈唐五代宋词选〉导言》,张晖主编:《龙榆生全集》第8卷,第1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关于建构当代歌诗与诗歌并存的观念,他在《如何建立中国诗歌之新体系》《诗教复兴论》中有更为成熟的论述。②见龙榆生:《如何建立中国诗歌之新体系》《诗教复兴论》,张晖主编:《龙榆生全集》第3卷,第402-427、547-5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梁启超在“诗界革命”时期就认识到诗歌概念过于狭窄的痼疾,提出诗歌与歌诗并存的“大诗歌”观念,他的提法是“广义的诗”:“中国有广义的诗,有狭义的诗。狭义的诗,‘三百篇’和后来所谓‘古近体’的便是。广义的诗,则凡有韵的皆是。所以赋亦称‘古诗之流’,词亦称‘诗余’。讲到广义的诗,那么从前的‘骚’咧,‘曲本’咧,‘山歌’咧,‘弹词’咧,都应该纳于诗的范围。据此说来,我们古今所有的诗,短的短到十几个词,长的长到十几万字,也和欧洲人的诗没甚差别。只因分科发达的结果,‘诗’字成了个专名,和别的有韵的文相对待,把诗的范围弄窄了。如今我们提倡诗学,第一件是要把‘诗’广义的观念恢复转来。”③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492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梁启超认识到由于学科的细分,现代诗学理念“把诗的范围弄窄了”,诗也成了“专名”,专指具有默读功能的徒诗,而歌诗的半壁江山却化为无形。他心目中“广义的诗”,就是要将“骚”“曲本”“山歌”“弹词”等可以传唱的现代歌诗纳入诗歌的概念中,实际上就是继承古代歌诗传统,将现代歌诗归入诗歌的范畴,建构广义的诗歌概念。可惜的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梁启超的“广义的诗”的设想不仅没有实现,而且,诗与歌分离的现象却愈演愈烈。今日看来,转变近百年来看似“约定俗成”的单向度诗歌观念,建构“大诗歌”的诗学理念,已成为诗歌研究和诗歌创作的当务之急。在古代歌诗逐渐式微的过程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相似的观点,如金人刘祁、清人焦循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叙述了。
总之,我们应用包容的心态对待当代歌诗,用开放的观念建构“大诗歌”的诗学观念。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诗歌的“诗性”与歌诗的“歌性”也不是绝对地一成不变,非此即彼,歌诗中也应有“诗性”,诗歌中也应有“歌性”,只是比例和功能不同而已,至于人们所担心的当代诗歌和当代歌诗谁压倒谁,谁改变谁,谁替代谁,我们也不必过于忧虑,我们首先要让二者充分发展,充分借鉴,充分提升,并希望在此基础上,通过这种当代“宋词模式”,产生一种养心悦耳的经典文体体式,如果假以时日,在二者的基础上出现“诗性”和“歌性”相平衡、相和谐的作品和诗体,如宋词一样,也正是我们所期望的,这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当代诗学理论也是大有裨益的。
再次,建构当代诗歌的“宋词模式”能够发现新的跨学科学术生长点,开拓新的研究空间。
“宋词模式”的创作与研究,势必会在音乐和文学,作词与谱曲,多媒体与诗歌创作,多媒体与诗歌传播等不同的学科和专业领域间形成交集和碰撞。歌曲创作中,谱曲音乐与诗歌语言二者间必须相配合,才能形成韵律和节奏的和谐变化。赵元任在《新诗歌集》中给现代诗歌谱曲时,就会选择韵律和节奏明显,具有较强语言“歌性”特征的诗歌,并配之相应的乐曲,使之“互通消息,交相为用”,如胡适的《也是微云》,该诗节奏明显,音节自然,体现了胡适倡导的“自然的音与节”的理论,做到了“平仄自然”“用韵自然”。④胡适:《谈新诗》,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7页,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赵元任在为之谱曲时,从三个方面处理诗与乐的关系:一是“谱曲时的音乐旋律,须配合新诗的音节的顿断,来作音长的调整”;二是注重“乐曲音高与歌词平仄的搭配”,如仄声字就要用短、高的音,或是变动很快、跳跃很大的音;三是“节拍与诗的情感的融合”,如诗中“害我相思一夜”一句中的“思”字,赵元任谱曲时,为突出诗人的相思之情,特意将节拍延长至三拍。①张窈慈:《论赵元任乐歌与胡适新诗的结合——以〈新诗歌集·也是微云〉为例》,第445-470页,《屏东教育大学学报》2006年第24期。当下,诗歌创作与多媒体传播之间,也会有许多学术增长点。如诗人与电影、电视剧等传媒技术合作进行歌曲的创作,使音乐与语言二者取得和谐的效果,既弥补了歌曲音乐中缺乏的诗性与文学性,也使诗歌通过影视平台进行了广泛传播,属于“诗乐双赢”。同时,还可以与新媒体深度融合,与舞乐画面配合,达到听觉、视觉完美融合,从而探索更多的歌诗创新之路,如上文论及的“经典咏流传”类的文化综艺节目。可以说,今天中国当代歌诗和诗歌的创新离不开现代媒体艺术,它们也为我们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②吕进:《论新诗的诗体重建》,《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因此,诗歌在21世纪跨学科的“再出发”,对其创新和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论,深入阐释和研究当代歌诗的“宋词模式”,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我们在强调其优势和合理性时,亦要认清它存在的弊端。由于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特性,当代“宋词模式”的作品,在迎合市场需求和多媒体特点的同时,有时会导致忽略和降低艺术要求,甚至出现低俗、媚俗的现象,所以当代歌诗创作须增强精品意识,从精致典雅的古代和现当代诗歌宝库中汲取营养,多出精品力作。如此这般,我们在“大诗歌”观念的总摄下,才会形成当代诗歌与当代歌诗互动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摸索找寻二者最佳的结合点,由此引导今后的中国诗歌走上一条既有广泛的受众群体,又有较高的诗学品位,既能“养心”,又能“悦耳”的康庄大道,并期许像宋词一样产生“诗性”与“歌性”互融的中国当代诗歌的经典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