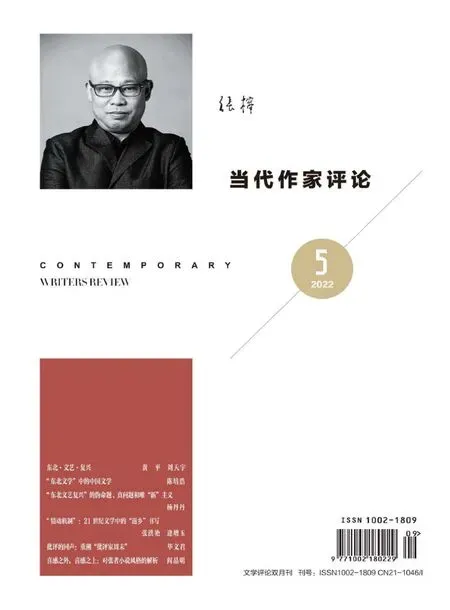21世纪文学中的小镇青年“新人”形象
胡 哲
文学“新人”是文学创作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新人物形象,代表着某一时段的社会风尚。自五四以来,现实主义始终是文学创作的主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一度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方法。从文学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到革命文学时期的民族资本家,再到解放区的人民群众,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始终注重对文学“新人”形象的刻画。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等多元思潮的大量涌入,使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逐步让位于对文学形式的探索,现实主义一度湮没于文学的多声部话语中。直到21世纪以来,现实主义题材文学创作的可能性才逐渐得到更加全面的审视。对文学“新人”形象的开掘和分析再次成为作家关注的重点。与以往文学作品中“典型人物”的概念有所不同,孟繁华认为当下文学创作中呼唤的文学“新人”“不是文学史画廊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也不是美学意义上的‘新人’。而是那些能够表达时代要求、与时代能够构成同构关系的青年人物形象”。①孟繁华:《历史、传统与文学新人物——关于青年文学形象的思考》,《文艺争鸣》2020年第2期。文学“新人”是新的时代环境发展的产物,反映全新时代背景下的青年人物形象成为21世纪文学的写作特色。小镇青年作为青年形象的一个分支,不仅存在于以往青年形象的塑造中,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成为一种类型化的景观,成为文学“新人”的重要构成部分。当下对于文学“新人”形象的呼唤,既是“典型人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接续和发展,也成为新时代条件下文学发展的重大主题。
一
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指出,小城镇“是城市的,更是乡下的;它有现代社会的影子,更是乡土中国的”。②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第19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赵冬梅在《小城故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中也表示:“小城镇可以说是中国的农业文明、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工业文明、现代文化相冲突相融合的前哨阵地。”③赵冬梅:《小城故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第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城市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在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空和地域的作家都曾经尝试对小镇和小镇青年进行开掘和描摹,但文本中的小镇是相对泛化的,小镇青年也未被提炼成一类单独的文学形象,而是被隐没在百年乡土叙事和城市底层叙事之中。
从现代乡土叙事的角度来看,小镇青年形象杂糅于各类乡土底层人物形象之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派作家们开启了现代乡土小说之先河,作品中出生于镇上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看作是小镇青年形象最初的萌芽。从20世纪20年代鲁迅、叶圣陶、王鲁彦笔下的乡镇青年知识分子,到30年代茅盾、沙汀、萧红笔下城乡过渡地带的青年人物,小镇青年形象在乡土叙事中得以延续。从城市文学的叙述角度来看,小镇青年形象孕育于城市底层的劳动者形象之中:30年代的海派文学和40年代的国统区文学,刻画了部分旧式乡镇家庭出身却辗转于战乱时代和现代都市的青年形象,揭示出这一时期小镇青年们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从文学“新人”形象的构建过程来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新时期到来之前,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农村青年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代表,但这一时期对青年人物形象的塑造略显生硬,文本中青年人的命运走向和人生选择也稍显单一。80年代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我国的农业发展逐步走向现代化,从《芙蓉镇》中的胡玉音、秦书田,路遥笔下的高家林、孙少平,到《古船》洼狸镇中的隋家两兄弟,小镇青年的命运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展现出更多可能。纵观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创作对于小镇青年形象的刻画始终在延续中有所发展;而小镇青年之所以没有形成一种类型化的景观,是因为他们作为故乡的“出走者”,城市的“异乡者”,始终面临着身份认同上的困境,并缺乏概念上的界定。
21世纪以来的小镇青年形象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已经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无名”状态,成为文学“新人”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小镇青年的崛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从“五条人”乐队的歌词中展现的小镇青年的思想状态,到纪录片对深圳“三和大神”生存真相的记录,小镇青年形象引发当下更多人的关注。另一方面,这类青年形象已经成为文学中的“新人”形象类型。21世纪以来,乡镇青年向城市的流动已然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现象,作家们更加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和命运——青年们从农村迈入小镇,经由小镇走向城市,成为文学“新人”形象的重要构成部分。从具体的作品来看,孙惠芬的《歇马山庄》《民工》等创作开始转向对进入城市的底层乡镇青年命运的书写;张楚的《野象小姐》《冰碎片》以小城镇作为切口,探寻曾经被忽视的小镇青年的“边缘”人生。此外,在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阿乙的《小镇之花》、葛亮的《迷鸦》、魏思孝的《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林培源的《小镇生活指南》等21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小镇青年形象大量涌现。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将小镇青年作为文本叙述的主体,描摹小镇青年们的人生选择和生命轨迹。
二
21世纪以来文学创作中的小镇青年形象大量涌现并出现群聚效应,迅速成为一种类型化景观,成为文学“新人”形象的重要分支。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原因?从城镇化进程中小镇地位和职能的转变,以及作家代际更迭的角度进行考察,也许能找到答案。
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对以江苏的城镇为代表的小城镇进行调研后,对中国的小城镇做了如下定义:“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①费孝通:《论小城镇及其他》,第1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在他看来,小城镇已经脱离农村并呈现出全新的样态和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小城镇发展规划的提出使得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农民进城务工潮再次兴起,小镇的发展为农村青年外出发展提供了大量机会,也成为青年们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中转站。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小镇的角色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据2019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2》的调研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我国城镇化进程在持续推进并取得显著效果,城乡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向城市过渡和转化的速度大大提升。小镇成为城市和乡村以外存在的实体概念,代表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中间样态。城乡二元对立模式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城—镇—乡”构成的三元空间结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文学创作进一步加强了对小镇的发掘和探索。刘大先提出:“小镇在中国是一种灌木丛式的存在,而不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草原,或高耸入云而底部草木稀疏的乔木林。”①刘大先:《文学小镇与灌木丛美学》,《福建文学》2018年第2期。小镇作为正在崛起的现代化产物,成为新的时代变革的象征。当下文学创作中的小镇,既是城市与乡村的连接处,又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叙事空间。徐则臣笔下的“花街”、朱山坡笔下的“蛋镇”、薛舒笔下的“刘湾镇”、张楚笔下的“桃源镇”和“清水镇”、鲁敏笔下的“东坝”、路内笔下的“铁井镇”、林培源笔下的“清平镇”等,都是作家对小镇生活和风土的记录。他们所描绘的小镇生活,既不同于传统乡村依靠土地而生的劳作结构,又与城市的日新月异相去甚远。这使得文学的小镇成为区别于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地带。也是在小镇异军突起的背景之下,作家逐渐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叙事空间。在这一空间下,小镇青年逐渐构成当下文学“新人”形象的一个重要分支,受到更多的关注。威廉·富特·怀特在《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中提出:“社会是由大人物和小人物组成的——中间有人起着在他们之间架设桥梁的作用。”②〔美〕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第356页,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小镇青年有别于城市和乡村青年的特质,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传统乡镇中青年的质朴,另一方面又受新时代条件的影响,增添了对新世界的渴望。他们不同于成长在乡村的青年那般闭塞和单纯,也缺少城市青年与生俱来的身份优越感。他们受到城市现代化的熏陶,却无法摆脱乡村带来的固化思维模式。他们是矛盾和冲突的结合体,是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产物。因此,他们拥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在文学创作中,以张楚、魏思孝等人为代表的北方作家,侧重表现北方小镇的落后,以及在社会体制变革过程中小镇青年经历的外部打击和精神上的失落。以路内、阿乙、盛可以、林培源等人为代表的南方作家,侧重表现小镇青年们身居故土的原生影响和精神上的迷惘彷徨。小镇在城镇化进程中地位和职能的扩大,也使这一空间形态在创作中引发了更多的关注。小镇青年作为这一环境中的主要活动者,自然成为文学创作主要的描写对象。除此之外,作家代际的更迭也为小镇青年形象的加固和类型化增添了更多依据和实感。
三
当下对小镇和小镇青年持续关注的作家数量众多,他们分布在不同地域并拥有截然不同的生长环境,但小镇却是他们多数人共同的成长起点。这些作家大多属于“70后”和“80后”群体。“70后”作家们刚刚由青年进入壮年,他们在青少年时期见证了改革开放中小镇的发展,生活经历也大多发生在小镇,对于小镇生活深有体会;“80后”作家则正处于青年创作时期,他们同时也是当下文坛创作的主力之一。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小镇的发展与他们的成长处于相对同步的状态。这些作家虽出生、成长于小镇,多数却在成年后离开小镇,到大城市求学和工作,以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作家们在城市生活中获得了现代性体认,逐渐摆脱了原有的生活习惯并形成了现代性的思维方式。距离感的增加使作家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审视故土与自己以往的生活经历。“当家乡成为故乡,意味着家乡已经同他隔离开来,曾经的联系变得愈加稀薄,它慢慢隐退为一个审美的对象。”③刘大先:《故乡与异邦》,《十月》2020年第4期。对于这批作家来说,离开家乡就意味着无根的漂泊。为了克服与故土之间的疏离感,作家们试图在创作中寻找成长的起点,从记忆深处出发,通过文本寻求自我与故土之间的联系。作家们的多数创作是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开始的。以徐则臣和薛舒为例:徐则臣出生于江苏东海,少年时成长于花街地带,在《如果大雪封门》《耶路撒冷》等作品中,青年人的命运轨迹无不与花街形成紧密的联系;薛舒出生于上海的小镇,她的创作呈现出颇有特色的“刘湾镇”叙事。成长于小镇的作家通过创作展现小镇的风土人情,丰富了小镇的书写内容和存在实感,小镇成为作家们创作的精神原乡。另一方面,这些作家的青春逐渐临近尾声或者已经结束,他们开始用更加成熟的心态来回顾之前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轨迹。小镇蕴含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乡愁和最真诚的情感,成为他们心灵深处永远的乌托邦,是他们渴望回归和坚守的精神家园。对小镇和小镇青年的刻画使得文学史中一代青年们的精神家园得以延续。以林培源的创作为例,林培源作为“80后”作家,正处于青年创作阶段。作为同样从小镇“出走”的青年,他对于南方小镇青年的生活状态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把握。在对小镇及小镇青年形象进行书写时,林培源与同时代的作家们表现出了类似的焦虑:“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我摇摆不定,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落脚点。在熟悉的故土面前,我是陌生的‘异乡人’。我无法融进城市的生活,也无法回到我所生长的故乡。”①林培源:《乌托邦与异乡人(创作谈)》,《西湖》2013年第11期。这一代作家正面临着无根的精神困境。在具体创作中,作家试图以自我对于故乡的想象构建起南方小镇青年的生活集,以一种崭新的样态构建起对青年生活的立体想象。《小镇生活指南》中林培源对故事的发生背景“清平镇”进行了如下描述:“这座小镇,被包围在一段公路和水稻田之间,房屋棋盘一般,错落有致。”②林培源:《小镇生活指南》,第22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小镇位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从石板路到小池塘,从小石桥到水利渠,作家所熟悉的场景在创作中得到了细致的刻画,凸显出潮汕小镇的地域特征。他笔下身处其间的小镇青年们所经历的各种人生样态,也代表着作家对于一代青年人不同生活可能的想象和建构。
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独特的创作背景和写作方式。正如乡土之于“50后”和“60后”作家的创作意义,随着作家代际的更迭,小镇也将成为更多“70后”“80后”青年作家们内心深处的独特记忆。作家对于小镇青年形象的塑造凝聚着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和想象。他们对于自己同时代小镇青年的书写,也是对与自己有着相似成长经历却呈现出不同生活轨迹的人物命运的探究。这些作家凭借其特殊的成长环境和经历,采用代际更迭下独特的叙述视角,讲述了坚守于小镇的青年生活中的各种可能,以怀旧感伤的笔调,讲述小镇青年的理想主义情怀,以及理想破灭后的精神异常。他们对于人物生存方式的揭示,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无意识的追问,使得当下小镇青年的形象更加丰富和立体,同时也完成了文学史中文学“新人”形象的传承接续。
四
纵观21世纪以来的小镇青年形象建构可以发现,小镇青年的形象塑造经历了从“出走”到“坚守”的蜕变。小镇青年作为文学“新人”形象的一种延伸,是城镇化进程和作家代际更迭的产物,为当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李壮认为:“在体量巨大且加速更新的时代经验面前,即便是青年本身,也已经被一种‘追赶’和‘适应’的节奏所裹挟,并且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停调整自我想象和身份认知。”③褚云侠、相宜、李壮、林培源、朱明伟:《青年形象变革:时空、想象与未完成》,《当代文坛》2019年第5期。城镇化进程仍在持续,小镇青年这一群体还在持续扩充壮大,文学创作中的小镇青年形象也处在不断更新的状态中。
与以往文学史中刻画的“出走”的青年形象有所不同,当下文学中的小镇青年们在经历过大城市的奋斗和打拼后,大部分选择了回归小镇并坚守小镇。魏思孝的《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展示了小镇青年的种种生活困境。作品写出了一些小镇青年的“废物本色”,表现返乡小镇青年精神世界的空虚和颓废,以及小镇青年生活经历的荒诞。魏思孝认为,小镇青年的最终归属在乡镇,在向传统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路内的《少年巴比伦》中的路小路在戴城小镇和大都市之间取舍,展现出小镇青年面对未来选择时的迷茫。传统与现代的交缠和暧昧导致了他们结局的惨淡。阿乙的《小镇之花》中的益红一心渴望离开小镇,却迫于世俗压力嫁人,放弃远走他乡的想法,留在镇上。作家们对于小镇青年的生活转型已经有所察觉,并在创作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对部分选择“出走”的小镇青年们的跌宕命运进行反思。从“出走”到“坚守”,这种转变也体现出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作家代际更迭后对于自我内心精神家园的坚守。小镇青年们经历了“出走”之后的回归,他们重回故土,重建起自我的精神家园。作家试图在创作中展现出他们对于小镇青年形象的未来走向与人生可能的思考。以《小镇生活指南》为例,作家以小镇为中心刻画了类型迥异的小镇青年形象。镇上的青年们大部分拥有“出走”的经历,但最终多数人选择返回小镇,安守故土。姚美丽少年时期离开清平镇到漳州,经历了几年的奔波后又重回熟悉的小镇生活,为小镇带来新潮和时尚。《拐脚喜》中的庆喜也曾离开清平街外出务工,后返回小镇,一事无成。姚美丽和庆喜的人生经历恰恰相反,前者化经历为阅历,选择与世界和平相处,后者则将欲望化作与世界对抗的资本,最后被生活吞没,二者构成重返小镇青年形象的两个维度。《濒死之夜》中,没有姓名的“他”为了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成为离乡者,因为理想的破灭而重回小镇。他们“像一件穿皱了的衬衫,被生活的熨斗一遍遍地烫平”。①林培源:《小镇生活指南》,第23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这类小镇青年的选择表现出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小镇这一精神家园的眷恋,但是他们也绝望地发现,历尽辗转依然寻不到生活的出路。还有一类青年,他们成长在小镇,从未离开,如《躺下去就好》中的“棺材仔”庆丰和《秋声赋》中的阿秋。这众多失败的小镇青年仍坚守在小镇,成为小镇最坚实的构成部分。虽然选择“坚守”的青年们在总体上仍然呈现空虚迷茫的思想状态,但他们却为坚守自我精神家园做出了努力和尝试。经历“出走”的小镇青年们面对着小镇与城市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曾经的城市梦逐渐破碎,内心感到失望;未曾经历过“出走”的青年们面对着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同样感到前路迷茫。从“出走”到“坚守”,文学作品中的小镇青年的选择正逐渐发生着改变。多数作家在勾画这类青年形象时,并没有为他们的命运走向做出最终的预判,这或许正体现出作家对于小镇青年人生走向的持续性思考从未间断。
此外,作家们对于小镇青年的不同选择和命运可能性的书写也凸显出当下文学“新人”形象的现代性特质。他们逐渐意识到小镇青年的“坚守”实际上面临着二次适应的问题,因此在创作中展露出一种观望的状态,对于小镇青年的未来发展状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方向,这也使得小镇青年形象在当下的文学形象中成为更加辩证性的存在。从“出走”到“坚守”,这批青年作家共同展示出文学“新人”形象在当下的转变,也提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时代背景下,也许放缓脚步,回望过去,反思当下,才是更恰当的选择。从这一层面来看,正是小镇青年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对于家园的“坚守”,才使得人们重视起小镇这一地域形态的发展和存在,激发人们对小镇和小镇青年生存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关注和思考。作家们对小镇青年的“坚守”进行的追问,展现出小镇青年的不同侧影,使得小镇青年的“新人”形象得到了多视角的阐释,从而也建构起当下创作中相对立体化的文学“新人”类型。
五
对文学“新人”形象的呼唤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迫切需求。针对这一点,吴俊提出,文学“新人”的特质在于“某种(些)新的人物特质经作家作品的艺术表现而使该人物(形象)成为文学史上的首创或新创”。①吴俊:《新中国文学“新人”创造的文学史期待》,《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前文提到,城镇化进程中小镇职能的转变和青年作家代际的更迭推动小镇青年形象成为一种类型化景观。小镇青年的选择从以往的“出走”转化为对小镇的“坚守”,符合当下文学“新人”形象塑造的特质。这批小镇青年是从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过渡过程中的先行者。他们既与传统有所黏连,又展现出现代性的特征。作家笔下“坚守”的青年们表现出对小镇的难以割舍,捍卫他们生存的家园,也就意味着对传统的“坚守”。作家透过文本试图完成对处于传统与现代冲击夹缝中小镇的构建,并通过小镇青年的人生经历和选择揭示出他们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表现出其文化人格的双重特质。
一方面,小镇青年们选择“坚守”故地表明了作家延续传统之根的创作诉求。城镇化最终指向的目标是城乡一体化,走出乡土进入城市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小镇是中国城市化道路中的一种独特景观,也是小镇青年们身体和灵魂的故乡。它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地带和存在形态,最终很有可能面临消失的境遇。作家们书写小镇青年的“坚守”表现出对于文学寻根的继承,其中既有对小镇文化劣根性的批判,又呈现出对优秀传统和精神之根进行探寻和发扬的希冀;既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以深情的姿态呼唤在外游子的回归。以阿乙和魏思孝的创作为例,阿乙的《模范青年》刻画了两个性格迥异却都渴望离开小镇、扎根城市的青年,最后玩世不恭的艾国柱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被大家标榜为“模范青年”的周琪源却放弃了梦想,留在了小镇。魏思孝将自我标榜为游手好闲的小镇青年,却在创作中表明他对于故土的留恋和回归的态度。由此可见,故土中仍有值得期待和挖掘的优秀文化和故事,而坚守于小镇的青年们身上展现出的劣根性也是作家想要进一步揭示和批判的对象。当下作家们对于小镇青年形象的刻画展示出他们对于文学寻根进行融合的尝试。
另一方面,当下对“坚守”故土的小镇青年形象的塑造也表明了作家们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反思。美国社会学家雷德菲尔德曾经提出“乡土—城市”连续体的概念,指出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必然性,这种转变就意味着原有群体构成部分的逐渐消失,以及社会关系的转变。迁移理论也指出,迁移者在迁入新的环境后仍然受到流出地原生环境的影响,在陌生的环境中很难找到自己的定位。虽然小镇青年们的身体曾经进入城市,但他们的思想却与新的时代环境脱节,缺少精神上循序渐进的成长过程,很难受到城市人的认可,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青年们在进入城市之后沦为边缘人的命运。而小镇青年的“坚守”却使得小镇这一空间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逐步走向常规化,成为一种固定的存在形态,为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提供动力。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下,“出走”城市是否是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文学作品中放缓脚步、“坚守”小镇的青年为我们提供了青年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从以上两个角度来看,作家们塑造的小镇青年形象响应了新时代对于文学“新人”形象的召唤,既展现出对小镇精神文化传统的溯源,又表达了对现代化进程中小镇青年形象建构的反思。作品塑造的坚守小镇的青年属于时代发展进程中的初探者,虽然大多以怀旧感伤的失败者姿态出现,却为21世纪以来小镇青年形象的树立增添了更多的层次感。通过对失败者的描摹,小镇青年形象逐渐从平面化走向立体化,摆脱了曾经的失语状态。小镇青年自我身份认同和归属问题也在作品中逐渐明晰。城镇化进程仍在推进,处于这一代际更迭之下的作家们通过对自身成长经历的回望,反思时代的进程,并打造出小镇青年的全新形象。这也是他们介入历史的独特表达方式,不仅为青年形象的树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也丰富了文学史中“新人”形象的参照谱系。
阿甘本曾经提出:“同时代的人是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以感知时代之光芒及其黑暗的人。……同时代人,确切地说,就是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的人。”①〔意大利〕吉奥乔·阿甘本、王立秋:《何为同时代?》,《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青年作家们在当下文学创作中进行的尝试正属于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写作,他们通过文学创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小镇青年发声,整合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以小镇青年为代表的一种全新的生活经验。他们笔下的小镇青年拒绝成为现代化进程中被耗费的生命群体,他们试图通过努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成为文学“新人”形象的代表。当下对于小镇青年形象的刻画仍然处于一种尝试阶段,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这一形象必定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书写和更全面的展现。“‘新人’其实不是‘现实中人’,不是文学与现实严丝合缝的对应物,而是精心‘提炼’、‘拼接’、‘塑造’出来的‘典型’。”②金理:《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第4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当下,文学“新人”形象中的小镇青年是新时代背景下树立起来的形象典型。期待作家们在创作中能够以多元的姿态介入当下,捕捉时代的脉搏,进一步完善小镇青年形象,更大限度地开发和诠释其背后的文学寻根意蕴和现代性反思内涵,使这一类文学“新人”形象能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