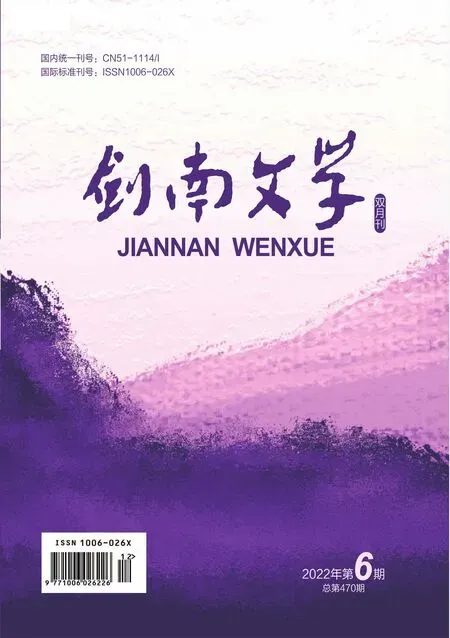希梅小镇
□陈永华
古镇是安静的、厚重的,有着幽深的岁月痕迹。坐在无人的角落,泡一壶清茶,静听雨落;或在雨后裹起披肩文艺地漫步小巷;或看夕阳斜照在某处院落,如油画般深邃。一切都那么具有美感,然而,走过之后,心中却再无想念之意,它们终究抵达不了我的内心。只有一个默默无闻、朴素的小镇时常让我午夜梦回!
我还小的时候,父亲在那个小镇工作。每当他从小镇回来,总会在他的包里翻到我喜欢的东西,糖、油酥坨坨、小发夹或者画报。我缠着父亲一遍又一遍地讲关于小镇的故事:河边那棵黄葛树越来越高大茂盛;赶场天树下喝盖碗茶的人越来越多;卖油酥的老奶奶每次总是笑嘻嘻地多给父亲装一两个油酥;一个烫着卷发的女人,从县城来到小镇医院上班,穿起高跟鞋“叩叩叩”地从小桥的青石板走过,镇上的男人与女人偷偷地看一眼再一眼,又偷偷地彼此交头接耳……当然,关于卷发女人的事是父亲讲给母亲听,被我不小心听见的。所有的一切,让我对在我心中很是遥远的小镇充满了一个孩童最美好的憧憬。我经常跟随母亲去县城我祖父的家,我懂得县城是大于小镇的,但我渴望去小镇的心情远远超过了去县城。父亲口中的小镇还有个温柔的名字。“希梅”,多好的两个字!多像我们女孩儿的名字!我甚至因为想去希梅几次私自出走到坝上的村口,遥望一阵远方,又独自走回去。
那年夏天,突如其来的一场特大洪水冲垮了我们在坝上的房屋。年幼的我不懂伤悲,反而因为终于要随父亲去小镇居住而兴奋不已。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离开坝上时对已是断壁残垣的房屋、对被洪水淹没的菜园子要久久注视。她长久的沉默与严肃,让我不得不掩藏住快乐的心情。
其实,从坝上到希梅并不远,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只是在我心中才那样远。它是川中的一个小镇,那时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街,街两边是一间间陈旧的青瓦房。走到街的一半,便是青石板桥。站在桥上,即使是盛夏,也感觉得到河水的清凉透骨。父亲所描述的黄葛树屹立在河岸遮天蔽日,古老得像有千年万年。我好奇地看着,居然见它在对我微笑,像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
九月开学,我在小镇接着读小学四年级。完全陌生的学校、陌生的同学,我没有朋友。下午放了学,过了石板桥,我总要在黄葛树下逗留。下几级台阶看清澈的河水缓缓流淌,或者望着树发呆,或者在石桌上做作业。那个时候,即使是赶场天,也早已散场,周围静悄悄的。除了树和我,就是鸟。在小镇最初的那些日子,黄葛树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我们成了忘年交。我还因此写了一篇作文《一棵古老的黄葛树》,并获得镇上作文比赛一等奖。老师们说我的作文有独特的风格。夕阳西下,天空美得无以言表,河面泛起金色的粼波。我抬起头,迎着风,把作文大声朗读给树听。我坚信它能听见,因为我又看见它在微笑,像我初见时看见的微笑。我抚摸它粗糙的躯干,依偎在它的怀里,莫名地泪流。那刻,我完成了从孩童到少年的蜕变,因为我懂得了什么叫寂寞与孤独。
我开始了在小镇的少年生涯,并开始融入小镇的生活。
八十年代初期,农村经济还较落后,交通也闭塞。乡下人有些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对他们来说,赶小镇是一种荣耀,是出来见世面的。逢场天的小镇,从街这头到街那头,人群摩肩接踵、密密麻麻,两边摆满交易的农作物与商品。有鸡、鸭的叫声,有贩卖的吆喝声,有彼此讨价还价的声音。卖油酥的老奶奶个子小巧,慈眉善目,极像我的祖母。我买过几回油酥后,她就认得我了。逢场天她在桥头摆摊,她的摊位前挤满了人。卖掉农作物有了钱的乡下人,舍得的便买几个油酥给儿女们带回去,或买两张画报拿回去。更舍得的便扯一两节好看的布料给爱美的女儿做条裙子。
黄葛树下热闹非凡。男人们翘起腿,大口喝盖碗茶,大声武气摆龙门阵,露出满口黄牙爽朗地大笑。背篼、箩筐堆得像座小山。还有掏耳粪的、摆理发摊的、摆图书摊的、讲评书的……小镇喧嚣的集市,近似于《清明上河图》的局部!中午时分,人们渐渐散去,等完全散场后,一切归于平静,静得能听见叶落的声音。
一阵风,一场雨,季节从秋过渡到冬。黄葛树下铺满落叶。随着时间的推移,久而久之,我在小镇也有了要好的朋友。但是,我依然时常会去树下的石凳坐坐,向老朋友倾吐我少年的心事。
记得那是一个初冬的午后,离上学时间还早,我又来到树下。那天,我终于见到父亲所说的卷发女人了。她长长的波浪形卷发披在胸前,像一条条弯弯的小路。她的皮肤白皙,嘴唇很小,眼睛不是双眼皮,但很好看,后来才知道那叫丹凤眼。她果然穿的是高跟鞋,身材又苗条,走路婀娜多姿。当她慢慢向我走来时,我紧张得有些不敢出气,好漂亮!她来做什么?她来做什么?我努力想。“小妹妹,你还不去上学?”“还早。”我的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清。“来,别怕,坐下来。叫什么名字?”我不吭声。“那我先告诉你吧,我叫夏玉,今后遇见我就叫玉孃。”她笑笑,那笑中有淡淡的忧伤,声音很是温柔。沉默与紧张让我额头略微出汗,虽然天寒。见我无语,她便独自望着河水发呆。我想,她是不是也孤独?我有少年的孤独,她有我读不懂的孤独。
第二次见到玉孃时,还是在黄葛树下。虽然我没叫出“玉孃”两个字,但在心中我这样叫她了。她那细长的眼睛有点红,像是哭过。她仍然微笑着和我说话,我不再紧张和拘谨。我甚至告诉她我的名字,并说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太难听了,喜欢她的名字。“夏玉、夏玉”,夏天的玉石,晶莹剔透!她笑了:“喜欢月亮吗?”我点点头。“那我叫你小月儿吧。”“嗯,要得。”她又问:“爱看书吗?”“爱看。”“晓不晓得老舍?老舍说月亮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东西。”说完,她不再言语,陷入沉思之中,不知在想什么。
生活是一首歌,对玉孃来说,生活是一首难言的悲歌。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成为精神病患者。
见过玉孃两次,我觉得她很好,有些喜欢她。喜欢她与众不同的美,喜欢她温柔的声音。那以后,每次我到黄葛树下,都希望遇见她,可次次都失望。我甚至渴望得一场小小的病,要是母亲带我去医院看病,说不定能见着她呢,她在医院上班啊。
想是那么想,毕竟年少,没过多久,我就把她淡忘了。
一个逢场天,因为学校举行了体操比赛,中午放学早。集市还未完全散场,卖油酥的老奶奶也未收摊。闻到香香的油酥味道,我便觉得有些饿。虽然买油酥的人多,我还是耐心排队等候。无意间,我听见前面两个女人说起玉孃的名字。“你晓得那个烫卷发的夏玉嘛,妖里妖气的,她男人经常打她,说她有作风问题,领导找她谈了话,叫她注意影响。整个医院和镇上的人都晓得这事。没过好久,她精神出现问题,被送回县城医治去了。”“我好久没来赶场,还不晓得哦。就是嘛,烫个卷卷头,走路一摇一摆,一看就不是个守规矩的。”两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挤眉弄眼,不像和善之人。卖油酥的老奶奶插话了:“夏玉是个好女人,就是长得好看,爱美,她哪有作风问题,全是造谣!唉,可怜哦。”两个女人脸色顿时不好看,骂骂咧咧地走了,连油酥都没买。
天突然阴沉下来,风开始呜呜地吹,像女人的哭声。我的脸冰凉,心也冰凉。走到家门口,有些迷迷糊糊。作风问题?精神问题?我问母亲:“啥子叫作风有问题?啥子叫精神有问题?”母亲很吃惊地看着我:“小孩子家家的,你问这些做什么?”“那你说夏玉孃孃作风有问题没得?精神有问题没得?”因为刚才那女的说镇上的人都晓得这事,应该是大人都知道,母亲肯定也是知道的。母亲跟老奶奶一样地叹气:“唉,可怜哦,那是个好女人,我去医院看病见过她无数次,对人很好的,怎么可能有作风问题嘛。就因为她长得好看,人又柔和,那些男的喜欢找她说话,就说别个有作风问题,她男人信了外面的谣言还打她。”“那精神问题呢?”我又问。“怄多了气,又受不了流言蜚语,精神可能有点恍惚。”母亲非常委婉非常同情地说。“好了,好了,你还小,不懂,莫问这些。”母亲很是不耐烦。
我躲在自己的房间悄悄流泪。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被玉孃的悲惨遭遇影响着。刚进入初中,正是懵懵懂懂的年纪,爱看小说的我,常常把她想成是小说中的悲剧人物,而不是现实中的悲剧人物。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和男生说话,我怕被冠以“作风问题”。有个男生我们本来挺好的,下课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但那之后,我老是回避他,怕他找我说话。多少次他向我走来,我都慌忙走开。后来,我见他下课后总在座位上独自看书,也很少与其他同学说话,好像有些自卑。我想,我是伤害到他了,他可能不明白好好的我为什么对他要那样冷漠。我很难过,是什么让我们少年的心蒙尘?是落后的时代?是人们的狭隘偏见?还是其他?
当我读初二的时候,县城建市,城市人口大增。父亲的工作也调到城里,我们也要跟随父亲进城生活。知道第二天要离开小镇,我心里像有什么堵着,沉甸甸的。我不愿离开小镇,我想在小镇等玉孃的消息。
晚上,我来到黄葛树下,向我的老朋友道别。月亮出奇的大,出奇的圆。月光静静地洒在河面上、地面上,清凉洁净。“那我叫你小月儿吧?”“晓不晓得老舍?老舍说月亮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东西。”我仿佛又听见玉孃温柔的声音,仿佛看见她婀娜的身姿穿过月光缓缓向我走来。我依在树上无声地落泪,我感觉到树在哭泣,听见河在呜咽。仰望纯洁的月亮,我轻声悲歌一曲,为那个叫我“小月儿”的人。
走在城市的街道,我希望奇迹出现,在某个拐角处,前面那个人回头一笑,啊,是玉孃!但多少年过去,这个奇迹也没出现。
如果玉孃现在还在人世,和我母亲一样,也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不知她的病是否已好?如果现在见到她,我想问她:你是一个知识女性,当年为何要屈服于不幸的命运,甘心做流言蜚语的牺牲品?是柔弱的性格使然吗?这是一直以来我困惑难解的结。
还有那个男生,我很想当面说声对不起。虽然我心里说了无数次的对不起,但也无法减轻我的内疚感。我知道当年我们不是说不说话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年少的我伤害了年少的他。
微风轻拂,院里的花开得正好。怀旧,是中年的情怀。能在这样的一个下午,慢慢喝着茶,把小镇的人和事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回想一遍,是难得的。小镇的逢场天、那棵黄葛树、叫我“小月儿”的玉孃、和善的老奶奶、还有那个男生,忽远、忽近。
我一直相信,月亮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