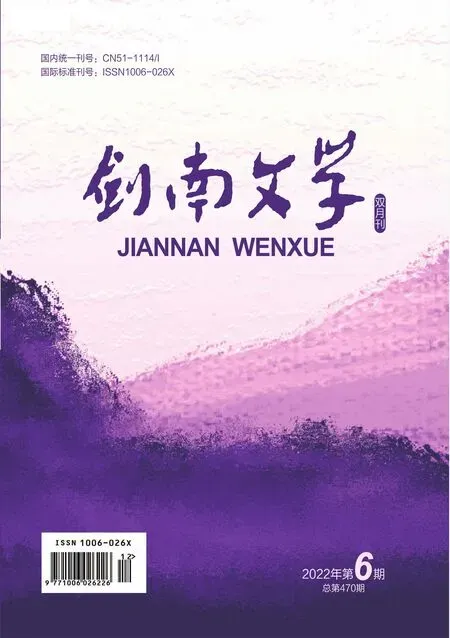回归平静
□南川
当陈小亮再一次爬到高高的线杆顶端的时候,他被展现在眼前的风景吸引住了。这里是距边境不远的最后一片河谷,越过南瓦河再翻过那道森林葱翠的山岗就是27 号哨所。一路上他一直数着,这是他爬的第十四根线杆。如果那处该死的故障还不在这里,他就只好涉水过到河的对岸去爬第十五根线杆了。十月的热风吹过来,摇得河边的竹海翻起阵阵绿浪,他下意识地紧了紧腰间的保险带,试着摇了摇军分区总机班的电话。
“我是东海,请讲。”耳机里立即传出总机班班长于玲的声音,这声音还是那么好听,但陈小亮立即就彻底地泄气了!显然,那个该死的故障还不在这儿。“还得找,真把我折腾熊了!”他忍不住恨恨地骂了一句。
“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于玲不客气地责备了一句。
“喂,我是陈小亮!”他没好气地叫了一声,自己都能听出来声音中带着明显的颓丧。
果然,于玲在那边马上开心地笑了起来,从耳机中甚至都能听出她的笑声在机房里回荡。
“哎呀,就等你的消息啦。现在你在哪儿啊?”
“我已经到了南瓦河的边上啦。”
“声音好极了。”于玲故意说,“可惜不是从哨所打来的。”
“算了,我马上过河去吧!”陈小亮知道今天他必须将前面的最后一段线路也彻底查完,才能找到那处断线了。
“去吧,雅珙寨的姑娘可漂亮呢!”
“去你的吧!”陈小亮没好气地回了她一句,没等于玲再笑出声来,就拉下了接头,收好话机,哧溜一声滑到了杆底的草丛里。
亚热带的秋天热得过中原地区的炎夏,此时已过正午,空中,太阳明晃晃地照耀着,从西南边吹过来的热风将河谷里的杜鹃和石榴吹成一片火焰,只有坡上一蓬蓬茂密的芭蕉叶像雨伞似地撑着,给山道投下一片又一片的浓荫。陈小亮背着修线的工具,沿着这条山道,向山下的河边走去。
山道在山脚下向北弯去,清清的南瓦河逆行而上。沿着河边转过一个山坳,就可以看到雅珙寨的竹楼和塔影了。于玲在电话里说的漂亮姑娘,就是指的那里的小卜哨们。关于她们,通信连里流传着很多传说,都说那是这一带傣家最有名的出美人的地方。这些传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当地驻军有关的,其中就包括陈小亮今天要去的27 号哨所。大概是三四年前吧,那时陈小亮还没有当兵,27 号哨所的副班长去集市上买给养时认识了当时这个寨子最漂亮的姑娘。在随后的一年里,谁也不清楚他们是怎么发展关系的,反正在副班长复员的第二天,那个姑娘失踪了。不久以后,两人在山东老家照的结婚照片寄到了寨子里,人们才知道他们幽会的地方竟是边境线上早已废弃的地堡。据说有干部专门去考察过,回来说那地堡收拾得赛过哨所花几十万元修的士兵宿舍!于是,那段姻缘,不但当时就成了一个轰动的新闻,而且后来简直就成了一个美丽的神话。那种风情,别说连队里的大兵,就是总机班那些漂亮的话务员们,说起来也是啧啧称奇,羡慕得不得了,但那种福分,看来也只有27 号哨所的边防班才有了。至于陈小亮他们这号人,只有偶尔查线时才能在这里望一望。陈小亮背着线拐在山道上走着,心里不禁冒出一丝念头:说不定,咱今天也能碰到一个呢!但他立刻就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因为自从那个老兵不声不响地带走了一个姑娘以后,军分区就作了警告式的死规定:今后谁再违犯驻地纪律,就给最严重的处分,然后开除他的军籍!陈小亮吐了吐舌头,马上就打消了那个挺“超前”的危险念头。自己的入党申请刚刚报上去,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不敢出洋相啊!他望了望已经出现在对岸的掩映在竹林中的高脚楼,转身向青石滩的方向走去,他决定避开寨子,不走渡口,渡口就有摆渡的姑娘,他实在有点害怕,害怕真的见到雅珙寨的姑娘们——他怕他管不住自己啊!
青石滩,是南瓦河上游的一个峡口,无数乱石横亘在水中,将河水分割成许多的激流。从那里摸着乱石就可以涉水过去。天太热了,他还想找块僻静的大石头下冲个澡呢。他选好了一处小小的石潭以后,便钻进了草丛,将工具丢在一边,开始脱衣服。但他总有些心神不定,这里已经完全看不见寨子了,平时也很少有人来,不会碰上什么人吧?但有人来也算不了什么,一起洗就是了。他还有什么念头呢?哦,不上雅珙寨转一遭多多少少有些遗憾。他毕竟还没有领教过那里的姑娘有多漂亮啊!但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自己真是一个蛮能管得住自己的人——革命军人么,总得有些大丈夫气概,干什么要让那些与自己根本不相干的姑娘来添什么麻烦呢?反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陈小亮可不给连队抹黑,要不,于玲那班女兵也会笑话我的,我才不作别人的笑柄呢!他这样想着,对自己感到有些放心了。至于雅珙寨的姑娘遗憾就遗憾吧,回来时不是还有一趟么?想到这儿,连他自己都忍不住要笑了。算了算了,实在想看看回来再说吧,反正现在咱是过了这一关啦!
想到这里,他脱掉军装,光了脊梁,只剩下了一条短裤头。刚要起身,却突然被一阵什么声音吸引住了。那是一阵轻轻的银玲般的笑声,这笑声,淹没在一片轰鸣的流水中,隐隐约约,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他警觉地支起了耳朵,悄悄地探出脑袋,透过身边浓密的凤尾竹向四周望去。周围没有人,河边也没有人,对岸——对岸呢?对岸好像也没有人。但是,附近肯定是有人的,而且——准是姑娘!因为那笑声是只有姑娘才有的笑声。陈小亮哪怕别的什么都不懂,姑娘的笑声,他是绝对懂得的!陈小亮的心不可遏制地剧烈跳动起来。
什么事情都会是这样,漫不经心的时候,你觉察的会非常有限,可神情一专注,那景象可就是看不到的也听到了,听不到的也猜到了。果然,就凭着当兵两年多学到的这点侦察经验,他终于发现对岸大石头后边随意放着几条刚脱下的筒裙,在阳光流水间闪着花花绿绿的光。很快,他又在一个水边的草丛中发现了几双小巧精致的拖鞋。没错,笑声就是从那个地方发出来的。这一下,陈小亮慌了,进退两难,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那银铃般的笑声也实在是太不给陈小亮时间了,不容他多想,一只手臂轻轻一扬,一个洗澡的姑娘便滑出了那块藏身的大石头。她虽然全身都浸在水中,但湿漉漉的长发下,那圆润的肩头,洁净的胸脯,光滑的脊背,在阳光下裸露得那么大胆,那么从容,那么无所顾忌,而这些就足以让陈小亮魂飞魄散了。
更让他如雷轰顶的景象还在后面。这个姑娘刚游出来,另外三个姑娘也跟着追出来了。她们互相泼着水,打闹起来,轻轻的笑声变成欢快的喧哗,身体也暴露得更加放肆了。他愣在那里,目瞪口呆,既不敢动,又不敢走。他满眼都是从未想象过也从不敢想象的美丽胴体,心里却只剩下一个让他战栗不已的念头:千万不能动!只要他一暴露,那些姑娘们也会立刻魂飞魄散的!这个后果可是更加不可想象的可怕!于是他张着嘴巴,直着脖子,瞪着眼睛,几乎一动也不能动,只有身子悄悄地缩了下去,几乎完完全全地缩到草丛中去了。
这时的陈小亮几乎进入了麻痹状态,好久以后,他才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他说:在那个要命的时候,自己简直就像青蛙见到了蛇,那可是一些真他妈漂亮的蛇啊!可也正因为这样,在全神贯注的注视中他才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姑娘游出藏身的水湾到底是要干啥。她们嘻嘻哈哈地笑着,一条条光滑的手臂在空中飞扬着,将水花溅得漫天飞舞,兴高采烈地围攻着那个最先游出来的姑娘,逼着她游到对岸来,然后赤身裸体地走到那一丛丛墨绿色的凤尾竹中,采摘那满山遍野的火焰般灿烂的杜鹃花。姑娘们要让她在光天化日之下考验自己的美丽!
没有几个回合,这个倒霉的姑娘便被逼到河中心来了,其余三个姑娘轰笑起来,用手推、用水泼,绝不允许她退回去。那个姑娘看看四周没人,只好从水中站起来。
这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啊!那姑娘在流水乱石之间直起了身子,水面上立刻跃起了那双结实而丰满的乳房。
“罕香真美啊!罕香真漂亮!”姑娘们故意高声叫着。
那个被叫做罕香的姑娘小心地东张西望了一下,终于大胆地直起身子走出水面。于是那优美的曲线、洁白的肌肤、匀称的肢体,立刻在蓝天碧水间耸起一尊动人心魄的塑像,姑娘们更加欢快地大笑起来。罕香将瀑布般黑亮的长发甩到身后,用一条白纱巾系住,便小心地扶着石头,慢慢探索着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到了深水处,罕香轻轻扎进水中,游动开了。她的游姿很美,悠悠地仰在水面上,用两只灵巧的手臂一晃一舞地划动,她那黑黑的发丝随着她的身体飘浮在水面上,随着身子的摆动,那纤纤细手溅起一粒粒珍珠般闪亮的水花。那是一双多么动人心魄的小手啊!陈小亮痴痴地看着,突然想起了一个传说。据说傣家姑娘会做一种手酿的傣药,若她喜欢上哪一个小伙子,只要将那傣药放在茶里,让那小伙子喝下,那小伙子就会迷恋上她。陈小亮凝视着罕香那双优美的小手,不知怎么就想到了那种傣药。他想若是那个叫罕香的姑娘就用这双手捧上药茶,哪怕是有毒的,他也会毫不犹豫喝下去的!
趟过深水,罕香迅速来到了对岸。河面上轻轻刮过一阵风,吹来满山遍野的花香。罕香解下了发际上的纱巾,用手拂了拂湿漉漉的长发,一双秀气的脚丫小心地踩着光滑的乱石,径直向着陈小亮藏着的草丛走了过来。阳光下,她那水淋淋的身子发出缎面般的光泽,陈小亮屏住了呼吸,他的自我防线早已经彻底地崩溃了。
但就在这一刻,当她俯下赤裸的身子采下第一朵杜鹃花的时候,她一下子愣住了,天哪!几乎是面对着面,她看到了躲在草丛中的陈小亮。于是,四目相对,立刻就形成了一个空前危机的局面:赤身裸体的罕香忽然面对着一个潜伏以待的士兵。仿佛看见了一个正在冒烟的炸药包!陈小亮面对这样一个姑娘无异于遭遇一串迅雷不及掩耳的惊雷,他大脑里出现了一片空茫。这位姑娘那弯弯的眉毛有点像于玲,但比于玲要美丽。去年有一个来营区写生的画家评论说,于玲这样的女孩子,只能说是漂亮,但不能说是美丽。这话让于玲琢磨了好几天。而陈小亮此刻面对这姑娘那高高扬起的充满了惊愕的眉梢,觉得这就是画家所说的美丽。而她那明亮的眼睛,也似乎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只是此刻陈小亮那一口袋浆糊似的脑子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但说不准那惊恐得睁得大大的眼睛,就是所有好看的眼睛中最好看的眼睛了。还有高高的线条分明的鼻梁,小巧的微微张开的嘴唇,以及圆润的脸颊,光洁的额头,都让人心灵震撼。至于姑娘的身体,更无疑是天下所有最苗条最匀称的姑娘的身体中最具魔幻力的身体了。只是所有好看姑娘的身体,都包裹在各种各样好看的衣服里面的,当然也包括军装,而这位姑娘……一丝不挂!陈小亮什么也想不起来,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他彻底地垮了,完完全全地崩溃了。
这个局面似乎象凝固了一样,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实际上却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情,因为当罕香走出水面的时候,正巧有一只蝴蝶也从水面上游扑扑闪闪的飞过来。当罕香惊得立住了脚、四目相对时,那只蝴蝶便陡然升起,飞上了她的头顶,而那只蝴蝶还没有离开,罕香的脚已经在向后惊慌地退去了。也就是在这一刹那间,她的脚在乱石间的青苔上一滑,扑通一声,人便四脚朝天地跌到身后的潭水里面去了。
南瓦河的水面,清净光滑得犹如一面镜子,但在乱石之下,却有许多纠缠在一起的旋涡,罕香显然对这道潜藏的激流毫无防备。她的头还没挣出水面,手在水面上徒劳地乱抓了几把,人便沉下水面不见踪影了。
陈小亮似乎连呼吸也凝固了,紧紧地缩在草丛中一动也不敢动,而河岸的三个姑娘却已响起了一片惊叫声:
“罕香姐!罕香姐跌到水里去了!”
“救人呀!”
那条白色的纱巾,像一条柔软的鱼,缓缓地跟随着罕香沉下水底,打着旋钻向深处。就在它将消失的一瞬间,陈小亮被一种不知哪里爆发出来的力量从地上弹了起来,他一步跨到岸边的石头上,对准纱巾一头扎了下去。
水是温暖的,有如被太阳晒热的软缎,陈小亮的全身都浸在这温水中,他迅速地挣脱鞋子,奋力向下钻去。当他的指尖触到河底的冷水层时,立刻感到了湍流的涌动。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奋力钻了进去,一阵激流将他的身体翻卷过来,滚过水底杂乱的水草,直入中流而去!
陈小亮几乎是带着绝望跃入水中的。因为他知道,这完完全全是因为他,是他把姑娘吓到水中去的,如果他不把这个姑娘从水中救上来,那么,他就是一个坏透了的王八蛋了。老天爷,让我游得再快一点!他此刻只剩下一个念头:抓住她,抓住她的身体!他的前方很快出现了一团白糊糊的影子,透过厚厚的水障,他睁大眼奋力一挣,终于抓住了罕香的一只胳膊。那胳膊很滑,他一把没抓牢,但刚刚脱手,罕香乱摸着的手就又碰到了他,他就势攥住了她的手腕一拽,便将罕香的身体拉到怀里来了。
正在与死神拼命挣扎的罕香,此刻的力量比陈小亮想象的要大得多,还没容陈小亮挟着她往上浮,她已经将陈小亮紧紧地抱住了。她抱的真是一个要命的地方,是脖子!她两只手死死地揽住他的脖颈,两条腿还盘在了他的腰上!这使陈小亮不但用不上力气,而且身体也翻倒过来,鼻子里立刻进了水。他眼睛一黑,赶紧将鼻子里的水咽进了肚子,好险啊,要是一呛可就马上没命了!他一狠心,想用脚把罕香蹬开,或者用膝盖将她顶开,但罕香的腿盘在他的腰上,根本够不上。时间不多了!他已经感到心脏快要在水中憋炸了,陈小亮已嗅到了死亡的气息。那是个充满了恐怖的黑洞,一旦被拉进那个黑洞,他俩便同时完蛋了。这时他的背部碰到了水底一块嶙厉的石头,一阵钻心的刺痛,让他猛然一激灵,一种求生的本能刺激了他。于是他将双手并拢,使劲将自己与罕香的身体分离开来。就在罕香的小腿经过他的头顶向激流飘走时,他一把扯住了她的脚,然后奋力跃出水面。阳光顿时在头顶上爆裂开来,蓝天、白云、碧树、河岸历历在目。他喷着水,用力地呼吸着失而复得的空气……得救了!
“我的天哪,我今天都干了些什么?”当终于苏醒过来的罕香姑娘在那个万分尴尬的场面中,被陈小亮横放在膝盖上控出了满肚子的水,然后被有气无力地丢在河滩上,又被那三位匆匆忙忙穿好衣裙的女伴们羞惭满面地搀扶而去以后,河岸边的乱石堆中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陈小亮落汤鸡似地坐在自己的装备旁,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垂头丧气地回想今天发生的一切,感到自己简直就象是平白无故地掉在人家设好的陷阱中似的,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今天可以说是把以前想看而不得看的东西着着实实地看了个够,同时又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天打五雷轰的罪过……以后的事情,他却是连想也不敢去想了。隐隐约约中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胀满了他整个发懵的大脑。
那天发生罕香事件后,他湿漉漉地走到了27 号哨所,终于查清了断线就在哨所值班室的接线盒里。当时他只说自己掉到了河里,向老乡借了套军装换上就回连队了。现在已经过了快一个星期,他啥也没敢说。他已开始怀着几分侥幸,估计要是再过几天没有动静,这事儿可能就算过去了。
还是在新兵连上纪律条令课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第七条“不许调戏妇女”,最早有“洗澡避女人”。而当地的傣家妇女又有着河边集体洗澡的习惯,在这种时候,男人们必须远远地躲开的,哪个年轻的后生要是偷看了姑娘们洗澡,便会一辈子讨不到媳妇了。当她们浸在水中的时候,偶然经过的老人和孩子可以目不斜视地走过,甚至转过头说几句话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不停住脚就行了,但是这种待遇,年轻人绝对要除外。这都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既不明确,也不成文,何况陈小亮还是一个“外乡人”。虽然军人在当地是很受尊敬的可以例外,但陈小亮撞上的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罕香,而且……还跟人家“动手动脚”了。这个事情就完全复杂化了。罕香是什么人啊?他曾隐隐约约地听说过,她是雅珙寨最漂亮的姑娘,是年轻后生眼中的金丝孔雀!事情到底有多严重,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陈小亮心里是一点谱也没有。于是陈小亮留了个心眼儿,跟谁都没说,能混过去拉倒,混不过去呢?驻地的群众纪律可不是一件小事啊!陈小亮这么一想,自己肯定是罪责难逃了。陈小亮就这样提心吊胆过了好几天。那天,他正在屋里发呆,只听一阵轻轻的汽车引擎声由远而近,一辆挂着军分区车牌的军用越野车,驶进通信连的营地,在连部的门前停住了。
陈小亮的心里咯噔了一声,警觉地竖起了耳朵,很有些惶惶然地透过窗户,注视着那辆车的动静。连长立刻就出现在连部门口。车门打开,只见军分区政治部的曹副主任跨下车来,身后还跟了一个不认识的干事。当一脸困惑显然对曹副主任的到来毫无准备的连长敬过礼握过手后,他将他们让进连部。陈小亮被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紧紧地笼罩住了。
曹副主任算不了多大的官,可这个胖胖的副主任是专管群众纪律的,部队驻在少数民族地区,对这个问题上级当然就抓得格外紧。自从那年那个副班长从驻地带走了一个姑娘,分区对他们这个经常有人单独外出执行任务的连队,就关照得格外紧了。“不许去驻地找对象。”就是他亲自在直属分队面前宣布的纪律,据说那件事,连军分区司令员都知道了。那件事让他这个专管驻地纪律的副主任很没面子,所以讲的时候吹胡子瞪眼,声色俱厉,后来总机班有一个上海战士在下面嘀咕:“哪条法律规定战士不许搞哪一类的对象了?”结果到了年底,愣是给提前复员了!这个官厉害!陈小亮清楚自己这下碰到克星了。
午休起床以后,是队列训练。陈小亮正在队列中忐忑不安地踢着正步,通信员跑过来,对班长说:“连长叫你们班的陈小亮马上去连部。”当时他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可是当他战战兢兢地走进连部以后,看到的却是三张灿烂的笑脸。曹副主任很高兴地与他握手,问:“你就是陈小亮?挺精神的小伙子嘛!”
“不错,是个好兵。”连长附合着。
“这是宣传科的李干事,把你那天的事好好汇报一下,怎么样?”
陈小亮傻眼了:“汇报?啥事?”
连长一巴掌拍在他肩上,差点没把他拍一个跟头:“干了这么大的一件漂亮事,还瞒着?好你个陈小亮,这下可叫咱们连露脸了!”
李干事软绵绵的手也伸了过来,笑着说:“别急,慢慢讲,我在你们连要待几天,把那天的事细细讲清楚。”
曹副主任眯缝着眼儿,吸了一口烟,神情中透着浓浓的满意和欣赏之情。“你配合李干事好好整一个材料,弄不好,这回你要当英雄了!”
“什么?”陈小亮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连长哈哈一笑:“你还装什么傻?那天你救了个漂亮的姑娘的事儿,人家已经反映到军分区来了,连司令员都很重视这件事儿呢,让马上核实。如果情况属实,你看会怎么着?”
陈小亮张着大嘴瞧着他们。李干事打开了本子,扶了扶眼镜:“大概至少是一个三等功吧。”
陈小亮好像被人从悬岩边上拉起来,心“咚咚咚”地剧烈跳动。
“全体起立——”随着军分区军务科长的一声口令,满满一礼堂的官兵呼啦一声全站了起来,一声“立正”之后,军务科长笔直地转过身向站在主席台正中间的军分区首长们报告:“司令员同志,军分区机关和直属分队全体集合完毕,请指示!”司令员挥了一下手:“开始吧!”台前的军乐队顿时嘹亮了起来,一个乐段后,军分区政委宣布:“陈小亮同志立功表彰大会现在开始!”于是在又一次的军乐嘹亮声中,陈小亮披着大红花走上了主席台,那脚步,摇摇晃晃,就像是踩在了棉花上似的。
陈小亮活这么大,各种各样的主席台着实见过不少,村委会的、乡政府的、县影剧院的,一直到军分区礼堂的,都在下面看过电影呀节目呀什么的,开过会的更是不计其数,可从来也没上去过。他这次终于走了上去(他自我的感觉好像不是在走,而是飘上去的)。他一走上台,几乎是第一眼就瞥见了坐在第一排的总机班的那几个女兵。记得刚当兵不久时,他看过她们的一次演出,小合唱,唱的是苏芮的《牵手》,于玲她们拉着手,在聚光灯下显得那么鲜亮。虽然后来才听说那首歌是女的拉着男的手唱的,根本不是女的拉着女的手唱的。
他记不清他是在怎样的掌声中走到讲台上的,更记不得他是怎样向军分区首长敬礼又怎样被戴上军功章的,他只记得当他打开讲稿,终于念到“……下面就把我奋不顾身抢救落水少女的经过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一下”这一句时,世界上的逻辑就开始变得混乱不清了。
这混乱差不多就是从李干事开始给他写稿子那时候开始发生的。李干事在听了他前言不搭后语的汇报后,最关心的经过,似乎不是他怎么把罕香姑娘救起来的,而是罕香姑娘怎么跑到水里去的。
“她们当时在河边干什么呢?”
“洗……洗衣服。”
“那罕香姑娘怎么就掉到水里了呢?”
掉到水里?她原来就在水里!陈小亮这样想着,眼中又浮现出大石头后面飘出的长发和那只伸出水面缓缓划出来的长长的手臂,但他却怎么也没法儿把当时的情景描绘出来。
“哎,你好好想想,详细描述一下她掉到水里时是一个什么样子。”
“她是一个什么样子?她是光着身子自己退到水里去的!”陈小亮想着罕香当时那亭亭玉立的情景,脸腾地一下红到了脖领子里去了。
“比如,她手里拿着什么,或者再简单点,她当时穿着什么?”李干事仍然不依不饶。
什么穿着什么?他妈的她根本就什么也没穿!陈小亮给逼得几乎要叫起来。可是声音出来却变成了无奈的哼哼唧唧。他不能说啊,这一切的真实都不能说啊,这不只是为自己,他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什么,而是怕更大程度地伤害罕香的名誉!
李干事绝对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很精干的小兵竟是这样的窝囊,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一个经过也说不清楚。而陈小亮觉得这个戴着眼镜的家伙是专门来跟自己作对的。那天的事情怎么可能忘记呢?所有的情景和经过都历历在目。可是,那是能说的事吗?他们之间的谈话进行了三天,最后也没弄出个结果,其实到最后陈小亮自己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在介绍所有情况的时候,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就是想给罕香把衣服穿上。可是罕香一旦穿了衣服,这个故事就怎么也讲不顺溜了。这个看上去是那么简单,却又总是讲不顺溜的故事,终于让两个人都不耐烦了。于是,李干事干脆把这个傻子似的大头兵完全抛开,几乎是像写小说一般地构思出了陈小亮自己无法讲完整的全部英雄事迹。那个故事的大概是这样的:
那天,陈小亮站在高高的线杆顶上,看到南瓦河因为上游下了雨而涨水了(其实上游根本就没下雨,南瓦河也根本没涨水),赶集的姑娘归来,在涉水过河时,被水冲倒(尽管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座直通村中的竹桥,鬼才知道她干吗要涉水过河),于是陈小亮从线杆顶上滑下,飞奔而至,跃入河中(那段距离足足有两千多米,若是等陈小亮从线杆处跑到河边,姑娘不是自己爬出来,就是早被水给冲远了)。陈小亮在急流中几番挣扎,终于将姑娘救起,又用自己平时掌握的战场急救知识(这一条连长特别喜欢听)将姑娘救活,然后送回寨边,就又继续执行任务去了(这最后一个情节基本没有错,但就是姑娘的状态完全没说对)。
材料写出来,当然是先让陈小亮过目。陈小亮心里想着:“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嘴里却完完全全地同意了,当时他自己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把脑袋点得那么肯定。可不点头肯定又怎么说呢?完全说真话既害了自己更会伤害到人家罕香姑娘啊!
没认真阅读这先进材料时,陈小亮对自己的谎言和李干事编造的天衣无缝的谎言感受并不十分深刻。他想,不管怎么说,我总是在关键时刻救了罕香的命,这一点是绝对真实的,至于那些难以示众的过程,我为什么还要傻乎乎地说出来?管他妈光彩不光彩,立功总是比受处分或遭人白眼好一千倍一万倍啊!现在面对满礼堂熟悉的面孔认真念这份藏脚露脸的材料,陈小亮突然感到全身阵阵发热,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念完讲稿最后一句时,他无意识地抬头扫了一眼台下,猛然发现台下满场人头皆是一张张讥笑的面孔。他像遭电击似的,忽然一股强大的电流直冲头顶,眼前一片模糊,他“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我……我不该立这个功,我……我根本不像材料上写的这么好……呜呜呜……”
会场上空气一下子凝固了,陡然发出一片由小而大的蜂鸣声。
千钧一发之际,坐在一旁主持会议的曹副主任慌忙抓过麦克风微笑着说:“陈小亮同志太激动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吧。”台下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那天的大会开得热烈而又热闹,这个庆功会不但是一个士兵的辉煌,而且也是所在部队的荣誉。甚至,连整个军分区也生了光彩。整个军分区大院,都因为陈小亮胸前的军功章而笼上了一层愉快的气氛。
可不知咋的,给大家带来愉快的陈小亮却郁郁寡欢心事重重忽然病倒住进了医院。
谁都猜不透他有什么心事,但曹副主任似乎察觉了什么秘密。曹副主任到医院里看望陈小亮时,沉默半响,关上门慈祥地问:“小亮,这件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如实告诉我!”
陈小亮就受委屈似的急得哭了起来,向曹副主任坦白了一切。
曹副主任听完他的哭诉后,平静地说,这事不许再给任何人讲,情况太复杂,静观地方的反应吧!
曹副主任的话含糊不清,陈小亮决定登门去向罕香赔罪,彻底解脱自己心灵上的压力。就在陈小亮硬撑着从病床上爬起,准备请假去雅珙寨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又发生了:罕香带着鲜花从几十里外赶到医院敲开了他的门。
陈小亮接过鲜花热泪盈眶对罕香说:“罕香姑娘,我真不知道怎么给你说啊!我……我真的不是有意躲在那儿……”
罕香淡淡一笑:“不用说了,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谢谢你!”
陈小亮怔了怔,他的心忽悠一下,终于回到了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