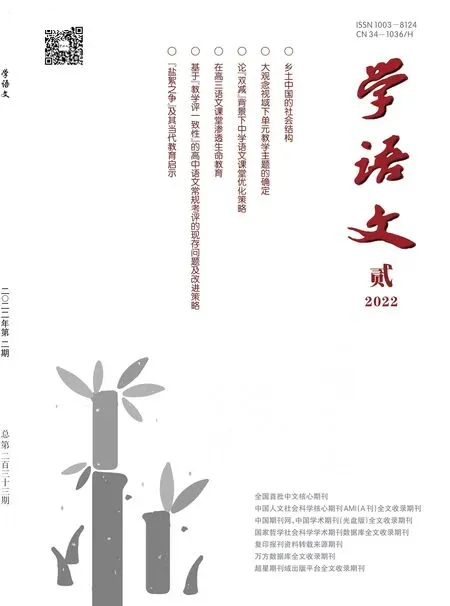“盐絮之争”及其当代教育启示
□ 李欣鑫
统编教材七年级上册课文《咏雪》,选自南朝刘义庆组织编写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全文如下: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1]110
教学实践中,鉴赏《咏雪》“柳絮”“撒盐”两处比喻是常规设计里不可回避的重难点。笔者在多次磨课、听课时发现,几乎所有执教者都在潜移默化地传授着“柳絮”之喻优于“撒盐”之喻的经验。在本课的“思考探究”中也一直有“把大雪纷飞的情景分别比作‘撒盐空中’和‘柳絮因风起’,谢安认为哪个比喻更好”一问。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中,对这一问题的推荐答案是:“从课文中谢安‘大笑乐’的反应来看,他更倾向于‘柳絮因风起’的说法。”另一本同样较为权威的《教学设计与指导》,对此回答道:“从谢安‘大笑乐’的反应来看,他认为‘柳絮因风起’这个比喻更好。文章结尾只对谢道韫作了介绍,也隐含着谢安对谢道韫‘咏絮之才’的肯定。这是咏雪,更是咏才情。”
在日常教学中,高“柳絮”而下“撒盐”似乎是一以贯之的“教学正确”。笔者不以为然。
一、现代“盐絮之争”的三种立场
《咏雪》“盐絮之争”古已有之。苏东坡曾盛赞谢道韫“柳絮才高不道盐”,代表了东晋至北宋的主流观点。但,两宋之间也曾出现异议,陈善《扪虱新话》专辟“文字各有所主未可优劣论”条驳之:“谢氏二句,当各有所谓,固未可优劣论也。”[2]5559这是现今可考的“盐絮之争”的源头,可惜苏陈二人的争鸣似池塘落花,虽涟漪各异,终究有言无据。
《咏雪》一文被编入教材后,教育工作者们对其投去好奇目光,这一“公案”再次被拉入研究视野。梳理近十年“盐絮之争”,有三类言据丰满的主张:主张“柳絮才高”的“咏絮派”;主张“各有所谓”的“兼美派”;主张关注情景构建和谢安教育方式的“模糊派”。
“咏絮派”是现代“盐絮之争”的主流。蒲日材《未若柳絮因风起——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对文学形象美的追求》肯定“撒盐未若柳絮”观点,理由有二:柳絮作为喻体更精美,更具有文学价值;谢安“大笑乐”的态度表现出了对“咏絮”的赞赏,并代表了魏晋士人的一般态度,而且由此反映出魏晋士人对文学形象美的追求[3]。焦雷《究竟哪句比喻用得好——由〈咏雪〉一文的“问题研究”谈起》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一个论据:谢道韫身份的单独介绍侧面烘托咏絮之优[4]。之后,“咏絮”派的论据基本也都围绕于此。
“兼美派”主要针对上文“公大笑乐”一点提出异议。如詹丹《笔记体和〈短文两篇〉》,认为谢安“大笑乐”的背后是联句圆满的得意和快乐,无关某一人的出彩[5]。宣卫东《公缘何“大笑乐”——兼品〈世说新语〉的“简”与“玄”》,将“公大笑乐”缘由一一细解:赞兄女的咏絮之才;叹兄子的才思敏捷;凸显简约玄谈的至真性情,以此反驳“咏絮派”言“公大笑乐”为赞咏絮之才的说法[6]。
公案一时难解,便有学者提出略过两喻高下,关注言语情景的构建,用现代教育视野发掘谢安的教育方式。这一类以《〈世说新语·咏雪〉中的教育理念解析》[7]和《言语情境:文本分析的重要途径——以〈咏雪〉为例谈文本分析与教学内容的开发》[8]为代表,因其淡化“盐絮”孰美之争,姑称之为“模糊派”。
“咏絮”与“兼美”中,笔者甚为赞同“各有所谓”的“兼美派”,但“兼美派”在论述中因史料有限,驳斥面狭窄,亦存在论据淡薄之失。笔者在此补充一些史料,剖析《世说新语》审美生态,在驳斥“咏絮派”的同时,进一步探析“盐絮兼美”的历史实质。
二、“咏絮派”之误
(一)所谓“文章对谢道韫身份的介绍是侧面烘托咏絮之优”,有移花接木之嫌。
纵览“盐絮之争”,问题的关键在于评价优劣的主体是谁?是提问者谢安?是回答者谢朗与谢道韫?是编者刘义庆?还是跳脱时空之外的我们?笔者以为应是谢安。原因有二:其一,我们问“撒盐还是咏絮”时,期待的是一个基于魏晋审美视野中的客观评价,这个评价显然由同时空、同境地的谢安作出最为恰当。其二,无论是课文还是教参,都明确针对“谢安认为哪个比喻更好”提问及作答,而各家学说在论证时,也或明或暗的提及魏晋风度和时代审美,说明这一公案的根源仍在“寒雪日内集”。
回归“寒雪日”可知,三人对话的现实情景在“公大笑乐”后戛然而止。文本结尾对谢道韫身份的补充说明,乃是编者刘义庆所为,这种“画外音”确实带有一种“恍然大悟”式的揭秘效果,这种效果对渲染“咏絮之才”功不可没。但,这显然是不在场的刘义庆的心声,只能代表后世撰评人在此事上的倾向,它既不能代表当时未置一词的谢安,更不可能成为谢安赞赏“咏絮”的佐证。
(二)谢安的态度确可代表魏晋士人对文学形象美的追求,但谢安“大笑乐”并不等于只赞赏“咏絮”。
谢安作为《世说新语》中主要人物之一,其言谈举止彰显了魏晋士人风度自然、美意纵横的精神毋庸置疑,但要还原谢安对咏雪一事的态度,必须参考一个重要因素——谢安与子侄辈交往时所流露的一贯性情。
同为“言语”门中所记:“谢公云:‘贤圣去人,其间亦迩。’子侄未之许。公叹曰:‘若郗超闻此语,必不至河汉。’”[1]114谢安与子侄相聚纵谈,他感慨圣人、贤人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子侄辈们没有赞同他的,谢安便感叹如郗超在此,定会同意他的观点。
“文学”门有一条与《咏雪》相类的记载:“谢公因子弟聚集,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1]196
趁子侄辈在一起的机会,谢安询问《毛诗》最佳句,这一原始情境类似于“寒雪日内集”,但结局大相径庭,遏(谢玄)回答自己的看法后,谢安并未“大笑乐”,而是不以为然,另答一句。
“品藻”门也有谢安与子侄相交的记载:“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1]445谢安见谢玄等臧否竹林人物,提醒其对比先辈的为人处世来自省。
凡此种种,不难看出,谢安常与子侄辈交流品评文学。在交往中,谢安一贯机敏而坦率,觉察晚辈偶有失品,他会委婉制止,加以警醒,如有不同看法,他也会坦荡反驳,慨然陈述,并不会拘泥于身份而一味包容或模棱两可。
因此,回顾《咏雪》一文,谢安欣然抛出一问,在谢朗、谢道韫接连作喻时未有置言,却在两人答后以“大笑乐”作为回应,当是其内心的真实表达——“撒盐”“柳絮”,两喻兼美!否则,以其本真心性,如有臧否,必会出言点评,而不会一笑置之。
(三)所谓“柳絮作为喻体更精美,更易引起文学联想”,这一观点乍看在情在理,实则狭隘无据。
《咏雪》明确用“雪骤”“白雪纷纷”等词语描摹雪的情态,强调了那日雪具有来得急、下得大、形态乱的特征。在此情景下,谢朗将飞雪比作“撒盐”,是抓住大雪纯净密集,纷乱难辨的特点,谢道韫用“柳絮风起”比拟,则是侧重其轻盈柔阔,翩然无影的特质。可以说,两个喻体都极为符合那一日的雪态,且各有侧重,自有风格。
诚然,柳絮作为自然喻体,比盐粒更远离世俗烟火,更阳春白雪。但在文学领域,雪作为一个审美客体,其由联想而引起的审美元素越多样,越迥异,其内在文化张力越可得充分发展,其本身越能保持常新长盛。倘使雪的形象“只此一家”,成为不刊之论,那么随着日推月移其外延消失,这一意象便会在审美领域迅速枯萎。何况,那一日寒雪中谢安正在“讲论文义”,谢朗和谢道韫的回答无疑是心中“文义”迁移到现实的一次实践,于理于情,两个喻体并不存高下之别,只“各雪入各眼”罢了。
三、“盐絮兼美”的时代根源
为何谢安眼中“盐絮兼美”呢?答案需向时代中求。《世说新语》中不乏引起“孰更优”之问的设计。如“品藻”门:桓玄曾问太常刘瑾“我何如谢太傅”?刘瑾回曰:“公高,太傅深。”对这一各得其赞的答案,桓玄并不满足,于是再说:“何如贤舅子敬?”刘瑾巧妙运用一个比喻,“楂、梨、橘、柚,各有其美”[1]646,重申并坚持自己的态度。用各不相同的几种水果作喻,强调不同的人自有其独特的色盛香浓,不可简单比较为孰优孰劣。
又如:“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1]269在魏晋士人心中,“理之所在”并非第一要义,“共嗟咏”的和谐共生方是意趣所在。
因此,《咏雪》中,谢朗面对长者提问虽急言抢答,以“撒盐”之喻彰显自我审美,却仍留下“共嗟咏”的余地——以“差可拟”谦逊退让。作答既迅又缓,既展才气又藏锋芒。谢道韫不急不争,最后娓娓道来,这是她的谦恭与淡然。用“柳絮”作喻,并直言前喻“未若”,是对自己审美联句的自信与傲气。
一率真而有礼,一谦恭而坚定,两人都在雪色之中表达自我,坚持自我,但这种坚持与表达并不是“有我无他”式的,而是“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式的,“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1]544,张扬自我,各有其美,平等对话,美人之美,以此成就一段雪中美谈,折射出一段魏晋风流的弧光。
四、“盐絮兼美”的当代教学启示
深耕教材,回归课堂。《咏雪》,这篇七年级首篇文言文,在承担积累文言知识等教学任务外,还应具有独特的启迪质疑,引导探究,健康审美,浸润文化之效。
鲁道夫·斯坦纳曾言:“从远处看到一片森林,它显现为一个整体,而不管它是由多少棵树组成的。”[9]118课堂亦然。课堂中的思考探究,不是为解答某一道题,具体认识某一棵树,它需要见微知著,从一道题培养一种思路,从一棵树走向一片林海。
七年级的学生初识文言文,对一切充满好奇,充满憧憬。执教者引领学生走近文言森林时,以开放思维鼓励他们“争奇斗艳”。面对“谢安认为哪个比喻更好”这一类问题,执教者应主动搭建时代背景,引导学生纵深思考,不必也不可强求统一化答题模板,不必也不应拘泥于教参标准的框架。执教者率先钻研、深思、开放、兼存,受教者因此体悟、深思、切问、交流。唯有如此,这一问才能问出一颗知人论世的种子,埋下一脉寻根问源的引线;唯有如此,这一课才真的开启探究质疑之门,展现万物参差之态,引领学生走进文言森林,对文学世界进行多元审美。
同时,“盐絮兼美”的事实,也提醒大众在基础教育中更多关注健康的审美理念,既要关注阳春白雪,又要走向下里巴人。“咏絮派”在评判“柳絮”与“盐”两个喻体时,常认为盐之生活化,使其粗鄙、无美感,不配在文学一隅闪现。其实,审美本身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过程,世事洞察皆学问,柴米油盐也可作美的代言。盐之晶莹岂弱于雪?柴之粗细横斜未尝不有疏朗之美?执教者如已在心中存有美的“傲慢与偏见”,认为纷雪只像春天自由飞舞的柳絮,而不像橱柜顶打翻倾洒的粗盐;月牙只能是山水画中泊着的小船,而不能成为夏日被啃得薄薄的一弯西瓜皮……执教者的眼睛里只看得到“高大上”的雪月,而黯淡田间地头、灶下瓦上的星辉,执教的途中又怎会“接地气”,让文学落地生根?又如何培养四体勤、五谷分的新一代学子?又何言素质的教育、人的教育?
比喻之妙正在于其生动又多姿,文学之美正在于其开放而多元,教学之道也要有“楂、梨、橘、柚”。千百年前的小庭院里尚且能平等对话,倡导“人的教育”的今日课堂,难道容不下各有其美的答案吗?身为执教者,当既有求真务实之心,亦存开放平等之态,以使教学更有思辨、更有温度,吾愿与同侪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