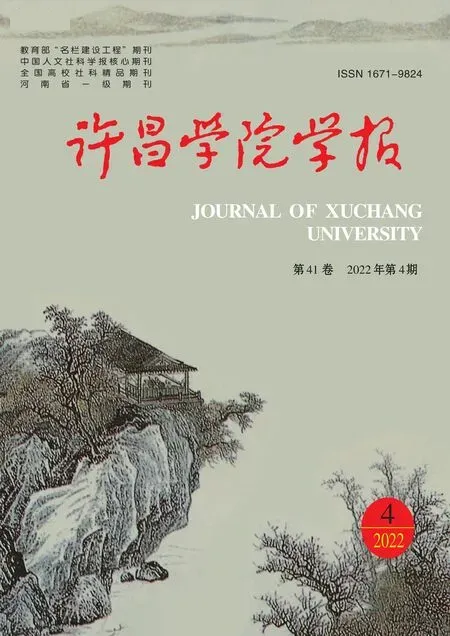钟嵘为何置惠休于下品
倪 缘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诗品》研究者众,但对“齐惠休上人”条的研究却甚少,可能是现存文献较少的原因。然惠休却是《诗品》研究乃至齐梁文学研究极为重要的一环。《诗品》中提及惠休者共有四处:中品“宋光禄大夫颜延之”条:“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1]351下品“齐惠休上人”条:“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1]560下品“齐黄门谢超宗……齐秀才顾则心”条:“余从祖正员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1]575下品“晋参军毛伯成……齐朝请许瑶之”条:“汤休谓远云:‘吾诗可为汝诗父。’以访谢光禄,云:‘不然尔,汤可为庶兄。’”[1]585
在刘宋诗坛上,惠休与鲍照齐名,但为何钟嵘将鲍照置于中品,而反常地将惠休置于下品呢?以钟嵘对惠休的评语来看,诗情淫靡似乎是其诗被置于下品的原因。但问题在于,同样是抒发闺怨,为何秦嘉、江淹等人的品第却高于惠休呢?
一、问题的提出
惠休在当时影响颇大。作为诗僧,他与当时文人有着广泛的交游。《宋书·徐湛之传》记:“时有沙门释惠休,善属文,辞采绮艳,湛之与之甚厚。”[2]1847除徐湛之外,鲍照、吴迈远和谢超宗等人也与惠休有所来往,如鲍照诗集中存《秋日示休上人》《答休上人》等,而惠休也现存《赠鲍侍郎》诗一首。《南齐书》记:“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3]908钟嵘在《诗品》中亦言:“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1]575可见在刘宋诗坛上,惠休与鲍照的诗歌创作与影响几乎是并立的。
唐释怀信《释门自镜录》载:“慧休,字茂远,俗姓汤,住长干寺。流宕倜傥,嗜酒好色,轻释侣,慕俗意。秉笔造牍,文辞斐然,非直黑衣吞音,亦是世上杜口。于是名誉顿上,才锋挺出。清艳之美,有逾古歌,流转入东,皆良咏纸贵,赏叹绝伦。自以微贱,不欲罢道。当时有清贤胜流,皆共赏爱之。至宋世祖孝武,始敕令还俗,补扬州文学从事。意气既高,甚有惭愧。会出补勾容令,不得意而卒。”[4]809通过这段记载可知,惠休的文学创作极受欢迎,一时造成“洛阳纸贵”的现象。江淹也曾拟五言诗《休上人怨别》,模仿惠休的五言诗创作,而同为其拟诗对象的还有曹植、阮籍、谢灵运等文坛翘楚。可见,在江淹看来,惠休也可称为创作怨别诗的代表。
朱右道:“予尝观晋唐来高僧,以诗名者概不少也。若支遁之冲淡,惠休之高明,贯休、齐己之清丽,灵彻、皎然之洁峻,道标、无本之超绝,惠勤、道潜之滋腴,虽造诣不同,要适于情性,寓意深远,至于今传诵不衰。”[5]73-74惠休对后世诗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李白“君同鲍明远,邀彼休上人。鼓琴乱白雪,秋变江上春”[6]1823、白居易“道林谈论惠休诗,一到人天便作师”[6]4875、杜甫“隐居欲就庐山远,丽藻初逢休上人”[6]2563等。王树平、包得义认为惠休与鲍照的交往在唐代甚至具有重要的文化符号意义[7]。
那么,为何钟嵘要将惠休诗放在下品呢?钟嵘云:“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1]560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惠休之诗并不如鲍照,钟嵘也确实可评惠休诗于下品,但问题在于钟嵘对惠休的评语并不能完全解释将后者置于下品的原因。
首先,钟嵘认为惠休诗歌情感淫靡。但在当时这样的诗人并不少,江淹、鲍照等都创作过这类诗歌,如江淹《征怨诗》《咏美人春游时》、鲍照《代白头吟》《幽兰五首》等。而江、鲍二人却被列入中品,钟嵘评鲍照诗道:“其源出于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俶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凐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1]381钟嵘甚至未提及鲍照爱情闺怨类五言诗。而钟嵘对于江淹的评价亦是如此。
惠休诗现存十一首:《怨诗行》、《秋思引》、《江南思》、《杨花曲》三首、《白纻歌》三首、《楚明妃曲》、《赠鲍侍郎》。存五言诗五首,其《怨诗行》:“明月照高楼,含君千里光。巷中情思满,断绝孤妾肠。悲风荡帷帐,瑶翠坐自伤。妾心依天末,思与浮云长。啸歌视秋草,幽叶岂再扬。暮兰不待岁,离华能几芳。愿作张女引,流悲绕君堂。君堂严且秘,绝调徒飞扬。”[8]1243此诗源于曹植《七哀诗》,感情悲怆婉转,抒发了深闺少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以及美女迟暮的悲伤。《杨花曲》其三:“深堤下生草,高城上入云。春人心生思,思心长为君。”[8]1244这首诗也表达了恋人相思之情。倘若钟嵘认为闺怨诗诗格较低,则不应将秦嘉夫妻诗列入中品。可见,至少在诗歌情感表达方面,钟嵘因惠休诗“淫靡”而置其于下品实难让人信服。
其次,钟嵘认为将惠休、鲍照相提并论是因为颜延之嫉妒鲍照而故意为之。这一观点源于羊曜璠,其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1]560。羊曜璠是谢灵运的好友,《宋书·谢灵运传》:“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2]1774羊曜璠认为颜延之心胸狭窄,妒忌鲍照的文采,因此将鲍照与惠休并立。但羊曜璠的话有两个理解方向:一、惠休诗确不如鲍照诗;二、借此贬低颜延之的人格。
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颜延之与惠休曾有过争执,惠休评谢灵运与颜延之诗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1]351颜延之因此“终生病之”[1]351。而颜延之亦作惠休诗评:“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9]881倘若说惠休对颜延之诗的批评尚是从辞采出发,那么颜延之评惠休诗则近乎毫无道理的攻击。“委巷中歌谣”在颜延之这样的上层文人眼中乃是俗体,诗格卑下,“作家一旦使用这种俗体进行创作,那么他在这种艺术形式上的一切文学表现,无论水平多高,也还是一种低俗的表现,逃脱不了被歧视的命运”[10]。鲍照对颜诗的评价与惠休语极为相似:“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9]881因此,面对二人负面的评价,颜延之极有可能因诗体的格调将鲍照与惠休并列,而此非关乎诗歌艺术水平的高下。再从第二个角度来看。颜延之曾与谢灵运争名,作为后者的好友,羊曜璠的立场显然站在谢灵运这边。因此,羊曜璠所言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并不能直接证明鲍照诗优于惠休诗。
最后,虽然在《诗品》中并未言惠休诗歌辞采方面的问题,但《宋书》记惠休“辞采绮艳”[2]1847,那么,钟嵘是不是因此置其于下品?答案是否定的。上品之班婕妤、张协,中品之张华等皆有绮丽之评,下品“晋东阳太守殷仲文”条亦言:“义熙中,以谢益寿、殷仲文为华绮之冠,殷不竞矣。”[1]524显然,钟嵘没有将辞采绮丽作为诗歌品评等级的标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不论是从诗歌情感,还是从诗歌形式等方面,钟嵘在讨论惠休诗时都未能给出充足的理由将后者置于下品。
二、酒肉与入仕:惠休的身份特征
要解决这一问题,则不得不先了解惠休的特殊身份。自昙标道人谋反之后,孝武帝意识到佛门中未必都是潜心学佛者,于是诏令:“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2]2386-2387而惠休也在沙汰之列。释神清《北山录》云:“惠休为文,名冠上才。嗜酒色,无仪法(蜀僧可朋亦然,死于逆旅,而尸弃郊野)。孝武以其污沙门行,诏勒还俗,补扬州文学从事,患不得志,终于句容令焉。”[11]629惠休虽为僧人,却“嗜酒好色”[4]809,完全不守沙门戒律。但惠休被勒令还俗后,孝武帝因其文采斐然而引其入仕途,任扬州文学从事。可见,惠休有两重身份特征——嗜酒好色与入仕。
佛教有着严格的戒律。戒学被看作佛教戒定慧三学之首,戒律文献也被看成三藏之一。《四十二章经》言:“弟子去离吾数千里,意念吾戒必得道。在吾左侧意在邪终不得道。”[12]724可以说,戒律的遵守与否直接关系着僧人能否实现解脱。虽然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不断转向,但始终都保持着对戒律原则的重视。佛陀耶舍译《四分比丘尼戒本》言:“善护于口言,自净其志意,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净,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13]1040只有在身、口、意三个方面止恶行善,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僧人首先就要受戒持戒,而戒有两种,分为出世戒与世间戒。在实践中,僧人所持的出世戒往往比世间戒严格得多,其基本的止持戒律有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对于饮酒,佛教戒律中亦有限制,如《十诵律》:“佛种种因缘诃责饮酒已,语诸比丘。……‘若比丘饮酒者,波逸提。’酒者有二种:谷酒、木酒。……若比丘取尝,咽者亦名为饮,是谓饮酒波逸提。波逸提者,煮烧覆障,若不悔过,能障碍道。”[14]121佛教认为凡违反戒律饮酒且屡教不改者,不能得道。
尽管在佛教中戒律这般重要,惠休却“嗜酒好色”。会不会是因为当时未有戒律经文传译过来而致惠休对此不知情呢?据文献记载,律学五论之一的《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在刘宋时期的元嘉十二年已由僧伽跋摩译出。《高僧传》卷三《宋建康龙光寺佛驮什传》也记载:“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龙光寺,译为三十四卷,称为《五分律》。什执梵文,于阗沙门智胜为译,龙光道生、东安慧严共执笔参正,宋侍中琅琊王练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于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并行于世。”[15]96可见,至南朝已有相当数量的戒律文献流传了。
即使惠休并未接触过这类经论,但其对刘宋僧侣因违戒而受到处罚的事迹也应有所耳闻。孝武帝时期,周郎进言:“自释氏流教,其来有源,渊检精测,固非深矣。……复假精医术,托杂卜数,延姝满室,置酒浃堂,寄夫托妻者不无,杀子乞儿者继有。而犹倚灵假像,背亲傲君,欺费疾老,震损宫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内教之所不悔罪,而横天地之间,莫不纠察。人不得然,岂其鬼欤。今宜申严佛律,裨重国令,其疵恶显著者,悉皆罢遣,余则随其蓺行,各为之条,使禅义经诵,人能其一,食不过蔬,衣不出布。”[2]2100此足见当时佛教广泛存在各类违戒事件,严重者甚至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惠休活跃于僧团和文人之间,对此肯定是知悉的。
同时,惠休诗的题材主要集中在闺情方面。闺怨诗,多以情贯穿,缠绵悱恻,表现男女之间浓烈的爱意,往往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毫无疑问,创作这样的作品与惠休的僧人身份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四十二章经》云:“佛言:人为道去情欲,当如草见火,火来已却。道人见爱欲,必当远之。”[12]723佛教将男女之爱乃至由其产生的欲望称为“染污爱”,而“染污爱”又会引发恶行,致人犯下恶果,造下恶业。《别译杂阿含经》云:“欲爱染着能生恼乱,于现在世,增长恶法,忧悲苦恼,由之而生;未来世中,亦复如是。”[16]392但惠休不仅没有因创作闺怨诗而获罪,反而凭此出仕。
从《北山录》的记载来看,惠休任过扬州文学从事与宛朐令两个职务。作为州郡官员,文学从事主要从事文化教育,一般由明经者担任。刘宋孙法宗“单身勤苦,霜行草宿,营办棺椁,造立冢墓,葬送母兄,俭而有礼”[2]2252,因此被辟为扬州文学从事。雷仲伦“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2]2292-2293,也被辟为江州从事。朱百年“颇能言理,时为诗咏,往往有高胜之言”[2]2292-2293,扬州亦辟其为从事。《隋书·经籍志》记梁扬州文学从事太史叔明撰《孝经义》一卷[17]934。与这些人相比,惠休显然并不具备任文学从事的基本条件。且据所见史料,惠休出生素族,无显贵家族所依傍。因此,诗歌才华成为惠休得以入仕的原因,也为惠休贴上了不同于其他僧人的标签。
三、诗情与政治的交织:惠休被置下品的原因
钟嵘评诗方法之一是知人论世,如《诗品》“汉都尉李陵诗”:“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1]106钟嵘将李陵的诗歌与其“颓丧”的人生经历相结合,由此得出“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的结论。而钟嵘对惠休“上人”的称呼表明钟嵘对其经历有基本了解。《释氏要览·称谓》云:“佛言:若菩萨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乱,是名上人。”[18]34在当时,文人对惠休亦称“上人”,如鲍照《秋日示休上人》《答休上人》。钟嵘面对惠休两段截然不同的经历,依旧选择以僧人的身份称呼惠休。
钟嵘既然注意到惠休的僧人身份,那么在品评惠休诗歌时自然会用以参考。与惠休同条的康宝月、帛道猷现存诗较少,康宝月存有《估客乐》二首,文辞清丽,帛道猷存《陵峰采药触兴为诗》,描写景色,清新自然。而其他佛教僧人所写诗歌,如支遁《四月八日赞佛诗》《咏八日诗三首》等、慧远《庐山东陵杂诗》,皆充满佛理而别有隐逸之气,这与惠休诗风形成鲜明的对比。对钟嵘而言,优秀的诗歌情感表达皆由直寻:“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1]220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山林僧人的诗歌似不应该有闺怨之情。惠休诗歌毫无疑问与这一观念相左。因此,惠休诗自属下品,完全不能与鲍照相比。值得注意的是,钟嵘在评惠休诗时言其“情过其才”[1]560,这里的“情”是指本不应该属于僧人的俗情,而所谓的“才”更没有超过“情”。然而,惠休却恰恰凭借诗才担任官员。考虑到钟嵘的政治经历,则不得不再从政治角度来寻找其将惠休置于下品的答案。
钟嵘出身世家,但官位卑末,他曾上书梁武帝云:“臣愚谓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侥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19]694钟嵘认为官员的任免应该与其家族次第紧密关联,不应当以军功等条件为任官标准。从钟嵘上书梁武帝可以看出,他依然保留着强烈的门阀意识。梁武帝虽重视门阀,并修订谱牒,“‘……窃以晋籍所余,宜加宝爱。’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离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9]1462,但是他并非要重用倚靠门阀贵族,而是要溯流正本,严辨清浊以拉拢高族对他的支持。实际上,当时具有实权的职位无一不是寒门把控。如《通鉴》一四五记:“霄城文侯范云卒。云尽心事上,知无不为,……及卒,众谓沈约宜当枢管。上以约轻易,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同参国政。……舍豫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掌之。”[20]4529-4530此中所提及的士人,皆出身寒士。所谓“寒士”,非底层人民,而是士族中的中下层。
《魏书·萧衍传》:“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云国家强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悦。是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风旨,莫敢正言。”[21]2184-2185《隋书·五行志》亦云:“时帝自以为聪明博达,恶人胜己。”[17]659一方面,萧衍自恃甚重,另一方面,钟嵘家族在齐梁时代已经式微。因此,钟嵘只能忍耐内心的矛盾,迎合皇帝。如在《诗品序》中,钟嵘极为夸张地称赞了梁武帝的才华:“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学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1]83
正如上文所言,汤惠休本是下层素族,入沙门期间行事颇为浪荡,目无佛法,创作淫辞,如此违背佛家戒律的僧人却因孝武帝赏识其才华而入仕。钟嵘并非认为有才的素族不能入仕,也没有将政治势力纳入评诗的标准,但问题在于惠休“情过其才”。在钟嵘看来,惠休没有多少诗才,不应有的俗情却充斥在字里行间。相比之下,惠休的人生经历无疑构成了对钟嵘遭遇的某种讥讽。因此,钟嵘在评价惠休时或许不自觉地掺进了个人政治情感的因素,而不是仅从诗学层面对惠休诗歌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
邬国平《梁武帝与钟嵘〈诗品〉》详细地谈论了梁武帝对钟嵘《诗品》写作的影响[22]。梁武帝在《述三教诗》中写道:“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不毁惟平等,至理归无生。分别根难一,执著性易惊。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23]352虽然在诗中,梁武帝直陈自己的信仰变化,并主张将三教调剂合一,但实际上,梁武帝更偏爱佛教:“至天监十年四月五日。(郝)骞等达于杨都。帝与百僚徒行四十里,迎还太极殿。建斋度人,大赦断杀。挂是弓刀槊等,并作莲华塔头,帝由此菜蔬断欲。”[24]389天监元年,梁武帝派郝骞等人迎佛像。天监十年,梁武帝与诸官徒行以迎佛像还。再如,天监六年,范缜写作《神灭论》,梁武帝集结诸臣对此文进行反驳。梁武帝亲自主持这些声势浩大的崇佛运动,以致社会中无处不弥漫着佛香。在梁武帝崇信佛教的背景下,将负有诗名的僧人惠休放置在下品似乎有些冒险。
事实上,梁武帝在崇佛的同时也对佛教进行了规约,其中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倡导僧尼食素。在梁武帝的推动下,中国佛教戒律开始变革,其根本目的是确保众生佛教信仰的坚定性和佛教团体的纯洁性。在梁代僧官体系中还增加了白衣僧正的职位,所谓白衣僧正,是指俗人管理佛门事务,梁武帝甚至想要自己担任此职务。《续高僧传》言:“逮梁大同中敬重三宝,利动昏心。浇波之俦肆情,下达僧正,宪纲无施于过门。帝欲自御僧官,维任法侣,敕主书遍令,许者署名。”[25]170-171因此,即便是梁武帝,也会厌恶惠休的所作所为,并不会因其有僧人身份而网开一面。更何况,南朝佛教徒鱼龙混杂,甚至有人有过反叛的行为,如宋僧人昙标与羌人高阇谋反,梁沙门僧强起义。在这种背景下,惠休违戒的行径实际上成了对统治阶级挑战的象征。钟嵘将惠休诗置于下品恰恰符合梁武帝规范僧团的政策,并不会招致萧衍的反感。
四、结语
在南北朝时期,惠休与鲍照齐名,然钟嵘却一反众说将鲍照置于中品,将惠休置于下品,仅从钟嵘所给的评价与解释来看实难令人信服。钟嵘论惠休乐府闺怨诗“淫靡”,可同写闺怨诗的其他诗人却鲜见被置下品。惠休虽为僧人,但其行事乖张,经常违反佛教戒律,以致宋武帝强行使其还俗,后因宋武帝欣赏其才华而得以入官。钟嵘将惠休置于下品,从诗学层面而言,在于惠休诗歌所抒发的感情并非直寻。同时在钟嵘看来,惠休浅薄的诗才并不足以支撑他出仕。在诗情与政治两种因素的影响下,钟嵘将惠休放置在下品。或者此举未为允当,但也不得不强调这是由于惠休身份、经历特殊,且并非意味着钟嵘将诗人的出身作为评诗的标准之一。
——以《登大雷岸与妹书》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