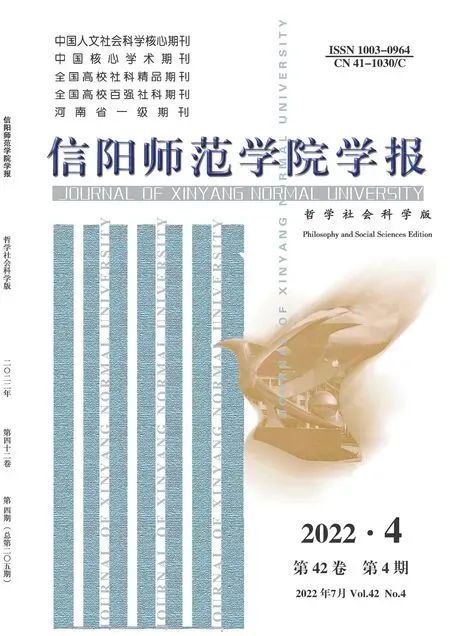亲情、历史和童年想象
——论“梅子涵新小说”的叙事艺术与美学走向
李 燕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7)
作为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坚持艺术探索的“少数派”之一,梅子涵近期的创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收入《绿光芒》中的《快递》《校长》等近百篇散文;二是在《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上海)等杂志上陆续发表的《麻雀》《妹妹》《押送》《乡下路》等一系列精致饱满、内涵丰富的儿童小说。后者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广泛关注,被命名为“梅子涵新小说”。在“梅子涵新小说”系列创作中,梅子涵告别了初登文坛时的艺术实验和标新立异,他以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态度调整着自己的探索,延续和强化了其早期儿童小说创作的抒情色彩和叙事创新,同时呈现出更深邃的心灵探究、更奇特的幻想融合等美学变化。本文尝试从整体上阐释“梅子涵新小说”的艺术特质,进而把握梅子涵儿童小说创作的美学走向,并重新审视他对当代儿童小说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一、叙事视角及其美学意蕴
20世纪80年代,在成人文学中的马原、洪峰等以先锋派的姿态备受关注之时,儿童文学界也出现了班马、梅子涵等新派作家,他们的“探索性作品”在主题内容和叙事形式上都表现出大胆的创新与突破,而梅子涵是“探索性儿童文学中走得最远,陌生化程度最高,当探索逐渐退潮,他也是将探索姿势坚持得最久的一位”[1]127。进入新世纪以来,儿童畅销书和轻阅读盛行,类型化的童年叙事大行其道,儿童文学的艺术个性日渐消失,但梅子涵依然坚定而从容地走在儿童文学的新“征途”上。2007年,他在《押送》的创作谈中再次明确释放出艺术创新的强烈信号,他说:“小说的写法是可以发明的,可以创造,可以实验,写作应当探索。探索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天天要做的事情……我很喜欢前进。”[2]由此开始,梅子涵陆续完成了《麻雀》《妹妹》《押送》《乡下路》《小脚奶奶》《蓝裙子》《妹妹》《饭票》等一系列儿童小说,延续了他“对更新儿童小说叙事模式、创造新的叙事可能的依恋和执着”[3]272。
对儿童小说写作来说,叙事角度和人称的选择也是富有意味的表现形式。梅子涵的儿童小说常常选择“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这有助于他在小说中倾诉个人经验、表达主观情感、确立自我立场,这种第一人称“我”与作家自我之间复杂的美学关系,是梅子涵儿童小说的显著标识之一。而在“梅子涵新小说”系列中,第一人称“我”的身影和声音更加频繁地出现,无论是讲述“我”自己的故事的《饭票》《一年级的故事》《十三岁的故事》等,还是讲述亲人、朋友的故事的《妹妹》《蓝裙子》《小狮子》等,都采用了第一人称“我”叙事。事实上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就开始自觉采用限制性叙事视角来突破传统小说的全知叙事,郁达夫、废名等作家更是以第一人称叙事表达人物的隐秘内心,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情感效果。相较而言,在“梅子涵新小说”中的叙事者“我”与“隐含作者”始终交错在一起,散发出一种“元叙事”的现代气息。作为作家的“我”经常现身与读者直接对话,如《吃饭的故事》开头写道:“我知道你不喜欢听,因为如果我是一个小孩儿,也不喜欢听。谁喜欢听一个讲吃饭的故事。”在《十三岁的故事》中,他直接问读者:“你觉得作家写故事、写孩子,为什么喜欢写出一个具体的年龄,是不是写出具体年龄就意味深长了呢?”第一人称叙事的灵活运用在“梅子涵新小说”中呈现出强大的叙事功能和美学效果,使得这一系列作品反复出现一个叙事者的声音,其语调或娓娓道来,或啰唆絮叨,或冷眼旁观,但从不犹疑自己对世界的观察、讲述和评判,让读者感受到作家强烈的对话意识,产生出一种深刻的情感联系和价值认同。
在“梅子涵新小说”中第二人称的使用也越发炉火纯青。如《侦察鬼》一开篇就对读者发问:“你看见那五个男孩儿了吗?”由此邀请读者去观看一群小孩儿侦察“鬼”的游戏。作家借助第二人称“你”巧妙设置了一个叙事的套层结构:传言中的“鬼”——侦察“鬼”的小分队——抓住侦察“鬼”的孩子们的老伯——观看这一游戏的“你”,由此让这个平常、简单的童年故事变得妙趣横生。再如《乡下路》也有意使用第二人称叙事:“你现在就是重新走在去乡下的路上,外婆走在前面,你拉着妹妹的手走在后面。那是好长的路哦……”在这里,“你”的使用实现了作家与童年自我的跨时空对话,让小说中长长的土路、炎热的天气、热闹的中山桥、叫卖西瓜的人、淹在水里的树,都透过“你”的目光变得生动、鲜活起来,从而引领读者沉浸于童年记忆。
“梅子涵新小说”对叙述人称娴熟自如地运用与转换,常常与小说的思想内涵互为表里、相互推进。申丹认为在回忆性叙事作品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眼光:一种是叙述者追忆往事的眼光;一种是叙事者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体现出叙事者“在不同时期对时间的不同看法或对时间的不同认识程度”[4]187。在“梅子涵新小说”中,作家一方面以充满童真的“叙事视角”绘声绘色地讲述故事;另一方面又以成年的“经验视角”介入其中,以弥补儿童视角造成的叙事简单化等不足,让个体性、片段性的回忆产生现实的延伸和思辨的深刻性。小说《押送》描述了“文革”中一群小红卫兵押送校长下乡的过程,作者抛开描述历史往事的全知视角,采用第二人称对多年前押送路上的情景进行模拟和揣测,他接连抛出了一连串自己的猜测和对“你们”的询问:“你们一路对他凶不凶?有没有给他喝水?……你们带着的馒头有没有给他也吃一个?”这一连串看似琐碎的询问如同不动声色的逼问,让读者尤其是包括作者在内的历史当事者一起反思自我、反思那段残酷灰暗的历史,因此梅子涵说:“我的讯问也是我这一篇小说的‘写作法’。”[2]可见作家对第二人称的使用已超越叙事技巧的层面,具有了深层的美学意蕴。
梅子涵具有鲜明的文体自觉与创新意识,他很早就认识到偏离正题的枝节中隐藏着小说的生命,不断“离题”有助于作家随意调动一切琐碎、混杂的人生经验。《妹妹》《小狮子》《游泳裤小孩》《十三岁的故事》《吃饭的故事》等都采用了这种自由随性的叙事方式。《游泳裤小孩》描写游泳池边的小男孩一边四处观看,一边遐想自己是如何跳水、潜泳,作家不断变换叙事口吻使故事虚虚实实、不断反复,尽显形式变换的机趣。《吃饭的故事》实际上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我”受邀前往同学豪春家吃饭的故事,另一个是“我”去妈妈同学家吃饭的故事,在叙事中不断插入“老丹”的往事,“老丹”是其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他的出现“那完全是写小说的需要,是为了前后一种感觉所渲染的气氛”[5]12。梅子涵说:“我从来就喜欢在说这个的时候也说说那个,不要寸步不离、紧紧联系……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6]179在此他对“老丹”往事看似即兴的发挥,确增强了小说的怀旧色彩。整体看来,这种在特定主题和主要人物的统摄下旁逸斜出的“离题”和恰到好处地收回,彰显出了作家收放自如的叙事技巧,构建起了一种气韵流动的开放性结构。而儿童小说《一年级的记忆》的开放性来自故事的三种结尾,作家先是讲述了“我”在上学路上被一个大孩子戴凯荣无缘无故地欺负的故事,而后设计出三种不同叙事走向:一个是“我”用扫堂腿挽回了自己的尊严;一个是警察正义凛然出手相救;一个是戴凯荣的妈妈及时为“我”解围。这三个并置的结局都暗含着儿童不同的心理逻辑,呈现出与生活本身一样的开放性。
如果将“梅子涵新小说”系列与其散文集《绿光芒》加以对照,不难发现作家在有意识地尝试打破儿童小说与散文的文体边界。如《绿光芒》中的《奶奶》等怀念亲人长辈的散文与《小脚奶奶》《隔了那么久的一首诗》等儿童小说取材内容相似,但在小说中,作家用朴素平白的语言、充满情感的细节描写了奶奶、舅舅、舅妈朴素的样貌、善良的内心,沉重的自我忏悔成为推动小说叙述的情感力量,昔日童年的精细描绘与今日追悔莫及的反思相互呼应,构成了时空不同却彼此应答的生命和声。散文《扑通》倾诉了作家为在“抄家”风潮中烧掉爸爸珍藏的旧书和爷爷唯一的照片的悔恨心情;《饭票》《麻雀》《押送》等儿童小说也都涉及作家对那段历史的个人记忆,在沉重灰暗的背景下展现特定历史中的儿童生存与成长。散文《台灯》以红台灯的柔光象征着妈妈无声的爱;《十三岁的故事》《饭票》等儿童小说同样浸透着对妈妈的温暖记忆和不尽思念。不难看出,梅子涵在“新小说”及其散文中真诚而绵密地抒写了作家备受家人疼爱的童年时期、迷乱激情的少年时代,这两种文体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形成了相互印证的叙事勾连,构建起其独特的精神自传,而自由灵活的叙事视角、丰富饱满的细节、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又让这些童年絮语式的“新小说”最终区别于纯粹的抒情散文,形成了极具个人经验的童年叙事文本。
梅子涵非常重视儿童小说的叙事技巧和个体经验的书写,“梅子涵新小说”系列中收放自如的“离题”、灵活变换的人称、张弛有序的节奏、情感的无痕融入等,都呈现出一种更纯熟的“无技巧”的艺术境界。从文体特性上看,短篇小说具有活泼灵动、难以把握的特点,从胡适提出写作“生活的横断面”到人生碎片的连缀,从摒弃故事到努力讲好故事,从强调文体规范到超越文体限制,短篇小说一步步走向成熟与多元。作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梅子涵从不拘泥于固定的写法和技巧,而是善于根据短篇小说的文体优势不断寻求各种叙事创新,表现出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的艺术面貌,如同刘绪源所说,“他的文学野心始终蓬勃存在,并不因年龄和写作经历的增长而稍减,他始终在摸索,在寻求突破,始终希望自己能跑在这一领域的最前端——这正是他的令人欣喜、赞叹之处”[7]135。在“梅子涵新小说”中,他再次将自己独特的童年经验和人生体悟执拗地放入小说的书写当中,以敏锐的文学审美直觉和理想主义情怀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形式探索与叙事创新,以近乎严苛的标准和精益求精的书写姿态捧出了一篇篇杰作。在他的手中,儿童短篇小说已然成为“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状态”和“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8]438、442。在短篇小说逐渐被市场边缘化的当下,捍卫了其艺术尊严和美学价值。
二、童年经验的散文化书写
文艺心理学表明,作家面对生活的感知方式、情感态度、想象能力和艺术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的“童年经验”[9]94。这种“童年经验”或隐或现地影响和制约着作家的题材选择、创作姿态乃至整体美学趣味的形成。如果说莫言、迟子建等成人作家常常通过“儿童视角”表现出对童年经验的潜意识回归,那么儿童文学作家们则会大量调动自己的童年记忆。瑞典作家林格伦曾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孩子能给她创作灵感,那就是童年时代的自己;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评价其好友盖达尔时也说:“盖达尔最主要、最惊人的特点,是根本无法把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分开。盖达尔的生活似乎是他的作品的继续,有时也许是他的作品的开端。”[10]308在某种意义上说,永驻童年和不断地返回童年是儿童文学作家共有的心理状态。
在《乡下路》《小脚奶奶》《饭票》《十三岁的故事》《妹妹》《隔了那么久的一首诗》等“梅子涵新小说”中,作家集中而持续地挖掘了自我的童年经历、生活经验及其鲜活的情感记忆,并“愈发走向了心灵深处”[11]。小说中那些细碎的往事、生动的细节、鲜活的场景,经过作家的精心提炼剪裁和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充满创新意识的叙述,构建出“梅子涵新小说”的崭新面貌。如《打仗》中,充满英雄情结的“我”费心组建了“游击队”并名正言顺地当了队长,妹妹被迫当上了“侦察员”,孩子们的认真投入赋予了游戏无比的庄重与神圣之感,随着情节发展,被边缘化的妹妹出乎意料地改变了故事发展的方向,“品尝无花果”事件让小说变得温暖、轻盈,充满童年的味道。《十三岁的故事》以“蓝马”和“苍鹰”这两个饱含情感的意象,塑造出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形象:故事前半段中“我”像一匹奔跑的小“蓝马”护送着妈妈穿行大街小巷;小说的后半段则借助女同学的侧面描述,让“蓝马”变成校园运动会夺冠的“苍鹰”。作家轻松而幽默的语调让这一童年往事的叙述变得生动有趣、跌宕起伏,具有鲜明的画面感。
弗洛伊德认为,个体童年时期生命体验的圆满性对其一生具有深刻意义。作家的童年经历经过岁月沉淀常常会生成一种带有想象性的心灵图式,作者的童年书写以一种艺术的形式“重返童年”,帮助作家完成对童年的自我整合和精神确认,由此也带有作家重塑和建构自我的美学意味。“梅子涵新小说”大多取材于作家的童年记忆,浸透着作家自我的童年经验、心灵感受、性格气质、思想情感,让读者看到了“梦中的真”和“真中的梦”,也感受到了作家对童年和亲情的眷恋与回归。正是这样温暖感恩的童年滋养了作家梅子涵的浪漫和诗意、敏感与博爱,让他对作品中所写的清洁工、修理工、保安、快递员等普通劳动者都报以尊重、体谅与友善,他的笔下也始终流淌出澄澈、明亮的爱与美好。
亲情是童年心灵最好的滋养,以亲情为主题的作品常常质朴平实却感人至深,朱自清在《背影》中对父亲形象的白描、法国女作家科莱特在自传体散文《茜多》中对母亲的思念,都充满永恒的感人力量。在“梅子涵新小说”中的很多作品用饱含深情的语调讲述着外婆的故事、小脚奶奶的故事、妈妈陪“我”找饭票的故事、妹妹的故事,结成了一张时光编织的亲情之网。如小说《乡下路》真切而细腻地描绘了外婆带着小主人公晓明和妹妹去乡下走亲戚的见闻和感受,漫长的乡下路散发着夏日午后的炎热气息,祖孙三人互相买冰棒的童趣,路边的大饼、油条和豆浆以及橱窗里的小鱼和米饭等细节与场景的描写,都氤氲着一种岁月如诗、童年如梦的人生感喟。小说《春天》以纯净的文字讲述“我”在春天里去外婆的墓碑旁重温与外婆相处的温馨时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时空交错的对话犹如一场灵魂深处的记忆之旅,传达出生命易逝、岁月变迁的怅惘和感伤。在小说《饭票》中,这个叫“明儿”的男孩因饥饿一下子用完全部饭票,却对妈妈撒谎说饭票丢了,最后“我”收到这样的留言条:“明儿,你丢了的饭票妈妈找到了。中午吃饱,不够就多买一个馒头。”妈妈没有戳破“我”的谎言,而是编织了另一个谎言安慰“我”,母亲的宽容和慈爱让“我”内心升腾出难以言表的愧疚和温暖。“梅子涵新小说”以真实而饱满的细节表达了对童年和亲情的眷恋和赞颂,倾诉着作者内心的温暖、感恩与忏悔,他的一次次讲述、回味构成了一次次的心灵洗礼,铺设出一条通往人情人性的隐秘通道,引领读者去发现美好的人生真谛,陷入含泪的微笑和静静的沉思。
徐鲁认为:“梅子涵是一位极其讲究儿童文学文体和叙述语态的作家。他所讲述的童年故事,有着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充满童趣的故事里荡漾着单纯的诗意。”[12]224与其他儿童文学作家相比,梅子涵的儿童小说大多情节单纯而情感饱满,他的《走在路上》等早期作品就呈现出忽略情节、注重书写人物内心的艺术追求,“梅子涵新小说” 则以回望的姿态反复咏叹亲情,呈现出更鲜明、更浓郁的抒情化倾向。梅子涵曾这样写道:“每个人的记忆都是海洋,很远的日子在下面,昨天的故事在水上。离开童年,童年反而加倍情深,每条小鱼的游动都是感情的尾巴在摇,情深处没有不美好的风光。”[13]2岁月和时光诗化了他的童年记忆,在 “梅子涵新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宏大的主题、复杂的情节,作家和他笔下人物的欢乐、哀愁与慰藉都来自平淡的日常生活,这种贴近个体生活和情感体验的审美表达,体现出卡尔维诺所说的“平淡的坚实性”和一种真实的诗意。在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鲁迅、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等人都曾将散文笔法带入小说创作,汪曾祺也曾以《小说的散文化》《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等文对“散文化小说”正式命名,这种淡化情节、虚化人物的散文化小说构成了一种别样的风景。 在“梅子涵新小说”中的《春天》《外婆你好吗》《隔了那么久的一首诗》等作品专注于描写人物性格的某个侧面、心灵的一次震颤、情感的一段波澜,以抒情的诗意氛围替代了传统儿童小说的情节模式,与之相应的是,“梅子涵新小说”的叙事语言摒弃了《女儿的故事》等小说中充满反讽的“梅式幽默”,拒绝了一切重叠繁复的长句,而是采用简约而节制的笔墨,这种看似波澜不惊、洗尽铅华的语言技巧,也意味着梅子涵儿童小说由绚烂而走向平静、深沉。
从文化意义上看,童年代表着新鲜丰沛的想象与创造,并日渐成为一个具有审美和救赎意义的文化符号。因此,泰戈尔说,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而罗兰·巴特认为童年所在才是故乡。梅子涵从未忘记过自己的童年,独特而宝贵的童年记忆是他绵绵不尽的书写源泉,他“一方面选中生活中艺术含量较为丰富的人物、故事、场景、语言等,使生活向艺术靠拢;一方面创造散文化的情节、生活化的故事,向生活靠拢,不仅有效地化解了二者间的对立,而且相得益彰,成为一种很别致的创造艺术世界的方式”[1]130。在“梅子涵新小说”中对个体童年的生动讲述,传递出对童年精神的不舍与守护,在作家笔下,成长被表现为一种日常化的生活体验与生命过程,童年成为怀旧的“乡愁”与精神家园,阅读这样的儿童小说有助于启迪读者回归童年及其内心的诗意与美好。
三、童年幻想与历史沉思的融合
汪曾祺曾说过:“创作短篇小说的每一篇是每一篇的样子。每一篇小说由它应当有的形式风格,你不能写出任何一个世界上已经有过的句子,你得突破,超出。”[8]432他还特别指出:“(散文化)这样的小说写个一二十篇是可以的,但写多了,如何能够超越自己,就是摆在作家面前的很严峻的考验。”[14]33梅子涵是一位深谙叙事艺术的作家,他最早将现代小说的意识流手法引入儿童小说创作,运用“内聚焦”式的叙事人称及倒叙、插叙等叙事时间的间断、错位等手法展现儿童丰富多变的内心,以轻松幽默的口吻营造出《曹迪民先生的故事》《女儿的故事》等小说的“生活流”叙事风格。而在《一年级的记忆》《排长和小马》《麻雀》《蓝裙子》《打仗》等“新小说”中,梅子涵从儿童特有的心理和想象出发,表现出一种近似“轻幻想”的神韵和调式。
梅子涵说:“无论儿童文学作家写什么,具有超凡的想象力、幻想力不会是坏事,我的写作其实是现实性很强的……从儿童文学经典的经验来看,有时不妨可以把文体进行杂糅。”[15]91比如,在《一年级的记忆》中,为解救在上学路上被无辜欺负的“我”,作家给出了三个并置的结局,这些解救方法无不充满了儿童的想象和游戏精神。《排长和小马》以幻想的情节描写了童年的孤单,独自玩耍的“我”将陪伴的小马视为会说话的伙伴,而后这匹小马变成一个小女孩出现在“我”身边,小说将儿童这一真实而奇特的心理转化为形象,通过幻想最终让小男孩得到了友情的慰藉。儿童小说《打仗》也因幻想元素的加入弥漫出一种亦真亦幻的色彩,小说前半部分若无其事地描写着充满游戏色彩的顽童生活场景,随后逐渐推向一个令人震颤的情绪高潮:“……后来我们去拔过草。拔草的时候没有看见老爷爷,房子四周静悄悄,田里长着蚕豆,梁晓芒领着我们轻轻地唱着《五月的鲜花》,我们的眼里含着泪水。”小说中的老人、墓碑和歌曲都因幻想带上了明显的象征意味。作者没有让坚守儿子墓地的老人严肃地给孩子们讲一段悲壮的英雄故事,而是让孩子们去猜测、去想象,正是这个无意之中的发现触发了孩子们顿悟式的成长。
在“梅子涵新小说”系列的后期创作中,真实的童年生活越来越多地融入带有童真童趣的想象与幻想,出现了被虚化的美学迹象。如小说《蓝裙子》以温婉哀伤的幻想传递出长歌当哭般的心灵震撼,作家一开始就交代妹妹一岁时生病夭折,但在幼小的“我”的眼中,妹妹一直穿着一条蓝裙子生活在“我”的身边,陪我吃药、陪我上学。后来我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看到一条小狗,并在这条小狗的眼睛里看到了妹妹的眼神!当小狗开口说“哥哥不要走”时,“我‘哇’的一声,哭得一步也迈不动”。如何诉说死亡这一沉重的哲学命题,高明的儿童文学作家总会找到一种符合儿童理解和接受的审美表达,《蓝裙子》对死亡的独特而奇幻的描写来自作家对儿童幽深内心的洞察。在这篇小说中,蓝裙子寄寓了作者无尽的深切思念和童年幻想,小狗是“我”对妹妹思念的折射和变异,而超越生死的相遇引发了作者压抑多年、痛彻心扉的亲情,因此幻想和真实并存,而“幻想不仅修正、弥补着我们的生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建构成主体和世界……使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具有了审美的意味”[16]10。
如果说《蓝裙子》里的幻想指向的是儿童幽深的情感世界,那么儿童小说《麻雀》则以充满童真的幻想指向了深层的历史反思。混乱的年代、物质的匮乏、人们的盲从,让饥饿和荒诞成为无数人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麻雀》生动地描写了“除四害”运动中人们锣鼓喧天地吓唬麻雀,使其惊惧疲惫而死的历史场景。小说以锣声、鼓声、敲钢精锅声和震耳欲聋的呐喊声渲染出那个时代的特定氛围,那时还是孩子的“我”加入了驱赶麻雀的大军,却在爬到房顶上不慎滑倒时,反而被两只麻雀搭救了。这两只善良的、会说话的麻雀不仅挽救了“我”的生命,也唤醒了“我”的良知。这个幻想性结局充满了救赎的温情和明亮的人性光芒,启发读者在人性冲突中学会思考和成长。有学者认为,作家自我的童年书写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摆脱私人性的童年生活和情感记忆对于作家个人的精神笼罩,使之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至更普遍、更有高度的童年趣味和童年精神”[17]。在《饭票》《麻雀》《押送》等“梅子涵新小说”的创作中,作家看待自我、童年和历史的目光都在发生悄然而深刻的变化,他在鲜活的童年记忆中含而不露地注入了对人情人性、社会历史的独特感受和深层追问,使充满童趣和幻想的儿童小说承载起深沉的人文内涵。
新时期以来,借助儿童视角揭示和反思“文革”对童年造成的心灵创伤成为很多作家的艺术策略,刘心武的《班主任》、张洁的《从森林来的孩子》、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黄蓓佳的《阿兔》等是较早产生的一批佳作,梅子涵在他的《马老师喜欢的》中也曾隐约揭示“文革”对儿童造成的心灵伤害,《我们没有表》更是真实反映了一群少年在“串联”路上自由而慌张的模样,以象征的形式隐喻了一代人失去信仰的精神迷惘。相形之下,在“梅子涵新小说”中对历史的审视更加深沉内敛,作家将童年记忆、充满童趣的幻想与对历史和人性的理性审视完美融合,而《麻雀》更是创造性地脱离了惯常的回忆性叙事模式,以儿童特有的夸张、神秘的感知展开了充满黑色幽默的幻想,展现出儿童文学既清浅又厚重的美学气质。
想象是童年理解和建构世界的特有方式,“梅子涵新小说”通过带有儿童心理特点的想象和幻想,将变形、象征、隐喻等现代手法引入其中,以充满童趣和夸张色彩的幻想,完成了对童年心灵的关照和对荒诞现实的救赎,不仅给读者带来温暖和感动,而且赋予了读者深沉的思考。与童话不同的是,在“梅子涵新小说”中这些从作家个人真实的童年记忆和情感深处生发出来的幻想从未进入与现实并置的“第二世界”,而是指向了对童年生命的现实关怀,表达出对历史与人性的深沉反思。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艺术的目的不是成为真理的助手……而是以更开阔、更丰富的形式重返世界。”[18]30可以说,童年幻想的加入和渲染赋予了“梅子涵新小说”另一种真实,一种超越现实世界表象的心灵与哲理层面的真实,幻想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成为作家返回现实的有效途径,由此实现了对主题意蕴的开拓与深化。
在儿童文学界,梅子涵一直以“先锋”著称,这一标签所对应的不是某些写作技巧或叙事形式,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学精神和写作姿态。雷达认为,“一个人在他的精神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历史构成一种密切关联,哪怕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多么渺小,甚至微不足道。这些不但构成我们时代的精神史,而且构成了文学的丰厚资源”[19]。尽管“梅子涵新小说”系列作品大都是作家从自身生活中选择最具文学性的人物、事件和心理情绪作为素材,但它们绝非作家的“私人叙事”。梅子涵以面对历史和童年的真诚与勇气,将个体的童年生命体验和亲情记忆与时代、历史密不可分地粘连在一起,在一以贯之的叙事创新中倾注了对童年和亲情的眷恋、咏叹,在充满童真童趣的幻想中蕴藏着耐人寻味的历史与人性反思,从而给当代儿童文学增添了深沉、阔达的美学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