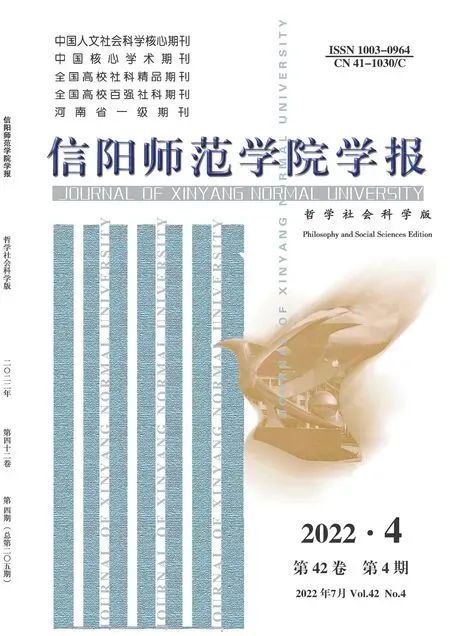论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的精英意识
施要威
(信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抗日战争时期联合而成的一所临时大学。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贫乏的物质条件下,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都难以得到保障,维系其精英意识的物质基础几近不复存在,但其精英意识却在严酷现实的考验下越发得以彰显,并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支撑西南联大教师经受多重考验坚守学术岗位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教育成就。
精英意识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概念,有着复杂的精神内涵。由于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史料阐释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的精英意识,所以在此无意花太多笔墨去探究精英意识的抽象内涵。在已有相关研究中,汪丁丁关于精英意识的理解对本研究颇有启发意义。在他看来,精英分“外在的精英”和“内在的精英”,分别对应精英身份和精英意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个体或群体的精英身份一般通过物质财富、权势地位、社会名望、影响力等外在指标得以彰显;而精英意识则主要体现在个体或群体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等内在品质方面。汪丁丁把精英意识的内涵概括为:“对重要性的感受能力,也就是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在足够广泛的公共领域显示出被感受到的重要性时必须具备的表达能力和道德勇气。”[1]汪丁丁认为,某一个体或群体的精英意识与其能自觉承担公共领域的道德责任有着密切关联。西南联大教师群体作为学术精英和社会精英,其精英意识在专业领域和公共领域都有所体现:在专业层面,他们坚信学术的本体价值,也相信学术发展对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正是这样的信仰支撑他们在贫乏的物质环境和动荡的战争环境下,依然坚守学术岗位,为学术文化发展做出坚韧的努力。在公共领域,西南联大教师敢于对抗权势,捍卫符合国家和人民福祉的价值理想,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可以说西南联大教师精英意识的精神内核是在专业领域和公共领域表现出的责任担当。
一、在战乱年代,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精英意识的物质基础几乎不复存在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有秩序的社会环境里,特定社会群体的精英意识和精英身份总体而言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群体有内在的精英意识,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责任感,那么作为回报,他们通常也会获得不错的物质待遇、社会地位来维持其外在的精英身份。而西南联大教师群体身处动荡的战争与革命年代,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环境都遭受着严峻考验,西南联大教师群体作为学术精英中的佼佼者,支撑其精英意识的物质基础几乎不复存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自抗战爆发后,通货膨胀不曾间断,从1939年下半年起,物价更是急剧上涨,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的薪金虽有所增加,但薪金增加的幅度远不及物价飞涨的幅度①。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的物质生活急剧恶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西南联大教师想尽办法维持生计:卖书、卖衣服、卖文稿、卖图章、卖花、做兼职等等,即便如此,依然无法摆脱生活困境。下面从衣、食、住三个方面来看西南联大教师物质生活的贫乏和窘迫。
衣着方面。李广田1941年在昆明的街上遇到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朱自清时,他“穿了一件很奇怪的大衣,后来才知道那是赶马的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颜色却像水牛皮……以后我在街上时时注意,却不见有第二个人是肯于或敢于穿这种怪大衣”。若不是朱自清老远就打招呼,李广田简直不敢认。与李广田的难以置信不同,在西南联大校园里,教师们对各种奇怪的穿着习以为常,并不会特别留意。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时常穿一条黄咔叽布裤子,膝盖上都补上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丁。他说:“在西南联大校园里,虽然有人穿得好一点,但不论谁穿什么,倒也没有人感到稀奇。”[2]169-170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师王力说得更为直接和辛酸:“身份早已经没有了,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3]89-90
膳食方面。随着战争的持续和通货膨胀的恶化,西南联大教师的薪金已经不能应付日常饮食开销。为了节省开支,部分没带家眷的西南联大教师组成了一个膳食团,推举西南联大植物学李继侗担任膳食团的总干事,成员有朱自清、陈福田、沈同、陈岱孙和金岳霖等人,只有这样才能勉强维持生计。据陈岱孙回忆:“我们的工资除了勉强付饭费之外,更无甚余钱。每个月初,在领到薪水的当日,我们把几乎每个人全部的月薪交给了这位总干事,他也就立即同厨师一起上街把本月该用的柴米油盐和其他厨房用品购买齐全,还得余下一部分钱为每日买荤素菜肴之用。”[4]345随着物价的飞涨,膳食团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只好自力更生把附近两亩多的荒地开垦为菜地,李继侗担任菜地负责人兼技术指导,沈同为助理,大家一起锄地、种菜、浇水、除草。没带家眷的教师尚且如此,需要养家糊口的西南联大教师则更为窘迫。中文系教师王力1944年曾特意撰文描述了生活的窘迫:每月薪水还不够买薪买水,开门七件事,六件没着落,把薪水改叫“茶水”更为贴切,等到茶水都买不起,只能改叫“风水”,喝喝西北风了。王力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绝食是有而不吃,绝粮是没有东西可吃。现在的公教人员距离绝粮还差一步,他们只是吃不饱。……我们的饭里至少有百分之五是谷,百分之五是砂。我常常设想:假使我是一只小麻雀,那够多么好!麻雀喜欢吃谷,它肚子里又有一个砂囊,以砂磨谷,岂非得其所哉?无奈我是一个人!”[5]154-155不但教师们面临吃的问题,西南联大负责人之一、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家的生活也很拮据,为了减少饮食方面的开支,梅贻琦和潘光旦两家一起在办事处包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6]63-64。
居住方面。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师生作为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昆明,住房困难是这些文化精英们首先要面对的难题。因为找不到房子,陈寅恪、罗常培、郑天挺、郑昕、游国恩、朱自清、陈福田、沈同、陈岱孙和金岳霖等不少西南联大教师都只能住进狭窄的单身宿舍里。闻一多和华罗庚两家14口人曾共住一室,隔帘而居。直至抗战结束西南联大教师的居住条件始终没能得到显著改善。20世纪40年代前半叶,华罗庚一家6口在距离昆明城20里的村庄里,租了两间小厢楼,楼下是房东饲养的猪马牛羊。“晚上牛擦痒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华罗庚不由感慨道:“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也。”[7]43-60抗战后期,历史系教师吴晗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场旁边的一座破楼里。“说破楼,其实还是冠冕话,四面都是纸窗,上面瓦缝可以见天,在楼下吃饭时,灰尘经常会从楼上掉在钣碗里”[8]439-440。梅贻琦的住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在1946年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嚥下灰土不知多少。”[9]206如果说落些灰尘杂屑还能凑合的话,碰上连阴雨就疲于应付了。社会学系教师陈达在1943年7月6号的日记中描述了下雨时屋中的情形:“刚听到雨声,余用饭碗接漏,灶上共摆五碗,各碗很容易漏满,余忙于倒水,辗转倒换,周而复始,此外有一漏甚大,另用铝饭锅接之,如是者一小时半,雨渐小,余才开始煮稀饭。厨房长10步宽7步,今日有漏14处。余杭有谚描写贫人的住屋云:‘晴天十八个日头(太阳),雨天十八个钵头(接漏用)’,我们的厨房离此标准已不远。”[10]168-169
通过对衣着、饮食、居住情况的简单素描,我们不难看出,西南联大教师不仅几乎失去了支撑其精英意识的物质基础,就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得到保障。但恶劣的外在环境并没有让西南联大教师意志消沉,得过且过,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坚守岗位,完成了时代和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和责任。在战争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冲击下,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的精英身份大打折扣,但他们的精英意识并没有随之衰微,反而在外在恶劣环境的反衬下,越发得以彰显。
二、在贫乏的物质条件下,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精英意识的学术支撑彰显力量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贫乏的物质条件下,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精英意识的物质基础几乎不复存在,但他们对学术信念的坚守和学术救国抱负的追求,为其精英意识提供了有力且持久的内在支撑。
1.学术信念:支撑精英意识的价值理性
士大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他们也不缺乏精英意识,有自己坚守的价值信念和理想抱负,但他们的精英意识是政治本位的,政治和仕途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传统读书人通常把读书治学作为进入仕途的工具和手段,他们的理想抱负一般也在政治秩序中得以展现。与传统读书人不同,西南联大教师群体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接受了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对学术的本体价值及其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深远意义有深刻的体认,并且能够经受住来自政治和权力的诱惑,志愿长期致力于学术创新和文化传承。正如希尔斯所言,现代知识分子会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终极真理而产生一种自重感。西南联大教师也因为学术产生了自重感,而学术也成为他们精英意识的内在支撑。换句话说,西南联大教师的精英意识是基于学术本位的,学术替代政治成为其安身立命的根本。
近代中国基于学术本位的信念并不是到西南联大教师那里才出现和形成的。伴随着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冲击,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有识之士在清朝末年就意识到了学术依附于政治的弊端。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也为开明的文化精英讨论现代学术的价值开辟了空间。早在清末民初,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就开始宣扬学术的价值和作用,为日后学术价值的张扬奠定了思想基础。梁启超在1912年对北大学生的演讲中,对学术精英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进行了鼓舞人心的宣扬:“诸君受学于此最尊严之大学,负研究学问之大任,唯祈诸君能保持大学之尊严,努力于学问事业而已……以发挥我中国之文明,使他日中国握世界学问之牛耳,为世界文明之导师,责任非轻,诸君其勉力为我中国文明争光荣。”[11]2527-2528蔡元培在1913年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谈话中说道:“国事决非青年手足之力所能助,正不若力学之足以转移风气也。……唯一之救国方法,只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即使不幸而国家遭瓜分之祸,苟此一种族,尚有学界之闻人,异族虐待之条件,必因有执持公理之名人为之删减。”[12]105梁启超、蔡元培等人极力宣扬大学和学术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价值以及学术精英对国家存续和文明绵延所承担的使命,甚至认为学术发展是唯一救国方法,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观念固然很难转化为现实,但作为一种思想启蒙和精神鼓舞,它产生了应有的效果:引导年轻一代学人树立了学术信念,并为其产生基于学术本位的精英意识奠定了思想基础。
如果说梁启超等人在民国初年对学术价值的宣扬止于思想层面的话,蔡元培在执掌北京大学以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则为学术价值的张扬打下了制度基础。蔡元培引进了一批崇尚学术又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消除了北大师生间原有的官僚习气,把北大从一个饱受诟病的官僚机构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机构。蔡元培在对师生讲话时,时常强调学术的重要性,并认为青年学生作为现代学术发展的生力军,也因此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13]89胡适1920年、1921年连续两年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强调了北大师生对提高学术的责任,1921年更是喊出了“努力做学阀”这一颇具轰动性的口号,意在呼吁“北大同人更应该从浅薄的‘传播’事业,向‘提高’的研究功夫回归”[14]362。胡适“努力做学阀”的口号在大学师生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喊出了大学知识分子的心声,更加坚定了他们抵制当时盛行的民粹主义浪潮,致力于从事提高学术的工作。民国初年,多数西南联大教师正处于求学阶段,蔡元培、胡适等人对学术价值的宣扬为他们的学术理想和信念埋下了种子。
陈平原在谈及他看西南联大老照片的感受时说道:“西南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和聪慧,全都写在脸上。”[15]101这或许正是西南联大教师精英意识的最直观体现。希尔斯认为:“各高级文化中,知识分子都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最终极的真理而发生一种‘自重’(self-esteem)的感觉,无论这种真理是宗教、哲学或科学。”[16]63西南联大教师因为学术所产生的“自重”感是其精英意识的内在支撑,正是这种学术支撑让他们得以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贫乏的物质条件下依然展现出难能可贵的精英意识。
2.学术救国:支撑精英意识的工具理性
在动荡的战乱年代,西南联大教师依然坚信学术和文化对于抗战救国有长远价值。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钱穆的文化本位思想在他的相关论述中可以得到清晰地展现:“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17]32钱穆的文化本位思想让他相信,文化的续绝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文化灿烂,则国家不会亡,文化衰竭,国家亦不能长存。钱穆进一步指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他的这种观念让他坚信历史研究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价值:“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功夫。”[18]5陈寅恪坚信学术思想对于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都有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他在1942年曾指出:“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19]162-164在抗战时期,哲学系教授贺麟更是在他的著作中不厌其烦地阐述学术文化对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和长远价值:“如果一个国家的学术文化不发展而徒有政治军备,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百年来之受异族侵凌,国势不振,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学术文化不如人……我们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必是文化学术的胜利。我们真正完成的建国,必是建筑在对于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发展、应用上。换言之,必应是学术的建国。”[20]26-27因此,贺麟认为教师学者担负着“学术建国”的神圣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使命,需要各自领域的代表人物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20]244。
透过以上表述,我们可能会觉得西南联大教师学术救国的抱负过于理想化。在现实政治中,尤其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学术并不会显得有多么重要,至少不像西南联大教师宣称的那样,发挥根本性作用。但也正是这样理想化的抱负和追求,成为其精英意识强有力的内在支撑,也是他们在严酷的战乱环境中坚守学术岗位的内在动力。西南联大负责人之一梅贻琦对此有着清晰的认知:“在敌人进占安南,滇境紧张之日,敌机更番来袭,校舍被炸之下,弦诵之声,未尝一日或辍,此皆因师生于非常时期教学事业即所以树建国之基,故对于个人职守不容稍懈也。”[21]94正是由于对教育和学术长远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使得西南联大教师在如此窘迫的生存环境下,并没有悲观气馁,得过且过,而是用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于学术的理想信念,展现出作为学术精英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责任担当:西南联大教师精英意识的精神内核
西南联大教师的精英意识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责任担当是其精英意识的精神内核。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贫乏的物质环境下,西南联大教师没有消沉堕落、得过且过,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学术精英的责任担当。正是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西南联大教师的精英意识成为一种可贵的精神品质,而精英意识使西南联大教师确信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是重要的、无可替代的,而且是多维度的。西南联大教师的责任担当既表现在学术和文化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丁文江的描述颇能代表当时学术和文化精英的普遍心态:“中国的人民,号称有四万万:进过小学堂以上的学校的人,最多不过四百万;中学堂以上的,不过四十万;进过大学堂的,晓得一点科学,看过几本外国书的,不过八万。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负责任的能力,谁有负责任的能力?”[22]196更何况西南联大教师大都学有所长,并任职于国内顶尖大学,可以说是学术精英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精英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不言自明的。
1.专业层面的责任担当
西南联大教师作为学术和文化精英,如果外在条件允许,他们会优先选择在学术和文化领域持续耕耘践行自己的担当意识。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经写道:“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23]265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跃然纸上。正是这种对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闻一多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心无旁骛地寄身于学术。即便在战争环境下随校南迁时,他还因为潜心治学而很少出门,获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贺麟非常推崇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对王夫之文以载道的担当和作为深表认同。贺麟在文章中也曾引用王夫之的言论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随后,贺麟指出:“足见在一切政治改革,甚至于在种族复兴没有希望的时候,真正的学者,还要苦心孤诣,担负起延续学统、道统的责任……”[20]249冯友兰在《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中强调了大学在文化传承、知识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大学一方面是教育机关,一方面是研究机关。它不但要传授已有底知识,而且要产生新底知识。它应当是一代知识的宝库。它对于人类的职务,真正是所谓继往开来。从前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应当说一事不知,大学之耻。”[24]457大学教师作为大学中的学术主导力量,大学的学术责任也主要由大学教师来承担,从“一事不知,大学之耻”不难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沈从文在谈及文化精英的文化使命感时也没有了平时的低调,显得底气十足。他说文艺创作者可能是平常人眼中的“痴汉”,行为“与多数人庸俗利害观念相冲突”,可能被人们以各种恶名中伤,但他们却能够“超越习惯的心与眼,对于美特具敏感”。沈从文以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一切文学美术以及人类思想组织上巨大成就,常惟痴汉有分,与多数无涉,事情显明而易见。”[25]32沈从文这番表述不是为了显示作为学术和文化精英的优越感,而是为了彰显其在学术和文化领域所承担的特殊责任与使命,体现了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
西南联大教师对学术和文化使命的强调在战争年代或许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被人看作不切实际的痴人说梦。毕竟处在民族危亡的战乱时期,有太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学术文化的发展看上去对眼前问题的解决没有太大助益。但西南联大教师对学术价值的体认已经化为一种信念,这使他们坚信,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大学及其教师群体承担起学术和文化责任。正如冯友兰所说:“学术知识,对于人生的功用,不是短时间之内所能看出来底,也许有些是永远看不出来底,因为有些功用是无形底。一个大大学中,必需有许多很冷僻底学问。因为他是要包罗万象,而有许多学问,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冷僻底,然而维持这些学问的研究,正是大大学的责任。”[24]458正是这种对于文化和学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西南联大教师克服战时艰苦条件并取得教育和学术成就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2.公共领域的责任担当
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止局限于文化和学术层面,他们作为身处战争与革命年代的现代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冲动需要面向社会表达公共关怀。在现实环境的激励下,西南联大教师时常超越各自专业的限制,围绕公共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试图为普通民众争取权益或为政治改革发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面向社会时,西南联大教师凭借自己的知识优势和社会声望,基于自己的理性和道德判断,围绕公共议题发出自己的主张,试图影响政治和社会改革进程,承担起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在学术支持下,才能认清真实的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钱穆在论及历史研究对改革的重要性时写道:“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的历史有真实之了解。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唯借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唯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26]5西南联大历史系教师王赣愚则强调知识分子要担负起启蒙民众的责任:“一国知识阶级,其言论举止本有左右社会的趋向;在促进民治的时候,尤应负起领导民众的伟大使命”[27]67,知识分子虽然不是一个阶级,但他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引导舆论。知识分子“在国事上愿以坦白的态度,各抒所见,各献所见,而当权在位者绝不应妄予干涉或禁止”[27]67。通过以上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骄傲和底气,或许在现实政治面前有些过于理想化,但其中所展现的担当精神确是真挚和强烈的。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在种种现实问题的激励下,西南联大教师的关注焦点被从学术拉向了社会。吴晗在“中国社会与士大夫”的演讲中慷慨激昂地讲到:“上古的士是为天子诸侯大夫服务,秦以后为君主服务。但士受着特别教育,有特别义务——忠。因此历代危难时,舍生取义慷慨殉难的都是这些士。士对历史的贡献很大。这次战争中,文士和武士都出了力,今后文士和武士都要负起救国赴难的责任。”闻一多当即站起来接着说道:“我完全同意吴先生的看法,我们就是现在的新士大夫。我们应该负起我们神圣的责任!”[28]89闻一多还在1944年的一次师生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喊道:“现在,不用说什么研究条件了,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请问,怎么能够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29]228-230闻一多从埋头学术不问时政的纯粹学者到走向街头的民主斗士,这是一个180度的转变,但这两种角色所蕴含的精英意识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却是一脉相承的。
1945年10月1日,张奚若、周炳琳、闻一多、朱自清、李继侗、陈岱孙、吴之椿、陈序经、汤用彤、钱端升等10位西南联大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对国事的主张。此电文曾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为题,刊登于1945年10月17日昆明《民主周刊》第2卷第12期上。电文中写道:“奚若等内审舆情,外察大势,以为一党专政固须终止,两党分割亦难为训。敢请先生等立即同意召集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政治会议,共商如何成立容纳全国各方开明意见之联合政府,再由此联合政府于最短期内举行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定期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根本大法,以产生立宪政府……奚若等向以教学为业,目击政治纷乱所加于人民之损害,亦既有年,值此治乱间不容发之际,观感所及,不容缄默,率直陈词,尚乞察纳。”[30]204-206通过这段电文,我们不难感受到西南联大教师在关键历史节点对时局的忧虑和关切,作为学术精英的公共关怀和责任担当也在短短的电文中得以充分显现。作为当事人的陈岱孙认为,这种责任担当对于战火中的西南联大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在数十年后感慨道:“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31]序西南联大教师的精英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超越了个人所面临的生活窘境和精神压力,支撑他们坚守学术岗位,完成了时代赋予他们的学术和文化使命。
四、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精英意识带来的启示
通过对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精英意识和责任担当的考察,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精英意识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品质,有助激发大学教师的责任担当
通过以上历史考察不难发现,精英意识是西南联大教师对自身价值追求和角色行为高于常人的自我期许和定位,这让他们真切体认到自己所承担的独特责任和使命,并能够激励其在严酷环境中坚守岗位,不断攻坚克难,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时代背景、社会文化等诸多宏观因素的影响下,当代大学教师群体精英意识的整体性弱化或许在所难免,但不能因此否认其精英意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在社会文化、制度环境、个体价值追求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事实上已经主动或被动地蜕变成了学术老板或学术工人,这可以看作大学教师精英意识弱化乃至丧失的一个现实表征。大学教师以学术老板自得或以学术工人自嘲的同时,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扭曲其价值追求和角色行为,使其变得庸俗化和功利化,弱化其作为大学教师本应具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西南联大教师的历史考察清楚地表明,精英意识是一种可贵的、值得追求的精神品质,是庸俗化和功利化的解毒剂,能够激发大学教师产生较高的价值追求和角色定位,更好地体认其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进而激励其在各自岗位上自主、自觉地践行责任担当。因此,在大众文化盛行、高等教育逐渐普及化的今天,依然有必要培育和呵护大学教师群体的精英意识,这有助于增强其作为学术和文化精英的担当精神,进而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外铄与内发相结合,唤醒大学教师的精英意识
西南联大教师群体之所以能在严酷的外部环境中保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学术长远价值的体认给予了他们自重感和使命感。而反观现实,当前高校功利化、数量化的科研考评制度使学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高校提升排名、教师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与此同时,高校教师自身也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完成科研任务的学术工人。在频密的、功利化的科研考评制度下,学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价值被忽略,高校教师建立在学术基础上的自重感和使命感被侵蚀,其精英意识的不断弱化乃至彻底丧失也就可想而知了。科研考评制度对大学教师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对其学术观念和角色行为有着不言自明的导向作用。科研考评制度的优化有助于在整体上唤醒和激发大学教师的精英意识和责任担当。如何建构科学合理的科研考评制度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我们不可能在历史考察中找到一个现成的可行方案。但西南联大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减少对量化指标和物质奖惩的依赖,建构有利于维护教师尊严和精英意识,激发其担当精神的科研考评制度应该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寄希望于外部环境和相关制度优化的同时,高校教师也不能放弃主观努力和积极作为,西南联大教师群体正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贫乏的物质条件下展现出了强烈的精英意识和担当精神。当前高校教师面临的环境和制度固然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并不能成为高校教师放弃精英意识和责任担当的理由。精英意识和责任担当作为行动主体内在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期许,本身也需要大学教师能够经受外在环境的压力和诱惑才能得以更充分的体现。作为高校教师,要能够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坚守治学育人理想,展现作为学术和文化精英的使命担当,而不是消极等待一个完美制度环境的出现。作为政府和高校管理者,要致力于营造让高校教师安心治学育人的良好制度环境,而不是一味呼吁教师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总之,大学教师精英意识和责任担当的弱化问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得依靠多方形成合力持续改进,既需要相关考评制度的改进,也需要大学教师的道德自律和积极作为,还有赖于制度环境和学术生态的持续优化。
注释:
① 据杨西孟在《几年来昆明大学教师的薪金及薪金实值》一文里说:“自抗战以来,由于物价剧烈上涨而薪金的增加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于是薪金的实在价值如崩岩一般的降落。到三十二年(即1943年)下半年薪金的实值只等于战前法币八元。由三百数十元的战前待遇降落到八元,即是削减了原待遇百分之九十八。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上半年薪金实值盘桓于十元左右,这主要是因为米贴按市价计算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