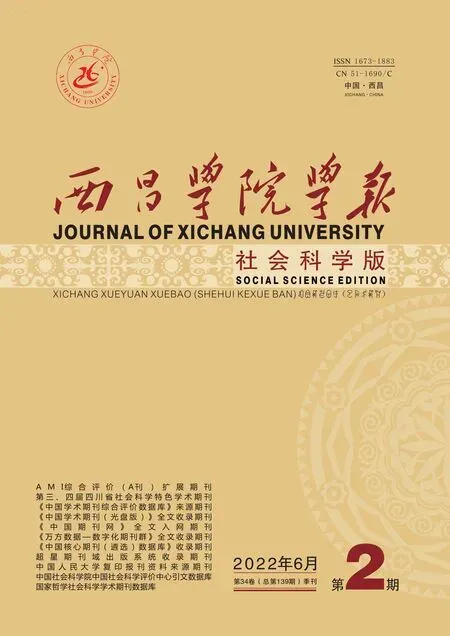生的自由与死的光亮
——《额尔古纳河右岸》生命诗学探析
达则果果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蕴含着历史的哀婉、现实的动荡无奈与文化的变迁等丰富意蕴的作品。作者以抒情的口吻追溯了一个族群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繁衍、兴盛到衰落的复杂历程。 “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1]。 小说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与立场,迟子建以民族志工作者的姿态对鄂温克族的文化结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生存哲学进行了探索,用细腻柔情的笔调呈现了鄂温克民族在生产生活里表现出来的生死意识,试图展现一个古老族群生命图景的深层况味,张扬了其热衷繁衍和渴望生存的原始生命力,以及在现代文明的诱惑前把守孤独、坚守家园的宝贵品性。
一、孤独与自由:生命底色的坚守
弗洛姆认为,人在不经意的时间和地点无来由地被抛到世上,于千千万物种中人是最绝望的一种。 可见人之孤独与生俱来,但现代人的孤独承受力是很有限的,他们总是试图通过群体的热闹去缓解或逃避孤独。 同时,他们又渴望自由,不愿活在他人的监视之下,却浑然不知“孤独是自由的必经阶段,真正的自由是对孤独的超越和扬弃”[2]。 而超越喧嚣的孤独亦是真正的自由。 驯鹿民族从熟人小圈子汇入现代社会的那一天起,就注定要沾染上现代人的孤独,追求自由即是奢侈。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民族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历经了从凝聚到分散、群居到个体、热闹到冷清的生存变迁。 在百年大变动中,这个族群从山上搬往山下试图融入城市文明,没过多久,他们中的部分人又重新回归到大自然,有的则始终坚守家园从未离开,呈现了一种不为世俗的喧闹所迷惑,坚守孤独与自由的生命底色的执着。
鄂温克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然家园,他们每一次搬迁前都把垃圾埋掉以防止散发臭味,他们从不会砍伐活树木,为防止烧毁树林而发明了不用点火的口烟。 吊死在树上的人要连同那棵树一起烧掉,金得为保护树木选择一棵没有生命力的树木吊死。 然而,滚滚而来的现代文明带来科学技术与丰富物质的同时,也对安宁祥和的自然家园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大兴安岭的被迫开发使得鄂温克人的搬迁更为频繁。 现代家园的开发切断了鄂温克人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纽带,他们被抛入孤立无援,无家可归的迷茫境地。 无奈之下,乌力楞的人纷纷迁往山下,但他们离开时的眼神是无助迷茫的。“文明有时候是个隐形杀手。 当我们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而战战兢兢地与文明接近时,人适应大自然的能力也在不同程度地下降”[3]9。 许多生来就与大自然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一旦贪恋“山下”世界的便利后就不会再回归大自然,但象征族群原始精神的“我”对文明这个“杀手”一开始就保持距离与警惕,“我”怕听不到鹿铃声耳朵会聋,看不到星星眼睛会瞎,“我”认为让驯鹿下山无异于将他们关进监狱,“我”觉得汽车放出的尾气是“臭屁”。 “虽然营地只有我和安草儿了,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孤单。只要我活在山里,哪怕是最后一个人了,也不会觉得孤单的”[4]3。 比起虚无的热闹与狂欢,散发着神性光芒的大自然比人更加丰富,也更加诚实。“我”、伊万、安草儿等人始终是属于大自然的,留在山上的人极少,却不觉得孤独,没有要与他人接触、交往的心理需求,觉得不孤独是因为在大自然里找到了精神与灵魂的寄托。 这种看似孤独的不孤独实际上是对心理学意义上孤独的超越,因为这种“孤独”是个体生命体验与独立人格的彰显,从而让人更加接近内心的真实与自由。 尽管拒绝了山下的热闹,但那不是孤僻的、封闭的、消极避世地逃避变化,而是对“生命独立与自由的追求”[5]。 此外,作为鄂温克族群最后一位族长的遗孀,“我”的坚守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个族群最后的自然神性与精神光辉。
“我”等人的坚守是一种超越孤独的精神自由,依莲娜的孤独回归则是对现代性的反叛。 迟子建说:“二十一世纪能真正给予我们一些什么? 更高更新的科学技术? 如秋水一般波澜不兴的和平?只有教堂而没有监狱的空间? 人人都成了彬彬有礼、深有教养的文明人? 倘若人类果真发展到这种境界,世界还称其为世界吗?”[3]10现代文明带来了理性、技术、教育的普及等一系列积极变化,然而许多富有生命力与独特个性的文明正在遭遇挤压甚至消逝,人的精神家园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受损。依莲娜是鄂温克民族的第一个大学生,她从小在山下的乌启罗夫读书,毕业后当了一名美术编辑,嫁给了一名工人。 相较于祖辈们物质贫乏的狩猎生活,依莲娜的人生应是充满幸福与安全感的,但她的灵魂却生长在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处,集体记忆将她往驯鹿、流水、星空与月亮处拉扯,现代生活的喧嚣与便利又将她唤回山下,这使她的心理发生了某种分裂。 在山上才住上一段时间她便感到寂寞,没过多久就回归城市,却又觉得“城市里到处是人流,到处是房屋,到处是车辆,到处是灰尘,实在无聊”[4]242-243。 在城里,她丧失了弗洛姆所说的伊甸乐园,失去了与自然的相依和灵魂的自由,成了永恒的孤独流浪者。 她想回归自然同祖辈一样生活亦不再可能,因为她已从原始状态走出,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她不可能再完完全全回到过去。 在城市的束缚与山里的自由间她痛苦挣扎,二者之间她终究厌倦了城市,辞职回到山里画完氏族的最后一场萨满仪式后,带着画笔伴着贝尔茨河水走向另一个世界。 与“我”不同,她的孤独是一种漂泊无依,找不到精神归属的存在的荒诞感。 于她而言,死亡是对孤独的最好摆脱和自由的最后去处。 作者将依莲娜的死亡描绘得诗情画意,出于反叛现代发展观蕴含的毁坏人类家园的力量,迟子建对为捍卫心灵自由而死的伊莲娜是充分同情与赞扬的。
“我”与伊莲娜、安草儿等人或以生命捍卫自由,或以孤独捍卫自我。 他们的坚守是对原始信仰,精神自由、自然家园和原始生命状态的坚守,是对淳朴、简单、真实的向往。 他们的灵魂是宁静而孤独的,这种“孤独并非消极地无所依傍,而是指人彻底的自由——没有什么决定论”[6]。 他们保持人格独立,不求功名利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这种孤独是达观自由,高标己见的,同时也反映了狩猎民族对现代城市与时代变迁的不适。
二、性与食:原始生命力的表征
性与食是日常的,生活的,充满人间烟火味的。但在迟子建充满灵性的笔调下却变得富有生机与诗意,同日月星辰,山河大海互融互生。 郁达夫说:“种种情欲之中,最强有力,直接动摇我们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 诸本能之中,对我们的生命最危险而同时又最重要的,是性本能。”[7]迟子建笔下的性描写不追求露骨大胆的性特征或动作,而是一种充满隐喻色彩的诗意抒发,用艺术的审美笔触对性爱的过程进行朦胧地描绘,呈现出水中赏月的含蓄委婉之美。
《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写道:“希楞柱里也有风声,风中夹杂着父亲的喘息和母亲的呢喃,这种特别的风声是母亲达玛拉和父亲林克制造的。”[4]7“风声”来自大自然的空旷悠然,作者将它隐喻为性爱过程中发出的喘息声是充满深刻含义的,即达玛拉与尼克的交融是人与大自然交融的隐喻,释放激情与血液的时刻人与自然是同一的。 新生命的诞生正是在大自然的风声与人造的风声中得以延续,繁衍。 鄂温克民族生活在边地,广博的天地自然赋予他们充沛自然,丰富细腻的情感底色,敢爱敢恨的性格彰显了其生命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达玛拉在林克死后不因畏惧世俗的眼光,丝毫不掩饰对爱的渴望与需求,嫁给了另一个部族的酋长瓦罗加,婚后他们在希楞柱的夜空制造“风声”:“我和瓦罗加诗那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就像水与鱼的结合,花朵与雨露的结合,清风与鸟语的结合,月亮与银河的结合”[4]167。 灵与肉完美融合,这是力与美的抒发,在性爱的张力中人回到了生命最真的原初状态。 描写鲁尼与妮浩、维克特与柳莎、达西与杰芙琳娜结合时的笔调也同样深情流露,诗意盎然。 如老伦斯所言,在男女关系中,纯粹的精神或者纯粹的肉体的结合都是病态的,有缺陷的,只有将两者结合才会带来生机与希望。 迟子建对性的描写并非为迎合世俗心理有意为之,她的出发点不在于寻求肉欲挑拨或者感官刺激,而是在探寻人的自然天性。 “艺术无性则干枯”,贯穿《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风声”使得小说色调饱满丰盈,每一次的“风声”都是人之灵魂在往自然和生命之道回归。
迟子建笔下的北国风土灵动温暖,人情纯真美好。 不过她也写生的凋敝,破败与人性的丑陋,如懒惰,贪婪,冷漠。 也正因为如此,其笔下的文学世界才更加丰富,完整。 性爱在达玛拉等人身上皆是爱,但在依芙琳与坤德那里则变成了恨。 依芙琳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最复杂也最鲜明的女性形象,她有着刚烈的反叛性格,得知坤德与她结婚前曾喜欢过一个蒙古族姑娘后,一直不愿与他同床,她反感儿子金得与父亲一样萎靡不振,不顾金得反对为他娶了歪嘴姑娘,金得为此自杀。 从此,夜晚的希楞柱里常常传来依芙琳的叫声:“坤德没有讲话,但我听见了他沉重而急促的喘息和一种鞭挞人的风声,他就好像在对伊芙琳‘哒哒哒’地发射着子弹。”[4]129坤德和伊芙琳之间的性关系源于责备、恨、报复与惩罚。 一股浓厚的仇恨气息将他们笼罩,带着仇恨情绪的性爱于读者接受而言是残忍的,性的生机在他们身上不再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但却是深刻的,因为“性描写既然是文学作品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就必须服从于艺术整体的辩证法和谐地交织在故事的叙述、情节的发展之中为人性的开掘、心理的刻画、性格的塑造和主体表现服务”[8]。作者创造伊芙琳这个角色正是服从于艺术整体的辩证法,充实人物形象及其心理,揭露人性的不同面和人物心灵深处的波涛汹涌。 伊芙琳从拒绝“性”到被迫接受之间呈现了生命的悲、喜、爱、恨等不同的维度,从而演绎因强烈的情感渗透而生成的生命意识和审美意义。
食物是生命存在的最基本需求。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民族在同恶劣环境的搏斗中获取食物的行为表露了人对食物的深切热爱,但迟子建刻画鄂温克人的食物欲望并非仅仅表达一种世俗化的物质性生活观念,她以神秘的笔调再现了鄂温克民族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形成的庄严神圣的狩猎文化,且“食”的背后蕴含着他们艰难困苦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境遇。 “我”的父亲林克是氏族打猎好手,在捕获堪达罕的时候林克像个功臣似的春风得意,而氏族的其他人则兴致勃勃地集体去驮运猎物,晒肉条。 食物的来之不易令他们格外喜悦和珍惜,用猎物维持生活但不为战胜它们而感到优越,出于万物有灵的生命观念,他们对猎物的牺牲充满敬畏与感激,因而在“吃”的隆重中赋予猎物充分的仪式与祭奠。 饥饿贫穷,生存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人对生命的认识和体验会更加深刻,人之本性亦最易暴露。对待食物的态度映射了鄂温克人勤劳、踏实,善良的生命品性。 老达西求孙子不得而养了一只老鹰将其作为情感的依托。 那时正值驯鹿遭上黄尘雪一只只死去,氏族人心惶惶,食物尤显可贵。 达西的善良与对动物的尊重即在此时跃然纸上,为了让老鹰吃饱,达西拒绝食物,把自己省下的都给了老鹰。 老鹰也懂得达西的牺牲,叼回一只山鸡送到达西面前。 那晚,吃着山鸡的达西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在这里,食物不仅仅停留在生存与温饱的物质层面,它更多的是心理和情感的,是人与动物之间情感互通,共生共存的和谐,一种牺牲自我成全他人与生命皆可贵的思想呈现,流露出善良,淳朴的生命色彩。
三、诞生与死亡:互渗互照的生命张力
生与死互渗互照,生向着死,死来于生。 《额尔古纳河右岸》呈现了“生死互渗”的生命张力,“死”并非作为生的对立面存在,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作为另一种新生。 鄂温克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生,于神性世界中豁达看待死亡,他们渴望孕育生命,并具备旺盛的生殖力,把“诞生”看作生存与血脉的延续,但生的每一天也都在朝死亡迈进。 迟子建以温情怜悯的口吻书写了作为生命两端的生与死,透露出别样的人性美与生命美。
贯穿《额尔古纳河右岸》始终的是一层浓浓的死亡气息,人们借死亡体悟生的意义和价值。 迟子建善于刻画充满神性色彩的死亡事件,其背后暗含着博爱、济世,关怀万物的深层意蕴。 鄂温克人的死亡意识首先表现为“以死换生”,鄂温克人可为保护驯鹿而不惜生命,老达西从狼口中救下了驯鹿而牺牲了自己的腿。 列娜在病危之际能够被救活,是因为有一只驯鹿崽代替了她死去。 人与驯鹿生死相依,互敬互爱。 在人性与神性交相辉映的世界里,淡然、乐观、平静,充满希望的死亡观念指引鄂温克萨满义无反顾牺牲自己的骨肉去救赎他人。妮浩作为萨满拥有神秘莫测的力量,她每一次跳神救活别人都是以牺牲自己的孩子为代价,第一个孩子果格力代替何宝林的孩子死去,第二个孩子交库拖坎代替马粪包死去,第三个孩子耶尔尼斯涅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尼浩。 救人之前明知自己的孩子会死去,却不忍见死不救,这种舍生忘死的“英雄”色彩代替了死亡的悲痛,让死亡具有一股诗意的浪漫色彩,蕴含温暖的审美意义和道德意义。 这样的生死替换观淡化了人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死亡本身的悲剧性。 尽管“我”以沧桑的口吻诉说死亡的阴霾,但作者笔尖流露的对生死的悲悯情怀使得死亡氛围染上一层救赎众生,万物有灵的盎然诗意。
除“以死换生”外,《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还通过众多的意外死亡情节来反映和关照生命,阐释一个族群的生存困境。 林克死于雷电,达西死于狼口,列娜死于寒冷、就连枪法极好瓦罗加也死于熊掌之下。 死亡的阴影始终伴随着鄂温克人,“因为每个人都会死。 每个人的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却是各有各的走法”[4]222。 鄂温克人对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充满敬畏,但在生命的有限性与脆弱性面前,他们难免遭受大自然无情的伤害与剥夺。 不过,他们并不因此悲观绝望。 乌力楞族长去世的那一天本该将维克特的婚礼推迟,“但我想生命就是这样,有出生就有死亡,有忧愁就有喜悦,有婚礼也有葬礼,不该有那么多的忌讳”[4]174。 因此在酋长葬礼当天依然举行了维克特和柳莎的婚礼。 对死亡的理智认识让鄂温克民族在苦难中追求快乐,在无情的大自然面前勇敢生存,强大的生存意志激励他们走出死亡的悲伤,苦难的现实生存条件导致的死亡早已成为常态,死亡意识已成为一种原始的直接经验,从而经验教人“充分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性和有死性,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积极筹划并从容度过人生”[9]。
生儿育女是种族延续的必然途径。 生命的诞生,是个体生命体验和香火延续的基本条件。 迟子建的笔下诞生同死亡一样频繁,《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鲁尼与妮浩在孩子们一个个死去后擦拭悲伤,继而努力孕育新生命,拉吉米捡回被遗弃在马圈里的孩子并对之百般呵护,马伊堪在决定结束生命前为养父孕育了新的生命等,整个乌力楞都永不停止孕育繁殖是鄂温克民族热爱生命,渴望生存和壮大人丁的心理映现。 玛利亚与杰芙琳娜为得子去拜玛鲁神,祈求神赐子则将本为自然现象的生育神化,展露出一个原始民族的生殖崇拜现象,人们迫切希望得到神的保佑以绵延子嗣。 繁衍是生命生生不息的延续,孕育新生在某种层面上亦是对死去的生命的弥补,老达西死后不久玛利亚竟有了怀孕迹象,“他们恰恰觉得是达西的灵魂保佑他们有了孩子”[4]52。 施韦泽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秘密,每个生命都有价值”[10]。 小说中作者除描绘人的生命外,也刻画驯鹿的孕育,诞生和成长。 鄂温克人为找驯鹿的优良配种不惜跋山涉水,为鹿仔的诞生欣喜不已。 在他们看来一切生命平等,充分肯定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权利。 他们对待生死的态度彰显了舍身忘我、救赎众生、豁达乐观,万物平等和诗意栖居的人性之美,也展露了作者独特的生命价值判断。
四、结语
综上,《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孤独与自由是迟子建生命书写的底色,在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鄂温克民族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过程中“我”与伊莲娜等人对自然家园的坚守与回归具有一定的反现代性色彩,他们的孤独是一种保持独立人格,捍卫自由与真实的生命品质。 其次,生命书写表现为性与食的原始生命力的表征,鄂温克民对动物的捕猎是不得已的生存需求,对捕获的动物要举行仪式示以歉意,展现出尊重和珍爱生命的善良品格。 另外,他们敢爱敢恨,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张扬性力,散发出蓬勃的原始生命力量。 最后,鄂温克民族用“以死换生”的自我牺牲来拯救他人的生命,于艰难的生存环境中繁衍孕育,以博爱情怀和别样的生死观念淡化了死亡悲剧,彰显出积极乐观的生命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