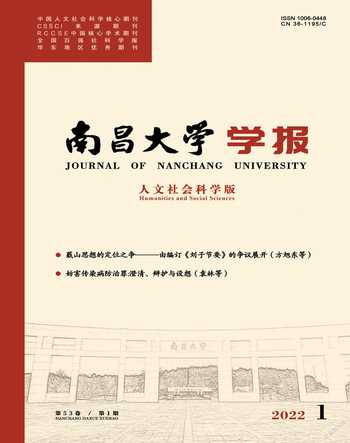技术媒体、具身认知与万物闪耀
摘 要:德雷福斯從技术现象学视角对技术媒体的迭代发展进行了哲学反思,形成了面向未来智能技术的媒体理论,这使他成为人工智能、互联网、认知科学和现象学等领域最具经典性的学者之一。在德雷福斯看来,如果脱离了身体的在世存在,人们将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然而,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技术正在使人逐渐遗忘身体的重要性,消解人们对具身智能、情感互动、身体技能、信责伦理及聚焦性公共生活的正确认知和热情。一旦人们痴迷于离身认知、远程具现和虚拟交流的幻想,不仅无法在智能技术的开发方面获得成功,而且还会由于现实与生活的虚无化而导致孤独、抑郁甚至自杀。因此,他认为在技术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应该平衡技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通过恢复面对面的交流、重视技能学习并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等“聚焦性”身体实践,使万物由此而重新闪耀,使生活充满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技术媒体;具身认知;万物闪耀;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22)01-0076-11
21世纪是技术媒体兴盛的时代,蓬勃发展的数字媒体技术不仅改变了传统媒体形成的文化,也给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带来了认知新媒体文化及其现象的挑战。数字化、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是新兴媒体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它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从媒介考古的视角看,这些新媒体技术的出现都有其历史时间上的纵深,对于这些新媒体现象的研究也早在它们初露端倪之时就已经引起了技术思想家们的重视。享有盛誉的技术现象学家德雷福斯正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媒体哲学家,他是人工智能、具身认知、远程具现以及互联网批评领域最早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雷福斯是典型的“未来”型媒体研究者,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所专注的研究对象是“未来”的科技媒体,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采用的现象学立场及其方法,为人们开启了思考“未来”技术媒体的方向。
对于21世纪20年代的媒体研究者来说,德雷福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专注的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网络传播、远程具现等议题,正强有力地变革传统的媒体研究的知识地图,并日益成为新的媒体议题的中心。尽管他在87岁高龄时离开了人世(2017年),然而传媒界对于他的学术遗产价值的认知似乎才刚刚开始,德雷福斯已然为我们提供了生存论现象学视域下技术媒体研究的成功范例,并由此发展了技术现象学研究的新路径,深入发掘他所遗留的这些学术遗产,无疑将会极大地助益我们对新的技术媒体的思考与研究。
一、德雷福斯的主要成就及其现象学基础
回顾德雷福斯漫长的学术生涯,他除了将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福柯等欧洲经典思想家引介到美国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以这些思想为基础,发展出对当代科技媒体的广泛分析与诠释。他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使其成为当代人工智能哲学、网络与虚拟现实、认知科学等领域最重要开拓者之一,2001年他因杰出的学术贡献及影响而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一)智能科学与网络媒体现象学的开拓者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施拉姆和贝雷尔森还在为传播领域的生死存亡展开激烈辩论时,德雷福斯就已经开始着手评估最早的一批人工智能倡导者们关于机器智能的设计理念与实现路径了。在标志着人工智能领域正式诞生的“达特茅斯”会议(1956年)后不久,德雷福斯就从他供职于兰德公司的胞弟那里了解了“人工智能之父”赫伯特·西蒙等人的人工智能方案,他“研究了西蒙等人的方法,他所感兴趣的哲学使他相信,如果以他们的方式来做的话,人工智能将会失败”[1](P104)。
20世纪60年代初期,德雷福斯正式接受兰德公司的委托对艾伦·纽厄尔和赫伯特·西蒙等人的符号主义人工智能研究计划作出评估。在随后提交并出版的评估报告《炼金术与人工智能》(1965)中,德雷福斯对早期人工智能的符号主义路径提出了措辞严峻的批评,该报告几乎摧毁了兰德公司正在进行中的AI研究的基础。1972年,德雷福斯在大量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人工智能哲学领域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系统地批判了早期人工智能中的符号主义方案,并阐述了存在论现象学路径下的智能观念,强调身体机能、整体性情境等因素对于智能涌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该著作在1979年和1992年发行新版时,德雷福斯根据人工智能最新的发展趋势撰写了新的序言。
人工智能的研究孕育了与此相关的认知科学和哲学,作为最早的人工智能哲学家之一,德雷福斯在1986年与其胞弟斯图亚特·德雷福斯合作出版了《心智胜于机器》一书,较早地阐述了他们关于具身心智和技能学习的学说。也正是在这一年,来自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领域的F·瓦雷拉、E·汤普森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走到一起开展合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在1991年出版,系统地论述了身体与心智之间的关系,为认知神经现象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这本奠基性著作中,作者梳理了认知科学研究的学术谱系,他们认为,“在北美,休伯特·德雷福斯长久以来一直是认知科学视野中的海德格尔的牛虻”[2](P12)。
当互联网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迎来快速发展期时,德雷福斯又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技术事件的重要性,并从存在论现象学的视角,对方兴未艾的互联网传播现象发表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从网络搜索到网络政治,再到远程具现和网络教育,以及网络信责和虚拟世界中的“第二人生”,德雷福斯围绕互联网时代广泛的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评论,这些见解后来也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文献。
(二)媒体研究的身体现象学基础
与人们通常所见的媒体理论家不同,德雷福斯首先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他在存在论现象学方面的深厚积淀为他的技术哲学思考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在此基础之上,他将现象学引入到工程技术领域,并参与到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
受海德格尔关于存在意义问题的引导,德雷福斯首先在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上强调存在论的区分,也即将“存在”与“存在者”两种思想范型加以区分。从整体论和生存论的视角上关注此在与其环境及其所处世界之间的缘构发生关系。这在哲学层面就已经决定了他在研究有关技术和媒介现象时都必须将它们放在由人与物共同构建的整体性生存境域之中,并在此一整体性的境域之中追问存在的意义。
在此一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范式之下研究当代技术媒体现象,必然需要将“身体—心智”(具身心智)这一基础作为研究的重心和焦点,因为唯有身体才是人与外界产生交互作用的基础媒介,也是智能涌现的前提条件与场所。“具身(身体—心智)”这个词本身内在地包含了对物与人之间的缘构发生关系的指涉,这使得德雷福斯很自然地援引梅洛—庞蒂有关身体—知觉现象学的思想作为其技术研究的依据。在他看来,身体不仅是技术媒体拓殖其市场的牧场,也是理解人的存在意义这一终极问题的关键。
通过身体这一媒介,人工智能的设计与制造、技能学习与训练、网络远程具现以及互联网交流等问题都将获得新的研究视角。身体维度的引入,使得人们不再忽略认知和智能的生物物质基础,而是注意到肉体与心灵、感知与意识之间彼此互涉的復杂关系。这为学术界摧毁长期统治西方思想界的笛卡尔理性主义传统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具体支撑点。可以说,身体及其知觉的激活,开启了技术阐释的新视野,德雷福斯由此切入人工智能、认知科学与互联网传播等前沿技术领域,不仅成为这些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学者,并且他的深刻见解也成为这些领域中经常被回顾的经典论述。
二、无身体的智能如何可能?德雷福斯论人工智能的极限
人工智能哲学是德雷福斯影响最大的研究领域,几乎所有该领域的经典教材与文献中,都会频繁地提及、介绍或讨论他所提出的观点。这种影响力不仅源于他是最早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基于身体现象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的极限”提出了最强有力的质疑:对于机器而言,没有身体的智能如何可能呢?具体而言,“如果身体真的是智能行为不可缺少的条件,那么我们所想到的问题就是身体能否用启发程序数字计算机模拟出来。如果不能,人工智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3](P243)。
(一)早期人工智能的形而上学假设及其失败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其正式诞生的标志是1956年夏季在美国召开的达特茅斯会议,而有关机器智能的早期思想则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自从笛卡尔开创了近代理性主义以来,包括莱布尼茨、拉美特利、拉普拉斯、布尔、威廉·詹姆斯、冯·诺依曼、图灵等在内的思想家,都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事实上,人工智能是西方理性形而上学思维漫长演化历史的结果[4](P122),也是近代“数学筹划”[5](P84)的产物。根据这种形而上学和数学筹划的观点,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形式化和可计算的,并且世界的本质乃是原子的规则组合。因此,只要将人类智能以形式化和数学化的方式加以把握,并根据规则对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进行拆解与再造,就可以以机械物理的方式模拟出人类智能,并且这种智能可以全面地模拟人类智能。“这种观点是由两股巨大的水流汇合而成的一股浪潮。这两股巨大的水流中,一是柏拉图把全部推理都规约成明晰的规则,把世界规约为不需解释地运用这些规则的原子事实;二是发明了数字计算机,一种通用信息加工装置,它可按明晰的规则进行计算,并把数据当成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原子元素而加以接受。”[3](P239)
早期人工智能的倡导者们对此深信不疑。为此,他们在人工智能的哲学层面分别从生物学、心理学、认识论与本体论四个领域做出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假想,这些假设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认为,人一定是一种可按规则对取原子事实形式的数据做计算的装置。”[3](P239)然而,德雷福斯早在1965年提交给兰德公司的报告中就对这种理性形而上学的人工智能方案加以严厉批判,并在10年后出版的《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中,对个中缘由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证。
德雷福斯有关早期人工智能注定失败的预言得到了历史的验证。赫伯特·西蒙在1958年曾乐观地预测,计算机在10年内会成为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但这预言的实现用了40年,而不是10年。更严重的是,当处理更广泛、更复杂的问题时,几乎所有的早期AI系统都悲惨地败下阵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人工智能”[6] (P132)。失败的原因不是技术上不够先进,或是“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而是它的整个概念框架”[3] (P240)。因为他们“恪守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的传统,这种传统始终把躯体看作是智能和理性的多余之物,而不是智能和理性的必要之物”[3] (P243)。人们应该尝试从整体设计上考虑理解人类智能的其他路径,将身体的维度纳入智能理解的视域中来。
(二)具身的智能: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本质差别
对于存在论的现象学家而言,人类智能的本质并不能完全以符号化、形式化及其数学计算来加以模拟。因为人类智能的基础在于身体与世界之间的交互性实践关系。虽然计算机所擅长的形式规则和数据计算属于人类智能中的高级智能,但这种智能的基础却奠基于人的身体机能,更确切地说,奠基于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的“在世界之中存在”[7](P71)。换句话说,唯有当身体与它所处的周边环境处于空间性交互关系之中;同时,身体处于它自身及其环境的时间性历史关系之中时,智能才有可能涌现出来。正如德雷福斯所言:“把人同机器(不管它建造得多么巧妙)区别开来的,不是一个独立的、周全的、非物质的灵魂,而是一个复杂的,处于局势中的,物质的躯体。给人工智能招致麻烦最多的,正是智能行为的躯体方面。”[3](P244)身体在智能涌现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很多作用,并不完全能够被机器所模拟,因为两者的工作方式是全然不同的。
一方面,人类智能在思考某个事物的意义时,总是需要从整体上对场景意义加以宏观把握,而这种整体性场景意义的全局把握能力是不能被形式化表达和把握的。这个整体性的全局把握涉及人的内在意识背景(内景)以及人们所处的外部环境(外景),“内景”有点类似人们称为“前理解结构”“潜意识”或者“记忆”等的机制,它构成人类思维的精神背景,人们对这些内景的认知尚处于初级阶段,它们是任何机器都不具备的人类生物学特征。另一方面,人类对外部事物的感知,也总是需要在不确定的场景/背景(外景)之中进行,正是对整个“外景”的全面感知和了解,组织并引导我们进行细节的感知。“例如,在识别一首乐曲时,音符是被感知为这首乐曲的一部分才获得它们的值的,而不是按照辨别出来的独立音符识别乐曲。……同样一层模模糊糊的东西,当我以为面前是一个蜡制苹果(身处玩具店情境),我会把它看作是灰尘;当我认为看到的是一个新鲜的苹果时(身处水果店情境),它就成了水气。各细节的意义以及它们的样子确实是由我们对整体的感知来确定的。”[3](P246)由于计算机没有身体,因此无法通过身体记忆存储经验,以形成“内景”,作为其智能活动的精神基础;计算机也不能与自己所处的空间环境构成交织与融合“外景”关系,因此机器人也不能像人一样灵活自如地与所处环境之间形成交互性关系。计算机只能通过“查找由可分离的、中性的、具体的特征构成表”[3](P245),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计算来工作,也即按照特定的规则,对明晰化的信息从细节到整体进行机械加工。因此,人和机器的区别在于,人对于部分的理解和解释取决于身体所处的整体空间,从整体的角度定义什么是部分(相对位置)。计算机没有整体把握能力,没有相对位置,元素就只能依靠独立的定义来进行逻辑标示与计算。
其次,人类的需要、兴趣与目标不可形式化。人作为世界上唯一能够领悟自身存在状态的存在者,与世界相互交往而形成一个“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共在体。人类所有的实践任务均产生于与世界的交互性关系中,人类并不是与世界截然区分的,相反人与世界之间是相互镶嵌、相互作用、相互成就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通过身体机能来加以协调。人的身体使我们能在视觉、味觉和触觉协同工作的情形下探查物体,并且身体感知的同一性完全不同于机器感知的多信道叠加效应,它不能被加以彻底地形式化分析,也不需要不停地检测和确认细节,这种探查具有连续性、模糊性、灵活性特征,并且仅仅服务于我们“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生存需求、个人兴趣或价值目标。
奠基于身体的原初功能与作用而进行的整体化信息加工,以及无法形式化把握的人类情感性经验基础,说明了高阶的、确定性的、逻辑的和独立形式的智能必须从在原初的身体与世界之间的交互关系中衍生出来,而不是相反。对于计算机而言,模拟人类逻辑运算、抽象思维等高阶的理性智能并非难事,但如果想要模拟人类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自如地快速行走,或者通过面部表情的微妙变化来传达复杂的意义就显得非常困难。因为这些较为初级的智能行为与身体在进化中所形成的自动反应能力有关,正因为身体具有无法被机器模拟的不可形式化的机能,所以缺乏身体维度的人工智能想要实现全面模拟人类智能的目标必然会招致失败。
三、虚拟生活与具身离场:反思互联网传播的“神话”
如同20世纪60年代敏锐地意识到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性一样,当互联网浪潮在美国初露端倪时,德雷福斯便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前沿领域,并在其中继续拓展技术媒介的现象学理论。
与人工智能跌宕起伏的技术发展进程不同,互联网的发展几乎是一路高歌猛进,很快就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互联网技术的神奇效应使得人们对它充满期待,部分较为乐观的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帮助人们摆脱了身体的局限性,使得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遨游于网络的虚拟空间之中,开启所谓“第二人生”。另一些人则认为互联网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实现,因为网络公共领域看起来类似于古希腊时代的“阿哥拉广场”,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讨论公共事物,实践他们的民主政治理想。还有一些人认为人们可以借助互联网开展以远程具现为基础的教育,这对于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从理论上讲,网络公开课程对全社会的每一位学习者而言都是开放的。
这些模糊的乐观前景浮现于人们的脑海中,使得他们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了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然而,正如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所展示的那样,人们对于互联网的预期过于乐观,互联网确实重构了人们的工作、商业、学习、教育等行为模式,但它所带来的并不全是好处,也造成了诸多预想不到的棘手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互联网用离身的虚拟存在替代了具身的现实存在,这使得人们与自己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及社会相脱节,世界万物由于这种脱节而虚无化,人们的生活也因此失去了意义。
(一)互联网技术解决方案的身体维度:人类主观需求与谷歌搜索技术
在近代以来的科学观念中,科技以其绝对的客观性和离身性,试图克服人类在身体上存在的种种缺陷,当代互联网技术对虚拟世界的构造将这一观念发展到了极致,按照那些“最热爱网络的人的设想,网络的长期目标是让我们超越生理上的极限”[8](P4)。然而,科技发展史上的无数事实表明,如果完全超越身体维度的考量,科技进步便难以取得真正的成功,早期人工智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其技术方案排斥了智能的具身性。同样,互联网技术中的很多难题如果缺乏身体维度的引入,将长期得不到解决。
比如在互联网搜索问题上,早期的技术方案仅仅着眼于统计学上的概率计算视角,将蕴含人类经验意义的“信息检索”等同于“追踪无意义数据之间统计关系”的“数据挖掘”和“数据检索”[8](P17),这导致人类主观意义需求与无意义数据检索结果之间的严重脱节。然而“成功的信息检索是大多数网络用户的首要目标”[8](P12),有意义的信息与无意义的数据之间的脱节,曾经一度严重影响到互联网的发展。因为随着用户的增加,网络中的数据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如果不能快速精准地搜索到用户所需的信息,那么人们将陷入杂乱无章的数据海洋之中。
如果不能在人类需求与网络数据检索之间建立起联系,那么海量的数据将成为网络使用者的噩梦,因为要在海量的数据中寻找人们所需要的那一条信息,无疑就是在大海里捞针。为提升网络中信息搜索的质量,人工智能先驱特里·温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指导的博士生拉里·佩奇(Larry Page)开发出允许人们基于无意义的超链接进行搜索的革命性搜索引擎谷歌(Google)。温诺格拉德明白纯粹统计方法的局限与人工智能失败的原因,他将海德格尔哲学引入到计算机课程中,以便寻求人工智能新的解决方案。温诺格拉德为拉里·佩奇打开了一扇门,让他将人类的身体维度与客观数据的统计结合在一起,开发出全球性的网页评级系统PageRank,以挖掘人们搜索的特定兴趣领域的网页的“重要性”,这项技术构成了谷歌成功的基础。
谷歌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使用从人们的搜索中捕捉到的关于结果的重要性来实现语法搜索,不需要一個能够理解搜索内容的搜索算法。如同他们所指出的那样:网页的重要性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属性,他依赖于读者的兴趣、知识和态度。但网页的相对重要性则是一种称得上客观的东西……PageRank是一种对网页进行客观而机械地评级的方法,它能够有效地评价人们对网页投入的兴趣和注意力”[8] (P26-27)。可见,PageRank以链接结构中页面A向页面B的跳转作为一次“重要性”的投票,通过投票分量的累计评价人们对网页所投入的兴趣与注意力,并以此作为谷歌搜索中对页面相对重要性排序的依据。当然,作为一项精确的技术,“Google还会同时检查网页内容的数十种属性(甚至包括链接到该网页的其他网页的重要性),以决定一个网页是否切合一个搜索请求”[8](P28)。可见,正是这种将人类主观评价和需求整合到网络数据统计中加以考量的技术,使得搜索引擎展现了新的前景。因此,技术媒体的发展及其应用,并非完全与身体维度无关,也并不是需要逃逸人类不完美的身体机能,与此相反,新媒体技术一方面致力于为人们构建一个摆脱了身体束缚的虚拟世界;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根植于人类原初身体存在的需求与限制,这两种趋向形成了新媒体现象的内在张力,使得新媒体在引领人们超越肉身限制的时候,又不得不处处受制于它的存在。
(二)匿名公众与信责缺失:离身交流与电子阿哥拉广场的幻灭
在转而考察互联网政治现象的时候,德雷福斯指出,由于虚拟的政治讨论与交流都是在身体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人们发展了新的政治行为方式,其特点不仅是政治观念自由而充分的表达,而且伴随着信用缺失、责任规避以及行动乏力等问题,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足以毁灭人们对网络民主所寄予的幻想。
德雷福斯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基于网络政治和网络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易被察觉的问题:作为传统政治实践基础的社会信念和责任在网络时代已受到严重冲击。网络交流的离身性与雅典民主中面对面的交流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离身交流抹平了现实政治中存在的身份区隔,网络匿名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依赖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及社会地位,不论你在现实生活中是身居高位的官员,还是身处底层的百姓,一律都成为无差别、非具身的“网民”,因此在网络离身且匿名的状态下,人们不必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世界中,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差异也是被抹平的,尽管人们会为了不同的观点而发生争吵,甚至相互谩骂攻击,但几乎所有的观点都具有平等的地位。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网络交流的非具身性所导致的。身处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由于处于社会网络结构的不同位置,会根据自身位置表达与之相匹配的思想与价值观。然而,在离身的网络世界中,身体缺席为人们随心所欲地扮演不同的虚拟角色提供了方便,在这种情况下,网民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表达很多时候或许仅仅是一种表演,与他的实际身份和社会地位无关。
由于人们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发表言论,因此每个人都会对感兴趣的公众事件评头论足,却不需要亲自参与其中并调查真相。事实上,亲身参与和把握真相在很多情况下对网络评论来说都不是首要的,而宣泄情绪和满足自己的表达欲望反倒成为网络言论的首要动机。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所有的网络政治行为都止步于“嘴炮”,既没有人对所涉及的议题展开调查研究、设计对策,也没有人按照他们在网络中宣扬的观点行事。这就形成了互联网政治的奇特现象,很多时候网络争议的热烈程度与现实行动的苍白无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折射出具身政治实践和网络政治行为之间的反差。
由此,德雷福斯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网络政治面相:“来自全世界乱出主意的匿名者,在电子世界无须承担风险地聚在一起发言和相互辩驳。作为灭绝的公共领域的延续,电子阿哥拉广场将会成为真正的政治社区的坟墓——问题并不在于莱茵戈德的‘电子阿哥拉广场’太过于乌托邦;问题在于网络根本不是阿哥拉广场,而只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匿名者们聚集的一个莫名奇妙的空间。正因如此,它是危险的反乌托邦。”[8](P181)
(三)身体“意向弧”与情感卷入:网络教学活动的局限性
互联网中另一项引人注目的应用是远程教育与远程学习,人们期待网络教育可以克服线下教育的弱点,弥补线下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知识鸿沟。但直到2020年爆发全球新冠疫情之前,人们有关网络教育与学习的设想都未能得到充分验证。疫情的爆发为人们提供了一個重新认识网络教育的契机,也为人们认知身体在学习过程的作用提供了理想的社会实验场景。人们注意到,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学校停止了线下教学,但学生们依然可以通过线上渠道继续他们的学业,并未因疫情的困难而耽误学业;然而,长时间的居家线上教学让大多数教师和学生备受煎熬,因为虽然线上学习比线下学习更加简便易行,但这种教学方式的效果并不理想,教师对着屏幕教学的热情不高,学生则更是难以维系在屏幕前学习的兴趣。师生之间的隔屏交流将网络教学的弊端显露无遗,因此,等不到疫情彻底消除,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早已盼望着能够早日重启面对面的线下教育,回归到正常的课堂教学。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不愿采取远程教育的方式进行教学呢?同样的教学内容,为什么在网络上的教学效果不如线下教学的效果?德雷福斯早在网络教学刚刚兴起时就对此进行了深度考察。在他看来,学习是一种具身性的认知行为,在学习的过程中,身体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能够在现场参与的情况下通过身体位置的移动,将自己对环境的整体把握调整到最佳状态,这种状态是最有利于信息接收和理解的状态。梅洛—庞蒂将这种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交互性反馈协调能力称为“意向弧”,他指出:“意识的生活——认识的生活,欲望的生活或知觉的生活——是由‘意向弧’支撑的,意向弧在我们周围投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人文环境,我们的物质情境,我们的意识形态情境,我们的精神情境,更确切地说,它使我们置身于所有这些关系中。正是这个意向弧造成了感官的统一性,感官和智力的统一性,感受性和运动机能的统一性。”[9](P181)
意向弧所揭示的身体感知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提示我们,身体与环境之间形成的最佳感知效果,并非单一感知渠道的累加(如媒体视觉与听觉或触觉的叠加)所能模拟的,这也正是为什么远程教育中的场景模拟总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原因。在网络场景中,人们不能通过移动身体而使得屏幕中的画面焦点出现变化,也没办法看到屏幕里周边环境的情况。因此,“我们在远程教学和远程具现中所失去的,便是可以控制自己身体移动以更好地掌握这个世界的可能”[8](P73)。不论屏幕中呈现的画面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只能被动地照单全收,这会严重影响人们对信息接收的状态和效果。在现场教学的过程中,师生在教学情境中形成的身体(包括表情、情绪)互动,构建了整体性场景氛围,会直接影响到知识学习的掌握程度,尤其是与身体技巧密切相关的技能性知识;而那些位于远程教学屏幕前的学生将始终处于场外观众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课堂学习的情境中,从而会错失太多镜头之外的重要信息。
有鉴于此,远程教学的一大局限就在于真实性感知的减弱。互联网无法为人真正提供真实的现场环境,只能通过图像的转播、声音的传递等单线讯息为屏幕前的人展现现场的状况。当然,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未来可以通过增加信息通道,如除视觉、听觉之外,未来技术对嗅觉、触觉的模拟将有效消除网络用户的不真实感,但他们忽略了真实环境中的共享情感(情绪)所带来的影响。海德格尔曾经指出,情感具有一种调谐机制,多数情况下,大部分人都可以通过共享某个情境,来达到与他人情绪上的“调谐”。情绪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受我们的控制,却能够主宰我们的社交行为[8](P146-147)。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学习的过程中,情感代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德雷福斯与其胞弟斯图亚特·德雷福斯将技能学习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新手(novice);高级初学者(advanced beginner);胜任者(competence);熟手(proficiency);专家(expertise)[10](P21),此后,又增加了大师(mastery)及与此相应的“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 阶段[8](P35-49)。
从新手阶段到胜任阶段,学习者主要通过学习与情感无关的概念、规则等形式化知识,并尝试在较为简单的场景中运用这些知识。此时,身体介入对人的学习能力、技能提升的程度影响并不大。但从熟手阶段开始,情感代入的重要性逐渐体现出来,“当且仅当,经验以非理论的方式体知合一地得到积累时,熟练阶段才算是达到了。那时,知觉的反应将替代由推理得出的应对。”[11](P174)不过,熟手虽然能够灵活地运用知识和技能,但当他想要去做自己的一件事情时,还需要根据现场状况仔细思考如何完成。而专家的情况则不同,“专家具备了在众多不同情境中区分出哪些情境需要回应,哪些则需要另一种。对大量的不同情境有了足够的经验后,……就促成了对情境的即时的直觉性反应,这是专家阶段的特征”[11](P174)。相比于专家而言,大师的标志性特征则是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这与大师的身体性存在是密不可分,合二而一的,与此同时,风格的形成也必然是一个转益多师的学习过程;学习者需要综合诸多前辈大师的风格,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整个过程必须在面对面的亲身教授和学习过程中才能完成。因此,“达到大师的程度,似乎是远程学习者力不能及的”[11](P177)。
至于“实践智慧”,那是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它高度依赖身体实践与互动,“以至于不能通过理论来获取或在课堂中来传授。它只是潜移默化地从身体到身体的传递,然而它却又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各种学习只有以它为背景才得以可能。只有通过跟从父母和老师来学习,才能学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实践智慧’”[11](P179)。显然,“实践智慧”超越了形式化的理性知识的学习,如果我们不是从“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具身性生存论视角看待知识和技能学习问题,那么学习就将会止步于“胜任”的阶段。因此,远程学习的热衷者们必须意识到,“只有情感的、代入的、具身的人类才能达到熟练和专家阶段。因而,当教授具体的技能时,老师必须是现实中具体存在的老师,并鼓励学习上的情感代入。此外,通过学徒关系学习需要老师的言传身教;而传承文化的所赋予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我们与长辈共同生活。在此基础上,才如叶芝所说:‘道可行,不可知’”[8](P56)。
四、具身实践与万物闪耀:在新技术时代过有价值的生活
作为存在论现象学家,德雷福斯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精神,对新技术所引发的存在危机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不过,与海德格尔对技术危机所持的悲观绝望的态度不同,尽管德雷福斯严厉地批判了沉醉于技术媒体乌托邦幻想中的那些乐观主义者,并总是以其无可辩驳的思想深度给乐观主义者当头棒喝,但他也承认“悲观主义在今天已经不再适宜”[8](P168)。在德雷福斯看来,学术研究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向人们展现危机,而是要通过对危机的展现提醒人们注意技术所导致的虚无主义陷阱,而要避免落入这些陷阱,人们就需要调节自身对技术的认知,并协调和平衡好技术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
德雷福斯在谈及网络教学时肯定了网络教育的积极一面:尽管线上的网络教育无法与线下的精英教育相媲美,但线下精英教育中非具身性的那些内容,依然可以通过网络课程惠及广大普通民众,“这是因特网最好的一面,它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尽管是非涉身的,但没有它我们连这些也得不到”[8](P174)。这一断言在多年后得到了印证,新冠疫情期间所进行的网络教学尽管效率不高,效果也欠佳,但就其在维持学生学业,使之不至于荒疏方面,无疑具有积极作用。然而,技术的这种积极面只能在我们恰当地掌握了技术生活的辩证法之后才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相应地抵制互联网的负面效应,那么现代技术“最好的一面”也会荡然无存。
(一)具身技艺
现代技术的真正危险,主要在于它削弱了人们的具身实践能力,使得身体与自然万物之间的肉身性关系变得日益微弱,从而导致生活价值和意义的虚无。为此,德雷福斯提醒人们注意网络生活对于人类具身性社会实践的褫夺危险:“使用因特网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文化已经堕落过两次,先是柏拉圖,然后是基督教,让我们试着超越自己脆弱肉体的企图——最终导致了虚无主义。这一次,我们必须抵抗住这种企图,坚守自己的身体。这并非无视自身的局限和脆弱,而是因为没有我们的身体——如尼采所见——我们将什么都不是”[8](P186)。
技术对身体实践的抹除,首先是体现在传统手工技艺的消除上。工业技术文明的一个趋势就在于:尽可能地把一切工作都交给机器完成,从而逐渐减少对身体技能及其实践的依赖。在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模式下,人们似乎只需要掌握简单的操作程序,便可以坐享其成。这种结果看上去确实很美好,然而它却隐含了难以察觉的危险:人们与万物之间建立在身体实践基础之上的传统技艺走向消亡,万物与人之间肉身性的亲密关系由此而变成了出于控制或牟利目的而采取的主客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这使得人们曾经拥有的那些熠熠生辉的神奇技艺,以及由此生产的精美手工艺品,如今全都黯然无光。
与机器对待万物的方式不同,对于传统的木匠而言,“木材远不是面对机器的一个猎物、一个无助的受害者。或者可以说,木材会将自身微妙的品质传递给人,而木工也知道怎样适应它——对待一块木料,如同对待一个彼此理解的朋友,他们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也许更重要的,每种境况的独特性赋予手艺一种神性的性质。……木工与他所用的木料之间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木料微妙的品质期待培育与呵护。这种与木料的亲近感在木工身上产生了一种呵护和尊重的感情”[12](P203)。沉迷于机械生产效率和标准化优势的人们,可能会认为机器制造的木件更加美观,“但木工师傅能够看出,这些轮子是完全不动脑子做出来的。然而,比质量低劣更糟糕的是,能够识别特质的技能消失了。我们失去了手艺知识,世界则日趋失去价值的判断力。……在一种无需技能的生活中得到的危险,就是拥抱当代虚无主义的、平淡无奇的世界”[12](P207)。
面对这种危险的恰当反应不是去反对技术本身,而是在接受这种个体的技术进步的同时,保持能够抵制技术生活方式的poietic实践。这里所谓“poietic”,在古希腊世界中含有“制造”和“实践”的意思,属于具身性“技艺”(téchne)的范畴[13](P32),用以意指“有助于培植和生长的实践……在一些场合,这种poietic 风格表现在工匠巧夺天工的技能中。这是文化中一种古老的实践”[12](P200)。在这样的实践中,人们能够从劳动中培育出对万物喜爱与尊敬的情感,这样的尊敬并不只是“拿在手里,满口称赞,而是呵护它,让其获得最佳的用途——让它闪耀出价值的光芒”[12](P207)。
(二)聚焦实践
另一种与此密切联系的技术危险,则是人们面对面进行社会交际和公共生活的技艺也在逐渐削弱。技术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也将他们变成了足不出户的宅男宅女。人们减少了外出购物和交际的传统生活方式,转而回到家中沉浸于网络和游戏中的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成为绝对的中心和命运的主宰,完全不用担忧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麻烦与危险;即便遭遇失败或者不幸,虚拟世界也会提供无数次复活重来的机会。
在不断地探索、试错与重复后,最终的胜利者必定属于虚拟世界中的游戏者,人们由此而成为无所不能的胜利者,甚至获得了上帝一般的视角和位置。然而这种极端的主体性幻觉恰好就是虚无主义的典型症候,它会使人们妄图“凭一己之力无中生有地创造意义”[12](P198),并由此而消除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意愿,消除他们发展人际交往技能的意愿;技术社会的生活由此也变得日益“孤岛化”,并伴随着人们普遍存在的焦虑、抑郁和虚无。
显然,人们不仅应该在个体生活层面通过具身技艺的实践,修复与世界万物的肉身性联系;而且应该在公共生活层面参与“聚焦实践”活动,抵制技术虚无主义的困扰。“聚焦性实践”是由阿尔伯特·波哥曼在海德格尔的“聚焦物”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概念,用以指称那些由人们共同参与的、具有社会整合团结功能的仪式化活动。如身临其境地参与一场足球或篮球的比赛,参与富有意义的聚会或聚餐,或者与志同道合的人们看一场精彩的音乐戏剧演出等等。在这些聚焦性场景中,具有神秘性的非凡体验会通过我们的身体交互关系而涌现出来。运动员神乎其技的身体技巧使他“能够像一位希腊天神一样闪闪发光”[12](P186);在此基础上,受到感染的现场观众的情绪互动与分享会让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一下子“凸显出来,闪闪发光”[12](P187)。对此,波哥曼将它比喻为“神性”时刻的降临:“美好舒适的球场会让人感到同样的和谐。它激发公众的自豪和欢乐,一种共享的季节感和地域感,一种共同的戏剧性参与。具有这样的协同作用,戏谑和欢笑自然而然地在陌生的人中间传递,将他们结合成一个群体。当现实和群体以这种方式合作,神性就降临在赛场,这是一种非个人,然而有力量的神性。”[12](P187)
需要注意的是,“聚焦性”实践所产生的强大情感共鸣,虽然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共同生活的价值与意义,感受到世俗生活中那些万物闪耀的时刻,但也同样会让我们失去对个人理性和判断力的控制,滑向非理性的“乌合之众”状态。为了应对这样的危险,人们需要发展更为高级的共同生活的技艺,“这是一种在身不由己时对何为不利的应对方式,何为有益的应对方式,做出辨别的高层次技能。……要在我们这个世俗、虚无主义时代生活,就需要这种高层次的技能,即能够识别什么时候与欣喜若狂的大众一起欢呼,什么时候转身而去”[12](P205)。当然,这种能力的获得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人们在不断参与公共生活的实践和冒险中得到提升;但如果人们转身沉浸于电子媒体所建构的虚拟生活中,减少与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或者脱离公共性的聚焦实践,那么他们也将无法获得这种宝贵的技能。
五、结论
身处高科技媒体不断涌出的时代,时常让我们深陷困扰的并非媒体使用经验上的不足,而是对这些经验的沉思与理解,这就需要我们“辩证地审视传播媒介、传播现象和传播活动的多面性和复杂性”[14](P90)。现象学强调日常生活世界对于人类生存经验的先验意义,从存在论的视角观照技术对于生存经验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富有成效地探索人类“在技术媒介化世界中存在”[15](P36)的境况,寻求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人作为传播主体被重新“询唤”[16](P96),這一学术旨趣在德雷福斯的技术媒体研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存在现象学在技术媒体领域的成功运用,不仅为技术媒体研究的开拓树立了典范,而且为现象学在21世纪的复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美国学者肖恩·加拉格尔在评价现象学运动时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象学运动迎来了低潮期,“要说出一本1960年以后出版的重要的现象学著作并不容易。……一个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例外是休伯特·德雷福斯的著作。德雷福斯在20世纪70年代及之后的写作中,用现象学发展了一种对人工智能的批判。他的主要依据是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的理论,这是对现象学原理在一个之前从未被现象学化处理过的研究领域中一次重要而且具有创新意义的应用”[17](P12)。德雷福斯所开创或最早涉足的人工智能、具身认知、网络教育、虚拟生活等议题,如今正在成为方兴未艾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前沿课题。当我们在21世纪的当下,开始关注媒体生活的身体维度、技术的物质性影响及生存境况时,对德雷福斯学术遗产的再度发掘,无疑将会给我们当下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与启迪。
参考文献:
[1]成素梅,姚艳勤.哲学与人工智能的交汇:访休伯特·德雷福斯和斯图亚特·德雷福斯[J].哲学动态,2013(11).
[2]F.瓦雷拉,E.汤普森,E.罗施.具身心智[M].李恒威,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休伯特·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M].宁春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4]王颖吉.作为形而上学遗产的人工智能:休伯特·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现象学批判[J].南京社会科学,2018(3).
[5]马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M].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6]冯天瑾.智能学简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7]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玉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8]休伯特·德雷福斯.论因特网[M].喻向午,陈硕,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9]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0]Dreyfus Hubert &Dreyfus Stuart.Mind over Machine[M].Washington:Free Press,1986.
[11]伊万·塞林格,罗伯特·克里斯.专长哲学[M].成素梅,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2]休伯特·德雷福斯,西恩·多兰斯·凯利.万物闪耀[M].唐建清,译.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
[13]汪文圣.现象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
[14]陈世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新闻大学,2021(8).
[15]Vieta Marcelo & Ralon Laureano.Being-in-the-Technologically-Mediated-World:The Existential Philosophy of Marshall McLuhan[J].The Popular Culture Studies Journal,2013(1).
[16]喻发胜,张玥.沉浸式传播:感官共振,形象还原与在场参与[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
[17]肖恩·加拉格尔.现象学导论[M].张浩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Technological Media,Embodied Cognition and All Things Shining:Hubert Dreyfus' Phenomenology of Media and Its Contemporary Relevance
WANG Ying-ji
(School of Arts and Media,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1800,China)
Abstract:
Dreyfus has philosophically reflected on the iterativ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media from a technological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forming a media theory for future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which has made him one of the most classic scholars in the fiel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 Internet,cognitive science and phenomenology.For Dreyfus,human existence is essentially bodily existence,and one would fall into the abyss of nihilism if one were to detach oneself from the body's earthly existence.However,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are gradually making people forget the importance of the body,dissolving their proper perceptions and enthusiasm for embodied intelligence,emotional interaction,bodily techniques,ethics of trust and responsibility,and focused public life.Once people become obsessed with the illusion of disembodied cognition,remote embodiment and virtual communication,they will not only fail to succe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but will also become lonely,depressed and even suicidal due to the nihilization of reality and life.Therefore,he believes that in today's highly advanced technological media,people shoul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life by restoring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valuing skill learning an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activities and other "focused" physical practices,so that everything can shine again and life can be full of value and meaning.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media;embodied cognition;all things shining;phenomenology
(責任编辑 陈世华
)
收稿日期:2021-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多样性视野下的中国媒介考古研究” (20&ZD3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胡塞尔传播与媒介思想研究”(20YJA860016)。
作者简介:
王颖吉(1978-),男,贵州贵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从事媒介现象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