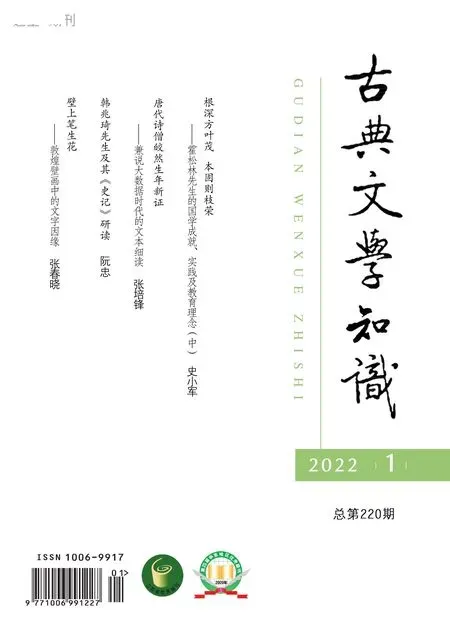谁是淳于楚
李小龙
唐人传奇《南柯太守传》是一篇名作,其结尾作者出现时叙述却有一些参差。其云:“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觌淳于生棼,询访遗迹。”不同版本的《太平广记》此段均同。仅看这句话本身似乎并无不妥,但稍稍梳理一下作品的情节关目,就会发现参差之处。这看似校勘问题,其实却是情节关目的逻辑问题。
我们看一下本文的时间线索:传文开篇说淳于棼入幻之时为“唐贞元七年九月”,这里的“七”字很可能是“十”字的形误,因为后文清楚地说:“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时年四十七,将符宿契之限矣。”贞元“丁丑”为贞元十三年(797),则前文当为“十年”。其实,无论故事开始在“七年”还是“十年”,在李公佐“自吴之洛”的贞元十八年,淳于棼都已经逝世多年,作者自然不可能“偶觌淳于生棼”。王梦鸥先生《陈翰异闻集校补考释》云:“淳于棼既卒于贞元(十)三年,至此十八年,李公佐何由‘偶睹淳于生棼’,‘八’字疑为‘一’字之讹。”把李公佐“自吴之洛”的时间提到淳于棼逝世之前,自然可以避免前揭之矛盾,但无版本依据,不免于臆断;而且在叙述安排上也有些颠倒,先述其贞元十三年去世,再补叙作者两年前与主人公的偶遇,《南柯太守传》似无此笔法。更何况如果是贞元十一年,淳于棼未死可以避免“见鬼”的矛盾,却也留下了新矛盾,就是李公佐那时还不知道两年后淳于棼“将符宿契之限”而死,怎么记录呢?
在没有找到更多校勘资料的时代,此字虽然不合情理,但整理者也只好保留,并不加任何解释。如鲁迅《唐宋传奇集》和汪辟疆《唐人小说》均如此。此后发现新的校勘材料,于此方有进展。如明沈与文钞本《太平广记》作“偶觌淳于生貌”,这仅从语意上似乎亦可通,即云李公佐来时淳于棼虽已去世,但作者还是通过某种途径看到了淳于棼的相貌,这虽然解决了前述“见鬼”的龃龉,但并无理路,因为见淳于棼的相貌与故事逻辑显然并无关系。陆采辑八卷本《虞初志》作“偶觌淳于生兒楚”,七卷本《虞初志》则作“偶觌淳于生貌楚”,似乎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程毅中先生《〈虞初志〉的编者和版本》一文指出前云之矛盾,并云:“《虞初志》作‘……偶觌淳于生貌楚’(应作‘棼貌’),近似。”但仍不能解决问题。
张友鹤先生选注《唐宋传奇选》时,据陆本《虞初志》改,并云:“‘儿楚’,原作‘棼’。按贞元十八年淳于棼已死,下文亦明言‘访询(按:当作‘询访’)遗迹’,何能再觌见本人?鲁本古籍刊行社编者校记,疑‘棼’应据沈本作‘貌’,是遗貌、遗容意。虽亦可通,究嫌牵强。作‘儿楚’,指其子淳于楚,则完全可解矣。”有趣的是,李時人等先生选注的《唐人小说选》中,此句校改为“偶觌淳于生子楚”,注者云:“底本作‘偶觌淳于生貌’,疑有脱误。据文中所述,至贞元十八年淳于棼已卒,作者不可能再见到其人,故下文有‘询访遗迹’语。此据明刊《虞初志》本《南柯记》改。意为偶然见到淳于棼的儿子淳于楚。”两家意思均同,亦均据《虞初志》改,但一改为“儿”,一改为“子”。事实上,前者改为“儿”有版本依据,即陆采八卷本《虞初志》作“偶觌淳于生兒楚”。据此来看,从明沈与文钞本与陆采《虞初志》本的异文来看,此处确当作“兒”,后讹为“貌”。总之,新的校勘资料出现轻松地解决了这个文字上的拦路虎。
但实际上,如果再深入思考,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未完全解决,因为这句话语势尚有不合。一般来说,“儿”多用于父称子,而他人描述父子关系时用“子”更恰当;这样来看,后者改为“子”似乎更顺畅,但可惜的是完全没有版本依据,或许只是选注者据语势不小心误改了吧。然而,即便我们找到了为“子”的版本,仍然会发现,此校改还有一个缺陷,即淳于棼的儿子名为淳于楚,与乃父之用字同一偏旁,不得不说颇有些奇怪。古代家族的取名规则,若有谱字,则同辈人姓名第二字相同,若无谱字或为单字名者,则以偏旁相同来表示同辈——比如说《红楼梦》中贾府从贾政到贾珠再到贾兰等莫不如此。此为小说家言,自然不必深究,但也正因如此,拟名特意父子同偏旁,似乎也启人疑窦。另外,作品也有其他一些描写与此似未合。如淳于棼虽然于“丁丑”年即贞元十三年去世时年四十七岁,至贞元十八年李公佐“自吴之洛”时又过了五年,淳于棼若活着也当五十二岁了,则其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儿子亦合情理。但从作品的描写来看,作者并未给淳于棼安排妻子和子女。一者,淳于棼入梦时,还隐约记得其父之事,但当大槐安国要招其为驸马时,他却从未有因已有妻室的犹豫,似可知作品一如其所仿效之《枕中记》一样,并未给主人公安排妻室,以便在幻梦中获得因妻而贵的际遇。二者,作品开头时淳于棼醉酒,二友人“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之下”,二人还要“俟子小愈而去”,如果淳于棼有儿子,则此时亦二十岁左右,自当出现以侍奉其父,又可共同见证其父之历幻,然作品中全无踪影,直到后来出梦寻穴等事,亦未见其有家室,除“二客”外,就是僮仆之辈。可知将此句定为“淳于棼儿楚”无论从校勘、惯例还是情节关目来看,都并不合适。
此字的矛盾及致误的理路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梳理,直到《太平广记》孙潜校宋本出现,才有了解决的可能。孙校本此处作“偶睹淳于生兄楚”,是其独有的异文,得此则前述积疑焕然冰释。从致误之因来看,知此“兄”字先讹为“兒”(即陆本《虞初志》的异文);因其字不通,又为人校改为“貌”;“兄”字即从传文中消失,故后之“楚”字亦无着落,后人又将此字校改为“棼”,以至不可究诘。从文中逻辑来看,淳于生名“棼”,其兄名“楚”,兄弟二人单字名有共同的偏旁,亦甚贴合。
从叙事传统来看,唐人传奇常于文末让作者现身说法,且常安排作者与主人公或其亲友等小说世界中的人物来往,以增加故事的真实性。《离魂记》末云:“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祖,而说极备悉,故记之。”《任氏传》末云:“大历中,沈既济居钟陵,尝与崟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李娃传》末云:“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东城老父传》中云:“元和中,颍川陈鸿祖携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觐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此传拈出其兄为作者讲述淳于棼之经历,亦与传统体例相合。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考察唐传奇的作者,会发现最擅长将自己融入小说叙述,让作者与小说中人有交往的有二人,一为沈亚之,一即李公佐。就李公佐来说,他现存四篇完整的传奇作品中,其余三篇情况如下:《庐江冯媪传》末云:“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天水赵、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釴具道其事,公佐因为之传。”作者出现了,也有特意讲述此事的人(高)。《无支祁传》(即《古岳渎经》)是中国古代小说作者身份变化最复杂的作品,传文开始时,“唐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杨将永泰中楚州刺史李汤见淮水中锁巨猿的异事讲述给李公佐;然后“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饯送给事中孟简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馆待礼备。时扶风马植、范阳卢简能、河东裴蘧皆同馆之,环炉会语终夕焉。公佐复说前事,如杨所言”,则李公佐从故事的接受者变成了讲述者;此时,这还只是一个“征异话奇”的小异闻,尚无神异色彩,但接下来,李公佐又从倾听者与讲述者转变为行动者或者说故事的推动者了,“至九年春,公佐访古东吴,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庐。入灵洞,探仙书,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这部古经道出了来龙去脉,把此前异闻背后的复杂背景交代出来,也使得这部作品从异闻变成一则带有神话性质的诡奇之作。至于《谢小娥传》,李公佐已经不满足于作者出现,并与作品中人发生联系,甚至干脆就进入到叙事世界之中,成为自己笔下的人物,为主人公谢小娥破解字谜,寻绎真凶,然后又遇谢小娥于尼寺。从这三篇作品的惯例来看,李公佐最杰出的作品《南柯太守传》也当符合这一叙事逻辑。
本文的考证虽然仅仅是一个字,但一方面梳理清楚了《南柯太守传》的文本,让我们对此传叙事逻辑有了更丰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还让我们看到,文言小说的校勘,是如何地依赖校勘材料提供的异文,如果没有丰富的异文资料,校勘者面对文本中扞格难能之处,在思维中完全没有通向正确文本的“路线图”——事实上,有时候哪怕是错误的异文,如本文提及的陆采《虞初志》作“兒”,但至少也能给我们指出文字致误的方向。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常衮与建州茶业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