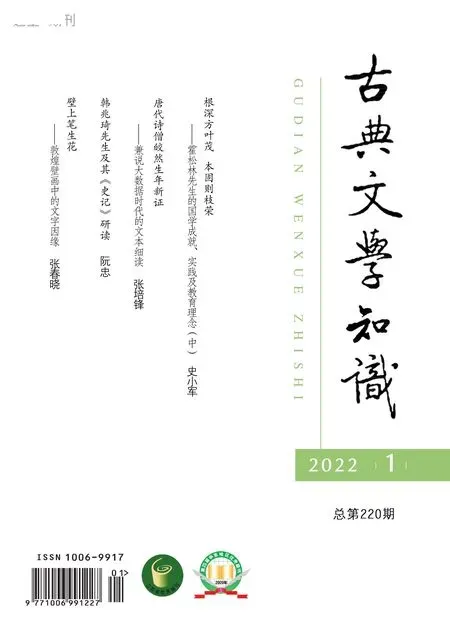哀婉的风雅:花冢与诗冢
李鹏
冢,《说文解字》说是“高坟也”,即封土高高隆起的坟墓。《红楼梦》第六十三回里邢岫烟说妙玉认为从汉晋五代至唐宋皆无好诗,只有“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两句好。这两句诗出自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二十八《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是他在给自己营建墓地时有感而发,原诗“铁门槛”作“铁门限”。范诗诗题里的“寿藏之地”和诗句中的“土馒头”,指的都是冢,只不过前者典雅,后者则直白而形象。此前王梵志早就写过两首白话诗,其一为“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其二为“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范成大巧妙地将这两首诗绾合在一起,熔铸成工整精粹的一联,更显得警醒,也更有冲击力,因此受到《红楼梦》作者的激赏。小说中除了借妙玉之口特意予以标举外,还设置了“铁槛寺”“馒头庵”这样的地名,并在第十五回回目“王凤姐弄权铁槛寺,秦鲸卿得趣馒头庵”中加以对举,该回说“因他庙里做的馒头好,就起了这个诨号”,不过是小说家的障眼法。情种秦钟这一回里还在馒头庵和智能幽会寻欢,下一回便夭逝黄泉成了土馒头里的馅儿。馒头庵里的馒头,表面上带给读者的是肉感的香艳,隐藏在背后的却是凄冷的惊心,真给人一种忙着生、忙着死的无常感。不过,《红楼梦》里这种几乎挥之不去的生命无常感,在黛玉葬花的“花冢”前尤显得哀感顽艳。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宝玉读《西厢记》至“落红成阵”,正巧风把树上的桃花吹落在他身上、书上,宝玉不忍花瓣被践踏,便兜至水边抖落,让其随流水飘荡而去,倒也应了《西厢记》里“花落水流红”这句唱词。此时恰逢黛玉担着花锄、拿着花帚过来,却说:“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凈。”黛玉这里提到的花冢,第二十七回回目作“埋香冢”。在这一回里,黛玉一边葬花,一边感花伤己,随口吟唱:“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堆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沟渠。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一旁宝玉听了,“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一念及此,可谓空落落无所归依。其实,有人没人,花照开照落,花冢里葬的不是花,而是有情人伤春自怜的意绪。
黛玉葬花,因为《红楼梦》影响巨大,花冢为人所熟知;而清代顾光旭葬诗,虽为一时佳话,但知道诗冢的人并不多。
顾光旭(1731-1797),字华阳,一字晴沙,号响泉,江苏无锡人,清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官至署四川按察使司,著有《响泉集》三十卷等。生平详见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四《甘肃凉庄道署四川按察使司顾君墓志铭》。据王昶所撰墓志铭,顾光旭归隐林下后,“以无锡东南文薮而贤人淑士湮没未尽彰,网罗诗什,人各系以传,成《梁溪诗钞》四十八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顾光旭编选的《梁溪诗钞》是一部郡邑类诗歌总集,选录了古称“梁溪”的无锡一地自东汉至清乾隆间一千一百余位诗人两万余首诗,全书并非王昶所谓四十八卷,而是五十八卷。有意思的是,选完诗之后,在同乡贾崧的建议下,顾光旭将选诗时所用各家集子原本埋在锡山南麓,建一亭子,上立石碑,号曰“诗冢”。除了在葬诗时邀请众多士人会葬外,顾光旭还专门派出贾崧向诗坛名流广泛征题索诗,一时之间轰动不小。
翻阅《清代诗文集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及其他清集,我检得题咏此事诗歌如下:
袁枚《诗冢歌》、
赵翼《顾晴沙选梁溪诗成,瘗其旧稿于惠山之麓,立碑亭其上,名曰诗冢,为赋七古一首》、
翁方纲《诗冢歌》、余集《戏题贾素斋诗冢诗》、戴殿泗《梁溪诗冢(有序)》、张云璈《诗冢歌并序》、
法式善《顾晴沙光旭观察选〈梁溪诗钞〉,贾素斋综其遗稿为冢,纪以诗》、吴文照《诗冢歌》、曾燠《梁溪诗冢》、刘嗣绾《梁溪诗冢歌为贾文学崧作,兼哭响泉先生》、郭堃《梁溪诗冢》、宋鸣琦《无锡顾晴沙观察选其乡自汉魏以来诗,都为一集。既竣事,贾上舍崧汇各遗稿,葬于锡山之麓,名曰诗冢。索诗》、潘世恩《诗冢歌》等。
与葬花一样,葬诗也是痴,正如余集题诗其二所谓“能诗本是痴人事,想到埋诗事更痴”。不过,贾崧与顾光旭并非诗冢的首创者,郭堃题诗中的“自今名始创,于古事希闻”其实并不准确。明初宋濂《文宪集》卷十五有《诗冢铭(有序)》,序中提到有个叫鲁修的诗人,“惧其诗失传,埏埴为甓刻,瘗芝山中”,即将诗烧制在土砖上埋于地下,企图借此让自己的诗躲过战乱传到后世。显然,从时间上看,鲁修的诗冢创立在前。
而比顾光旭稍早一些的陶元藻(1717-?)在编订自家诗集时,也将刊落之诗放入一石函中,埋入地下,题曰“诗冢”。陶元藻《泊鸥山房集》卷三十四中有《诗冢》两首,诗中虽然认为这些被葬的诗只是“鸡肋”“瓦砾”,之所以割爱埋掉是为了“免使人间论短长”,但一句“惆怅敲门月下僧”(见《汇编》第341册),也能看出对作者来说,要亲手埋葬这些当年曾费尽心血仔细推敲写出来的作品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诗写完之后,陶元藻还特地写信邀请一众好友唱和,梁同书《频罗庵遗集》卷三有《萧山陶篁村元藻自订诗集竟,不入选者置石函埋之,题其阡曰诗冢,撰二律索和,因简寄五首》,而吴骞《拜经楼诗集》卷十也有《山阴陶叟篁村诗集刊成,复汇其不入梓者,作石函而瘗之,号曰诗冢,自为之记,遍征友人题咏,山舟太史邀予同赋》。
上述诗冢间略有不同的是,鲁、陶所建诗冢,虽然一个是为了传世,一个是为了藏拙,但所埋均为自己的诗;而顾光旭修的诗冢,埋的却是他人的诗。
顾光旭同年钱载《梁溪诗钞序》说该总集“取例于元遗山《中州集》、朱竹垞《明诗综》,上遵御定《国朝别裁》之义,大要以诗传人,而亦以人传诗”,话里所揭示的编纂宗旨,实际就是顾光旭自己在该书跋文中所谓“志在献不在文”,即之所以抄录诗篇,为的是让这些诗人的名字流传下去。对于诗人而言,写下的诗作实际上是其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渴盼的是文字能够穿越时空成为永恒。可是,文人仰屋著书,诗人呕出心肝,真正能流播人口的又有多少?最后只落得个诗冢同归,一抔黄土掩风流,到底令人心酸不已。曾帮助顾光旭选诗的刘嗣绾题诗所谓“诗魂古今同一丘”,顾光旭建一诗冢将众多诗魂汇聚在一处,一瞬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中所谓“千红一窟”“万艳同悲”。只不过,一为女儿,一为诗人。
在张云璈题诗中,他对诗人传世的渴望表达了极大的同情,所谓“从古名心不肯死,姓氏长教堆故纸。骨虽已朽力可争,所志区区只在此”。因此,他很赞许顾光旭选诗“隐然以诗为性命”。不过,他认为葬诗之举并不妥,因为“文字潜幽气不灭,浆酒寒浇心尚热。请看一字二字间,犹是千痕万痕血”。他觉得,最好学前人将诗集藏于古寺的做法,将这些集子都安置在锡山龙光塔上,以便后人续选诗钞,“来补先生所不足,不教沧海有遗珠”。
除了张云璈,顾光旭的老乡秦瀛也特地写信对此举表示明确反对。秦瀛《小岘山人文集》卷二有《与顾丈响泉书》,中云:
吾邑自汉以来迄近今之诗,先生以前无有裒而录之者。先生殚数年之苦心,搜罗采择,发潜阐幽,人系以传,登之梨枣,甚盛举也。然诸家之诗之原本,或锓刻,或钞写,或专集流传,或错见别本,或藏之于其子孙之家,或不必子孙而他人藏之。先生之钞梁溪诗,多者不过一人钞数十首至百首,少且一二首至十数首耳,岂能尽其人之诗而钞之?即谓所钞之诗,其人之真精神已在于是;而此外未鈔之诗,其人一生心血所在,亦应听其自存自亡于天地之间,不应举而弃之土壤也。瀛意先生方采诗时,邑中之人各以诗送钞,先生必且逐一标识;俟钞既成,一一还之。夫古人往矣,其骨已朽,幸其诗仅存,不至与形骸俱敝,为狐貉啖尽。今先生欲不朽之,而又欲速朽之,何欤?(《汇编》第407册)
秦瀛信的后半提到唐代刘蜕建文冢。刘蜕《文泉子集》卷三有《梓州兜率寺文冢铭并序》,文章开门见山:“文冢者,长沙刘蜕复愚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也。”可见他埋的只是自己文章的草稿而已。由于刘蜕该文极有名,顾光旭等人建诗冢很可能受其启发。唐人刘蜕外,秦瀛还提到当时有一个叫朱榈香的同乡也曾想建诗冢埋他朋友的诗作,但并未实行。在信的最后,秦瀛直言:“先生道高德重,不宜听后生小子无知之言而有是举。”
而在赵翼题诗里,他认为建诗冢的先例除了文冢外,可能也包括笔冢,即所谓“文冢笔冢可援例”。关于笔冢的传说,唐代李绰《尚书故实》说是王羲之孙子智永“积年学书,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后来埋了,号为“退笔冢”。巧的是,李绰还提到因为来找智永题字的人太多,把门槛踩坏了,于是用铁叶把门槛给包上,称作“铁门限”。另外,唐代李肇《国史补》卷中“得草圣三昧”条则说:“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看来,与埋诗作冢一样,埋秃笔成冢的书法家也不止一个。
在顾光旭之后,清咸丰六年(1856),黄琮辑完《滇诗嗣音集》之后,也将遗稿埋葬在太华山,并作铭文。据由云龙《滇故琐录》卷三“黄文洁诗冢铭”条记载,冢上也立了一碑,“约高五尺,阔一尺五寸,上书‘诗冢’二大字,下为铭”。这真可谓流风遗韵,嗣响不绝,令人叹惋。
倘若说花无知,人有情,花冢里葬的落花寄托的是伤春女儿的愁绪,那么诗本身就是生命的结晶,诗冢里掩埋的,绝不仅仅是文字,而是诗人们的魂灵。其实,无论是花冢,还是诗冢,风雅的背后,都是对短暂而真实存在过的生命的温情关注。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