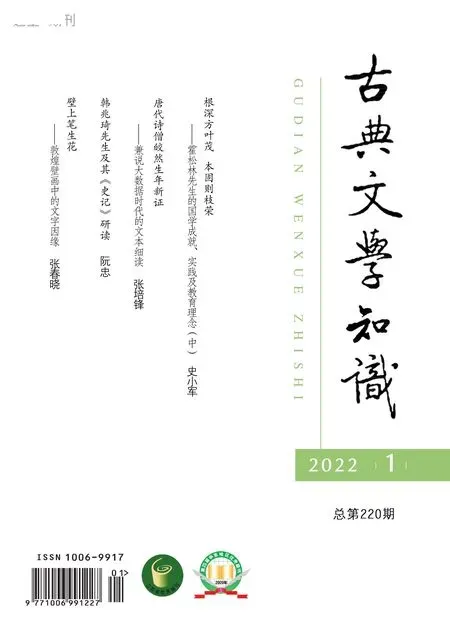解读魏晋名士服药(下):服药活动的精神和社会功效
宁稼雨
作为一群精神贵族,魏晋士人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服药的实际功用。他们还不断发掘服药活动的精神文化追求和社会实际作用,从而把服药活动从传统意义上的治病养生上升到企求长生,追求精神愉悦,以及社会政治活动中的面具作用等更高层面的价值实现中,扩大了服药活动的历史文化价值深度和广度。
企求长生:从帝王到平民士人
无论是帝王服丹、民众服符,还是士人服石,其源头均为先秦神话传说中的不死之药。一种是神话传说神医手中的起死回生之药。如《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所说六巫“皆操不死之药”。另一种是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死之药。如《归藏》中提到的“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为月精”,《楚辞·天问》中也有嫦娥窃不死之药奔月的故事等。从两种不死药的功用效果来看,长生不死之药与嫦娥奔月有关,说明它是早期羌人飞升神仙观念的产物;起死回生之药则表现出稍晚一些时候人们希望保持肉体与灵魂同在的观念意识。
秦汉时期帝王寻丹服药的行为,本来是方士为改变自身社会地位而向帝王献媚的手段。但这一手段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使寻丹服药的求仙目的特权化,使早期神仙观念中人人可以成仙的可能变为帝王独自享用的特权。与此同时,随着帝王成仙希望的破灭,士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也就出现破裂。这就意味着不仅丹药的享用者孕育着变更的可能,而且“道统”与“势统”的关系也产生重新组合的必要。葛洪在《抱朴子·论仙》中通过至道仙法与秦皇汉武远离仙道的鲜明对比,已经把帝王在寻药服丹领域的特权彻底取消,从而表现出汉代以后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士人群体在道教服食领域打算对帝王特权取而代之的强烈欲望。葛洪在其《神仙传》中又以许多神仙故事形象地体现了这种新鲜的神仙思想。传中故事普遍写到武帝求仙的失败,同时还具体点明帝王求仙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其身份地位使得其求道不诚。如《李少君传》写到李少君指明汉武帝求仙失败的原因时说:“陛下不能绝骄奢,遣声色,杀伐不止,喜怒不胜。万里有不归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不仅如此,一些神仙传记中还对帝王与神仙(实为方士)的君臣关系提出质疑。《卫叔卿传》中当汉武帝得知卫叔卿为中山人后说:“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语。”不想这句话却引起了卫叔卿的极大反感。“叔卿本意谒帝,谓帝好道,见之必加优礼,而帝今云是朕臣也,于是大失望,默默不应,忽焉不知所在”。可见方士已经不能接受自己与帝王主仆式的君臣关系。此正如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中指出的那样:“《神仙传》中李少君所叙述的内容,实际上代表了与襄楷、葛洪等人的神仙思想、初期道教思想有关联的知识阶层的主张。把追求‘永生’作为君主特权的古代神仙思想,被这种知识阶层的伦理价值观念否定了;以这种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新神仙思想,在这一时代发展繁荣起来了。”于是从汉末开始,随着汉朝政权的动摇和君权的日益削弱,求仙服药以求长生已经开始成为士人自己向往的享用目标。
先秦时期帝王服用丹药的动机绝不仅仅是为了延长他们个人的生命,而是将服丹与其政运的久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将其作为革命改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汉末以来的民间道教往往都将与道教有关的各种服食等法术可能具有的治病及长生作用作为诱饵,来吸引教徒入道从戎,扩充队伍。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治病的方式传道。据《晋书·孙恩传》,孙恩起义时势力蔓延如此之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于这种宗教力量。孙恩世奉五斗米道,据会稽后,号其党曰“长生人”。“长生人”的口号的确投人所好,所以不但徒众甚多,有的妇女背着孩子不能从军,便把孩子放在筐中投入水中,对孩子说:“祝贺你先登仙堂,我随后便到仙堂找你。”直到孙恩失败,被迫赴海自沉,他的党羽和妓妾还认为他已成了水仙,“投水死者百数”。张角和孙恩发动的人员对象主要是社会下层民众,但他们自身的行为目的是为了称帝。应当看到,他们在把以往帝王独自享用的成仙之术提供给广大徒众受用这一点上是与以往的帝王服丹有所区别的;但他们在以长生之术为政治目标服务这一点上却又与秦皇汉武如出一辙。显然,这些长生服药中的政治动机恰恰就是嵇康所指责的“神躁形丧”的荒谬服药之举。相比之下,士族文人所继承的,正是嵇康所指明的脱离政治动机的属于士人阶层的服药中的长生愿望。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所列举的东晋天师道世家的服药修道行为明显地体现出嵇康所认定的疏离政治、注重精神修炼的服药宗旨。尤为引人瞩目的是王羲之,他不仅与道士许迈等人“共修服食,采药石”,而且“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见《晋书·王羲之传》)“我卒当以乐死”一句是值得玩味的。如果理解上没有偏歧的话,那么在王羲之看来,“乐”的意义要远远超过“不死”,至少可以用“死”来交换“乐”。这也就是说,精神上的安详和愉悦远比肉体生命本身的存在要重要得多。这种注重士人自身的精神修养的取向不仅与嵇康的倡导遥相呼应,而且也与整个魏晋时期士族文人注重精神养炼的潮流密切吻合。明白了这一背景,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两晋士人服药过程中的精神取向。
再看这样一个故事:一天,王恭服过寒石散后,到外面行散,在弟弟王爽的门前见到弟弟,便问他:“古诗中何句为最?”弟弟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王恭自己却吟咏起来:“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认为此句最佳(见《世说新语·文学》)。显然,人生无常、及时行乐,这是王恭一路行散考虑的问题,他認为这是服药的目的,并用《古诗十九首》中的诗句加以表述。而这一问题,是魏晋整个社会的普遍思潮。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直接对人的生命造成威胁,人的平均寿命也普遍降低。而随着儒家思想地位的动摇,它所宣扬的“未知生,焉知死”的逃避态度也不能为人们所首肯。生的意志呼唤着人们,而人为地延长生命又集中体现了生的意志。人们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服药的目的。王充《论衡·自纪篇》说:“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嵇康《养生论》也说:“夫神仙虽不自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道教在汉末至魏晋间兴盛起来,就是因为它所鼓吹的服食之法可以有限地延长生命,而成仙之法则可绝对地延长生命。这对希求长生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当时的士大夫,也把服药作为企求长生的重要手段。郗愔“与姑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见《晋书·郗愔传》)。这些上层人物主要信奉天師道。像王羲之等人,都是天师道世家。由对生命无常的感慨想到以服药等方式人为地延长生命,这是建安至正始间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心理,也是这个时期很多文化现象的重要动因。不仅曹操这样的雄才大略者要大唱“人生几何”,三曹及七子的诗歌中,都可感受到这种格调。阮籍的《咏怀诗》则最为明确:“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
“神明开朗”的超然境界
所谓“神明开朗”大约是指服用五石散后人的大脑受到药物的刺激而感到精神上的兴奋和舒畅。皇甫谧《寒食散·发侯篇》称服用五石散可以使“心加开朗,体力转强”。孙思邈《千金药方》卷二四:“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万事休泰。”“所以常须服石,令人手足温暖,骨髓充实,能消生冷,举措轻便,复耐寒暑,不著诸病,是以大须服。”这种功用在汉代服丹术士那里就已经开始受到注意。《后汉书·方术列传》:“王真年且百岁,视之面有光泽,似未五十者。”《汉武帝外传》:“(武帝)断谷二百余年,肉色充美,徐行及马,力兼数人。”魏晋时期也是如此。曹操《与皇甫隆令》:“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如果说汉代以来帝王和术士注意的仅仅是服食以后面容的光泽和“充美”的话,那么到了魏晋士人那里,这种面容的光泽便与精神世界的内涵连在了一起。何晏所讲的“亦觉神明开朗”,指的就是服药后容光焕发的外表所体现的内在精神活力。这一点大约是许多士人服药后的共同的感觉。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诗》:“开芳及稚节,含彩各惊春。尊贤永照灼,孤贱长隐沦。容华坐消歇,端为谁苦辛?”由于服药后大脑的兴奋,所以在行散途中总是以激昂的神情去观察外界的事物,使诗中的外界景物带有明显的诗人主观感受色彩。
把服丹用药作为士人内在精神养炼的手段,是魏晋时期道教分化后士族丹鼎教派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一点在魏晋时期的炼丹诗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黄庭内景经》二十四章:“隐景藏形与世殊,含气养精口如朱。”两句诗虽然字数有限,却清楚地描绘出服用内丹后的显著功效:倘若远离尘世,与世俗相异,抚养内气元精,则可以精神焕发,口如丹朱。尤为明显的是该经《心神章》:
心神丹元字守灵,肺神皓华字虚成,肝神龙烟字含明,翳郁道烟主浊清。肾神玄冥字育英,脾神常在字魂停,胆神龙曜字威明,六府五藏神体精,皆在心内运天经,昼夜存之自长生。
尽管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这首诗的艺术水准很难得到恭维。然而它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士人服丹后存想过程的例证和范本。诗中罗列的各种神的名字及其能量描绘,实际上是服丹者存想时精神世界驰骋想象的内容。按照诗中的说法,身体的各部器官各有所能,均可与“神”相通,以至能“六府五藏神体精,皆在心内运天经”。道书中很多存想之术的描绘可以与之相证。《三十九章经》在谈到存想“太微小童”时说:“读高上虚皇君道经,当思太微小童千景精,真气赤色,焕焕从兆泥丸(指大脑)中入,下布兆身,舌本之下,血液之府。”该书在谈到存想“无英公子”时又说:“读上皇先生紫晨君道经,当思左无英公子玄元叔,真气玉光奕奕,从兆泥丸中入,下布兆左腋之下,肝之后户,毕微祝曰:‘无英神真生紫皇,三气混合成宫商。招引真气镇膀胱,运流三丹会洞房。为我致仙变丹容,飞升云馆入金墉。’”将这些具体存想的描绘与前面《三十九章经》和《心神章》的介绍相对照,就可以看到服用丹药者在所谓存想的过程中是将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联想为神的寄托所在,进而对其神驰遐想,增强自己服药后的良好感觉。这或许就包含何晏所谓“神明开朗”的意思。
正始名士服药后注重精神世界的建设还与当时哲学文化思潮中注重形而上对形而下的超越,无限境界对有限境界的超越的主流有关。何晏本人就是正始玄学的开山大师,为“贵无”学说的开创者。这些内容学界已有涉及,兹不赘述。这里要谈的是何晏不仅在理论上大谈无限胜于有限,而且还十分自觉地将其理论化为人生实践,在个人精神与行动上也将“神明”之境作为人格理想。《世说新语·夙惠》:“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这一点是贯穿他的人生过程始终的。《魏氏春秋》记载:“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自况诸己也。”何晏以他玄学家的敏锐感觉和深刻见解看到“唯深”“唯几”在境界上与“唯神”的天壤之别。尽管所谓“深”和“几”是“极未形之理”“适动微之会”,本身具有形而上的性质,但重要的问题是它们最终的目的是为“天下之功”“天下之务”服务,又回到了形而下的层次。而“神”的境界却与它们不同,无论是手段,还是目的,都是超现实,都是形而上的。所以何晏对于“深”与“几”虽然不无首肯,但他肯定的也只是二者手段的玄虚性,而不是目的的现实性。因而他对夏侯玄、司马师这样能够“极未形之理”、“适动微之会”的形而上才能是赞赏的,但却从根本上鄙薄他们涉身世务的功利行为。他竭力推崇的正是他始终为之向往的“至理微妙,不可测知,无象无功于天下之事”的玄远境界,所以裴松之才会说他“欲以神自况”。
了解到何晏对“神”的境界的无限向往,也就能够从更加深刻的背景上体会到他服用五石散后何以会为“亦觉神明开朗”而沾沾自喜。而这种服药中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恰恰体现了士族阶层在服药领域中取代帝王特权,使之为我所用的士族特征。
服药与逃避政治漩涡
服药之后产生的副作用,被一些人用来躲避政治灾祸。魏晋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有些人为了逃避政治漩涡,往往诈称寒食散症状发作。因为服寒食散患后遗症者往往被视为残疾之人而容易避祸。比如八王之乱时,王颙派人游说成都王司马颖,准备杀掉齐王冏,司马冏向王戎请教对策,王戎劝齐王冏:“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推权祟让,此求安之计也。”但齐王冏的谋臣葛旟却不同意齐王冏放弃权力,准备杀掉王戎。王戎就伪装药性发作,掉进厕所茅坑之中,才免除了杀身之祸(见《晋书·王戎传》)。殷任南蛮校尉时,其从弟荆州刺史殷仲堪在王恭的怂恿下,准备发动内战,并动员殷一起参加。殷严词拒绝:“吾进不敢同,退不敢异。”后来殷仲堪举兵成功,贪得富贵,并记恨殷前言。殷知道殷仲堪将排除异己,任用党羽。便借服寒食散外出行散,托疾不还。当殷仲堪去看望他的时候,殷因服药已经严重散光,只能见人半面。这也就是皇甫谧说的“服药失节度,则目瞑无所见”。殷仲堪难过地说:“兄病殊为可忧。”而殷却义正辞严地说:“我病不过身死,但汝病在灭门,幸熟为虑,勿以我为念也。”后来,殷仲堪在与桓玄的作战中失利,被逼自杀。殷则因服散致病,忧郁而卒(见《晋书·殷传》)。
又据《高僧传》,桓玄征讨殷仲堪时,大军经过庐山,桓玄邀名僧慧远出虎溪见面,慧远称疾不堪,桓玄只好入山去见慧远。晋安帝自江陵凯旋回京师,路经庐山,辅国何无忌劝慧远候迎,慧远仍然称疾不行,晋安帝只好派人劳问。慧远在给晋安帝的信中说:“贫道先婴重疾,年度益甚,猥蒙慈诏,曲垂光慰,感惧之深,实百于怀。自远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在晋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因寒食散药物发作而病倒,六天后就奄奄一息了。临终前,弟子耆德等人劝他饮用豉酒解毒,慧远却不肯违犯佛教不许饮酒的戒律。请他喝米汁,也不允许。又请他喝蜂蜜水,慧远则命律师查阅经文,看是否允许。律师刚查了一半,慧远已经合上了眼睛(见《高僧传·晋庐山释慧远传》)。
此外,如陈敏之乱时诈称诏书,以贺循为丹杨内史。贺循辞以脚疾,手不制笔,又服寒食散,露发袒身,示不可用。陈敏竟不敢逼(见《晋书·贺循传》)。晋武帝几次诏敦皇甫谧应命,皇甫谧皆以服散患疾相辞(见《晋书·皇甫谧传》),皆属此类。另外,有些帝王因服药变得性格暴躁,以至影响政局,则是服药对政治生活影响的另一种形式了(详后)。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