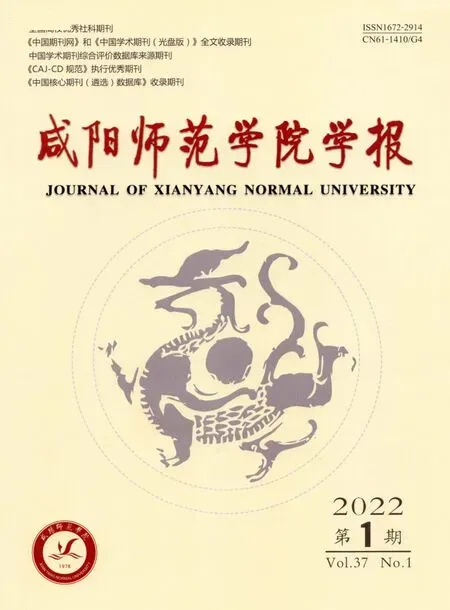秦人石文化的特殊性及其汉代影响
崔建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作为一种自然物产,石材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甚大。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被定义为石器时代,以石器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工具,是如此定义的直接依据。然而,事实表明,尽管石材在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时间里扮演着主角,但它并没有将这个角色保持下来。在中国,虽然它的很多原始功能被延续,且有创新,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还是被青铜、铁等金属所取代。直到与秦人相遇,古老的石材才再一次大放异彩,最终成为承载两千余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角色之一。
一 秦史所见石材应用的记录
秦人自受封立国以来,发生过一系列与石有关的事件。《史记·封禅书》:“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所谓“若石”,《集解》引苏林曰:“质如石也。”而《索隐》同引苏林之说,却稍有不同:“质如石,似肺。”[1]1359《水经注》的描述又有不同:陈仓县“有陈仓山,山上有陈宝鸡鸣祠。昔秦文公感伯阳之言,游猎于陈仓,遇之于此坂,得若石焉,其色如肝,归而宝祠之,故曰陈宝”。[2]431而《通典》引苏林曰:“质如石,似肝。”[3]1554与《水经注》之说一致。若石究竟“似肝”抑或“似肺”,准确的说法已不易判定。不过,古人很可能以为若石为赤色。《周礼》“大司寇”职掌包括“以肺石达穷民”,郑玄注:“肺石,赤石也。”[4]871若石既被描述为“似肝”“似肺”,亦当以赤色为是。①有学者认为秦文公所获石为“大陨石”,(梁云《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10页)若如此,则非赤色。但论者并未就陨石说作充分的论证,本文暂不取其说。
后来,秦人将文字刻于石制乐器上。凤翔秦公大墓墓主被学者认定为秦景公,时当春秋中晚期。石磬“最少当有三套,其总数当有数十枚”。但因遭盗掘,皆残断。发掘者挑选了一些文字比较清晰的残磬,对其铭文进行了缀合。残磬铭85 凤南M1:300与1982年出土的另一残铭缀合后可得三十七字铭文:
残磬铭85凤南M1:495+549+517三条接读后可得如下铭文:
……绍天命,曰:肇敷蛮夏,亟事于秦,即服……[5]
此外,属于春秋时期的石磬还有宋人著录的秦怀后磬,铭文曰:
在中国传统金石学视野中,还有几批著名的秦人石刻。其一为石鼓文,每石一诗,共十首,字体为小篆。这组石刻最初为唐代人所注意,直到现在,对其刻写年代仍是众说纷纭,主张春秋时期者不乏其人。但亦有主张战国说者,比如郑樵判断石鼓文字体为秦篆,他通过铭文中的“嗣王”称谓,推断石鼓文刻于秦惠文君称王之后。唐兰同意将石鼓文定于战国时代,但他认为,“郑说是有缺点的,因为铭文里秦君还称公,嗣王是指周天子,所以应该在惠文称王以前”。[7]从学者的此番辩难中可以感觉到,“嗣王”称谓是判断石鼓文年代的重要线索。现将出现“嗣王”的石鼓诗《而师》录于下:
□□□□,□□□□,□□而师,弓矢孔庶。□□□□,□□□以,左骖□□,滔滔是炽。□□□不,具□□复,□具吁来。□□其写,小大具□,□□来乐,天子□来。嗣王始□,古我来□。[8]760
唐兰所谓“秦君还称公”的铭文,见于组诗的另一篇《吾水》,该篇既有“天子”又有“公”。[8]797-798然而,他的判断其实也存在逻辑疏漏。首先,不同诗篇中出现的“公”与“嗣王”是否会形成排斥效应?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即两诗是对不同时段的描绘,所绘为秦君称公阶段的情形即称之为“公”,所绘为称王阶段的秦国则称秦君为“嗣王”。其次,如果《而师》中的“嗣王”亦指天子,那么,天子的称谓为何会在同一篇中不同称?对于这些疑问,高明先生的见解值得重视。他对石鼓文作了一个基本定性:“十件石鼓雕刻了十首古诗,诗的内容皆为颂扬当时秦君一生最得意也最有兴趣的事迹,都是他的实际活动。”而《吾水》《而师》两篇所记即为某位秦君不同人生阶段的事情,“《吾水》前称‘天子’,后称‘公’,显然是对周天子和当时执政的秦君的不同称谓。《而师》鼓文‘天子□来,嗣王始□’,‘嗣王’也是对当时执政秦君的称谓”。而在秦国历史上,“既称公又称王的只有一位,那就是秦惠文王”。由此,高明最终推断,“石鼓文制作当在秦惠文王废‘公’称‘王’改元后的十四年之内”。[9]笔者以为,这个断代结果说服力更强一些。
传统金石学中的另一组秦人石刻被称为《诅楚文》,发现于北宋时期,共有3件,分别为《告巫咸文》《告大沈厥湫文》《告亚驼文》。②《告亚驼文》往往被视为赝品。但裘锡圭认为“决不可能是伪刻”,所谓“亚驼”应读为“虖池”,西汉时期的安定虖池苑即据此水为名。参见氏著《诅楚文“亚驼”考》,载《文物》1998年第4期。它们内容相似,只是告祭之神不同。秦人在诅文中提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勠力同心,两邦以壹,绊以婚姻,袗以斋盟,曰世万子孙毋相为不利”,而当今楚王“康回无道,淫失甚乱”,“兼倍十八世之诅盟,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由于楚人无道,秦王遂请求神灵惩罚楚人,保佑秦军取胜。①释文据杨宽《秦〈诅楚文〉所表演的“诅”的巫术》,载氏著《古史探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06-407页。笔者对标点有所更动。对于诅楚文的断代,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在秦惠文王时代,②比如杨宽说“《诅楚文》是秦惠文王时期的作品”。(《古史探微》,第408页)李开元认为:“秦楚两国的联姻结盟关系,从秦穆公到秦惠文王,正是第十八代。到了秦惠文王在位的最后年间,两国关系破裂,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诅楚文》的产生,就是在这个时候。”(《秦始皇的秘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1页)因为其中反映的秦楚决裂事件发生于秦惠文王末年。与创作于秦惠文王称王之后十四年内的石鼓文相比,诅楚文的年代即便极致前推,也不过与石鼓文大体相当。更大的可能,它要稍晚于石鼓文。
以上与石材相关的事例皆发生于秦统一之前,兼并天下后,秦人对石材最为显著的应用莫过于一系列东巡刻石的创作。《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封禅后,秦始皇“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之后“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此年分别在邹峄山、泰山、之罘、琅邪立石刻,凡四处。二十九年(前218),秦始皇“登之罘,刻石”。三十二年(前215),“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③刻辞中有“群臣诵烈,请刻此石”的说法,故知“刻碣石门”亦为刻石。三十七年(前210),“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综合以上记录,秦始皇刻石共七处。秦二世即位后,“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二 秦人石文化的特殊性
通过对材料的梳理可以认识到,目前所见秦人运用石材的记录均与隆重的礼仪活动密切相关。尽管礼仪取向并非秦人独有,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秦人在礼仪活动中使用石材时,具体的用法非常富有个性。
以石材作为祭祀的对象,西周时代即有此现象。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的庭院中“有一处长方形的铺石遗迹”,“铺石的北侧正中树立着一块青灰色砂岩制成的长方体立石。立石通高1.89 米,地面以上现存部分高0.41 米,地面以下部分高1.48米”。而在“立石的四周地面上,特别是前方的铺石遗迹上,分布着大量立石被破坏而散落下来的小碎块,重量达164千克。根据这些残块,可知立石原本至少比现存状况高0.34 米”。发掘简报认为,凤雏三号基址“可能是一处西周时期的社”,而庭院中的立石可能是社主。[10]社是祭祀土地神的,西周人以石为社主,说明他们认为石柱与土地神之间具有紧密的相关性。
陈宝祠供奉的实际对象为一块色泽鲜明的石料,祭此石可引出“雄鸡”“野鸡”。但鸡本身其实并不属于难得一见的稀有动物,它之所以能够为众人所瞻仰,关键在于其夜晚现身时所伴生的“光辉若流星”的神奇光影现象。依现代科学度之,地上一块体量有限的石料与划过漫漫夜空的流星般的光影,二者之间很难存在什么物理性的必然联系。基于此,关于陈宝祠的生成机制,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若石本身因色泽极其特别而受到秦人的供奉,人们觉得此石非同一般,遂将供奉后偶尔发生的光影现象归因于此石;其二,光影现象发生在前,秦人在探求原因的过程中遇到了引人注目的若石,遂将其视为光影出现的根源。无论哪种解释,都包含着秦人的一个观念,即若石与光影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显而易见,周人社祀与秦人陈宝祠之间存在一个共性,即两者皆将石材与某种神异联系起来。但这一共性只是表象,就祭祀的性质、生成机制而言,二者并不相同。性质上,给土地献祭的社祀属于一种历史悠久的普遍化的宗教形式,而对神奇光影的迷恋则是一种临时性的即兴崇拜,在笔者看来,或可称作神迹崇拜。神迹不常有,神迹崇拜一般来说是偶然才会发生的。在生成机制上,周原社祀的形成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先认为土地有神灵,但神灵不可见,故而寻觅、加工石材,以一种具体可观的方式来再现土地神,祭祀时,神寄托于此石。至于为何以石代神,《周礼》注家认为原因在于“社既以土为坛,石是土之类”,[4]767也就是说土、石同类相从,祭石亦相当于祭土地神。如此说来,周原石材能够吸引土地神,是因为它与土在成分上的同源性。而陈宝祠的若石之所以能够导致光影现象,并非因为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列维·布留尔指出,历史早期的人们会“把原因和前件混淆起来”,在思维方式上,他们常犯“在这个之后,所以因为这个”的“极普遍的逻辑错误”。在他们的意识中,“表象的连贯性,就是这些表象彼此连结起来的足够保证:更正确地说,他们没有想到连结还需要什么保证”。[11]66据此,仅仅由于时间上的前后关系便认为两个现象有内在关联,这是原始思维的特征。而秦人将原本并不相干的若石与光影现象捆绑在一起,总体来说,思维方面仍未脱离这种原始色彩。反观周原社祀择石祭地,在建祠理念上讲究以类相从,这与依据若石与光影现象的时间相近性而建立陈宝祠相比,无疑是理性化了许多。
周原社祀废于西周晚期,陈宝祠立于春秋早期,然而,后者以石为祭的层次却低于前者。这应当与周、秦社会发展的非同步性有关,因为西周时代的秦人还是周人势力范围内的一个部族,两周之际才受封建国,他们的宗教在建国初期表现出较为浓烈的原始色彩亦属自然。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成熟,秦人对石材的政治功用有了新发明。
众所周知,铜器刻文是商周时期彰显权力极为重要的方式。固然也有在石器上刻字的情形,比如殷墟五号墓出土七十余件石质器物,其中的一件石磬刻“妊冉入石”四字,发掘者认为,妊冉为方国名或人名,原意为“妊冉入贡一件石”。[12]不过,这件石磬似属特例。有学者说“相较于其他种类乐器,磬在殷墟的发现较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见诸正式报道的殷墟随葬石磬,大约在30余个出土单位中发现了40余件”,[13]但见到铭文的仅此一件。况且这件石磬的文字内容只是交代贡品来源,并无强烈的政治宣示意义。至于西周石磬,有学者统计西周时代的石磬纹饰,只有周原召陈乙区遗址编磬刻有夔纹、鳞纹、重环纹,其余十四处发现的磬皆为素面,连纹饰都没有,遑论文字。[14]时代为春秋早期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坑所出编磬,“造型特点为表面光素,无刻纹或图案装饰”。[15]这说明在建国早期,秦人对石磬的处理方式与大传统基本一致。然而,这种情形至迟在春秋晚期发生了改变。凤翔秦公大墓残磬的出土,意味着秦人已将石磬作为值得重视的书写载体。在铭文中,秦公不仅以工整典雅的语言陈述了自己与天子、近祖、远祖、蛮夷、华夏的关系,他还明确告知,自己的统治权因“绍天命”而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其政治宣示的目的一览无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石磬上刻字,并非春秋以来的普遍现象。1961年发掘的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其中13 号墓的时代为“春秋中叶与春秋晚期之际”,墓中出土石磬十件,上面没有文字。[16]1970年,湖北江陵发现二十余件战国时代楚编磬,彩绘石磬的图案特点是“以一至三只凤鸟为主题,其余部位则用羽毛花纹填补和衬托,从而构成为富丽多彩的图案”,但没有文字。[17]即便刻了文字,其内容也与秦公大墓磬铭迥然不同。比如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曾发现一件石磬,其上阴刻铭文“乐室”二字,张龙海认为:“应是东周时期齐国乐府所用之乐器。”[18]所谓“乐室”,只是表明石磬的归属。曾侯乙墓时当战国前期,三十余件石磬上的铭文“内容均为音律、音阶名称和编号”,只是为了对器物作出技术性说明。[19]因此,若说将石磬用作政治宣示的书写载体,开其端者应非秦人莫属。而战国以来秦人陆续创作出石鼓文、诅楚文、秦始皇石刻,都以政治宣示为旨归,可以说延续了自身开创的石材应用模式。
三 秦人以石材进行政治宣示的原因
秦人为何喜欢将政治宣示刻于石材上?回答这个问题,有三个因素需要考虑:其一,人类当中普遍存在着对于石材的神秘主义认知;其二,秦人对石材的神秘认知具有特殊的情感取向;其三,秦人成长的特定政治环境。
首先来看第一个因素。人类学、民族学调查展示了石材在早期人类心目中的神秘功能。有的族群认为,石材寓居着动物的灵魂。比如北美祖尼人将“各种猎物都分为六类,每一类都被认为是附属于一种特定的‘猎兽’。赋有这种特权的每种猎兽都居住在某一个区域内”,“这些猎兽的灵魂居住在一小堆石头中,人们相信这些石头就是它们的外形,而石头有时候也被涂上它们各自特有的颜色”。[20]59还有一些群体认为,石材“具有一种带来雨水的性质,倘若将它们浸入水中或洒上点水,或作其他适当方式的处理就可带来雨水”。比如,“在罗马城外,马尔斯神殿附近保存着一块特别的石头,人们称之为拉庇斯曼纳利斯。干旱时这块石头就被拉进罗马城内,人们认为这样一来雨水将会立刻降临”。[21]131-135早期人类将石材与动物灵魂、降雨气象联系在一起,就理解大自然的思维方式而言,与陈宝祠反映的秦人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只不过与石材相联系的具体对象变换为光影现象而已。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对石材持有神秘认知的群体都会在石材上刻字。神秘认知的情感取向有吉凶之分,对于那些持负面认知的群体而言,刻石的动力恐怕不会很强,而秦人显然对石材秉持一种积极看法。《史记·秦本纪》记载,商周交替之际,秦人祖先“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1]174这个故事虽然无稽,但作为一种观念史的材料,故事本身仍足以表明,在秦人心目中,一个有利于自身族群命运的预言被刻于石棺上是最为合适的。如此,预言将被应验,进而成为本族群现实存在的一种合理化阐释。
若论对石材的情感取向,石棺预言无疑是令秦人欣喜的。而陈宝祠以及种种刻石的出现,也反映出秦人对石材的喜闻乐见,①秦史上也发生过令统治者厌恶的刻石事件。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但这次刻石并非秦人主导,并且在选材时重点似乎不在于是否用石材,更被看重的应当是陨石来自天外的特性。这与周人传统是不一致的。《左传》昭公八年:“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凭焉。不然,民听滥也。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国语·鲁语下》:“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魍魉”。[22]191在东方传统里,石若有言即属灾异,石可为怪,对石这种材料更多地持有负面认知。反观秦人,他们却认为石材带来的是福音。在此心理基础上,秦人沿着自身的文化轨迹,将始现于石磬的政治宣示性石刻发扬光大,是顺理成章的事情。②《周礼》有所谓“嘉石”。如“司救”一职,“凡民之有衺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郑玄注:“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门左,使坐焉,以耻辱之。”又如“大司寇”一职,亦有“以嘉石平罢民”的责任。郑玄注:“嘉石,文石也,树之外朝门左。”贾公彦疏:“云‘嘉石,文石也’者,以其言嘉。‘嘉’,善也。有文乃称‘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罢民思其文理,以改悔自修,树之外朝门左,朝士文也。”揣贾氏之说,“嘉石”似为刻有训诫文字的石头。但此为唐人的理解,未必可靠。否则的话,《周礼》记载“嘉石”,将意味着先秦时期刻字于石属于传统做法。另外,目前固然可见不属于秦人的战国石刻,比如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陵石刻曰:“监罟尤臣公乘得守丘,其齿将曼,敢谒后叔贤者。”意思是“任监罟之职的有罪之臣公乘得看守着陵墓,年龄已长,敬告于后来的贤者”。(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76-77页)但就内容而言,该石刻强调守墓的职责,并非宏大的政治宣示。
政治宣示意味着对某种政治功效的强烈期盼,而这种心态往往受自身所处政治环境的刺激而形成。就秦人政治环境的特殊性来说,秦国建立时,由于长期受周王朝支配,秦人不可能摆脱西周时代刻铭于铜器以彰显地位的惯例,于是便有了秦公簋、秦公镈、不其簋等秦系青铜器物。③有学者即指出,早期秦人的青铜器虽然“注意发展创新属于自己的文化特点”,但发展创新是在“对周文化的继承”基础上实现的。参见高士荣《从秦公器看秦人早期的历史文化》,载《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然而,与东方列国相比,秦国的生存环境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点。首先是长期居于周王朝的西部边陲,这势必导致秦国的发展会更多地受到非华夏族群的影响。有学者在讨论秦汉石雕起源时认为,应当将目光投向“中国的西部和北部”,甚至向更远的“欧亚草原”。[23]247对探求秦人刻石的发生而言,这个看法值得重视。毕竟在古代文明中,欧洲、中亚、北非常以石材作为建筑材料,与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异趣。空间上更近一些,阿尔泰山南麓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克尔木齐文化具有“强烈的自身特点”:用石板构筑方形坟院,坟院内建多座石棺墓,墓上建石冢,墓前立石人。[24]16公元前8世纪的阿尔泰山大石冢,冢堆高15米,直径76米,用30~40厘米大石块垒砌而成,估计有15万~20万立方米堆石。[24]39距今四千年左右的陕北石峁遗址用大量石材垒砌城墙,并且也有石雕出土。类似的西北因素是否构成对秦人用石的引导作用,其间的可能性不宜断然否认。④苏海洋认为,斯基泰-塔加尔与早期秦文化“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只不过由于地理间隔较远,这种联系并非“面对面的直接的文化交往”,而是要经历一个“环环紧扣的类似于接力棒式文化传递过程”。(《论早期秦文化和西戎文化中域外因素传入的途径》,载《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本文所引克尔木齐文化即为其中的一环。
秦人生存环境的第二个特点是起步很晚、强敌环伺。受封前后的秦国正处于由血缘性部族向更高级的封国政治体转变的阶段,相比于立国甚早的齐、晋等国,秦国属后起之秀,在这个新兴的政治体内部,部族社会常见的原始色彩浓烈的文化观念应当还有较多遗留,陈宝祠的建立过程就体现了这一点。春秋时代,秦国在政治上不仅要与东方诸国平起平坐,甚至谋求霸权,可以推想,在这个过程中,当石材有灵的神秘认知与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激烈碰撞时,激发出以石材为介质的政治文化创造,实无足怪。在石磬上刻写政治宣言的做法,可能就是因这样的机制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刻字于石磬可以视为对政治宣示手段的新开拓。
此前,铜器铭文是宣示权威性的最重要的途径,至于传递铭文信息的具体方式,有学者指出,“通常铭文刻于祭器内部,这意味着仪式期间,铭文被容器内的祭品所覆盖。钟铭则刻于钟外,但并不面对仪式的人间参与者”,由此似可推知,“铭文不是直接面对人的眼睛,或是通过人的声音传递的,而是凭着通感体验与莅临的神灵交流”,也就是说,“铭文文本的内容主要是通过馨香、声音传达给神灵”。[25]56如果此论成立,则石磬铭文承载的信息将是通过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传达给神灵。同样是通过声音传递,此前只适用于钟镈之类的金属乐器,而在秦人手中,这种传递方式的适用对象则扩展至石质乐器。
宣示手段由钟镈向石磬的延伸,这还属于工具种类的量的增加,而战国以来的秦人刻石则包含着政治观念的质变。容器、乐器铭文字体较小,位置较隐蔽,显示其主要意图在于与神灵沟通,在这样的情境中,人是被回避的。战国刻石则不同,它以体积较大的整石形态对外展露,既不能盛放祭品以释放馨香,又不能通过敲击而发出乐音。与神灵沟通时所采用的香味、音乐等通感机制,对这种石刻而言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因此,或可推断,战国时代秦人在石材上刻字,宣示的主要对象已不是神灵,①由于文本内容的特殊性,《诅楚文》的信息传达对象似乎仍是神灵。然而,诅文起始部分便说“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愍,告于不显大沈厥湫”,可见,尽管文字刻于石材表面,视觉上清清楚楚,但实际上,对楚人的指责能够上达天听,是通过其他的人、物中介实现的,刻石本身只是文字载体,并不具备神秘功能,它的实体存在仅仅表明一个事实:秦王为打赢战争,想尽了一切办法,其中包括向神乞福。而是政治生活的实际参与者,包括治下的臣民甚至敌国。
那么,是什么原因驱使着秦国统治者转换了石刻的宣示对象呢?应当考虑这样的时代背景:战国时代的历史总基调已非形式上崇礼重信的尊王攘夷,而是诸侯兼并、兵强为雄,加之秦国比东方诸国所受的周人传统影响较小,其极度崇功务实的价值取向,自然使得它对更具现实意义的社会层面投以更多的关注,在此情形下,政治宣示的重心向治理对象及政治对手倾斜,便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四 秦人刻石对汉代历史的影响
秦始皇将以石刻为形式的政治宣示推上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然而,随着秦帝国的二世而亡,这种做法便陷入了尴尬,因为刻辞中一再表达的“刻于金石,以为表经”“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后嗣循业,长承圣治”“请刻此石,垂著仪矩”等愿望,最终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在深刻反思秦政之失的氛围中,汉帝国的统治者不再热衷于高调张扬的巡狩刻石活动,但有一项例外,那就是封禅用石。
《史记·封禅书》记载,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在举行封禅典礼前,“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1]1397司马彪《续汉志》亦记此事。刘昭注引《风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26]3163若据此说,则武帝泰山立石亦有刻字。但《风俗通》所言封禅刻文乃应劭“谨按《尚书》《礼》”等较早经典文献抄录,未必就是武帝刻石文。顾炎武判断,《封禅书》记载“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他认为,“世传为秦始皇立”的“岳顶无字碑”,即“为汉武帝所立也”。②对于顾氏的说法,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后汉书·张纯列传》:“帝乃东巡岱宗,纯从,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据此,姜氏曰:“若无文字,则不当云刻石文矣。”(顾、姜二说俱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7页)但姜氏之说亦有问题。范书《张纯传》原文曰“帝乃东巡岱宗,以纯视御史大夫从,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这里所谓“刻石文”,实为中元元年(56)光武帝封禅文。理由有二:其一,武帝封禅如果有石刻文字的话,本应属于“元封旧仪”的一部分,“刻石文”既与“元封旧仪”并列,所指应非武帝刻石;其二,《续汉志·祭祀上》抄录了很长的光武帝封禅刻石文,但在抄录之前先有这样的表述:“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刻石。文曰……”侍御史正归张纯“视御史大夫”的管辖,该职官既是刻石的监工,此次封禅的刻石文字由其长官上呈皇帝,从逻辑上讲,似乎可能性更大一些。王利器曰“武帝封禅,徒上石立之泰山颠,无文字,即今所传没字碑”,显然“从顾说”。[27]74
如果顾氏之说成立,那么,汉武帝就是立石而不刻石,这个行为颇令人费解。笔者以为,汉武帝的最终目的并非只是立石于泰山之巅,立石应当还是为了刻石。但封禅仪式筹办的过程中可能出了变故。《史记·封禅书》曰:“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祀太一之礼。”“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1]1398可见,向山巅攀登这一段行程,与汉武帝同行者只有一人。需要特别注意司马迁所谓“其事皆禁”的表述,汉武帝为何对泰山之巅的行事如此保密?司马彪认为是汉武帝“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26]3163果真如此的话,以郊祀太一之礼“封泰山下东方”的过程中,也存在礼节上“施用非是”的嫌疑,汉武帝为何又允许“侍中儒者”参与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彪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笔者推测,汉武帝此次封禅的山巅环节或许存在着不便宣扬的缺陷。
汉代皇帝行封禅大典的还有光武帝,就时间而言,光武帝的封禅正月始二月终,汉武帝封禅三月始四月终,两次封禅都是完成于两个月内,如果一切正常的话,两次仪式应当都能圆满举行。但从相关迹象来看,汉武帝封禅的石料准备颇费周折。光武帝在决定举行封禅大典之后,“遂使泰山郡及鲁趣石工”,“取完青石”。封禅队伍抵达山脚后,又遣官员“将工先上山刻石”。封禅当天,光武帝遂与群臣共上山巅举行仪式。然而,据马第伯《封禅仪记》,光武帝封禅时,马第伯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处。入其幕府,观治石。石二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时石也。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26]3167可见,汉武帝封禅用石的运输并不顺利。当五车石留置山下后,重选石材,重新运输,都需要额外的时间,这便有可能导致刻石在封禅吉日到来之前无法完工。就实际效果来说,烂尾刻石还不如无字空石,因此,仓促运上山巅的石材最终没有刻字。但这个结果与武帝原意相悖,当现实与理想发生背离的时候,无字空石就成了政治忌讳,这可能就是汉武帝封泰山之巅而“其事皆禁”的原因。
虽然汉武帝封禅刻石未能完整地实现,但反观“其事皆禁”的处理方式,不难体会到,以刻石的方式铭记自身功业,对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而言,还是颇具吸引力的。而复兴汉室的光武帝亦行封禅刻石,这个事实更是表明,秦人开创的刻石纪功模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它是不世之功的突出表征。
不过,有资格封禅的皇帝毕竟是极少数,就秦刻石传统的历史影响而言,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行为模式有向下传导的趋势。赵超对西汉石刻发展的阶段性有这样的判断:“在西汉早、中期,石刻主要是人物的姓名、年月、建筑材料的记号等简单的刻辞,属于‘物勒工名’的性质。至西汉中、晚期,出现了地界、符契一类的实用石刻。西汉晚期至新莽时代,产生了坟坛、祠堂神位等丧葬用石刻。”总体来说,西汉的文字刻石“还处于刚刚开始实用的幼稚阶段”。[28]86但也有一件例外,河北永年发现的群臣上醻刻石,铭文十五字为“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有学者考订其年代为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29]观其文辞,并非“物勒工名”,亦非符契、丧葬之用,而是记录一次贺寿典礼。从精神实质来讲,与记录政治事件的秦人刻石是一致的。只不过,这场祝寿典礼发生于汉王朝的一个诸侯国内,无论是参与者抑或接受祝福者,均比秦始皇时代歌颂统一功业的君臣集会低一个层次。东汉时代,碑刻盛行,立碑者以及碑刻的纪念对象更是等而下之,涵盖了举主与门生、高官与故吏、宦官与爪牙、父亲与幼子等类型繁多的社会关系。这个非常具有东汉特色的文化现象之所以形成,固然离不开家族勃兴、经学盛行、士大夫政治、外戚专权等极其复杂的现实因素,但若缺少了刻石颂功的传统,仅凭这些因素自身恐不足以使刻碑成风。
五 结语
除了石碑的流行,汉代墓葬建筑的其他部分也大量应用石材。对于这个现象,巫鸿如此描述:“公元前2 世纪至公元1 世纪这段时间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两百年中,中国人发现了一种新的艺术与建筑材料——石头。”“在此之前,庙与墓按惯例均为木结构,汉代以前的墓地也绝少设置石碑或石像。甚至连雄心勃勃的秦始皇也似乎满足于以陶土抟塑兵勇,用青铜铸造马车。但自公元1 世纪,各种各样用于丧葬的纪念性建筑与墓仪,如阙门、碑、祠堂、人兽雕像等,大量采用石材建造。”针对建筑材质的变化,巫氏发出一个疑问:“是什么引发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他的解释是:“石与木相对——石头的坚硬、素朴,特别是坚实持久的自然特性和‘永恒’的概念联系起来;木材则因其脆弱易损的自然属性而与‘暂时’的概念相关。”[30]132-133也就是说,人们因追求“永恒”而在墓葬中大量使用石材。此说诚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墨子·兼爱下》曰:“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31]121所谓“镂于金石”企图使“后世子孙者知之”,显然已点明了刻石的目的在于超越暂时的生命,从而达成永恒的存在,这种意识既然见诸《墨子》一书,那就绝不是公元前2世纪才开始的。而秦人刻石的种种材料更是确定无疑地表明,春秋晚期以来的秦人早已经习惯于将石材的“永恒”特质与国家的政治运作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附记:本文承蒙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汪华龙先生提示重要材料,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