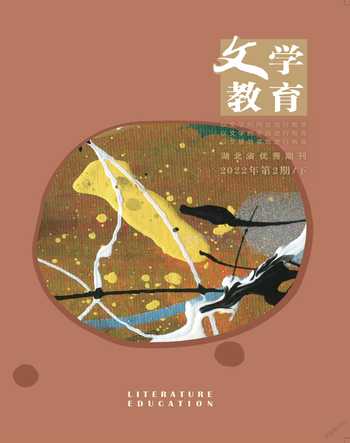《促织》与《变形记》的对比阅读
陈家溪
内容摘要:《变形记(节选)》和《促织》这两篇课文有着同样的“人变虫”主题,这给教师践行“1+X”的阅读理念提供了素材,适合采用对比阅读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深入理解文本,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关键词:人变虫 对比阅读 教学策略
根据2017年版课程标准编写的2019年普通高中语文教材于2020年秋季学期在全国正式投入使用。“1+X”是语文新教材的阅读理念,根据这个理念进行文学作品的比较阅读,可以帮助学生培养思维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视野。在语文必修下册中编者将《促织》和《变形记(节选)》这两篇文章都编入了第14课,而这两篇文章都采用了“人变虫”的主题,是教师尝试实行“1+X”理念的良好素材。本文尝试从对比阅读的角度对两篇文章进行分析,为广大师生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教学参考。
一.对比教学的必要性
1.适应师生教学的需要
高中语文新教材共五册,两本必修,三本选修。新教材在教材编排体系上有很大的创新,以人文主题和学习任务群两条线索来组织单元。首先,教材以人文主题为线索,围绕“理想信念”“文化自信”“责任担当”这三大精神主线,分解出若干人文主题来组合单元和选择内容。在必修上册中涉及的人文主题有:青春的价值、劳动光荣、生命的诗意、我们的家园等等。以第一單元为例,在这种以读写为主的单元里,编者围绕人文主题精选了中外诗歌和小说文本,虽然体裁各异,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精神内涵。从学习任务群来看,同一个任务群可能要通过几个不用的单元来落实,例如第1单元、第3单元和第7单元都属于“文学阅读与写作”学习任务群。这样以人文主题为统领,并且以学习任务群为旨归的教材编排方式,相比较老版的教材而言,可以在打破文体界限的同时聚焦于语文学科知识学习。这种编排体系也要求广大师生们掌握以一篇带多篇的阅读方式,由单一文本的阅读教学走向多文本的阅读教学。
2.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最近发展区”即“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人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维果茨基认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学生现有的水平,指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也就是通过教师指导后所获得的潜力。教师确定的教学内容要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内,让学生有主动阅读作品,发现问题的兴趣,锻炼学生自主分析的能力。《促织》和《变形记》虽然分别为古典文言小说和西方表现主义小说,但两篇文章一个共同的“人变虫”主题,在布置好预习任务基础上,在课堂上提出思考题,能够帮助学生在阅读、讨论中自主探索、自主解决问题,更好的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
3.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语文学科的课程目标之一是鉴赏文学作品,其具体要求为“感受和体验文学作品的语言、形象和情感之美,能欣赏、鉴别和评价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具有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品位。”《促织》和《变形记》这两篇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小说,恰好为广大教师们达成这一教学目标提供了教学材料。通过比较阅读教学,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把握不同文本之间的异同,增进学生对文本的进一步理解,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中外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感受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
二.细读文本,对比分析
作为中外小说的经典作品,虽然二者的成书时间相隔近两百年,作品的艺术特征、主题思想方面和作者的人生经历都有很大的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人变虫”的主题来表达作者对于当时人与社会的关注。
在作品的创作背景方面,蒲松龄生于晚明时期,战乱使得他家道中落,他天资聪颖,19岁就应了童子试,中了秀才,但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屡试不中,在科举这条路上,蒲松龄蹉跎了大半生,直到72岁才破例补为贡生,但这对于年老的他也只是虚名罢了。从蒲松龄的其他作品如《叶生》《王子安》《考弊司》中可以看出他对待科举制是有一个从“满怀希望”到“怨”到“愤恨”再到“嘲讽揭批”的心理变化过程的,而《促织》一文借主人公成名久试不第,最终却凭促织得以升官发财的故事,嘲讽了腐败、形式主义的科举制度,说明封建社会末期科举考试已经逐渐失去它选拔人才的功能。卡夫卡出生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事业有成,但也有粗暴专制的性格,而卡夫卡的母亲则软弱悲观,这让卡夫卡与家人之间的沟通存在着隔膜。作为一个生活在二战时期的犹太人,他又不为当时的社会群体所接纳,可以说“孤独”是他人生的主题,他害怕与人交往,至死他都没有组建家庭,不难看出《变形记》里的格利高尔有卡夫卡自己的影子,无论是小说中格里高尔与家人的关系,还是其他社会交往上,都体现了格里高尔与他人的隔膜,这些实际上也是卡夫卡现实生活的一种投射。
作品艺术特征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方面,受《史记》、《资治通鉴》等传统历史记事文学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对人物的心理描写通常少而简略。蒲松龄在《促织》中准确的把握了人物的心理,并运用白描的手法把它表现出来,例如主人公成名在捉不到促织时是“忧闷欲死”,在经驼背巫指点找到健壮的促织时他又“大喜”,得知促织意外被弄死后则是“如披冰雪”,而当看到儿子尸体时,成名则是“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在发现儿子一息尚存时,他找回了一丝希望,将儿子“喜至榻上”,转眼看到蟋蟀笼中空无一物时,他不由得“气断声吞”,但却不舍得再怪儿子。这一系列的白描手法不仅让小说的语言更加凝练,也生动地描绘了成名由忧到喜,由怒到悲,由绝望到希望的心理过程,使得小说故事更加生动且具有真实感。而西方小说受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思想的影响,重视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以此来反映人物的个性。卡夫卡在《变形记》中的人物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他用了大段的直接心理描写和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心理,让读者能与格里高尔共情,例如下面这一段话:“格利高尔心里清楚,他无论如何不能让协理怀着这种情绪回去,不然的话他在公司里的地位会受到极大的损害。他父母哪里明了这一切?他们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儿子在这家公司干活儿,一辈子生活都无须忧虑的。现在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哪里还管得了将来的事?”在自己变成甲虫的事被协理发现之后,他想到的是自己的父母、工作和前途,因为格里高尔的一家都是靠他支撑,但是格里高尔却没有考虑过自己还能不能从一个大甲虫变回来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段详细的心理描写,我们就很难感受到格里高尔内心的挣扎。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所谓异化是指事物在发展变化中逐步走向对自身的否定。”在小说人物异化的原因上,二者也有很大的差别。《促织》的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在读者不禁为成名一家的命运担忧时,他们总能绝处逢生,最终成名一家因为促织而生活变得优渥:“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这看起来是一个喜剧的结尾,但却给读者一股浓郁的悲凉之情。成名寒窗苦读几十载,学无所成,但最后因为凭借他儿子所变成的促织得到了圣上的欢心,从而中了秀才封了官职,这难道不是对当时科举制度的一种莫大的讽刺吗?成名因为找不到合格的促织几欲寻死,成名的儿子因为不慎弄死了促织而吓得离家出走,跳井自杀。凡此种种莫不是人对于自身价值的否定。成名一家遭遇如此大的灾祸,究其原因,是在当时虫的价值远远大于人的价值。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他们一家人的出路在哪呢?“作者既不能从现实中找到解决矛盾的答案,又不愿让无辜的良民陷于无法摆脱的厄境,所以只好借助于‘志怪’和‘传奇’式的浪漫主义手法,使成子的灵魂化为一只‘轻捷善斗’、‘应节而舞’的促织。”[1]所以这看似离奇的结尾却也有其内在逻辑的合理性。导致这一切的是封建制度对于普通百姓的压迫,小说的开头其实就提醒了读者:“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古语有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个小小爱好,下面的人必定会比他爱好得更厉害,而这些落到老百姓身上就会是沉重的负担,在人的命运全凭上位者喜好支配的社会,人的价值还比不上一只蟋蟀,人异化成虫也就有了它的必然性。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借格里高尔这一角色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物化”对于人性的摧残。格里高尔只是身体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的样子,但依旧保留了人的思维和意识。他为什么会变为甲虫?从社会角度看,联系到卡夫卡所生活的年代,社会巨变,制度更替,底层的人们生活压力巨大,在生活的高压中人都变成了“非人”,人作为人的价值被抹去被物化,卡夫卡则将这种异化呈现在《变形记》中,甲虫有着坚硬的外壳,这使得它的身体善于负重,这正符合处于生活高压下人民的特点。小说采用极其客观、平静的语调来描述人变成大甲虫的经历,仿佛这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也从侧面反映出“异化”的普遍性。从个人角度看,甲虫的壳其实是保护自己的一道屏障,但是这个屏障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将他与世界隔绝了,所以变成甲虫之后的格里高尔无论内心多想和外界沟通,外界都接受不到他的讯息,因为他的说话声在外人听来就是虫鸣。纳博科夫说过:“格里高尔虽然外表虫形,但却更像是个人,而他的亲人则像是外表人形的虫。”格里高尔虽变为了虫形,但他的人性依旧如故,并且以甲虫的第一视角去观察外界,各人的表现统统被格里高尔看在眼里,变成甲虫让格里高尔失去了在家庭中的经济价值,失去了金钱这个维系他与家人关系的纽带,他的家人对他或惧或厌,让格里高尔感受到的是更加深切的独孤与悲哀。作者借格里高尔变为甲虫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人性的更深刻之处。
三.对比阅读,教案设计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当人遭遇不能承受的巨大压力时,往往会在生理或心理上产生变化,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两篇小说是第14课的《促织》和《变形记(节选)》,在这两篇小说里蒲松龄和卡夫卡这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人变虫”这一主题来反映当时人承受的社会重压。今天让我们深入他们的小说世界,去感受,去思考。
(二)分享与交流
1.通过课前的资料收集,同学们应该都对《促织》和《变形记》这两篇小说的时代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都说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文学,你觉得这两篇小说反映的时代分别有怎样的特点呢?
(预设:《促织》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时的老百姓受剥削严重,封建官吏制度腐朽落后,官员们媚上欺下。科举制度走向末期,已经逐渐失去了它原本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功能。《变形记》说的是西方近代工业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物”主宰着一切,人变成了“物”的奴隶,在激烈的生存压力下,人渐渐地丧失了自我,最大限度的压抑自己的感情,人们深受被物化之苦)
2.作为中国古典文言小说和西方表现主义小说的代表,《促织》和《变形记》都很典型的体现了该类型小说的特点。能结合具体段落说说你的发现吗?
(预设:中国古典文言小说语言精练,情节紧凑一波三折,善于制造悬念;西方表现主义小说在内容上表现人与社会的对立、人的孤独和对自我生存价值的怀疑,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
3.刚刚有同学发现两篇小说在描述人物心理时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促织》中的心理描写少而简略,《变形记》则用大量直接的心理描写将人物心理刻画的细致入微,这也是中西方文学的一个典型差异。除了以上的区别,这两篇小说的作者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一个艺术元素,你发现是什么了吗?
(预设:人变成了虫,人的异化)
(三)思考与探索
1.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所谓异化是指事物在发展变化中逐步走向对自身的否定。”作者为什么要设计这些异化情节呢?或者说两篇小说中的人物是怎样走向了对自身的否定呢?
(预设:《促织》中异化情节的作用:①使小说情节更加丰富。②人变成虫才有出路,深化小说的悲剧性。③贴近现实,增加讽刺性。
《变形记》中异化情节的作用《变形记》中异化情节的作用:①用异化将格里高尔打出常规,反映他所承受的重压。②对比反映出家人对他的冷漠。③暗示现代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孤独。)
2.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可以发现,“异化”使得人变成非人,使人作为人的价值被否定了,你觉得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存不存在这种“异化”的现象?
(预设:①在应试教育下,某些地方学生变成了做题机器。②不合理的消费观念将人异化,成为金钱的奴隶③对于权和欲望的追逐使人异化。)
(四)课堂练笔
1.我们这次所学习的《变形记》只是节选,我们不知道格里高尔接下来的命运是什么。假如你是作者,你会让变形成大甲虫的格里高尔迎接什么命运呢?你会如何体现你作品的主题呢?请试着来续写一下《变形记》。
通过对两篇课文的对比阅读,可以让学生对于“人变虫”这个主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對于不同的社会形成初步的认识,同时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相比较单篇课文的教学而言,对比阅读教学的难度更高,需要教师对两篇小说有整体的认知,在认识它们差异的基础上把握好共同点,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学生能在课堂中锻炼比较、分析、综合思维,这让学生的收获也会更大。
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M].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
[2]常青.比较阅读法在高中语文群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探索[J].课程教育研究, 2020(13):97
[3]高尊平.一样化“虫”两样“情” ——《促织》和《变形记》比较赏读[J].语文教学与研究·上,2021(02):157
注 释
[1]张稔穰、李永昶:《聊斋志异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79页。
(作者单位:喀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