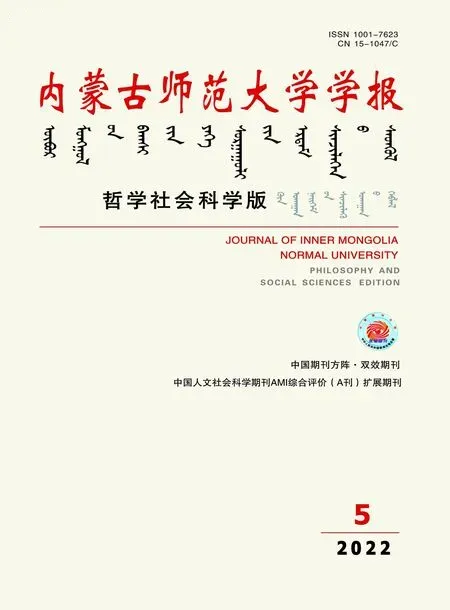阮籍的悲剧意识与精神超越
宋 颖
(北京交通大学 文化教育中心, 北京 100044)
自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将嵇康、阮籍归入“贵无”之学的同一个阶段[1]134,学界论及玄学、美学时就多将二者并谈。嵇康、阮籍都有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倾向和玄学探索,对个体的心灵自由和精神超越有强烈渴求,他们都试图将王弼“无”的精神本体落实到具体人生之中,构建一个以超越性审美为主要特征的诗化人生境界①。
与嵇康相比,阮籍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阮籍在现实生活中有强烈的积极入世之心,这与本来就爱好自然任心的嵇康不同。阮籍少年时“本有济世志”,只是因为“天下多故”,“由是不预世事,遂酣饮为常”[2]899-900。他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本来是建功立业的儒家追求,但因为现实政治太过黑暗,与曹氏关系又比较密切,司马氏掌权后,阮籍经纬天下的理想没有用武之地②,才不得已转向道家的高洁出世的精神。所以,相比可以托于本真生活的嵇康,阮籍更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其他价值的寄托。
第二,在玄学思辨上,阮籍没有像嵇康那样真正构建起一个可以践行的诗化人生境界。他既没有达到王弼以“无”为本体的理论构建高度,也没有像嵇康一样在“心”“性”和“自然”等概念的基础上真正会通儒道两家,只能以老庄为基础追求一种无法行之于现实的纯粹精神超越,所以在价值上寻寻觅觅、反复自苦。因而,阮籍的悲剧意识③更为强烈,他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更为复杂。
第三,阮籍极富于自觉的反思精神。他对司马氏政权无法采取决裂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要保命全身,更深层的原因是他找不到一套可信可行的价值体系。因为在现实中和精神上都没有出路,阮籍难免时时流露出儒家谐俗保身及道家和光同尘的思想,但他又带着对高洁人格的渴求及苛刻的目光对自己时刻进行反思审视。于是,阮籍的文化人格空前复杂。他既高傲又自卑,既脱俗又平庸,既狂放不羁又至谨至慎,既沉醉在清远超逸的精神之游中,又淹没于焦灼孤独的痛苦之河里。强烈的无法弥合的悲剧意识造成了阮籍内心的深度分裂和现实的双重人格,折射出一代士人的精神困境。
当现实中“政统”与“道统”背离时,阮籍这样复杂的文化人格,更能充分彰显深层次的悲剧意识是如何从多个方面作用于士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与嵇康相比,阮籍没有在现实中建构起一个可以践行的诗化人生境界,但其纯粹的精神超越,却为诗化人生境界贡献了“清”“简”“远”“逸”的特点,对后世的文化人格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嵇康的独特影响。
一、阮籍早期调和名教自然的思想
阮籍早期和王弼、嵇康一样,都有过会通儒道④的探讨,他对名教自然的调和,主要表现在《乐论》和《达庄论》⑤中。《乐论》作于正始年间,对儒家的音乐教化作用做了详尽的发挥,可以感受到正始之音力图调和儒道的时代气息,其贡献主要在诗化人生境界的“清”“简”等特征的形成上。《达庄论》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篇以专论形式正面阐述《庄子》理论主旨的文章”[3]29。《达庄论》全文的论述基于庄子的“齐一论”和两汉的“元气说”,借虚构的道家先生与“缙绅”之徒的辩论,阐明了庄子与儒家圣人的区别在于观察世界的角度不同,其根本观念并非对立。
“缙绅”之徒首先以儒家思想是因循天地万物的本来面目而创造的等级秩序为论据,对庄子的齐一万物提出了质疑:
天道贵生,地道贵贞,圣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经,务利高势,恶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死生,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无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为诚是也?(《达庄论》)[4]136-137
道家先生则指出,首先,从概念的角度讲,自然是至大无外的概念,而万物皆属天地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天地就是一物,“自然”就是“天地”的称呼: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达庄论》)[4]139
其次,日月阴阳冰火风雨等等诸物,包括人的身体性情,都是一气变化的不同形态。从总体上看,天地“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所以大小、生死、寿夭的变化都是相对的:
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达庄论》)[4]139-141
所以儒家的思想和庄子的思想并没有根本对立,只是目的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儒家重在建立社会名分法则,使人民有绳墨可循,所以有重视区别个体事物的特点;庄子则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宇宙万物的相同之处。给人的耳目分别立名是为了区分其功能的不同,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身体,而不是为了把耳目手足割裂开来;给万物区分判别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整体,而不是为了区分而区分。但后世浅薄者拘守章句名分,片面夸大纲常名节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为自然本性服务的根本目的,舍本逐末甚至以末害本:
凡耳目之任,名分之施,处官不易司,举奉其身,非以绝手足,裂肢体也。然后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残生害性,还为仇敌,断割肢体,不以为痛;目视色而不顾耳之所闻,耳所听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适性之所安,故疾萌则生意尽,祸乱作则万物残矣。(《达庄论》)[4]143
人们在区分的情况下忘记了区分的初衷,反而把区分出来的“小我”当成全部的目的,为了小我全此害彼,互相争夺,于是出现了种种社会弊端。阮籍也说“儒墨之后,坚白并起”[4]152,认为现实社会之所以是非纷然,是因为人们失去了原始混沌的状态:
故至道之极,混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闻。伏羲氏结绳,神农教耕,逆之者死,顺之者生。又安知贪污之为罚,而贞白之为名乎!使至德之要,无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贰其纪,清净寂寞,空豁以俟,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达庄论》)[4]151
阮籍认为,在“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朝夕失期而昼夜无分,竞逐趋利,舛倚横驰,父子不合,君臣乖离”[4]146的情况下,再去从礼义名节这些表面内容去追求社会之大治,不但不能得其根本,反而使本已混乱的社会增添更多纷纭驰骛的标准,适足起到相反的效果。克己为人只能治标不治本,甚至促使万物更加相异自别。阮籍这一思想没有太大创新,基本是对老子“大道废,有仁义”的理解和展开。
那如何达到社会大治呢?人必须从更高的角度出发,认识到宇宙万物都是一气之变化的“齐一”之理,导引以自然,使其治平:
夫善接人者,导焉而已,无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绣而见,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阙,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来,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发而开之,使自舒之。(《达庄论》)[4]157
这与王弼一样,主张从道家的思想中去寻找儒家之本。但阮籍没有运用自然的概念,没有对自然概念的辨析,而是沿用了道家的万物一气的观点,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一气之盛衰”。这就比王弼简单得多,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深度。但无论如何,都可以看到阮籍调和儒道的鲜明意图,他认为,领会道家万物一体思想的儒者才能得大道之本,以治天下。阮籍甚至进一步否定了纯粹的庄子思想,而希求儒道结合、自然而然的天下大治和人格自足:
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夫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无所毁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离而上下平。兹客今谈而同古,齐说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发不相须也。(《达庄论》)[4]157
显然,这是一个带有鲜明主观色彩的美好世界。与其说它能够落实到现实中,不如说它更具有理想的感召色彩。
从《达庄论》中,我们既能看到庄子“齐一”的思想,又能看到汉代“元气说”的影响。在这里,万物齐一不是复通于“道”,也不是通向本体之“无”,而是万物都是实体的“气”的变化形态。阮籍的“自然”也就区别于道家、王弼乃至嵇康的“自然”,是指由“气”构成的“天地”了。阮籍会通儒道的出发点从王弼的形而上又回到汉代的形而下,既没有本体论的高度,也没有对于人的性情的深入剖析,只是道家思想、汉代“元气说”和儒家思想比较简单的融合。综观阮籍的作品可以看出,相对于王弼、嵇康来讲,阮籍在理论的探索上是薄弱的。王弼从形而上的高度论述了名教自然问题,并在肯定人的自然性情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理想人格,赋予圣人人格以“无”的本体意义;嵇康⑥虽然没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解决名教自然的关系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一问题更复杂化了,但在具体探讨中却从心理和生理的角度拓展了人的性情内涵,提出了“有主于中,以内乐外”的“至人”式理想人格,使得通体洋溢着“冲粹之美”的个体有了在审美化生存状态中实现“自我超越”的生命至境的可能。而无论在形而上之道的构建,还是在形而下的心性探索中,阮籍都没有特殊的创建。
在王弼、嵇康处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无”“道”“性”“情”“心”“神”等,在阮籍的作品中被泛泛使用,没有系统严密的思考。可见,阮籍的会通儒道比较简单,流于表层。阮籍没有达到真正会通儒道的思想高度,也没有形成一套浑融的价值体系,这对于理解阮籍强烈的悲剧意识非常重要。
二、阮籍的悲剧意识与内心分裂的双重人格
阮籍留给后人一个颇费思量的矛盾形象。一方面,他至谨至慎,“喜怒不形于色”[2]899“口不论人过”[5]118;另一方面,却任心放言,“杀父乃可,至杀母乎!”“礼岂为我辈设也!”[2]900一方面,他看不起司马氏与何增等辈的腐败,以及他们倡导的名教的虚伪,有着超迈的人格追求和对精神自由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他却违心出仕,甘处平庸以求自免。阮籍集谨慎小心、随俗浮沉的平庸渺小形象和任诞狂放、洁身自好的高洁宏大形象于一身,显示出双重的人格面貌。
现实行为的双重性源于阮籍内心的分裂,阮籍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思想在其82首五言《咏怀》⑦诗中反映得更为全面细致。它展现了阮籍对价值的多方探讨,又全面反映了他价值追寻失落所带来的强烈悲剧意识,是其在黑暗政治现实中何以有高洁而又不无庸俗的双重性格的最佳注脚。
在《咏怀》诗中首先可以清楚地看到,阮籍的思想资源主要还是儒道两家。他积极在儒道思想中寻找心灵的归宿,力图弥合悲剧意识。但是,由于他无法在深层次上真正会通儒道,所以只能在儒道两家之间摇摆,不断出现价值选择的矛盾。他用对英雄功名的崇尚否定老庄⑧,在《咏怀》诗中怀念少年时的济世理想,追慕建安的时代英风,对现在的碌碌无为感到悔恨,说:“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其三十八》),向往“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其三十九》)的济世理想。同时,他又从现实出发,意识到求名反而会给自身带来伤害,所谓“荧荧桃李花,成蹊将夭伤”(《其四十四》)。
于是,阮籍又用老庄的道和自然来否定儒家骄矜、求名、恪守礼法形式这一套追求:“(儒者)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其六十七》),“烈烈褒贬辞,老氏用长叹”(《其六十》)。他认为在生死无常、万代同一的观照下,功业终归尘土,荣辱宠耀也不值崇尚:“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如何夸毗子,作色怀骄肠”(《其五十三》);“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其十五》)。他甚至否定了儒者的功业追求,“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其三十一》),兴衰成败在宇宙中是瞬间之事,千秋万岁后荣名泯灭,功业无存,只有保身全道最为重要:“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其七十四》);“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其四十二》)。
阮籍时而用对儒家人生规划的眷恋来显示道家理想的虚幻,时而用道家大化流行的自然来消解对功名事功的热衷,这种相互否定在82首《咏怀》诗中交替出现,凸显出贯穿阮籍思想始终的矛盾。这再次证明,尽管阮籍在《乐论》《达庄论》中想要调和儒道,但这一调和流于表面化。在阮籍思想的深处,儒家价值和道家价值基本还是两套分裂对立的价值体系,儒家的济世之志和道家高洁的精神追求共同构成了阮籍文化人格的基本特质,二者却没有在更高的层次或更深的程度上相互融合。
逼仄的现实和儒道之间的摇摆造成了阮籍主导思想的混乱。他忽而说要遗俗独立:“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其四十三》);忽而又要随俗俯仰,与世浮沉:“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其三十四》)。一方面用道家的齐一思想为自己的两栖寻找安慰:“是非得失间,焉足相讥理”(《其五十二》);一方面又对自己和光同尘感到自责、委屈和无奈:“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其五十四》)。这样的反复自苦固然有保命全身的顾虑在:阮籍身处曹魏和司马氏党争的漩涡当中,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现实之下,即便想“不与世事”,以其在名士中的地位和影响,也难以做到全身而退。嵇康就是一个为保全高洁人格而牺牲的例子。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阮籍不得不在自己的原则和司马氏的要求之间走钢丝。欲出不愿,“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其五十九》);欲处不能,“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其三十四》)。这样两难的现实处境足以给人带来很大的精神折磨。
更深层的原因是阮籍高洁的精神追求找不到能在现实中践行的价值寄托。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儒家无可行之道,道家又太脱离现实。缺乏终极价值依归的迷惘感,导致阮籍在现实中不知所从。在《咏怀》诗中阮籍把自己比作有着独立自由人格追求的鸿鹄和玄鹤。鸿鹄、玄鹤虽然“一飞冲青天”(《其二十一》)、“抗身青云中”(《其四十三》),却产生了不知去向何方的困惑:
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其八》)
鸴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摇安可翔,不若栖树枝。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但尔亦自足,用子为追随。(《其四十六》)
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其四十七》)
尽管他在“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其四十一》)的情况下,有着清醒的自觉反思精神,独立于泛泛浮凫、随波逐流的人生之外,却始终找不到现实的价值依托:“荣名”不值得追求,“声色”的感官快乐不足为依恃,同归宇宙大化的“神仙”也是虚幻的,到底什么是终极价值?阮籍如徘徊在高空不胜寒的孤鸟,失去了精神上的归宿。既然如此,有时不若效法“栖树枝”的鸴鸠和燕雀,只把鸣鹤当作一种理想,在精神上相“追随”也就罢了。这种观念落实在阮籍的生活中就体现为矛盾的双重人格,在没有心灵家园的情况下,他的底线是不出卖自己的人格,尽量不同流合污,所以可以在司马氏的统治下依违避就。
秉持着高洁的人格和志向追求,却深陷时时违心的处境不能自拔;现实中找不到一套可行的价值信仰做支撑,却以高度的自觉精神不断地反观自我、自检自省,造成了阮籍内心深度的矛盾和痛苦。反思不但无法解决个体与社会相矛盾的悲剧意识,还进一步加剧了自我内在的分裂。这使得其因两难处境带给自我的创伤更为敏感,价值信仰追寻不得的悲剧意识随之异常强烈。越是痛苦,就越控制不住追寻的强烈愿望,价值悲剧意识促使阮籍发出了一系列急切的追问:
惊风振四野,回云荫堂隅。床帷为谁设?几杖为谁扶?虽非明君子,岂暗桑与榆?世有此聋瞆,芒芒将焉如?(《其五十七》)
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三山招松乔,万世谁与期?存亡有长短,慷慨将焉知?忽忽朝日颓,行行将何之?(《其八十》)
“惊风”的惊心动魄感来自主体的自觉价值警醒,“回云”的阴影重叠在心灵之上,生活中的一切到底为了什么?茫茫然追寻什么?象征理想的佳人不知所踪,求仙问道又难以坐实,忽然之间生命的时光就流逝了,却依然不知“行行将何之”!阮籍还经常用“路途”和“空堂”来表现茫然和无所依归的寥落:“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其五》),“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其七》)。这种追寻没有凭依,是在茫茫的宇宙大化中人对存在根据的孤独追问。
孤鸟和离兽也是阮籍诗中常见的意象:“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其一》);“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其四十八》);“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其十七》)。精神上没有归宿的孤独是无处言说也不知如何言说的:“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其十四》);“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其十六》) 。
就在这种反复不已、无法停止的徘徊彷徨的追寻中,“白日忽西幽”“人生若尘露”(《其三十二》),青春与生命转瞬间就“飘若风尘逝”(《其四十》)了。阮籍诗中常用“忽”字,不但形象地传达出“殷忧令志结,怵愓常若惊”(《其二十四》)的情势瞬变的不安怵惕感,而且鲜明地呈现出“逍遥未终晏,朱晖忽西倾”(《其二十四》)的潜在焦虑。而短暂的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难以长久,相聚必有别离、得到必然失去,更使人产生“盛衰在须臾”(《其二十七》)的汲汲顾景唯恐不及的痛惜。于是: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每一分的时间流逝都使阮籍感到极度不安,因为伴随时间流逝的是容颜的衰老、气力的衰竭、精神的空自消耗和生命的无意义浪费。这使价值自觉者的内心如怀汤火,每一寸时间都因浪费而被无限放大、加倍难熬。没有价值归宿的人生是无意义的,生命的延长也是徒增恻怆:“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其五十五》)更何况生命中的一切都难以持久,都在变化,也只能“悦怿犹今辰,计校在一时”(《其五十五》)了。
《咏怀》诗中充满了不同思想的反复交锋和斗争、不知所从的迷惘、错失美好的焦虑感和无可诉说的孤独感。如前所述,这一悲剧意识从根本上不仅仅来自屈节活命的现实悲剧性存在,还来自自觉心灵对价值归宿的急切渴求和这一渴求的无法实现,这也是古今学者认为阮诗旨趣难求的根本原因之一⑨。
只有从悲剧意识这个深层文化心理动因上进行分析,才能真正理解阮籍的意义所在:阮籍思想的矛盾和反复的反思自苦,不仅仅是遭际沉浮和是非得失的个人情感,而是代表了一个时代士人的普遍价值困境。司马氏的时代,虽然社会动荡相对汉末魏初不再那么剧烈,但随着司马氏夺取政权的斗争开展,名士的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了。司马师东征时征召上党李喜,问李喜说,当年我父亲征召你,你不来,现在为什么来了?李喜说您的父亲是以礼见待,我能以礼进退;而您却以法见绳,我只能畏法而至了[6]21。山涛入仕、向秀失图、嵇康被杀,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专制统治下士人难以自全的处境。
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现实下,王弼调和名教自然的理论彻底失去了社会条件,这也给士人带来了更大的心理创伤。这一悲剧性现实不仅仅超出了阮籍的理性所能把握的范畴,也超出了以阮籍为代表的一代士人的把握范畴。嵇康探索的“有起码的物质生活必需,有朴素的亲情慰藉”“真实可感”[7]49的诗化人生境界,对传统的人生境界有极大的补充意义和现实价值,但这一价值并不能完全取代人的社会责任和价值,也不具备适于所有时代和人的普适性。阮籍的探索没有出路,原因不仅仅在于阮籍的理论抽象能力欠缺,更在于悲剧性的现实生存境遇的确无法解决。阮籍所体现出来的强烈悲剧意识和分裂的人格,正是当时士人重建价值、追求诗化人生境界历程中复杂文化心理的一个典型代表。
在现实生活中,阮籍性格分裂就体现为谨言慎行和放纵任诞的强烈对比。纵观阮籍一生,他对曹氏政权的两次征召均托病辞;而在司马氏治下却做过从事郎中、东平相、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辞了做,做了辞,在保全自己的生命和人格的两难中走钢丝,始终至谨至慎,在对司马氏要求的依违避就中生活。但他又“白眼向人”“穷途而哭”,母亲去世更是喝酒吃肉,公然违背礼法,以至于招致何曾的当面谗毁。与其说他们的放纵任诞是一种对当政的无言反抗,毋宁说这是一代士人在强烈的悲剧意识促动下无法以中庸自处的狂狷心理和行为体现,其中有着很大程度的不得已。所以当他的儿子要学习他的放达时他坚决不允,因为没有文化心理深层的悲剧意识动因,这一切将流于缺乏意义的表演⑩。
总之,阮籍在《咏怀》诗中呈现出来的多重形象非常有意义。他是一个悲观虚无者,因为他是一个对生命有着深沉眷恋的理想者;他是一个与世俯仰者,因为他是一个有着对生存的审视与反思精神的、远远超越现实世俗的高远追求者;他是一个不得已的叛逆者,也是一个在寻寻觅觅的彷徨者。他的悲剧意识,集中反映了社会巨变的时代士人的思想裂变和心路历程。
三、阮籍对纯个体精神境界的追寻
阮籍同嵇康一样,思想在高平陵政变之后发生了激变,从对名教自然的调和走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任自然”在阮籍思想上的表现,主要就是在悲剧意识的促动下,追求一往不返的精神超越。这一精神超越虽然最终没有形成浑融的诗化人生境界,但却为魏晋士人的诗化人生境界追求贡献了“清”“简”“远”“逸”等重要特征。这突出表现在其《大人先生传》和《清思赋》中。
《大人先生传》先是对“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4]163的儒家的君子进行了辛辣的讥讽,认为他们目光短浅;继而认为“抗志显高”[4]173“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4]174的隐士,也没有达到“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4]174的境界,不足为道;至于深达盛衰变化之理,与物推移、宠辱不惊的薪者,也仅仅达到了“虽不及大,庶免小矣”[4]177之境。在对儒者和典型的道家传统形象全部否定后,阮籍提出了“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4]165的“大人先生”,他“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4]162,“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飨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4]171。
显然,大人先生不是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人物,他与自然为一体,与道冥一,与天地并生,泯是非,齐善恶,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这是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人格,具有极强的美学色彩:
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沕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欲纵而仿佛,洸漾而靡拘,细行不足以为毁,圣贤不足以为誉,变化移易,与神明扶。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夫如是则可谓富贵矣。(《大人先生传》)[4]186
这脱离世俗人群,在太始之前和变化之中自由游弋的大人先生,与其说是一个神仙人物,不如说是在想象的自由空间中任意驰骋的阮籍的主体精神和心灵象征。这一个体心灵超迈不羁,向着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无外”“四运”“八隅”进行着不倦的远游,从而奠定了魏晋诗化境界重“远”“逸”的特征。
这一心灵存在环境的主要特征,就是恍兮惚兮:
无存忽合,散而上臻。霍分离荡,漾漾洋洋。飙涌云浮,达于摇光,直驰骛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无为之宫。太初何如?无后无先,莫究其极,谁识其根。邈渺绵绵,乃反复乎大道之所存,莫畅其究,谁晓其根。辟九灵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其万天而通观,浴大始之和风。漂逍遥以远游,遵大路之无穷。遗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径行。超鸿蒙而远迹,左荡莽而无涯,右幽悠而无方,上遥听而无声,下修视而无章。施无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大人先生传》)[4]189
恍兮惚兮显然非常类似老子所说的道。“大道”“无为”的说法,也就是王弼所提倡的“无”。这里说大道“所存”、无为“之宫”,就是强调本体之“无”在个体精神空间中的存在,这个空间是“无”停留的地方,是“无”之“宫室”。
此处大道所存之处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它具有鲜明的审美性,是一种凭借想象构筑的审美境界。从中能看到庄子艺术人生的风致,也能窥见屈原想象的风采,比老子和王弼对“无”的描述增添了很多富有美学意味的特征。
第二,它是一个人的精神空间,可以用“人生境界”概括。阮籍用“左”“右”“上”“下”来形容这个“大道所存”的空间性;但这个空间又不是一个在现实中存在的实体,因为它是“无涯”“无方”“无声”“无有”的“无为之宫”。这种描述与“境界”一词非常切合,境界的本来含义就是指疆界,而人生的精神又是无疆界的,人生“境界”与此处描述的兼具有容性和无限性的特点相契合。
显然,阮籍把“无”充分落实到现实个体的人生境界上。“大人先生”象征着一颗卓尔不群、高洁远迈的心灵,游于一个无疆界的、永恒的自由之境,在这样一个境界中远迈不拘,遗弃世俗。这是精神向外的追寻和远游,这个精神在阮籍处是“神”:
时不若岁,岁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大人先生传》)[4]186
虚形体而轻举兮,精微妙而神丰。(《大人先生传》)[4]181
至人者,不知乃贵,不见乃神,神贵之道存乎内,而万物运于外矣;故天下终而不知其用也。(《大人先生传》)[4]173
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积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达庄论》)[4]141
这个作为“自然之根”的神指的就是人的精神。阮籍和嵇康一样,把精神视作人的主宰,重视“神”的主导作用,只是嵇康重在“栖神”,使精神安于心性而不逐欲而迁,从而于内在的心灵中获得诗化境界;而阮籍重在“神游”,使精神脱离现实俗世,向想象之境体验诗化境界。
如果说《大人先生传》把本体之“无”落实到具有审美意味的个体人生境界中,同时也通过心灵的远游而奠定了这一境界“远”“逸”的特征;《清思赋》则突出了进入这一境界的审美心理特点,同时还确定了“清”在诗化境界中的地位。
《清思赋》是阮籍易为人所忽略的作品,它在《大人先生传》的基础上,更突出地体现了形而上本体与审美诗性精神的关系。开篇就提出“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4]29。真正的美是本体之美,它不是具体感官所能感受的,要想达到这种终极之美,必须先除去日常的生活感受,离开现象界的具象:
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飖恍忽,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皦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清思赋》)[4]31
这种哲学的至高境界体验,显然与审美的心理状态是相通的。这一境界的突出美学特征,就是“清”。摆脱现实的功利追求和欲望,收束情感的驰骛,沉浸到一个物我两忘、冰心玉质、洞彻贯通的状态中去,即是“清”的具体内容。它受庄子“虚静”“物化”的影响,但把这一状态拿出来当作一个重要人生境界做一个专门论述,无论在哲学探讨还是在艺术理论上,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把“焉长灵以遂寂兮,将有歙乎所之。意流荡而改虑兮,心震动而有思。若有来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辞”[4]33与陆机的文赋相比较,更能看出这段话与陆机描述灵感和文思之来的过程是何其相似。“焉长灵以遂寂兮,将有歙乎所之”是“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的过程,“意流荡而改虑兮,心震动而有思”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结果,“若有来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辞”更类似于灵感若即若离、若有若无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完全靠自己把握,必须虚静以待,顺其自然,才能得其要道。不论陆机有否受其启发,但阮籍已经把从老庄到王弼的“无”落实到了审美心理之中,沟通了哲学境界与审美境界,还谈到了体验超越境界所需要的心理条件,这一条件与审美所需相似。这说明魏晋之际的诗化人生境界是哲学与审美境界的互相生成,它是魏晋人士在弥合悲剧意识中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
因此,《清思赋》不仅仅展现了阮籍所追求的并不存在的逍遥世界,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把自由的精神本体“无”与个体审美感受联系起来,提出在审美心理体验中获得精神超越,把这种纯粹的精神超越向诗化人生境界进一步推进了。
此外,阮籍的《乐论》对诗化人生境界的另外两个特征的形成也有所影响。一是重视形式之简:“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4]81二是提倡“和”的精神追求:“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4]100这点与嵇康一致。
虽然学界历来嵇阮并称,他们都把价值追寻从外在社会转向了内在的心灵,转向了对无限、自由、超越的精神的追求,但阮籍有自己的特点和意义。“如果说嵇康侧重于向内的返归,阮籍则更向往向外的远游。”[8]78嵇康的养生论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内在的心性做了更多的探讨,而阮籍的心灵却一直处于对心灵家园追逐不得的动荡之中。在阮籍那里,象征理想价值的佳人总是“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其十九》),那样飘飘渺渺、可思而不可及,所以代表自己心灵精神的大人先生,只能一往不返地奔向审美的空间。
与嵇康相比,阮籍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在《咏怀》诗中所展现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强烈的悲剧意识,使我们透过他可以看到从王弼到支遁的魏晋一代士人,追寻有新内涵的人生境界的文化心理动因,体现出悲剧意识对士人心理建构的重要作用。
第二,在人生境界方面,他对精神自由独有的探索,为诗化人生境界增添了“清”“简”“远”“逸”等审美特质。
魏晋士人精神的两面:无法消解的悲剧意识促动对新的人生境界——诗化人生境界的追求,其产生根源是个体与社会失衡的普遍现实困境。没有现实践行的普适性的纯精神超越不但无法为个体提供价值归宿,反而会促使悲剧意识更深化、文化心理复杂化。尽管逼仄的社会现实情况造成名教思想暂时无法实行,但其思想主干“儒家价值体系”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最契合农业文明的、无法替代的价值体系,真正超越名教是不可能的。因此,继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和缓,继之而起的是郭象对名教自然更深层次的调和。
注 释:
① 此处采用“诗化人生境界”而不用“审美人生境界”,是为了突出魏晋士人人生境界的独特性:审美的境界依赖于对象而存在,是物我合一、我同于物之中的心理体验;而魏晋的诗化境界受玄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其极致境界固然有追求物我玄同、忘我之境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不依赖于物、物我双谴的空冥之境的一面。当然,二者也有共同之处,其生发都依赖于个体情感和感性体验,归宿都是从有限向无限的超越。
② 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详细论述,如宁稼雨:《阮籍:痛苦煎熬中的自我超越》,《文史知识》2020年11期,第40页。
③ “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源于对人的生命有限性的感知。”参见冷成金:《论孔子的内在亲证价值建构思想》,《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29页。悲剧意识就是既有信仰失落、主体意识觉醒、具备自觉精神的人对人生普遍悲剧性生存的文化意识,即对有限与无限、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感性与理性、自由与必然等现实生存中存在的根本矛盾的、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意识。
④ 名教和自然当然并不等同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关于“名教”的定义,可以参见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载《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119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3—405页;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312页;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247页。而“自然”的含义从老庄到王弼到嵇康再到阮籍,也在不断地变化着。但当从总体上概括时,“会通儒道”是一种“调和名教自然”的近义提法。当代学者普遍把阮籍和嵇康放在一起,用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来概括他们共同的思想特征,也是就其总体思想倾向而言的。事实上,在阮籍的作品中从未出现“名教”一词。
⑤ 陈伯君认为,《达庄论》创作时间是甘露四至五年,即259—260年,在高平陵政变之后,表达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参见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王晓毅《阮籍〈达庄论〉与汉魏之际庄学》一文认为,该论创作于正始八至九年,即247—248年,在高平陵政变之前,表达的是调和名教和自然的思想。参见《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考察《达庄论》思想,多调和之说,后一种解释似更合理。
⑥ 嵇康与阮籍一样,也秉承了汉代的“元气说”。《太师箴》:“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明胆论》:“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元气所造。在整体上嵇康也没有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他虽然没有把“心”和“性”提升到本体意义上,却在心性的探讨和从内在心性的超越上开辟了一条新路。
⑦ 本文所引《咏怀》五言诗均出自这82首,下文仅标注以数字为序的诗名,不一一注明出处,以免繁琐。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207—405页。
⑧ 两汉之前学者多“黄老”并称,阮籍做《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后,《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学者始老庄并称。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九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2页。
⑨ 梁钟嵘《诗品》:“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清沈德潜《古诗源》评:“阮公咏怀,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令读者莫求归趣。”王夫之《古诗评选》:“千秋以还无觅脚跟处。”
⑩ “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参见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1年,第900页。如汤用彤先生言:“其放达并非为放达而放达,亦不想得放达之高名,晋之名士,则全异其趣,而流弊多矣。”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