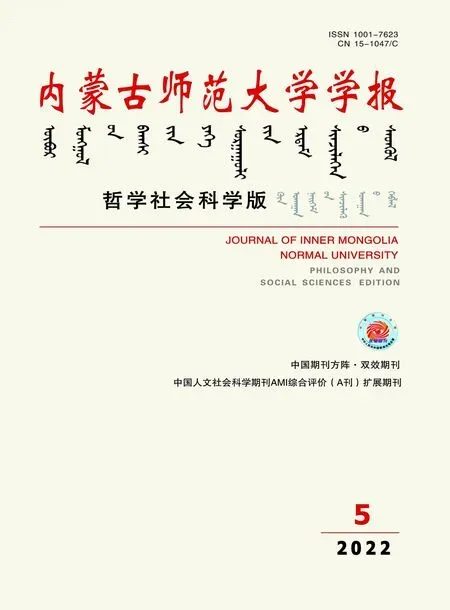编辑眼中的译著
——以马克斯·韦伯的两个演讲为例
安新文
(人民出版社, 北京 100706)
不同文明之间交流,需要翻译做桥梁。但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因为时代及译者的背景等缘故,呈现给读者的文字也是不一样的。很多读者是会挑选版本的。但读者到底需要什么版本,还是需要甄别的。职是之故,这里以马克斯·韦伯的两个演讲版本为例,仅从编辑的角度谈谈译著的版本和注释问题。
据学者苏国勋介绍,马克斯·韦伯的名字第一次在中文世界出现,是1936年郑太朴从德文翻译的《社会经济史》。20世纪40年代,北京大学发现费孝通先生的一篇题为《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佚稿(稿子上面未标明具体写作时间)。苏国勋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研究韦伯思想的中文学术文章。韦伯思想真正在中国受到重视是改革开放伊始的20世纪80年代。1987年,由于晓、陈维纲等人合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北京出版。自此,中国大陆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学科意义上接触韦伯思想的中文著作。其后又有洪天富(1993年)和王容芬(1995年)分别译自德文的《儒教与道教》,以及阎克文译自英文的《经济与社会》(2010年)问世[1]。
韦伯的两个演讲在20世纪80年代前应该没有中文版本,笔者能看到的最早的中文版本是中国台湾地区钱永祥等人翻译的《学术与政治》(1985年)。本文仅比较以下五种版本:第一种是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学者钱永祥等译的《韦伯作品集Ⅰ 学术与政治》(台湾1985年版的修订版,以下简称钱永祥版或者钱版),第二种是199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冯克利翻译的《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以下简称冯克利版或者冯版),第三种是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容芬翻译的《伦理之业:马克斯·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的修改版,以下简称王容芬版),第四种是201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李猛编的《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以下简称李猛版),第五种是202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吕叔君翻译的《马克斯·韦伯全集(第17卷)·以学术为业(1917、1919)以政治为业(1919)》(以下简称吕叔君版或者吕版)。
一、版本
从德文直接翻译韦伯原著,中国大陆起步较晚,最早要算冯克利的译本。但在解释这个译本前,需先介绍台湾地区钱永祥的译本,因为钱永祥版出版在前。钱永祥等人译①的《韦伯作品集Ⅰ 学术与政治》(所用母本是H.H.Gerth & C.Wright Mills,trans.& eds.,FromMaxWeber:EssaysinSociology,New York,1946年,即格特和米尔斯本)于1985年在台湾允晨文化实业公司出版。当时这个本子在大陆不容易买到。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了这个版本,在内容上比原版仅多了一个序。
冯克利版的母本有二,《以学术为业》是出自比格特和米尔斯本更晚(1989年)的R.C.Speirs之手的英译本,《以政治为业》是E.Matthews的英文摘编本。冯克利版最早的出版时间是1998年,一直再版至今,多次重印。从母本的出版年看,钱版和冯版的母本出版相差了40年。一个版本离韦伯的时代更近,一个版本离我们的时代更近。冯克利在翻译过程中,也参考了王容芬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译本,以及当时李康已经译出但未刊印的《以学术为业》[2]16,即后来李猛版里李康翻译的《以学术为业》。
钱永祥和冯克利都是粗通德文,但精通英文。为了译文的准确,钱永祥曾请专人对核日译版、法译版[3]153,2004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该书时,还参考了王容芬译本②;其中《以政治为业》还与德文原文对勘[3]153,193。而冯克利是把德文原文放在手边,“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将韦伯逝世不久出版的这两篇演说德文版小册子复印回家,以便在一些语句及概念的要害或疑惑处可以时时参酌”[2]14。
大陆第一个把韦伯的两篇演讲直接从德文翻译过来的是学德语出身的王容芬。王容芬使用的母本是联邦德国莫尔出版社1985年重新审阅的第6版《科学理论论文集》中的《以学术为业》和1980年增订索引第4版《政治论文集》中的《以政治为业》。2008年再版③时提到,“中译本再版修订时参考了1992年德文版《马克斯·韦伯全集》第17卷(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4]再版译序第Ⅰ页,此即吕叔君译本的母本。
李猛版中李康所译《科学作为天职》(即《以学术为业》)的版本没有译者说明,从段落看,和吕叔君版完全一致,边码位置也完全一致。李康译文前引用的德文版的封面,和吕叔君版里所引德版原文的封面也一致[5]6。冯克利在他的译本中提到参考了李康翻译未刊的《以学术为业》[2]16,因为冯克利版最早在1998年出版,也就是说,早于1998年,李康已经翻译了《以学术为业》。从李康的履历查阅,李康应该没有德文背景④。仅从译文看,李康的母本无从判断。
从时间上看,钱永祥版最早,出版于1985年,冯克利版出版于1998年,和钱版相隔十几年。其后是李猛版,出版于2017年。这三个版本都是研究性质的,里面除了韦伯的演讲(李猛版只有一个演讲),还有多篇研究韦伯的文章。因为有了时间跨度,这三个版本的研究性文章实际上代表了截至出版年中外学术界对韦伯关于学术和政治主题研究的最新成果。版本的递进也标示着学术进步的脚印。
王容芬版和吕叔君版均是从德文翻译的版本。王容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把韦伯介绍给读者的人,其译本第一版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于1988年出版,比钱永祥在台湾地区1985年的版本仅晚了3年。王容芬版里收录了她自己的两篇研究性文章《联邦德国的韦伯复兴运动》和《韦伯小传》⑤,是其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该书再版时已经是2008年,那时候《马克斯·韦伯全集》德文版已经出版第一部分(共22卷),王容芬版再版时就参考了这个德文全集的第17卷,即吕叔君的母本。所不同的是,王容芬仅仅是按照全集“校订”[4]出版说明了自己的译文,并没有按照全集的体例翻译。
吕叔君版的母本是历史上首次以历史批判版的形式出版的[6]前言第1页。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本在手,可以了解韦伯这两篇演讲方方面面的情况。比如在书名上,就与其他四个版本不太一样。《马克斯·韦伯全集(第17卷)·以学术为业(1917、1919)以政治为业(1919)》这个书名,在母版里是这样解释的:“本卷还收录了马克斯·韦伯为其《以政治为业》的演讲草拟的提示词手稿,以及一篇发表于1917年的关于韦伯《以学术为业》的演讲的报纸报道,该报道包含了一些有关此次演讲的原始面目的附加信息。我们在本卷《以学术为业》的标题下之所以标示1917、1919年,也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一实际情况。”[6]前言第1页还有一个情况,“韦伯在写作这两篇文章时放弃了标注参考文献的惯常做法,因此对其做评注成为一种艰难的尝试。韦伯的论述中所援引的内容是开放性的,但是更多又带有隐蔽性。他常常援引自己的著作,而且其所涉及的知识范围也已与我们今日有别。除此之外,其中的内容所涉及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些观点意见和事情,今日对其再做准确的解释已不太可能”[6]前言第2页。韦伯原文的注释问题,其实所有翻译韦伯这两篇演讲的译者都会遇到,也曾经给钱永祥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以至于他在多年后,还写文章回忆编译这本书的艰辛⑥。在中国学者研究韦伯的同时,德国对韦伯全集的编辑工作也在开展。这个全集的第一部分共22卷于1992年出版。这个历史批判版对全世界研究韦伯的学者来说都是个福音。如果这个全集考证版在20世纪80年代前就出版的话,也许钱永祥、冯克利等版本就不会出现了。因为韦伯全集在考证方面细致入微,译者不需要再像钱永祥一样做很多考证工作。当然,全集体例虽然非常严谨,但也非常复杂,翻译并不容易。吃透韦伯的意思,把这些结构消化了,工作量非常巨大。这就是一本中文字数30多万字的译著,经历了8年[6]315之久的原因。
版本的不同,也可以从词汇的翻译上见出一点端倪,因为不同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及词语的内涵和外延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当一种语言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很多表达是没有现成对等词汇的,因此有意译和死译等区别。假如再以这另一种语言的译文为基础翻译成第三种语言,译者就要分外小心了,这也是钱永祥在编译时找各种版本校译的原因,也是冯克利在翻译时,时刻对照德文版的缘故。在编辑吕叔君这个译本的时候,有时候会拿别的译本来参考一下,还是能感受到一些不同。因为无法把那些版本的原词都找出来,笔者这里就仅仅列举一个句子,有心的读者或者研究韦伯的学人可以参照译者和编译者的说明,应该会有一些感悟。
Daß man schließ|lich in naivem Optimismus die Wissenschaft, das heiüt: die auf sie gegründete Technik der Beherrschung des Lebens, als Weg zum Glück gefeiert hat-dies darf ich wohl,nach Nietzsches vernichtender Kritik an jenen “letztenMenschen”, die“das Glück erfunden haben”,ganz beiseite lassen.[7]92
两个译自英文的版本是这样表达的:
经过尼采对那些发现了幸福的“终极之人”加以毁灭性的批评之后,我对此完全不用费词了[3]173。
在尼采对那些发明了幸福的“末代人”做出毁灭性批判之后……我已无需再费口舌了[2]33。
两个译自德文的版本的表达:
最后,人们又怀着天真的乐观,把科学,也就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把握生活的技术,作为通往幸福之路庆祝了一番——对此,我大概不必费口舌了,因为尼采早已对那些发现了幸福的“终极之人”进行了致命的批判[4]20。
至于还有人满怀天真的乐观态度将科学,也就是说,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控制生活的技术,歌颂为通往幸福之路,我也许对此种论调完全不必再浪费笔墨了,因为尼采早已对那些“发明了幸福”的“末人”进行过毁灭性的批判[6]94。
李康是这样翻译的:
最后,还有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相信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能够支配我们的生活,赞美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除了占着大学教席和编辑部的几个长不大的孩子,现在谁还信这个?[5]29
吕叔君是这样解释他把“letzten Menschen”译为“末人”的原因,他认为,这个词见于尼采所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意指一种无希望﹑无创造﹑平庸﹑浅陋渺小的人。“末人”也指和超人相反的病态的人群,信奉奴隶道德,限制了超人的人。
二、注释
一本书的注释,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本书理论的深度或者研究的深度。处理注释,是编辑工作中的硬功夫。关于各种书稿注释的处理方式,实可以写一本著作的。这里我们简要来看看韦伯的两个演讲中译本里注释的处理。
(一)注释形式
先看两个译自英文的版本。
钱永祥版的注释有五种形式。
第一种是文前说明。钱版是一个综合性集子,里面还有多篇研究性的文章,编者采用文前说明的方式厘清各类文字的性质。比如,第一篇《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文前,交代了本篇译稿所采用的母本、译者、参考了哪些译本,以及段落的处理方式[3]153-154。这个文前文字,在很多版本里都处理成页下注的形式,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注释。
第二种是日文注。在吕叔君版里,德文版编者提到,韦伯的原文是没有注释的[6]前言第2页。因此,各个译本的注释都是译者在翻译中做的译者注。钱版里的这个日文注,就是从日译本里拿来的注释。文前文字说,“张先生还帮我们译出了日文译本的若干译注”[3]154(就是说,没有把日文注释全拿来)。比如第160页的“不死之士”的注释、第163页关于梅耶尔的注释等。
第三种是德文注,即从德文版中拿来的注释。这个方式的注释很少。比如第155页注释1。
第四种是互注。韦伯全集的编者在前言中说:“韦伯的论述中所援引的内容是开放性的,但是更多又带有隐蔽性。他常常援引自己的著作。”[6]前言第2页引用自己的著作,就会在注释里产生互注形式,即“参见本书第几页注释”,钱永祥版第180页的注释1就是这样的。
第五种是译者的注释,即译者注(在本书“译例”第4条有说明)。译者注里,除了介绍人名、一些话语的出处,还有一些探究性的注释。比如,第168页的注释对Entzauberung der Welt这个德文词汇,探讨了词义的来源(日文译为“解除魔咒”),指出英文译者会错意的意思。《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篇演讲的注释一共30个,字数大约 2 780 多字(折算成中文)。
冯克利译本的注释,从《以学术为业》这一篇来看,方式只有一种,就是译者注。注释一共26个,字数 3 000 字左右(折算成中文)。其中,第一个注释非常长,类似钱版的文前说明,介绍了为什么要把这个演讲的题目定为《以学术为业》,分析了德语词汇Wissenschaft、Beruf,有译者序的功能。后面的注释和钱版的译者注在性质上无大差异。
再看李猛版李康译文的注释。
李康所译《以学术为业》的注释一共有32个,他译文第一个注释里说明“下文如无注明,均为中译者注”[5]3,其中,第12—13页的注释应该属于探究性注释,别的都是一般性的译者注,和钱版、冯版一样,注释文字大约有 2 500 字左右(折算成中文)。
最后看两个从德文翻译的版本。
还以《以政治为业》为例。王容芬本的注释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译者注。注释都放在页下,后面标注“译者”。这个标注是非常规范的。因为注释分很多种,有的是原文注,有的是编者注,有的是编辑注,有的是版本差别注,还有的原文注释就不止一种,因此,标明“译者”二字,是编辑思路清晰的体现,也可以让读者更好地厘清各种注释的关系[4]第3页注释。王容芬的注文内容和钱永祥、冯克利的译者注类型基本相同。第二个方式没有标明注释出处,猜想应该是德文版编者注[4]第30页注释。这篇演讲的注释一共有31个,其中译者注29个。这些注释大都比较短小,没有说明和探究性注释(可能因为王容芬版里有两篇研究性的文章),比如像冯克利版第50—51页一样的注释。
吕叔君版的注释。《以学术为业》篇(吕叔君版十个部分中的一部分)的注释一共有66个,1 3400多字(折算成中文),全部是母版的注释。与前几个版本相比,吕叔君版页下注释里没有人物注(文后有专门的人物索引),而前几个版本的人物注释占比较大。可以这样给吕版注释分类:
一是出自《圣经》、柏拉图著作、尼采著作等名著的注释。这样的注释和前面的版本有重复,也是重复率最高的,但吕叔君版更细致。
二是互释性的注释。比如第105页注释53,就是文内别处出现的注释。在钱永祥版里有互释性注释,其他三本基本没有。
三是考据性注释。比如第95页注释38,解释“无前提的科学”时,就追溯了西奥多·蒙森于1901年写的一篇文章。第93页解释斯瓦莫丹的名言时,追溯到他发表于1752年的《自然经》。从这些考据注释中,不仅可以看出韦伯学识渊博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它的体量也显示出德文编者几乎穷尽了韦伯两篇演讲所可考证的方方面面。
看着这恣意汪洋般的注释,感受到历史批判版德文编者巨大的工作量。体量巨大的考证和注释,再加上围绕这两篇演讲的导言和编辑报告,以及为了更好地呈现内容而编写的“符号与缩写”“人物索引”“人名索引”“主题索引”“页码对照表”,以及“《马克斯·韦伯全集》第一部分(著作与演讲)的结构与编辑规则”等文字,构建了一个严谨的编辑体系,照顾到了书中需要说明的方方面面,确实值得所有在职的编辑学习。
(二)注释结构
上面介绍的是单篇的注释问题,但全书的注释结构是个非常有意义的需要说明的问题。这里打个比方,建大楼是作者的事,但如何在大楼里方便地工作、办事、玩耍就是编辑的事(这个编,不仅是指编辑,也指图书的编者)。
一般的学术著作,作者会针对文中的引文、名词、事件、人物在文下给出解释,方式是每个页码的注码都从1开始。也有的注释采取文后注的形式,即一篇文字结束后,这篇文字的所有的注释集中在文后,注码从1到尾。还有一些注释采取文内夹注的形式,就是一句话后面加括号,把出处或者需要说明的情况交代一下。夹注一般出现在古典文献特别多的著作里,比如引述四书五经等著作,因为一段里一句一引,采取文下注就特别繁琐。译著采用这种形式一般是因为在正文中,原作者丢了信息或者有失误的情况,译者发现需要纠正或者补充,这时候一般会采用类似夹注的方式,即用方括号的形式放在相应的位置。这样的夹注一般要在译例里说明。比如钱版[3]11和吕版[6]“符号与缩写”第4页都有这种说明。
本文所列的五种版本里,编辑痕迹⑦最强的有两种,钱永祥版和吕叔君版。编辑痕迹大概有几种,一是文前文字,二是译例,三是注释,四是后记。钱永祥版有序,交代了书的结构问题;起注释作用的有三部分,一是页下注,二是文前文字,钱版还有译例。这里主要解析一本译著里注释的呼应问题。
钱永祥版里,除了两篇演讲,还有研究韦伯的文章7篇,总共9篇,分成三个部分。这些文章的注释有互用和呼应问题。如何处理清楚这些问题,就像如何走出迷宫一样,需要一定的编辑技巧。
举个例子,钱版里有一篇文章《韦伯小传》⑤。在此篇的文前文字里,编译者提到:
Gerth和Mills(即本书母本的编者)在引《韦伯传》的时候,根据的是1926年的德文版,在译文中,我们将这些引注全部改为1975年英文版的页数。……另外,我们也添加了一些引注和批注[3]3-4。
需要对这段话做个说明。第一,《韦伯小传》的原文是德文;第二,钱永祥版所依据的是Gerth和Mills的英文版,而Gerth和Mills翻译《韦伯小传》依据的是1926年的德文版,注释也是1926年版本的信息;第三,此文的英文版还不止Gerth和Mills这一个;第四,钱版编译时也有修订,如“根据玛丽安娜·韦伯的《韦伯传》,对原文中关于人物、事件、日期及文字的若干错误或混淆之处,做了一些修订”[3]3;第五,钱版编译时增加了一些引注和批注。
《韦伯小传》的注释有71个。这71个注码,是从此文第一页第一个注释1码开始,到此篇文章结束终止。钱版的9篇文章,都采用这种顺码的方式。顺码的优点是可以在不同的文章间互相引用和呼应。比如,如果别的文章出现和这个文章相关的注释或者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见某文第几个注释”。但这对编辑来说是一个非常耗神的工作,因为涉及多篇文章来参考这一个注释,出错的几率就会非常高。因为一个码错漏,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顺码的编辑方式如果完全正确的话,会给读者提供阅读上的方便。《韦伯小传》这71个注释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原注,有5个;一类是《韦伯传》的信息,有51个,其中补充和纠正信息的有3个;最后一类是编译者增加的引注、批注和修订的注释,共15个。其中,与别的部分有呼应的注释有3个[3]第26页注释44、45、46,分别涉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即《以政治为业》)和《韦伯的政治关怀》两篇文章。
这里不管怎么罗列,一般读者都不会理会这其中的奥秘,因为大多数读者只读文字本身,只有研究这个领域的人,才会有所关注,因此懂的人非常少。为了明白表达,可以打个比方。比如某人买了一套西服(上衣和裤子),但想穿出来好看,还要搭配内衣、配饰和鞋子。但这个内衣、配饰和鞋子,和这一套西服不是一个品牌。钱版的《韦伯小传》就是这样的产物。依英文翻译而来,用的是德文的注释,还对原文的人物、事件等根据另一篇德文做了修订。这其实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译著了,因为译什么不译什么,补充什么舍掉什么,都是依据于译者的判断。取舍,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纯粹的译者,如果不做相关的研究,还真做不了这个工作。当然,取的内容是否好,就得读者来评判了。这种形式的译著在国内国外都是比较常见的。
再举个例子。钱版中的《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韦伯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沃尔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即吕叔君版的母本——韦伯全集的编者之一。钱永祥在增订版序中说:
施路赫特(吕版译为:施鲁赫特)这篇文章对韦伯两篇演讲的论证结构有极为细腻深入的分析和重建,并取韦伯的观点与晚近社会理论关于知识与政治实践的一些新反省对观,可望对读者提供较多的帮助[3]增订版序,8-9。
这篇文章也是由英文转译而来。钱永祥把这篇文章放在两个演讲的前面,类似导论的角色,在前后文呼应上,有着特殊的作用。表现在注释上,这篇文章一共有137个注释,其中,涉及《以学术为业》篇的有24个,涉及《以政治为业》篇的有18个,涉及本书中别的篇目或者别的注释的有10个。其余的按序中所言,都是译者注。从这几十个和别的篇目呼应的注释来看,整理和编辑是个大工程。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版本是在台湾版基础上的增订版,文中涉及呼应注释的,都因为版式和页码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比如此文第35个注释“《学术》,p.185”[3]118,在第一版中,这个页码肯定不是第185页。人工手动的工作,是令人崩溃的。但是,吕叔君版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超市、农贸市场等主要采样地点和不同生产季节,餐桌酱油和烹调酱油中菌落总数的污染水平无统计学差异,分析原因,应该是研究对象为预包装且样品一般为高盐高渗透压,流通过程受环境影响较小,常见细菌在酱油的高盐环境下不易增殖且呈下降趋势[3]。主要产区和不同采样地区菌落总数的污染存在差异,应该与不同企业加工过程中卫生质量的控制效果存在差距,预包装产品的销售范围区域差别较大有关。采自农村的烹调酱油中菌落总数≥10 cfu/mL的样品比例(57.03%)高于城市(49.68%),可能与城市和农村地区该类产品的品牌分布有关[4]。
吕叔君版庞大的注释,完全覆盖了别的版本的注释,也就是说,因为吕叔君版的母本是个考证版,给译者吕叔君没有留下考据的空间,但并不是说,照搬原版的注释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图书编辑需要以善巧的方式来安排各类注释的出现。
第一,严格的边码,即在译本的页边空标注德文原版的页码。本文列举的书里,李康译文是有边码的,吕叔君版里除了后记,所有文字都标注了边码。其实,现在出版社出版译著,为了严谨起见,是要求注明边码的,这样便于读者查阅原文。
第二,采用顺码形式。吕叔君版分十个部分(原著),加上后记,共十一个部分。主体部分(即《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注释都采取顺码方式,所采用的互注方式是“参见本书第几页”⑧或者“本书第几页注释第几”[6]第182页注释36。这个“第几页”,指的就是译著的边码,而“本书”并非指此中译本,而是德文原著,也就是说,只要提到“本书第几页”,就是指德文版原著第几页,即边码所示。这个版本中,在第一次出现“本书第几页”的地方,加了一个编者注“指本书边码。下同。——编者”[6]第4页注释1。这个编者注解决了整本书注释的页码问题,而且不会因为改版而造成重新手动改页码的现象,比如钱版。
第三,图书结构不变。因为注释的问题,也使吕叔君版在结构上不能少译或者多译。和吕叔君版相比,钱版的篇目,本来译自英文,又参考了日译本、法译本和德文原文,因此,虽然图书的编译者意在使译文的准确性和关于韦伯的研究性文章更具有代表性,但也使这个本子变得不纯粹。吕叔君版的母本本身就是个严谨的考证版,编辑结构非常严谨,假如他少译一部分,有些注释就会对不上号。比如,第124页注释61和第125页的几个注释,都提到了韦伯手迹。假如本书不收录这些手迹(因为不翻译这些手迹也没关系),这些注释将没有着落,因为整本书有太多互释性的注释,书中别处所有提到手迹的注释,要不改动内容,要不调整注释的码数。这对编辑来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而且,稍不留神就会出错。
以《以政治为业》篇为例。韦伯做这个演讲的时候,并不是写好的成稿,而是写了个提纲似的提示词,拿了几张纸片就去演讲了[6]139-156。现在我们看到的《以政治为业》的演讲稿,是韦伯依据现场的速记稿进一步修改而成的。德文版的编者在编辑的时候,把提示词标注在了文旁⑨,也就是说,吕叔君版里的《以政治为业》这部分的注释是多重的,起码包括四个层次:提示词(放在和边码同一个位置,与页下注做了区分)、页下注、译者注[6]161、互释信息。比如,第200页注释80里面提到“由韦伯的提示词手稿我们得知”。假如不收入这些提示词,会使这个版本出现编辑失误。
结构上,全部翻译像韦伯全集这样的考证版,不仅使注释码容易编辑,也使对韦伯感兴趣的研究者能看到韦伯著作的原貌。因此,吕叔君版完全按照母本的结构整体翻译出来,就是中外编辑理念的完美贯彻。
注 释:
① 本文引用的五个版本,钱永祥既是译者也是编者,李猛是编者,但这个编不是出版社编辑意义上的编辑,他们是作者角色。行文中,提到这两位作者时,会用“编译”两个字作为权宜表述,以区分出版社编辑业务中编辑的意思。
③ 马克斯·韦伯《伦理之业:马克斯·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最新修订版),王容芬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出版说明”。王容芬译本初版是1988年,本文所引是再版的2008年版。
④ 李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⑤ 和钱永祥版里的《韦伯小传》不是一回事。这一篇是王容芬自己的研究成果。
⑥ 钱永祥写了一篇题为《在纵欲与虚无之上:回顾韦伯的<学术与政治>》的文章,回忆这段编译经历和体会。
⑦ 这里的编辑痕迹,钱永祥版指作为编译者的钱永祥所做的编译工作和图书的责任编辑所做的工作,吕叔君版指德文版编辑和中译本的编辑二者的工作。因为这二者工作高度契合,一本书才能呈现和谐的局面。
⑧ 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全集(第17卷)·以学术为业(1917、1919 )以政治为业(1919 )》,吕叔君译, 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注释1,是本书出现的第一个此类注释。
⑨ 比如吕叔君版第208页的提示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