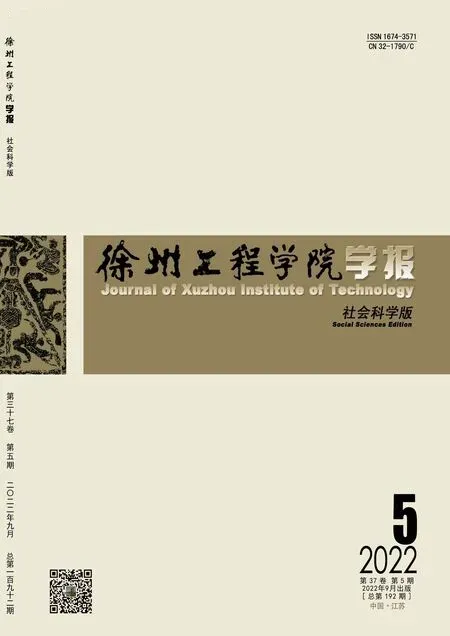实践民俗学视野中的“民”与“俗”
阎莉,孙鸣璐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在社会文化研究中,关于民俗学的研究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在这一研究历程中,民俗学经历了多次调整和改变,兴起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众多学者也各自站在自身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这门学科不同的阐释。在民俗学最近的研究中,实践民俗学异军突起,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民俗学学者关注的焦点和探讨的热门话题,迎来了民俗学的一次大转向,即民俗学的实践转向。这一次转向给民俗学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促使学者从实践视野中重新思考和界定何谓“民”、何谓“俗”,民与俗是如何联结在一起,如何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显明民俗固有的本质特征。如此的转向促使研究者不再把民俗看作静态的研究对象,而是看作动态的展现过程。
一、围绕“民”显示自身的“俗”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实践民俗学是在民俗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民俗学(Folk-lore)最早由英国的威廉·汤姆首次提出。但是自创立之初到现在,民俗学这一术语在学界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其外延和内涵在不断改变着。从字面意思来看,英语词组“Folk-lore”指的是民间知识,就是有关民众习俗、文化的知识和习惯。从最早的名词创造来看,民俗学是一个合成词,是由“民”和“俗”两部分组成,这里的俗可以被理解为习惯、风俗,但这些习惯、风俗在成为知识之前最初是由民发起的,是透过民成就的。由此决定了俗离不开民,离开民的俗只能成为一种知识和研究对象而不能成为反映民的思维观念、文化事项的通道。如此一来,“俗”与“民”就密切联系在一起了,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民俗一词进而产生,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对象和领域。
实践民俗学的转向首先是从“民”与“俗”的理解中开始的。实践民俗学在创立之初将自身的目的和任务确定为对过往习以为常的概念、事件、理论和方法提出怀疑和质疑,反思民俗学过往仅仅注重对事象和传承研究的不足和欠缺,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重新考察和界定民俗学关注的基本概念。基于此,实践民俗学对“民”与“俗”重新加以思考,对民俗学涉及的两个重要概念给出重新界定和评价。为此,实践民俗学将自身的学术实践定位于如何看待“俗”中之“民”,和“民”中之“俗”的问题,将民俗学置于民众的生活实践中加以考察,进而使民俗学脱离过往作为知识的研究局限进入关注参与实践过程的主体,就是民。具体而言,实践民俗学看重将研究视角回归至民众,以具体参与民俗建构的“民”的视角和立场来看待“俗”,重新发现俗构建中民众的历史。以周全明对罗山皮影戏研究为例,实践民俗学不再仅仅着眼于皮影戏这一文化事象和现象,而是将“人”作为讨论和关注焦点,探究“生活的艺人”怎样显明出来,以及“艺人的生活”怎样展开。显然,这种研究视角已经转向“以俗观人”,就是透过对具体的俗的考察来显明形成这些俗的人的特征。同时,“以人观俗”的维度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人们可以站在参与者的角度具体探究俗是如何形成和展开。在两个维度的探究中,以俗观人是民俗学诞生初期就采用的研究方法,属于民俗学的常规与经典的研究方式,实践民俗学的研究者将其看作经验实证研究范式,注重对民俗事实的研究。而以人观俗的研究需要还原艺人的先验意识与实践过程,是实践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框架[1]。
在实践民俗学的研究框架中,作为“俗”发起者和创造者,“民”是以实践主体的身份出现的。民不再是配合俗展开的静态的对象,也不再是同质的、单一的,而是流动的、异质的、多元的,俗围绕着民而形成,民俗在特定的语境和实践场域中被建构起来,而且是带着实践主体特定的意向被生成。按照实践民俗学的倡导者和理论建构者吕微的观点,实践民俗学将“民”理解为大写的“人”,这个“人”既是俗建构的具体参与者,也是具有抽象意义的自由的人。按照康德先验论的观点,人的本质显明为自由,由此,自由被看作是人的天赋权利,是伴随着人而出现的权利。这种透过自由标志的权利使人在自身的生存和生活中可以凭着对外界事物的理解自由地赋予所接触的事物以意义,使世界和自身的生活习俗带上文化的色彩和价值,被提升为民众的习俗,民俗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形成和保存乃至持续。从这种意义而言,民俗就是在人维护自身自由权利的过程得以产生,并以人所创造的文化形式得以保存和持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透过卡西尔所讲的人论得到阐述。
卡西尔在所著的《人论》里谈到,与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就是能够利用符号创造文化,这种创造的过程体现在人的劳作中。在劳作中,人不断用各样符号认知所打交道的世界,用符号对所触及的世界加以命名,使物质的世界成为负载意义的符号世界。卡西尔将这些过程总结为“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正是“符号活动”构成了拥有具象意义的世界,使世界具有意义和价值。由此,“符号活动”在人与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2]8。按照卡西尔的观点,民俗也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符号化自身劳作和生活中的各样习俗,并使这些习俗脱离具体的实践过程,成为人文化特性鲜明的载体。在这一过程中,参与民俗构建的每一位主体都成为积极追求的实践者,这些参与民俗构建的实践者处于共生状态中,他们共同建构着某些民俗,使这些民俗从最初的生活、劳作习俗转化为符号化的文化载体,以实践者共同拥有的文化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这方面意义来看,可以说民俗是反映人的生活、刻画人的特性的符号。透过民俗的反映和刻画,人的本性或本质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概念,也不再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而是一种功能性的体现。人的特征不再是靠经验观察能够确定的天生的能力或本能,而是在具象化的、实在化的劳作中显明。“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2]87卡西尔的这段阐述表明人是在劳作实践和文化创造中展示自我,反映的是人类活动的特征。民俗作为人类活动一个方面,同样也是人类劳作实践和文化创造的结果。虽然是以物质或习俗的形态存在,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特征,是将人生活的品性以物或习俗形态的记录,并且能够传承。如此一来,民俗中的“俗”不是目的,“俗”背后的“民”才是目的,“俗”的产生、传承都是由“民”发起的,也是围绕“民”展开的,更是为了体现“民”的特性而存在的。“民”是“俗”的实践者、参与者、继承者、传播者,“民”将“俗”带入自己的劳作和生活实践中,也在自身的劳作和实践中通过“俗”表征自己,让自己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由各种“俗”组合成的具象化的“民”,“民”与“俗”由此融合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民俗并展示在人类文化的舞台上,标示、表征着人的价值观、生存模式、生活风格等等,使人成为带着文化印记和标志的存在者,一代一代延续和发展着。
二、从关注“民”的日常生活而建立的“俗”
从民俗学词汇所包含的涵义来看,凡是与人相关的“俗”都可以被纳入民俗学的研究之中,而人的生活是丰富多样的,每一个族群都有他们自身特别的生活形式和环境。不同的生活形式和环境带给人的感受和习俗不同,由此产生的民俗也多种多样。繁多的民俗种类促使学者从不同的领域进行研究,以致于有关民俗研究的内容五花八门,纷繁复杂:有的是拜祖宗,有的是用偏方;一会儿是宴席上的吃吃喝喝、唱唱跳跳,一会儿是成年礼,一会儿是手工编织……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众多的研究对象如何相关?如何从这些研究对象中抽象出共同的特征?在研究中,学者们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尝试把民俗学研究的众多对象统一起来,让研究者可以在共同的概念之下探讨民俗的各个方面。这样,民俗学研究就从注重民俗事象转向民俗产生的生活世界。这种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其中钟敬文先生在借鉴日本民俗学的理念时就提出以“生活文化”来定位民俗学。钟先生认为对民俗之“俗”的定义和理解不应从古俗、文化遗留的历史角度来界定,而应当从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文化的角度将“俗”看作现实生活的文化传承,这对于中国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转变和实践民俗学的构建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说直接为实践民俗学指明了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就是回到人生活世界中建构民俗[3]。如此一来,民俗不再是古老的文化传统,而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展示出来,民俗中的“俗”被重新归回到人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文化之中。这样,民俗就从过往仅仅为古俗文化遗留物的理解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与人的现实生活联结在一起的实践过程。
实践民俗学将日常生活引入民俗学研究,实际上受到了哲学领域现象学认识的影响。按照现象学的开创者胡塞尔的理解,日常生活有一个基本属性就是“理所当然”(taken for granted)。他认为,日常生活就是人最基本的、最熟悉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展示着人对自身所生存的世界的最一般的理解和认知,就是常人以理所当然的心态自处和彼此相处的世界,人的各种文化就在这样的常识世界中被创造、被习俗化、被传承。显然,这样的常识世界也是民俗形成和构建的社会土壤,民俗内涵在其上被建构起来。
对于在日常生活中生存的人而言,这理所当然是正常的。由此决定了基于日常生活的民俗也是在理所当然中被建构起来,不带有任何刻意的痕迹。民俗就是人的生活,其形成之初不是为了成为“俗”而被建构,仅仅因为它是人生活的部分而被刻画、记忆和传承。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作为真实生活的承担者建构着自己的“俗”。如此一来,实践民俗学的转换不再将民俗学中的“民”置于过往的习俗中加以考察,而是将民置于每一个当下的场景中加以探讨。
实践民俗学将“民”的研究置于日常生活的语境中,这样的转向拓宽了民俗学的研究视域,同时将研究对象从探究具体的“俗”转向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关注。实践民俗学认为回到生活世界的主张意味着有关民俗学的学术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实证逻辑和知识求真的层面上,这样的层面更多地是将民俗学看作是一种知识来对待,虽然能够将民俗学带入客观性的探求之中,但是却难以反映民俗的真正来源和生活体验。所以,民俗学应该尊重自身诞生的源头,将“民”的日常生活置于探究的中心,关心普通人的欲求能力和愿望,实现实践求真。实际上中国民俗学研究者在早期的《民俗》周刊的发刊词里就提出了认识“民众的欲求”这样的口号,这其实是将“民”定位为民俗学研究的核心。这里的“民”不是皇帝、圣贤等等生活在社会高层的人物,而是广大民众,以及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在这样的学术倡导下,即便研究对象是乾隆皇帝所作的公开性文本——御制碑,实践民俗学也是将乾隆皇帝置于普通民众的语境下加以研究的。置于这一视角下的乾隆不再是居于万人之上的皇帝角色,而是以生活在旧时皇城根脚下普通的民众出现在研究者眼前,他也由此被看作是某些北京地方传说的重要搜集者与传播者,同时也是具体参与民俗学活动的一位创造者和传承人,仅此而已。如此一来,乾隆事实上是作为旧时北京城的普通居民与其他居民一起共享了某种“市民身份”,是那个特定社会时期中的一员。在构建这些民俗的实践活动中,乾隆皇帝放下他作为皇帝的至高身份,仅仅作为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参与了塑造地方性民俗和文化的活动,这样的参与实际上缩短了乾隆与民众之间身份的差异,到达了与民众之间身份认同以淡化族群与阶层差异的结果。这时候的“民”不是以特指的词汇出现在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不再看重追溯民到底是谁,这样的追溯已经失去意义,“民”只是作为普通民众的一员在一定的语境下创造着自己的俗,“使自己的俗成为人类文化长河中的一滴”[1]。
实践民俗学既然已经将人的日常生活作为研究民俗学的基本点,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切入人的生活实践?主张实践民俗学观点的刘晓春提出了“民俗性”。所谓民俗性,是以探究群体的特征为着眼点,指群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如何借用民俗化的方式认知、表象自身所生存的世界。群体参与的世界具有社会性特征,在其中形成的民俗可以被传承、记忆与认同。以民俗性概念为切入点的民俗学研究关注的是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围绕民俗形成的实践主体展开研究该学派认为,具体参与民俗形成和建构的实践者,就是“民”[1]。在日常生活实践语境中的民不再是抽象的认识主体,而是有着时代烙印和丰富生活的社会人,这样的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变化,体现为过去创造民俗的“民”可能是稳固的、同质的、单元的,而现今参与民俗实践的“民”却是流动的、异质的、多元的。“民”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改变意味着他们所创造的“俗”会有很大的差异,这根源于“民”是意向性地存在,他们有自身的自由意志,并且在所创造的“俗”中将自身的自由意志附加上去,使得“俗”是意向性地被生成,这意味着实践民俗学方法论视角下的民俗学研究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范式,而是强调“俗”形成的具体历史情境、俗如何动态地演变和发展、俗建构的过程性等等。
实践民俗学将日常生活作为其研究视域和解释框架,这意味着研究者不再将民俗看作是特殊事物,而是将民俗看作是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从人的日常生活角度理解民俗。这里的日常生活不是研究者附加的条件,而恰恰是民俗出现的具体语境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经济因素等等。这样的研究转向使得实践民俗学将民俗归为“日常”而非“特殊”。由此,民俗具备了维持传统重复性行为的特征,研究者可以基于这些重复性的“民”的行为框架探究“俗”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民俗学至此突破了仅仅考虑围绕传统观念本身的意识形态而转向探究人们如何体验、诠释、评价自身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进行某些重复性的行为进而将其形成被群体认同的俗,从而迎来民俗学新的研究视角和境遇。
三、从“俗”转向人重复性行为的民俗
作为解释民俗形成的框架,实践民俗学需要回答“为什么处于人的日常生活的‘俗’会成为民俗?”实际上,无论哪一种理论形态的民俗学,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民俗为何成为与人日常生活联系的人类文化?”既然是作为人类的文化标志而存在,民俗就如同其他人类文化一样,它一定是深深扎根于人的具体生活实践中,不仅被一代人所尊崇,而且是可以被代代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被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既扎根于过去,也显现于现在甚至是未来。这表明民俗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人类重复性的行为,既然是重复性行为,表明其中必然包含着某些作为个体的民与作为系统的民俗传统的东西,这些东西如同反馈回路一样被不断重复成为社会群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参与的俗。如此一来,参与民俗实践展示的民在每一次民俗表演和日常实践时,即便是由个体所做出的演绎、调整、创造甚至是抵抗,也会被社会群体所认可而被反馈到整体的民俗传统中,成为民俗传统演变和发展的新的因素,以此推动民俗系统的变化[4]。
民俗是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重复发生的行为,这一点是民俗学之所以被建立和传承的基础。因为民俗学被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反映人们最熟悉的日常生活体验,参与建构的人们通常以某些特殊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的生活体验会被抽象化、符号化,人们会用非生活性的夸张手法将其描绘或表演出来,甚至会赋予民俗某种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如此一来,当一项民俗被建构起来之后,通常会被人们设定在特殊的日期中用表演的方式表达出来,如同学者们所看到的,如果说民俗像一部大辞典,那每一次单独的民俗展演就是人们日常交流所说的话语。(1)Richard Bauman. Folklore,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 A Communicationgs-Centered Handbook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人们将民俗作为一种表演固然对其价值和意义的呈现起到了推动作用,有利于人们透过轰轰烈烈的表演加强对民俗的记忆和理解。但是如果单单将民俗纳入表演层面来诠释反而会遮蔽其中蕴含的实践含义和价值。原因在于立足于表演层面的民俗通常会将原本根源于民众生活的习俗消解掉,将民俗陷入“类型化”的模式之中。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80年代,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就曾尝试将民俗用“类型”加以框定并将其理解为“表演和阐释话语的指导框架”的一组文化特质”[5]48。这里的类型是指一套规则和期待。当被类型化之后,民俗就会进入特定的被“要求”的状态中,源于实践的民俗就会被引入某种框架中,被要求表演者如何在舞台上以模式化的方式加以表达。这样,置于表演理论取向的民俗研究将活生生的民俗注入了表演的成分,使其更多地关注个别情境中的景况、动态或特质,这显然是将民俗从人的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搬到被类型化的舞台上,注重民俗外在的呈现,却较少关注到那些时时刻刻都在发挥影响的民俗系统以及民俗产生的实践场景,也很少关注民俗产生过程中所发生的各样事情。而事实上,任何种类民俗的产生都是在一定的实践场景中与民众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只要与之联结的生活场景存在,民俗就会重复出现在人的各种礼仪交往、生活习俗中,即便建构民俗的生活场景发生了改变,民俗也不会就此消失,反倒会继续存留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只不过在形式和内容上会有一些改变而已。由此看来,民俗虽然可以被拿到舞台上表演,但是绝非舞台表演就能完全涵盖的。表演是带有刻意性质的,通常是一次性、暂时性的。对民俗的认识需要回到人的生活实践中来完成。基于民众生活实践的民俗最大的特点是重复性的,实践民俗学将研究重点转向就是要正本清源,引导研究者构建民俗学的实践理论模型,将如何理解日常生活中重复的作用看成民俗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这实际上是实践民俗学转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具体做法,因为人类延续了几千年的社会生活本质上就是重复的。事实上,民俗在实践的意义上将人社会生活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联结在一起,在实践层面上的民俗不再是一种被人所欣赏的艺术,不是在表演的层面上表现自身,而是在人生活的层面上体现,并且是重复地表现,以致于只要有人,有人的生活,就一定有民俗。这样,民俗就在人们的重复中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结在一起,无论是切近的过去还是遥远的过去,民俗都能将其与现代的人们联结在一起,这正是民俗特有的能力和魅力。
实践民俗学对于人们重复性行为的重视,引发了学者探讨的热情。西蒙·布朗纳(Simon Bronner)是其中极具热情的一位。他将研究视点致力于民俗学和民俗生活中的实践理论,关注流行观点如何在实践中被展开,他发现流行观点在实践中有对应的指代,通常指代那种“不假思索或习惯性的掩盖其文化意义”的行为,这里的“不假思索或习惯性”的就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重复发生的行为。西蒙·布朗纳以人们喜欢说重复性话语为例,阐述实践民俗学如何关注重复性行为的特征。比如在一些民族习俗中,人们喜欢在每个月的第一天重复“兔子”这个词,其中蕴含的是以此做法讨得好运彩头的想法。这看上去是一个想得到祝福的行为,但实际上是一种带着特殊含义的修辞,就是将此行为的表达标记为对人重复性行为的特殊修辞,给予这种特殊修辞的目的是将其与“普通的、习惯性的、世俗的”表达加以区分。借此行为显明重复是“一种揭示性的、象征性的实践,人类在文化上构筑重复以展现和创造传统感”(2)Simon J. Bronnner. The Practice of Folklore: Essays toward a Theory of Tradition. Jac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19。。民俗就是在人们一次次的重复性行为中得以形成、呈现和加强的,这些重复性行为以及与之关联的语境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实践因素乃至经济因素合力作用,促使人们将民俗归为日常而非特殊。由此,民俗学家不仅要探究传统的经验,而且要借此探究关注人们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如何维系民俗与维持传统的重复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引导传统成为一种解释性框架。通过传统,人们可以经历并阐释那些与过去相关的俗,并讨论它们如何在人们一次次的重复性行为中被建构起来,进而扎根于想象的过去、体验现今的显现并汲取今后的潜能,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实践中串联起来,成为贯穿于人类始终的文化载体[4]。
透过民俗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重复发生,构建民俗的“民”被联系在一起,以致于民俗虽然诞生于过去的传统,但是依然会流传至今,而且在不同时代的流转中。民俗不断汲取每一个时代的有益因素,从而使民俗可以始终充满活力,成为标志人类特征的文化符号。比如,建构于美国波士顿的“哥伦布日”民俗就是在不断的实践、反馈、传统和变革中持续存在和发展,以致于使原本具有排他性的民俗转变成可以接纳拉丁裔的民俗。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社会语境和话语等实践因素的变化,民俗也发生着变化,以致于该民俗既吸纳了新的人群的创造,也作出了对传统定义的重新解释,使这一古老的民俗焕发生机。重新构建话语和实践框架,并与当下社区文化土壤相结合,成为推动当下社区文化发展的文化因素,成为转化社区的潜在资源。这正是实践民俗学所要达到的目标。
四、结语
在民俗学的历史脉络中,实践民俗学起步相对较晚,其学科基础和理论还有待充实。但是实践民俗学的异军突起却给民俗学带来了新的生机,拓展了民俗学的研究视域,使原本扎根于传统的民俗不再停留于人们对过往习俗的描述和记忆。实践民俗学将民俗引入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加以分析,考察古老的民俗如何在当下的民众生活语境中展示自身,这就使民俗得以在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土壤中得到养分而持续存在。如此一来,民俗成为联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符号而长久立足于人类的生活实践中,既是传统文化的记忆,也是现代文化的标识,更是未来文化的期盼。人类的生活价值和意义透过民俗得到充分体现,以致于只要有人,只要有人的创造和文化,民俗就会一直存在延续下去。
当然,实践民俗学要想在学术领域枝繁叶茂走得更远,还需要民俗学研究者对其有持续的热情,更要有独到的眼光,不断拓展实践民俗学的问题意识,让其以独特的视角探究民俗学更为深层和深远的问题,真正将“实践”的涵义诠释出来。为此,实践民俗学的研究者需要有敢于越雷池的魄力,对固有的、“理所当然”的学术传统不断加以审视和追问,从中挖掘出可以用实践眼光加以考察的领域,真正构建以实践为核心要点的关键概念、知识谱系、话语方式。如此以来,实践民俗学才能建构自身的学术大厦,让自身在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实践民俗学在建构自身的学术基础时,还需要关注自身与传统民俗学的差异。以实证为基础的传统民俗学关注的是民俗学的“硬事实”,就是以已经成为现实的民俗事实为研究视点,而实践民俗学关注的是生成性的、开放式的民俗,这样的民俗学注重的是民俗动态的方面,是将民俗置于人活态的生活场景中加以诠释,这样一种对民俗的理解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生活语境中才能展示其中蕴涵的特殊意义。因此,实践民俗学始终是将民俗与创造民俗的人的生活场景连结在一起,这不仅是实践民俗学立足的根基,也是它始终关注的焦点。舍此,实践民俗学就无法真正体现自身的特色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