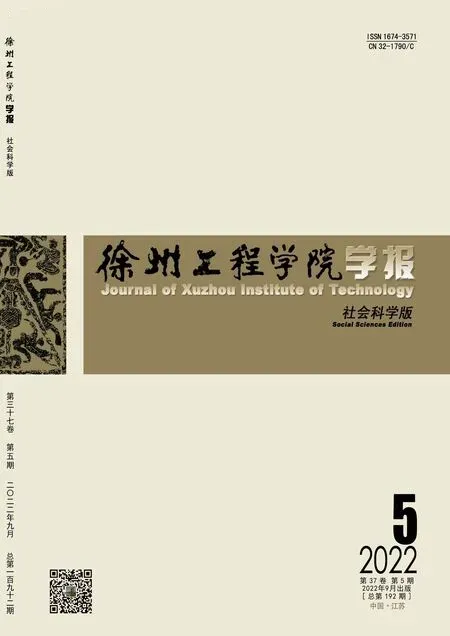视觉维度上的《朝花夕拾》
高秀川,王为生
(徐州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8)
学界对鲁迅《朝花夕拾》探讨颇多,但是鲜有从视觉维度上进行分析研究的尝试。事实上,《朝花夕拾》中大半篇什皆是以成年人的眼光捡拾儿时记忆,经由个人的独特体悟,省察出别有意味的情感悸动和历史反思,而这些“从记忆中抄出来”的篇章最大的特点即是情感与视觉化的关联,其由或真或幻的视觉化图幅的参差交错而建构出的文学景象令人印象深刻。显然,这些视觉化图幅何以建构了《朝花夕拾》文本的书写形式和思想内核,又提供了何种不同以往的体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一、视觉:鲁迅及《朝花夕拾》的另一个维度
论及鲁迅与“视觉性”的关系,学人周蕾的《视觉性、现代性与原始的激情》一文在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作者在文章中着意强调了鲁迅在“幻灯片事件”中所遭遇的所谓“震惊”,认为电影媒介的视觉力量对鲁迅的影响巨大。她认为:“鲁迅是通过了观看电影才认识到在现代世界中,‘作为一个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1]264因而,在周蕾看来,“幻灯片事件”促使鲁迅的国家意识得以萌发,也使其发觉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困境,感受到视觉的“令人嫉妒”的影响力。毋庸讳言,周蕾的文章从视觉化的角度切入鲁迅的思想动迁是颇有新意的,亦有诸多透辟的论析,但该文还是过度夸大了视觉力量对鲁迅的心理冲击,同时也弱化了鲁迅思想的承继性、渐进性。事实上,鲁迅离开仙台确乎不仅仅出于一种来自视觉层面的“震惊”,其内心世界所暗藏的情绪显然要复杂得多。日本学人藤井省三认为:“人们所说的这个‘幻灯片事件’,应该是经过漫长岁月在鲁迅心中形成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所讲述的,并非是事发当初(1905年)的回忆,而是鲁迅在回忆这一时刻(1922年末)的思考。”[2]确如其言,这样一个故事,有近20年的情感积淀和思想成长作为基础,并非一时一地的偶然触发。周蕾认为,20世纪以降,文学模式已经被“彻底媒介化”了;她还认为这种媒介化也包含着所谓“对技术化视觉的反应”。此种观点虽然有部分合理性,但周蕾还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新文学模式建构的时间线性。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媒介化”背后有着作家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发展的时代性及视觉媒介的多元性等复杂的因素,即经由视觉力量激发从而改变对文学的思考和表现的情状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譬如20世纪初相当多的乡土作家未必能有条件和热情对新媒体有所反应;而对不同区域的作家而言,京派作家与海派作家对“技术化视觉”的反应也截然不同。一如难以把沈从文和穆时英统统划归为建构“新文学模式”的“作家们”,因而把那些境遇各各不同、文化语境迥然有异的创作个体不加甄别地统合到预设的学术论断下,亦颇有削足适履之嫌。针对周蕾的一些学术论断,韩国学者全炯俊即很敏锐地指出其文中film(电影)与slide(画片)的混淆,他认为这种混淆“有可能正是她为了隐藏自己的这种不恰当性的一种策略性语法”[3]。总之,涉及鲁迅思想的议题,情形比周蕾文中所涉议题要复杂许多,其间诸多长久浸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因素并不容易把握,往往需要审慎考量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周蕾从视觉化的角度对鲁迅精神人格及文化思想的分析,展现出一种崭新的学术思路,虽然些许论述不免有所偏颇,仍然是有价值的。如果从同样的原点出发,即会发现对“幻灯片事件”有所记述的另一个文本《藤野先生》,在视觉维度上同样有着值得深入分析的空间。比较这两个文本中关于砍头场景的记述,会发现两种记述显然是有差别的。《〈呐喊〉自序》描绘了相对真实的场景,凸显出“看”与“被看”两方麻木的表情,给予更远一层的观看者鲁迅以视觉的强烈冲击。或者可以说,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想要讲述一个关于视觉化的故事,表达出那种弱国子民在当时日本政治文化语境下的震惊场面——即便这种“震惊”并不见得如同周蕾所说的那样对鲁迅的文学转向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在四年之后写就的《藤野先生》中,讲到“幻灯片事件”时,鲁迅则这样记叙:“……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4]317鲁迅把视角从幻灯片所展示的血腥场面中移开,蓦然见到教室里的情形——被砍头的示众材料、围观的国人、日本学生,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我’”!这便构成了更为复杂的“看”与“被看”的关系网络。由此可见给鲁迅带来心理冲击的不仅仅是幻灯片所展示场景本身,更有其时的空间环境所带来的重压。而谈到《藤野先生》,李欧梵也认为:“由于这是一篇回忆自己日本老师的散文,它在一个更具体化的场景中呈现了‘幻灯片事件’的始末,在《藤野先生》中,鲁迅透过这一事件建构了一个多重的‘看’与‘被看’的关系,而在这种多重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中,他表达出的体验极其深广而复杂。”[1]9李欧梵相当深入地分析了鲁迅的内心体验——不光作为一个观看者,同时还是一个被日本同学“观看”的对象,其所感受到的显然不仅仅是一种“震惊”,更有以往所未曾深刻体验到的五味杂陈的心绪。竹内好认为:“他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5]57总之,在《藤野先生》这篇回忆性的散文中,淡淡的文字所记叙的这一场景中交织着受刑者、看客、鲁迅、日本同学等多个主体的多重的视野,构成了复杂的视觉关系场。而这一场域中每个主体如何理解他所凝视的对象物,他们的麻木、兴奋、悲哀、鄙薄等种种心绪呈现出何种政治文化权利建构的秘密,这都是值得深入辨析的。事实上,“幻灯片事件”建构了一个富有政治意涵的公共空间,在这种空间中鲁迅承受了多重的刺痛,这种刺痛对其思想的转型起到了催化的效用;而寓所中藤野先生的照片却建构了一个私人的情感空间,其满蕴回忆和思念的个人凝视则在20年后继续激励着他改造国民性的努力——从视觉出发又以视觉收束的《藤野先生》多少可以说明以视觉维度对《朝花夕拾》的切入是有其合理性的。
当然,仅从《藤野先生》一篇来论证《朝花夕拾》的视觉性显然是不够的,也可以说不论是《〈呐喊〉自序》还是《藤野先生》中所提及的“幻灯片事件”,仅仅只是作为鲁迅作品视觉维度上“立人”思想建构的一个逻辑起点,一个改造国民性的发端。1907年,也就是“幻灯片事件”的次年,鲁迅写就《文化偏至论》一文,以放眼世界竞逐、叩问民族存亡的宏阔气度,把“人”的确立作为国族发展的核心要义,鼓励张扬个人精神,倡导实现个体价值——而追溯其来处,想必与“幻灯片事件”前后积郁甚久的压抑情绪不无关联。要之,《朝花夕拾》所凸显出的关于“人”的期许则集中在以人为本位的个性发展及以人情、人性为旨归的趣味张扬上。鲁迅在诸多作品中所表达出的社会历史观念和国民性塑造的理想并未在这部散文集中以严峻的形貌呈现出来,而是以或温婉、或戏谑、或嘲讽的口吻道出,甚而至于,在后记中,鲁迅以学术研究的方式,经由爬罗剔抉的考证来呼应其在往事追忆中所流露出的情怀——事实上,架构起这一切的显然还有往往为受众所忽略的视觉因素。王西彦在一篇札记里谈及对《朝花夕拾》的喜爱,他说:“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这种喜爱简直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只要一闭上眼睛,就看见长妈妈睡在床上摆成一个‘大’字的姿势,三味书屋里那位高而瘦的老先生仰起头大声朗读‘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的模样,还有那黑黑瘦瘦的戴眼镜的藤野先生向学生介绍‘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时的神情。”[6]这段印象式的评述特别强调了“看见”的阅读体验,充分体现出其对《朝花夕拾》中视觉化因素的敏感。可以说,《朝花夕拾》中种种可以“看见”的图幅虽然琳琅满目,然而并非是毫无理路的碎片,而是串接在“人的主体性”这一条线上的珍珠。鲁迅曾用文学的笔法怀想过已经消逝的故乡:“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7]502与《故乡》中那种想象性视觉化建构有所不同,《朝花夕拾》中的诸多篇什对记忆的重新体验往往基于具体而微的图幅。譬如《狗·猫·鼠》中画着“八戒招赘”“老鼠招亲”的画纸;《阿长与山海经》中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的《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中画着雷公电母、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等等;不惟如此,还有深刻在记忆中的种种视觉化场景,五猖会的盛况、百草园的景致、戏台上的活无常:从《朝花夕拾》的首篇《狗·猫·鼠》到《后记》一文都可以见到或隐或显地埋藏在字里行间中的记忆画幅,其或为令儿童印象深刻的民间图绘,或为闪烁在心灵深处的景象,所描绘大多是关于神话、民俗、生活和教化的图幅,但所关涉的却是教育、文化、国民性改造的重大议题。显然,在鲁迅这一文本的记述形式的背后,仍然还有诸多可以深入挖掘的空间存在——其对视觉化图幅的青睐、对儿童心理的描摹、对前尘往事的深情怀想,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源流,都是值得重视的。也可以说,《朝花夕拾》在不乏温情的记叙中凸显出与《狂人日记》所揭橥的“救救孩子”的主题和对礼教文化的批判的一致性是无疑义的,但应该更深入地看到其在文章中终究还是对“立人”念兹在兹的苦心。
二、读图:《朝花夕拾》中的画幅与人的主体性建构
事实上,鲁迅对人的个性、自主性及情感的充分肯定是自年轻时就抱持的一种态度,也是在各类文体创作中呈现出的思想。他曾在《破恶声论》一文中指出:“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8]即国人先得有自我意识,能够真正认识自我,发出自我的声音,做自己的主人,个人才有希望,国家乃可兴盛。鲁迅亦曾在《摩罗诗力说》中大力抨击老庄之学把国人引入脱离现实、蹈入虚无的用心,实质上即是一种对人的主体性建构的焦灼。鲁迅所期许的人的主体性建构落实在理性与情感两方面,即去伪存真,摈弃虚妄的教化与扭曲,重视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才能达成“人之所以为人”的目的。以上种种,体现在其创作上,则表现为真善美的倡导。事实上,鲁迅日本留学时期即对黑格尔的建立所谓“理性的宫殿”来供奉“诚善美”三位一体的女神之说是不无赞许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反顾《朝花夕拾》的写作,可以明显地看到其饱蕴乡愁、充满怀想的文笔之背后,并非仅仅是一种隔了久远时空的感喟,更有一份以现代意识审视传统文化、以人本思想反省道德规训的意图——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反顾与沉思,更多情况下是诉诸视觉层面的呈现及研判。《二十四孝图》一文,劈头就是“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4]258。鲁迅出人意料地沉痛掊击,剑指是古非今的名流、学者、教授,将这些颟顸卫道之流视为寇仇,其疾声厉色,未尝不令人讶异。鲁迅笔下的被诅咒者不光企图禁绝浅白易懂的白话文,甚而至于要荼毒一切有利于儿童身心发展的事物,这是鲁迅深恶痛绝的行径。他曾在文章中怀着深切的同情回忆这样的往事:“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4]259儿童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更多要通过视觉的途径,藉由图画的阅读,涵养爱美的天性,培养健全的人格,然后才有“人的主体性”得以建构的希望,可是在其时的中国这些竟成歧途禁区。在《上海的儿童》一文中,鲁迅讲到日俄德法英诸国的儿童画之各富特色,或聪明,或雄厚,或粗豪,或漂亮,或沉着,而反观中国的儿童画本,往往弥漫着衰惫的气象,难怪他痛切地觉出“中国儿童的可怜”。鲁迅认为种种施于儿童的压迫,不光来自家庭中亲权、父权,更有社会上道德威权,其中最为典型者莫过于对儿童爱美天性的戕害,以至中国儿童未及成年大都泯灭了天性,或堕入钝滞,或竟成顽劣。总之,其时的中国内以儒释道的哲学,外以伦纪道统的戒条,致力于取消人的主体性,瓦解个体的独立人格,终致国人在精神奴役中蹈入精神麻木、愚昧、无知的状态之中——这与鲁迅的“立人”思想有着根本的对立,也是《朝花夕拾》所着力批判的靶标之一。
《朝花夕拾》行文意出多端,文体驳杂,可如果细细梳理,仍然能够看出真正支起其行文桩脚的最终还是诸多意蕴复杂的图幅:这些图幅在视觉层面上大约可以划为印象式图幅和具象式图幅,前者大致都是从记忆中打捞出来的心灵幻景,而后者则是诉诸绘画的文本。譬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充满诗意地描摹了百草园的景致,显然是以充满童趣的“视觉再现之语言”呈现出满蕴生命活力的场景,更张扬儿童的天性。而在《五猖会》中,鲁迅先是特特肯定了《陶庵梦忆》所记述扮演水浒人物祈雨的盛况为“白描的活古人”,后又回忆自己亲见迎神赛会的热闹场景,以这样两幅充满欢乐气氛的图幅作为铺垫,陡然转入被父亲勒令背诵《鉴略》的场景:“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4]272鲁迅以三幅视觉化场景的对比,凸显出儿童在父权之下被压抑的天性,其用意显然不是藉由记忆重现民俗文化鲜活的一面,而是用不经意的笔墨披露出中国传统家庭所习见的压迫与扭曲。从受众角度而言,大多数读者往往并未注意到《五猖会》是在三幅视觉化场景的参差对比之中,道出压在作者心底无限的隐痛。而在鲁迅自认为:“写法较差”的《范爱农》一文,似乎在视觉层面的解读空间并不大,但事实上其在文章中还是展现给读者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肖像。1912年3月范爱农致鲁迅的信中写道:“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4]332其不无凄凉的控诉,实在是对黑暗的现实、非人的环境的一种控诉。是年7月19日收到范爱农死讯后的鲁迅,在22日挥笔写下《哀范君三章》的诗句,其中“白眼看鸡虫”的犀利笔锋直刺当时绍兴颟顸群丑,他在诗后有注解道:“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群小之大狼狈。”[9]鲁迅以“鸡虫”之谐音,暗讽中华自由党绍兴分部骨干何几仲等辈,诚为痛快淋漓,而范爱农之“白眼”的形象则在十余年后《范爱农》一文中再次呈现出来。鲁迅曾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范爱农》一文三次写到范爱农的眼睛,先是在轮船上初见范爱农,“他瞪着他多白的眼”。后是同乡会上对范爱农的印象,“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4]332。最后写到和范爱农在家乡的偶遇,“他眼睛还是那样”。鲁迅藉由这样“画眼睛”的笔法,呈现出一幅有着鲜明的特征“白眼看鸡虫”的人物肖像——此固然是一种记忆中的形象,仍然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化效果。藉由此种笔法,鲁迅在《朝花夕拾》图绘出在陈腐的礼教文化、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辗转的个体,流露出对那些备受凌虐的灵魂的同情,其用心最终还是回到人之主体性建构的议题之上。
除了前述“印象式”的图幅撑起《朝花夕拾》的行文之外,还有诸多篇章中对流传于民间的各种绘本给予深入述评,从儿童心理的角度表达出对虚伪礼教的深刻批判及对“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的所谓“下等人”的深切同情。这些流传于民间的画幅也是《朝花夕拾》中铺垫意绪的基石。在《朝花夕拾》中,《二十四孝图》当然算最为典型的视觉化文本,鲁迅通过“读图”的方式,从《二十四孝》插图中择取案例,以考据的方法呈现出中国近代孝文化如何由人之常情中出走,终至于偏执和虚伪的过程,其内核虽然延续了礼教伦纪“吃人”的判断,然笔触则更加深入地延伸到生活肌理层面,探讨到人之生趣的问题,其与鲁迅在诸多其他文章中揭批伦纪纲常、礼教道德的意旨实在是殊途同归。鲁迅认为中国的家庭早已崩溃,实则是讲维护家庭的礼教系统已经濒于瓦解,唯其无改革之方向和动力,只得一意提倡虚伪道德,才得以残喘。《二十四孝图》中的“老莱娱亲”“郭巨埋儿”及“卧冰求鲤”等教化图幅即是对这种虚伪的极致发挥,更是对人之本性的刻意扭曲。之于涵养人格、建构人的主体性而言,鲁迅认为后起的生命尤为宝贵,更有价值,因此对儿童的教育则尤为重要,而给予孩子阅读的图画如何择取至为重要。即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二十四孝图》中这种夸张孝行、一意卫道的企图,戕害人情、禁锢儿童天性的居心尤使鲁迅出离愤怒;另一方面,周遭所谓“正人君子”之流,鼓噪教化,宣扬人伦之“恩”,终至封建遗毒广为流布,延绵不绝,也是鲁迅所竭力攻击的。在鲁迅看来,纲常伦纪的压迫使国人湮灭了“爱”的天性和内心的纯净朴素,是令人痛心的。但鲁迅并未完全陷入绝望,对于回归“人的主体”仍有信心。他认为:“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7]138事实上,“纯白”之辞早就见于鲁迅十余年前作《破恶声论》一文,意指内心纯净,未受教化荼毒的元初、朴素的状态。而“纯白人”的主体一为劳作终岁的“朴素之民”,二则为儿童——在鲁迅看来,这些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由此可见鲁迅基于《二十四孝图》中的视觉化图幅所生发出的种种议论,“立人”思想仍然是其根本的源流。“鲁迅深味伪善对中国人的戕害,他一生都保持着对虚假的警惕。”[10]而其不遗余力地抨击,无非是要打破罩在国民身心之上的虚伪的礼教外壳,发掘出人的本真。《朝花夕拾》中的《无常》一文虽然信笔写来,漫谈民风民俗,却树立起奇异的无常形象,显然也是这样的用意。这篇文章对《玉历钞传》中的“活无常”画像进行了细致描摹,在行文中透露出了对于“活无常”的钟爱。鲁迅笔下的无常既愁穷落魄,又亲和有情,尤能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作出公正的裁判,“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11]。而在《后记》中尤以大篇幅进行图文并茂之考证的仍然是“死无常”的形象,他不仅在文中插入多幅北京、南京、广州、杭州、绍兴等不同地域、版本的“活无常”画像进行比较分析,考证出不同版本中“活无常”与“死有分”画像的种种差异,得出“‘活无常’和‘死有分’,合起来是人生的象征”的结论,究其用意,《后记》中的考证,既是《无常》一文的延伸,更是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挖掘。不仅如此,鲁迅甚至还亲手绘制三幅“活无常”的图像作为插图——这个奔走于阴阳两端的“脚色”最为投合鲁迅的志趣,在其貌似繁琐的“活无常”的考证背后却折射了其对于人情、人性、趣味、正义等价值观的亲近和向往,更展现出其内心关于人的主体性建构的种种期许。
三、互文:参差图文与《朝花夕拾》中的对立结构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4]235这是鲁迅1927年5月初在广州辑录《朝花夕拾》时所发的感触,而在“纷扰”与“闲静”的对峙背后则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显然,从绍兴出走,自南京而日本,自北平而厦门,最后至于广州的鲁迅,是经历了太多幻灭的鲁迅,他大约已经对这种种的纷扰有所厌倦。这样的心境下,鲁迅不光托北京的常维钧、李霁野搜集不同版本的《二十四孝图》,还在5月15日专门致信章廷谦信请他在旧书坊中搜寻不同版本的《玉历钞传》和《二十四孝图》。不难看出,其时的鲁迅多少有些藉由打捞记忆中的画幅来求得一份“闲静”的意思。也就是在这前后,鲁迅开始撰写《后记》,其间6月11日收到李霁野寄来的《二十四孝图》《百孝图》《玉历钞传》等不同绘图本书籍十余本。鲁迅在《后记》中对这些搜集来的绘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其中尤为细致地考证了《曹娥投江》在不同版本中的绘画表现。这类考证的思想根源还是在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用意则在于对历史或当下道统的虚伪性予以痛击。在对这些绘本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论孝女曹娥是“江干啼哭”还是正欲投江,亦或与其父“背对背”浮出江面的表现方式都折射出在虚伪道德的禁锢下幽微诡谲的文化心理。鲁迅不由信笔感喟:“‘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么艰难!”[4]336——在埋首故纸堆的一份“闲静”中,其仍对中国式的“虚伪”不能释怀。鲁迅在《后记》的行文中不仅插入吴友如所绘“曹娥投江寻父尸”的两幅插图,以视觉化的图幅表达传统文化中荒诞离奇的一幕,还把从不同版本书籍中亲手描下来的“戏彩娱亲”图三种加进文章之中,以不同形象老莱子的“诈跌”“为婴儿戏”之图幅来指斥血缘亲情被伦纪纲常扭曲到极端肉麻、无趣的地步。《后记》写作前后迁延两月之久——即是在这两月之内,人事纠葛繁杂,时局动荡不居,国家民族之未来晦暗难明。鲁迅内心的纷扰可以想见,即如其所言:“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12]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冲突从《朝花夕拾》文本的辑录本身就可看出。更需要指出的是《后记》一方面体现了鲁迅在视觉层面的志趣,另一方面则透露出其在困境中寻找“闲静”的心路历程和方法途径,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图文参差辉映的范本。
约翰·伯格认为:“我们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西,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13]《朝花夕拾》(含《小引》和《后记》)这一文本在视觉维度上的种种实践还隐含了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对立结构。一方面,文本内部的视觉主体藉由视觉形象确立自我的社会定位;另一方面,作家藉由视觉形象的择取确立自我的价值定位。譬如无论是二十四孝图还是“活无常”与“死有份”的视觉形象,实质上还是中国潜匿于民间的文化哲学的投影,即每一个社会个体所见到的并非仅仅是一种死亡的征兆,更通过这种形象来确认物我两者的关系,用以解释进而适应自我的处境。鲁迅在文章中讲到所谓“乡下人”对“死无常”的认知显明地透露出这一点。“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4]279最底层的民众把生之重荷负在肉体之上,却把死后的安逸寄望于阴间的公正,因而迎神赛会中最受欢迎的不是鬼王、鬼卒,而是“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的无常便可以理解了。另一方面,对于鲁迅而言,其所选择的图幅也往往隐含着自我与他者对立的思想核心,凸显出其对传统文化及现实种种的价值判断。钱理群认为:“鲁迅整个的思考,《朝花夕拾》里的回忆,始终有一个‘他者’的存在:正是这些‘绅士’,‘名教授’构成了整个作品里的巨大阴影,鲁迅在《朝花夕拾》里所要创造的‘世界’是直接与这些‘绅士’、‘名教授’的世界相抗衡的:不仅是两个外部客观世界的抗衡,更是主观精神、心理的抗衡。”[14]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从视觉维度去看这种对立似乎并不典型,但确乎存在,而鲁迅的个人性也因此得以更生动地呈现。述及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范爱农》一篇尤有可以圈点之处。报馆案中范爱农被军政府士兵用刺刀刺中大腿,身心俱痛,乃脱衣拍照,四处分送,以示地方军阀暴虐。但如鲁迅所述,因照片“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4]327。鲁迅以戏谑的口吻披露出个人的痛苦与抗争终究成为笑谈的荒谬现实。“身体是来源(herkunft)的处所,历史事件纷纷展示在身体上,它们的冲突和对抗都铭写在身体上,可以在身体上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15]这里作为视觉化的表征的身体,除了折射出自我与他者的抗争之外,也呈现出自我的精神伤痛。竹内好曾经就范爱农这一形象提出的问题:“这个让鲁迅倾注如此深情的人物是在何种条件下存在的呢?换句话说,鲁迅为什么在‘范爱农’身上看见了自己呢?”[5]31显然,之于鲁迅,这张照片即暗示着他的自我处境,渗透了其深刻惨痛的自我体验——换言之,这张照片中的“疯气”的形象,与其说是范爱农,毋宁说是鲁迅的自我镜像。鲁迅与范爱农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自我”,而他们所面对的则是强大的外部世界的“他者”。总之,《朝花夕拾》固然是追求“闲静”之作,但每一篇中都隐含着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一种对立,而从视觉层面去看,这种对立则尤能凸显出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有学者认为《朝花夕拾》熔铸了儿童和成年的两个不同的世界,“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却完满地溶合起来,化为一体”[16]。或可以说,这两个世界实则是一个有机的“自我”,而在其对面的则是充满恶意的外部世界,即“他者”——鲁迅实在是想用一种更为感性的、侧重于视觉的方式,用一种更温暖和更光明的方式去驱除巨大的“他者”的阴影罢了。
“鲁迅脚踏两只船,重提旧事并不是完全为了回到过去,而是有现实比照的动机。历史与现实互为镜子,旧事的温情折射出现实的悲哀,现实感受又激活历史的记忆,旧事与现实搅混在一起,提及旧事即想到现实,论及现实又勾连起旧时的记忆。”[17]以上种种,大概可以说明《朝花夕拾》的文本是一个异质的存在。其有追求“闲静”的企图,但是却无时不暴露出内心的“纷扰”;其有打捞记忆图幅的快意与温暖,但在文字中却透露着犀利和愤懑;其有意绪清和的情感抒发,亦有汪洋恣肆的奋勇掊击;其有儿童般纯净的视野,亦不乏思想者犀利的刀锋:这种异质涵盖文字、图像、文类等诸多方面,而在这些重重的发掘之中,就逐渐凸显出来“文本间性”的特质。总之,从外部而言,《朝花夕拾》与鲁迅其他作品当然可以形成一定的互文关系,而从其内部来说,诸篇之间亦有相当多的相互指涉,则形成一种内部的互文。如果在视觉维度上去分析《朝花夕拾》,当然可以见到其文字和图像之间跨文本的互文。就鲁迅与视觉艺术之渊源来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对鲁迅来说,视觉艺术和文学差不多具有同等意义。如果说他对这两个领域的趣味毫无联系,那倒是奇怪的事。”[18]但回到《朝花夕拾》的研究,文字与图像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久被忽略的一面,即便偶有视觉层面的解读,则大多是停留在审美层面的品鉴。而真正进入这一文本,在图文参差之中,所见并不完全是文字对图像进行意义阐释,亦不完全是图像对文字所述及的思想进行直观呈现,这两者之间的互释、映衬、增殖、对话等等才是要考量的重点,仍有深入挖掘的空间和意义。
“从重视想象力和形象的角度上看文学的时候, 视觉的东西是文学的本质性要素。”[3]《朝花夕拾》以鲜活生动的图幅,除了表达出对过往的缅怀之外,更由此生发出对传统文化、社会生活的精辟论述,其写作不仅是鲁迅对记忆中图幅的再整理,更是在视觉化维度上对其时传统文化、生活观念的一种检视和批判,而其深处所隐含的人的主体性,理想与现实、自我与他者的对立结构等具有哲学意味的议题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