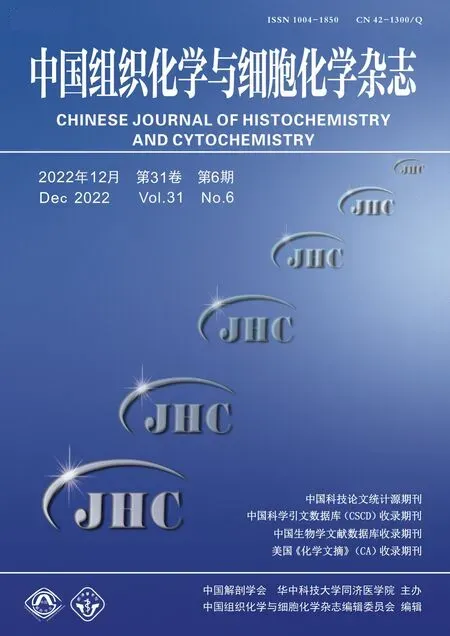NLRP3炎症体与肠道疾病
张瀚月,谷保红,高磊,蒲唯高,许钟明,陈昊*
(1兰州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2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肿瘤外科,兰州730000)
宿主通过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recognition receptors, PRRs)识别体内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DAMPs)或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s),进而诱导一系列免疫防御反应。炎症体是机体先天免疫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由PRRs、适应器蛋白与效应器共同组成,对多种“危险”产生免疫应答。Nod样受体蛋白3(Nodlike receptor protein 3, NLRP3)是一种经典的PRR,与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poptosis-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 containing a caspase-recruitment domain,ASC)、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原(pro-caspase)-1共同组成NLRP3炎症体。当受到细胞内外的刺激时,NLRP3炎症体被激活,pro-caspase-1活化为caspase-1,后者激活炎症因子白介素IL-1β和IL-18,并切割Gasdermin D(GSDMD),最终引起炎症和细胞焦亡[1]。生理情况下,NLRP3炎症体参与维持肠道内环境的稳态,当其被异常激活时,可引起或促进各种肠道疾病的发生发展,如放射性肠炎、炎症性肠病、结直肠癌等[2]。了解NLRP3炎症体的激活机制可能为明确疾病的发生机制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就NLRP3炎症体的激活机制及其在多种肠道疾病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NLRP3炎症体的激活机制
NLRP3炎症体的激活机制十分复杂,尚未完全阐明。现有研究表明,NLRP3炎症体可通过3种不同的途径被激活:NLRP3炎症体的经典激活途径、NLRP3炎症体的非经典激活途径与替代性NLRP3炎症体激活途径[3]。
1.1 NLRP3炎症体的经典激活途径
目前普遍认为NLRP3炎症体激活的经典途径需要两个信号,即启动信号和激活信号[4]。
启动信号由机体PRRs识别PAMPs与DAMPs或细胞因子受体触发,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受体、IL-1β受体[5]。目前研究表明,启动信号至少具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活化核转录因子-κB(NF-κB)通路,进而诱导 NLRP3、IL-1β 前体(pro-IL-1β)的转录。第二个功能是诱导NLRP3的翻译后修饰,包括NLRP3不同结构域中的泛素化/去泛素化、磷酸化/去磷酸化等,将NLRP3稳定在一种自动抑制的非活性但有信号能力的状态[6]。启动NLRP3炎症体后,三磷酸腺苷(ATP)、成孔毒素、病毒核糖核酸等诱导炎症体的激活信号,促进炎症体组装,响应各种外源性或内源性“危险”信号[6]。目前认为,NLRP3炎症体由多种上游信号事件激活,包括K+外流、活性氧(ROS)的产生、线粒体功能障碍、溶酶体损伤等,它们可能串联或者独立发挥作用。除少数情况下,K+外流被认为是NLRP3激活的必要步骤,K+外流能够激活炎症体,而细胞外高K+则抑制其激活[7]。线粒体和ROS在NLRP3炎症体激活中的作用仍有争议。大量研究表明,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是通过引起线粒体ROS的过量生成、线粒体DNA(mtDNA)的细胞质移位、线粒体与NLRP3炎症体共定位等事件,从而激活炎症体[8]。明矾、二氧化硅等颗粒物质被巨噬细胞吞噬后可破坏溶酶体膜,溶酶体内容物漏到细胞质内,进而引起炎症体的激活。近来有研究表明,溶酶体酸化与组织蛋白酶家族可能是激活炎症体的关键因素[9]。新的研究发现,代谢改变、嘌呤受体信号、坏死和ZBP1途径等事件也参与炎症体的激活过程[5],但详细机制尚不明确。
1.2 NLRP3炎症体的非经典激活途径
NLRP3炎症体非经典途径的激活依赖于人类的caspase-4、caspase-5和小鼠的caspase-11。由于非经典途径仅可被革兰阴性细菌而非革兰阳性细菌激活,故研究认为革兰阴性细菌细胞膜上的脂多糖(LPS)是非经典炎症体激活的关键物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LPS的保守结构脂质A与非经典炎症体激活密切相关[10]。由于caspase-11的基础表达低,故其激活需要启动信号。在巨噬细胞中,caspase-11的激活有赖于Toll样受体4(TLR4)与TRIF共同依赖的干扰素(IFN)-α/β的生成,后者同时参与提高pro-caspase-11的表达[11]。与caspase-11不同,caspase-4在人类细胞中呈高水平表达,故其激活无需启动步骤[10]。caspase-4/5/11切割GSDMD,释放其N端肽段,引起细胞孔洞形成,后者促进K+外流,进而激活NLRP3炎症体,导致炎症因子IL-1β、IL-18 的释放[12]。
1.3 替代性NLRP3炎症体激活途径
新的研究发现,在人和猪的单核细胞中,仅TLR4信号通路,无需第二激活因子的参与,就可激活caspase-1并诱导IL-1β的成熟与分泌,将其命名为替代性NLRP3炎症体激活途径[13]。与上述激活途径不同,该途径不依赖K+外流、不形成ASC斑点,也不引起细胞焦亡,是通过TLR4-TRIF-RIPK1-FADD-caspase-8途径促进NLRP3炎症体的激活[13]。但目前caspase-8介导NLRP3炎症体的激活机制仍然未知,需要更多的研究确定二者之间的联系。
2 NLRP3炎症体与肠道疾病
NLRP3炎症体在肠道免疫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量研究发现其异常表达可影响多种肠道疾病的发生发展与预后。近年来,随着对NLRP3炎症体的深入研究, NLRP3炎症体及其下游分子已成为治疗多种肠道疾病的潜在靶点[1]。
2.1 放射性肠病
放疗是治疗癌症的重要手段之一,放射引起的肠道损伤是临床常见的问题,具体机制尚不清楚。研究表明,NLRP3炎症体在放射性肠病(radiation-induced enteropathy, RIE)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接受辐射的小鼠及人小肠上皮细胞中,NLRP3、ASC、caspase-1表达上调。在敲除NLRP3基因后,RIE小鼠caspase-1、GSDMD-N蛋白表达显著降低,体重减轻、肠粘膜损伤情况均有明显改善[14]。体内实验发现,RIE小鼠血清中游离的IL-18表达上调,其拮抗剂IL-18结合蛋白(IL-18BP)表达显著降低,且这种表达与辐射引起的死亡率相关。当使用重组IL-18BP后,抑制IL-18/IFN-γ和IL-18/ROS炎症通路被抑制,肠道保护剂瓜氨酸的表达增加,器官损伤减轻,小鼠生存率相应提高[15]。上述研究提示,NLRP3炎症体及下游IL-18因子可能成为治疗RIE的潜在靶点。
2.2 炎症性肠病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种病因不明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是结直肠癌发病的高危因素。研究表明,NLRP3、IL-1β在IBD患者结肠粘膜中的表达增加,且其表达与疾病的活动度相关[16]。使用NLRP3抑制剂后,成熟的caspase-1、IL-1β蛋白水平降低,DSS诱导的小鼠体重下降、炎性细胞浸润等结肠炎情况得以明显改善[17]。目前,多项研究在IBD动物模型中研究NLRP3炎症体的作用机制。当给予NF-κB抑制剂后,DSS诱导的小鼠结肠炎症减轻,该作用与抑制NLRP3炎症体激活有关。这表明NF-κB信号通路参与调节IBD中NLRP3炎症体的激活[18]。之后的研究发现,TLR4/NF-κB信号通路通过作用NEK7的启动子区域以及调节NEK7与NLRP3的相互作用,调控NLRP3炎症体的激活,进而影响IBD的发生发展[19]。此外, ERK、Nrf2、JAK2/STAT3等多条信号通路同样参与调节NLRP3炎症体,并且通过调节上述通路,可能保护动物免受IBD的影响[20,21]。我国传统中药在IBD治疗中显示出了巨大潜能。研究发现,中药广藿香活性成分广藿香醇(PA),可通过乳铁蛋白修饰脂质体系统靶向运输到炎症性结肠的巨噬细胞,并通过抑制MAPK和NF-κB通路,降低NLRP3炎症体的形成与下游IL-1β的生成,进而改善结肠炎症[22]。该研究建立了一种新型靶向给药系统,为IBD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策略。同时,中药姜黄的成分姜黄素也在抑制NLRP3炎症体的激活、治疗IBD中表现出了良好的效果[23]。此外,研究发现,caspase-4/5/8/11介导的NLRP3炎症体激活同样参与IBD的发病机制[24,25]。总之,临床和动物实验均表明,NLRP3炎症体在IBD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选择性抑制NLRP3炎症体的成分或抑制其相关的炎性信号通路可能成为治疗IBD的有效策略。
2.3 结直肠癌
目前,NLRP3炎症体在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中的作用仍存在较大的争议。研究表明,NLRP3炎症体是CRC的负调节因子。当缺乏NLRP3、ASC或caspase-1表达时,偶氮甲烷和右旋糖酐硫酸钠(AOM/DSS)诱导的小鼠表现出结直肠肿瘤负担的增加[26]。大多数CRC细胞表达激活且具功能性的caspase-1/IL-18轴,有助于驱动由表达IL-18Rα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诱导的辅助性T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Th1/Tc1)反应,进而产生抗肿瘤免疫[27]。此外,Kupffer细胞中的NLRP3炎症体可通过与NK细胞协同感应致癌过程,引起FasL诱导的凋亡,进而增加杀伤CRC的活性。其中,炎症体下游的IL-18介导上述两种先天免疫细胞群之间的通信[28]。此外,IL-18被发现具有预防结直肠肿瘤形成的作用。成熟IL-18的释放,一方面增加IFN-γ的表达,从而刺激肿瘤抑制因子pSTAT1的磷酸化,另一方面刺激IL-22结合蛋白(IL-22BP)的表达,调节IL-22/ IL-22BP的比例,进而限制STAT3的磷酸化,二者共同作用抑制AOM/DSS诱导的CRC。IL-18的成熟与释放受到上游谷胱甘肽转移酶ω1 (GSTO1-1)的调节,GSTO1-1可谷胱甘肽化NEK7,进而刺激NLRP3炎症体激活,引起IL-18 的生成[29]。
然而,多项研究观察到,NLRP3炎症体在CRC中具有不利影响。临床研究发现,NLRP3是影响CRC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高水平的NLRP3与肿瘤的高TNM分期、血管侵犯、淋巴结转移、5年甚至10年低生存率相关[30]。敲除NLRP3或caspase-1基因,可降低IL-1β的分泌,显著抑制CRC细胞的转移。CRC细胞与巨噬细胞的相互作用激活巨噬细胞中的NLRP3炎症体,进而促进肿瘤细胞的迁移[31]。回顾性研究发现,IL-18在不同Dukes分期、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和远处转移下的表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IL-18表达水平越低,肿瘤复发率越低,预后越好,生存时间越长[32]。激活的IL-18能够调节CD11c+细胞中IL-22/IL-22BP轴,进而促进组织损伤与肿瘤发生[33]。上述研究提示IL-18有潜力成为CRC的预后标志物。此外,在患者CRC组织中发现,caspase-4、caspase-5在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浆细胞呈显著高表达,明显区别于正常肠组织与炎症肠组织[34]。这提示caspase-4/5介导的非经典炎症体激活通路有可能参与CRC的发病机制。
上述研究结果提示,NLRP3炎症体在CRC的发生发展与转移过程中很可能具有促癌与抑癌的双重作用,其中的转换调节机制有待更多的研究去说明。总之,靶向NLRP3炎症体及下游IL-18因子治疗CRC具有前景,但需要进一步阐明二者在CRC中的作用,从而明确治疗方案。
2.4 肠缺血再灌注损伤
肠缺血再灌注损伤(intestin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IIRI)是一种威胁生命的病理生理过程,常在阻断血液流向肠道的情况下发生。研究发现,NLRP3、caspase-1、GSDMD在肠道淤血再灌注(ischemia/reperfusion, I/R)过程中表达升高,且敲除GSDMD基因可显著恢复细胞活性。这提示,细胞焦亡是肠道I/R期间细胞死亡的主要形式之一[35]。同时,GSDMD介导的焦亡受到上游ROS/TXNIP/NLRP3轴的调节,该轴的激活促进焦亡的发生[35]。体内实验发现,自噬对I/R过程中NLRP3炎症体的激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激活自噬可抑制 NLRP3炎症体及下游IL-1β、IL-18的表达,进而改善I/R引起的肠道炎症[36]。值得注意的是,Homare等的研究指出,NLRP3、ASC、caspase-1/11、IL-1β的缺乏可延长小鼠肠I/R后的存活时间,但NLRP3或caspase-1/11缺乏不影响肠道炎症[37]。这一矛盾的具体机制还有待阐明。目前,由IIRI引起的远隔器官的损伤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如IIRI导致的急性肺损伤、肝损伤、皮质神经元死亡等。研究发现,NLRP3炎症体参与上述远隔器官的炎性损伤过程,且以NLRP3通路为靶点治疗IIRI引起的损伤具有较好效果[37-39]。
2.5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是新生儿最常见和最具破坏性的肠道疾病之一,发病率与死亡率居高不下。与健康组织相比,NLRP3、IL-1β在NEC小鼠的受损回肠组织中表达明显增高。使用NLRP3抑制剂MCC950处理后,NLRP3、caspase-1、IL-1β蛋白的表达显著降低,肠组织损伤减轻,NEC小鼠的生存率升高[40]。上述研究表明,NLRP3炎症体的激活参与NEC的发病过程。病原微生物感染是引起NEC的重要原因,其中阪崎氏肠杆菌是一种常见的机会性病原体。体内外实验发现,阪崎氏肠杆菌通过TLR4/MyD88/NF-κB信号通路促进NLRP3炎症体的激活,引起下游caspase-1表达的上调,促进IL-1β的释放和GSDMD介导的焦亡,从而引起NEC的发生[41]。给予益生菌脆弱杆菌ZY-312菌株治疗后,NLRP3炎症体激活被抑制,肠道炎症症状得以改善[42]。这提示益生菌对NEC中的先天免疫和肠道菌群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使用益生菌制剂可能成为预防NEC的新方法。综上,NLRP3炎症体和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与NEC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但其作用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因此,有待更多的研究探寻二者的联系,从而为NEC的预防与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2.6 肠易激综合征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是一种以炎症和免疫反应为特征的慢性功能性肠病,腹泻型IBS(IBS-D)是IBS最常见的亚型。IBS患者通常存在NLRP3表达紊乱、caspase-1与IL-1β表达增多的表现[43]。体内实验发现,抑制NLRP3的表达可减少炎症体激活,并下调NF-κB通路,减少炎症介质的生成,降低IBS-D的病理体征[44]。上述研究提示,NLRP3炎症体参与IBS的病理过程。此外,NLRP3炎症体及下游炎症因子IL-18还参与调节感染后IBS(PI-IBS)的内脏敏感性,下调炎症体及IL-18的表达可缓解内脏高敏感状态[43,45]。中药结肠灵汤被发现可通过上述机制改善PI-IBS大鼠的内脏敏感症状[46]。综上,NLRP3炎症体在IBS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相关研究较少,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阐明二者的关系。
2.7 急性胰腺炎诱导的肠道损伤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是胰腺的炎症性疾病,以持续性上腹痛和胰酶升高为特点,近年来发病率不断上升。在AP中,肠粘膜的结构受损,引起肠屏障功能障碍、肠通透性增加,进而导致细菌及内毒素从肠道侵入血液,引起内毒素血症、感染等严重并发症,进一步加重AP[47]。在动物模型中发现,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大鼠肠组织NLRP3、IL-1β、IL-18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当使用caspase-1抑制剂处理后,上述炎症因子表达减少,肠组织病理学改变减轻,提示NLRP3通过caspase-1途径参与SAP介导的肠道损伤[48]。之后,GSDMD介导的细胞焦亡也被发现参与到该致病过程。敲除GSDMD基因,可下调IL-1β、IL-18的表达,显著改善SAP引起的肠上皮屏障功能障碍[49]。此外,自噬可通过下调NF-κB/caspase-1/IL-1β信号通路,减轻炎症激活,进而改善SAP引起的肠、肺等多器官损伤[50]。肠道菌群失调与AP的发病密切相关。研究发现,相较于WT小鼠,NLRP3基因敲除小鼠在诱导AP时可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性。这可能是因为NLRP3基因敲除小鼠可抵抗AP诱导的肠道微生物失调,包括有益细菌的富集和致病细菌的减少,进而减轻炎症反应。同时,NLRP3基因的敲除下调NLRP3炎症体的激活,同样降低了炎症反应,保护肠道组织[50]。综上,NLRP3炎症体是AP诱导的肠道损伤中的重要调节因子,其通过调控肠道免疫和肠道菌群等影响疾病的进展。
2.8 药物引起的肠道损伤
除上述疾病外,还有多种药物可通过激活NLRP3炎症体对肠道造成损伤。化疗药物氟尿嘧啶(5-FU)主要用于癌症的治疗,但同时会诱导严重的肠道损害,而鼠李糖乳杆菌FLRH93通过下调NLRP3,减少炎症因子IL-1β、TNF-α的生成,可防止由5-FU引起的肠道损伤[51]。严重的胃肠道损伤已成为临床使用非甾体类药物(NSAIDs)的一个主要问题。Otani等[52]在动物实验中发现,NSAIDs通过上调NLRP3、caspase-1与IL-1β的表达引起小肠损伤,且秋水仙碱可通过抑制NLRP3炎症体的激活预防NSAIDs引起的肠损伤。体内外实验发现,神经毒性药物甲基苯丙胺(METH)可通过上调NF-κB的表达,促进NLRP3炎症体的激活,增加促炎因子的表达,进而引起肠道炎症,使用NLRP3抑制剂MCC950可改善上述症状[53]。
3 总结与展望
正常情况下,NLRP3炎症体参与肠道粘膜免疫应答并维持肠道稳态。当其被异常激活时,可通过炎症反应或细胞焦亡破坏肠道屏障,推动RIE、IBD、CRC等多种肠道疾病的发生发展。尽管研究证明,NLRP3炎症体激活的经典途径甚至非经典途径参与肠道疾病的发病过程,但目前炎症体的激活机制及其在各肠道疾病中的具体作用尚未明晰,仍需更多的研究进行阐明。同时,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也有助于理解肠道免疫与肠道稳态。
NLRP3炎症体为探索肠道疾病的发病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除了NLRP3炎症体本身,其上游的多条信号通路,下游的IL-1β、IL-18、GSDMD等分子均参与推动肠道疾病,且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靶向NLRP3炎症体通路将为肠道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提供新的策略。同时,设计新型给药系统可能有助于精准抑制靶点,提高药物疗效,为治疗肠道疾病提供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