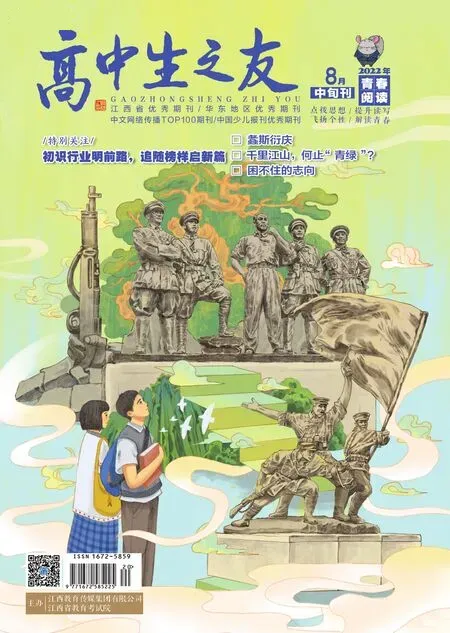虹关何处落徽墨
○石红许
在冬天,在春天……为了寻找一截久违的徽墨,我孑然一人蹀躞在虹关墨染了一样的旧弄堂里,闯进一栋又一栋装满了故事的深宅老院。我安慰自己,哪怕仅遇见寸许徽墨,也心满意足。行走在虹关,我一次又一次向墨的深处挺进,去追寻墨的身影。
婺源一文友善意地提醒我,虹关徽墨以及制作徽墨的人很难找了,你这样没有目的地寻找,白费心神,徒劳无功。我不甘心,相信在虹关一定还有人掌握了徽墨制作技艺,他们会告诉我很多关于徽墨的记忆。
欣慰的是,季节扯起的丹青屏风里,总有一棵需十余个大人合抱的千年古樟,华盖如伞。人累了,就在树下坐一坐,仰望绵延浙岭,聆听“吴楚分源”的回声。穿村而过的浙源水、徽饶古道,把琐碎的日常生活串成一幅恬谧幽静的水墨画,人在画中,画在人中。昔日贩夫走卒、野老道者的身影在徽墨涂抹的山水间渐行渐远,一丝淡淡的忧伤悄然在心里泛浮,随着雨滴从瓦片上、树叶间滚落下来,把人带进梦里故园。
虹关伫立,徽墨式微。近百年来,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书写工具,使得人们迅速地“移情别恋”。墨与砚台的耳鬓厮磨,早已被墨汁横插一杠,近年来渐渐被人遗忘。到后来,实现了从纸张到数字化的华丽转身,书写也已成为少数人的事情了。墨更是被束之高阁,制墨传习几乎无人问津。
墨,松烟的精灵,千百年来忠实地在纸上履行职责,一撇一捺站立成墨黑的姿势,氤氲香气里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徽墨,制作滥觞于南唐,兴盛于明清,享有“落纸如漆,万古存真”之美誉。听说,北京故宫博物院还保存着数十块虹关徽墨。徽墨无声,虹关有幸,虹关人因此而自豪。水口、民居,显然还有徽墨等,让虹关获得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称号。
虹关,等待着人们去擦亮这张泛着黑色光泽的名片——“徽墨名村”。在一栋民居内,我兴奋地发现,有人在挖掘、研发传统徽墨工艺,遗憾不见墨工,不知那一双手是怎样捣鼓着黑色的诗篇。不大的台面上摆放了刀、小锤、木槽、墨模等工具,还有一些不认识的物品,想必都是与徽墨有关的器皿、墨料。壁板上挂有制墨工序图《一块墨的前世今生》:点烟、和料、烘蒸、杵捣、揉搓、入模、晾墨、描金。从采取数种原料到试磨鉴定墨质,一锭墨才得以面世,具体制作起来,其工序之繁复岂是图解所能说得清楚的?想想真不容易,一锭墨,千捣万揉,浓缩的是精华,浓缩的是民族文化。
不经意间,我瞥见阁楼上站着一个白髯飘飘、仙风道骨的先生,便主动打招呼。他询问了我的来意,邀我上楼喝茶座谈。我,一个寻找徽墨的陌生人,沿着屋内与厢房连成一体的木质楼梯,漫步走上阁楼,轻轻地踏在楼板上,咿呀作响。我生怕踩醒了乾隆年间经营徽墨的原始账本,生怕踩碎了岁月的痕迹,更生怕踩破了一截遗落的留着明代指纹的徽墨。
先生姓叶,一个隐者、居士、制笔者,放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只身走进虹关,设立工作室,执刀执笔,刻刻写写画画。兴致来了,叶老师挥毫泼墨,正是徽墨磨出的浆液、芳香、光泽,正是新的徽墨传人制作出的徽墨。磨墨时,细润无声,我却听到了墨与砚台的呢喃细语。触摸着徽墨的韵律,我看到了,看到了徽磨沿着纸的纹理在翩翩起舞,入纸不晕,书写流利,浓黑光洁。真想只做一个书者,舀一瓢清清的湖水,每日轻柔磨墨,从容铺纸,蘸墨挥洒,过上一段墨落纸上荡云烟的幽静生活。
在虹关寻墨,我不为藏墨之好,只是警醒自己要时刻保持一颗对文化敬畏的心。在寻找徽墨中,我领略到徽墨走过的千年历程,也感受到浓淡相宜的虹关凸显出的古村文化。虹关,坐落在和风细雨敲开的绿茵茵的帷幔里,是徽墨润开的一首唐诗。深入其中,似穿越在一阕宋词里,时光铺陈,岁月静好。
蓦然间,发现村口一小店屋檐下旗幡招展——“有徽墨出售”,我加快脚步走去,带一截虹关徽墨,去描绘心中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