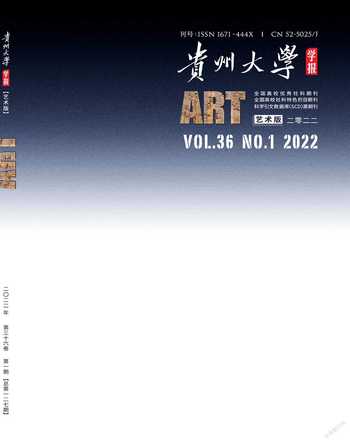未完成的“问题剧”:论小说《玉梨魂》的电影改编
黎万峡 李冀
摘要:从民初时期一味言情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到五四之后关注社会的“问题剧”,电影《玉梨魂》试图继承五四问题剧的批判精神。然而,随着不同社会问题在电影中的凸显与隐没,本就含混的问题意识在与观众的互动中消解,“问题剧”终未完成。这是双重“问题”的显现,不仅出于创作者们前后不一的批判意识,也与彼时外强中干的创作环境相关。《玉梨魂》作为典型文本体现了过渡时代的矛盾情态,也具象了“新”与“旧”的再阐释。
关键词:《玉梨魂》;小说改编电影;问题意识;鸳鸯蝴蝶派;问题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2)01-0069-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2.01.010
徐枕亚原著小说《玉梨魂》一经发行即受到时人的热烈追捧,开启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创作高潮,其后,小说几经改编搬上舞台和银幕。以这样一个广为流传又经久不衰的文本作为研究案例来观照民国历史,十分具有代表意义。从1912年小说问世,到1924年小说被改编为电影上映,期间五四运动带来的深切影响,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电影改编中,使之成为一个未完成的“问题剧”。《玉梨魂》在五四之后的重新阐释体现了新旧过渡的混沌,彰显了过渡时代的社会问题、时人的矛盾心理和早期电影创作生态,并为我们考察彼时鸳鸯蝴蝶派小说和五四问题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具象化的视角。
一、变迁:鸳鸯蝴蝶派小说到“问题剧”
小说《玉梨魂》讲述了一个悲情故事,寡妇白梨影与教书先生何梦霞两心相悦却碍于礼教不得结合,为顾全大局,梨娘将小姑筠倩指配给梦霞,不意葬送了三人的幸福,小说最后,梨娘、筠倩相继自戕而死,梦霞也殉国而死。
“情”与“礼”的冲突在小说中得到了合于时代的展现与解释。白梨影作为一名知书达礼的大家女子,时时牢记着“寡妇不能再嫁”的祖训,她极力压抑内心情感,设法为情人觅一佳偶,并以自我牺牲的方法,试图玉成情人的幸福。何梦霞作为一个满腹诗书的“忧时之士”,追求婚姻自主并大胆地爱上一位寡妇,却又从不曾逾越礼教半分,追求着一种所谓纯洁的精神恋爱,且最终服从于封建婚姻的俗礼,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因此一边是对于真挚爱情的热烈张扬,一边是对于封建礼教的默默恪守,小说没有赋予他们打破礼教的勇气,反而赞扬了他们“发乎情止乎礼”的“崇高”精神:“梨娘固非荡子妇,梦霞亦非轻薄儿,发乎情,不能不止乎礼义。”[1]
在这场“情”与“礼”的较量中,“礼”虽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正是礼教压抑下的真挚爱“情”使小说俘获了众心。在当时莺莺燕燕的文坛中,这种干净纯粹的精神恋爱与彻底无望的悲剧结局如异军突起,使人耳目一新。雖然小说传达的是情感的压抑,但是“《玉梨魂》中对情的警告几乎没有激起青年读者对浪漫情趣的强烈谴责,反而激起了他们对情及对忧郁、悲怆的迷恋,也增加了他们对类似作品的兴趣。”[2]这是因为,彼时的晚清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被程朱理学压抑多年,人们亟需情感的抒发,《玉梨魂》则正好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激发了读者们情感的觉醒:“言情小说正是国人情感觉醒在文学上的折射, 以《玉梨魂》为代表的民初言情小说正是因应了过渡时代读者阅读的心理期待而生的,是文学创作对社会的一次真实的回应。”[3]因此,“情感觉醒”一发而不可收,许多作家效仿徐枕亚,纷纷在小说中抒发自己的爱情感悟,鸳鸯蝴蝶派小说也由此再创高潮。
小说《玉梨魂》爱时人追捧主要缘于两个因素:纯洁的爱情和典雅的语言。
夏志清先生认为,《玉梨魂》代表了“中国旧文学中‘感伤——言情’传统之最终发展”,体现为“把情人无法相聚或无法结合时的消极心态——例如孤独、绝望、哀怨——予以诗化或抒情化,而当情人面临紧要关头,则他们牺牲自我的意欲及行为加以褒扬”,情人的自我牺牲实际上象征了一个“自我囿限的社会之瘫痪情状”。[4]也就是说,在描摹爱“情”时,作者刻意营构了感伤氛围和牺牲悲剧,而这种“刻意”来源于社会的不求进步情状和人们的集体无力心态。
小说通篇用文言文写就,以四、六句骈体文为主叙述故事,其中充斥着男女主人公唱和酬答的诗词,金章玉句,字字珠玑,体现了作者扎实的诗词功底与横溢的文人才情。优美典雅的语言甚至成为了小说《玉梨魂》受欢迎的首要因素。小说问世在五四以前,文言文仍是书面文学语言的主流形式,因此,华辞丽章激发了人们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书中词句一时蔚然成风,尤其被广大女学生钟爱:“为了词句的典丽,她们成段的熟读,玩味着事实,背诵着词句,甚至于友朋的书札,学校的窗课,不时的将些认为得意的词句引进去,可见其魔力之大了。”[5]
出于对爱情的迷恋和对古典诗词的喜爱,读者们仿照《玉梨魂》的诗词风格在报刊杂志中互相唱和,从小说出版的20世纪1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零零碎碎可见20余篇诗词,既有读完小说内容后自我感悟的抒发,如《读玉梨魂有感》,也有按照小说中诗词格律书写的仿作,如《读玉梨魂感赋用枕亚自题原韵》。1914年,师伶的《阅玉梨魂题以二律》表达了对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无奈和惋惜。[6]其后的诗词表达内容大多延续此类,对梨娘红颜薄命的悲痛、对筠倩追求自由反受桎梏的同情、对梦霞以身殉国的赞赏,无甚新意。如1931年天所生和邓石琴互相唱和的六首关于《玉梨魂》的七言律诗[7][8]、1914年海潮的《读玉梨魂书后》[9]、1915年一笑的《读玉梨魂六绝》[10]、1917年补拙的《文苑:读玉梨魂感赋四章》[11]和《艺文杂志》刊载的《读玉梨魂有感》[12],读者们执着于一个“情”字,既感动真情,又哀叹无情。直到1923年李蕴如的《读玉梨魂题其后》[13]、1928年王良士的《题玉梨魂书后》[14],仍然延续着对书中主人公的同情基调,他们还将自身经历投射其中与之产生了共情。与众不同的只有1925年海门丁炳若的《高阳台——阅玉梨魂有感》[15],作者不满于小说给大家带来的沉重伤感风气,奉劝读者不要过分沉溺爱情,但问题的症结仍是“爱情”。
读者们的诗词创作正是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以诗传情、以词达意、互相唱和在現实生活中的一种摹仿。他们反复吟诵小说中相爱相思的抒情场景,就是因为他们感同身受地为爱情感到哀伤。以此看来,作品传达的爱情悲剧精准地被读者接受了,共同形成了一股弥漫不断的感伤气息。但是,读者们对于小说的见解局限在爱情未能圆满的惋惜,却少了对于爱情问题的反思;沉溺于小说的悲剧、迷失于哀伤特质,却少了对于悲剧的质疑。我们应该进一步叩问: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无解局面?能不能做出相应改变,从而避免悲剧的发生?也就是说,对“情”的过分迷恋耗散了小说本身可以引申的现实问题和社会意义,即寡妇再嫁是否可能?婚姻能否自主?社会制度能否变更?读者们似乎把这些“问题”通通当作前提性的事实,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作者的安排,欠缺了怀疑精神和否定意识。正如范伯群先生所说:“徐枕亚的作品只能使读者感到‘天命不可违’,以及男女主人公的‘自误’‘误人’之类的磋叹, 压根儿听不到半点‘社会误我’‘礼教误我’的怨言。因此,象《玉梨魂》这样的哀情小说,其社会效果根本不可能使青年男女去不满封建礼教的束缚,热望去冲决‘形隔势禁’的罗网;也决不可能使青年男女引起一种争取婚姻自由的激情和共鸣。”[16]
我们知道,一个文本需要由作家和读者共同来完成,小说《玉梨魂》无论是从原作风格出发,还是从读者反应来看,始终弥漫着一股哀伤的气息,仅执着于爱情的迷恋,未激起问题意识和反抗精神,是一部典型的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然而,当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它原先的保守意义发生了转机。此时,距小说出版已有十余年变迁,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平等、自由等新思想广为播散,无论是电影本身真正实现了思想改造,还是为了刻意迎合社会思潮,改编的电影在触及社会问题上都更进了一步。
电影《玉梨魂》曾在试演时标榜:“该片注意三大主义,(一)对待寡妇主义,(二)提倡教育主义,(三)鼓舞国家主义。观众证以影片始恍然对待寡妇原来如此。”[17]寡妇问题、教育问题和国家问题,都是当时社会上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改编者希望通过电影的上映引发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寡妇问题”,电影果然引起了部分观众对于“寡妇能否再嫁”问题的重新思考。冰心即认为:“此剧为一问题剧,问题即为‘寡妇是否可以(可以二字,是一种可能性,阅者请不误解。)再嫁?’这个问题,非旧礼教的忠臣孝子,多承认有可能性了。此片虽没有直接说出‘寡妇再嫁之可能’,但在寡妇不得再醮惨状的描写内,及旧礼教的吃人力量的暗示内,已把‘寡妇不得再醮’的恶制度攻击,简接的提倡与鼓吹‘寡妇再嫁’的可能了。此种主义,合于新伦理,合于新潮流,合于人道的。”[18]也就是说,电影蕴含的问题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批判了旧制度,间接提倡了新思想,弥补了小说未能完成的批判任务,升华了小说的现代意蕴。
相较于小说这种旧的传播形式,新传媒艺术——电影在当时更加具有前卫性,更适宜于传播新思想与教育社会。所以,从小说本身与读者诗词的一味感伤言情,到改编电影升华至社会问题的探讨,鸳鸯蝴蝶派小说转化成了“问题剧”,它提出问题、暴露问题,并期待问题的解决。
二、改写:“问题”的凸显、隐没与消解
小说改编电影不是照搬,而是从原著出发的再创作。电影《玉梨魂》基本上遵循了原作的人物性格和情节结构,但却颠覆了小说的悲剧结局。故事发展到梨娘死后,筠倩感念她的深情,带着鹏郎亲赴战场探访梦霞,此时一人感其护孤之忠,一人感其爱国之热,于是名义上的夫妻从此相亲相爱。[19]沿着“问题”出发,我们试对电影中呈现的社会问题逐一分析。
首先,关于教育问题。电影花了足够多的笔墨讲述了同乡中富家三子的教育故事,这是小说中没有的情节。长子大元“其蠢如牛”,二元、三元“爱弄狡狯”,他们都在家中接受家塾教育,教学老师是一个“头脑冬烘之老学究”,极其古板迂腐。在二元、三元的无理取闹中,“老学究”终于愤而离去,三人得以进入当地的石湖小学接受公共教育。在这种学校教育的影响下,三人性情大变,竟从“蠢牛”“幼稚”“狡狯”至“有志上进”,后来更是义无反顾地参军。以此,在人物性格前与后的强烈对比中,电影突出了学校教育感化人、塑造人的重要性。但电影几乎没有叙述人物转变的过程,显得过于理想化。
其次是爱国问题。全片在渲染爱国问题上尤为突出。石湖小学的校长石痴本来就是一位军人,在民族危难之际,他毅然解散小学“为国长征”,在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的感召之下,不仅何梦霞被激励,“决意投笔从戎”,筠倩也极力赞许丈夫的决定,就连被称为“蠢牛”的方大元亦被“爱国思想所冲动”,自告奋勇去从征。大家同仇敌忾的状态呼应了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人群的共同卫国决心。有趣的是,为了不涉政治让影片顺利上映,电影将原作中的“武昌战役”改为了“蒙古战役”,前者是政治革命,后者是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显然更有助于获得大家的共鸣。
电影中的教育问题和爱国问题是息息相关的,教育就是一种爱国教育,普及教育不仅能提升国民素质,还能保家卫国。对应现实,这两方面都为彼时内忧外患的中国急切所需。电影中凸显的教育和爱国问题的确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尹民认为,以提倡爱国剧闻名的郑正秋先生在改编《玉梨魂》时的用意是十分深远的,他通过电影中的生动事例表达了普及教育的思想:“方大元的粗蠢,因为受了教育,竟然能够舍身爱国,效力疆场。这种地方,最能够引起一班热心的青年,发生普及教育的观念,对于目下的中国现状,真是对症良药,有功于世道人心不少。”[20]35但是,电影凸显的这两个问题与其说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批判,不如说是对当时潮流的刻意迎合,为满足观众需求或审查要求,“问题”不是改头换面就是草草了事,最后没有获得大部分观众的热烈响应。
其实,教育问题和爱国问题都不是原作主题,作为以言情著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原作的“情”“礼”冲突至多能与寡妇问题沾边。但电影在凸显教育和爱国问题的同时,却对寡妇问题展现得十分含糊。首先,关于梨娘和梦霞两人的恋爱,小说从“诗媒”到“芳讯”,从“赠兰”到“题影”,细腻地刻画了两人在传诗过程中由相怜、相知到相恋的情感变化,电影本事仅仅以一句“从此道名交谈,渐渐相怜相爱,久而久之,缘成不解”[19],一笔带过了两人的恋爱经过。其次,电影增加了梨娘“深夜弃家,欲投河自尽,因鹏郎惊觉,追寻阿母”[19]的情节,意在强调梨娘与鹏郎之间的母子深情。但这种不忠实原作、强行曲折故事的做法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因此遭到了观众的诘责:“恐天下没有这种聪明孩儿,事实上有点不合。”[20]电影还增加了筠倩的感情线索,她先被小学教员李生求婚,后又被媒婆介绍给方大元,一波三折,最后终于勉强和梦霞成婚,这些情节使筠倩这个人物得到了突出。
也就是说,相对于小说,电影着重刻画的主角、叙事结构和表达主题均有所转移:电影不再以梨娘为中心来叙述故事,而是前半段以梨娘与梦霞的故事为主,后半段以筠倩和梦霞的故事为主;电影省去了梨娘的心理活动过程,抑制了观众与人物的深层次共鸣;电影还美化了梨娘之死,她的遗书促成了筠倩和梦霞的相爱,故事终得圆满。由此,电影从小说的“寡妇”故事演变成了一个“恋爱”故事。筠倩和梦霞“至亲至爱”的结局替换了原作的悲惨结局,削弱了人们对寡妇境遇的同情,也消解了人们的感动与讨论空间,因此,除了前文提到的冰心以外,电影没有引起大部分观众对现实生活中寡妇问题的反思。我们可以说,在编剧倡导的三个问题中,寡妇问题让位给了爱国与教育问题。
而且,比起这些隐晦的“社会问题”,人们更关注电影当中其它肉眼可见的表面现象,如人物的表演、化装、背景的布置等,批评标准则是“合理”或“不合理”。如尹民在分析电影《玉梨魂》的佳处时,依次分析了电影的光线、背景、穿插和用意这四个方面,认为其中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蒙古战地拍得太不相像。[20]35苦生分析了《玉梨魂》的选角,认为饰演梨娘的王汉伦女士“表情细腻,哀艳动人”,饰演崔翁的演员也“表现得很切贴”,而饰演何梦霞的演員“面目凶险”“举动粗暴”“毫无半点深情”“画虎不成反类狗”,饰演英文教员李某的演员“举止浮荡,近于拆白,似欠稳妥”。[20]33-34情节方面,观众认为电影的情节有许多“穿帮”之处,如“公园中之游人疾走,行步匆匆,绝不类徜徉游园者,……蒙军太少,寥寥十数骑,自始至终皆见是此十数人”[21],“郎于母死后,未御孝,此又一疑点”[22]。总而言之,观众们更关注的是故事的“演绎”效果是否贴近现实生活和日常情理,这体现了早期电影观众对电影的基本认知,即对电影复制现实功能的重视。
与之相对的是原故事文本的缺席,梨娘、梦霞、筠倩的悲惨身世没有博得大家足够的同情,原作的“感伤——言情”特质也不为观众重视,这些都是以前小说读者的主要聚焦点。以此来看,这不是一次好的改编,“‘改编’之本质, 乃是一种文化的接续, 一种内在气质、蕴含和风采的生生不息的延宕, 原生的小说场景和后置的电影镜头一旦接驳, 潜藏于两者中的丰富蕴含, 会电火花般散射出来, 强烈地触动广大观众的心灵和情感”[23],这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不仅没有接续原作的内在气质和韵味,也没有散射出潜藏于两者中的问题意识,自然无法强烈地触动观众的现实反思。所以有时人说电影《玉梨魂》“空之议,则甚佳,谓其表演徐枕亚之说部,则余所不敢取也”[24]。
总而言之,在这个鸳鸯蝴蝶派小说改编电影的过程中,虽然曾标榜“三大主义”,体现了电影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但最终呈现的电影在突出社会共识问题的同时掩饰了社会敏感问题,导致电影情节流于理想化与圆满化,冲淡了原作的感伤特质和悲剧氛围;接着,在由早期电影观众完成的文本中,以“现实演绎效果”为主要批评标准,消解了电影的问题意识,弱化了最终的批判力度。
三、自反:双重“问题”的暴露与妥协
电影《玉梨魂》在改编过程中体现出的“问题意识”显然是受到了五四问题剧的影响。“问题剧”是以探讨社会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戏剧,五四时期,在以易卜生《玩偶之家》为代表的欧洲戏剧的影响下,中国剧坛兴起了问题剧的创作,它们具有着高度的怀疑精神,关注社会现实、暴露社会问题、主张社会变革,成为了五四运动的旗手。
虽然“问题剧”本指戏剧,但民国时期“影”“戏”不分,不仅电影可以称作“剧”,而且电影的许多技巧手法也都是从戏剧当中借鉴的。“问题剧”的核心理念是“问题意识”,是创作者对社会现存问题的关注。当时,在新剧家的带领下,“问题意识”的创作理念融入到了电影创作当中。郑君里在《中国现代电影史略》中写道:“许多新剧家,如郑正秋、夏天人、夏月润等参加了这运动,他们从这些剧本里接受了新的思想,学习了新的作剧手法,这些社会问题剧的影响经过了一些进步的新剧家的手里带到了土著电影里去。”[25]周安华教授认为,“问题剧”不仅仅是指戏剧风范,更是一种文化方式:“中国问题戏剧不光创造了一种戏剧风范,而且开启了一种文化方式,即:怀疑、认知、否定、启迪以及在怀疑、认知、否定、启迪中建构健康的华夏文明的方式。”[26]因此,电影《玉梨魂》不仅是郑正秋借鉴“问题剧”手法创作的“问题电影”,更是在此种文化方式的影响下多方合力的产物。但正如李道新教授所说:“由于各种原因,欧、美、日等国‘近代剧’与易卜生戏剧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与其说是强烈的现实批判,不如说是温婉的社会改良。”[27]由于原著小说、创作环境的限制,以及个人的思想矛盾等种种因素,电影的“问题意识”未能贯彻始终。
首先,关于小说原作者徐枕亚,他无疑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在大多数时候扮演着“封建卫道士”的角色。但他也曾体现出自身的进步思想,大胆写出《玉梨魂》这个寡妇恋爱的故事,还在小说中支持反清民族革命。徐枕亚在写作初期曾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小说之势力,最足以普及于社会,小说之思想,最足以感动夫人心。”[28]这体现了他社会问题意识的萌芽,但还来不及贯彻,他又立马否定了这种问题意识:“有口不谈家国,寄情只在风花”[29],收敛为鸳鸯蝴蝶派的“消闲”追求。其实,小说《玉梨魂》的故事来自徐枕亚的亲身经历,他曾爱上一位寡妇,并且逾越了礼教,但最后还是与寡妇的侄女走入了传统的封建婚姻。所以《玉梨魂》这个虚构的故事充满了真实的色彩,给我们增添了历史的况味:它不是无意中与社会现实问题切合,而是徐枕亚有意对自己人生经历进行的一次重述和修正。在小说中,他不仅美化了恋爱故事和恋爱双方,还掩盖了自己逾越礼教的行为:“情皆轨于正,语不涉于邪。”[1]84由此,其自述、其经历都体现了其人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徐枕亚一方面为了保存自身名节,一方面为了适应读者需求和市场审查,内与外的双重压力使小说既对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暴露,又最终对其采取了妥协的姿态。
即使徐枕亚的小说还不是一部“问题小说”,但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新文学家的鼓吹之中,小说的“问题意识”已经昭然若揭。早在1919年,周作人就注意到了小说中的问题意识:“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30]周作人对《玉梨魂》的评论说明,当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与新文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玉梨魂》不是只有“感伤——言情”和守旧,我们可以从中发掘出问题性和社会性。栾梅健教授认为,小说《玉梨魂》既非传统也非现代,而是一个“近代性的典型文本”,体现了彼时新旧杂糅、古今共存的时代特征。[31]
其次,如果说徐枕亚的问题意识还只是一种萌芽,并且很快被自己否定,电影改编者郑正秋的问题意识则更加明确。郑正秋始终提倡“戏剧必须有主义”,“我之作剧,什九为社会教育耳”,即“指摘人事中之一部分,而使观者觉悟其事之错误焉”。[32]郑正秋是一位戏影双栖的创作者。早在1914年,郑正秋就与张石川合导了电影《难夫难妻》,《难夫难妻》即关注封建婚姻的问题,被他自己称为“社会讽刺剧”[33]。之后,郑正秋带着出演电影的这班文明戏演员改做新剧。在新剧实践中,他高举“社会教育”的大旗,于1919年编演了戏剧《新青年》——这个剧名即昭示了五四运动予以他的影响,该戏旨在批判封建婚姻制度、提倡妇女解放,并奠定了他之后的电影基调。他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电影尤其关注妇女问题,如《玉梨魂》《上海一妇人》《盲孤女》等。20世纪30年代,面临国难,郑正秋直接提出电影应提倡“三反主义”,即在电影中包含反帝、反封、反资的思想。因此,郑正秋的电影在各个时期暴露不同的社会问题,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社会问题片”。
20世纪20年代初期,正是国产影片初兴之时,因为“外国人表现中国人,不是污蔑的,就是隔膜的,……我们既看到中国影戏非做不可,我们所以创办这个明星公司来实行创作的。”[34]在外国影片的激发中,最初几年,只要是“国产”的牌子就保证了受众,一是因为很多智识低下的市民看不懂外国影片,二是因为国人们生发了爱国的情怀,还因为国产影片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郑正秋关注社会问题的同时有着鲜明的观众意识,他在创作电影时十分注重迎合观众的欣赏趣味:“唯我则以为其权大半操自观众,编剧者往往因观众之倾向,以变更其原有之主张焉。……为营业计,又不能不迎合观众心理。”[32]再加上郑正秋的合作者张石川是一位典型的“电影商人”,他作为公司创办者,在制作电影的时候不得不以利益优先。两相妥协下,“营业主义加上一点儿良心”成为他们一贯的创作主张:“我们认为在贸利当中,可以凭着良心上的主张,加一点改良社会提高道德的力量在影片里。”[35]于是,本着“营业+良心”的创作主张,既为了谋利,也为了爱国,明星影片公司艰难地开辟了国产电影的摄制之路,在《孤儿救祖记》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他们趁热打铁,拍摄了《玉梨魂》。
然而,电影的拍摄过程也是一次极大的挑战。首先,《玉梨魂》是以诗词动人,小说情节比较简单,与电影的叙事体量不相匹配,改编之前,很多人都担心难以够到电影时长。但是小说实在太流行,明星影片公司为了获取利润,还是强行将它搬上了银幕。而且,为了抢夺读者群,明星影片公司在极短的时间内赶工完成:“今日我国之电影起涌之势,诚可乐观,然以之为投机事业,则不失败也,几希耳,闻明星于此片,系加工赶快,以供需要而捷足先登,为时不过二三月。”[36]实际上,赶工不仅是为了抢占先机,还由于设备的简陋和成本的限制。《玉梨魂》的主演王汉伦女士回忆说,《孤儿救祖记》采用日光拍摄,它的成功让明星影片公司升级了拍摄设备,购置了煤气灯,老板张石川为节约成本只好强迫演员们夜以继日地进行拍摄,只花了两个月便拍摄完毕,后又在拍摄下一部电影时添置了水银灯。[37]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如此快节奏的摄制不可避免使电影的最终效果显得“着急”。百郁贺良对电影进行了细节分析,指出众多可疑之处,如“开幕何梦霞别母,表情稍急”,“车站迓迎,石痴少欠自然”,“隔窗握语情理稍逊”,“途中姿态太失自然”,“梦霞迁入,即观梨花,亦似太忙”,“梦霞出而叹花,亦极匆遽”,“拾花后之步行,仍系太忙”……总而言之,全片的最大缺点是“匆遽过甚”。[20]36-38前文也提到观众们发现了电影选角的不妥和细节的粗陋。因此,既为了利润抢占读者市场,又受限于筚路蓝缕的生产环境,《玉梨魂》影片最终显得“粗制滥造”。
由此可见,“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电影文本之内,也存在于电影文本之外。虽然在五四问题剧的影响下,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问题意识”得到了发掘,但无论是原作者徐枕亚,还是电影编剧郑正秋、导演张石川,他们自身具备的“问题意识”就是暧昧不明甚至前后矛盾的;并且,他们希求暴露社会问题的同时也暴露了电影创作本身的种种问题,在早期兴盛的电影市场和艰难的生产环境之下,隐隐约约的“问题意识”在“匆遽过甚”的拍摄中殆无孑遗。
结语
从1912年小说出版到1924年小说改编为电影,中间隔着一个五四运动,电影打上了问题剧的烙印,但这个烙印显然是不深刻的。如果说,小说与读者诗词共通的一味感伤气氛象征了民初社会的集体瘫痪心态,五四之后,改编电影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则体现了五四运动使人们的批判意识得以觉醒。然而,电影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机器,也是一种受制于时代环境的商品。既源于小说原作者和电影从业者未能从一而终的批判意识,又掣肘于表面生机蓬勃、实则步履维艰的创作生态,“问题”在凸显的同时悄悄隐没,暴露之后又立马妥协,鸳鸯蝴蝶派小说《玉梨魂》没有走完它的“问题剧”改造之路——新与旧、现代与传统、革命与改良在这次小说改编电影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同时我们看到,彼时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五四问题剧的界限不是涇渭分明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也可以被时人发现“问题”,鸳鸯蝴蝶派电影也可以被时人认为是“问题剧”。章培恒先生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界,小说《玉梨魂》是在传统的形式当中蕴含了现代的内容:“如果我们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在内容上,实际上像《玉梨魂》这样的小说和许多现代小说是相通的。”[38]这也为我们重新审视民国时期“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关系提供一个契机。
参考文献:
[1]徐枕亚.玉梨魂 血鸿泪史[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56.
[2]E.Perry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50.
[3]李宗刚.《玉梨魂》:爱情悲剧和人生哲理的诗化表现[J].文艺争鸣,2010(21):67-73.
[4]夏志清.《玉梨魂》新论[M]//唐克勤,李珊.近代小说学术档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215-253.
[5]齐世铭.虚成佳话《玉梨魂》[J].妇女家庭,1939,1(02):23-24.
[6]师伶.阅玉梨魂题以二律[J].江东杂志,1914(01).
[7]天所生.读玉梨魂[J].师亮随刊,1931(04).
[8]邓石琴.读玉梨魂[J].师亮随刊,1931(112-114).
[9]海潮.读玉梨魂书后[J].小说丛报,1914(03).
[10]一笑.读玉梨魂六绝[J].文友社杂志,1915(10).
[11]补拙.读玉梨魂感赋四章[J].文友社杂志,1917(01).
[12]佚名.读玉梨魂有感[J].艺文杂志,1917(01).
[13]李蕴如.读玉梨魂题其后[N].先施乐园日报,1923-11-27(0002).
[14]王良士.题玉梨魂书后[J].学生杂志,1928,15(03).
[15]海门丁炳若.高阳台——阅玉梨魂有感[J].崇善月报,1925(16):18.
[16]范伯群.论早期鸳鸯蝴蝶派代表作——《玉梨魂》[J].文学遗产,1983(02):118-125.
[17]风蝶.昨日夏令配克试演玉梨魂[N].时报,1924-05-09.
[18]冰心.《玉梨魂》之评论观[J].电影杂志(上海),1924(02).
[19]郑正秋.玉梨魂本事[J].电影杂志(上海),1924(01).
[20]陈多绯.中国电影文献史料选编(电影评论卷 1921-1949)[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
[21]明新.评明星新片《玉梨魂》[N].时报,1924-05-16.
[22]赵再廉.评《玉梨魂》影片[N].民国日报,1924-05-29.
[23]周安华.新视觉力量:突显的当代性意蕴——小说的银幕化再造刍议[J].文艺争鸣,2018(10):145-147.
[24]游子.观《大义灭亲》与《玉梨魂》两片之平议[N].大公报,1924-05-30.
[25]郑君里.中国现代电影史略[M]//李朴园,等.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35.
[26]周安华.20世纪中国问题剧的艺术审视[J].戏剧艺术,2000(06):33-40.
[27]李道新.电影启蒙与启蒙电影——郑正秋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涵义[J].当代电影,2002(02).
[28]徐枕亚.振亚浪墨·答友书论小说之益[M]//陈伯海,袁进.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19.
[29]徐枕亚.发刊词[J].小说丛报,1914(01).
[30]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N].每周评论,1919-02-02.
[31]栾梅健.相思寸寸灰——再论《玉梨魂》的文学史属性[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08):146-157.
[32]郑正秋.我所希望于观众者[J].明星特刊,1925(03).
[33]郑正秋.自我导演以来[J].明星半月刊,1935,1(01):12-17.
[34]郑正秋.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M]//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无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220-222.
[35]郑正秋.请为中国影戏留余地[J].明星特刊,1925(01).
[36]舒廷浩.影片批评·玉梨魂之我觀[N].时报,1924-05-12.
[37]王汉伦.我的从影经过[J].中国电影,1956(S2):59-63.
[38]章培恒.传统与现代:且说《玉梨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02).
收稿日期:2021-10-15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现代电影文学资料发掘、整理与资源库建设”(项目编号:18ZDA262)。
作者简介:黎万峡,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电影文学。
李冀,文学博士,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影视艺术理论、影视批评。
An Unfinished “Problem Play”: on the Film Adaptation of the Novel Yu-li-hun
LI Wanxia/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LI Ji/College of Fine Art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54, China
Abstract:From the romantic novels in the school of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problem plays” that focus on the society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film Yu-li-hun attempts to inherit the critical spirit of the problem plays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However, with the emergences and disappearances of different social problems in the film, the inherently ambiguous problem consciousness is dispelled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audience, and the “problem play” remains unfinished.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twin “problems”, which is not only out of the creators’ inconsistent critical consciousnes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creative environment that was externally strong but internally weak at that time. As a typical text, Yu-li-hun embodies the paradox in the transitional era, and demonstrate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and “the old” as well.
Key words:Yu-li-hun; films adapted from novels; problem consciousness; School of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roblem pl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