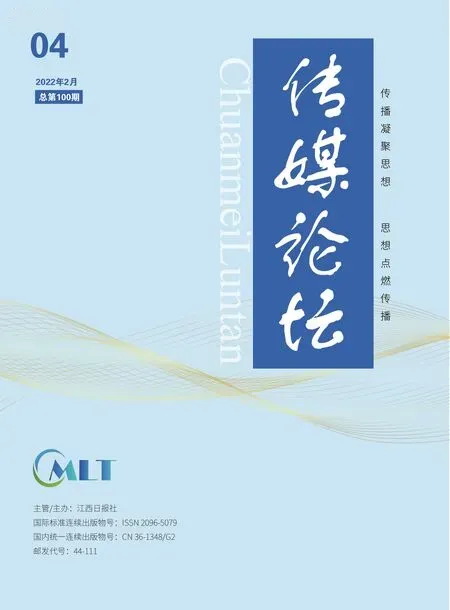从阿彼察邦看地缘文化对影视艺术的影响
贾晓萱
“所谓‘地缘文化’,是指同一空间区域内的社会群体因受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的具有共同内容和特殊特征的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系统的共同内容和特殊特征又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依托,受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1]通过地缘文化研究方法诠释具有特殊地域特色的电影,有助于拓宽电影在空间维度上的含义。本文通过对泰国著名导演阿彼察邦的作品的分析,力图寻找地缘文化与影视艺术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为阿彼察邦的影片中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符合做出充分的解读。
阿彼察邦从1994年拍摄第一部短片至今共拍摄了七部长片和二十余部短片,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地域特色。早期以实验短片为主,受美国先锋艺术的影响,其短片在形式上风格多变;从2004年的《热带疾病》开始,阿彼察邦由形式回归电影本身,开始了全面探索个人风格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影片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神秘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多种风格元素来讲述泰国本土的故事,虽在呈现中略显生硬,但其民族化创作已然可见。2010年,阿彼察邦凭借他的第六部长片《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标志着其个人影像风格已全面形成,即内容上具有泰国传统东方神秘主义哲学的色彩,形式上带有当代装置艺术的元素,通过诗意化的镜头语言来讲述阿彼察邦本人独特的审美取向。正是因为阿彼察邦自身的创作历程始终根植于泰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质,使得阿彼察邦成为当下泰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的领军人物。
一、热带景观对影片质感的影响
在地缘文化视域下,导演们都有着强烈的“恋地情节”,雪域高原之于万玛才旦,汾阳小镇之于贾樟柯,京城胡同之于冯小刚,而阿彼察邦的电影中到处充斥着潮湿、温热、虫鸣喧嚣的热带丛林,除了展示自身生存空间外,阿彼察邦赋予热带丛林更为广阔的含义。在《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中,影片从一开始就被广阔的丛林笼罩,同时在听觉上配以虫鸣和流水的声响,给观众营造一个始终身处丛林的“潜意识”。丛林意味着原始,在原始丛林中与人类的理性相对的则是人类自身基因中所蕴含的原始的动物性。影片中,波米叔叔的儿子追随鬼猴并最终化身其中的一员,在丛林中过上了原始的生活,其实是人向动物的一种回归。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传统佛教的观点则是“万物有灵,世道轮回”。人和动物的界限并不明晰,人回到丛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回归本源甚至回归自我的过程。阿彼察邦影片当中的大面积原始丛林的出现,实质上是在表达一种对城市化进程的担忧,对世界发展早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模式的一种追忆。例如在他2006年的《恋爱症候群》中,通过对乡村医院和城市医院的对比,反映出乡村地区的温暖、平和以及城市医院的紧张和严肃。影片中存在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觉感受,共同构成了阿彼察邦对于泰国现存城乡关系思考的这一大主题。或许,在阿彼察邦眼中高楼林立的城市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丛林,但在钢筋与混凝土构筑的丛林里人们所要面对的烦恼与压力要比原始的真正的丛林所面对的要多得多。在无数符合热带景观的象征符号中,只有丛林才能营造出阿彼察邦影片里贯穿始终的原始的热带质感。
二、宗教文化对影片创作的影响
各种文化形式是各地区的人适应不同自然环境的行为结果,因而在描述具有一定奇观性地域时,创作者往往偏向自然景观而忽视在这特殊地域下形成的人文景观,但阿彼察邦通过超强的想象力和实验性手法,将抽象的泰国传统东方神秘主义哲学用具体的影像镜头表达出来。泰国作为一个佛教国家,其佛教信仰早已成为民众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而万物有灵、因果报应、世道轮回等佛教教义在阿彼察邦的电影中均有展现。受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影响,阿彼察邦的影片中,没有太多对鬼魂、野兽、鬼怪等形象的修饰,而是以直给的方式,尽可能真实地描绘出在泰国民众心目中普遍的鬼魂灵兽的样子,比如在《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中,波米叔叔的妻子以鬼魂的形式出现而儿子以鬼猴的形态出现并未引起众人的恐惧,只是稍做惊讶,就转为正常的吃饭交流。这种对鬼神超然的态度正是佛教万物有灵的体现,人不仅与自然和谐共处,更能与万物和谐共生,这种人不惧鬼神的现象本质上也体现了一种人鬼神众生平等的佛教价值观。
阿彼察邦影片的宗教气息不仅是在某一部影片中有所体现,而是通过所有影片构建了一个属于阿彼察邦本人的具有强烈佛教意味的世界观体系。与贾樟柯建立的“汾阳宇宙”类似,阿彼察邦也有意的构建自己的泰国电影世界,他将佛教“轮回”的概念引入到自己的电影体系中,在不同的影片中重复出现同一个演员,同一个场景,以此来形成属于自己电影宇宙的独特印记。比如在《热带症候群》出现的瘸腿女人在《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中再次出现;其次是在多部电影的情节中建立联系,比如在《祝福》中与Orn偷情的Jim与《热带疾病》开头的死者是同一个人。这种“轮回”的概念已不再是具体到某个情节或某部影片中了,而是引入到整个人的世界观当中。世界就一个一个不断轮回不断重复的过程,而电影本身也是一种轮回。
三、自身的成长经历与政治隐喻
与贾樟柯相似,阿彼察邦自身也有一种边缘人物的游离感。贾樟柯这种游离感来自自己成长的汾阳小镇,远离城市所形成的特有的小镇青年的思维方式成为了贾樟柯电影最具地缘特色的一环。而阿彼察邦的游离感来源于自身生长在脱离主流话语权的泰国东北部的乡村,那里是泰国与老挝、柬埔寨、缅度的交界处,文化渊源上更接近老挝。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泰国共产党从东北部开始与泰国政府军开展武装斗争。为了打击东北部共产主义者的游击活动,泰国政府军开展了惨无人道“反共”“屠共”运动。这段残酷的历史对阿彼察邦留下了不可磨灭对印象,对其后期创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片有大量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政治隐喻。其目的不仅仅是保留这一段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当下泰国政治生态对反思与批判。在影片《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中,波米叔叔在临终之际讲到了自己所梦到的“来世”:他乘坐“时光机器”到达未来,却被未来的人残酷地屠杀,而他自己在这一世却是一个屠杀共产党的凶手。在屠杀与被屠杀的关系中,影片的政治隐喻意味显而易见。阿彼察邦曾在金棕榈的致谢词中讲到“献给战火中的祖国”,甚至直言“泰国是一个被黑手党控制着的暴力过度”,他影片当中经常会出现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的暴力情节,比如在《热带疾病》的第二段,肯在骑摩托的路上所遇见的暴力事件实际上所表露的是泰国的一种常态,即暴力无处不在,自由民主何存。
阿彼察邦作为一名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导演,其酷儿身份和边缘人身份也为其影片的多元解读提供了合理的依据。泰国这个自身具有矛盾属性的国家,一方面旅游市场与性别文化日益开放,另一方面军事政权和审查体系日益专制,两相对立使得人们在认知中容易出现二元对立的偏差。正如阿彼察邦本人所言:“不能越过某条线去批判会让你更想这样做,试图找到一种颠覆性的方式来观察或表达自己的生活状态。”于是视觉隐喻成为阿彼察邦的电影世界中最强有力的武器,他通过微妙的隐喻手法来质疑他的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成为了阿彼察邦电影世界中最独特的一环。
四、传统东方哲学的诗性表达
“电影都通过一个熟悉的社区来建立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这种类型的语境绝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场景……它是一种文化环境。”[2]阿彼察邦的影片充斥着自身对东方哲学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是为迎合西方审美旨趣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丑化,相反,他是将民族特性根植于独特的诗性语言之中,将极富泰国风情的宗教传统和充满东方神秘主义哲学的人文气质用客观冷静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客观不是表象上的客观,而是将泰国传统民族特质融入想象后达到的一种化抽象为具体的客观。正如阿彼察邦本人所说 “我希望我的电影能让你飘入梦境”。[3]阿彼察邦本人正是凭借自己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像造梦一样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泰国文化的别样特性。传统的东方哲学带有强烈的个人审美旨趣,摒弃西方传统的好莱坞式戏剧冲突,将叙事融入日常生活以此展现属于东方人所特有的含蓄而隐秘的情感,从台湾新电影运动大师侯孝贤开始,用长镜头表达东方人诗性的日常生活就已开始。阿彼察邦作为泰国电影运动先锋,也深受其影像,从侯孝贤的电影中寻找东方哲学的诗性表达的灵感。
安德烈·巴赞认为“长镜头使画面更具真实性,更能激发观众的思考与参与,更能表达现实的模糊性和多义性”[4],长镜头与短镜头相对,其自身具有保持时空完整的特点,在电影表达上能使故事时间与现实时间保持一致,使观众现实情绪与影片人物的情绪保持一致,将现实时空和故事时空相联系,拓宽了影片的表意空间。在影片中,波米叔叔躺在床上让艾贾帮他进行洗肾治疗,整个过程用一个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客观记录下来,此时观众的情绪实际上与艾贾相联系,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正常人,看着罹患重病的波米叔叔带有和外来人艾贾一样的怜悯和好奇。同时,大量描述自然环境的空镜头穿插其中,进一步渲染整个影片神秘、未知的质感,潮湿、温热的丛林,喧嚣虫鸣的背景音,相对原始的村庄,使得整个影片在环境上营造了一种未经现代化破坏的古早的诗意。影片中空镜头与长镜头相连,大量长时间的空镜头出现,进一步烘托了影片诗意的环境氛围,形成了阿彼察邦诗化纪实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彼察邦的影片大都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即使有简要的情节也会用零散的片段式的结构打破惯有的线性叙事,《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也不例外。影片充斥着大量梦境、前世、传说等与主线故事毫不相干的镜头,甚至相同片段重复出现,这在片段使得影片在结构上具有一种无序感。如影片开篇在丛林里出现的眼睛闪着红光的鬼猴的镜头和结尾波米叔叔看着丛林里的鬼猴的镜头相一致,除了在叙事上迎合“轮回”这一主题,更有在结构上营造一种混乱无序的诗意。
非线性叙事最大的特征就是打破和接触单一时间向度,通过时间不连贯的片段产生前后颠倒的效果,进而拓宽影片的意蕴。影片通过梦境和前世片段的插入营造了“虚与实”的二元叙事空间,但两个叙事空间在情节上并无关联,但在意蕴上却相互关联,面目丑陋的公主一步步丢弃尘世荣华的象征置身步入水中如鲶鱼交欢;和尚脱下袈裟在水中濯洗肉身,看似与主线情节毫无关联的片段一经组合便构建出跨越现实时空的虚空之妙境,进而产生比单一线性叙事更为意蕴深远的诗意效果。
阿彼察邦力图通过《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重构西方观众对东南亚历史和文明的想象,他拒绝用奇观化的手法过分向西方审美谄媚,他用一种真实的想象力传输了当下泰国真实的民族精神和社会状态。当波米叔叔在丛林深处的“子宫”里喃喃自语时,实际上也为其他人在东方哲学的诗性表达上找到了一条出路,即用本民族的语言讲述本民族的故事。如果没有,就创作出本民族的视听语言。对本民族的想象意味着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电影创作者在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前提下用想象重建叙事载体,创造能让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文化意向,真正实现东方文化和东方哲学的广泛传播。
从泰国东北部到戛纳金棕榈颁奖台,阿彼察邦自始至终都在都是在表现自己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人和事,无论是广袤的热带丛林还是当下泰国的都市生活,都是根植于本国的世界观和价值立场。用奇异和空灵神秘的视听语言讲述东方神秘主义哲学传统,展现了他对电影时空极具个性化的看法,把记忆与梦境结构重组,将当代装置艺术的思维方式引入电影视听语言当中,充分探索电影的可能性。弗洛伊德曾说,任何罪恶都将被归结为童年的阴影[5]。事实上任何创作也都离不开自身的成长的经历,导演们的“恋地情节”本质上是对自己成长过程的回溯。通过地缘文化的研究方法阐释具有地域奇观性的影视作品,对当前影视艺术风格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