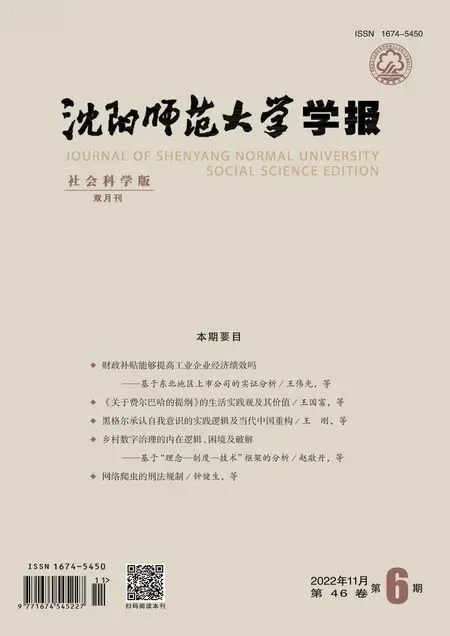《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唯物史观意蕴
于洪波,宓有睿
(沈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反映大革命期间湖南农村革命客观形势状况的党史文献,对当时党内关于农民革命斗争的非议、困惑和少知等问题作出了翔实全面和理性客观的历史性解答。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规律发现,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一切实践的指导理论,是以人本身为历史主体进而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视角。“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1]2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中恪守不变的政治原则和立党准则,是消除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和先进认知,是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堕化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意识堡垒和纯洁本源。当前,学界对《报告》的研究多在版本考察、农民观、革命观、农民运动和与其他农民运动进行比较研究等方面,以观念析出和史实考究为研究重点,而本文旨在以《报告》中的唯物史观意蕴为主要研究对象,侧重探寻唯物史观系列理论在农民运动过程中的存在场域和对革命进展的切实影响,综合分析《报告》文本对唯物史观的理论阐释和实际运用。
《报告》曾印发诸多历史版本,如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瞿秋白为其作序出版全文单行本”[2]等。本文以2008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为研究文本。该版本《报告》分为八个主要部分,围绕农民问题、农民组织、农会权力、农民革命、革命程度、革命现状、革命主体和斗争举措等方面展开阐述,深刻揭示毛泽东所实际调查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城农村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人民生存历史环境的客观实际,从而研析革命路线、权衡革命势力和把握斗争方式。《报告》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深度剖析湖南农民运动现实现状的同时蕴含了深邃的唯物史观理论,其所表现的革命理论客观地契合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理论,其所记述的革命实践彰显农民革命实践对农村社会推动发展和变革解放的唯物史观理论,以及对农民与农民运动有着本质性和规律性的理论认知。
一、《报告》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意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3]669。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到的“人们”,指的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的创造者、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和革命运动的实践者。毛泽东在《报告》中充分论述了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主体,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恪守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理论,坚持人民群众是农民运动的主体,发挥革命主体的革命力量,以广大农民群体的切身利益为斗争目标。
(一)人民群众是农民运动的创造者
《报告》一以贯之地阐述人民群众在革命实践中创造了农民运动,农民运动是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实践活动的现实产物,高度契合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理论。毛泽东在《报告》中表述“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4]13。文中的他们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人民群众。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范畴,在大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阶级范畴主要包括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和爱国军人等。其中,农民的数量在当时人民群众的历史范畴中是占比最重的。尤其是在农村,《报告》中说:“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4]20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农民身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剥削和压榨之下,受到的阶级压迫是中国各个阶级中最严酷和深重的。农民对社会革命的需要,对物质资料的需要,对生产力提高的需要,对民主权利的需要必然是中国各个阶级中最为迫切的。在中国诸多阶级和政党团体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和站在农民阶级切身利益的历史角度,并且自始至终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深刻分析农民对于社会革命、物质资料、生产力发展与民主权利的现实需要和对消灭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实践需要,而只有正确研判在农村的人民群众对农村客观物质现实的迫切需要,党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和道路决策选择中把握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和历史规律的革命实践方向。由此,毛泽东在《报告》中指明农民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4]16,首要革命对象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4]14。在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村,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以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人民群众的现实的和实践的需要,领导广大农民发动农民运动,在湖南省多地进行农村革命实践。人民群众进行的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沉重打击了封建专制势力,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推动了大革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在《报告》中郑重论述:“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4]15《报告》表明以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农民运动,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和革命成果,彰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理论。
(二)坚持人民群众在农民运动中的主体地位
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其领导的农民运动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坚持人民群众创造革命历史的唯物史观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创建了农民协会,毛泽东在《报告》中表述,“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4]13。农民协会是农民运动的实践载体和主要阵地,是有利于人民群众通过农民运动自己解放自己的组织形式。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明农村的现实情况是贫农群众占当时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贫农在农村中生存境况最为艰苦凄惨,生产生活资料占有量最低,“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4]20。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必然要吸收农村中以贫农为主的人民群众。《报告》将贫农群体根据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分为赤贫和次贫,以衡山县及其所辖乡村的农民协会成员成分为例,其中“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4]21。贫农群体在农民协会中占据了百分之九十,由此可知贫农在成员比重上是农民协会的主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发动的农民运动过程中,以贫农及贫农领袖为主的人民群众及其所属的农民协会是农村革命的实践主体。《报告》中实地考证了存在农会的湖南农村的革命实践现实状况,“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4]22。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通过具体的革命实践“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4]14,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4]14,人民群众享有了革命实践带来的物质成果——土地和物质生产资料,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自身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坚决同地主阶级和封建势力进行革命斗争,真正为实现人民群众自身的解放而革命。《报告》以诸多客观的农村现实变化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农民运动的实践主体,发动为自身解放而进行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并在取得革命实践成果的地方占有自身革命实践活动产生的物质资料,使得人民群众生产的物质资料回归于人民群众之中。历史性的农村现实变化客观地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群众在农民运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理论。
二、《报告》彰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意蕴
马克思认为,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5]14。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下,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人脑中的客观反映,社会意识从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到社会意识中形成而来,决定社会意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存在所包含的一切客观社会历史因素。《报告》具体表述了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活动,使农村社会存在发生变革而变革,客观地显现了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
(一)农村的社会存在因农民运动而变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运动通过农村革命实践,变革了湖南农村封建社会的社会存在。恩格斯指出,“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6]44。中国共产党根据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引导人民群众在农村进行全方位的革命实践,从而变革了农村中与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不相适应的社会存在。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4]15首先,人民群众的农村革命实践即农民运动变革了农村封建势力的政权结构,实现了“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4]14,使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农民协会将农村的政治权力回归到人民群众之中,并且被人民群众所掌握,为人民群众服务。其次,在人民群众获得农村政治权力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变革了农村的经济活动,如“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4]36“阻谷出境”[4]38和“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4]35。与此同时,农民运动变革了人民群众对物质资料的占有。经过农民运动后,地主土豪被农民协会所消灭,农民协会将没收的土地和生产工具重新分配给人民群众,满足广大贫农对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最后,经过农民运动的农村在生活活动方面也发生了变革。如“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4]19而被人民群众押送游乡,接受人民的批判和指责并收缴和销毁绅士所占有的鸦片枪;在农村教育方面,多地农民在农民协会的带领下大办夜校,并称之为“农民学校”[4]40。夜校的存在,满足农民对于文化的需要,切实提升了农民的文化需要和对农民运动历史认知,并且使被地主阶级垄断两千年的教育权彻底地转移和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中,为人民群众所用。《报告》中以坚实的事实和史实为现实基础,记述了在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农村现实地发生了在政权结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社会存在的深刻物质变革,种种社会存在的历史变革,现实地、历史地存在于和发生于农民运动革命实践作用过的湖南农村,并为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变革打下了物质基础。
(二)农村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因农村社会存在的变革而变革
农村的社会存在发生根本性变革后,必然决定和导致农村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从个体意识发生变革到首先贫农群体意识发生变革,再到多个群体意识受到贫农群体意识和实践的影响而逐渐变革,最后整个农村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发生彻底变革。1927年1月,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7]125-126,将农村社会存在的广泛变革的重要发现详尽地记述在《报告》中,证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农村发动农民运动,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推翻了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地位,致使农村教育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发生转移,从地主阶级的垄断转向农民所有,实现了农村的物质生活和生产活动的社会变革。当人民群众中的单个贫农个体参与农民运动的具体革命实践后,因自身实践的变化而拥有更多的生活物质资料和生产物质资料,并且单个贫农个体与地主阶级的被剥削的生产关系现实地被其自身的革命实践消灭后,存在单个贫农个体脑中的封建的落后的意识便被自身的革命实践所否定了。在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史观的引领和教育下,贫农个体的个体意识在已变革的农村社会存在和自身的革命实践的决定作用下,发生个体意识的彻底变革,从自在的存在变革为自为的存在。参与农民运动的是以贫农为主力军的人民群众,当单个贫农的个体意识发生自为性的变革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形成贫农群体意识的自为变革后,通过具体的群体革命实践对中农群体和富农群体的社会存在进行变革,使其群体意识发生变革。《报告》中描述,贫农群体对着富农群体警告:“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4]20富农群体看到“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4]19,“并且杀了大绅士”[4]19等如此现实的农村社会存在变革后,并在贫农群体的群体意识与群体实践的双重影响下,富农群体便从惶惑中加入了农民协会。而中农群体在“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4]20和“农会势力大盛”[4]20的社会存在发生时,方加入农民协会。二者的群体意识只有在农村的社会存在现实的发生变革之后和贫农群体的革命实践屡屡胜利后,才会发生群体意识的变革。当农村中的贫农群体、中农群体和富农群体的多个农民群体意识因农村的社会存在变革而发生变革后,农村中其他群体在现实的具体的农村社会存在发生变革后,其群体意识亦发生变革,正如《报告》中表述:“好些中小地主……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4]14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证了农村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因农村的社会存在的变革而变革的历史现象,这一现实的历史现象十分具体地彰显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理。
三、《报告》论证革命实践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意蕴
马克思曾强调,“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3]154。《报告》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农民运动革命实践及其革命成果,并且有理有据地论证了革命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理论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联合在农民协会之中,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并领导人民群众发动农村革命实践,进行农村政治革命实践和农村经济革命实践,将人民群众自身从地主阶级的政治枷锁和经济剥削中解放出来,对地主阶级统治下的阶级社会进行变革,实现农村阶级社会的变革发展。
(一)人民群众的农村政治革命实践推动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
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在人民群众发动的农村政治革命实践中发展的。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4]31,它们是建立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关系之上的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是地主阶级控制和压制农民的落后的政治上层建筑,必须通过政治革命实践来消除和取缔。在地主阶级统治的阶级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地主阶级政权是地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基石,对具有剥削性质的租佃关系和奴役关系提供政治庇护,是专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而存在的。毛泽东在《报告》中郑重地分析,对地主阶级政权的“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4]23。故而对地主阶级政权的斗争是摆在农民运动过程中需首要解决的现实矛盾。
《报告》中分层次具体地总结了对地主阶级政权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实践方法,其与革命实践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理论深度契合。其一,先行清算地主罪行,进而对地主实施罚款和迫使地主捐款以救贫民。这三种政治革命实践的方法重在“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4]24,使以往农村中地主阶级以其政治权力肆意惩罚人民群众的现实发生彻底变革,让人民群众惩罚剥削人民的地主阶级成为现实,由此正是农民政治地位提高的重要表现。其二,质问破坏农会声誉的地主,率领人民群众当面向地主劣绅示威,将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这三种政治斗争的方法直接地、现实地向地主展现了团结在农会组织下农民的集体力量和政治威慑。其三,将残酷剥削人民的土豪劣绅关进监狱,对畏罪潜逃土豪劣绅实施驱逐抓捕,枪毙罪大恶极的当地大土豪大劣绅。这三种政治斗争的方法是土豪地主最为恐惧的,是人民群众真正地掌握了农村政权和司法权力的现实表现。另外,在农民运动兴盛的县城中“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4]29和“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4]30。此类现象的发生和存在表明了农村政权中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不断地转移到农民协会及其各级组织之中,使得人民群众在司法处于公平地位,日常行政举措有利于农民的生产生活。其四,“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4]30,将地主阶级在县城的权力逐渐分化,由代表农民的革命民众团体掌握大部分政权,并对贪赃枉法的县政治进行彻底整顿。由此可见,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让人民群众在政治和司法上得到了应有的公平和参与的权利,甚至是决策者的地位。
《报告》详细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通过多种政治革命的实践方法,夺取地主阶级手中的政权,“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4]31。人民群众取得农村的政权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4]31。族权和神权是封建礼教社会下的农村礼治的产物,“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8]50的农村社会,“礼也可以杀人”[8]51且是可以不经过法律的允许。在农村祠堂中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是历史性的、一直存在着的。农村中土豪劣绅惯用借菩萨的名义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是生命生存权利。正因如此,《报告》多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4]32。只有在族权的破灭和神权的动摇下,夫权才能崩溃瓦解。毛泽东在《报告》中认为,“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4]32,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社会中,建立了维护自身权利的组织,从而获得了政治上的保护。《报告》所指出的上述政治革命实践的成果标志着农村的民主政治有了全方位的发展,人民群众真正地掌握了属于自身的政治权利和司法权利等,推翻了压迫人民群众的地主阶级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人民群众通过革命成为农村政权结构的主体。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维护农村社会政治权利的革命实践活动,是对唯物史观理论中革命实践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有力诠释。
(二)人民群众的农村经济革命实践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
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农民运动必须在“经济上打击地主”[4]26。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对在生产中剥削人民群众进而抢占农村的生产与生活物质资料的地主阶级进行经济革命实践,通过经济革命实践逐步消除农村中的剥削现象,将农村中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使农村中绝大部分土地和生产工具回归于农民之中,从而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最终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良性发展,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力获得应有的和足量的生产生活物质资料,昭示了唯物史观中革命实践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理论正确性。
《报告》中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4]21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4]6。之后,在《报告》中记录,在农村成员比重占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4]20-21,常常出卖自身劳动力,即便如此贫农也常常入不敷出,更有甚者乞讨为生,因此贫农只能通过借高利贷的方式来购买生命所需的物质资料,并且贫农在乡村中受到的压迫最为深重,对土地的需要最为迫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148人民群众作为现实的物质的人存在于物质世界之中,首先是要依靠生活物质资料而维持生命的存在,否则人民群众的生命便会消亡。不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物质资料问题,是无法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也是违背唯物史观理论的。
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述人民群众在诸多具体的经济革命实践中逐步消除地主阶级对自身的剥削事实。地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剥削方法以超乎常理地增加地租、增加土地押金和增加贷款利息为主,借此剥削人民群众的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财产。因此,人民群众在农会势力压过地主势力的地方坚决地进行“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4]27的经济革命实践,并且立刻得到当地农民的坚决支持。《报告》中记述:“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4]27在农民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只要交给地主的租钱和押钱少一分,那么自身便多获得一分自己的劳动成果,剩余劳动力便少一分被剥夺。虽然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这种封建生产关系——租佃关系不可能完全和直接消灭,但是农会所进行减租减押的生产关系革命的实践正在从根本上循序渐进地消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关系。《报告》记录了农民协会实行减息的经济革命实践,通过对农民与地主的旧债进行减息和不准债主逼迫农民交还本金,使农民协会盛行的“农村几无放债的事”[4]27,由此极大程度上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报告》深刻分析地主阶级通过退佃的方式来对人民群众进行变相剥削。另外,地主退佃使自身没有土地或占有极少土地的农民没有了可以出卖劳动力的途径,农民的生产力持续低下,物质生活资料固定在低水准。面对地主退佃的革命问题,《报告》记述了农民协会采用“不准退佃”[4]27的经济革命实践方法,阻止地主退佃,使人民群众的生产力得以发挥,劳动有了实践的对象即土地,由此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资料。中国共产党通过减租、减押、减息和禁止退佃等经济革命实践,极大地限制了地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剥削,保护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剩余价值,从而提高了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力,推动了阶级社会中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客观地论证了唯物史观中革命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原理。
四、结语
《报告》的诞生过程及其科学内涵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正确革命斗争道路的历史性探索,极大地推动了我党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运动、农民群体、革命对象、革命力量、同盟军和战略策略的现实认知,更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具体事宜的伟大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突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9]51本文研究《报告》中的唯物史观理论,整体而言初步明晰了文本的具体部分所蕴含和对应的唯物史观相关理论,及其理论在当时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实践效果,证实了唯物史观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实践具有科学指引和正确导向的理论功能。但本文仍有待于在其他相关党史文献的佐证下,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地探究《报告》中所蕴含的唯物史观意蕴。